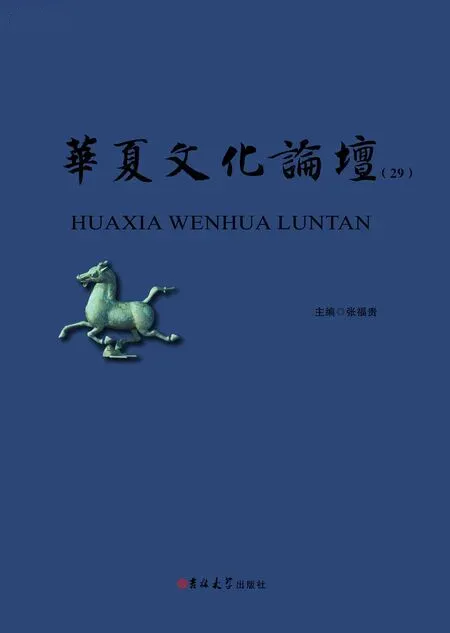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北去来辞》看林白女性成长小说创作新变
宋 瑶
【内容提要】《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分别是林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后创作的两部有关女性成长的长篇小说,两部作品内在具有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从林白与作品中人物的双线成长、主人公的漂泊流浪与自我救赎、他者包围下的主体成长、完整性的主体建构几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主体由成长“未完成”状态的迷茫转向成长完成时对理性的回归。林白也从“女性主义”的标签中挣脱出来,以“超性别”的视角去理解、建构两性关系,由最初的“私人化写作”走向个人心灵成长与民族时代变革相融合的叙事。
《一个人的战争》是林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揭示了主体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隐秘的内心世界。林白也因此被赋予了“私人化写作”“女性主义”等标签,一跃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中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林白也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无论是书写底层乡村的《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还是以回忆的视角进行写作的《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都显示了林白要突破种种标签走向社会现实的决心。其中《北去来辞》作为林白在21世纪极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将女性的个人成长史与国家社会半个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结合在一起,既承继了自己一直以来善于书写私人经验的特点,又在其中添加了新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虽然在创作时间上相隔了二十年左右,但其内在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地方。它们在人物、情节的设定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家庭背景都是父亲缺席,母女关系疏离;主人公都曾当过下乡知青,上过大学,热爱文学,性格相对孤僻;都曾逃离家庭,在都市中挣扎生存;也都曾有过多次受伤的情感经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北去来辞》仿佛是《一个人的战争》的续写,因为《一个人的战争》最后的结尾是多米为了留在北京,嫁给了一个老头,而《北去来辞》的开篇则是从海红在北京与大自己二十岁的史道良的叛逆婚姻开始写起。
多米和海红作为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部分叙事材料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成长组织而成的。虽然因为作者想要拓宽自己的写作视野而在《北去来辞》中添加了很多其他相关人物的支线发展,但是主线还是海红在结婚后的自我成长,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正如华莱士·马丁对成长小说的前身所阐释的那样,“当‘人物’本身成为变化和兴趣之所在,从而使一个多变的内心世界取代冒险故事的多变的外部世界时,叙事作品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就发生了。这个转变在教育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类小说里,成长中的磨难与寻求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都是在头脑和心灵中发生的”①[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现阶段关于《北去来辞》这部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的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现实反思的转型等等。而从成长小说的视角对《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探究林白在不同阶段对成长的认知和叙事的改变,也可以为成长小说在当下如何进行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作者与人物的双线成长
《北去来辞》在描写人物的类型上更加多样化了,除了主要人物海红,次要人物海红的母亲慕芳、乡下来的保姆银禾以及她的女儿雨喜等人物也占据了很多的篇幅。但是从人物的成长性上来说,这些次要人物的成长线并不像海红的那样清晰,性格也没有发生太大的转变。例如保姆银禾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盛的乡村女性的代表,她朴素善良也狭隘愚昧,自信好学却天真迷信。同样,她的女儿也继承了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始终怀揣着自己能够挣大钱的信念在不同的地域苦苦求生。虽然她们的性格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是这种特征却是被定型了的,缺少不断成长发展的叙事空间。这些人物毕竟与作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即使作者深入乡村收集了很多相关素材也创作了诸如《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等关于乡村底层的文学作品,作者还是无法与他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相较而言,海红这个人物则更贴近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林白在进行刻画时也更加得心应手,这也是海红取代银禾成为《北去来辞》中的灵魂人物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对两部作品进行分析时主要以多米和海红作为成长的主人公。
《一个人的战争》与《北去来辞》中涵括了女性成长的不同时间段,前者的主人公多米的经历集中于青春期、大学时光和工作后,以在北京与老头结婚为结尾。这个结尾给读者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成长主体处于成长未完成的状态。而《北去来辞》中主要书写了主人公海红婚后的经历,从结婚到离婚再到复合,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了人生轨迹的改变。林白在尾卷中写道:“下一年就是2012年,海红将满五十岁。经过这么多年纠结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终于褪尽了文艺青年的伤感、矫情、自恋与轻逸,漫长的青春期在五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终于可以结束了吧?”②林白:《北去来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48页。大多数成长小说中集中描写的是主人公的青少年时期,因为这个时间段一般是主体人生变化最剧烈并不断形塑自己的时期,但是林白并没有以传统的定义来理解一个女性的发展,而是将历经沉浮后的五十岁看作青春期的结束。延宕的青春期象征着现代社会中人的晚熟,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是迷茫的、纠结的。中国特殊的社会氛围造就了中国式的成长小说与西方的不同特点,就是“在生命起点上与西方没有太大差别,而在终点上则极其模糊,有着明显的‘成长期延长’的特色”①施占军:《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多米与海红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女性相对完整的成长历程,文中的人物比林白进行创作时的年纪略小但相差不多,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是共同成长的。林白本人就出生于广西北流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特殊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造就了林白相对孤僻敏感的个性,也让她像自己在小说中塑造的角色“多米”和“海红”一样渴望逃离自己的故乡。林白自身曾经插队两年,后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学习。她在90年代北漂京城,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这些人生历程与多米和海红何其相似,林白虽然拒绝将她作品中的人物全然看作她自己,但是她也承认这些女性人物“跟我个人的生命本体有着某种一致性,一种叠合”②林白:《林白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01页。,多米和海红的许多方面都投射着林白的影子。林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回望的姿态书写了两部半自传式的作品,这种回忆的视角可以覆盖第一人称叙事所无法触及的视域,又可以站在成年的“我”的角度对“我”曾经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理解与评判,展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间隔了二十年左右,林白的身份也从一个“北漂”的文学创作者变成了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人生经历的累积让她在两部作品中融入了不同的思想情感、成长认知,其中的种种转变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主人公的主体建构中窥见一二。
二、成长主体的漂泊流浪与自我救赎
多米和海红在童年时期都有着同样的创伤性经历,首先她们与母亲的关系是极其疏离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母女关系是因为母亲为了自己的幸福曾经把孩子丢给乡下的亲戚抚养,在乡下她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物质匮乏和寄人篱下带来的痛苦。虽然后来多米和海红都被母亲接了回去,但是她们已经自动与母亲之间建立了厚厚的壁障,冷漠地面对着来自母亲的讨好并从不回应。她们的父亲也都是处于缺席的状态,“中国文化历来有着尊父、崇父的传统,强调君臣父子的秩序,父亲处于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核心,扮演着家庭秩序的制定者、控制者、道德权威等角色,是强权意志的象征”③郑利萍:《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父”与“子”关系的变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虽然父亲的不在场给了主人公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不必被父权掣肘,但是整个家庭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无法带给儿童成长需要的安全感。家庭就是主人公最先接触的小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两位主人公与主要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交际呈现全面溃败式的面貌,为她们以后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林白也曾在文中以成年海红的视角对此进行评判:“在海红看来,她异峰突起的婚姻、兀促的爱情、高低起伏的异变情绪,以及节节败退的生活,无一不与她的幼年有关。”④林白:《北去来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4页。幼年时的伤痛经历让主人公的人格无法正常发展,那些受过的创伤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粒粒种子,在以后长大成人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固有的反射机制,一旦触碰到了某些阴暗面就会促使她们产生逃避的心理,而每一步错误的选择又造就了她们错位的人生。但也正是这种淡漠的亲子关系让文中的主人公有了逃离故乡的强烈愿望和条件,也成为多米和海红漂泊成长的起点和叙事动力。
在外漂泊的过程中,主人公多米大多数时间都是从感性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独自去旅游、与旅途中认识的男子发生一夜情、对渣男毫无保留地奉献等等经历,都是多米顺从内心却不考虑现实而进行的冒险活动。这本书中,膨胀的女性内心的自我意识压倒了社会中的现实存在,以“我”为中心成为叙事的底层逻辑。而《北去来辞》中,海红同样也是一个追求自我、自由、爱情的人,但是她开始承担曾经的任性所造成的后果。因为听凭自己孤僻自闭的个性不愿改变,所以在自己下岗、家庭陷入经济困难之时,狭窄的社会交往让她根本无处求人。后来又因为出轨追求自由而与史道良离婚,然而离婚后却更感空虚抑郁,与出轨对象之间的激情也突然消失。现实生存的不易让她不能再虚无缥缈地活着,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是多么地渺小。曾经无限张扬的自我意识与如今残酷的现实下渺小的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矛盾冲突正是让主人公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无比痛苦的重要原因,这种痛苦也是觉醒自我意识的人类所普遍感知的。
为了缓解这种自我与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痛苦,海红尝试了多种方法去救赎自己。她在离婚后又重新回到了家庭之中,然而史道良与她在生活理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始终无法避免,最后史道良还是因为女儿的叛逆和身体的变故离开了她。海红也曾经尝试过回归自然去改善精神、激发创作力,但是这种生活只能是暂时的,而且乡下也已经变得萧瑟破败,异化的场景让人心灰意冷。海红在丧失了爱情和生活伴侣后想要为自己黑暗的生活找到一点点光亮,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圭宁。对于故乡的回溯与父亲生前真相的探求,是海红对自我来源的追问,也是对既有秩序的回归。“因为‘父亲’是缺席的,‘寻找父亲’才成为必然的命运。这种‘寻找’落实在文本中,是对于‘父亲’形象的重新修正。那个在众多作品中被剥除了尊严和人格的‘父亲’被重新迎回子辈的精神生活与现实世界,‘父亲’之为‘父亲’的意义得以庄重诚挚地再现。”①郑利萍:《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父”与“子”关系的变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虽然所有自我救赎的方式均宣告失败,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却是主人公在挫折中不断建立主体性的过程。曾经的亲情缺失、童年创伤已无法弥补,海红只能在寻觅无果后回到都市中继续独立地面对生存的困境。
三、他者包围下的主体成长
在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主人公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成长的“引路人”。有的引路人会对主人公产生正面的引导作用,让他们褪去青涩,走向成熟。有的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作用,带领他们误入歧途。我们发现林白在两部作品中重点描写的“引路人”常常带给主人公以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这些创伤性经历使得主人公在人格品性方面发育不良,造成人生发展的阶段性的悲剧。这些负面的引路人“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反面参照,在与‘坏’的比较中,‘好’获得了清晰的界定”①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但这种创伤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主人公的情感认知,让他们更加了解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私与虚伪,从而在迷茫与痛苦中达到自我成长的效果。
从同性关系来看,多米和海红都曾遇到一个极其爱护她们却也给她们造成了伤害的女性朋友。多米在二十七岁的时候遇见了二十一岁的女孩儿南丹,她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经常将别人贬损的一无是处,却唯独对多米赞赏有加。海红同样也在大学认识了学姐邸湘媚,在海红感到自卑孤独的时候,邸湘媚主动接近她,与她成了朋友。一方面,南丹和邸湘媚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主人公保护人和男朋友的角色,这两位女性朋友都带着主人公领略了生活中不曾体验过的新鲜事物,让她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另一方面,这种接近带有暧昧的色彩,这两位女性朋友具有极强的占有欲,她们在某种程度上圈禁了主人公,让主人公只能依赖她们,无法得到自主的发展。林白在友情篇的结尾处也作了这样的点评:“由于湘媚不自知的侵略性和控制欲,由于两人多少反常的友谊,海红在大学阶段错过了健康成长的机会,也失去了正常恋爱的训练,情感的缺陷长久伴随着她,以至于,她后来的爱情都是不成功的。”②林白:《北去来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96页。畸形的爱即使再温暖也是有毒的,一旦主人公意识到这一点,这份变质的友情就会变得不堪一击。主角的成长需要挣脱这些枷锁,才能够迈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男女关系的描写也在林白的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女人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漫漫长途的每一步,都与如何认识男人如何处理和男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是女人和男人共同的宿命”③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大多数的女性主义作家在创作时都将男性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这些男性的面孔在文本中往往是可鄙又可憎的,具有很强的符号性。林白早期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也是如此,主人公多米经历了多段的男女关系,这其中既包括在激情与冲动下的身体关系,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爱情关系。身体关系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心灵的伤痛,例如在多米的独自旅行中,男人矢村简单粗暴地开启了她的第一段性经历。这段性经历让多米感到疼痛难忍,没有获得丝毫快感。“她开始意识到,她毫不被怜惜,她身上的这个男人丝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个恶棍和色狼,她竟眼睁睁地就让他践踏了自己的初夜。”④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这些男性在作者的塑造下就是一个个被激情和欲望控制了的动物,他们的身上带有男权的色彩而永远无法与主人公心灵相通。包括后来与多米建立恋爱关系的导演N也象征着这类只知索取、狡猾自私的男性群体。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多元化、开放式的发展,西方的很多女性主义思想也传入国内,很多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满女性的欲望和诉求在男权社会中被压抑,她们渴望张扬自我的隐秘欲望和内心体验,不再做男性视角中沉默的被言说者。所以在突出书写女性的自我意识的时候,男性在她们的笔下也变成了一群符号、叙事的工具,甚至带有某些刻板印象。
而这种情况在《北去来辞》中则有所不同,林白虽然也塑造了瞿湛洋、陈青铜等有如符码性存在的男性群像,但是其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史道良却并不像其他角色那样单薄。相对于极好或极坏的男性人物形象,史道良是处于中间的存在。他有着文人的清高,不屑于世俗的追名逐利,也不善于社交,但是清高中又带有腐朽落后的古板。史道良仿佛是被时代所遗弃的一个过时的古董,但是林白并没有仅仅展现他落后于时代的一面,而是试图走入他的过去、内心去探究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他从小接受了传统教育,后来经历了大饥荒,所以工作后返乡会尽可能为家里带去很多的吃食。那个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很友善,让人精神上感到温暖,史道良常常怀念那个年代。而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开始迅猛发展,社会的风气却也随之变坏,人们不择手段地去挣钱,金钱至上的观念取代了传统的义利观。这也是史道良厌恶世俗、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他甚至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去寺庙当和尚。在小说的结尾,海红也体谅了道良在婚姻中的不易,“回想起来,道良似乎一直有一种走向彼岸的冲动,他对此岸是鄙视的,惟其如此,他才会认为左边的和右边的邻居、楼上的和楼下的邻居,一概‘都不是人’。也许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多年来,出于责任他才熬到今天”①林白:《北去来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47页。。林白在创作《北去来辞》的时候,不再从相对狭隘的女性主义视角去塑造男性人物形象,而是以更加温和冷静的态度去理解每一个个体。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标签虽然凸显了林白创作的独特性,但是它也大大限制了其作品的阐释空间。林白也表达过对被局限于“女性主义”这个区域的不满,所以她在创作中不断进行转型和创新,以超越性别的视角去塑造男性角色,构建相互理解的两性关系。海红在这段婚姻中得到的不仅是伤害,还有丈夫所给予的体贴和关怀。她在婚姻中度过了最后的“青春期”,学会反省自身与体谅他人,明白了婚姻需要双方恒久的忍耐,而成长无法寄托于他者只能靠自身完成。正如钱锺书曾讲过的婚姻犹如围城,重要的是女性能否看清婚姻的本质,“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旧是他者”②[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827页。。
四、建构完整性的主体
张柠曾在《论叙事的整体性》中提出:“当此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无论创作还是理论界,能否将各种文化都整合到自己的血脉之中,并不断地追求对‘更高意义上的人的完整性’的理解,探索审美形式意义上的叙事整体性的表达方式,是中国的叙事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叙事能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③张柠:《论叙事的整体性》,《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林白如何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去塑造具有完整性的主体,也是她创作转型的重要标志。林白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抒发了女性在社会中被压抑的精神诉求和内心欲望,由此她也成为“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为了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她在小说中积极运用了很多现代叙事技法,如非线性的碎片化时间叙事以及大量的隐喻、暗示、联想的手法。林白还在描写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时铺陈了很多的心理描写,试图表现人性中更深层次的真实。例如在多米第一次加入群体共同洗澡时,她很不习惯也很害怕,当听到别人叫她的名字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心中一惊,瞬时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像子弹一样落到了我第一次当众裸露的身体上,我身上的毛孔敏感而坚韧地忍受着它细小的颤动,耳朵里的声音骤然消失,大脑里一片空白”①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47页。。对人物复杂性的描写以及心理的精准刻画是很困难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除了对内在的小世界进行探索并记录个体的喜怒哀乐,要是还能在此基础上与历史和社会相联系,就会为文本赋予更具时代性和经典性的内涵。
林白在《北去来辞》中完成了这种创作的转型,既延续了以往对人物自我意识的关注,同时也注意将个体的成长融入整个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将突出表现心理属性的人物主体塑造得更具复杂性和立体性。马克思曾指出完整的人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部本质据为己有”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7页。。所谓“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的各种属性的综合,如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等等,这些属性蕴含于人与外部世界以及自我的关系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人公海红经历了从乡村逃离到城市,然后又渴望回归乡村的过程。海红在都市中生活时常感到不安、孤独、焦虑,她吃饭没胃口,写作缺乏灵感,夜里想睡也睡不着,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她开始想要回乡下住上一段,“她希望以此改变生活,摆脱内心的无力感、间歇性的恍惚、内心的枯萎……或者说,希望通过乡村生活返回一个坚实的世界”③林白:《北去来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90页。。这种渴望回归自然以治愈自己的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海红在都市中所产生的价值危机、精神危机,功利的人际关系、残酷的社会竞争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自然也就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虚弱。席勒曾经批判给人造成创伤的文明,并指出正是因为各种精密的科学和严格的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④[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47页。。现代性的制度破坏了人的完整性。在乡村生活,干了几天农活后,她的身体和精神果然迅速好转,连眼睛都有了神采,皮肤也泛起光泽。此时,融入自然环境的人也开始达到了生命的一种和谐状态,这源于自然景观所具有的审美效应。自然本就是人的起始与归宿,它可以消除人在都市中被异化的感觉,回归于生命本初的涌动,在实践与认知中激发人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如果说《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的话,那么《北去来辞》中的海红开始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与他者和社会保持联系才能走入一种更好的生存状态。海红和史道良狭窄的社交范围就是造成家庭氛围荒漠化的重要原因,他们几乎很少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娱乐活动,这种闷不透风的家庭氛围让女儿春泱更加想要逃离,不想变成像她父母一样无聊的人。现实中的磨难促使海红开始从非理性的生命欲求回到理性的反思中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另外,林白在创作转型的过程中更注重将个体的自我心灵成长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相结合,由社会群体的立场去审视自我的缺陷,也从女性主体命运的曲折反思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阵痛。“文革”时期、计划生育虽然在文中都只是作为主人公的成长背景,但其中陨落的每一个生命都让读者感到触目惊心。1999年,海红的单位重组、解散,她也只能被迫下岗,她的遭遇反映了当年下岗潮的环境下每个底层小人物经历的艰难辛酸。21世纪后,打工少女雨喜所经历的工作影射了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她在一路漂泊中所遇的事情也揭示了在人们看不见的黑暗处所滋生的无数罪恶,传销、诱拐少女、代孕等等。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林白从个体出发,在每个个体的成长蜕变中感受时代氛围和社会集体心理的变迁。
五、结语
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以主人公多米内在的本能欲望和生命体验为中心书写了一个女性主体的成长过程,而在21世纪后的小说《北去来辞》中延续了这种“私人化写作”的特征,同时主体开始“发现和接受现实世界的真相和规则,逐步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①田广文:《新潮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历史语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5期。,主人公逐渐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的成长。多米和海红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面临了亲情的缺失、欲望的诱惑、友情的变质与爱情的失落。她们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渴望突破传统的男权文化的禁忌,追求“超现实主义”的自由。多米对身体的随意支配、海红对婚姻无谓的态度都是她们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特点,但是她们又不能完全逃脱伦理体系的束缚,还是渴望能够拥有亲密无间的女性朋友、理想的爱情或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在自由与稳定、独立与陪伴、理想与欲望中的反复徘徊正是她们面对世界的矛盾与困惑。在成长的后期,海红还是要回归于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现实,但是在由“多米”到“海红”的这个过程中,主体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增强了自己对苦难的承受力、对生活的价值判断力。当主人公开始由向外寻找依靠力量转向对内在自我的不断修行时,也许才是真正的成长完成的时刻。
林白在《北去来辞》中的创新性改变是将女性的成长主题与乡村异化、阶级差距、历史苦难等社会议题相结合,在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中构建完整的主体。但是在为长篇小说组织材料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是人物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作者虽然还是以主人公海红在婚后的成长为主线,但是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写与她没有太多交集的雨喜、安姬惠等支线人物,让情节结构显得相对松散。这可能是由于作者想要靠近主流叙事话语,将个体的心灵成长与民族时代的发展相融合,但是在叙事上对总体的把握还不够纯熟。瑕不掩瑜,林白在《北去来辞》中的创作转变还是给当下的成长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让我们思考很多成长小说中处于“在路上”的迷茫的成长主体在接下来应该走向何处。女性主义成长作家可以跳出女性主义的标签,用“超性别”的视角反思男女关系与女性主体的建构。很多擅长“私人化写作”的作家在聚焦个体的心理境况的同时也可以重拾以往被抛弃的宏大叙事,创作有叙事张力的成长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