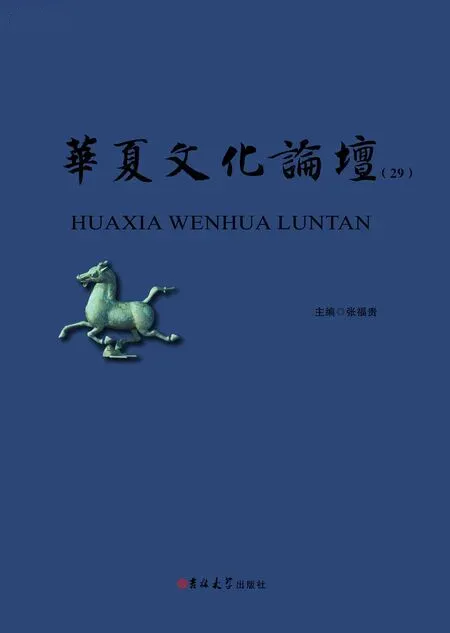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所载组诗之题名及构成
王 志
【内容提要】《周公之琴舞》应为整篇简文的题名,其所载组诗则应以《九絉》为题名。《九絉》或系周公诗《多士敬毖》与成王诗《敬毖》之合编。其所提及周公诗并不存在亡佚的问题。从《大武》及传说中的《康乐》来看,此类合编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公作为冢宰,有纳言之责,《九絉》很可能便是周公所编,而其文本则应是传乐者所传。在体制上,《九絉》颇可与传说中的一些上古诗歌相互印证,对它们的价值,宜有新的评估。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记载了周朝初年一组非常重要的乐歌,由于该组简第1支简背面题有“周公之琴舞”,所以整理者取以为篇题。另,清华简《芮良夫毖》的第1支简的背面曾误题“周公之颂诗”,虽经刮削,但文字依然可识。《周公之琴舞》所载组诗,包含了今《诗经·周颂》的《敬之》,在性质上,这一组诗也正可以说属于颂诗。并且,《芮良夫毖》简的形制及字体与《周公之琴舞》相同,说明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之,整理者认为,《芮良夫毖》第1支简背后的篇题,很可能是简文书写者原拟的《周公之琴舞》的篇题,只是不小心题错了地方。①李学勤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32页。古人写作,原多无标题。好之者抄写收藏时,为便检索,常取其开篇的若干文字作为题名书于竹简的背面。有时,也会从简文的叙说对象、内容特点或文体性质出发,拟一题名标于简的背面。今题《周公之琴舞》属于前者,原拟而误书在《芮良夫毖》简背的《周公之颂诗》属于后者。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简文的内容全都是组诗的歌辞,那么,这两个拟名自然可以看作是为组诗所拟的题名。但事实上,《周公之琴舞》的简文内容并不如此,其开篇就交代说:
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元纳启曰:“无悔享君,罔坠其孝。享惟慆帀,孝惟型帀。”
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元纳启曰:“敬之敬之,天惟显帀,文非易帀,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监在兹。”乱曰:“遹我夙夜不逸,敬之,日就月将,教其光明。弼持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①李学勤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33页。
其后,才是对组诗其他内容的抄录。可见,在组诗内容之外,简文至少还交代了与组诗相关的作者、立意以及乐舞状况。所以,这两个拟名,疑应视作《周公之琴舞》这篇简文的题名,而不当视为简文所载组诗的题名。其情况可以与清华简《耆夜》相较。《周公之琴舞》记的是周王与大臣的乐歌,《耆夜》记的也是周王与大臣的乐歌,并且也有类似诗序的文字交代君臣乐歌创作的缘起。但《耆夜》并不是其所载乐歌的题目,《周公之琴舞》应与之类似,也是整篇文献的题名,而不是所载组诗的题名。况且,如果是所载组诗的题名,则渊源有自,怎么可能一会儿题为《周公之颂诗》,一会儿题为《周公之琴舞》,竟然如此随意呢?
目前,学界还多将“九絉”当作音乐术语来理解,以为指奏乐九曲。李颖虽然也将“九絉”理解为乐有九章,但同时又认为:“‘九絉’虽不是篇名,但‘琴舞九絉’下统领九首短诗,实际上也具有篇名的性质。”②李颖:《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楚辞“九体”》,赵敏利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页。这一理解极有启发性。只是以“琴舞九絉”为组诗的题名,不如以“九絉”为题名;而且“九絉”所概括的,也不是周公与成王各自的诗篇,而是作为他们诗篇合编后的题目来使用的。李颖指出,“琴舞九絉”之前与之后都有许多以“九”为名的乐歌。不过,文献中还很少有将“琴舞”之类的术语放在“九”之前也作为题名来使用的。李颖之所以不愿直接用“九絉”为组诗题名,是因为她还接受“絉”指乐章而为言的一般说法。其实,“九”虽然可能是表明乐章数目的,但“絉”却未必一定是“终”“成”等乐章之意。如《玉篇》说:“絉,绳也。”而《诗经·大雅·下武》一诗,《毛诗序》认为:“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诗中曾赞美武王:“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毛传解释说:“绳,戒。”郑笺曰:“武王能明此勤行,进于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践之迹。”可见,“绳”是可以训为戒慎的。又,《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谓:“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可见周人作诗,也确常有“以绳文王之德”的用意。既然如此,《周公之琴舞》所载“九絉”之“絉”解为“戒慎”又有何不可呢?更何况,这一组诗的内容,无论是周公诗,还是成王诗,原本就以敬毖为主,因而合编在一起,名为《九絉》,意取戒慎,不正是十分合适的吗?
事实上,不但“九絉”应理解为诗歌的题名,就是“多士敬毖”与“敬毖”也应该看作是诗歌的题名。简文的这两句话正不妨标点为:
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
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
这样标点,也就是说周公和成王分别有称为《多士敬毖》和《敬毖》的诗歌,后来被合编为琴舞而名之曰《九絉》。古人编排诗歌,小题在前,大题在后,也是有例可循的。如《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先题“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后题“毛诗国风”。《周礼》一书先题“周官冢宰第一”,后题“周礼”。孙诒让指出:“汉以前经本,并小题在上,大题在下。”①[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
又,《周公之琴舞》简文在“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下仅附有周公半首诗,而在“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后则附有完整的九首诗,这种文本状况使不少学者相信周公名下的“琴舞九絉”亡佚了八首半。但这种理解实际上颇有些武断。其实,“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下的半首诗,与“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后所附的九首诗,实际正可以看作关系紧密的一组诗。因为周公的“元纳启曰”,是没有乱辞的;而成王的“元纳启曰”及“乱”又紧接着周公的“元纳启曰”,形式上正可以视为完整的一首;两首诗歌的内容也正可以很好地衔接。这一点,基本上已属学界的共识。它证明,《周公之琴舞》中,周公诗与成王诗并不是分散不相关的两组诗,而是有机的一组。蔡先金便认为“按照目前文献记载状况推断,该诗应该是周公与成王合作完成”②蔡先金:《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33-41页。。
李学勤也有类似意见。他率先提出,不能轻易认为《周公之琴舞》中周公诗亡佚了八首而成王诗全都保留下来了。其根据,主要是“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下所附九首诗歌并不完全是成王的口吻,不大可能全属成王的作品。他以为:“《周公之琴舞》全诗十篇,如以内容实际来说,以君臣口吻划分,是这样的结构:所谓‘周公作’:元入启(臣);所谓‘成王作’:元入启(君),再启(臣),三启(君),四启(臣),五启(君),六启(君),七启(君),八启(臣),九启(臣)。”据此出发,他“作一大胆的推想”,以为:“《周公之琴舞》原诗实有十八篇,由于长期流传有所缺失,同时出于实际演奏吟诵的需要,经过组织编排,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结构。虽然我们只能读到诗文部分,《周公之琴舞》本来一定是在固定的场合,例如新王嗣位的典礼上演出的。”③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9页。
李学勤说简文“成王作敬毖”之后所载九首诗篇中杂有周公诗作,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的。可是,如果此说成立,则“九絉”也就只好理解为题名了。因为,如果将“九絉”理解为“九成”,则“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就意味着此“九絉”所指九个乐章全然是成王所作了。而这显然与“九絉”中四首以臣的口吻出现的诗篇内容相矛盾。就这种情况来看,“九絉”也不宜理解为关于组诗乐章数目的叙述语,理解为组诗的题名比较合适。
至于李学勤说《周公之琴舞》可能是“新王嗣位的典礼上演出”用的,学界也基本接受,并大多认为《周公之琴舞》最初乃是周公还政成王典礼上所使用的乐歌。至于他的“大胆的推想”,目前还缺乏相关文献的有力支撑,尚难取信。并且,《周公之琴舞》所载诗歌,在内容上,前后关系紧密,也不像有所亡佚后才被混编在一起的样子。
从传世文献来看,周公和成王名下都有诗歌流传。当然,无论是《诗经》中,还是《周公之琴舞》中,成王名下诗篇皆不排除有臣子代作的可能。但即使他人代笔,也已在实际生活中为成王应用过,被人当作成王诗来记载和编排,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周公之琴舞》中,周公与成王的诗歌都以“敬毖”为主题,但周公诸作是以大臣的口气谈敬毖,成王诸作是以王者口气谈敬毖,且周公所作又主要是训诫众臣,所以,二人所作,一称《多士敬毖》,一称《敬毖》,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此外,说周公、成王君臣各有所作,而后被编成一组诗歌,这种事情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并且还与周公有关,事在成王之前。这就是周初《大武》乐的制作。如《庄子·天下》谓:“武王、周公作《武》。”《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克商后,“命周公为作《大武》”。《武》即《大武》,为周公奉武王之命所作。周公制作《大武》是如何作的呢?是凭空创作一组诗歌吗?不是的。他的做法是将已有的相关诗歌合编在一起而搞成《大武》。如班固《白虎通·礼乐》谈到周公、武王各有诗乐曰《酌》和《象》:
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乐,示以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文中说周公之乐曰《酌》,“言周公辅成王”,这可能是因为周公虽受命制作《大武》,但《酌》作为《大武》的一部分,实完成于武王死后成王当政之时。《象》则不然。《墨子·三辩》载:“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可见武王生前《象》乐就已制作完成。清华简《耆夜》载,武王曾即兴作诗两首。据此,武王是有一些诗才的,他生前能“因先王之乐”而制作出《象》,是有其可能的。从《礼记·文王世子》说:“登歌《清庙》……下管《象》,舞《大武》”来看,《象》也的确是《大武》乐的一部分,所以管吹《象》乐之时,跳的是《大武》中的舞蹈。不过,《白虎通》说《象》乐象太平,不太准确,而应说象伐纣以获太平。《文王世子》郑玄注谓:“《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这就是一证。又,《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孔颖达注《象》舞时引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据此皆可知《象》不是文舞,而是表现戎事的。这又是一证。《白虎通》说《象》为“象太平”,虽不准确,但指出《大武》由武王和周公君臣二人的诗作编排而成,对我们研究琴舞《九絉》也是有启发的。
与《大武》相类似的还有传说中的《康歌》。《吕氏春秋·古乐》载:“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其中《声歌》,《太平御览》《路史》俱引作《唐歌》。陈奇猷以为唐与康同,“唐歌”即“康歌”。此歌名为《康歌》,其内容有《九招》《六列》《六英》,共二十一章,下文云“以康帝德”正与《唐歌》之名相应。①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8、304页。
另,《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而《墨子·非乐篇》引《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将两则材料相比较,《墨子》所言“康乐”也不妨理解为乐歌《康乐》。所谓“淫溢《康乐》”或即指“开焉得始歌《九招》”而言。至于《九招》与《九辩》及《九歌》的关系,或以为因乐歌有九次歌唱,故名《九歌》;有九次变化,故名《九辩》。②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又,《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所谓《韶》音,一般认为就是指《九韶》,亦即《九招》。《九招》是《康歌》的一部分,《史记》不言闻《康乐》,而言闻《韶》,说明《韶》乐本身可以独立成乐。孔子在齐学之三月,亦可见《韶》乐本身体制已甚大,不可遽成也。
《九招》本身已是体制较大的组诗,《康歌》包含了《九招》以及其他乐章,其内容之复杂,规模之宏大,不难想见。这样宏伟的诗乐,出自一人之手,难以想象。《淮南子·齐俗训》载:“《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其中《六英》高诱注曰:“帝颛顼乐。”帝颛顼在帝喾前,这也可见帝喾命咸黑制作的《康歌》,并不是纯然自造,也是前有所承的。换言之,《康歌》的编者是咸黑,但其作者并非一人。
从《大武》以及传说中《康歌》这种制作情况来看,将若干首不同人创作的诗或组诗再编成一组大型诗乐,是周以前源远流长的一种艺术传统。所以《九絉》为周公诗与成王诗的合编,既有前例可循,也就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并且在诗体性质上,《九絉》与《大武》《康歌》也是一样的。《九絉》中,成王的一首诗以《敬之》为题被收入《诗经·周颂》,说明这一组诗歌也应属于颂诗。《大武》也收在《周颂》中,属于颂诗,自是不必多说了。而言及《康歌》,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曰:“帝喾之世,咸黑为颂,以歌《九招》。”《九招》既为颂,《康歌》自然也应属于颂之体。《康歌》与《大武》作为大型组诗,其所包含的诗篇可以单独使用,《九絉》也是如此,《敬之》被单独收入《周颂》就是明证。
与《大武》相比,《九絉》的构成状况或许更近于《康歌》,因为《大武》还只是若干单篇诗歌的合编,传说中的《康歌》则是若干组诗的合编;而从《周公之琴舞》所载来看,周公语气的诗不止一篇,成王语气的诗也不止一篇。这就不排除它们原是两组诗歌。《周公之琴舞》在叙述时,只在所列周公第一首诗歌前,标以“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同时,也只在所列成王第一首诗歌前标以“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而不在后面其他首诗歌前标以类似的说明,这也正可能是因为后面所列诗歌分属于周公的《多士敬毖》与成王的《敬毖》,并且诗中作者的身份语气较为明显,也就没有必要再一一加以标示了。当然,《九絉》的混编,是将两组诗歌有机混编在一起,而《康歌》虽是若干组诗的混编,但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推度,其各部分组诗应还是作为独立的单元而存在的。
将《九絉》与《大武》相较,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个启示,即《大武》乐包含了周公的作品,而且是周公奉命将其与武王的诗乐编排在一起的,那么,《九絉》会不会也是周公本人编排的呢?周公这样有文艺天赋,而且还是原作者之一,由他来编排,显然是最为合适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公在周王朝初年很可能肩负着纳言的职责。
纳言是我国上古王朝很早就设置的一种职官。据《尚书·尧典》,帝舜曾任命“龙”为“纳言”,伪孔传谓:“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益稷》亦载,帝舜指出“工以纳言”,并要求乐官“出纳五言”时,辅佐大臣禹要负责“听”,也就是为其把关。这里的“五言”,孙星衍解为“五声之言”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5页。,金景芳以为是五声配上言辞形成的歌咏②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2页。,甚是。
纳言之事,周人依然沿用而不废。如《大雅·烝民》,据《毛诗序》,是“尹吉甫美宣王”之作。诗中赞美宣王任用仲山甫,谓仲山甫“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仲山甫的时代,已是西周晚期,彼时仲山甫还可以“出纳”王命,则周初当然更不会没有纳言的职事。事实上,琴舞《九絉》中已明白无误地将《九絉》为纳言官整理而成这一事实标示出来了。因为简文交代这一组诗歌的开始部分时很特殊,不像后面各首诗,提示为“通启”“三启”“四启”等,而是连说了两个“元内,启曰”(周公作),“元内,启曰”(成王作)。这里的“内”,学界一般理解为“纳”的古字,解为献纳。可是如果说周公作诗献纳给成王,这还说得通,但如果说成王作诗献纳给周公,这就有些不合乎尊卑之常了。所以,这里的“纳”,宜指纳言官的纳言工作。元纳,就是首纳,指纳言时将某些诗句首先陈示给大家赏鉴。其后的“通启”“三启”等则是承前省略了纳字。这个纳字只是对乐工工作的提示,本身并没有什么其他含义。在传世文献中,“元纳”一语虽然罕见,但与之类似的言语也不是完全没有。如《论语·泰伯篇》载:“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孔子的这句话,今人一般在“始”字后断句,但郑玄注曰:“师挚,鲁太师之名。始犹首也。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洋洋盈耳,听而美之”③[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5页。,据此注来看,郑玄显然是以“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为句读。郑玄大概没有见过《周公之琴舞》一类的文献,所以还将师挚之“始”具体解为“首理”,而今将其与《周公之琴舞》所谓“元纳”相较,则所谓“师挚之始《关雎》之乱”,应是说师挚陈诗奏乐之时,是将整治男女夫妻之道的《关雎》作为开端加以献纳的。总之,师挚之“始”与《周公之琴舞》所谓“元纳”,都不过是指乐工献纳诗乐时诗篇演奏顺序而言。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曾指出,周诗的流传,有传诗者和传乐者之别。①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122页。《周公之琴舞》应该是由乐师传承的,所以才有这样的标识。就此来说,《周公之琴舞》这篇文献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它直接向我们呈示了乐师传诗的文本状况,而此类文献以前是极为罕见的。
可是,即便《九絉》确实为纳言官编排而成,那又与周公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当然是有的。譬如,《烝民》将出纳王命者说成是王之喉舌,毛传:“喉舌,冢宰也。”而《尚书·蔡仲之命》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左传》定公四年载,祝佗也说过:“周公为太宰。”就此来看,周公佐成王时,周公正与其前的大禹、其后的仲山甫一样,本身就是君主的喉舌,直接掌管着纳言的工作。就这种情况来说,琴舞《九絉》即便不是周公亲手编排而成,周公也一定是进行了指导,并最后加以审订。《周公之琴舞》之所以题以周公而不是别人,也应该是因为这组诗歌是由周公负责制定的缘故。
需要说明的是,《周公之琴舞》文中提到“周公作”,如果是周公编排的《九絉》,他会这样行文吗?我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周公之琴舞》与《九絉》不同,前者只是乐师所传诗乐文献,行文自然是后世乐师的口气。一是,即便认为《周公之琴舞》就是周公编订的《九絉》的乐章文本,其行文言“周公作”,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一文本并不是周公自己编来私下里看着欣赏的,而是要交给乐工们演奏,用于王朝典礼活动的。因而说“周公作”,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琴舞《九絉》与《大武》乐的联系,学界早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而除了《大武》乐,还有些相传是源自上古的诗歌,亦可以与《九絉》的体制加以比较。
一是《尚书·益稷》载: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帝拜曰:“俞,往钦哉!”
《益稷》是伪《古文尚书》从今文《皋陶谟》中分离出来的,因而这一篇今古文皆有,是较为可信的上古文献。其所载诗歌,古人常视为一组。其内容与《九絉》至少有两点相类。一是,其内容都是君臣间以诗歌相劝勉;一是,在诗歌内部结构上,同一首诗有前后两个部分。在琴舞《九絉》中,一首诗基本由“启”和“乱”两个部分构成。而《皋陶谟》所载,同是帝舜的歌,却先曰“作歌”,又曰“乃歌”。皋陶的也是,既曰“乃赓载歌”,又曰“又歌”。这种记录看似啰唆,但显然应该是事出有因的,至少说明,前后两“歌”,应该看作是一首诗的两个部分。并且,从内容上看,无论是帝舜所歌,还是皋陶所歌,诗歌的前后两个部分内容都明显具有相互承接的逻辑关系。这种状况,也正与《九絉》相类。所不同的是,帝舜与皋陶的这一组诗歌对答,当时似乎并没有被明确编排为一组诗并加以拟名。后人尤其今人谈到这组诗,往往笼统地名之为《股肱歌》《元首歌》,这两个名称对言的话,往往是指帝舜与皋陶各自的诗歌。若单言《元首歌》或者《赓歌》,则包括了“股肱喜哉”以下的诗句内容,这就又有点像是编排在一起的总名了。
值得指出的是,上古歌诗,多被疑为伪托,而《益稷》所载者则颇受后人的认可。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谈到这一组诗,也认为“可征信”,只是他没能看到身后出土的琴舞《九絉》这样的文献,所以还和前人一样,没有将帝舜的“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算在组诗之内。其实,无论从《尚书》所谓“作歌”来说,还是从内容上来看,这两句也应当算是组诗的内容。
当然,与《九絉》相较,帝舜与益稷的对答诗虽然各自也都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但毕竟缺乏“乱”字作为明确的标识。不过,诗歌文本缺乏“乱”字,而实际却含有“乱”的成分,因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的诗体形式,确实是早就有了。如《国语·鲁语下》曾记载鲁人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其中作为“其辑之乱”的所谓“自古在昔”云云,正都是《那》中的诗句,而《那》是十二篇《商颂》的首篇,所谓“其辑之乱”显然不会是指十二首《商颂》的“乱”,而只能指《那》这首诗的“乱”。《商颂》,学界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多认为是春秋时代宋人所作,现在则普遍认为这组颂诗是殷人遗作了。另,屈原《远游》以“重曰”为标志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重”与“乱”略同。这也可见,《九絉》每首诗一启一乱的诗乐结构,恐非新创,很可能与《远游》共同拥有悠久的历史来源。
一是《尚书大传》卷二载,帝舜将禅位夏禹时,有卿云出现:
于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于一人。”帝乃载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圣,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①[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二,清光绪二十二年刻师伏堂丛书本。
与《元首歌》比,《卿云》显然更近于《诗经》四言诗的艺术形式,因为是汉初伏胜《尚书大传》所传,前无所见,也就更不能蘧然信为是帝舜时代遗留的原始歌谣,不排除经过后世的笔削润色。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歌的结构体制对研究《九絉》亦有启发。一者,《卿云》歌非是一人所作,乃是帝舜与其大臣围绕共同的歌咏对象所作。这与《九絉》中周公与成王围绕“敬毖”作歌是一致的。二者,与《益稷》所载不同的是,《益稷》所载诗歌是君臣各有两章歌词,彼此构成应答,而《卿云》歌的结构则是君作了两章,臣作了一章。而我们前文曾谈到,《九絉》中周公的半首诗与成王“元纳”之诗应属于一首诗歌。其中,周公的半首诗可视为首章,成王所作“启曰”“乱曰”则可视为后两章,从结构上说,也正是臣一章君两章。这至少说明,上古君臣为某事相互咏和,未必一定要各有二章。三者,《卿云》三章歌词思想上联系紧密,先是帝舜因卿云出现,感慨“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进而是大臣强调“日月光华,宏于一人”,最后是帝舜结合“日月有常”,表示自己“菁华已竭”,应当“褰裳去之”。可见其结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而《九絉》中,周公的半首诗作为首章,强调的是臣工们若想“享惟慆帀”,就要“罔坠其孝”,“孝惟型帀”。而成王“元纳启曰”作为次章,强调的是“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乱曰”作为终章,强调的是“不逸,敬之”,“弼持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很显然,这三章的意思也是层层递进,与《卿云》歌无二。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九絉》中一些诗歌的结构方式或类于《益稷》所载,或类于《卿云》所歌,因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古君臣相和而歌的一些结构方式与艺术特点;同时,《卿云》等诗歌的结构特点既与出土文献所载者相类,也就说明它们很可能渊源有自,不大可能完全出于后世之伪托与虚造,应给予充分之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