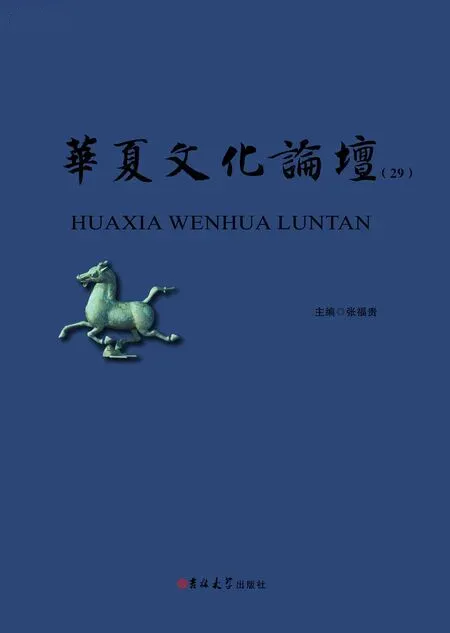论鲁迅笔下底层人物形象精神状态的生成过程
刘中树 曹志远
【内容提要】对鲁迅笔下底层人物形象精神麻木的讨论不能仅满足于封建礼教压迫导致的人性缺失这一概括性判断,还需要从这一异变过程中间的微观考辨回答为何底层民众会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丧失人性。从历时性的过程来看,封建礼教引发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丧失,同时必然地伴随着人类情感的丧失,而情感的丧失最终标志着人性的彻底沦丧。从共时性的表现来看,社会的黑暗导致了自我意识、对象意识和人类情感的同时丧失。只有将底层民众精神麻木的生成过程充分阐释,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在思想启蒙过程中精神深处的孤独与绝望,才能真正意义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鲁迅的思想资源。
一
以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形象的重要特征是其麻木的精神状态。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集中体现在他们普遍性地丧失人类本应具有的情感,既缺乏必要性的自尊自爱,更不会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共通感出发去同情他人。传统观点认为是封建礼教的压迫导致了人性缺失,黑暗社会的摧残引发了愚昧麻木,病态文化的荼毒催生了精神扭曲。从宏观上来看,上述判断深刻揭示出了鲁迅笔下底层民众精神痼疾的文化症候,也充分透析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理想的内在动力根源,有着重要的学术史价值。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上述共识性的认知是一种直接性的判断,欠缺从原因到结果这一过程的逻辑演绎与必要说明。对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麻木精神状态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于外部恶性因素的罗列,更需要从内部考辨中回答为何底层民众会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丧失人性,异变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生成的。同时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论证健全人性在封建礼教摧残中必然扭曲的悲剧历程,从逻辑学的层面演绎旺盛生命在黑暗社会压迫下的点滴消逝,从人类学的维度反思规避这一文化陷阱的可行路径。只有将底层民众精神麻木的生成过程充分阐释,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在思想启蒙过程中精神深处的孤独与绝望,才能真正意义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鲁迅的思想资源。
二
对自我尊严的充分强调、对个体价值的激烈捍卫构成“五四”文学的核心观念,这不仅是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思想观念的主动移植,更是“五四”新文学呼唤“人的文学”的自觉彰显。从民主与科学的视域出发,确证人的权利与尊严既是启蒙文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始终以异己性的他者价值取向评判自己和他人,这就导致了他们既难以清醒意识到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又不会因自我尊严的丧失与权利的被剥夺而主动反抗,相反却在群体性认知的强制之下被动形成扭曲的价值取向。阿Q自欺欺人与自我麻痹的“精神胜利法”则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因此,透析底层民众精神麻木的根源在于彻底揭示其自我意识丧失的根源,而揭示自我意识丧失的根源又需要厘清自我意识产生的根源,那么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出发,人类的自我意识源于历史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在漫长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意识观念,区别于动物在生理性本能支配下的自在活动,人类能够初步地认识到活动本身即自觉自为的活动。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2页。正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的自觉性和目的性构成了人类自我意识产生的基本前提。“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因此,自我意识本质上是把自己作为对象来看待的心理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原意并非人类带有自觉性与目的性的劳动过程直接导致了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而是自我意识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真正意义上形成区别于动物自在性的自为性活动,也即是说,人类的劳动与自我意识互为前提,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才能产生自我意识,也只有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才能摆脱动物性的自在活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对于这一问题只有在唯物史观中才能加以辩证地把握:“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③[德]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5页。因此,人只有能够进行自我认知之时,即具备自我意识之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人也只有具备自我意识之时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产生需要借助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象化能力,特别是那种将自我作为对象的心理机能。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是劳动主体目的性的现实承担者,而经由人类劳动改造后的劳动对象是劳动主体自觉性的客观物态化呈现。由是观之,自我意识同时也是对象意识。如果说自我意识是把自我作为对象来看待的话,那么对象意识则把对象作为自我来看待。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互为前提的。只有把自我作为对象来看待,才能把对象作为自我来看待;也只有把对象作为自我来看待,才能把自我作为对象来看待。无论是把自我作为对象还是把对象作为自我,贯穿始终的是需要情感的参与。没有情感的参与,人类不可能把自我作为对象或者把对象作为自我,人只有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对象中,才能以拟人化的方式把对象作为另一个自我来看待,才能像珍爱自我一样珍爱对象。同理,人也只有具备情感对象化的心理能力,才能真正意义上区分自我与他者。“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因此,只有具备自我意识,才能形成对象意识,也才能超越动物性的本能情绪,将其升华为人类性的对象化情感。反过来说,丧失自我意识,就必然丧失对象意识,也就必然丧失情感。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情感三者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关系系统,切除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另外两者的消失。
基于此,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精神麻木的中间过程基本清晰。从历时性过程来看,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迫使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自动放弃自我的认知,将自我的评判完全让渡给外在于自我的群体,进而以他者的价值标准衡量自我与他人,从而既不能将自我作为对象来审视,更不会将对象作为自我来看待。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丧失同时必然地伴随着人类情感的丧失,而情感的丧失最终标志着人性的彻底沦丧。从共时性的表现来看,黑暗社会的摧残与压迫催生了底层民众的精神异化,直接导致了自我意识、对象意识和人类情感的同时丧失。阿Q自始至终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可怜,甚至在生命终结之前所关注的依旧是尽全力将圆圈画圆,而非面临死亡本能的恐惧与战栗。究其原因,则是人性彻底沦丧后行尸走肉的自然显现:体验不到他人的痛苦,自然也感受不到自己的悲哀;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幸,自然也难以怜悯他人遭遇的摧残。精神一旦麻木,任何外界的刺激都无济于事;灵魂一旦毁灭,任何救赎的努力都丧失意义。鲁迅对在阿Q的人生际遇和精神图景的多维呈现中,将底层民众精神状态的本质深刻揭示。从深层机理来看,外部环境的挤压与摧残迫使底层民众的内在精神发生裂变,丧失人类原初的精神自觉和普遍情感,内在精神的裂变同时也加剧了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甚至为这种践踏人性的外部环境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扭曲证明。阿Q欺辱小尼姑的行为是那么自然而然,“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言辞又是那么浑然天成,在他的潜意识中,小尼姑就是可以恣意欺辱的对象,无须任何合法性的前提。他当然不会推己及人地思考自己在赵太爷面前也是如此的卑微懦弱,更不会感同身受地体验小尼姑的楚楚可怜。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施暴心理的满足和病态快感的获得。鲁迅借助阿Q的行为和心理将人性裂变的纯粹程度深刻透析。传统意义上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为自我麻痹和矛盾转嫁两个方面。前者意在说明阿Q在强者面前遭遇不公正待遇后只能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缓解自我身份认同的精神危机。①罗广荣:《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成模式》,《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后者着力阐释其以在弱者面前施加暴力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丧失的病态超越。②邹永常:《阿Q·精神胜利法·认知重建》,《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这种概括本身相当精准深刻,但距离全面透析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麻木精神状态尚欠缺临门一脚。即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呈现的自我麻痹与矛盾转嫁并非纯粹割裂的两个部分,而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阿Q丧失了自我意识,不能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看待,意识不到自己本应享有的生命尊严,所以他就不可能具备将他人作为自我来看待的情感本能,当然也就不会尊重他人,更不会同情怜悯弱者、共情于他人的悲哀。也正是因为阿Q丧失了人类固有的情感本性,不会对他者的悲哀产生本能的同情和怜悯,所以他也绝对不可能尊重自己,捍卫本应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权利。一个人只有爱自己,才能爱别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爱自己。这本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核心,却在封建礼教的扭曲之下已经变异沦落为压抑自我、扼杀他人的“无物之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相对厘清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作家的文化选择,他们并非单方面将西方现代启蒙观念直接平移,而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深恶痛绝中国传统文化在千年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畸变,迫切地希望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涤除糟粕,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文化观念。因此,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文化改造是以更加系统性的方式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总体设计。前者在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唤中确证思想启蒙的合理依据,后者在道德救赎的意义上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因子,二者在看似殊途的分野中共同指向“改造国民性”的立人同归。
三
以上述的观念审视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始终深陷于缺失自我身份认同的悲剧性境遇中难以自拔,并非仅仅出于对现实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消极认同与病态反抗,更源于他们在自我意识丧失后所引发的人类情感的畸形裂变。外界的压迫与自我的迷失共同造成自我精神的暗淡,自由的剥夺与依附的惯性催生人格尊严的消解,而情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以不易察觉的方式烟消云散。底层民众精神裂变的过程类似于马克思揭示的异化:“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③[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自觉自为本来是人区别于动物自在自然的特有属性,只有人才具备自我审视与自我预期的心理机能,也只有人才能在改造自然的结果面前产生自我确证的自由感即审美愉悦。人只有自觉其为人之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不能自觉其为人之时则与动物无异。但是人在自我确证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精神的重压。正是因为人自视其为人,所以按照属人的标准要求自我,如果不把自己当成人,也就不必承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就可以像动物一样按照本能欲望来生存,不必考虑尊严的捍卫、权利的争取、价值的实现和意义的创造。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正是出于对精神危机的本能逃避,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放弃尊严、让渡权利、回避价值、漠视意义,主动放弃属于人的特性,以动物性的伪装勉强维系生命的持续。在王胡的巴掌之下,“我是虫豸,还不行么”的自我贬低与尊严放逐换取的是免受皮肉之苦,被赵太爷殴打之后“儿子打老子”的自我麻痹与自欺欺人谋求的是精神危机的短暂消解。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人格尊严丧失为代价的,都是以自甘堕落为动物的耻辱为结果的。“我们家之前阔多了”之所以永远是过去时,是因为丧失自我意识和人性尊严的行尸走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创造出现世的财富和价值的。另一方面,无对象性的情绪和生理性的本能欲望本来是动物的固有属性,人虽然不能完全脱离欲望本能,脱离欲望不能满足的负面情绪,但是人可以自我确立规则并严格自律,从而超越动物的自在存在,享受自由的体验。而鲁迅笔下的底层民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该属于人的自尊自爱病态地视为某种外在的束缚与压迫,将本该属于动物的欲望满足与情绪宣泄畸形地认作人的自我价值实现。阿Q欺辱小尼姑收获的快感足以抵消被小D欺辱所造成的自我认同危机,甚至在这种对弱者施暴的病态满足中,使他彻底忘却之前遭遇的所有不公正待遇。阿Q根本不会意识到他的这种行为与动物的弱肉强食已无本质差异,被动物性支配的阿Q不会对小尼姑这样的弱者产生任何同情与怜悯。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人都会对阿Q“哀其不幸”,因为只要是人就一定具备人类固有的普遍情感,就一定会对他人的不幸产生类似于自己同样遭受不幸的悲哀,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但阿Q自己却不会对自己或与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人“哀其不幸”。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人也都会对阿Q“怒其不争”,因为他悲剧命运的制造者除了不合理的黑暗社会之外,还有其自甘堕落的推波助澜。但阿Q却不会对自己或与自己相同的人“怒其不争”。《故乡》中的杨二嫂被贴上尖酸刻薄的标签,其实她的尖酸与刻薄只是外在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一边埋怨,一边顺手牵羊将母亲的手套塞进裤腰里”。从人性的视域出发,远归的乡亲是颇为珍贵的情感,而从动物性的视域出发,手套才是货真价实的功利。从根本上来说,鲁迅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多数是以物的观念评判自己和他人,鲜有从人的观念审视自我与世界。从物的尺度只能导向功利的满足或失望,从人的尺度却可以通达情感的交融与共鸣;从物的尺度只会催生对他者的漠视或倾轧,从人的尺度却可以在情感的交流中抚慰受伤的心灵。阿Q对赵太爷、王胡、小D、小尼姑的具体态度虽然明显不同,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即“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①鲁迅:《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页。。“羊相”或“凶兽相”的交替变脸则完全取决于对方的实力,特别是与他本人之间的实力对比。因此,无论是显“羊相”还是显“凶兽相”,都是奴隶意识的本能流露,即便在羊面前显露凶兽相,在弱者面前找寻到主人施虐于奴隶的病态快感,也依旧还是奴隶,而不具备主人意识。真正的主人意识是建立在人格独立的平等观念基础之上的,不是对他人的支配,而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自我责任担当的清醒认知而非单方面压迫他人的畸形变态心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①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这种略带激进的文化批判自然引发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质疑,如冯骥才就曾指出:“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传教士们在世界所有贫穷的异域里传教,都免不了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在宣传救世主耶稣之时,他们自己也进入了救世主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站在与东方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看中国,会不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化’的思维,敏锐地发现文化中国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并抛之以优等人种自居的歧视性的目光,故而他们只能看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症结。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②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鲁迅对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批判不是对其个人或个人所代表的群体的批判,而是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前者指向腐朽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后者致力于对病态社会的整体性反思与改造性探索。问题不在于批判的内容与对象,而在于是否存在批判与反思的精神自觉。“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③[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3页。,鲁迅与萨义德存在时空隔绝,但他终其一生的努力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真正产生与形成,其所开创的思想资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依托和必要环节。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著名的“主奴关系辩证”。在黑格尔看来,主人本来具有高贵意识,奴隶本来具有卑贱意识,但在实际中,主人脱离劳动,只会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沦为寄生虫,成为奴隶的附庸,而奴隶却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养活主人,成为主人的主人。④[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144-146页。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奴隶身份的转变根源于劳动,奴隶在劳动中产生的自我意识构成其反奴为主的重要性条件。而鲁迅则深刻地意识到封建礼教荼毒下的底层民众不存在这种反奴为主的任何可能,虽然他们从事劳动,但是他们的劳动已经是外在于他们生命之外的异化劳动。“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⑤[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页。在异化劳动的作用之下,被迫以动物性的机能替代人类本应具有的全部机能,将自由自觉的劳动降低为维系生存的手段,劳动过程不再是将劳动者主观目的客观物质化的过程,不再是具有能动性的摆脱物质需求的精神创造,因此劳动的结果也就不可能成为劳动者自我确证的对象,无法帮助自我意识的确立,劳动成为非自愿性的强制劳动。“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阿Q在“革命”之后的所思所想充分暴露了自身奴隶意识的深刻烙印。阿Q的“革命”不是制度的革新与观念的变革,而仅仅是财富的转移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法是统治阶级人员的内部调整更替。阿Q“革命”的几项重要举措无非对他人财物特别是曾经的统治者的强制性剥夺,如打劫赵太爷家;对昔日凌辱者的打击报复,如统领王胡和小D。这样的“革命”本身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危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是革除现有统治者被上天赋予的使命,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新的阶级统治取代腐朽没落阶级的不合理统治。而阿Q的“革命”则仅仅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强盗行径,是在非正当前提下对他人财物的非法占有,这种行为所暴露的除了动物性的占有欲望本能之外,就只剩下摆脱不掉的奴隶意识。“革命”前后阿Q对吴妈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革命”之前吴妈是阿Q动物性欲望的想象宣泄对象,“革命”之后阿Q对吴妈脚大的厌恶则不仅充分揭示跳梁小丑在身份变革后“品味”提升的丑陋嘴脸,更在客观上暴露了作为封建礼教忠实拥护者的阿Q形影不离的奴隶意识。需要指出的是,阿Q的这种奴隶意识不是外部强加的,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必然存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但真正凸显奴隶意识实质的是阿Q不自觉其为奴隶,甚至主动以奴隶的方式评判自我、规约他人。这也在客观上揭示思想启蒙与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与任重道远。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所承载的奴隶意识已经渗透到集体无意识之中,贯穿其全部生活,支配其整个人生,并非可以像机器取代手工那样轻而易举地完成现代转型,也绝不是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所以从文学的专有名词升级为今日的常规词汇,正是因为其所揭示的文化痼疾依旧存在,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在今日依旧需要加以坚守和继承。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并非只有阿Q个人自我意识丧失、本能情感匮乏。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形象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也许会有质疑认为祥林嫂、单四嫂子对自己孩子的情感至少是真切的,更是感人至深的,爱姑对不公正婚姻的反抗也彰显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但是需要加以厘清的问题是,祥林嫂、单四嫂子对自己孩子的爱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还是人类应该具有的普遍情感;爱姑对不公正婚姻抗争的根本动力是野性生命桀骜不驯的本能还是自我尊严捍卫与平等婚恋观的坚守。具体来说,虽然不能彻底否定祥林嫂、单四嫂子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感人至深的母爱,但这种母爱是出于生命本能的驱使而非自我精神的自觉领会,更不是源于将自我之爱的情感对象化过程。她们的母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动物的舐犊之情,舐犊的动物并非能够自觉意识到它们的情感投射,仅仅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舐犊之情之所以感人至深是源于人在情感观照之下的感情移入,而非动物本身固有的情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祥林嫂还是单四嫂子,都只是把孩子作为唯一的生存依据,没有明确的自我认知,自我是依附于甚至消融于作为对象的孩子之中的。当孩子悲惨的离开人世,她们立即彷徨迷失不知所措,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明确位置。昔日以孩子母亲的标签确立自身,当孩子一旦消失,并不充分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消亡,随之而来的则是精神的麻木与情感的丧失。当祥林嫂反复讲述“我真傻”的时候,除了满足看客们的病态精神需求之外,在她空洞的眼神和乏味的言语中找不到任何情感性因素。当单四嫂子惴惴不安地“等待明天”之时,除了令人窒息的死亡氛围之外找不到半点生命消逝的悲哀。因此,祥林嫂与单四嫂子的母爱仅是发自生命的本能,而非健全人性本应具有的情感。这也正是在读者层面哀其不幸之中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怒其不争的深层思想根源。当成年之后的闰土木讷地喊出“老爷”时,不仅切断了两人儿时的友谊,更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双方都无法逾越的主奴鸿沟。少年闰土与成年闰土的鲜明反差是自我意识存在与丧失的最佳写照,少年闰土带着银项圈拿着铁叉奔跑在黄色沙地中不仅是自我生命绽放的优美画卷和自在圆融的绝佳境界,更是理想人性自由创造的生命赞歌。而成年闰土挥之不去的麻木与僵化则以不争的事实宣告着封建礼教与剥削压迫双重摧残之下的人性异化与扭曲。
四
对鲁迅笔下人物形象精神状态生成过程的分析,特别是对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情感三者内在关联的辩证理解有助于在学理层面更为科学合理地探究鲁迅创作的文学史价值与思想史意义。虽然鲁迅研究持续深入,突破性成果不断积累,但始终难以避免对鲁迅创作的僵化理解与片面阐发,对阿Q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精神状态的理解始终停留于愚昧麻木与不觉悟的概念化惯性认知之中。无论是鲁迅同时代人对其的批判还是当前试图驱赶鲁迅走下神坛的激进行为,都是在以偏概全的主观臆断和某种现实功利的驱使之下对鲁迅本真价值的歪曲与遮蔽。钱杏邨曾以“死去了的阿Q时代”为依据批判鲁迅思想启蒙的不合时宜。在他看来,鲁迅所揭示的愚昧大众是革命之前的大众,在革命文学兴起时大众已经觉醒且成为革命的主体,因此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义和团时代的思想。①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1928年3月号。这一论断正确与否暂且存疑,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鲁迅的价值不在于其批判对象,而在于其批判精神本身。如果说哲学是以概念的方式揭示时代的主题,那么文学则是以形象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时代特征的把握程度决定着其文学价值的根本实现。鲁迅的独异与深刻之处在于既敏锐地将现代转型过程中民众精神的撕裂与文化碰撞的阵痛充分揭示,又能够以超越时代的深邃视域探究突破文化困境找寻精神慰藉的途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始终以“过客”的方式独自一人行走在文化荒原之上,以“死火”的心态一个人承载反抗绝望的焦灼,他从未以领袖的姿态号召众人必须与他保持一致,相反他总是陷入自我剖析的否定与无以复加的反思之中。“铁屋子”与“醉虾”的隐喻集中体现了鲁迅在是否该直面黑暗、扼杀希望问题上的彷徨踟蹰。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参见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420页。]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参见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9页。]这两处经典的表述都是鲁迅对启蒙质疑与反思的自觉流露。因此,对鲁迅思想的研究与继承不能仅仅局限于对鲁迅作品的概念化理解,更需要从个体中深入鲁迅的鲜活生命。前者是概念化鲁迅,后者是鲁迅化概念。概念化的鲁迅只会不断偏离鲁迅思想的本真,与文学史现场渐行渐远;鲁迅化的概念才能永葆鲁迅思想的生动与鲜活。美国学者詹姆逊提出著名的“不断历史化”论断:“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narrativation)。”②[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6页。在詹姆逊看来,对历史的认知只能借助于文本,文本的产生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人们对文本的理解又直接作用于当前具体的历史建构。以这样的观念反观鲁迅的评价史,则不难发现“鲁迅的历史化”始终在进行,而“历史化的鲁迅”则尚未充分展开。前者是在对鲁迅作品概念化理解中加剧对鲁迅理解的片面,后者则将鲁迅本人的独异创造性思想作为新的思维观念参与到新历史的建构之中。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对鲁迅的理解与阐释是否伴随着观念的变革,前者只能陷入无限的循环,后者则践行着根本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