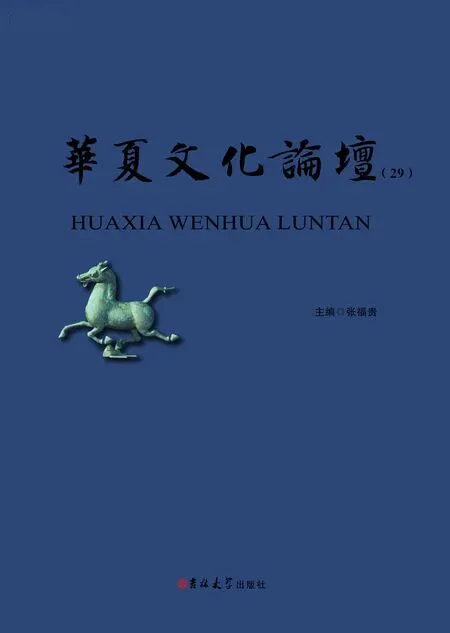论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对日本能剧艺术审美的影响
韩 聃
【内容提要】儒释道思想的融会贯通对日本中世文艺思想的形成给予深远影响。从中日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来看,从日本接受舶来文化并自觉转化形成自己本民族的信仰认同、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的进程来看,禅宗思想在此期间奠定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品格。从日本古典戏剧的艺术理论著作、能剧剧本到舞台表演,均能洞见其深受儒释道艺术精神浸染的痕迹。以儒释道思想对能剧进行审美观照,是理解日本艺术美的又一视角,也是面向日本文艺的一种审美期待。
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对日本中世(12—17世纪)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能剧,在日本称之为“能”,是在室町时代(14—16世纪),脱胎于大和猿乐,经由能剧表演艺术家、理论家世阿弥(1363—1443)的改创,融合日本民间艺能而形成的古典戏剧。世阿弥写就二十几部有关能剧剧本创作、表演理论的书籍,也称之为能乐论书。纵观能乐论书,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意识与盛行在日本中世的歌论相当,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以往世阿弥只被冠以艺术家的称号,实际上,他本人与道元(1200—1253)、岐阳方秀(1363—1424)等禅师有过亲密接触,他们都是习得儒家经典,尊崇程朱理学,精通佛理的僧侣。以儒释道思想对能剧进行审美观照,是理解日本艺术美的又一视角。
一、儒释道思想的浸润:中世艺道思想内涵
从日本中世文艺样式的歌道、书道、连歌道、能乐道以“道”命名来看,日本有将文艺纳入“道”范畴的艺术传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艺道思想。曾有学者评论说,日本精神中的“至诚之心”这一传统观念正是对日本艺道思想的最好诠释。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道与天道一致,人道本于天道。既然诚是天之道,人之道就应该思诚,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存在于人内心的至诚是与“天地之诚”的观念相通的,是以完善人格为初衷的精神体悟。日本中世艺道思想的核心是要通过一种技艺,或是艺术的方式,来传递与天同构的精神体验,并将其视作拯救人类灵魂的希望。①[日]冈崎义惠:美の伝統,東京:宝文館出版株式会社,1969年,第439页。
文艺与“道”相互关联在我国文艺思想框架中自古就占有重要位置。道家视“道”为万物的本源: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②郭庆蕃:《庄子集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6-247页。
在中国哲学中“道”是具有一定先验性质的存在,原本与艺术无涉,但却在文艺观念上反映出以自然为本位的审美判断。如同柏拉图将美视作理念的显现,而老子把美视作“道”的显现,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意表“道”是美的一种根本显现。道家“体道”过程与艺术精神相通,工匠之于技艺与艺术家之于艺术的态度相通。徐复观先生如此解释:“‘道’之与艺术,本是风马牛不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形而上的思辨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功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功夫;他们由功夫所达到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当庄子把它当做人生经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体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日本文论家小西甚一(1915—2007)指出,“道”本有道路、方法和途径的意思,“道”起初从宗教派生出来,后引申为“专门之道”。④[日]能勢朝次:能楽研究,東京:八代印刷株式会社,1952年,第43页。在中国的艺术精神之中,“道”体现在文艺创作与审美精神态度两方面。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对“技”的理解与把握。专注、努力是把握“技”的有效途径。如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虡的故事所折射出的极力摆脱外界干扰、精研技巧,最终追求达到合乎自然的艺术境界。能剧就是以身体“塑型”为根本,锻炼成为一种以静态为美的舞台艺术。能剧演员在舞台上以克服、忍耐、超越自己的身体来拟态表演角色类型。
世阿弥将能剧表演视作能役者(能剧表演者)需经过多年习得才能掌握的、身体的技艺。
高超的演技要通过多年的身心修炼来完成。在舞台上懂得控制住自己的身体,所谓动七分身,就是能够绰有余力、从容地演艺。初习者若忽视这一修炼的过程,直接进入模仿阶段,就只会停留在七分艺①七分艺在此指不尽完备的演艺。的艺境而止步不前。②[日]加藤周一、表章:世阿弥·竹,東京:岩波書店,第162页。
他在能乐论书中借用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中的偈语作为解释: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
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③[日]世阿弥:《风姿花传》,王冬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要求能役者以宗教般敬虔的态度来面对学习技艺这件事,把习艺过程比作修炼身心的修行过程。日本中世的许多艺术家们不单纯为了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为自家艺道的昌隆努力精进,从少年时代开始学艺,就抱有生命有限,艺道无限的信念。④[日]能勢朝次:能楽研究,東京:八代印刷株式会社,1952年,第46页。他们具备超越、克服、忍耐的能力,遵循艺道,磨炼技艺。日本的艺道思想是为了追求主客合一,使文艺能突破具体物质载体,而获得精神上更大的价值。⑤王向远:《道通为一——日本古典文论中的“道”、“艺道”与中国之“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日本艺道思想深受儒释道精神的浸染,包含文艺审美价值判断、艺术家的人格修养功夫以及将艺术视作技艺得以传承的艺术精神。
二、儒释道艺术精神的绽放:世阿弥与能剧艺术之美
在世阿弥的能乐论书中蕴含着东方艺术哲学的思维方式。周易的阴阳说、老子有无相生的辩证法、宋代诗论等思想都曾深刻地影响着世阿弥对能剧艺术的审美规范。
(一)世阿弥与禅宗
世阿弥的艺术理论思想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世阿弥与道元等禅僧的交往是他接受禅宗思想的一大来源。世阿弥从小受连歌师二条良基(1320—1388)的影响,与室町时代以来的贵族学问僧一样具有良好的汉文学功底与学习禅宗、参禅的人生经历。不同之处在于,世阿弥成长在大和猿乐世家,历史赋予他改良大和猿乐的使命。他出身卑微,本是日本民间杂艺的表演者,却与将朱子理学带入日本的著名汉学家禅师岐阳方秀、入宋求佛法的道元禅师有过密切的往来。可以说世阿弥在中世时代是一个身份特别的学问僧。
室町中期歌人、著名连歌师心敬(1406—1475)对世阿弥有过相当高的赞誉,在心敬的心目中,世阿弥之所以伟大,是他能够懂得如何将艺道传承。心敬作为一个连歌师,有其心得:
诸道,都是稽古、功夫于一心。从圣教、格物着眼。修行,以至达到冷暖自知。西行上人曾说:“歌道乃为禅定修行之道。”诚然,入道是为顿悟直路之法。①[日]奥田勲,表章,堀切実,复本一郎校注:連歌論集·能楽论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182页。
尧为圣贤,其子愚。舜为圣贤,其父钝。家业并非都能传递给子孙后代,继承此道之人亦是家人。②[日]奥田勲,表章,堀切実,复本一郎校注:連歌論集·能楽论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194页。
世阿弥在《风姿花传·秘传》篇最后写道:
此《特别篇·秘传》中所述之事,乃“能”这一艺道之大事,亦为吾家一门重中之事,一代只可单传一人。但即使是吾家嫡系子孙,若无此才能,亦勿相传。“家,只有血统的延续并不能称其为家,一门之艺得以相传才成其为家。人,并非生于某艺道名门世家,才能弘扬艺道,只有深知明其道奥秘之人才能成为其道优秀之人。”此秘传,是使“能”演员提高技艺,获名利双收绝妙之“花”之秘传。③[日]世阿弥:《风姿花传》,王冬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世阿弥的能乐论思想与心敬如出一辙,二者都以儒道与禅宗思想论文艺。
在二条良基的《筑波问答》中谈论连歌:“连歌在天竺称作偈,种种经文的偈语也可算作连歌。在唐国称作连句。”④[日]奥田勲,表章,堀切実,复本一郎校注:連歌論集·能楽论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194页。其中对《诗人玉屑》中关于作诗与禅之间的关联深有心得。宋魏庆之所撰《诗人玉屑》共二十卷,成于理宗淳祐年间(1244)。以辑录体的形式,收录选辑了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谈片,其中又以南宋为主。一至十一卷论诗歌艺术、体裁、格律及艺术手法;十二卷之后评论两汉之后的作家作品。八十年后,镰仓末期(1185—1333)传至日本,备受日本歌人的珍爱。在《诗人玉屑》中曾有此评论:“学诗魂似学参禅,要保心传与耳传”,这一点被中世歌人所推崇。二条良基深受此书的影响,在《系蒙抄》《十问最秘抄》等处都引用过此书。歌论、连歌论与禅宗的关系密切,间接影响到世阿弥能乐论创作。歌论、连歌论、能乐论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是日本中世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家思想对能剧艺术美的影响
日语中“能”字的含义出自汉字原意,指才能、能力。从世阿弥用“能”为日本古典戏剧命名来看,能剧这一戏剧形式是非常注重舞台表演的技艺与能力的。日本传统戏剧除了改良日本本土艺能和引进国外戏曲形式以外,在艺术观念上也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日本传统艺能中所传达出的美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艺”最初被指作农耕之事,是人们为解决生存、生活需要所发生的行为,从而形成的特殊才能与本领。在儒家文化渗透之下,与人格修养息息相关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贵族修身所必备的六种技艺。其中的“礼”与 “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样式,因为行礼时须有仪式之美、礼器之美、服饰之美以及仪式进行中的左右周旋、进退俯仰、祷告赞唱,逐渐发展为音乐舞蹈之美。“礼”“乐”之所以与书、数、射、御同列,是因为它们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技艺才能实现。大凡需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去实现的有关物质和精神的创造,都可归入“艺”的范畴。①陈良运:《文与质·艺与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7-148页。
在中国古代六艺中,“礼”“乐”得到特别的重视。《礼记》的《乐记篇》中有:
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其心,油然而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②[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7页。
音乐的本质是能治心,让人生发出朴素、直率、诚实的心,正如泉水涌溢一般。音乐可以陶冶心灵,使之获得安定和快乐。
故乐动于内,礼动于外。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互不争。③[日]今道友信:《东方的美学》,蒋寅等译,林焕平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6页。
音乐令人内心和平,仪礼(典礼)使人外表顺正,人们彼此相处而无猜忌之心,与世无争。音乐与典礼两者齐备,内外相承,可以平顺民心,使世界和平。
在《汉书·艺文志》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之源。”艺术的功用被认定为与天地万物融合,让人的内心宁静与平和。世阿弥在他的能乐论中也谈到了日本艺能演出的功用:
艺能创作之初乃为使人心变得柔和,感动上下,增加福寿。归根到底,诸道都是为其福寿加添。④小宮豐隆,久松潛一,能勢朝次:日本芸能史講話,東京:紫乃故郷舎,1926年,第73页。
能剧与许多日本传统艺能一样担当着陶冶民众性情的作用。
日本的艺能常是与人的教养美紧密相连……茶道、花道等许多日本中世的艺道都是将生活之美外化,以带给人内心充盈与平和作为艺能创作的目的。⑤小宮豐隆,久松潛一,能勢朝次:日本芸能史講話,東京:紫乃故郷舎,1926年,第74页。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艺术的界定是从某种技艺开始,最终上升到艺术审美的高度。这一艺术审美的高度并不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模塑,而是能够创作出“天文”“地文”“人文”兼具的艺术作品,最终让人生发感动之心。日本的神乐、舞乐、猿乐等艺能汇聚,最终被改良的能剧也同样担当陶冶民众性情的作用,欲求把众人之心引向静谧、安详之处。由此可见,日本在艺术审美观念上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正、温柔、敦厚的艺术审美原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日本的古典戏剧以及其他文学艺术领域。
世阿弥重视培养能役者(能剧表演者)的表演技艺,他选用《论语》的语句放置在《游乐习道书》每一段落的开头,为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主张提供根据。世阿弥引用了《论语·子罕》篇:
子曰,苗而不实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①[日]表章、加藤周一:世阿弥·竹,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第163-164页。
《集解》注:
孔安国曰,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育人亦然。②[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89页。
《集注》注:
谷之始生曰苗,吐华曰秀,成谷曰实。盖学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贵自勉也。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0页。
世阿弥用苗—秀—实来比喻演员成才的过程,间接受到日本歌论的影响,实际上是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连歌师心敬曾如此评价:
常语道,在世间迅速博得声名,声名也会瞬间流逝。苗而能秀,秀而能实才是诸道的关键。遵循仁、义、理、智、信,是破万道之理。诸道都有此三位:种、熟、达。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这样理解,不要习得不相称之位,乃是一切要相衬。④[日]奥田勲,表章,堀切実,复本一郎校注:連歌論集·俳論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196页。
在世阿弥内心深处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中,能剧表演是使观众心灵得以净化、灵魂得以救赎的精神之旅。他反复告诫能剧演员的是,台上的表演要依靠台下刻苦的训练,而只有将这一训练过程视作对生命的体悟、修行,才能理解能剧艺术美的真谛。因此,世阿弥格外注重对能剧演员精神品格的塑造,以儒家经典作为培养能剧演员的家训,将艺术的精进态度与反省批判的精神相互融合。
三、儒释道思想的融通:从能剧剧本到能剧舞台艺术的审美原则
(一)《三笑》剧目的由来
《三笑》是能剧现行演出中的一个经典剧目,深受日本观众喜爱。这幕剧是根据“虎溪三笑”的故事创作而成。据说中国晋代高僧慧远禅师(334—416)专心修行,送客从不越过东林寺前的虎溪。但有一次,因与陶渊明(365—427)及庐山简寂观道士陆静修(406—477)畅谈义理,兴犹未尽,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以至于慧远所驯养的老虎马上吼叫警告,三人相顾大笑,欣然道别。经唐宋文人绘图作文,大肆渲染后,影响甚大。这是一出寓意中国接受佛教,与原有的儒道文化相融合的剧目。但据后人考证,慧远去世时,陆静修只不过是十岁孩童,因而此事纯属虚构无疑,只是故事背后隐含的“三教原来是一家”的意味,颇足深思。
佛教于六朝初期传入中国,以长安的罗什门和庐山的慧远一派为中心。佛教的传入为盛行于当时的儒学、经学与庄老思想带来新风。为将这些多元思想融会贯通,慧远禅师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佛法精进,为人谦逊,翻译难解的佛经,阐明蕴含其中的深刻哲理,深得后人敬仰。《高僧传》第六卷这样描述慧远禅师:
见庐峰清净,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①[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2页
宋陈舜俞(1026—1076)在《庐山记》中记述道:
流泉匝寺下入虎溪。昔远师游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合道,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本于此。②[清]永瑢编:文渊阁《四库全书》,2003年影印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85册,第21页上栏。
这就是“虎溪三笑”故事的由来。被众人景仰的慧远禅师及围绕他所发生的“虎溪三笑”故事,被历代僧徒文人所传讲,彰显出在儒、释、道思想多重洗礼下的文人情怀。在《慧远文集》中:
夫神道茫昧,圣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将可见。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凌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便可严下,在此诸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或山居养志,不管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训作范,幸兼内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①[日]木村英一编:『慧远研究』遗文篇,東京:创文社,1960年,第237页。
慧远禅师在千载之后仍被仰慕的原因在于他教化陵夷,为曾一度颓废的佛教界带来新的光辉。按照《高僧传》等史料所记,慧远、陶渊明、陆修静的生卒年考证,“虎溪三笑”的故事应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在《宋书·周续之列传》中载: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②[清]永瑢编:文渊阁《四库全书》,2003年影印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8册,第589页下栏。
三隐是指周续之(377—423),刘遗民(1082—1155)和陶渊明。“虎溪三笑”的故事虽有假作之嫌,但却流传下来,寓意儒、释、道三者合而为一。以慧远为中心,选取年代相隔较近的人物,代表儒家的陶渊明,代表佛家的慧远和信奉道家的陆修静最为合宜。这一故事被后人虚构,至石恪画《三笑图》开始更加广泛流传。
《三笑》这目剧中并未以庐山和欣赏瀑布为背景,而在谣曲(能剧剧本)中引用了李白(701—762)《望庐山瀑布》和曹松(828—903)《天台瀑布》的汉诗来增添作品的情趣。世阿弥论及在创作一些有名胜古迹的剧目时,必须引用与此相关的名歌名句,这样创作的谣曲才会取得成功。基于此,他在《三笑》中完整地引用了《天台瀑布》这首汉诗。舞台上虽然没有庐山和瀑布,却通过能役者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来体现一种情致。看到舞台上的陶渊明,马上会想到属于他的菊与酒,在这曲谣曲中又加入了陶渊明的《饮酒》一诗: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③[清]永瑢编:文渊阁《四库全书》,2003年影印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63册,第493页下栏。
在这首谣曲中,充分体现出汉诗的情趣。在世阿弥所处的时代,欣赏能剧演出的观众大都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贵族和被供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将谣曲的情节段落烂熟于心的,不同于今天欣赏能剧的观众都要拿着谣曲唱词的手册入场。室町时代的观众们大都是先听到能役者和地谣的唱词,然后才观赏在舞台上能役者的装扮演出。世阿弥所言“先闻后见”“最初的妙所乃是曲”在这一曲中最为明显。
(二)能舞台艺术的审美原则
能剧舞台的设计简素,主要由白州(主舞台)和廊桥以及三棵松树组成。唱词的旋律单一,伴奏乐器以鼓为主,加有地谣的伴奏,整个舞台表演的动作都极其缓慢,有停顿。能剧在艺术上追求幽玄的艺术美感。幽玄与物哀是产生于我国老庄哲学的玄妙,又渗入了佛门思想的幽奥,传入日本后演变成为具有民族审美特性的诗性范畴。幽玄一词在《尔雅》中解释为:“浚幽深,浚亦深也”,在《周易·系辞上》有:“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①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3页。“幽玄”一词源自我国道家思想,其义主要在于“玄”字上,“幽”是为了说明“玄”字的性质。“玄”在老子讲道中常被用到,即“玄之又玄”。“玄”被古人注释为“幽远也”“黑色也”“幽深难知”等,于是“幽玄”的最初含义应该是“幽远或幽深难知”。②[日]谷山茂:谷山茂著作集(一),幽玄,東京:角川書店,1992年,第199页。《临济宗》中有“佛法幽玄”也是采幽深难解之意。能剧目大多取材于《平家物语》等中世文学作品,反映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武士阶层的内心世界,常常表现出寂寥、孤独、怀旧、恋慕之意,整场演出呈现出一种含蓄、寂静的美感。
观众如何欣赏能剧演出?在《花镜》中作以论述:
从演“能”成功实例看,可分为,听之成功的“能”、观之成功的“能”、用心体味之成功的“能”三种。……从细微、静谧处加以体会,才会感到“能”的无限生趣,这就是观之成功的“能”。
听之成功的“能”是指有一种“能”是在肃穆、沉稳的气氛中开场的,曲调适中,风格沉静、安详,极富深意。……只有对“能”有自己的理解与把握,在身、心都得以修行完备的基础上才适合于此种类型的“能”的演出。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感到:“怎么会如此有趣?”这是表演者的一个秘诀。
用心体味之成功的“能”是指能演员可以掌握“能”的很多曲目,“能”的各种风体,并在唱腔、舞蹈、演技、对谣曲的理解等诸多方面业已准备精良。所上演的能剧目几乎都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与喜欢。在那静寂、浓厚、低沉、哀婉的谣曲调中带给台下观众以至深的感动。在欣赏“能”的演出过程中,能够鉴别出能剧演员是否用心,这样的鉴赏者才是真正的“能”的鉴赏者。鉴赏的心得是:不曾记得台上演出的样子,只是看到了“能”;不曾记得“能”为何物,只是看到了“能”的表演者;不曾记得是谁在表演“能”,只是看到了表演者的心;不再关注表演者的心,是因为知道“能”为何物。③[日]加藤周一,表章:世阿弥·竹,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第101-104页。
世阿弥将欣赏能剧设定在见、闻、心三个审美维度。留存日本至今有这样一句话“‘能’本不是用眼睛来看,乃是要用心看”,正是回应于此的艺术审美原则。能剧演员的演技功夫体现在身体的控制力上。能剧表演动作单一、迟缓,曲调中没有过多的音律,整个演出中看似缺乏连贯性。这被世阿弥解释为一种“空白”或是“空隙”,而看似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空白是被能剧表演者的绝妙演技所控制的。在静谧处忽然发出一声低沉的谣曲调子,在近在咫尺的一段距离上留下了能剧演员漫长的足踏轨迹,这些都被比作能剧的“魅力之花”。
因此,世阿弥提出观看能剧演出时,不仅要看表演者多年习得的演技功夫,还要体会表演者是否具有统摄外部,控制表演节奏、气氛的多种能力。应该说这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鉴赏理论,在很多地方尚不能用语言精准地阐释,甚至可以说世阿弥将他所改创的能剧舞台艺术视为自身的一种信仰,他所说的“万能绾于一心”之事,就包含着禅定的思想,所以当台下的观众在观看“能”的表演时,是与台上的表演者在心灵上达到会通,共同完成一种冥想的体验。
四、结语
日本自中世时代以降,在狂热学习中国文化之后,进入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是把鲸吞豪取的中国文化细细品第、慢慢消化,从中培植出具有民族特性的政治制度、艺术形态、艺术样式的一个时期。①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姻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为日本中世文艺思想的形成带来深远的影响。从日本古典戏剧理论著作,能剧剧本到舞台表演,均能洞悉深受儒释道艺术精神浸染的痕迹。以儒释道思想对能剧进行审美观照,是理解日本艺术美的又一视角,也成为面向日本文艺的一种审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