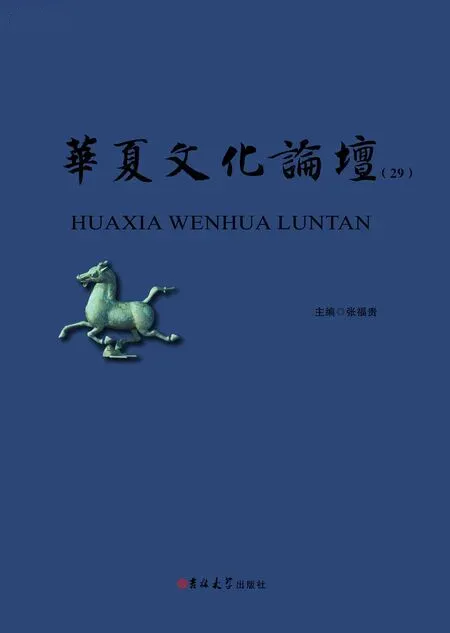茅盾对《新结婚的一对》的翻译与接受
徐晓红
在挪威文学史上比昂松与易卜生齐名,他与易卜生几乎同时被译介到中国,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期间开始关注比昂松,撰写过作家小传,之后又翻译了二幕剧《新结婚的一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文学辞典、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传记、西方戏剧史、世界文学史等著译中,均会提及比昂松的《新结婚的一对》,也有不少知名编辑、剧评家、翻译家做过《新结婚的一对》的短评,由此可见该剧是作为挪威文学经典而被接受的,并引起了国人对女性问题、婚恋问题的一些探讨。但新中国成立以来鲜有人涉足易卜生以外的挪威作家研究,即使在“茅盾与外国文学”的专题研究中,《新结婚的一对》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茅盾的挪威文学译介也只是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框范下被一笔带过。本文聚焦茅盾对《新结婚的一对》的翻译以及同时代评价,尝试对其挪威文学译介与接受的特征做一探讨。
一、茅盾与《新结婚的一对》的翻译
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积极倡导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写实主义文学。茅盾也做出附和,1920年元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①雁冰:《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1月1日。茅盾将此文做了细微的修改,作为《“小说新潮栏”宣言》,刊登于《小说月报》1920年1月第11卷第1号。,指出“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还“用严格的眼光,单注意于艺术方面”,甄选十二位外国作家的三十部作品,作为翻译计划“第一部”。其中列在首位的是比昂松及其两部剧作Newly Married Couple和A Gauntlet,他非常重视比昂松,在为《学生杂志》撰写的《近代戏剧家传》中,首位介绍的也是比昂松。在此所列的比昂松剧作可能是参考了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即推荐译入中国的百部写实派戏剧)。茅盾强调,这是艺术性优先的选目思路,同时指出“翻译研究问题的文学固然是现社会的对症药,新思想宣传的急先锋,却未免单面”,可能他对当时易卜生问题剧翻译扎堆现象颇有微词,因此将不同风格的比昂松放在显著位置给予介绍。
很快,茅盾以身示范,先译出了Newly Married Couple,题为《新结婚的一对》②茅盾的译本并非首译,1920年5月20日至7月8日,周瘦鹃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剧本”栏上曾连载一圭译《新婚夫妇》。茅盾很可能留意到此译本,当时他正向鸳鸯蝴蝶派文学发起强烈的攻击,对周瘦鹃麾下的翻译可能有所不满,便进行了重译。收录《新结婚的一对》的茅盾译《新结婚的一对及其他》,曾作为单行本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但未见出版。茅盾是依据英文转译本进行的翻译,因其所依据的英译本底本信息阙如,无法从翻译的角度对其译文做出评价。,刊载于其主编的《小说月报》革新号上。在《小引》中,他透露出对该剧艺术性的赞赏,写道:“此剧的体裁是很特别的——就是第一幕内所含的意思在第二幕内明白地喊出来,显示一个解决办法。这种体裁在般生那时也许是盛行的,般生一生所著剧本甚多,就艺术价值而说,此篇算得是头挑的了。”他还发表了《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介绍了作家生平及创作历程,比较了比昂松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指出“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本的唯一使命是揭开社会黑幕,指出社会病的根源给我们看,却毫不说到一个补救方法——是只开脉案,不开药方子”,而比昂松“于补救方法一面,也略略讲一点”,例如,《新结婚的一对》“对于这问题的解决法参在中间”,因他“是个大小说家,又是个理想家,所以应用小说的理想来装到戏曲的模子里,也常常带有理想的色彩”。他虽然未对比昂松所开的药方,即“问题的解决法”,做出详细点评,但能窥见他对直面问题的理想主义者比昂松颇有兴趣。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③雁冰:《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1920年9月5日第7卷第9号。一文中,他对易卜生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赞扬其剧作能把社会问题“完全剖解开给人看”,但又指出其缺点是“只开脉卷,不开药方”,使人无法对人生进行“补救诊治”。在茅盾看来,尝试做出“补救诊治”的比昂松,是值得向国人做出介绍的。
不妨对茅盾翻译《新结婚的一对》的动机做一探讨。
从1919年起,茅盾积极介入女性解放问题的理论讨论,在《妇女杂志》及《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等上发表了若干评论、译文。有一篇译作《现在妇女所要求的是什么?》,介绍“脑威虽然只是小小一块地方,而在男女关系上,却做得最公平而且也最早”④戴维斯女士(Margaret Liewelyn Davies)作,四珍译:《妇女杂志》1920年1月5日第6卷第1号。,加上当时媒体很早就对挪威发达的女权做过报道,这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曾介绍比昂松是“第一个创立脑威新戏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倡讨论‘个人权利’和‘个人解放’的人”①雁冰:《近代戏剧家传》,《学生杂志》1919年7月第6卷第7号。,可能早对其戏剧有所涉猎。例如,《新结婚的一对》让不懂“恋爱”的新妇学会了爱,强调了恋爱之于婚姻的重要性;《挑战的手套》抨击双重道德标准,反对要求女性单方面为男性守贞操,这些剧作所反映的思想对茅盾正视婚姻中恋爱因素的重要性、建构两性平等性的道德理论均会有所启发。但当面临翻译对象的选择,即使他从理论层面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但从情感层面而言,他仍会觉得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某些因素还有意义,相比《挑战的手套》中有些激进的女性观,《新结婚的一对》中的女性形象更加符合他的想象性期待,并让他产生了翻译的想法。
另一方面,从作家自身婚恋体验的角度而言,茅盾遵从母命迎娶了不识字的孔家小姐,新婚时期他与妻子的沟通比较困难,产生过对立情绪。《新结婚的一对》中的阿克尔苦恼于如何将罗拉改造成理想的妻子,茅盾可能也有类似的苦恼,首先他要帮助妻子识字,让她接受新文化(最终茅盾将妻子改造成了“新女性”——孔德沚),某种程度上他较容易对剧中人物产生代入感。还有《新结婚的一对》中的妻子、丈夫,在婚姻关系中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依附性,尤其阿克尔是借助了罗拉陪读麦昔尔特的计谋,才成功捕获了爱情,他十分依赖麦昔尔特,即使婚后仍对她有很大的依附性。茅盾性格偏阴柔,对母亲有很大的“依附性”(包括后期在日本避难时,与秦德君的交往中也体现出“依附性”),较容易对该剧男主角产生亲近感。即使当时已有一圭的译文了,但仍不妨碍他做出重译。
二、《新结婚的一对》的同时代评价
比昂松是挪威最早创作社会问题剧的作家,他的戏剧风格迥异于易卜生,茅盾对《新结婚的一对》的翻译,可谓丰富并拓展了国人对西方问题剧的审美视野。正如王统照所言,《小说月报》“介绍挪威写实主义之重要文人般生,以及他所作的独幕剧《新结婚的一对》,在新开辟的文坛上可谓创举”②刘增人:《王统照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9页。王统照所言有误,《新结婚的一对》是二幕剧,并非独幕剧。。当时最早评论《新结婚的一对》的文字见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李石岑称赞该剧“叹为该号中压卷之作”,还大段摘录剧中对话,赞赏“冬芬君译笔,何其体贴人情,恰到好处,至于如是”,并指出“此种材料,于我国今日社会与家庭最黑暗之时,最为适宜。读沈雁冰君《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一文,尤可见般生之主张,足以医我国不自然之社会状态者匪浅”。
实际上茅盾选译该剧是看重其艺术性及戏剧技巧的运用,李石岑的评价侧重于内容方面,有些过誉。虽然茅盾在1920年2月4日,发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补充了“合于我们社会”③沈雁冰:《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2月4日。的选译目标,这似乎意味着他在一个月前提出的优于“艺术角度”的选译取向发生了“松动”,但《新结婚的一对》与“合于我们社会”的选译目标显然有些距离。因循守旧的岳父母向锐意进取的阿克尔做出妥协,表面上是革新派战胜了保守派,但实质上是基督教教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很难说这于当时社会“最为适宜”。茅盾好像也意识到了“艺术角度”与“合于我们社会”之间存在龃龉,因此未对李石岑的评价做出回应。
李石岑在赞赏比昂松理想主义精神这一点上与茅盾保持了一致,他认同比昂松“爱人类”的主张,并指出这对当下社会改革有所助益,这一观点尤为可贵。比昂松重视家庭的和谐,通过独具匠心的情节设置,让新婚夫妇得到外界助力,顺利解决了爱与忠诚、爱与嫉妒、爱与孝道等问题。之后也有人发现了比昂松精神的重要性,例如,马彦祥认为他的创作比较富有人性,对于反抗那些阻碍人类前进的恶势力,实在是很有裨益的,进而指出“一个人能站在国家的生命与命运上而有这样的贡献,是我们所很少见到的”①马彦祥:《戏剧讲座》,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159页。。傅东华在《般生百年诞》的按语中写道:“在现代,在从军阀到革命家一是皆以残酷为本的现代,在报复循环以暴易暴的现代,现实的本身已足够叫我们认识它的厉害,足够叫我们警省,足够叫我们灭却幻想了。我们再用不着易卜生那样严肃的解剖家来警惕我们,来替我们解释现实的可怕,却要般生那样温煦的劝导者来安慰(当然不是欺骗)我们,来指示我们怎样打开现实的桎梏。”傅东华也赞赏作为“劝导者”的比昂松,认为其“打针培补”的工作于当下中国具有指引作用。他还评价《新结婚的一对》“是一部教训主义的喜剧,作者对于剧中每种人物都给他一个功课。做丈夫的必须学习忍耐;做妻子的必须遵守结婚的义务;做朋友的应该助人,不应该妒人;做父母的对于结婚的儿女应该听他们的自由。这样平凡的教训,照理是应该要令人厌恶的,但是般生能够把这种冷的公式温暖起来,因为他的人物都是日常见面的真正人物——他的道德的理想主义是经实际的写实主义调剂过的”②傅东华:《般生百年诞》,《东方杂志》1932年12月16日第29卷第8号。。傅东华并不反感此剧流露的“教训主义”色彩,指出青年男女在婚姻中是需要不断成长的,他的这一评价在当下也不无参考意义。
茅盾翻译的《新结婚的一对》也受到了妇女问题研究者的关注。俞长源在《现代妇女问题剧的三大作家》③俞长源:《现代妇女问题剧的三大作家》,《妇女杂志》1921年7月第7卷第7号。中,将比昂松和易卜生、萧伯纳列为现代妇女问题剧的三大作家,视《新结婚的一对》为“第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杰作”,并对该剧主旨做出了分析,“阿克尔说:‘我们这婚姻不是一个快乐的婚姻,因为缺少了一切东西中最紧要的东西。’罗拉的父亲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答道:‘罗拉不爱我。’这便是此剧显明的主旨”,强调了恋爱之于婚姻的重要性。还有金仲华在《妇女问题的各方面》中,也指出“没有恋爱的虚伪婚姻的悲惨结果,显然是为许多作家所注意的”,他评价《新结婚的一对》是“把一对年青的没有相互了解的夫妇的苦痛情形完全形容了出来”④金仲华:《近世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妇女杂志》1931年7月第17卷第7号。。以上评论为国人探讨婚姻家庭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在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被国人广泛接受的同时,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近代的恋爱观》也备受瞩目。厨川白村对比昂松颇为欣赏,他提出“娜拉已经过时了”,而比昂松的作品正可“补正易卜生的娜拉式的思想”。①“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日]厨川白村著,夏丏尊译:《近代的恋爱观》,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第26页。这一观点可谓向国人打开了《新结婚的一对》批评的新向度。广州戏剧研究所的胡春冰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卞尔生所有一切的特质,恰是与易卜生互为补角”②Dickinson Thomas Herbert作,春冰译:《现代戏剧大纲》,《戏剧》1929年11月15日第4号。。还有人抛开与易卜生在创作上的差距,认为“在技术的成就上,般生的作品却赶不上易卜生的了,也只有这一点称为易卜生较之般生可以夸耀的地方;然而就两人的气质讲起来,我们却应该重视般生”③丁伯骝编:《戏剧欣赏法》,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第106页。。以上评价也可以视为茅盾论比昂松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延展。
三、《创造》与《新结婚的一对》的关联性分析
1928年茅盾发表了短篇小说《创造》,描写了一个“旧”青年用“新”知识改造另一个“旧”青年,却创造出一个“新”青年的故事。茅盾坦言,《创造》是“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④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的。小说结构、人物性格设置等与《新结婚的一对》有很多相通之处。以下对两者的关联性做一探讨,先看《创造》。
大致而言,茅盾对娴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君实是持批判态度的。君实与娴娴身上呈现出“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君实对西方理论不过是一种生吞活剥式的涉猎,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些西方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适性。他们刚结婚时,娴娴被牵手都会脸红,流露出“旧式女子的娇羞的态度”,之后在丈夫的引导下,“出落得活泼又大方”。可以说正是由于娴娴身上的这种可塑性,才让她涌起了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巨大热情。但娴娴对新的思想并无分辨能力,只不过受时代浪潮的裹挟,在对新思想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机械地变得很激进。她并不知道所谓的“女性独立运动”会将自己引向何处,这也让她发出了“后天怎样?自己还不曾梦到”的感慨。娴娴的举动表现出革命运动的复杂性,也暗示了当时尚未形成真正的女性解放的思想基础,她还没有对革命现实做出审视的能力,虽然可被“塑造”,但难以实现自主性的“改造”。貌似她主动选择了投身革命,实际上很可能会陷入另一个旋涡中。
茅盾在塑造娴娴这一女性形象时,旨在凸显“新女性”无畏、独立的精神特质,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娴娴仍未完全抛弃陈腐的思想。娴娴从小受其父亲影响,不关心政治,养成了乐天达观的性格,后受丈夫影响,突然关心起政治,又变成了唯物论者,而且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未见她做出丝毫的抵抗,完全是听从男人的指挥,连她自己也承认“我是驯顺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动,全受了你的影响”。“驯顺”一词如此自然地从她口中吐出,可见她是自甘处于被“驯顺”的地位,而非真正的有自主意识的“新女性”。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娴娴的“依附性”,可以说娴娴一直在选择强势的、有力量的一方进行依附。比如,从最初对父亲的依附,之后对丈夫君实的依附,再到对李小姐背后那股强大的革命力量的依附。她虽然踏出了“出走”的一步,貌似摆脱了对丈夫的依附,但在她走出小家庭,投身于革命思潮洪流后,是否也会习惯性地再追寻下一个力量更强大的一方进行依附,而最终沦为随波逐流的弱势一方呢。这可能是茅盾通过小说的开放性结局留给我们的一个思考。
至于《创造》与《新结婚的一对》的关联性,首先,两部作品中丈夫对妻子身份的认知具有相似性,不能否认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地位的理解上多少都带有大男子主义的一面。君实与阿克尔都认为妻子应当属于丈夫,对妻子有占有欲、控制欲,尤其君实更为明显,他站在启蒙者的地位,欲将娴娴“创造”成理想的妻子。阿克尔对罗拉的态度和行为,实质上也隐含了一种“创造”。他始终将罗拉视为男人的附属物,期望“她的目光必须融化在我的目光里,完全献出自己”,口口声声称罗拉“小仙女”,对她说,“我无论在哪里都要你在我跟前,使我忘忧,引我笑”。阿克尔还对岳父母说:“在此地,罗拉为你们而生活,一旦你们死了,罗拉也完了,这不是结婚的意义。”在阿克尔看来,罗拉结婚就是为了寻找父母之外的下一个依靠,他娶了罗拉,罗拉就应该依附于他,而结束对她贵族父母的依附,他并没有将罗拉视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
其次,两部作品中的妻子身上也呈现出相似的依附性,娴娴与罗拉相比,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自主性,虽然在小说结尾她“出走”了,貌似一种果敢的行为,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摆脱依附性的关系,只不过依附的对象发生了转变。娴娴在依附父亲、依附丈夫这两个阶段,与罗拉并无不同,茅盾又将女性的这种依附性继续向前推了一步,让娴娴“依附”了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新结婚的一对》与《创造》均留下了开放性结局,一个是夫妇和解,一个是妻子出走,而实际上遗留的问题都未得到彻底解决。罗拉对阿克尔涌起了爱意,但并不代表罗拉从此完成了女性成长,成了阿克尔理想的妻子。尤其在麦昔尔特离开后,阿克尔没有了这一“智囊”的指引,他是否会再次与罗拉发生争吵?而摆脱了君实控制下的娴娴,又能否凭借一己之力而生存下去?以上可视为具有连续性的两个问题,即从“女性是否能真正地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发展到“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后的女性将何去何从”。
从《创造》和《新结婚的一对》中,可见两位作家对丈夫眼中理想妻子形象的一些思考,从两位妻子的性格转变中,也可窥见女性自我精神成长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这两部作品关联性最大的是男主人公的“主人意识”,即主导者的男性将女性视为自己的从属者,并要求从属者发自内心地认同主导者。阿克尔在说服罗拉搬离父母时,说道“你总听人说过,从前有一时,男人是他妻的主人,妻是他的附属。如果我欲如何办,你一定要听我,不可听别人”;当他重新赢得罗拉的爱情,向岳父母宣扬“她的眼波必须投进我的目光里,完全降伏”,“她的思想必须拥抱我的思想”,均流露出阿克尔强迫罗拉归顺于他的一种“主人意识”。君实也呈现出类似的思维模式,接受新知识后的娴娴逐渐有了异于君实的理解,而且这是君实无法把控的,他本来希望娴娴可以像吸收新知识前一样认可自己,若不能使娴娴完全认同自己的观念,即便娴娴再怎样示爱,君实都不会好受的,因为他作为主导方的自尊受到了严重打击。无论是阿克尔,还是君实,两人身上的“主人意识”具有相通性,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了作家思想以及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四、结语
以往研究者指出,茅盾是继承和发展了《域外小说集》及《新青年》开创的“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他对挪威文学的翻译,旨在激励人生、警醒国人。但若仔细检阅茅盾的挪威文学译品,可见他更侧重个人审美趣味,重视作品的艺术性,而不是“为人生”的、足救时弊的这一功利性需求,不能简单地将其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做一框范。例如,他对哈姆生的关注就不是遵循写实派作家优先介绍的原则,除了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身份外,如他所言,哈姆生是挪威“新理想主义”代表作家,“是一个智识上的贵族,然而同时又是近代文化的怀疑者”①博耶尔作,佩韦译:《脑威现代文学》,《小说月报》1922年11月第13卷第11号。,唯独不是写实派作家。还有茅盾翻译了他最喜爱的挪威作家包以尔的短篇小说《一队骑马的人》和《卡利奥森在天上》,两篇作品均充满了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他称赏后者是“充满着熙和气氛乐观色彩,而又微感人生无常的诗样的美丽的小品”②《雪人·自序》,茅盾译:《雪人》,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第5页。。正如他所说的,包以尔等挪威现代作家“正恳切地哀求片刻的安息”“只求一个安宁的无忧无虑的日子”③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一三一)《脑威现代文学的精神》,《小说月报》1922年7月第13卷第7号。,这种安于命运、与世无争的文学,显然迥异于茅盾介绍的“总是多表现残酷怨怒等病理的思想”的“被迫害的民族的文学”④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9月第12月第7号。。
“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仅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挪威文学的一种路径,茅盾所偏嗜的挪威文学并不都是“血与泪”“怨与怒”的文学,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来框范其翻译。茅盾对《新结婚的一对》等挪威文学的译介,体现出了译者主体性及多重审美维度,折射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自身的复杂形态。19世纪末挪威文学步入繁盛期,易卜生、比昂松等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又出现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挪威一跃成为文学强国,而且在1905年“瑞挪联盟”解体,挪威成为独立国家,将挪威纳入“弱小民族”“被损害被侮辱者”这一范畴难免有些违和感。其实茅盾在指涉挪威时,一般使用“小民族”或“小国”,他是以其地理区域较小来界定的,并区别使用“弱小民族”“被压迫被侮辱民族”和“小民族”等概念⑤例如,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的《最后一页》上,预告“本刊从第七期起欲特别注意于被侮辱民族的新兴文学和小民族的文学”。查阅第7号,如期译载了比昂松的短篇小说《鹫巢》,他是将挪威置入“小民族”这一概念中的。再如,茅盾辑译《近代文学面面观》的《序》中,介绍“此册内所述,除德奥外,皆为小民族”,并做出了颇为独特的区域划分,“计北欧的四国,丹麦,挪威,冰地和荷兰;中欧的两国,德和奥;南欧的两国,葡萄牙和南斯拉夫;被压迫民族一,犹太”。茅盾在“被压迫民族”中仅列出了犹太,挪威是被视为“小民族”的。,体现出作为翻译家、文论家的严谨。关于这一话题,今后将另备论文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