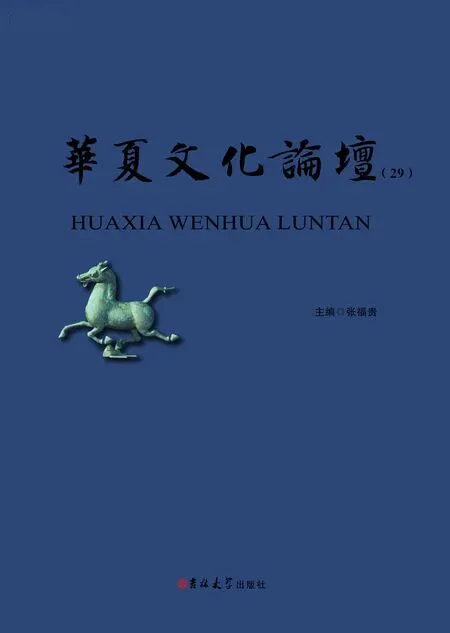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日本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
王 珏
【内容提要】1904年日俄战争至1945年日本战败,20世纪上半叶,众多日本作家来到中国短期游玩或者长期居留,他们笔下的东北叙事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带有强烈殖民意识的书写。直到日本战败后,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中才开始更多地出现对自身殖民意识的反思,表达对反战的诉求。本文以历史文献及作家作品为依据,结合历史学、形象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下,分时段探讨日本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
近代以前,中国农业高度发达且礼仪文化昌盛,日本文人仰慕中国者不在少数,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也多被作家理想化,中国成为日本文人的“乌托邦”。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中国,众多日本作家也来到了中国,他们笔下的东北叙事却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历史背景
丰臣秀吉之后,日本著名布衣学者佐藤信渊,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出发,于1823年提出“宇内混同”论,认为日本身负上天的使命势必要征服邻国,侵略要从中国东北开始,进而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德川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侵略朝鲜,满洲乃至中国,从政治、经济、精神方面来补偿日本屈服于欧美的损失。明治天皇将此“补偿论”奉为最高国策,发布《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明确明治政府的侵略主张。
与此同时,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手工业,英国工业迅猛发展,这也驱使英国资本家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明末清初的中国正在日渐衰落,“天朝大国”早已名存实亡。1840年英国的远征军用战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最终战败并割地赔款。这也刺激了日本的扩张主义者。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①[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60年,第10卷,第240页。转引自王民学:《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古代文明》,2008年第四期。并具体提出率先占领东三省的作战策略,并鼓动士兵进行搜刮抢掠,将金银财宝乃至中国人身上的衣服都带回日本。日本国内侵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惨淡局面,冲淡了日本近代以前文人对中国的“仰慕”之情,扩张主义者对中国的蔑视和跃跃欲试的扩张冲动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不可抗力,这也为日本由东北开始进而占领全中国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来华作家东北叙事的思想根源。
1890年,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在上奏给明治天皇的《外交政略论》中提出,必须将中国划入日本的利益线之内进行防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思想由此正式走上政坛。同时,明治政府也加紧舆论宣传工作,贬低、诋毁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人为激化日中矛盾,鼓动敌对情绪,中日冲突不可避免。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清朝政府的腐败不堪……这一切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动因。1894年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辽东半岛、台湾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东北2万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达6 900万两白银,最终日本夺回辽东半岛,日俄两国分据东北,日本同时取得了安奉路经营权,长吉铁路修筑权以及铁路沿线驻兵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忍辱负重,艰难求存,顽强奋斗,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
二、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
1906年,“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作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创建的殖民统治机关,为了宣传“满铁”的成就和形象,宣扬日本的大陆政策,向日本民众渗透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每年都组织日本的文化人士来华旅游,全程由“满铁”出资,要求作家们回到日本,按照要求创作文学作品,并在“满铁”审核通过后,于日本国内发表。夏目漱石、与谢野晶子夫妇、长与善郎、横光利一等都在邀请之列。他们的作品“如愿”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收到了“满铁”所期望的宣传效果。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作家来华取材,创作出众多文学作品,“像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国木田独步的《爱弟通信》、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等;再现日俄战争的樱井忠温的《肉弹》、芥川龙之介的《将军》、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押川春浪的《海岛冒险奇谭 海底军舰》等不计其数;反映日本侵华战争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的‘御用文人’火野苇平的《粪尿谈》《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林芙美子的《命运之旅》、丹羽文雄《海战》等,另外还包括大量日本作家的游记和殖民体验文学等等”①刘伟:《殖民体验与他者镜像》,《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年,第2期。。不同时期,从军、考察、特派、自费旅行等原因专程来到东北的作家人数也非常庞大:甲午战争中,森鸥外、国木田独步、正冈子规等来到东北;日俄战争前后二叶亭四迷、田山花袋等来到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前后,林芙美子、叶山嘉树、小林秀雄、水上勉、德永直、川端康成、火野苇平等等先后来到东北。这些来华作家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创作出众多以中国东北殖民地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但他们的东北叙事很多都沦为了日本政府大肆鼓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工具。
国木田独步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在日本军部的批准下,作为记者,登上了千代田舰,他在船上的见闻均以家书的形式传回日本,刊登在《国民新闻》上,后以《爱弟通信》为名结集出版。其中曾记载作者在登上千代田舰的当晚,西京丸上的士官拿出一颗未爆炸的炮弹,认为该炮弹之所以击穿船舷而未爆炸,是因为里面的火药被中国军士吃掉了。这样的无稽之谈,在《爱弟通信》中却言之凿凿。该文全篇皆贯穿着如这般对中国民众及军队赤裸裸的蔑视和讥讽。又有樱井忠温于日俄战争时作为松山的步兵旗手来到中国,在他的作品《肉弹》中,描写中国东北人,老头是迷迷糊糊好像没睡醒的样子,小孩则流着长鼻涕,从这家、那家蜂拥而出,像看什么宝贝似的来瞻仰“我”,还有人咬着长烟管咕嘟咕嘟抽着大烟,对中国的处境仿佛一无所知,无知到令人可怜。中国的住宅则污秽不堪,里面的中国人肮脏丑陋,对于“我”这样刚到中国的日本人来说,不捂着鼻子是一刻都呆不下去的。说是宿舍,可实际臭气熏天而且破败不堪,下雨时到处漏雨以致“我”无法入睡。带着大蒜臭味的“大锵小锵”(日本人侮吾国人曰锵锵。盖锵锵者猪尾之谓也。所以诮吾国人之垂辫也。此处云大锵小锵者,盖即大人小孩之谓是也)②[日]樱井忠温:《旅顺实战记》,黄郛译,新学会社,l909年,第26、28页。坐在一起好像一群猪。樱井忠温将中国人比作猪尾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描写日军则是,自从日军来到东北,对民众秋毫未犯,而且还时常加以抚慰,让民众们得以安家立业,故而民众看到日军都拿着美食美酒夹道欢迎。樱井评论中国民众:“彼等皆系抱金钱主意之狗奴具有一种由祖先传来之吝啬根性。所谓要钱不要命(即为金银故,虽生命亦不足惜)之怪性质是也。”③[日]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王成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43、159-160页。树立日军光辉形象的同时,贬损中国人,这种反衬的写法是作家刻意而为,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日本人能够得到自我确认和自我满足。此时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更注重的是按照社会需要对东北进行主观重塑,这个社会需要就是日本殖民意识、侵略思想宣传的需要。
1909年9月时任“满铁”第二任总裁的中村是公邀请同窗好友、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来东北旅游。夏目漱石怀揣着对文明中国的好奇和殖民地宣传的任务,从大连登陆,后经旅顺、奉天等地在东北游玩,并在回国后写成他唯一一部中国游记《满韩漫游》。文中描写第一次见到中国马车,就让人心生反感,“是那种从泥土里挖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后、已经褪色的马车……我等爱好和平之辈乘坐这样的马车已经是受罪。赶车的人当然是清国佬儿,摇动着落满灰尘的油光光的长辫子,不时用满语发出喊叫声。我的眉头皱成了‘八’字,不停地注视着马的屁股。我想到如此鲁莽地把鞭子抽到骨瘦如柴的马身上来取悦乘客的做法和训斥自己的老婆来接待客人的做法同出一辙”①[日]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王成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43、159-160页。。夏目漱石记录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被马车压伤,围观的中国人无动于衷,受伤的老人也面无表情。看到这些,他认为中国人残酷至极,并为自己即将离开中国而感到高兴。《满韩漫游》多处描写东北的肮脏,即使住在豪华的宾馆,享受着美酒美食,夏目仍旧觉得连中国的水都是肮脏的,“喝茶时尝到一种又酸又咸的味道”②[日]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王成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43、159-160页。,洗澡时发现水是浑浊的。夏目漱石描写初到中国下船时看到的景象:“河岸上人头攒动,大都是中国苦力”,觉得“单个人显得很脏,两个人凑在一起仍然难看,如此多的人挤在一起更加不堪入目”。看到有邮轮停靠,“苦力集团就像炸开了的马蜂窝一样,立刻开始吵吵嚷嚷”,以至于他觉得“被突如其来的吵闹吓破了胆”。③[日]夏目漱石:《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王成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43、159-160页。类似的对东北底层劳动人民的描写在当时的日本文学中比比皆是,就连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1925年)中的中国形象也不再是《黄粱梦》《杜子春》中的乌托邦,而是转变为破败不堪、肮脏混乱的中国,他笔下的东北人民也是肮脏丑陋、野蛮贪婪的。芥川刚刚下了船,就被几十个黄包车夫蜂拥围住,“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④[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三)》,陈生保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16页。;还写了有因受伤膝盖像石榴一样炸开的乞丐,浑身溃烂、散发着恶臭,坐在路边伸长舌头舔着自己的腐肉;站在湖心亭向湖里撒尿的中国人;用擦脸毛巾擤鼻涕的中国人……肮脏、丑陋、卑琐是这一时期日本来华作家作品中东北人形象的重要特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自此,日本开始了在经济、政治、文化全方面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日本的来华作家们,绝大多数或参加陆海军报道班,或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文学日趋彻底沦为日本政府宣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工具。这些作家在日本战败后,也不同程度受到了日本政府的追究和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
八木义徳于九一八事变后来到沈阳铁西工业区“满洲理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任职,在华期间文学创作在日本国内的《早稻田文学》上发表。他的小说《刘广福》获得了1944年的芥川奖,小说描写主人公中国工人刘广福,工资最低,干的却是厂里最脏最累的活,但他任劳任怨,无论如何辱骂他,他也总是笑着,当见到厂长日本人时,他会突然严肃庄重起来,向日本人敬一个军礼,表达他对日本人最高的敬意。每当发工资时,他也从不像其他工人那样怨声载道而是毕恭毕敬地敬个礼,再微笑着退出去。八木义徳还写到工人偷盗成性、毫无廉耻心,“对他们(工人)来说,偷盗本身并不是坏事……偷盗,被发现,还回来,这样就可以抵消之前的一切行为”。还写到工厂为了推动文化设施的使用,在工人宿舍安装了冲水马桶,工人们要么依旧在户外方便,要么就因为不会使用致使马桶损坏,之后也依旧去户外。在《刘广福》这部获奖作品中,这种对中国东北人卑躬屈膝、落后卑劣行径的描写还有很多,因为对于殖民者而言,这样的服从者、被改造者才是他们需要的。
日本战败之前,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中,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描写比比皆是,目的是为民众强行灌输一种观念,中国人天生就是肮脏贫穷的“劣等民族”,就应该做着最卑贱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而日本人天生就是圣洁高雅的“优等民族”,就应该享受所有人的尊重,不需要任何理由。这种区别对待在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中也多有记述,比如清冈卓行的成名作《槐花飘香的大连》(1969年)中记载了中日两国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日本人的街区干净整洁、绿树成荫,每年的五月,大连的南山麓路两旁槐花树如约盛开,馥郁芳香的槐花香沁人心脾,弥漫在整个街区,是“东洋的小巴黎”;而中国人的街区则是阴暗闭塞、破烂不堪、窝棚摇摇欲坠,让日本人感到恐怖而肮脏。清水良江也曾描写沈阳“除了(铁西)社区所雇佣的中国人居住的是几间简陋的土屋以外,这附近都是整齐又奢华的住宅”。对于这样显著的差异化,石堂清伦表述得非常精辟:“不管是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让你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无论在工资方面,还是在住宅方面有如此之差距,是因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先天性差异造成的——这是殖民地统治的重要诀窍之一。”①[日]石堂清倫:大連の日本人引揚の記録,東京:青木書店,1997年,第74页。转引自柴红梅、郭丹、金慧莲:《沈阳题材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日本人在中国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而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却是粗鄙不堪的下等人。保尔·利科解释说:“当意识形态描述被某一种特定社会的权利体系所吸引时,掩饰的功能确实超越了整合的功能。事实上,一切权利都竭力使自己合法化。”②[法]保尔·利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57页。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其实质是被日本的权力体系吸引,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的宣传工具,作为殖民地统治的“重要诀窍”,丑化的中国东北形象更容易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和敌对情绪,如此一来,日本政府也更容易赢得民众对于发动侵华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舆论上的支持。同时,反衬之下,日本人的优越感、自豪感也令更多的日本民众冲昏头脑,让他们乃至国际社会更加认可侵华战争的“正义性”,即帮助中国东北建立“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而现实诚如森鸥外在《辽阳》中写的那样:“今に今こそは 作戦の/ひろげし網を 志ぼりつつ/かの北溟のおほ魚を/とるべき時の 来ぬるなれ”③[日]森鸥外:うた日記,埼玉県立久喜図書館,1971年。(中国东北只是日俄网下的“北冥之鱼”,列强瓜分的对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已。)还有日本早期的无产阶级作家中西伊之助,将在大连看到的景象写进长篇小说《槐树荫》中,隐晦地揭露了日本殖民者的本质:“我要把我发现的真理告诉世人,那就是只有贫穷,才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何以作威作福,中国人为什么就要穷困潦倒、卑躬屈膝,忍受日本残酷的剥削和殖民统治。这些也被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记录在了作品中,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日本文坛,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以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照,进行着不同的东北叙事。牛岛春子的《姓祝的男人》获得了芥川奖提名,其中描写了一位比日本人还西化的中国人,他英明果敢、雷厉风行、言辞犀利,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满系不曾有的严厉和果敢……这似乎完全类似于雷厉风行的日本人”的优秀中国东北人形象。虽然作者的描写仍带有很强的蔑视,但祝的出现仍然打破了固有的中国东北人形象,作品的提名,让更多日本民众知道,还有不一样的中国人,这一意义可能超过了作品本身。
三、1945年日本战败后
日本战败以后,日本文学不再肩负殖民统治的使命,作品中,殖民意识逐渐衰退,开始显露出了中国东北真实的模样。清水良江并不是一位职业作家,日本侵略中国时,她随丈夫一同来到东北,日本战败后返迁回日本。在她的小说《大陆上的小家庭》中描写了她在沈阳等待返迁时的经历,在她以往的印象中,八路军是被日本人厌烦和提防的,他们是带着白色兽皮帽子,扛着抗日大旗的“红鬼”。可当几名八路军战士来到她家时,她的印象大为改观。八路军很有礼貌,请求“我”帮忙给首长做饭,却自带食材锅具,还自己在院里支起炉灶;他们亲切友好,询问“我”的生活情况,甚至在做好之后还将饭菜分给“我”,让“我”给孩子们换换口味,就当作帮忙的费用了。隔日早上,士兵来归还餐具时还送了“我”满满一碗白米饭,这使得清水“时隔许久再次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性的温暖”。松下满连子也是曾经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二代日本人,在她的小说《再见·大连》中描写了郭君、郑士兵、刘君、仁凤小姐等中国青年,她发现中国也有与日本人一样,懂得人情世故、有正义感、内心丰富的人,但为什么一直以来日本人都不曾看到呢,她分析,是因为日本人自我搭建起的“优越感”成为阻隔。松下满连子和清水良江一样,虽然一直生活在中国东北,但他们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日本人居住区,以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被日本政府严格把控的,看到的文学作品也渗透着强烈的殖民意识,尽是对中国人的贬低和诋毁。当他们脱离日本人居住区,才真正接触到中国和中国人,才发现,中国人是和日本人一样的人,有血有肉而且不乏优秀者,一刹那他们一直以来看到的日本文学就变成了满纸的荒唐言。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我们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回望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北的真实现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战败以前的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也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此时绝大多数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是基于日本作家有目的的殖民体验的,是建立在宗主国优越感之上的,带有强烈殖民意识的写作,是日本政府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呈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有目的的形象塑造,其目的就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殖民行径寻找合理化的理由,以及向世界证明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而到了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文坛也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此时来华作家的东北叙事更多地反映作家对战争的反思和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