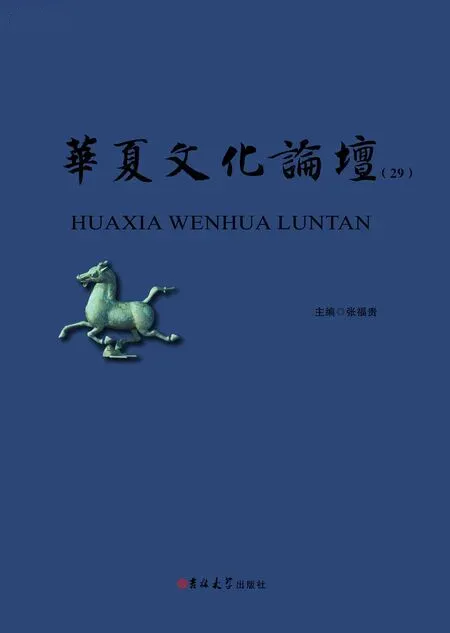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死之棘》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创伤记忆书写
宿久高 张景荣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也是文学恒久的话题。家庭题材小说不同于战争题材、历史题材等抽象性、观念性的宏大叙事,而是将视角凝聚于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事件,以家庭的日常起居、风俗习惯、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内容为主要叙事元素。关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文学书写并不拘泥于衣食住行等细微的生活琐事,作者关注更多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基于爱情和血缘的伦理关系、伦理困惑,意欲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感悟生活的真实和生命的价值。
在战后的日本文坛,活跃着一个善于书写家庭日常生活的作家群体——“第三新人”。他们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汲取创作素材,将视线投向日本家庭的生存境遇和人际关系,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创作了多部以夫妻、亲子关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死之棘》是“第三新人”代表作家岛尾敏雄基于个人的婚姻生活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对曾经在战争中生死与共的夫妻,在战后平凡的生活中由于他者的介入而婚姻破裂,最终导致家庭瓦解的生活悲剧。岛尾敏雄立足于叙述家庭中的人际交往、行为活动、空间建构等日常生活全貌,揭示了战后日本家庭的伦理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以“第三新人”即物性、日常性的文学书写方式讲述了一部“家庭的战后史”。
一、日常生活的空间隐喻
作为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象之下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原理。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生存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①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日常生活是以人为本位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人类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依托,重复性、习惯性、稳定性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属性。家庭是以血缘和夫妻之间的天然情感为前提构成的社会基本单位,涉及家庭成员的饮食起居、行旅休闲等日常生活行为,彼此之间或者与他人的日常人际交往,以及家庭长年积累的生活经验、传统、习俗等日常观念。因此,家庭是人类日常生活集中体现的领域,在重复性实践过程中建立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作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家”既是家庭成员居住和从事日常活动的物理场所,也是集中体现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场域。家庭需要相对封闭的空间为基本保障,用于满足家庭成员对稳定性、安全性和私密性的心理需求。在家庭题材小说中,“家”的空间性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以厨房、抽屉、阁楼、庭院为代表的局部空间通常被作家赋予特殊的隐喻色彩。岛尾敏雄在小说《死之棘》的开篇,便介绍了主人公敏雄一家四口的寓所——东京郊外一处和式房屋。在这处简陋的房屋里,妻子因无意间翻看丈夫的日记而得知其婚姻出轨。持续三天无休止的盘问使妻子变得狂躁和偏执,一定要让丈夫拿出来“爱的证明”,由此引发了疾风暴雨般的家庭危机。家庭空间内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息,狭小拥挤的房间、阴暗昏黄的灯光、歪倒倾斜的书柜、墨汁喷溅的墙壁,这一切均暗示了一场家庭风波即将来临。
“家”是居住者生存的客观环境,也是异于公共领域的私人内部空间。在家庭之内,丈夫、妻子和子女是紧密连接的生存共同体;家庭之外却是充满诱惑和未知的危险地带,区分“内”与“外”的界限便是庭院内的墙垣。“日本传统式住宅的内部是自给自足式的,然而有着严整的秩序,以家族为中心围以墙垣来保持‘内部秩序’。”②[日]芦原义信:《外部空间设计》,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死之棘》中出现了多处关于墙垣的描写。作为生活空间的标记,墙垣不仅圈定了敏雄一家的私人领域,也从主观意识上将外部与内部、公共与个体、他者与自我建构成相互对立的关系。如果说被砌起的墙垣是家庭成员警惕和防范外界事物的象征,那么,其残破不堪的状态即可视为家庭危机的征兆。
除了家庭内部与家庭外部的界限,墙垣也是区分性别话语空间的象征。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外部的公共领域多为男性主导的权力空间,男性将社会当作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舞台。相比之下,“与‘公’相对的‘私’的领域,首先是家庭与家属,这几乎是被赋予了法律地位的女性的唯一领域”①[日]水田宗子:《逃向女人及逃避女人》,《女性的自我与表现》,吴小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已婚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依旧活跃在社会领域,不得不被约束在家庭的私领域和“贤妻良母”的身份之中。《死之棘》中的女性人物美穗安于本分地守护着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庭;而丈夫却以工作为借口终日不归,甚至为了疏解烦闷而与其他女性有染。在某种程度上,墙垣内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暴露了日本社会性别分工的弊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成了男性推卸和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以及抹杀近代女性追求独立自主权利的工具。小说中令人悲悯可怜的妻子正是战后日本家庭主妇形象的缩影,其凄惨的命运揭示了残酷的生活现实和社会偏见,不禁引发了人们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伦理状况的强烈批判。
“住宅空间中被分离的‘表’与‘里’这两个领域,在都市空间里变换成日常世界与非日常世界的对立构造。”②[日]前田爱:《都市空间中的文学》,东京:筑摩书房,1984年,第52页。此处引文原文为日语,译文为笔者自译。后文日语引文同为笔者自译,不再另注。对于小说中的妻子而言,无微不至地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是她曾经全部的日常生活,丈夫流连忘返的外部环境则代表着威胁家庭安全的非日常世界。然而,自从遭到强烈的精神打击,妻子对日常和非日常的观念认知发生了改变。在家庭之外,妻子从不轻易发作,总是表现得大方得体,有意在众人面前树立和谐美满的家庭形象。然而,回家之后,敏感多疑的美穗不停地逼问、嘲讽、指责和谩骂丈夫,把原本正常的家庭颠覆为异化状态的修罗场。归根结底,日常世界和非日常世界的区别并不取决于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是居住者的心理意识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丈夫的情感逆转和夫妻关系的恶化扰乱了妻子对日常生活的判断,使她本能地排斥和丈夫相处在同一空间,因此其在家庭内外的行为举止便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面对妻子的质问和仇视,无法逃避伦理道德谴责的敏雄选择重新回归家庭,恳请妻子忘记过去,同时将重建家庭的希望寄托于生活空间的改造。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修复破碎的家庭关系,唤醒神志不清的妻子。在经历一系列家庭风波之后,夫妻二人动手翻新了围栏,粉刷上清洁明亮的白色油漆,以此表达了重建家庭的美好祈愿。“有时候我们只要把房间里面的几件陈设重新布置一下,就可能会感到舒适。有时候则也许需要对房间进行很大的改动。但有时也许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我们不得不迁出这个房间,因为它基本上是跟我们内心格格不入的。”③[美]伊利尔·沙里宁:《形式的探索——一条处理艺术问题的基本途径》,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当修复家庭关系的希望破灭之后,敏雄再也无法忍受妻子的精神折磨,决定改变现有生活环境,搬回到位于东北农村的故乡。他希望借助大自然的生命力来治愈妻子的精神疾病,也试图让迷失方向的自己重拾信心。
在小说《死之棘》中,岛尾敏雄捕捉到人物希望通过改善居住空间来拯救家庭的迫切心理,将家庭危机书写与空间叙事巧妙地融为一体。“在日本作家中,岛尾或许是对生活空间最敏感的一位。他深入探求熟悉的空间和适应的空间,即使是百万分之一的不协调,也会敏感地做出反应。”①[日]奥野健男:《文学的原景象》,东京:集英社,1972年,第19页。岛尾敏雄利用空间描写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也将局部空间的隐喻作用发挥到极致。挂在门口的邮箱、快速转动的电表、拥挤不堪的厨房、污浊晦气的水井,空间视域下“家”的脏乱、失灵、神秘、禁忌等外化表征体现了家庭危机的浸入和恶化,暗示了家庭人际关系的失调和家庭成员异化扭曲的心像。
“如果说日常交往世界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编织而成的狭小而封闭的网络,那么亲情、爱情和友情则构成了日常情感交流世界的三个最稳定的支撑点。”②贺苗:《日常交往与日常思维的生成》,载丁立群主编《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9页。尽管空间视域下的家庭危机相继发生,但日常生活的叙事主线始终贯穿于小说的文本之中。岛尾敏雄通过描写饮食起居、风土习俗、子女入学等日常生活细节,讲述了平凡家庭生活中朴实的爱情与亲情。这些生活片段再现了家庭生活样貌,调节了紧张、凝重的生活氛围,表现出主人公对回归正常生活的渴望。此时的家庭生活空间依旧简陋如初,却充满了无尽的温馨、和谐、欢愉和感动。因此,日常生活之中既饱含着温暖与安定,也潜藏着惶恐与不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空间维度,被居住者敏锐地察觉或者有意地忽略。然而,家庭危机的解决并不取决于生活空间的改变,多次的住所迁移未必能够化解家庭的内部矛盾,失衡的家庭伦理关系和主人公的精神缺失则会使家庭呈现出异化的趋势。
二、异化日常的伦理呈现
“日常生活的特点其实是噩梦和希望并存,黑暗和光明与共,一如王安忆旧时上海弄堂景观的描写。”③陆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5-6页。日常生活并非一直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也会产生异化反应。异化本义泛指“分离、疏远、陌生化”④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第74页。,既是哲学、社会学、翻译学等领域的抽象概念,也广泛存在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现代消费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物欲追求、权力争夺和道德沦丧等问题,都是异化侵入日常生活的表现。家庭日常生活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伦理维度,尤其当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与家庭伦理准则、社会道德规范无法调和时,伦理冲突、伦理困境等异化特征便显露出来。
“‘家’的伦理意义在于它的工具价值,‘家庭’的伦理意义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因此,如果说‘家’和‘家庭’都是伦理精神实体,它们所内含的伦理精神就是‘爱’。”⑤向玉乔:《家庭伦理与家庭道德记忆》,《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82页。“爱”是家庭成立的条件和持续的动力,然而,当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荡然无存时,伦理关系的紧张就会使家庭面临巨大的考验。《死之棘》讲述的是家庭主妇得知丈夫婚内出轨之后,精神走向崩溃的家庭伦理悲剧。曾经的南岛少女美穗依依不舍地告别故乡的亲人,不远千里跟随丈夫来到陌生的城市生活,却遭遇了丈夫的无情背叛。一直将丈夫视为崇拜对象的美穗丧失了人生信仰,以仇视的目光和犀利的言语宣泄着内心的愤怒与无奈。面对妻子的诘问和指责,敏雄为自己的利己主义行为感到自责,忏悔地恳求对方原谅,并承诺今后会对她言听计从,以此弥补对妻子造成的伤害。然而,在妻子的逼问和一系列行为的刺激下,敏雄极力遮掩的心理伤疤不断地被揭起,疲劳、空虚、耻辱与孤独令他的精神状况也出现了异常。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产生了双向作用效果,如同首尾咬合的两条蛇一般,相互伤害的同时也被摧残得体无完肤。
家庭社会学认为,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与家庭和谐的关键。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将夫妻结合为彼此信任、平等的命运共同体,也使婚姻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显然,他者的介入导致夫妇感情产生了裂变,丧失了对彼此的信任,同时脱离了原本的家长身份。“如果家庭成员不能彼此承担重要的角色义务,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①[美]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08页。敏雄与美穗之间的伦理冲突无疑是破坏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因素,疏远、破裂的婚姻关系也同时引发了敏雄夫妇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冲突,稳定的家庭结构遭受到全面破坏。《死之棘》中描写的家庭危机正是家庭成员人际关系紧张的结果,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家庭伦理濒临解体的社会现实。
当妻子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时,主治医师以第三人称视角一语道破了妻子发病的原因:身为独生女的妻子自幼就没有学习过如何处理嫉妒、憎恶等不良情绪,由此陷入了应当原谅还是憎恨的为难处境,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她强迫自己抑制内心的情感。事实上,偶然发现丈夫出轨只是妻子精神失常的诱因,而真正令其烦恼的则是应否原谅对方的心理纠葛。当疾病发作时,她会毫不留情地痛斥丈夫自私懦弱的性格,咄咄逼人地挑战对方的心理承受底线;但在恢复正常之后,又开始反思自己的鲁莽行为,怜悯地乞求丈夫原谅自己。妻子在精神正常和异常状态下判若两人的表现反映了其激烈的思想波动,以及试图突破困境却又难以找到出口的心理迷失。
众所周知,《死之棘》是岛尾敏雄基于切身生活经历改写的一部私小说作品,小说中妻子形象的原型正是岛尾敏雄夫人大平美穗。大平美穗出生于远离日本本土的一座岛屿,在与海军军官岛尾敏雄邂逅之后,便放弃了自由舒适的生活,跟随丈夫离开故乡,婚后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在《死之棘》中,岛尾敏雄虽然没有直接描述这段往昔的生活经历,但从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中不难察觉,婚前的岛上生活对岛尾夫妇带来极大影响,这也是促使他们决心重返该岛的主要原因。
命运截然不同的二人因为爱情而步入婚姻,但在夫妻伦理关系中包含了更为复杂抽象的关系。“丈夫和情人都是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妻子则是古代人。因为她是一个不知道怀疑的古代自然人,也是深信宿命这种绝对的情感牵绊把自己与丈夫联结在一起的通灵者。况且在妻子的眼中,丈夫并不是普通的具有小市民性的近代知识分子,他是为了守护故乡岛屿而从彼岸的本土渡海而来的邪神和稀客。”②[日]奥野健男:《岛尾敏雄》,东京:泰流社,1977年,第95页。“近代”与“古代”、“知识分子”与“自然人”象征着夫妻二人对立的个体身份,他们正是被彼此独特的气质吸引而萌生了爱情。然而,这也成为家庭伦理危机产生的根源,悬殊的身份差异为家庭矛盾的激化留下隐患。在婚后,美穗与敏雄之间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悄然发生了改变。
“稀客”是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折口信夫提出的民俗学概念,意指从大海彼岸的异乡定期来访,为人们祈福之后离开的神灵,用来形容被派遣到海岛驻守的岛尾敏雄恰如其分。他是给岛民们带来安全感的守护之神,也是完成使命之后势必离去的他者。相比之下,少女时期的美穗自幼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是深受村民爱戴并被赋予神职的“通灵者”。然而,与“来访者”的恋爱注定使其遭遇前所未有的磨难,这在《死之棘》的叙事情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美穗甘愿放弃“通灵者”的特殊身份,成为“无法感知神通力与解放感的渺小都市生活者的‘妻子’”①[日]吉本隆明:《岛尾敏雄》,东京:筑摩书房,1990年,第86页。;另一方面,她为家庭付出一切却因被丈夫厌恶而丧失自我,受到了婚姻失败带来的精神打击。从淳朴自然的海岛来到日本本土的都市,美穗在努力适应家庭主妇新身份的同时,强烈地感受到近代都市文明带来的文化冲击。不知所措的她只能把丈夫当作唯一值得信赖的对象,却不知不觉地舍弃了自我的独立和完整。相反,丈夫却从“稀客”摇身变成了家庭的主宰者,随心所欲地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显而易见,妻子原本的主体身份被丈夫取代,夫妇非对称的身份关系中夹杂着古代与近代、自然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可调和的矛盾动摇了婚姻基础,致使家庭在外界条件的诱发下被破坏,妻子也因此罹患了文化冲击导致的精神障碍。
归根结底,家庭伦理道德解体的表象之下掩饰的是人际关系的紧张,更是异文化冲突带来的家庭悲剧,家庭日常生活的异变必然伴生出家庭成员的异化心理。倘若将婚姻危机视为显性的非日常现象,那么人物抑郁纠结的心理状态则是隐性的异化表现。妻子在离开故乡、身份转变和婚姻变故等事件的刺激下变得神志错乱,敏雄则是因为曾经的战争经历而无法融入战后的日常生活。在日常与非日常、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中,已婚中年男人颓废无力的弱者形象跃然纸上,无法拭去的精神创伤和文化记忆导致家庭陷入了瓦解危机。
三、被日常生活不时唤醒的创伤记忆
《死之棘》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值日本从战后经济复苏过渡到高速增长的时期。尽管日本自此进入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战争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尽,颓废的情绪与幻灭的梦想依然是这个时代的象征符号。小说的主人公敏雄是生活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在他人眼中看似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堪回首的战争创伤记忆。
重复、闪回和幻想是创伤的主要症状,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在外界事物的刺激下总会突然闪现在敏雄的幻觉和潜意识之中。当被妻子要求泼冷水的时候,他会猛然想起服役期间殴打下级士兵的经历;当修葺一新的白色墙垣映入眼帘时,会不禁联想到手持武器与家人共同守护家园的场面。望着妻子跪在地上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双脚一边痛苦流泪的神情,敏雄尘封已久的记忆被瞬间唤起,眼前浮现出在海军基地执行任务期间,少女模样的美穗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军靴的情形。触景生情的敏雄不知道为何在“战败后沸腾的社会喧嚣声中”①[日]岛尾敏雄:《死之棘》,东京:新潮社,1978年,第49页。,自己与妻子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屈辱与不安始终萦绕在心头。
如前文所述,主人公孤独颓废的心理映射了从战场上侥幸生还的岛尾敏雄本人的真实心境。1943年,26岁的岛尾敏雄从九州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加入旅顺海军预备生培训部,此后成为一名海军特攻队队员,并于1944年11月被派遣到一个日本海军基地当指挥官。在岛上生活的村民因日本海军舰队的到来而看到了生存希望,坚信在岛尾队长的守护下必能躲过战争灾难。然而,岛尾敏雄无力扭转战局,在接到特攻出击命令的三日后便收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如果没有出发,那天会和往常一样别无变化。一年半以来,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最终在八月十三日傍晚接到了防备队司令官发出的特攻战行动指令,被告知死期即将到来,身心也都穿戴好死亡的装束。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出击的指令,在等待中逼近的死亡猛然停止了脚步。”②[日]岛尾敏雄:《出发终未到来》,载《对妻子的祈祷——岛尾敏雄作品集》,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6年,第100页。这是岛尾敏雄在小说《出发终未到来》的开篇处对这段切身经历的描述。自从加入海军特攻队以来,无数次接近死亡的岛尾敏雄深陷罪恶、不安与耻辱之中,也常常因为与下属之间的人际关系感到恐惧。虽然他侥幸地生存下来,却因突如其来的事实而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从令人敬仰的守护神到一败涂地的退伍军官,身份的转换使他感到世间的变化无常和社会集团中个体存在的微不足道,强烈的无力感和虚脱感频频向他袭来。
“我将自己的宿命偏离了以往认真行进的方向和轨道,任放手的宿命远离自己而置之不理,为此而感到灼热疼痛。宿命转过身来,歪着嘴大喊着背叛、背叛。”③[日]岛尾敏雄:《死之棘》,东京:新潮社,1978年,第13页。“放手的宿命”是指岛尾敏雄不战而败的人生经历,命运玩笑般地让他偏离了既往的人生轨道,狼狈地离开了战场。对岛尾敏雄为代表的“第三新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经历无疑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是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度过青春岁月的一代人,战争不但为“第三新人”带来了肉体伤痛,更作为一种创伤记忆被根植于脑海深处。岛尾敏雄与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等“第三新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在战争中体会到了丧失亲人的彻骨之痛,也饱尝到了社会集团对个体的约束和限制,更为丧失理想和精神信仰而痛苦万般。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数以自我为原型,是丧失理想和人生目标的小人物。
在日本战败之后,岛尾敏雄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归到循规蹈矩的家庭日常生活。然而,他因严重的精神创伤而萎靡不振,总是试图寻找外界的物欲刺激来逃避现实。这种空虚的精神状态是创伤应激障碍的表征,也是导致夫妻关系失和的罪魁祸首。因遭遇战争创伤而带着不健全心理步入家庭生活的敏雄,其种种行为注定为家庭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死之棘》中,作者利用多种叙事手法来表现人物起伏的异化心理。红色、黄色、黑色等视觉冲击强烈的色彩配比,机器轰鸣声、人群喧嚣声等听觉效果的呈现,以及对主人公身上散发气味的描述,感官叙事描写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敏雄焦躁苦闷和自我厌恶的内心情绪。除此之外,作者不惜笔墨地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从对家庭的忏悔内疚到自我的空虚迷茫,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和冗杂的饶舌体句式,逼真地还原了主人公失序、跌宕的异化心理。
《死之棘》中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揭露与忏悔意识,这一点从小说的题名可见一斑。“死之棘”出自《新约圣经》第十五章,其内容大意为:死的荆棘被视为罪的表现,若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死的毒钩将永远无法奏效,人类惧怕死亡是源于良知驱动之下对罪的忏悔。当人类的思想与行为违背或逾越伦理道德、规律准则时便会面临罪罚,而罪的最大代价即为死亡。唯有诚恳地忏悔才能减轻与生俱来的原罪,从而拯救堕落的自我。在日本战败之后,苟且偷生的敏雄因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屈辱的文化记忆而背负着强烈的罪恶感,他始终无法与自我和解,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烦闷。然而,妻子的歇斯底里令他幡然醒悟,对自己的软弱和颓废深感厌恶,也痛彻地认识到曾经的自私行径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因此心甘情愿地接受妻子的精神惩罚。敏雄是数十万步入战后日常生活的士兵的缩影,是被时代烙下印记的真实个体存在。他因战后生活的巨变而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将自我封闭在狭隘的个人世界,也因家庭风波的来袭而深感自责和忏悔。面对神志失常的妻子和岌岌可危的家庭,敏雄在怀疑和徘徊之中选择了家庭,陪伴妻子共同面对挑战,这也成为他实现自我救赎的最佳方式。
除了情感羁绊下的家庭共生,对当年的海岛生活的追忆和憧憬是敏雄夫妇疗愈精神创伤的另一路径。岛上质朴的方言、神秘的习俗、古老的歌谣与浓厚的乡情,都成为夫妇难以割舍的精神羁绊与心灵慰藉。该岛是他们爱情萌发的原点,也必将成为修复家庭关系的命运归宿。回归美惠故乡小岛的诉求寄托了人物渴望摆脱困境的意愿,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无限憧憬。或许只有在自然、乡土与爱情的感召之下释怀过往经历,重拾生活信心,才能使精神创伤得以疗愈。
岛尾敏雄的文学创作中包括三个主题词:梦境、战争、家庭。毋庸置疑,《死之棘》是岛尾敏雄家庭主题文学的扛鼎之作,也是“病妻小说”系列的代表作品。作者以朴素平实的笔触描述着日本家庭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同时以夫妻、亲子之间的日常交往和情感发展为线索,真实地反映了现代家庭中异化的伦理关系和个体心理。在现实与幻想、回忆交织的跨时空叙事中,岛尾敏雄把“日常”和“非日常”巧妙地融为一体,深刻揭示了战后日本家庭的伦理危机和个人心理危机。
日常性是岛尾敏雄等日本“第三新人”文学的主要叙事特征。从极限状态下平凡人物的日常表现到战后家庭的日常生活,“第三新人”习惯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感动,以作家各自的生活经历为底色,在平淡的现实中感受生活的意义。曾经在战场上直面生死的“第三新人”出于对社会和他人的不信任,本能地选择躲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从底部观察社会与人生的视角。而岛尾敏雄似乎比其他作家更善于洞察和感受生活,他以日记的形式将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期间发生的家庭风波详尽地记录下来。这成为其日后创作《死之棘》的主要素材,同时也奠定了该小说日常生活叙事的主题基调。
然而,家庭的日常生活并非只是重复与平淡,也隐藏着惶恐与不安。岛尾敏雄的日常书写不是在事无巨细地做家庭生活记录,而是通过讲述灰色基调的市民生活,在不同时空和日常情境中体验生活的真实与瑕疵,探求人类生存的价值,并借此疗治因战败经历而遭受的精神重创。这既是岛尾敏雄《死之棘》日常生活叙事的意义所在,也体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家庭题材小说的文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