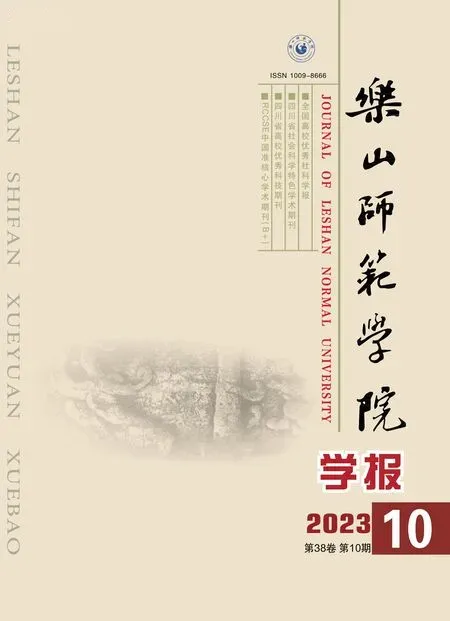无偿法律行为行为人的权利研究
——以赠与人权利为对照
杨 棋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91)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无偿法律行为的规定,最为全面而详细的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规定的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中,基于赠与的特殊性,立法规定了一系列赠与人的权利以平衡赠与双方的权利义务。但立法并未规定其他的无偿合同是否可以参照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并且无偿行为不仅包含无偿合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众多的无偿法律行为,例如债务免除、以赠与为目的的债务加入,给予赠与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等。对于这些无偿行为,是否允许行为人参照适用赠与人的权利,实践中各法院的看法不一。
(一)债务免除
2018 年10 月,江苏省宏玮大酒店与张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2018 年11 月到2019 年3 月30 日免收张某租金。2019 年2 月,张某停止经营酒吧,并向宏玮酒店提出解除租赁合同。二审法院在确定宏玮酒店的损失数额时,认为,租赁合同中关于出租人免除承租人租期债务的性质应当属于附义务的赠与,由于承租人解除合同,出租人期待得到的利益落空,因此出租人可以撤销赠与。①
但在另一件债务免除的案件中,法院有不同的看法。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件当事人以赠与为由要求撤销债务免除行为时,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91 条的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基于债务免除行为消灭,并不存在可以撤销的内容,因此驳回了当事人的请求。②
(二)第三人利益合同
第三人利益合同并不是一种合同类型,而是合同的当事人约定,使第三人可以享有合同上的给付请求权,原则上来看,任何类型的合同均可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1]实务中存在大量构成第三人利益合同,但当事人事后主张其为第三人设定的权利属于赠与,并主张赠与撤销的案例。这类案例最常见的便是夫妻离婚协议中约定某项财产归子女所有,但事后反悔,认为其约定构成对子女的赠与,要求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约定。
就案例来看,大部分法院认为该条款不能被撤销。有法院认为父母作出的财产归属于子女的约定构成实事实上的赠与关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合同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 条的规定,就离婚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夫妻双方均有约束力。因此法院认为,对于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分配,夫妻双方不享有赠与的任意撤销权。③有的法院以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条款,因此不适用任意撤销权。④还有法院认为应当区分离婚协议与赠与合同,该离婚协议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而非赠与合同,因此不能适用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⑤除了不支持赠与撤销观点外,也有法院认为该赠与不属于救灾、扶贫等公益、道德义务的合同,因此该赠与可以撤销。⑥
(三)债务加入
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既存的债务关系之中,加入后与原债务人就债务的承担连带责任之债。[2]《民法典》第552 条弥补了《合同法》中关于债务加入制度的立法空白,正式确立了债务承担中“并存的债务承担”制度。而实务中也有许多债务加入人以赠与为由请求撤销债务加入行为,法院对此也有多种看法。
大部分法院严格区分债务加入合同与赠与合同,认为这属于两种不同的合同类型,因此债务加入人不可行使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权利。⑦但也有法院认为:“就债务加入人的行为性质看,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赠与行为,属于无偿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应当参照赠与合同的规定,在赠与财产转移前撤销赠与。”⑧
以上述案例来看,实践中对于各类无偿行为是否可以参照适用赠与人的权利还存在着众多争议。大部分法院严格区分赠与合同与其他无偿行为,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支持无偿行为人适用赠与人的权利,但也有少数法院认为行为人的无偿行为属于实质上的赠与,出于利益平衡的角度支持当事人的请求。在此情况下,无偿行为人究竟能否适用赠与人的权利,其理论依据为何便是本文将展开讨论的问题。
二、赠与人权利体系及法理基础
要讨论其他的无偿行为人能否适用赠与人的权利,首先应当厘清赠与人权利从何而来,立法为何为赠与人规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权利。就立法来看,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第658 条、662条、663 条以及666 条分别规定了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减轻的瑕疵担保义务、法定撤销权以及穷困抗辩权。
我国学界曾长期存在赠与合同属于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的争议。[3-7]《民法通则》中并未对赠与合同的性质进行规定,但其后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将赠与合同划分为实践合同。⑨但《合同法》在对赠与合同的立法选择上,放弃了实践合同的立法模式,选择将其置于诺成合同下⑩,并辅以任意撤销权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纵观各国立法例,德国[8]、法国[9]等国均采用要式合同的立法模式,只有日本放弃了要式主义,采用非要式合同辅以任意撤销权的模式。对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学界研究颇多。但研究多集中于任意撤销权的性质以及法律效果。[10-14]大多数学者在论述为何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时,将其归因于我国的赠与合同立法中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而赠与合同属于单务合同,仅赠与人负有合同上的义务。因此,出于利益平衡的角度,赋予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任意撤销权,使其拥有“后悔权”。而也有学者指出,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法理基础。该学者认为,并非所有无偿合同都有此规定。之所以为赠与合同设置任意撤销权,主要是因为赠与合同属于“转移不需要返还的所有权+无偿”,以及我国赠与合同的“非要式主义”。[15]
就法定撤销权而言,几乎各国对赠与合同的立法都规定了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关于合同的订立的论述表达为:“就合同的订立,要么是交换等价物品的正义德行,要么是一个人使他人令产增加的慷慨德行。”[16]即合同可以分为基于交换正义的合同和基于慷慨德行的合同。显然,赠与合同属于典型的基于慷慨德行的合同。因此,法律使赠与人拥有法定撤销权,令赠与人可以在受赠人实施“忘恩负义”行为时有权撤销自己慷慨的赠与行为。撤销赠与的权利是对受赠人“忘恩负义”行为的反制措施,是受赠人实施不正当行为所产生的理所当然的结果,由其承受赠与被撤销的结果具有相当的合理性。[17]
当赠与人的经济条件显著变差,并且对其生产与家庭生活产生影响时,赠与人有权不再履行赠与合同,我国学界称之为“穷困抗辩权”。学界对其性质争议颇大:有的学者认为该权利属于为抗辩权,并且属于消灭的抗辩权。认为当条件满足时,该权利可以对抗受赠人的履行请求权。[18]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抗辩权只能一时对抗受赠人的履行请求权,当赠与人经济状况恢复时,应当继续履行赠与合同。[19]而对于法律为赠与人设置穷困抗辩权的原因,现有的大部分学说均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出发,认为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存在显著差异。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未取得任何回报而付出利益,而受赠人未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便取得了利益。因此应当从利益平衡的角度为赠与人设置权利以优待赠与人,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20]
至于赠与人减轻的瑕疵担保义务,根据《民法典》662 条,原则上来说,赠与人不对赠与的财产负瑕疵担保义务,除非故意隐瞒瑕疵。但若是附义务的赠与,则应当在附义务的范围内承担和出卖人一样的瑕疵担保责任。由此不难看出,赠与人减轻的瑕疵担保义务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单务性。
综上,立法上为赠与人所设置的各项优待的权利,其法理基础基本上均立足于赠与的无偿性。但是否所有的无偿行为人均可以基于其行为的无偿性,而享有类似赠与人的权利,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三、作为财产变动原因的赠与
《民法典》合同编第十一章规定了赠与合同,在我国,“赠与”是作为一类债权合同意义上被使用的。但纵观各国立法,“赠与”不仅可以作为一项债权合同被使用,还可以作为财产变动的原因而被使用。
《德国民法典》“赠与”一节中,将“赠与”的含义(第516 条)界定为“某人因为一项给予而以自己的财产使得他人得利,且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关于无偿给予的合意,该项给予为赠与。”[8]187但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又另行条文规定了“赠与合同”(518 条)[8]188。《德国民法典》第516条与518 条存在明显的区别,516 条是关于“赠与”含义的阐述,而518 条则是规定了基于赠与的合同需要作成一定的形式方能生效。很多学者认为516 条解决的是“现物赠与”的问题。[21]因为并非所有的赠与均会先订立一个赠与的合同,再依据赠与合同进行交付,现实中存在大量的“现物赠与”的事例。梅迪库斯就此明确指出516 条并未讲明赠与人的义务,而只是说明财产给付在何种情况下构成赠与。[22]
除《德国民法典》外,《意大利民法典》中也对赠与进行了特殊的规定。其并未在合同中规定赠与,而是将赠与置于“继承”章之中。虽然条文中仍然肯定赠与的契约属性,但从体系来看,赠与和死因继承一样,更对的是表达财产变动的效果,而非成立一项债权债务关系。并且,《意大利民法典》在809 条规定了“间接赠与”。所谓“间接赠与”,是指某一法律行为欲达到与赠与相同的效果,但该法律行为本身并非赠与合同。[23]正如上文列举的基于赠与目的的“债务免除”“债务加入”等行为。并且进一步规定“间接赠与”可以在法定撤销权上适用赠与的相关规定。[24]
回溯历史便可发现,赠与作为一种财产变动的方式,在罗马法时期便已存在。在罗马法古典时期,赠与就并非合同,而是作为财产权利变动的原因而存在。有学者将罗马上的赠与阐述为:“一方为使另一方受益,向后者转让自己的财产权利的无偿性原因。”[25]即赠与可以作为任何财产取得的原因,但财产取得的效果不是由赠与引起的,而是由其他相应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根据具体的法律行为产生债的效果,而赠与为财产的变动提供正当基础。[26]除此之外,在区分法律行为的原因因素时,罗马法上将“赠与”“清偿”“借贷”并列为抽象给予法律行为的原因。[27]若“赠与”与“清偿”属于并列关系,即此处的“赠与”并非先创设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再对其进行清偿。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赠与”除了作为一项债权合同,还有可以将其作为“财产变动原因”。不应当将赠与的含义拘泥于一项产生债的合同,而忽略其作为财产变动原因的含义。
四、无偿行为人的权利
(一)现行法中无偿行为人的权利
除赠与合同外,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无偿行为有设立居住权、无偿保管、无偿委托以及好意同乘行为。居住权是我国民事立法最新的成果,《民法典》366 条至371 条对该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侧重于建构居住权制度中基本法律关系,如居住权关系的产生、消灭等,未涉及无偿为他人设置居住权人的权利问题。无偿保管行为中,立法规定无偿保管人非故意及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赔偿责任。⑪无偿委托、好意搭乘行为中也有类似规定⑫,无偿行为人只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减轻的赔偿责任。
通过对《民法典》中所规定的无偿行为人权利总结发现,除赠与人外,大部分无偿行为人的特殊权利均为减轻的责任,即不对一般过失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有学者认为,无偿的行为可以分为转移不需要返还的所有权的无偿行为与其他无偿行为,赠与人之所以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法定撤回权等权利,其原因就在于赠与行为属于转移不需要返还所有权的行为,而其他的无偿保管、无偿委托等行为并不具有这一特质。[15]诚然,无偿保管、无偿委托等行为确实不具有前述特质,但并非其他的无偿行为便不具备该特质。正如上文所提出的出于赠与目的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债务加入以及债务免除等行为中,也存在无偿转移所有权的情况,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无偿行为人也可以享有赠与人的权利呢?显然这一问题并不能一概论之,而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
(二)典型无偿行为的法律关系及赠与权利分析
1.第三人利益合同
从法律关系来看,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学界一般将其称为“补偿关系”,而债权人之所以会为第三人设立合同上的权利,一般是因为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某种“对价关系”,其法律关系如图1:

图1 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
因此,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可能是有偿的买卖关系,也有可能是无偿的赠与关系。由于本文讨论纯粹的无偿行为,即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有偿的对价关系。按照法律逻辑,两个法律关系相互独立,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对价关系”不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补偿关系”。
当债权人出于赠与第三人的目的,与债务人签订合同,使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交付最终使得第三人获的财产上的利益。由于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并未就赠与达成合意,第三人有可能完全不知道债权人是谁,但第三人确因该合同获得了利益,此时债权人能否向第三人主张赠与人的权利?有学者就曾提出,当债权人出于赠与的目的为第三人设定权利时,应当享有赠与人所享有的权利,因为在此情况下没有理由将债权人置于劣于赠与人的地位。[28]但经过分析,赠与人的权利包括任意撤销权、穷困抗辩权、法定撤销权等,并非每一种权利均可适用。就任意撤销权而言,债权人若是想要在第三人取得财产之前行使任意撤销权,必然会改变债务人的履行方向。而债务人的履行方向是由合同双方达成合意的,不能由债权人一人的意志便更改合同的内容,由此,行使任意撤销权必然会涉及到债务人的利益。此外,穷困抗辩权是指由于赠与人经济条件变差严重影响生活而赋予赠与人的一项履行抗辩权。但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并非由债权人向第三人履行,主张穷困抗辩权甚为勉强。并且穷困抗辩权的性质属于抗辩权,而抗辩权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对方的请求权,显然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并不对债权人存在履行请求权,因此也无适用穷困抗辩权的空间。最后,对于法定撤销权,其权利意在当被赠与人实施忘恩负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撤销权以救济赠与人的“慷慨精神”,维护基本的公平正义。该项权利的目的效果在于推翻已经发生的财产变动。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已经履行后,债务人从该合同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此时债权人向第三人主张法定撤销权并不会涉及债务人的利益,并且可以纠结出于赠与目的的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法定撤销权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存在可适用的空间。
2.债务加入
债务加入是本次《民法典》制定时新增加的内容,填补了之前债务承担中只有免责的债务承担的立法漏洞。本次《民法典》规定的债务加入有两种方式:一是债务人与加入人订立债务加入合同:另一种是加入人当方面向债权人表示加入债务。其法律关系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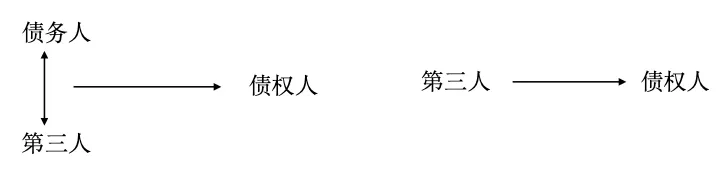
图2 债务加入关系图
第一种方式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利益第三人合同,但该合同与前述的利益第三人合同有较大差异。前述的利益第三人合同中,赠与的目的存在与“对价关系”中,但债务加入的合同中,赠与的目的存在与“补偿关系”中。第三人以履行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担的债务,来达成向债务人实施赠与的目的。此时的加入人的赠与人身份是针对债务人而言的,而非“第三人”,即债权人。因此,当加入人实现自己作为赠与人的权利时,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
在债务加入制度中,加入人能否基于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对抗债权人存在众多观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多认为应该类推免责的债务承担制度。[29]但德国学界通说应该区分债务加入的不同方式:当债务加入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加入债务时,加入人不得根据其与债务人的关系对抗债权人,因为法律关系具有独立性;但若以债务人与债务加入人签订合同的方式加入债务时,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基于该合同产生的抗辩,因为债权人的权利产生于该第三人利益合同,应当受到该合同的影响与制约。[30]并且根据前述,此时的债务加入合同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22 条的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因此,本文认为,当加入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债务加入合同能够构成赠与合同时,债务加入人属于赠与人,可以向债务人主张赠与人的权利,但仍应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
当加入人以单方允诺的方式向债权人表示加入债务,债权人没有拒绝的情况下,债务加入成立。这种由债权人与加入人达成的债务加入,加入人不得以对债务人的赠与而对抗债权人。债权人向加入人主张清偿债务时,加入人必须清偿债务。在此情况下,并无任意撤销权、穷困抗辩权的适用空间。当加入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实际上达成了对加入人的赠与效果。如前文所言,法定撤销权的目的是推翻已经发生的财产变动效果,在此情况下,应当允许加入人向债务人主张法定撤销权,但财产返还应当是向债务人主张,而非债权人。
3.债务免除
对于债务免除而言,我国大部分学者根据《合同法》的规定⑬,认为债务免除属于单方法律行为。[31-32]因此债务免除行为无法构成赠与合同,因为赠与合同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就单方法律行为而言,仅一方的意思表示便可发生法律效果,因此单方法律行为大多都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学者认为,单方法律行为中对方的自由意志可能被侵害,因此应当对单方法律行为加以控制,而控制的方式就是赋予对方一定期限内的拒绝权。[33]而《民法典》中对债务免除的规定正体现了这一观点。⑭这样的立法规定体现了对债务人意思自治的保护,但在债权人出于赠与的目实施债务免除的情况下,似乎未考虑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
当债务免除中的债权人出于赠与的目的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同样是无偿的变动财产,赠与人享有众多反悔的权利,但债务免除中的债权人毫无反悔的余地。从基本的利益平衡角度出发似乎并不合理。但若假设免除人也可行使赠与人权利,也存在众多不妥之处。债务免除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免除的意思一旦到达债务人处即发生免除的效果。在此情况下,任意撤销权与穷困抗辩权均无适用空间。但即使债务免除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对于法定撤销权仍存在适用空间。债务免除,当发生法定撤销权的构成事由时,出于利益保护的角度,允许债权人撤销债务免除的效果更符合公平原则,且不会影响债务免除的单方法律行为属性。
五、结论
《民法典》目前并未对无偿行为作出较为抽象统一的规范,除了延续以往赠与合同的规定外,在无偿行为方面立法较为空缺。但是各种各样无偿行为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以非赠与合同的方式存在着,缺乏对其规范将导致无偿行为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合同编中规定其他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可以参照适用最相类似的合同规定,这一规定为我们利用赠与合同的规范调整其他无偿行为留下了空间。出于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没有理由仅对签订赠与合同的赠与人进行最优待,而毫不保护其他出于赠与目的的无偿行为人。
在《民法典》最新的规定中,第三人利益合同、债务加入以及债务免除行为中的受利方都被赋予单方拒绝的权利,却其并未规定这些行为中失利方“反悔”的权利。出于利益平衡的角度,本文认为可以将赠与分为狭义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与财产变动原因的赠与。若将赠与作广义意义的理解,当允许无偿行为人可以享有赠与人的权利。但基于对赠与人权利以及各项典型无偿行为法律关系的分析,并非赠与人的权利每一项均可适用。从分析来看,法定撤销权的适用范围最广。将赠与理解为财产变动的原因,而法定撤销权正是推翻已经发生的财产变动,这样的救济方式有立法例可借鉴,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空间。但这也仅是在最低程度上的救济,即发生受利人“忘恩负义”行为时才能主张的救济。
民法是规范私行为的法,随着经济活动在生活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也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有偿行为的研究似乎更具有经济意义。但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大众的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加。无偿行为的作出某种意义上属于行为人对一种慷慨精神的追求。但目前无偿行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无偿合同。无偿行为人基于慷慨精神而作出的无偿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福利,没有理由不对其进行合法的权利保护。因此,无偿行为人的权利还需更多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参见《江苏宏玮大酒店有限公司与张奇、袁鑫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苏09 民终3342 号。
②参见《梅全、刘德赠与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云01 民终5601 号。
③参见《冉某1 与冉某2 冉、某3 等离婚后财产纠纷二审判决书》,(2018)渝04 民终129 号。《杨郴薇儿与杨永康、胡宠英赠与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浙0482 民初5968 号,《王林生、王某赠与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闽06 终3210 号。
④参见《华正才、华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判决》,(2018)黑12 民终920 号。《蔡昊恩、蔡永强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粤01 民终11761 号。《蔡家琪、蔡家璐等与蔡尧初等赠与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粤0604 民初9057 号。
⑤参见《高某1 与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鲁0113 民初1933 号。
⑥参见《郭某与江某、郭建赠与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川1621 民初3795 号。
⑦参见《徐彪、刘鹏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云07 民终21 号。《李艳娜、李艳涛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冀10 民终2647 号。《朱勇东、何金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01 民终21017 号。《林受对,汪修书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6)桂02 民申175 号。《曹存学与永善宸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888 号。
⑧参见《赵某与吴某1、吴某2 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晋0202 民初3734 号。
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 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财产的交付为准。
⑩《合同法》第185 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⑪《民法典》第八百九十七条:保管期内,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⑫《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⑬《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⑭《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