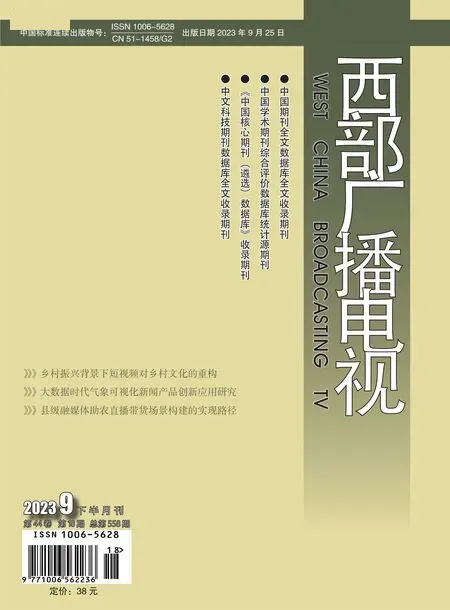现实主义电影《何以为家》的艺术探析
受希文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曾提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多通过真实还原社会本貌、暴露存在的现实问题、剖析人性中的矛盾,引发大众对社会事件的思考。《何以为家》是由黎巴嫩、法国、美国联合制作,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赞恩·阿尔·拉菲亚、约丹诺斯·希费罗联合主演的一部剧情片。影片通过讲述一个12 岁黎巴嫩小男孩赞恩的悲惨生活遭遇,展现出了黎巴嫩底层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现状,且赞恩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是一个真实的“儿童难民”。本片在2018 年举行的第71 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及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并在2019 年第91 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这部聚焦了黎巴嫩底层人民生活困境的电影因其反映的真实人性纠葛与社会现实问题,也引起了国内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深度思考,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究。
1 斯德哥尔摩式的悲剧循环
在近几年中,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呈现出一种复归影坛的趋势,从国外《绿皮书》《小偷家族》《寄生虫》《宿敌》,到国内的《我不是药神》《暴裂无声》《学爸》《孤注一掷》等。这些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多以关注社会、直面现实、聚焦问题、探析人性为基点展开各自的叙述,在以宏大制作、感官刺激、明星云集等为主要影视宣传市场的当下,是一股引人深思的清流。影片《何以为家》上映后,受众关注的焦点大多在赞恩的父母身上,大部分言论是在谴责赞恩父母的行为,抨击作为父母的他们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养育之责,因为生而不养,导致“无以为家”。纵观全片,悲剧的出现原因既在于家庭中赞恩父母对子女的漠视,社会大环境对底层的关注不足,同时又根植于人的奴性。
人的奴性源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1]。这种情节会使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和依赖性。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一个疯狂的劫持者,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托付给劫持者,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这种屈服于权威的弱点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表现。
影片中赞恩家房东阿萨德用几只鸡就可以将赞恩的妹妹萨哈娶走,在这个社会中女孩儿成为一种廉价交换的商品。得知这件事后,赞恩悲愤反抗,但他的行为是无力的,在他父母与这个社会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在萨哈的事件上,赞恩的父母属于“人质”,阿萨德属于“劫持者”。时间久了,赞恩的父母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都是阿萨德对他们的宽容与慈悲——阿萨德租房子给他们住,给赞恩在店里工作的机会,经常给萨哈送蔬菜和拉面,以满足赞恩家的生活所需。阿萨德成为他们生存的依赖,他们逐渐习惯并满足于现状。赞恩的父母也曾因这样糟糕的状况反抗过,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屈服了,最终习惯性地成为“人质”。在法庭上赞恩的父亲这样陈述:“我们是为了萨哈好,因为我们什么都给不了她,她跟着我们一点活路都没有,在我们家里没有吃的、喝的,连一个睡觉的地方都难找,我是想让她嫁到一个好人家,那样她就有吃的,还有被子盖。”
在影片最后部分,赞恩因为生活所迫将一岁的约纳斯卖给了人贩子阿斯普罗,他从之前的反抗者变成了“人质”,在面对拥有更大权力的“劫持者”时,他只能无奈屈服于“劫持者”。他作出了和他父母同样的选择,这个选择成为他们悲剧的缩影。而悲剧不断在他们身上循环,成为他们的命运,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奴性,造成了他们的悲剧。
2 立象以尽意的空间叙事
从整体叙事结构来看,影片采用了非线性回环倒叙的讲述方式,打破传统叙事中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叙事时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来回穿梭跳跃,一方面使故事更带有悬念感,加强观众观影好奇心理和联想互动能力;另一方面也让作品更富有艺术性和深刻性。例如,影片开场部分展现了赞恩这样一个未成年小男孩被戴上手铐进入法庭状告父母的场面,直接将戏剧矛盾和故事悬念开门见山呈现在观众面前。该影片不像线性叙事中正序逻辑那样清晰明了,因为众多的信息未加任何解释和说明,所以观众会产生很多疑问:被铐起来的小男孩是谁?他犯了什么罪?他为什么会状告父母?这一系列的疑惑也正是引起观众好奇心,让观众聚焦后续情节,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
电影在现实和回忆的双重视点交叉展开叙事。在现实视点中,是赞恩在法庭上状告父母的故事,主要人物有法官、被告(赞恩父母)和原告(赞恩和律师),每个人都通过发言来阐述各方的立场;在回忆视点中,主要展现赞恩真实的悲惨境遇,从赞恩的“被压迫—抗争—离家—流浪—回家—复仇—入狱”这一故事线索和现实视点交叉闪回完成叙事。现实和回忆视点中叙事可以并行发展,相互补充,共同塑造故事的观赏性和完整性。
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一书中,把故事和空间分成“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是故事发生时所在的空间环境,“话语空间”则是指故事的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所在的空间环境[2]。《何以为家》因其影片画面内容的鲜明性使影片的空间叙事更加侧重“故事空间”,以画面和声音为表现力的电影艺术,通过镜头和声音记录着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与小说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想象力相比,电影以画面为表现手段会给人视觉上最为直观的艺术感受,可视化的画面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效果。
影片《何以为家》在开头通过几个俯拍镜头将黎巴嫩逼仄、凋敝、混乱的社会空间展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看到的是破烂的街道、拥挤的房屋、抽烟打闹的不良少年。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都是黎巴嫩贫民窟真实状态的写照。关押不良少年的监狱则是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一个房间里关着十几个犯罪少年,在这里他们没有得到良好的改造,反而方便他们聚在一起“犯罪”,为了寻找刺激,他们喝“袜子汁”(一种毒品的替代品)。监狱里关着赞恩的哥哥,哥哥却是赞恩妈妈的“骄傲”,哥哥可以将妈妈带来的“袜子汁”在监狱卖得比猪肉的价钱都高,妈妈竟对这样的赚钱方式乐此不疲,这是家庭正向教育完全缺位造成的悲剧。一幅幅真实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而对于这群不良少年而言,少年监狱却是一个“好归宿”,在这里他们不用流浪街头,也不担心食不果腹,在这里他们至少有一口饭吃,因为饥饿是大部分黎巴嫩孩子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赞恩得知妹妹萨哈要嫁给阿萨德之后,影片中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被悬挂在阴暗的两栋破败楼宇之间,十字架上的霓虹灯本应该发光却没有发光显得很暗淡,且十字架画面周围充满了不和谐的晾衣架,破坏着它的构图,给人以不稳定、不协调的感受。十字架本身象征着爱和救赎,在这里却暗淡无光,隐喻着在这里人们救赎的行为是无力的,就像赞恩的行为,虽然为妹妹的事极力与他所认为的“坏人”反抗和斗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凸显出抗争的苍白无力,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公平得不到保障,正义得不到伸张。
3 隐喻现实的梦魇式台词
语言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人们可以从语言中感受到情感与意蕴。在电影中,台词是传达情感的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够让影视作品更具魅力和吸引力。同时电影台词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关系到电影情节的推动[3]。
影片里梅森的一句话引来了受众的热议,梅森对赞恩说:“在瑞士,你有自己的房间,你想让谁进来谁就可以进来,这是你自己的权利,那里的小孩没有一个是惨死的。”看似极为平静的一句话,却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因为生活在和平国家的人的日常生活,竟是他们的奢望。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恶劣——随时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饿死、被虐待而死。他们希望自己能被善待,这是赞恩和梅森的心声,也是每个黎巴嫩孩子的愿望。
赞恩在法庭控诉时,说出一段震撼人心的台词:“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否则以后回忆只有暴力、虐待、侮辱、殴打,在我的生活中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就是——给我滚臭小子,走开混蛋。”一个12 岁的孩子说出字字诛心的话,每说一个字都在自揭伤疤,这些伤痛似梦魇般围绕着他,使他一直都生活在“黑暗”中。他唯一的愿望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大人不再生育,这是他得知母亲再次怀孕后发出的“呐喊”,因为他预见在自己家这样生而不养的家庭诞生的孩子,会重复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不想再看到更多的孩子遭罪,周而复始形成“个人—家庭—社会”的悲剧循环。在成长过程中他从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怀与呵护,他不希望再有孩子像他这样痛苦地活着。
正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述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赞恩的家庭经济状况糟糕,也缺乏关怀和爱。他大声控诉道:“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以为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正因从未得到父母的关爱、感受过家的温暖,赞恩觉得生活处处皆炼狱,他只能打电话给电视台传递自己的声音,寄希望于法庭之上,期待通过法律守护他心中残存的余温。
4 形象鲜明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视剧的核心,而人物的塑造是影视创作的重中之重。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中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该影片在叙事空间的“典型环境”和空间下的“典型人物”相得益彰,贫民区的真实场景和演员本色出演真实还原了社会现实。
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和个人身份的缺失现象贯穿全片,分别对应在赞恩和拉希尔身上。在影片开头两组镜头就分别隐喻了他们的身份问题:医生通过检查赞恩牙齿的方式从“生理”上判断年龄,因为赞恩没有出生证明,无法证明真实年龄,对应的是“身份模糊”;拉希尔因偷渡来到异乡,通过画痣“扮演”假身份证上的女人,在听到海关人员点自己假名时流露出的恍惚和不安,对应的是“身份缺失”。在后续的剧情中,身份问题一直隐藏在两人的故事线中,同时故事设定也让两人有了交集,让观众更能共情于有着同样悲惨命运的两个人,最终身份问题带来的结果是两人悲剧的结局。
本片颠覆传统的人物设置,即孩子的“成人化”、父母的“孩童化”,成为影片的亮点。角色外在表现力的置换是这部影片的主要冲突点,叙事视角也一直围绕赞恩。在影片中,与赞恩的父母相比,赞恩才真正是家庭中的核心。他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重任,养家赚钱,不仅上街卖果汁、拉煤气,还贩卖毒品。他的父母却整天无所事事“养尊处优”,不仅时常辱骂虐待赞恩,还剥夺了他上学的权利,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是他们给予了赞恩生命,实则更像是榨干他的“寄生虫”。这样矛盾的人物换位设置,更加突出赞恩这一人物的悲剧化色彩。
影片通过两条叙事线将两位母亲——赞恩的母亲与拉希尔进行了鲜明对比。拉希尔没有身份证明还是一个未婚先孕的单身母亲,从一开始就被困难包围,她不仅身份缺失,独自抚养儿子,每个月还寄钱给父母,但她并没有因为这些外在困难就选择弃养。相反,她为了儿子放弃在雇主家的固定工作,与赞恩和儿子欢乐的“三人时光”是影片中唯一能让人感到温暖的片段。虽然最后拉希尔因没有身份证明被捕坐牢,但她一直担心儿子的安危,儿子在她心中始终是第一位,因为儿子她才有拼搏的勇气与力量,相比赞恩妈妈,她是合格的。而赞恩妈妈则是那个赞恩口中、人们眼中不称职的母亲,她的行为是自私的,她只知道将孩子生下来,却没有承担起养育的责任,她给赞恩最多的是拳打脚踢,时常还将赞恩最小的妹妹用铁链拴起来,这种“非人化”的管教模式隐喻着日后一代代孩童的悲剧。画面极力刻画出一个不具责任感的母亲形象,这样鲜明的人物设置既加深了影片中的戏剧冲突,也准确传递出了影片中所暗含的人文关怀,同时提升了影片的可看性。
5 结语
电影是用画面和声音来呈现的[5],《何以为家》通过对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传承,即拍摄场景大部分运用自然光、手持晃动摄影、大量非职业演员出演、冷峻写实画面和哀婉伤感的音乐,真实刻画了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现状,影片在艺术和票房收益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优秀的电影是可以改变现实的,如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关于性侵学生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韩国相关部门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娜丁导演曾说她不奢求电影能够改变世界,但她希望电影是改变的开始。影片最后赞恩的宛然一笑充满了阳光、温暖和希望,像一道光芒穿破社会现实的阴霾来治愈苦难大众,给人以无穷力量和勇气。这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这一笑,就是英雄主义的有力象征。这定格在画面中的笑容,同时寄托着的是导演对本国美好生活的向往,导演自己作为黎巴嫩的公民,希望黎巴嫩能恢复往日平静、宁和的景象,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尤其是让孩子们能得到应有的关爱与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