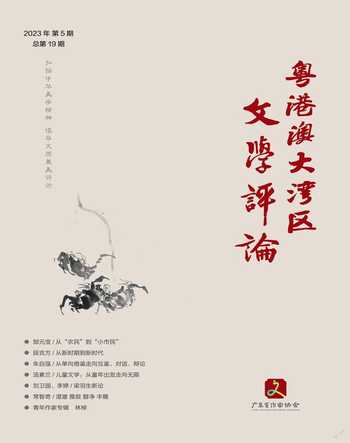从单向借鉴走向互鉴、对话、辩论
摘要: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发展和质量提升始终离不开对西方儿童文学学术资源的学习和借鉴。但是,如果中国儿童文学在借鉴中不有意识地、不积极地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就难以从单向的学习和借鉴这一低级阶段,发展到互鉴、对话、辩论这一更高阶段。本文持着“审视”的目光,针对西方后现代理论中的反启蒙倾向以及盛行的后殖民主义这两个问题,围绕儿童无法“被理性理解”“儿童文学是一种殖民儿童的方式”这两个观点,展开中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双向交流的一次实践。
关键词:单向;双向;交流;主体性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呈现出特异的文学史面貌,那就是先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其后有受西方理论影响而产生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然后才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具有外源性特征。百年历史已有证明,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演化中,与外国儿童文学交流便进步,隔绝则退步。
改革开放的四十几年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国际交流的背景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给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引进和输入创造了良好的出版条件。近十几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此起彼伏,除了《书,儿童与成人》《欢欣岁月》《英语儿童文学史纲》《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等为数不少的单部著作之外,还陆续出版了《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方卫平主编)、《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王泉根、约翰·史蒂芬斯主编)、《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译丛》(朱自强主编)、《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朱自强、徐德荣主编)等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翻译丛书。在纷至沓来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中,保罗· 阿扎尔、杰克·齐普斯、彼得·亨特、约翰·史蒂芬斯、玛丽亚·尼古拉耶娃、金伯利·雷诺兹、佩里·诺德曼等数量可观的世界一流儿童文学学者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眼前。
毫无疑问,自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等人创立儿童文学学术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发展和质量提升始终离不开对外国,特别是对西方儿童文学学术资源的学习和借鉴。但是,也必须意识到,时代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儿童文学的学术交流需要打破单向学习和借鉴的惯性思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需要建构自身的“主体性”,谋求互鉴、对话、辩论这一新型交流模式。为此,我想就西方后现代理论中的反启蒙倾向以及盛行的后殖民主义这两个问题,围绕两位西方学者的具体观点,通过对話、辩论,展开中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双向交流的一次实践。
一、儿童是否可以“被理性理解”?
我在近期发表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三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凝视”“谛视”“审视”这三种学术目光。文中说,所谓“审视”目光,“也可以说是怀疑性、批判性目光。‘审视性研究提倡的是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重视的是学术讨论的对话和辩论,指向超越性、进步性的学术深化。‘审视式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既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1这里所说的“他人”,当然也包括西方儿童文学学者。也就是说,对西方学术,中国学者也理应采取“对话和辩论”这一学术姿态。
阅读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著,我既怀着强烈的期待,也持有“审视”的目光。在阅读中,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佩服的心情,但偶尔也会产生挥之不去的疑问。我们会受启发于很多新的学术观点,受教于不少新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们也会面对可以与之探讨、商榷的问题。
在我和徐德荣教授主编的《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中,收有英国学者杰奎琳·罗丝的《〈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一书。这部在西方儿童文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的写作目的如作者所述,是“以《彼得·潘》这一案例为基础,尝试追溯虚构儿童文学概念背后的虚幻。”2罗丝的学术目光是敏锐的,所作的研究也是扎实而深入的。不过,其立论的根基似乎并不牢固。罗丝指出:“最重要的是,对洛克和卢梭来说,孩子可以被看到、观察到和认识到,就像世界可以被理性理解一样。因此,虚构儿童文学产生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儿童和世界都能够以直接和无中介的方式为人所知……”3
显而易见,手握后现代理论工具的罗丝这是站在反“启蒙”的立场,所持有的是“世界”不“可以被理性理解”这一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但是,罗斯真的是认为“世界”不“可以被理性理解”吗?我们让多次被著名杂志评选为“顶尖思想家”的史蒂芬·平克来戳穿这一类假象——“后现代主义的信条认为理性是行使权力的借口,现实是社会所建构的,所有的陈述都困于自我参照的大网之中,最终崩溃成为悖论。就连与我同属一个部落的认知心理学家,也经常公开宣布对启蒙运动理念的反对态度,不认为人类是理性主体,并由此破坏了理性本身的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任何尝试将世界变得更加理性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但所有这些立场,都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它们对自身进行了反驳。它们不认为有理由相信自己提出的那些立场。只要辩护者一张嘴,就输掉了这场辩论:因为辩护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想要去说服别人、利用理性去维护想要辩护的观点。也就是说,辩护者认为,根据自身与听众都接受的理性标准,听众理应接纳他们的观点。”4儿童文学也是一个“世界”,罗斯写作《〈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一书,当然为的是“想要去说服别人、利用理性去维护想要辩护的观点”,从而让读者“接纳他们的观点”。罗斯如果没有这一目的,这部书稿就应该一直锁在抽屉里,甚至压根就不会提笔写这部书稿。
我认为,罗丝可以指出《彼得·潘》的儿童观或许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因为《彼得·潘》的儿童观有问题(假定),就质疑“孩子可以被看到、观察到和认识到”,质疑“世界可以被理性理解”。在对儿童的认知上,我们既承认人类理性目前存在着局限,但也信任人类理性巨大的发展潜能。事实上,洛克的“白板”论和卢梭的“自然人”教育思想都早已被超越,而近年来保罗·布卢姆对婴幼儿的道德观念的实验研究,1艾莉森·高普尼克对婴幼儿的理性能力的实验研究,2都已经证明,在极不容易被“观察到”的婴幼儿心灵这一领域,“理性”已经取得了不起的胜利。
这里有一个儿童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看到、观察到和认识到”的问题。在罗斯的论述中,看似思想激进,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固化问题,因为她似乎认为,儿童要么是“可以被看到、观察到和认识到”的,要么,理性地研究儿童就是一场“虚幻”。然而,像我这样的“理性”的拥护者都知道,儿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被看到、观察到和认识到”,“但是,儿童研究中的‘儿童最终也只是儿童的近似值,是对儿童的迫近,而不可能完全成为儿童本身。儿童研究中的‘儿童永远是可能的儿童,儿童研究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儿童文学研究也是永远走在没有穷尽的路上。儿童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魅力正在这里。”3
二、“儿童文学是一种殖民儿童的方式”?
西方后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中存在着不少悖论。比如,这一理论反对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方式,但是,自己在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上,却不自觉地在作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判断。“儿童文学是一种殖民儿童的方式”这一著名论断就是其中一例。
上述杰奎琳·罗丝的《〈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一书,就说过“儿童文学是一种殖民(或破坏)儿童的方式”4这样的话,而对这一观点论述得最为起劲,同时也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则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
佩里·诺德曼是在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在中国也有为数不少的拥趸。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合著的《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的译者陈中美就是佩里·诺德曼的崇拜者,她在题为“儿童文学的极致”的译后记中说道:“不管是书的内容,还是书中所体现的精神,本书均可称得上是一本巨著,是儿童文学思考的‘极致,面对‘极致,我们不由会心生崇敬。”5
佩里·诺德曼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三部学术著作,其中的《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乐趣》都有对“儿童文学是一种殖民儿童的方式”这一观点的论述。在《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一书中,佩里·诺德曼以包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杜立德医生》《下雪天》这三部经典在内的六本儿童文学作品为样本,探究儿童文学的定义。诺德曼指出:“这些文本认为成人有权利对儿童行使权力和影响;因而,它们可能表现出一种对不太强大的生命存在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被认为是‘殖民主义者的。”1诺德曼的这种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在早于这本书的《儿童文学的乐趣》中就有表述——“儿童文学代表了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的努力:让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成人希望中的样子,并为自己本身难以避免不符合成人模具的各个方面感到惭愧。这或许是专制規则的另一个(也是非常强大的)方面。”2诺德曼指出:“殖民主义思维的这种特殊变体在儿童文学批评中仍惊人地常见,老练世故的成人经常赞美童年的明智纯真,将其作为攻击其他不太明智的成人的一种方法。”3
在儿童文学学术研究这一维度,诺德曼是一位悲观主义者。比如,他说:“就像我本书中一直描述的那样,儿童文学是这样一项事业:它总是超乎一切地试图成为非成人的,但总是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从我描述的变奏模式和那些模式所能产生的丰富含混性来看,它总是在做努力,然后再次失败。”4诺德曼显然是在说,无论怎样努力,儿童文学都命定就是“殖民主义者的”文学。
在译者陈中美眼里,《儿童文学的乐趣》是“儿童文学思考的‘极致”,但是,就像杰奎琳·罗斯一样,佩里·诺德曼在思想方法上依然存在着固化和偏见这些问题。他认为,儿童文学不可能成为“非成人的”文学,而不能成为“非成人的”文学就必然沦为对儿童进行殖民。在诺德曼这里,儿童文学就是铁板一块,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但是,我所看到的整个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并不支持诺德曼的看似“深刻”的观点。
英国学者Deborah cogan thacker和Jean webb在《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强行役使的知识,和自由发掘无限世界的可能性,这两个对立的论点落在儿童文学发展的核心。”5“在整个儿童文学史上,控制与自由之间的紧张气氛,依然不停地在两端拉扯着。”6我在《儿童文学概论》一书中则指出:“儿童文学上的‘两个对立的论点或‘控制与自由之间的紧张气氛的出现,根本上是受两种儿童观思想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一个是以约翰·洛克为中心的立于经验主义之上的儿童观,另一个则是对卢梭儿童观中的一些思想产生共鸣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儿童观。前者关于认识产生于经验的观点,面向儿童时,便演化为教育和教训;后者关于儿童具有与神相似的创造力和内宇宙,而随着长大,这种能力会逐渐丧失的观点,面向儿童时,便表现为对儿童心性的解放。”7
可见,对浪漫主义的儿童观的性质的认识,在诺德曼与我和Deborah cogan thacker、Jean webb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以我对中国儿童文学演变、发展的历史的考察,诺德曼的“殖民主义”这一单一理论是缺乏阐释的有效性的。
周作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儿童本位”这一理论,虽然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仍然具有中国的主体性,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并不像诺德曼所描述的那样,“总是超乎一切地试图成为非成人的”的儿童文学理论。1922年周作人翻译柳泽健原的《儿童的世界》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大人在本质上不能再还原为儿童,是当然的了。……大人对于儿童应做的事,并不是去完全变成儿童,却在于生出在儿童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的那边的‘第三之世界。”1周作人在译后附识中说,“这篇小文里有许多精当的话”。我想这“许多精当的话”,就应该包括这一段。同是1922年,周作人在与赵景深就童话作书信讨论时,使用“第三之世界”这一用语,比较了安徒生与王尔德的不同——“安徒生与王尔德的童话的差别,据我的意见,是在于纯朴(Naive)与否。王尔德的作品无论哪一篇,总觉得很是漂亮,轻松,而且机警,读去极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因为在他童话里创造出来的不是‘第三的世界,却只在现实上覆了一层极薄的幕,几乎是透明的,所以还是成人的世界了。安徒生因了他异常的天性,能够复造出儿童的世界,但也只是很少数,他的多数作品大抵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这可以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我相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2
的确如诺德曼所言,儿童文学中隐藏着成人,但是,儿童文学中隐藏的成人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可以大致上把儿童文学分成好的儿童文学和坏的儿童文学两类,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把好的儿童文学和坏的儿童文学中“隐藏的成人”也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教训儿童的成人,一类则是解放儿童的成人。我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解放儿童的这类成人——“不是把儿童看作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如历史上的教训主义儿童观)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童心主义的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3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诺德曼的将儿童文学一律看作是“代表了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的努力”这一观点就不只是简单化,而是甚至有些粗暴了。
人总是“他者”,甚至是他人的地狱吗?人与人、成人与儿童就宿命性地不可能走向对话、沟通乃至融合吗?我们在《仙境之桥》《托德日记》《宠爱珍娜》等西方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是对这一假设的拒绝。
中国儿童文学学术谋求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儿童文学学术是必得借鉴的可贵资源。不过,如果中国儿童文学在借鉴中不有意识地、不积极地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就难以从单方面学习和借鉴这一低级阶段,发展到互鉴、对话、辩论这一更高阶段。在中西学术交流中,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的“主体性”,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
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三种方法》,《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2 [英]杰奎琳·罗丝所:《〈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明天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3 [英]杰奎琳·罗丝所:《〈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明天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4 [美]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1—382页。
1 [美]保罗·布卢姆:《善恶之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加]艾莉森·高普尼克:《孩子如何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4 [英]杰奎琳·罗丝所:《〈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明天出版社2022年版,第41页。
5 陈中美:《〈儿童文学的乐趣〉译后记》,[加]佩里·诺德曼、[加]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1 [加]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2 [加]佩里·诺德曼、[加]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第149页。
3 [加]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4 [加]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義儿童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0—361页。
5 [英]Deborah cogan thacker、Jean webb:《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杨雅捷、林盈蕙译,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2页。
6 [英]Deborah cogan thacker、Jean webb:《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杨雅捷、林盈蕙译,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5页。
7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
1 周作人译:《儿童的世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周作人:《童话的讨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