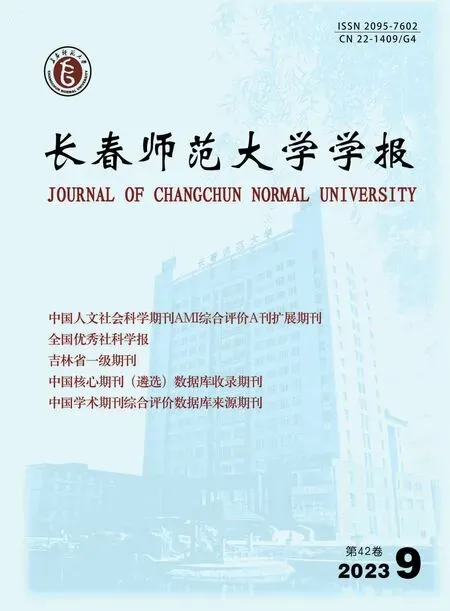胡塞尼的焦虑与身份选择
——《追风筝的人》的文化立场探析
郭 飞,张德文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近年来,学者们利用家庭伦理、叙事空间、生态批评、需求层次等理论对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展开持续研究。例如,郑光锐结合家庭伦理探究小说人物关系及主人公阿米尔的心灵蜕变特征[1];尹付利用空间理论剖析地理空间对个体精神的影响[2]。该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因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胡塞尼于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追风筝的人》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聚焦于它在文化层面与读者建立的沟通机制及情感共鸣。它的文化内涵也曾受到不少媒体的高度评价,如《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是对阿富汗人与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3]1;《旧金山纪事报》认为它是“关于文化的不可思议的故事”[3]1;《爱荷华城市新闻》认为“它的文化在书页上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3]1。可见,胡赛尼的小说文本透出多元文化印迹。探讨作家的民族身份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立场,也随之成为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点。比如,张秀丽认为西方文化已成为胡赛尼主要的情感动力;“我”的身份完全是西方式的,这种救赎是西方对东方特有的救赎[4]。就民族文化身份而言,以往的研究多单纯地从文本角度分析,然而“作家对自己身份的选择与认同,是主观行为,受动机、时间、情感等因素的操纵”[5]。2001年,藏身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策划制造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让阿富汗成为焦点,变成抽象的政治标识。胡赛尼认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不是阿富汗的全部,这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有饱受磨难的人民。虽然他在小说前言中写道:“我认为全美国没有人会听一个阿富汗人诉说”[3]3,但事实上他更相信夫人罗雅的话,当前正是“向世界讲一个阿富汗故事的良机”[3]3。透过胡赛尼文化身份的表象,探讨他的主观动机与情感走向,找到作品与读者之间达成共鸣的生成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小说及作家。
一、官方叙事与小说家的创作动机
“9·11”事件后,美国政要们纷纷演讲,将事件定性为一帮仇视美国民主与自由制度的人犯下的反人类、 反人性的罪恶行径。美国“9·11”调查委员会的最终调查报告再次渲染“仇美”势力,将悲剧和灾难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美国的官方叙事助推了民众本已高涨的爱国热情。胡赛尼在小说中写道:“一夜之间,世界改变了,美国国旗出现在每个地方”[3]35,流浪汉的帽子、街头艺人手风琴的盒子上都贴着美国国旗。几天之内,美国接连爆发反穆斯林暴力活动,“到处是对阿富汗的误解和偏见”[3]3。到9月17日小布什总统呼吁停止国内反穆斯林暴力活动,事态才有所收敛。一时间,胡塞尼感到焦虑与不安。他的处境正如拉什迪所说:“处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本身不同甚至具有危害性的人群中。”[6]新政治氛围加剧了胡赛尼作为一个阿富汗裔美国人的身份焦虑,迫使他对民族身份进行再思考:
“9·11”发生后,我感到一种撕裂感。跟所有美国人那样,我感觉自己正在遭受攻击;我同时也从一个阿富汗人角度来体会该事件,我很担心即将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切。这两方面在我内心有着剧烈的冲突。[7]
胡赛尼逃离故国、漂泊他乡,是在东西方文化间游走的作家。流散的人生阅历铸就了他复杂的文化身份:他既是美国的新移民,又有阿富汗之根;既是阿富汗的“他者”,也是美国的“他者”。“9.11”事件后,官方话语叙事频繁使用“我们国家”“美国人民”等字眼激发美国民众的凝聚力,而其他关于阿富汗人的文章“多数围塔利班、本·拉登和反恐战争展开”[3]4。强烈的语境反差激活了作家的民族身份意识,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政治话语凸显的文化差异。民族身份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对身份主体而言,最初可靠的身份源头只存在于想象中,我们“可把作家族裔身份的源头视为一种召唤力,吸引力,凝聚力”[5]。在美国反恐与反阿富汗的态势下,胡赛尼受到族裔身份文化之源的召唤与引领,把对故国的感情融入小说创作,力图修正西方对阿富汗人“妖魔化”的认知与偏见。他用书写展示了有血有肉的阿富汗人及与美国迥异的阿富汗文化。胡塞尼借用小说创作表达对故国的怀念与想象,是寻根与确认身份的过程,也是寻找认同与归属感的过程。
二、族裔身份确认与形象重塑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问题关注的焦点是“作家如何构建、规划自己所宣称的身份及其目的”[8]。胡赛尼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的一个显赫家族,他曾在故乡生活过十几年。因此,童年记忆是他族裔身份的文化源头。自传体小说《追风筝的人》前九章记叙了“我”和父亲在阿富汗的生活,其对当时的生活场景有细致描述,这一点从作家对“我”的房子的回忆便可窥见一斑。这所房子在喀布尔,胡赛尼详细描述了室内陈设,瓷砖、挂毯、水晶灯等装饰都极具阿富汗特色。精美的马赛克瓷砖是主人公的父亲在伊斯法罕购买的,家里还挂着“从加尔各答买来的金丝织成的挂毯”[3]7。
胡赛尼在创作中回忆童年生活,详尽描写居家场景,这是文化与情感的洄游,佐证了作家与故国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我”用记忆重构因战乱而面目全非的故乡,回忆具有饱满的情感意蕴与归属指向,是在地域角度上的精神寻根,也是对文化之源的寻溯。胡赛尼的书写突显祖辈的传统根基和血缘纽带,这是对自己族裔身份的再确认。正如荣格所说,“儿童生活是今后一切生活的根基,为今后的生活提供滋生土壤。”[9]
小布什总统在“9.11”后的系列演讲中多次说过“愿上帝保佑美国”“愿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之类的话。在官方爱国主义叙事中,“上帝”与“祈祷”一再被重申,用来号召民众坚定对美国主流文化精神的信仰。[3]3对胡赛尼这样的美国文化“他者”来说,通过小说书写在精神上回归阿富汗宗教信仰,是对精神生命的确认,也是消除身份焦虑的一剂良药。穆斯林国家将伊斯兰教视为唯一宗教信仰,该教影响力不言而喻。《古兰经》对民众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影响力和约束力甚至超过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胡赛尼受到熏染,其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受到最初的塑型。小说里频繁出现 “毛拉”“真主安拉”“斋月”等词,“安拉保佑(inshalla)”在小说中就出现过36次。《追风筝的人》还有大量关于学校伊斯兰课的描述,毛拉向学生讲授伊斯兰教规,告诉孩子们施天课的益处及朝觐的责任,教给学生每天五次礼拜的复杂仪式,要求他们背诵《可兰经》。他说“饮酒是极大的罪,嗜酒的家伙们将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审判日)受到惩罚。”[3]15-16
“9.11”后的官方叙事进一步强调美国文化精神的信仰力量,这必然给胡赛尼带来一定的精神迫力。他在小说中注入伊斯兰教的相关描述,是寻找自我身份的应对策略,是身份的阐释与表达。在美国,当索拉博自杀被送进医院时,“我” 跪在地上向真主祈祷,“我”相信“他真的存在”[3]335。这隐喻着潜藏在“我”血液里的伊斯兰教信仰意识最终复苏,这样的书写折射出伊斯兰文化对胡塞尼的深厚影响。
胡赛尼还利用故国语言建构自己的阿富汗族裔身份。他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美国《图书馆杂志》评介他“可能是唯一一位用英文写作的阿富汗作家”[3]2。跟母语相比,他使用英语或许更加娴熟。但胡赛尼依旧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词汇与俗语,它们“很自然地交织在情节当中,尤其在对话里。”[10]“我”称父亲“Baba”(12次)或“Baba Jan”(18次),阿富汗主食“Naan”在小说中出现29次。还有其他词语,如“Allah-u-akbar(真主伟大)”“哈拉米(私生子)”“巴巴鲁(哈扎拉人)”等。胡赛尼并未翻译或解释这些方言俗话,只是让读者在上下文中获得意义。这些词语让读者“获取更为形象逼真的体验,仿佛他们自己参与场景并与人物进行交谈。”[10]
胡赛尼曾告诉记者:“诗歌是阿富汗文化意识的重要内容,它绝对影响了我”[7]。他把这种文化熏染融入小说创作,“我”十一岁能背出“迦亚谟、哈菲兹的数十篇诗歌,也能朗诵鲁米著名的《玛斯纳维》”[3]19,哈桑最热爱的书是“《沙纳玛》,一部描写10世纪古波斯英雄的的史诗”[3]29。这些故国词语和文化典籍的出现揭示出胡赛尼潜意识里对家乡的依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9.11”事件激发出美国民众保护家园、打击恐怖分子的决心,恐怖袭击下的官方叙事同样唤醒了胡赛尼对故国家园的怀念之情。当遥远的阿富汗遭受西方的谴责与打击时,胡赛尼在小说文本中嵌入故国语言文化符号,亮出族裔标签,构筑起一个心灵家园。
胡赛尼的小说隐藏着他的终极目标,那就是重塑民族形象,修正“9.11”后美国民众对阿富汗人极为负面的印象。“9.11”事件影响下的西方媒体将阿富汗描述为贫穷落后、无知愚昧、野蛮暴力的民族。袭击事件后,美国国内仇视穆斯林的情绪高涨,“事件后不久,就有600名阿裔和穆斯林遭到遣返”[11]。而美国认定阿富汗这样的国家“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巨大威胁”[12]。胡赛尼指出:“这本书很大的部分发生于苏联侵犯阿富汗战争前的70年代,对许多读者而言,这段时间实际上算个盲点”[3]3。最终他采用“人性化”书写方式,让读者在《追风筝的人》里看到曾充满异域特质且生机勃勃的阿富汗,那里有热闹的集市、温馨的家庭聚会、有趣的风筝比赛,生活那么安宁,然而战争将一切毁灭。“我”的童年十分幸福,但索拉博的童年万般悲惨,这是战争造成的。小说展示父亲、哈桑、拉辛汗等人及“我”的不同个性,旨在强调他们是万千阿富汗普通民众的代表,他们向往和平、热爱和平。个体在战乱中无法控制自我命运,他们经历背叛、遗弃、流亡,胡赛尼让读者看到了真实、鲜活的阿富汗人。“我” 不远千里返回故国打败塔利班头目,救出索拉博,这不仅是心灵救赎,也是“我”对族裔身份的精神认同与皈依。胡赛尼描述个体,重新塑造阿富汗的民族形象,他要告诉世界:阿富汗人不是妖魔,与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大多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是有血有肉、热爱和平的人。
三、美国立场与主体身份选择
胡赛尼受到族裔身份源头文化的召唤,把对故国的情感注入小说创作,意图重塑阿富汗民族形象,通过小说“打开一扇窗,让人们换个角度了解那个在各大媒体出现的遥远国度”[13],这种意图产生于他对自我的选择与定位。胡赛尼在美国接受过系统教育,能够娴熟地使用英文创作。《追风筝的人》语言简练直白,其背后的逻辑与思辨具有西方教育的明显痕迹。后殖民理论先驱法侬认为,“使用某语言就代表着接受某种文化”[14]。从生活环境与语言使用角度看,胡赛尼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同化。在“9.11”语境下,通过小说书写获得西方社会认同,维护内心的安全感,对胡塞尼来说是一种必然诉求。虞建华指出:“族裔作家会与文化语境协商,与预设读者群协商,利用功利或超功利的姿态与自己协商,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民族文化做出坚守、扬弃或者折衷妥协的选择”[5]。因此,透过“9.11”事件的文化语境考察胡赛尼在《追风筝的人》中呈现出的西方文化身份,是认识作家身份特征的必然要求。
“9.11”事件后,伴随“爱国叙事”出现的还有 “悲情叙事”“逃生叙事”“英雄叙事”等艺术创作模式。这些叙事大多关涉家庭,反映出恐怖袭击后人们的精神痛感、困境中的求生本能及顽强本性。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胡赛尼同样痛恨恐怖分子,深切同情恐怖袭击的受害者。2016年9月,胡赛尼接受腾讯文化电话采访时称:“家庭关系是我书写中最常见主题,在我的身份认同里,家庭是最重要的层面,它决定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生活和世界”[7]。胡赛尼在小说中关注家庭主题,描述家庭的破碎与回归,响应小布什总统“继续去帮助悲剧受害者”的号召。他将受到创伤的集体预设成他的隐含读者,用作品抚慰鼓励自己的美国同胞,帮助他们重新认识家庭温情的力量。这能给美国民众心灵以慰藉,与他们的内心世界达成默契、产生共鸣。此时,胡赛尼是一个美国人,他用小说抚慰同胞的集体创伤。
胡赛尼的西方身份特质还体现在他对塔利班脸谱化的形象塑造及单薄的“英雄叙事”上。“9.11”事件后,“虽然塔利班政权并未采取明显的反美举动,但因其在本·拉登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成为美国的敌人”[15]。针对美国的反恐战,有学者认为,“当时国际上同情并支持美国,美国打阿富汗战争时,国际上基本赞成。”[15]胡赛尼本人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感觉自己也受到攻击。身为作家,他用文学创作发声,通过塑造与官方话语中恐怖分子形象十分贴近的小说人物阿塞夫,对官方叙事作出积极回应。阿塞夫的极端性格在与“我”的对话中得到充分显现:
我们把尸体扔在街道,如果家人试图将他偷偷拉回去,我们就把他们一起干掉……留给狗吃,狗肉应留给狗。[5]267
胡赛尼在小说中对阿塞夫的心理、外貌着墨甚少,主要通过语言展示人物形象,因此阿塞夫的形象十分脸谱化。他是阿富汗与德国的混血儿,从小便是个十足的极端分子。他常欺辱哈桑且在斗风筝比赛后对其进行性侵。此外,他还认为“希特勒生不逢时”[3]40。多年后,阿塞夫摇身变为塔利班头目。关于塔利班,有学者认为:“许多作品采取极端贬义的视角解读,把塔利班跟‘叛乱分子’、‘恐怖主义者’等同”[16]。我们暂且不去评断胡赛尼在小说中是否把塔利班组织极端化,但离开祖国30多年的作家对塔利班及阿富汗当今社会的认知应有不足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说:“太久没有在阿富汗生活,对那里的很多问题都不够了解”[7]。胡塞尼在创作中塑造的“阿塞夫”这一形象代表着邪恶与恐怖,美国民众是恐怖袭击的直接受害者,胡赛尼的脸谱化人物塑造本质上符合西方集体对恐怖分子罪恶行径的想象。有学者指出:“胡赛尼对阿塞夫的人物塑造,虽有平面化特点,但他试图去影响读者并向他们证明美国打击阿富汗的合理性”[10]。此外,胡赛尼采用美国社会推崇的“英雄叙事”描述“我”跟阿塞夫最后的对峙:“我”赤手空拳,在对手百般击打之下“我”都要站起来。最后索拉博用“美国制造”的弹弓打败对手,“我们”突围跑出戒备森严的塔利班办公地。有西方学者通过考察亚马逊网上的千余篇普通读者关于《追风筝的人》的评论后发现:“不少读者认为胡赛尼脸谱化人物塑造及单薄的‘英雄叙事’是这本书的不足之处”[17]。但笔者认为,胡赛尼正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方式满足了西方民众的“阅读期待”,表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立场。
“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美国的强者形象,不少民众甚至对美国价值产生质疑。比如,苏珊·桑塔格认为恐怖袭击是“美国人的罪孽、无知和懦弱造成的,我们一直以来都忽视了自己的缺点”[18]。相比之下,胡赛尼却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坚决拥趸者,他在小说中呈现美国文化的优越性及对“他者”的拯救力量,塑造美国救世主形象,这揭示了他的美国身份。
《追风筝的人》第二部分叙述了“我”和父亲的美国生活。来美国后,“我”的内心生发出对这个国家的无限热爱:
我为这个国家的幅员惊叹不已,……它是一条河流,把我带向远方,带向没鬼魂、没罪恶、没往事的远方……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3]132。
相比美国,喀布尔是“鬼魂萦绕之城”[3]132。胡赛尼频繁在小说中使用这种优劣对比,以凸显美国生活的优越感。“我”返回阿富汗寻找索拉博,夜宿司机法里德家。他说地雷夺去了两个女儿的命,而“我”告诉他:“在美国的杂货店里,你随便就能买到十五到二十种麦片,羊肉永远新鲜……自来水很干净,电视都有遥控器,能收到五百多个频道”[5]132。美国与故土的鲜明对照中暗含着作家同西方读者的情感互动。在“9.11”事件后的特定语境里,胡赛尼通过这样的文本操控,激发西方民众对家园的珍视与热爱,表达自己对美国生活的认同。在小说中,阿富汗被描述成地狱。夜深人静时“我”“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它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3]258。小说中,瓦西德让“我”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上的其他人们”[3]229。作家通过小说文本向西方社会指出,让这个国家 “没有希望”的罪魁祸首是塔利班。阿塞夫是塔利班的典型代表,是毫无人性的极端人物,而“我”来自美国,是官方话语中自由的人性的文明代表,两者是敌对的。最后的对峙中“我”对阿塞夫的胜利,隐喻着美国的胜利。“我”借父亲之口说出:美国是个“鲁莽的救世主”[3]121。胡赛尼还在小说中表达出奔赴美国是摆脱歧视、不公正、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有学者指出:“‘我’和父亲逃到美国象征着改变与解放”,索拉博在小说最后的那微微一笑则体现出“他在美国的护佑下会得到安全与幸福”[10]。至此,胡赛尼通过主观身份选择,在“9.11”事件后的特定语境中颂扬美国主流文化的优越,告诉西方民众美国有消除贫穷、落后与不公正的能力,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四、结语
“9.11”事件将阿富汗变成国际政治焦点地区,西方官方话语对故国民族的扭曲描述召唤出胡赛尼对文化源头的怀念与渴望。他通过小说确认个体身份并试图重塑阿富汗民族形象,这是主体的选择与定位。针对“9.11”事件带给西方社会的极大震撼,胡赛尼通过文学创作彰显身份主体的西方视角,响应官方话语的呼吁,构建与西方读者的情感交流机制,进而巩固身份,维护内在心理安全感。胡赛尼的双重民族身份交织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身份双重性赋予他独特的创作视角,也为其带来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