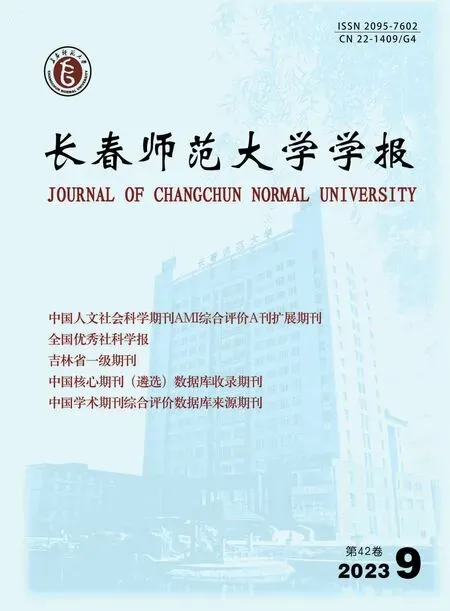近十年国产青春类型电影的情节设置
李佩遥
(长春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近年来,青春类型电影已经在国内类型片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此类影片通过场景的构建、情节的铺展增强观众的代入感,抓住观众缅怀青春的心理感受,在虚构的情节中倾注真实的情感。但是,片面地追求票房、轻视情节会把观众的情感消耗殆尽。情节是电影的核心。如果没有好的情节,就无法实现故事创作者的表达和诉求。当前,国产青春类型电影如何摆脱模式化创作,将人物的青春经历更好地与社会现实、时代变革相融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
一、空间设置对国产青春类型电影情节设置的作用
在电影叙事中,影像空间是一种带有隐喻和大量信息元素的重要符号集合。正如安德森在《文化地理手册》一书中所说:“主体性与空间连接在一起,而且不断与空间的特定历史定义重新绞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和主体都不是自由漂浮的:它们相互依赖,复杂地构成统一体。”[1]人物不能脱离场景而独立存在。因此,导演要展开故事情节的铺设,就要为故事选取合理的空间设置。相较于文艺片的精巧、考究,青春片的空间构建策略显得简单很多。“校园”作为统一秩序的代名词或象征物,自然而然地成为青春片首选的故事场景。以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为例,电影以从校园到都市写字楼的两个主要叙事空间的转换为线索,牵引人物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成长。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校园场景的取景地为南京,但对这座古都的选取却并不是为了增加电影叙事的厚重感。在影片开场时选取了校园迎新活动的场景,以张开与许开阳的视角,将观众带入到布满彩旗、横幅的校园门口,渲染出大学校园充满活力的热烈氛围。导演采用以暖调为主的影视造型手法,使影片画面色彩饱满、艳丽。导演为了将“青春”与“美好”进行勾连,在影像空间上呈现了既明亮、艳丽又带有柔焦质感的“滤镜”式处理。例如,郑薇第一次进入男生宿舍时,宿舍空间场景的搭建主要突出男生寝室的脏乱,让本就不甚宽敞的宿舍显得更为拥挤、凌乱。这种近乎“满目疮痍”的脏乱环境与陈孝正制作的精致建筑模型形成强烈的反差感。在阮莞与郑薇关系“破冰”的情节中,通过光影与空间的结合处理,女生宿舍中台灯的光芒营造出烛光的效果,建构了青春校园的集体归属感。郑薇在舍友七嘴八舌的聊天中意识到自己对陈孝正的感情,只能怀着纠结的心情,穿过空寂无人的校园,寻求情感热线的帮助。空寂无人的过街天桥象征着郑薇内心的孤立无援,在桥的两端一蓝一黄的灯光便是少女情感中忽冷忽热、阴晴不定的感受。小卖店外的狭窄公共电话亭是一个无人的空间角落,为主人公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让她可以倾吐内心的苦闷。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影片的前半段构建的空间场景多是校园生活场景。这种“日常感”代表着国产青春类型电影的氛围选取,通过大多数人近似的青春生活经历,营造出集体回忆,进而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作为叙述空间主体的大学校园,隐含着有限的自由。之所以说是有限的自由,是因为大学生一方面有更多可供自我支配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不能逾越基本的社会身份规训。这种社会身份规训意味着相对简单的人物关系,与故事后半段中都市生活的漂泊感带来的无序性形成鲜明对比。
影片的后半段情节主要发生在大都市。这一阶段的空间场景设置更加简洁、空旷,暗示着都市生活的压抑和冷漠。例如,郑薇陪同走投无路的阮莞去医院打胎的情节中,医院走廊的场景突出了狭长的纵深感,地板和窗外的蓝色光线反射在主人公的脸上,使光线成为影像中阴影式构图的突出点。清冷、灰暗的色调下,镜头中的人物一直处在画幅的边角位置,象征着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预期和掌控也处于边缘的位置。在郑薇与林静重逢的情节中,空旷的走廊干净、单调,显得极度压抑。这些都显示了青春幻梦的破碎和现实生活的残酷。“空间不仅是被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它还是由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要求、伦理和美学,也就是意识形态来塑造成型并加以调整的。”[2]情节的叙事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激化了种种冲突。面对爱情与社会的双重打击,郑薇青春时期懵懂、冲动毛躁的情感模式逐渐转变为沉静成熟。这既是导演对美好青春时代的向往与指认,也揭示了青春成长必经的阵痛与迷惘。
导演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有机而连贯的情节结构,通过校园和都市两个叙事空间的对比,以及光线、色调和环境的营造,成功地呈现了国产青春电影关于成长阵痛的主题,同时饱含着导演对青春时代悲凉的礼赞。这满足了观众对国产青春类型电影的观影期待,为影片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和审美意识。
二、镜像对照下国产青春类型电影情节设置的叙事作用
青春类型电影将人物身份聚焦于年轻人。青少年群体在情感模式上尚未成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自身的体验感,因而对未来生活的选择充满不确定性。他们的成长道路并不顺遂,需要在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不断冲突中完成自我人格的独立。自我认知不再依靠外部评价,而是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路历程。身份认同问题广泛存在于各年龄层中,其中以青少年尤为明显。”[3]国产青春类型电影注意到青少年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并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青春电影并非单纯呈现少女情感和生活状态,而是以此为载体,挖掘其从青年到成年的过度中的自我意识的觉醒”。[4]
在影片《七月与安生》中,安生父亲早逝,母亲忙于工作,导致她的性格放荡不羁、孤僻,却又渴望关爱;七月家境优渥,倍受宠爱,造就了她单纯、温婉却步步为营的性格。影片的情节叙事起始于七月与安生在学校操场上的相识。导演通过对人物外在形象的塑造,区分两人截然不同的生长背景,如:七月梳着干净整齐的头发,公主裙;安生则留着爆炸头,袜子有洞。除了人物造型上的差异,人物的对白也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别:安生常对七月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老土”,七月则常说“我不敢”。七月的男友是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安生的男友是放荡不羁的流浪歌手。这些差别强化了两个年龄相仿女孩的性格差异:安生散漫自由,七月渴求安稳。
两个女孩被对方身上的特质深深吸引,却因为都爱上男生家明而分道扬镳,使故事线从此开始一分为二。影片的叙事采用镜像对照的方式:安生在十八岁的时候辍学,与歌手男友同去北京,一路流浪;七月则在家乡按部就班地上学,去银行工作,准备和初恋结婚。个体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面对自我时认清自身的平凡乃至平庸,真正做到与生活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5]。
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曾经漂泊流浪的安生想停下来过安稳的生活,而寻求稳定的七月则由于新郎逃婚,终于开始逃离沉闷的生活轨迹。无论是早慧的安生,还是青春叛逆期迟来的七月,她们对生活的反叛实际上是一种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无奈的逃避。“当鲜活有力的内心遭遇无可奈何的岁月,他们只能借助思想或行动上的逃离来宣泄心底奔腾的怒意。”[6]幼年与成年的分界线是在与坚硬的外部世界的碰撞中逐渐形成的,个体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少年时通过外化的叛逆行为强调自身精神品格的与众不同,也终将随着时间流逝,被岁月磨平棱角,最终选择回归“平凡”与“庸碌”的生活。
《七月与安生》用镜像化交叉叙事的方式表现两位主人公交错对调的人生轨迹,通过“他者”发现“自我”,继而产生自我身份认同感。电影之所以成为一种感染力和影响力极强的艺术表现形式,除了因为其包含积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更是因为其具有伟大的艺术审美和娱乐功能。当情节设置的感性细节贯穿叙事过程时,情节设置与影片情境共同发挥作用,使电影产生了充满审美意趣的整体力量。电影对每个角色的出场都通过情节设置进行了细致描摹,采用双线并行的剪辑手法,增强了情节设置的冲击力和艺术表现空间,使观众更好地感受电影传达的情感力量,并引导观众理解情节和情境。
三、近十年国产青春电影情节设置的反思
(一)“怀旧视阈”下情节设置的同质化
国产青春类型电影能展现一代人的青春生活,能传达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其背后的文化力量不容小觑。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导演都曾拍摄过带有自传性质的青春类型电影,青春片的真实性和普遍性让观众主动投射情感。
自《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并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后,电影投资方看到了同类型题材影片的市场前景,随之而来的一批情节设置类似的国产青春电影纷纷上线。但是,这些影片甚少展现青春时期的迷茫、困惑,主要展现“怀旧视阈”下同质性的青春追忆。青春记忆被笼罩在过于厚重的滤镜之下,丧失了青春期情感所特有的复杂而矛盾的审美特质。“作为一种现代性社会别具一格的社会情绪,‘怀旧’呈现出对历史黄金时代或者黄金时刻的‘回忆’,含蓄的隐藏对当下社会的缠绵怨怼。”[7]基于“怀旧视阈”的国产青春电影,在情节设置上以对青春臆想式的怀旧为主,无可避免地变为一种同质化的作品。
“怀旧视阈”下的国产青春类型电影同质化严重,在情节的设置上,通常都有怦然心动的瞬间、短暂热烈的相爱,又通常以男女主角分手作为结局。《匆匆那年》(2014)和《同桌的你》(2014)中有着非常类似的情节设置,在影片中采用双线叙事,以对青春的追忆作为开端。《匆匆那年》通过画面叠化处理,将故事叙事带回校园时光。《同桌的你》则以林一准备参加初恋情人林小栀的婚礼为开端。林一在飞机上打开他准备送给林小栀的结婚礼物,画面逐渐虚化,转入青春时代的校园场景。在人物设置上,林小栀和方茴都由转学而来,在与男主见面后经历了怦然心动的瞬间,并经历了美好又温暖的初恋。从情节设置的符号来看,茂密葱郁的树荫与校园、明亮宽敞的教室、混乱的打群架、无坚不摧的友谊等,都在其表意系统里提供特定的叙事功能。两部影片在情节设置上都融合了负载青年人怀旧符号的重要历史时刻,营造了过去的时空氛围。
当“怀旧视阈”下的青春命题斩断了与现实生活的直接联系,青春的广袤被压缩得只剩下“臆想式的爱情”和“俗套校园故事”,情节设置也不免落入同质化的陷阱。“怀旧语境”下的痴女怨男情节和“同质化”下俗套的电影情节,伤害了观众的审美愿望,偏离了大众的生活经验,对青年人带来错误的价值观导向。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应该竭力避免盲目跟风,在情节设置上要将青春的尺度拓宽,为观众提供多重维度、多种形式的青春讲述。
(二)“后喻时代”下情节设置的无序性
《七月与安生》由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被改编为同名网剧。在屡次改编的过程中,创作者关注的不再是人物在境遇改变过程中由内而外的成长,而是对世俗伦理的叛离。实际上,青春题材影片吸引观众的核心绝不在于对人物表面上离经叛道行为的演绎,而在于对乖张行为背后隐秘的情感波动的呈现。当下的许多国产春青电影只学到《猜火车》(1996)等经典欧美青春电影的皮毛,却未掌握影片的内核与精髓,呈现出一种“后喻时代”的无序性。
“后喻时代”的概念来自玛格丽特·米德。刘建平教授认为:“‘后喻时代’主要指传统处于被教者的年轻世代扮演了施教者的角色,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年轻人,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代际角色反转造成了传统断裂、价值失序、代际和族群对立等文化冲突”[6]。在“后喻时代”的背景下,许多导演试图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用“恶搞”“拼贴”“无厘头”等方式进行创作,很难捕捉到真实的青春感受。如《遇见你真好》(2018)在选角和宣发等方面做了努力,但无法弥合国产青春类型电影情节设置的无序化和情节逻辑的不自洽。该片充斥着“小鲜肉”“X飞行器”“弹幕”等台词,宛如一场拼接时下流行元素的荒诞闹剧,使影片无法得到观众的共情。
“后喻时代”电影需要迎合互联网语境与年轻一代观众的观影偏好,但不能忽视青年人的现实生活。国产青春类型电影情节设置的失序性和电影情节结构的断裂,会摧毁电影观众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近年来国内市场涌现出一批青春类型电影佳作,这些影片阐述生命个体的生存困境,聚焦内心身份的自我认同,如《过春天》(2017)、《嘉年华》(2017)、《少年的你》(2019)等。这些国产青春片以个体经历的情节设置,挖掘年轻人独特的价值和思想,于青春底色之上勾联现实生活的不同层面,并尝试作了不同程度的类型融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青春物语,展现了电影艺术的审美意蕴与人文关怀。创作者应当从中汲取经验,创作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作品,逐步把中国青春电影精品化、特色化,产出本土特色和国际视角兼具的电影。
——评电影《七月与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