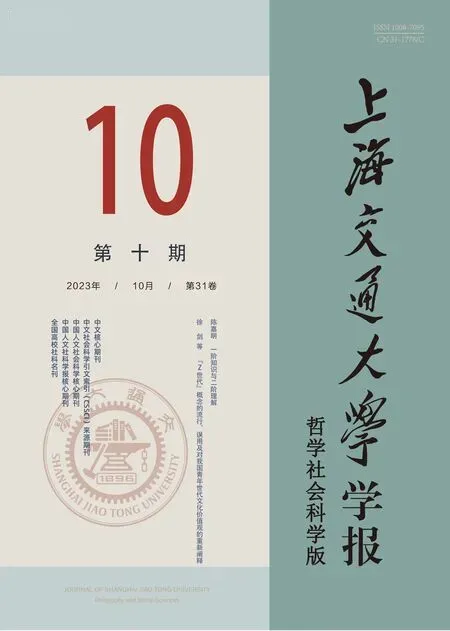“连接”与“重构”: 反思媒介社会学的议题、理论与方法
韩瑞霞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如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就以“结构与能动的辩证: 数字时代的媒介社会学再出发”为题组织了专门的会议,而在思想理论界,一批对媒介社会学进行理论和学术脉络梳理的研究成果也爆发式地涌现,(1)李红涛、黄顺铭: 《“驯化” 媒介社会学: 理论旅行、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践》,《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42卷第3期,第129—154页。如李红涛、黄顺铭从理论旅行视角,运用文化中间人的概念就国内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的认知进行了画像勾勒;白红义则从韦伯和帕克经典研究追溯了媒介社会学起源,并从新媒介STS转向、新理论以及呼唤中层理论的想象力等多重角度对当前媒介社会学走向进行了阐发;(2)白红义: 《作为“理想型”的媒介社会学经典创立者: 重访韦伯与帕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2卷第12期,第34—41页。戴宇辰则从ANT理论视角揭示出未来媒介社会学视角从物质性向社会性方向的转移趋向。(3)戴宇辰: 《“旧相识” 和“新重逢”: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 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1卷第4期,第68—88页。与此同时,大批媒介平台社会学研究、数字新闻劳动、媒介社会史的实证实务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散布在新闻传播研究的各大学刊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媒介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现状?是否在当前兴盛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或一个共识性的争议问题?媒介社会学是应该属于新闻传播学科和社会学学科之下的交叉型二级学科,还是应该成为一个新型的不应被过度定义的“涌现”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该领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梳理和学术范式廓清的意义。
实际上2022年姚文苑、胡翼青(4)姚文苑、胡翼青: 《再思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兼与李红涛、黄顺铭商榷》,《国际新闻界》 2022年第44卷第5期,第88—109页。和黄顺铭、李红涛(5)黄顺铭、李红涛: 《何来“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兼论媒介社会学的“连续统”观念与诠释社群》,《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44卷第6期,第108—129页。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对话性文章可以被视为对这个问题的争议性协商。相对于黄、李注重从传播学的视域将媒介社会学看成一个连续统而划分为大众传播社会学、新闻生产组织社会学以及当代互联网媒介社会学,姚、胡从社会学学科脉络出发,指出对于媒介实际是媒介作用的三阶段认知才是社会学视角媒介研究的核心,因此并不能在对“媒介”与“社会”概念无法一致廓清的前提下谈边界问题。而黄、李回应指出,自身研究是聚焦“实然”而非“应然”,对媒介社会学的术语使用也是基于约定俗成,学术研究不应聚焦壁垒,而应更多地注重对学术空间思考的激活。实际上,近年来国外传播与社会学界也开始对学科领域范式激活进行了思考,以该方向活跃领先的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近年来推出的课程大纲观之,主要体现为多元视角的切入,而不存在统一的范式方向构成。该校华人学者陈文泓在传播领域期刊发表的文章(6)Wenhong Chen, “Abandoned Not: Media Sociology as a Networked Transfie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 vol.21, no.5(2018), pp.647-660.也集中阐明了这一观点,她认为之前对社会学“遗弃”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说法是一种过度误读,通过梳理美国之外的学术贡献和美国国内社会学制度和组织发展中的集体和个人记忆,她主张将媒介社会学视为由问题驱动的网络化跨领域。通过总结三篇文章代表的学术观点,可以发现“语境”构成了三篇文章的立论基点。姚、胡的文章是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综合的知识语境对“媒介社会学”整合术语发出质疑,并基于时代语境,以黄旦媒介射入视角为代表,指出在当下深度媒介化阶段媒介社会学的可行性;而黄、李的总结则是以传播学领域为主体的实然梳理;陈文泓的文章则从传播学和社会学学术场域的美国学术界的发展历史梳理中重申媒介社会学作为一种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网络研究的意义。可以说这些研究构成了我们当下思考媒介社会学展开的学术起点或“边沿”,那么具体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呢?2022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与国际传播学会(ICA)合办的“智能传播与真实世界”会议中,部分学者的发言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如特里·弗洛(Terry Flew)讲述了媒介信任在组织运作研究中的重要性,刘幼俐解读了未来生活场景变化的多元启示意义,而喻国明则从智能传播革命的深度实践逻辑对未来社会形态构建上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也就是说当下学术界出现了将媒介嵌入普遍生活场域微观、中观、宏观的总体学术思考趋向,真正回归到了媒介“全面中介化”各类议题的思维范式。
本文是在上述研究背景下,尝试将“媒介”引入社会学“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经典解释框架中,对“行动-媒介-结构”视野的“媒介社会学”展开进行前期议题、理论和方法的准备工作。本文认为,当前媒介社会议题已经进入媒介成为社会变迁和运转结构性及中介性变量的语境时刻,而经典社会学理论家,无论是吉登斯、布迪厄,还是哈贝马斯都在理论框架中预留了媒介的位置,同时以布洛维、格兰诺维特和桑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中层理论又为解析媒介全面中介化的各类具体社会议题提供了解释资源,最后,“界面”(又译“接口”)方法在统合社会科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为未来媒介社会研究提供了方法进路。总之,对媒介的呼唤,乃是经典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传统的继续,同时媒介的全面渗入也在重构当下我们对媒介社会研究的理论进路和实践思维,本文希望从第三条道路出发为当下媒介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提供助力。
一、 议题与视角
(一) 学术史: 出走的“罗拉”与新闻生产社会学
与国内传播学界把社会学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源流从而开放地对待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不同,长期以来,国外的媒介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的主流领域并没有占据一席之地,(7)Matthias Revers, Casey Brienza, “How Not to Establish a Subfield: Media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49, no.3(2018), pp.352-368.以至于如卡茨等著名的传播研究学者都提出了“社会学为什么把传播抛弃了”这样的问题。(8)Elihu Katz, “Why Sociology Abandoned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40, no.3(2009), pp.167-174.相反,大量从事媒介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学者主要寄居在新闻传播系科中,这一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30、40年代传播研究向心理学议题的转化,从而越发远离传统社会学对结构议题的关注。(9)Silvio Waisbord,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2014, pp.1-8.如在2014年出版的《媒介社会学再评论》导言中西尔维奥·韦斯伯(Silvio Waisbord)就指出,尽管早期芝加哥学派树立了把媒介与社会勾连起来的学术传统,并出现了以帕克移民报刊研究为代表的实践佳作,但最终20世纪30、40年代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学者对传播效果关注导向的后续媒介研究更多是向认知传播脉络演进。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研究视域内,“公众舆论”也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量,尤其是在反映社会重大变革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查尔斯·蒂利(C.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 Skocpol)以及迈克尔·曼(M. Mann)等有重要影响力学者的开创性著作中,公众舆论和媒介的作用几乎没有被提及。换言之,困在功能主义、文化主义和实证主义范式中的公众舆论,在涉及社会权力变革相关的集体行动中几近失语,这也导致了在反结构主义和反功能主义脉络中媒介及其相关议题无法得到重视。(10)Silvio Waisbord,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2014, pp.1-8.既然媒介只是正式规范社会体制中维系社会的桥梁,那它对于反结构的变量生成就基本没什么助益,因而这类研究遭到忽视也就变得理所当然。然而,近年来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凸显,尤其是2010年前后社交媒体与中东变革的直接关联,促使对媒介作用的重视重新进入了社会学视野,并进而产生了对媒介在社会动员集体行动中多层作用的思考。(11)Bruce Bimber, “Three Prompt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34, no.1(2017), pp.6-20.不过,即使这一发展从新闻传播学科来看值得欣慰,但总体而言,社会学从媒介研究中出走,无论是系科建制还是实际学术成果积累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确是事实。在这期间,媒介社会学更多是以新闻社会学的面貌呈现。
当进行媒介社会学的学术搜索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关键词涌现,都可见迈克尔·舒德森(M. Schudson)、盖伊·塔克曼(G. Tuchman)、赫伯特·甘斯(H. Gans)和托德·吉特林(T. Gitlin)是最为核心的贡献者。而国内学界则以陆晔、潘忠党、黄旦等学者的早期实践为范本,(12)陆晔、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7—59页。(13)黄旦: 《传者图像: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之后引起了人们对新闻场域社会学分析的重视。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被称为“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这些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将新闻生产实践与市场和国家、权力和行动等社会学的结构性概念联系了起来,并将行动者置于社会实践网络来考察,近年来布迪厄(Bourdieu)“场域”概念的引入更是丰富了社会学新闻生产议题的实践操作能力。库兰(Curran)等人认为,这一领域可分为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组织网络和文化取向路径,(14)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Janet Woollacott, “The Study of the Media: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15-34.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总结容易削弱新闻生产研究的“行动—结构”视角,而被传播学传统划分范式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路径所覆盖。(15)Graham Murdock, “Misrepresenting Media Sociology: A Reply to Anderson and Sharrock,” Sociology, vol.14, no.3(1980), pp.457-468.事实上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媒介社会学研究在更大范围议题内不可见的原因。如库尔德利(Couldry)、麦奎尔(McQuail)所分析的: 尽管社会学视角事实上长期以来支撑着许多批判性研究领域对传播、文化、信息和媒体的分析工作,(16)Nick Couldry,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edia: Do They Connect and on What Terms?” in A. Hepp, F. Krotz, S. Moores, et al., eds.,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Inc., 2008, pp.93-110.(17)Denis McQuail,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1(1985), pp.93-111.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分支名称的固化,社会学视角总是不可见。(18)Silvio Waisbord,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2014, p.6.但无论如何,围绕着新闻生产、记者劳动等主题确实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的平台研究,诸如劳动过程理论的引入,丰富了媒介社会学的学术积累。(19)R. Dickinson, “Accomplishing Journalism: Towards a Revived Sociology of a Media Occupation,” Cultural Sociology, vol.1, no.2(2007), pp.189-208.也正是平台生产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为新闻社会学向媒介社会学转型提供了契机。
(二) 方法路径: 两种变量逻辑与媒介中介化视野
尽管有韦伯等更早的先驱者,但学界一般把媒介社会学的源流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帕克所做的报纸与移民研究,这种梳理与罗杰斯传播学史的主流脉络相一致。(20)E. M. 罗杰斯: 《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帕克的经典研究,(21)Robert E. Park, “Urbanization as Measured by Newspaper Circ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5, no.1(1929), pp.60-79.直接将报纸发行视为理解一个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际互动运转的切入视角。在帕克那里报纸不只是作为如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运转的沟通工具,即传播的行政研究或曰结构功能视角对其的定位,而是将报纸的发行和传播与城市社会的组织运行、结构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在此种意义上,报纸的传播形态和状态更接近于城市连接模式的“表征”,媒介的作用实质上实现了凯瑞传播仪式观和传递观的完美融合。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后,正如雅各布斯(R. N. Jacobs)总结的: 对媒体效应的关注,导致对媒介形态的研究对标的不再是整个社会的结构运转,而是“大众社会中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个体”,(22)Ronald N. Jacobs, “Culture, the Public Sphere, and Media Sociology: A Search for a Classical Founder in the Work of Robert Park,”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40, no.3(2009), pp.149-166.即便是如卢因等人的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行动而非社会结构。再加之“宣传”研究的盛名,(23)Jeffery Klaehn, Andrew Mullen, “The Propaganda Model and Sociology: Understanding the Media and Society,” Synaesthesia: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vol.1, no.1(2010), pp.10-23.媒介研究的心理学转向几乎导致媒介的工具化视角盛行。媒体研究逐渐地与社会学关涉主题脱离。而在另一面,被视为媒介社会学重要代表人物的甘斯就曾直言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许多社会学家对媒体及其产品表现出明显的蔑视。(24)Herbert J. Gans, “The Famine in American Mass-Communications Research: Comments on Hirsch, Tuchman, and Gec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7, no.4(1972), pp.697-705.其背后显现的就是社会学的关注兴趣从媒介退回到了人口、组织生态、资源动员和精英再生产这些对社会结构变迁有更大解释力的影响变量上。(25)Ronald N. Jacobs, “Culture, the Public Sphere, and Media Sociology: A Search for a Classical Founder in the Work of Robert Park,”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40, no.3(2009), pp.149-166.
上述追溯点明的一个重要事实是: 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正式成立并将“媒介”或曰“传播”视为主要研究对象后,学科的独立在使研究对象具象化的同时,却将传播与其他的社会结构议题分离开来。这在研究路径上显现为将“媒介”视为因变量而非影响因素。如本森(Benson)在重要的旗帜性文章《将媒介社会学带回来》(26)Rodney Benson, “Bringing the Sociology of Media Back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21, no.3(2004), pp.275-292.中借用菲利普·施莱辛格(P. Schlesinger)的警告指出: 多年来新闻传播研究界“媒体中心化”的趋势导致别的研究学科出现“媒体恐惧症”现象。媒介传播领域过度精致化的趋势导致在将媒体作为自变量分析其他社会或政治现象时,只能笼统地提及“媒体因素”,而在将媒体作为各类社会事实发生的空间时,却不足以将其作为充分的结构性环境变量。本森就借用卡斯特的研究指出,当下政治尽管显得被电子媒介逻辑“结构化”了,但是显然只依赖于媒介不足以解释真实发生的社会政治现实。(27)Rodney Benson, “Bringing the Sociology of Media Back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21, no.3(2004), pp.275-292.也就是说不论把媒介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如果不将其与其他社会结构性变量勾连,不与其他更为宏观及具体的社会演进过程相连,媒介研究就无法走向纵深。
那到底应该如何破局?事实上当下媒介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理论界近30年来的积累为其提供了双重契机。首先,从媒介发展角度观之,当下媒介的发展已经从工具使用视角更有解释力的阶段向平台及环境视角转移。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层面。在物质层面体现为媒介传输工具成为继公路、铁路后社会维系的基础设施架构;而在社会层面则体现为以App为代表的智能媒体平台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以Web2.0向Web3.0的转型为例,2010年左右中东地区多个国家发生变革,在短期内将社交媒体的动员及组织能力研究推向高潮,产生了与之前积聚十年的互联网研究汇合的趋势,并由此兴起了一波媒介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研究的高潮。(28)Homero Gil de Zúiga, Nakwon Jung, Sebastin Valenzuela,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17, no.3(2012), pp.319-336.因为该事件代表着媒介能在社会变迁最为基本的结构面实现转型和断裂推动,如果说这是从社会上层建筑改换方面体现了媒介的驱动力量,那么2000年前后卡斯特(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基本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群体认同各个层面指出了互联网所代表的信息科技力量在社会基础架构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时空二维的影响基本奠定了媒介场景构建时代的分析范式。而从时空的角度谈论社会变迁恰恰可以跟同一时期综合派社会理论家吉登斯(Giddens)关于“脱域”的研究和布迪厄“场域”的研究实践结合。说明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和中观层面,互联网都带来了结构性的动力。当前互联网的影响进一步向“行动”视角蔓延,表现为梅洛-庞帝(Merleau-Ponty)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关于知觉具身研究在媒介场景时代自我及群体互动研究中的强大延展力。也就是说随着3G往上技术的发展,媒介和人的融合正在快步向多年前唐娜·哈拉维(D. Haraway)所提的“Cyborg”型构迈进。(29)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p.117-158.2021年元宇宙概念的崛起,进一步将媒介构建场景及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组织运转中的中介化作用全面推进。在此情势下,媒介在社会学两大支撑概念“行动”和“结构”中的中介影响力变得可操作和迫在眉睫。提倡“媒介作为‘实践’”的视角和媒介中介化其他所有社会事实的研究在当前时代变得切实可行。(30)Roger Silverstone, “The Sociology of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p.188-207.(31)Nick Couldry,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vol.14, no.2(2004), pp.115-132.
上述发现可概括为: 伴随Web1.0到Web3.0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媒介已经具备作为社会变迁结构性变量的能力,是社会再生产运行黏合剂和场景空间,并助推社会行动者概念从“人”向“人机联合体”型构转型。也就是说从浮现的研究议题角度观之,现在已经到将“媒介”与社会学经典解释概念“结构”与“行动者”紧密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的时刻,而这是形成“行动-媒介-结构”研究路线的基石。
二、 理论迁移与生发
(一) 基于传播学科主体的STS向ANT视角的转移
相对于空泛地谈论将媒介研究推向中介化所有社会事实的视角转向,寻求更适合解释当下媒介全面建构人们行动和社会组织再生产的理论支撑显得更为必要。对这一方面的理论梳理我们需要遵循渐次化逻辑。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后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比尔·盖茨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标志,预示着媒介对人们的影响将从技术嵌入社会空间的物质层面展开。瑞斯(Reese)和苏梅克(Shoemaker)在总结卡斯特、布迪厄、哈贝马斯理论适用性的同时指出媒介的地理隐喻转向可以被称为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32)Stephen D. Reese, Pamela J. Shoemaker, “A Media Sociology for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The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19, no.4(2016), pp.389-410.尽管人们努力地从传播研究甚至社会理论的原有资源中寻求力量,然而在这一时期具备技术倾向的概念无疑更具有解释力,典型体现为STS即科学技术研究理论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瓦伊克曼(Wajcman)和琼斯(Jones)于2012年《边界传播: 媒介社会学和STS》的文章中指出卡尔霍恩(Calhoun)将传播/媒介视为“现代性基础设施”的观点适合弥合科学技术研究注重技术“物质性”和传统传播研究注重“象征性”的界限。(33)Judy Wajcman, Paul K. Jones, “Border Communication: Media Sociology and STS,” Media, Culture &Society, vol.34, no.6(2012), pp.673-690.在物质性的部分,利夫鲁的定义更有启发意义,即“技术设备/设施作为客观实体所具有的物理特征,它使技术在某种条件下基于特定目标值得并能够被使用”。(34)易前良: 《平台研究: 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基于传播学与STS 对话的学术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28卷第12期,第58—75页。与技术的物质性和使用性密切相关的是近年来关于“可供性”的研究。可供性是指“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与其需求或目标有关)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35)Ronald E. Rice, Sandra K. Evans, Katy E. Pearce, et al., “Organizational Media Affordances: Operationalization and Associations with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67, no.1(2017), pp.106-130.随着Web2.0向Web3.0过渡出现的平台经济兴起,以平台的物质性结合可供性为媒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客观上也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STS研究与传播研究的汇合。(36)易前良: 《平台研究: 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基于传播学与STS 对话的学术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28卷第12期,第58—75页。
那么STS研究到底在如何展开?巴杜阿尔(Badouard)等人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国家STS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现状的分析具有总结性意义。第一类即STS 和媒体研究只是高度借鉴和应用对方的一些概念和经验案例,但没有形成真正的融合视角。第二类以“中介(mediation)”和“配置(dispositif)”作为“边界对象”,两个领域之间就这些概念进行探讨。第三类则是将“mediation”作为共识背景,通过多重实践策略将传播研究与STS研究深度融合起来。(37)R. Badouard, C. Mabi, A. Mattozzi, et al., “STS and Media Studies: Alternative Path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ECNOSCIENZA: Italian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 vol.7, no.1(2016), pp.109-128.也就是说“mediation”是STS和媒介研究结合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STS传统中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路径成为最为实用的范型,即脱离“技术决定论”,将技术与社会文化实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此思路下,戴宇辰在梳理了奥德松(Oudshoorn),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利夫鲁(Lievrouw)和利文斯通(Livingstone)等人的研究后,将STS和传播研究的走向概括为从对技术的关注转向注重被赋予更多“能动性”的使用者,从对注重传者“权力”的媒介生产领域的关注转向注重媒介使用者“驯服”能力的媒介消费领域,从对微观认知行为视角的媒介效果的关注转向对媒介具有社会实践型构力量的媒介影响研究。(38)戴宇辰: 《传播研究与STS 如何相遇: 以“技术的社会建构” 路径为核心的讨论》,《新闻大学》2021年第4期,第15—27页。而从更为操作性的层面,当前的“界面”(interface)研究可以看作一个可为路径。尽管如马雷斯(Marres)和格利茨(Gerlitz)等研究者常常将这种方法简化为以“共现分析”为代表的对数字媒体界面人类行动动态实现追踪预测的方法,(39)Noortje Marres, Carolin Gerlitz, “Interface Methods: Renegotiating Relations between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STS and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4, no.1(2016), pp.21-46.但实际上“界面”研究就像当年的Cyborg转向一样,它可以成为描述分析人类行动者与媒介结合的各类实践场域。
区别于传统注重物质性的STS研究与传播研究结合的讨论,(40)Pablo Boczkowski, Leah A. Lievrouw, “Bridging ST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holarship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pp.949-977.ANT (Actor Network Theory,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似乎走得更远。相比STS研究注重从技术这一相对结构性的元素入手,ANT视角注重从行动者入手来进行媒介化社会中的实践研究。这一理论视角一般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 Latour)、米歇尔·卡伦(M. Callon)和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 Law),但在传播研究中被上升为显性问题却是始于2008年库尔德利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媒介: 它们是否连接以及以什么条件连接》一文。(41)Nick Couldry, “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edia: Do They Connect and on What Terms?” in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et al., eds.,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Inc., 2008, pp.93-110.ANT视角的最核心认识论表述就在于它拒绝将行动者仅仅限制在人的本体论认知中,而是强调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在此情境下,行动者不再只是个体,还可能指涉任何非人类实体,更重要的是该理论注重在“关系”中理解各类“行动者”的存在。而媒介的发展,恰恰在于改变ANT中N的存在形式。即N(network)必须经过media的中介,呈现出非媒介就无法理解当下语境中行动者网络的状况。(42)Maekus Spöhrer, “Applications of Actor-Network Theory in Media Studies: A Research Overview,” in Markus Spöhrer and Beate Ochsner, eds., Applying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in Media Studies, Hershey, Pennsylvania: IGI Global, 2017, pp.1-19.以此为起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行动者已经被媒介全面建构或者与媒介全面勾连在一起时人类实践场域的全部社会活动。ANT理论反复强调的一个前提是: 放弃行动者是一种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能力的假设,在此基础上,以新的“行动者”概念为基础才能理解完全变化后人类实践场域的生活。尽管有研究批评这种视角可能在人类活动的表象领域如权力、政治问题上出现失语,即库尔德利所担心的理论解释的“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tism),(43)Nick Couldry, “Form and Power in an Age of Continuous Spectacle,” in David Hesmondhalgh and Jason Toynbee, eds.,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pp.175-190.但是从学术理论层面来讲,以媒介为中介基础的新的行动者理论对于理解媒介全面中介化后社会实践场域的行动和结构变化无疑更有解释力。
(二) 一种保守却实用的路径: 社会理论的全面挪用与嫁接
相对于前景式地从媒介视角对社会研究的对象、理论进行重建,将当前广泛的社会理论挪用嫁接到媒介社会议题中,显得更为务实。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理论界三大宏观理论家吉登斯、布迪厄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都可作为基础。(44)Stephen D. Reese, Pamela J. Shoemaker, “A Media Sociology for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The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19, no.4(2016), pp.389-410.吉登斯社会学理论的集大成贡献体现在将结构和行动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弥合,“结构二重性理论”或曰“结构-能动”理论弥补了涂尔干谱系注重“结构”研究路径和韦伯强调个体“行动”研究路径的缺陷,通过规则、资源等概念实现了行动和结构的互动连接。这一理论取向天然避免了媒介技术论的结构主义倾向,同时对社会过程的关注,又为人们解释性理解媒介在各类社会行动展开和社会关系形成中的建构性、联结性作用提供了基础。最后,它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也有利于将媒介引入规范研究视阈。在此框架下技术和结构、行动的关系可以解析为技术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取决于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使用技术,而从结构视角观之,媒介既是虚拟的内在结构形成的中介物,本身也是外部物质性环境条件。(45)Matthew R. Jones, Helena Karsten, “Giddens’s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MIS Quarterly, vol.32, no.1(2008), pp.127-157.
布迪厄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也适用于媒介化社会议题的解析。以布迪厄理论为例,“惯习”的概念直接有利于破解媒介唯技术论倾向。在他看来,技术本质上是惯习的子集,“我们无法在事实发生之前确定一个物体何时成为一种技术,因为它的‘技术’用途的一部分来自人们看待它的方式——或者仅仅是持有它的方式”。(46)Jonathan Sterne, “Bourdieu, Techniqu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Studies, vol.17, no.3-4(2003), pp.367-389.即技术在作为实践的结构性物质条件之前,首先是一种社会性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之类的技术和其他物质实体相比,与人类的关系并没有差别。技术在人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参与实践也是在使实践具体化的同时,又以物质的形式体现出特定的性格和倾向,促成做事的特定方式。(47)Jonathan Sterne, “Bourdieu, Techniqu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Studies, vol.17, no.3-4(2003), pp.367-389.总之,布迪厄的理论有利于人们从社会性视角重新定位媒介作为人的延伸的方法论实现,更有利于人工智能阶段各类行动实践的解析。哈贝马斯理论与前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其从诞生以来的规范理论色彩,在将传播作为公共领域型构条件之时就为当下“信息茧房”环境下公共领域建设的方法提供了破解思路,即他主张要在克服数字流动带来的新自由主义理想市场镜像的同时,从宪法而不是政治上矫正媒体结构,这才是包容的公共领域出现的架构基础。(48)哈贝马斯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参见Jürgen Habermas, “Überlegungen und Hypothesen zu einem erneuten Strukturwandel der politischen Öffentlichkeit,” in 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Co. KG, 2021, pp.470-550.由此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媒介架构的合理性是理性政治对话展开的基础。这种阐发充分证明了媒介在规范议题上的重要性。
更多理论资源散落在众多跨学科中观理论中。如布洛维(Burawoy)的劳动过程理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社会网理论,以及泰勒(Taylor)和桑斯坦(Sunstein)的助推理论。布洛维理论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关注和解析将个人劳动与国家、市场连接起来。(49)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85, p.193.以布雷弗曼(Braverman)科学管理的三个原则,即认为工作现场工人的去技术化、概念与执行的分离以及知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合力实现了发达社会劳动场景中国家、市场对工人的控制或者三者反身性作用机制作为解释参照框架,布洛维的理论有利于人们将媒介引入个体全面参与社会劳动过程的机制分析。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则为社会网络已经被媒介全面中介化的当下,了解不同空间关系网络串联和游移机制提供了分析基础。由此,新的社会规范的建构、群体沟通标准的形成、关系构建的阻力全部可以在媒介架构基础上获得解释。(50)C. Haythornthwaite, “Strong, Weak, and Latent Ties and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8, no.5(2002), pp.385-401.泰勒和桑斯坦的“助推”概念则有利于对不同思维习惯、经验法则和情绪驱动下的个体如何在媒介提供的“选择性框架”中实现个体行动选择和国家社会需求的结合的实践进行分析,(51)Peter John, Sarah Cotterill, Alice Moseley, et al., Nudge, Nudge, Think, Think: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Change Civic Behaviour,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促进媒介学术研究的具体开展。
上述总结分析的关键意图在于阐明,从STS向ANT理论视角的转移,意味着对媒介的理解正在从“物质性”向“社会性”转移,而三大宏观理论家与布洛维、格兰诺维特、泰勒和桑斯坦等人的理论著述,均可以移植或嫁接“媒介”视角,共同促成媒介化社会理论网络生成,最终在实际应用和操作层面促进媒介社会学研究理论和经验成果涌现。
三、 方法实践与浮现
(一) 经典方法在结构能动视野上的前沿议题应用
类似于传统社会学理论可运用于媒介社会学议题,经典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继续在当下媒介社会议题上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传播的行政研究范式被认为是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原因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主导的调查方法、霍夫兰和卢因主导的实验方法,拉斯韦尔主导的内容分析法在二战期间的广泛应用,决定了传播研究作为“卡方人”与职业取向的新闻人“绿眼罩”的差异。与此同时,基于观察法和访谈法的民族志研究方式也作为二战后从人类学、社会学移植来的质性研究方法在传播领域被广泛使用。两种研究路径在社会科学方法范式上被简略归结为方法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其背后根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歧在于对“社会”的认识是结构论的“实体”存在还是“建构论”的“个体”存在,这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议题的争论核心,然而随着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结构-能动”理论的流行和布迪厄“实践”概念对规则和惯习的融合,单纯的方法论竞争在以“问题”为第一导向的具体经验研究中事实上并不居于第一位。在大量的具体研究中,人们对方法的选择和应用表现出更为“权宜”和“流动”的一面,也更接近韦伯“理想类型”角度的条件和起点说明。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既然任何一项研究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有限企图,都需要一种方法工具的帮助,那么近年来经典研究方法在媒介社会议题上发挥作用的方式就值得探究。首先在议题覆盖范围上体现出全局性。就以传统被规范理论主导的议题媒介体制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为例,2000年哈林(Hallin)与曼奇尼(Mancini)《比较媒介体制》一书的出版,(52)丹尼尔·哈林、保罗·曼奇尼: 《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陈娟、展江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标志着即便对于媒介体制这样的宏大议题也可以通过合适的指标概念框架进行经验分析。而迈克切西尼(McChesney)则以大量详实的经验数据表明新自由主义传播体制在西方的实际运行存在悖论和缺陷,(53)Robert W. McChesney, “Global Media, Neo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New York-, vol.52, no.10(2001), pp.1-19.贝克尔(Becker)则分别以国家和市场为坐标,从国际横向和国内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了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媒介体制的变化,(54)Jonathan Becker, “Lessons from Russia: A Neo-Authoritarian Media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9, no.2(2004), pp.139-163.库兰(Curran)等人更是在2009年运用经验指标统领性地对公共服务模式、二元模式和市场模式三种西方主流媒介体制模式进行了比较。(55)James Curran, Shanto Iyengar, Anker Brink Lund, et al., “Media System, Public Knowledge and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424, no.1(2009), pp.5-26.这些研究充分证明经验研究和指标体系对于解读宏大议题也是适用的。其次则表现为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在“因果机制”挖掘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以量化研究为例,通过“调节”或“中介”分析推进人们对超越相关关系之上因果关系的挖掘成为近年来流行的研究方式,而这种研究趋势的形成则显示出人们构建问题和解释问题思路的转变。既然“概率”的解析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对社会世界出现的越来越多“怎么办”问题的解答,(56)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 《为什么: 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江生、于华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5—29页。那么回归到结构性影响因素的挖掘就成为必然的解题思路。在此过程中,“媒介”(media)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基础性解释力。既然社会世界由媒介“中介”而来,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揭示这种媒介化(mediation)的中介(mediated)机制。而在质性研究路径上,则表现为学者们对常人世界媒介中介世界的“深描”与展示。此方法路径的转变也间接实现了凯瑞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融合。

(二) 浮现的研究议题与浮现的研究方法
当前我们呼唤将媒介切入社会学经典研究关系概念的重要动因在于我们看到了媒介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建构能力。不同于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的对媒介建构结构能力的启示性描述,也不同于李普曼从个体认知形成的信息环境形成的视角性解读,当下社会现实的建构显示出从梅罗维茨中层理论视角的“场景”结合到莱文森“人性补偿”的媒介的全面中介建构效应展现。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Web3.0技术的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传播媒介从物理媒介、关系媒介向算法媒介的全面转型,从对传播技术的信息提供视角向场景构建视角转移,(62)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 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 到“元宇宙” 再到“心世界” 的未来》,《新闻界》2021年第10期,第54—60页。在此语境下,浮现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必然呼唤新的研究方式的诞生,“界面”研究由此应运而生。在马雷斯和格利茨的分析中,(63)Noortje Marres, Carolin Gerlitz, “Interface Methods: Renegotiating Relations between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STS and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4, no.1(2016), pp.21-46.“界面方法”主要表现为: 人与机器数据的协同共生逻辑、共现分析方法和“动态”问题的捕捉能力,这种研究方法尤其适合前文所述的Cyborg相关研究。事实上,当前媒介社会的发展对研究方法的冲击,主要在于其提供了新的适用场景并进行了更强大的技术赋能。如当下大热的大数据分析其实是原来公共意见调查分析的延伸,而社会模拟分析也可看作实验方法在当前媒介场景供应与计算能力支持下的发展,近年来从医疗领域扩展而来的录像分析则可视为访谈方法的媒介化演进版本。
以大数据分析为例,无论从实际应用的议题、使用的场景还是背后的驱动原因来看,它都是社交媒体普遍使用的当下公众意见收集的一种手段呈现。如麦格雷戈(McGregor)在2019年的文章中指出,传统的民意调查暗含的假设是公众意见是个性化的、可测量的、私人的现象,民意调查人员因而可以访问,而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由于可以呈现点赞、转发、评论等信息,事实上为公共意见形成动态机制挖掘提供了机会,因而成为一种更高效的民意捕捉方式,(64)Shannon C. McGregor, “Social Media as Public Opinion: How Journalists Use Social Media to Represent Public Opinion,” Journalism, vol.20, no.8 (2019), pp.1070-1086.不得不说当前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机器的边界和数据痕迹的动态追踪,体现出大数据研究相比于传统调查研究更为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尽管这种研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如数据风险和全数据获得等实际问题。(65)Tauel Harper, “The Big Data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Big Data an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Society, vol.19, no.9(2017), pp.1424-1439.总体来看,在新的媒介研究议题的强大需求促发下,时至今日,大数据分析方法已经发展成一套综合连接RFID标签、传感器和智能计量方法进行界面数据及生活趋势分析的基本工具。(66)Jai Prakash Verma, Smita Agrawal, Bankim Patel, et al., “Big Data Analytics: Challenges and Applications for Text, Audio, Video, and Social Media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Soft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IJSCAI), vol.5, no.1(2016), pp.41-51.而随着多种数据格式兼容以及跨系统连接、匹配、清理和转换数据能力的提升,这种方式正在嵌入Web3.0时代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场域,成为各类媒介社会议题分析可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

从方法视角层面,本文认为经典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嫁接于媒介社会研究从政治体制到微观人际互动的各类议题,而各类方法的结合使用和迭代版本也扩展了经典研究方法在当下各类媒介社会议题中的解析力。最后,以数据捕捉为特征的“界面”研究正在统领调查、访谈、实验等研究方式,最终成为考察人类数字化生存状况的基本研究方式。
本文从“连接”和“重构”两个层面尝试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就媒介社会学议题、理论和方法进行的探讨,意在呼唤建立一种基于社会学经典“行动-结构”研究框架的“行动-媒介-结构”媒介社会学进路,希望这种进路在议题解析上能够在已有“传播”与“社会”研究积累基础上以当下媒介社会发展语境为第一关照,主张对“研究议题”进行“媒介+”的思路转换。而在理论解释资源和策略上,则主张对经典社会学理论三大家成果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他们理论与“媒介”关联的深度挖掘著述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借助各类经典中层理论与媒介议题结合的开放性,实现社会理论的“媒介+”转型。而在方法使用上,则主张以“界面”研究为代表,重建经典研究方法调查、实验、访谈与大数据方法的谱系关联,实现线上线下研究的统合而非分离,更好地从未来取向合理搭配各类研究方式,推进具体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倡导还面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如“行动-结构”视角本身作为经典社会学理论架构从20世纪末就面临着各种冲击,近几年法国社会学界拉图尔等人的理论在媒介社会领域的崛起客观上也加重了这一情势。但是正如媒介社会图景是逐步展开的一样,对于当下人们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空间,各类问题的解析和研究需要我们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富尔卡德关于算法阶序化社会的分析,(70)Marion Fourcade, “Ordinal Citizenship,”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2, no.2(2021), pp.154-173.就证明了我们在当下面临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理论走得不够远的问题,而是缺乏运用已有理论资源进行真正有意义研究的能力和实践。基于此,本文对媒介社会研究领域议题、理论、方法的分析总结,更多是希望唤起人们对已有学术资源谱系的重视,促进媒介社会研究领域具体研究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