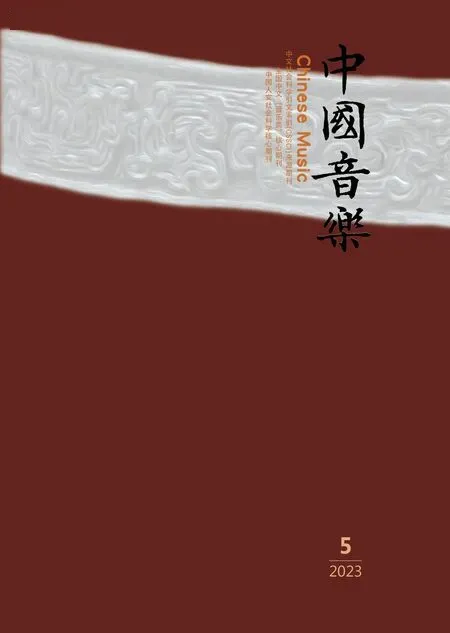“泛东方”认知中的文化想象与创造
——德彪西《中国回旋曲》与《月落荒寺》中的“中国元素”
○ 冯嘉卉
引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阶段,中法之间在外交、文化、贸易往来等方面更加紧密,爱德华·萨义德甚至将19、20世纪之交的巴黎称为“东方主义世界的首都”①François de Médicis and Steven Huebner.Debussy's Resonance.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18,p.272.。在那个时代,汉学蓬勃发展,文学、艺术领域也诞生了许多包含“中国元素”的作品。音乐方面的“中国元素”则与1867年至1900年相继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有关,不少法国音乐家借此机会真正接触到了来自东方本土的音乐,并由此创作了许多带有东方情调的音乐。作曲家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1862—1918)亦在其列,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异国情调。例如,钢琴曲《塔》模仿佳美兰乐队中多种打击乐器的效果,《格拉纳达之夜》使用了哈巴涅拉舞曲,《木偶的步态舞》中含有美国黑人爵士步态舞的节奏,《亚麻色头发的少女》等作品则带有英伦风情。而其1881年在巴黎音乐学院读书期间创作的《中国回旋曲》,以及1907年在拉卢瓦和谢阁兰②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法国汉学家,他与德彪西于1902年结识并成为知己。分析德彪西书信等史料可以得知拉卢瓦对德彪西音乐的理解十分深入,他曾通过参加音乐会前的讲座、撰写乐评、发表论文与专著等方式介绍、推广德彪西的音乐。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égalen,1878—1919),法国汉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谢阁兰一生三次赴华,前后约有六年时光在中国度过,代表作有以中国碑文化为灵感的诗集《碑》、以中国皇帝和紫禁城为象征的小说《天子》等。德彪西与谢阁兰在1906年之前便已熟识,两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从1908年12月23日谢阁兰寄给柏哈特(Max Prat)的信中可知,是德彪西介绍谢阁兰与拉卢瓦相识,这两位挚交好友的汉学研究对德彪西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影响下创作的《月落荒寺》则是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音乐作品。
近年来有关“德彪西的异国情调”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兴趣,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德彪西音乐中的“东方情调”“中国元素”或“中国因素”等话题展开。本文所谓“中国元素”与相关研究文献所用“中国因素”概念意义相近。如毕明辉认为,以中国为标题、以中国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素材或是受到中国文化思想启发的西方音乐作品都是“中国因素”作品。③毕明辉:《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前景”,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2页。他还将西方音乐“题材”中的“中国因素”进一步细分为标题、情节、歌词等元素,将“音乐语言”中的“中国因素”细分为中国曲调、中国调式音阶、中国节奏和中国音色等元素;创作思想中的“中国因素”则包含中国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等元素。这些观点为我们研究德彪西音乐中的“中国元素”带来一定的启发。
那么,德彪西音乐中的“中国元素”究竟体现在何处?在为数不多有关德彪西音乐与“中国元素”的相关研究中,以下论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Angela Kang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音乐风格》(Musical Chinoiserie)④Angela Kang.Musical Chinoiserie.PhD thesis,University of Nottingham,2012.的第三章介绍了20世纪早期德彪西、法雅和鲁塞尔的几部音乐作品,认为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乌托邦式的中国景观;Chuqiao Guo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德彪西钢琴音乐的影响》(Chinese and Other Asian Influences in Debussy's Piano Music)⑤Chuqiao Guo.Chinese and Other Asian Influences in Debussy's Piano Music.MaD thesis,University of Alabama,2021.中以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德彪西与亚洲、德彪西钢琴音乐中的亚洲元素、中国音乐与德彪西音乐的区别等内容;台湾学者廖慧贞在《从书信手稿谈音乐学者与作曲家的关联——以拉卢瓦和德布西钢琴曲〈月落古庙〉的创作为例》⑥廖慧贞:《从书信手稿谈音乐学者与作曲家的关联——以拉卢瓦和德布西钢琴曲〈月落古庙〉的创作为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5年,第4期,第89-129页。一文中,从德彪西的书信集与拉卢瓦夫人写给拉卢瓦的一封未公开家书为出发点,探究了德彪西创作钢琴作品《月落荒寺》的灵感来源,并尝试分析其中蕴含的中国音乐元素;澳大利亚学者普瑞斯特(Deborah Priest)的专著《路易·拉卢瓦论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Louis Laloy on Debussy,Ravel and Stravinsky)⑦Priest Deborah.Louis Laloy(1874-1944) on Debussy,Ravel and Stravinsk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2018.中第一部分“论德彪西”篇幅长大,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对德彪西及其音乐创作做出了深入的论述。上述研究均论及拉卢瓦与德彪西的友情、拉卢瓦早期对德彪西的影响等问题,并在讨论德彪西的音乐语言时涉及对《意象集II》等作品的技术性分析。此外,穆勒(Richard E.Mueller)在《中国风味的美与创新:法雅、德彪西、拉威尔、鲁塞尔》(Beauty and Innovation in La Machine Chinoise:Falla,Debussy,Ravel,Roussel)⑧Richard E.Mueller.Beauty and Innovation in La Machine Chinoise: Falla,Debussy,Ravel,Roussel.Hillsdale,New York: Pendragon Press,2017.一书的第四章着重分析了体现德彪西异国情调的延展的作品——《月落荒寺》。
上述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德彪西音乐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综上,本文以德彪西《中国回旋曲》和《月落荒寺》两首作品作为研究主体,对其音乐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及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一、标题与歌词中的“中国元素”
《中国回旋曲》与《月落荒寺》是德彪西音乐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作品,它们的成曲背景、“中国元素”的运用与音乐风格等都有所不同,折射出不同时期德彪西对创作东方情调音乐的不同理念、心态与审美情趣。
《中国回旋曲》(Rondel Chinois)是德彪西于1881年根据诗人迪拉德(Marius Dillard)⑨迪拉德,法国诗人、音乐评论家,担任过《鲁昂艺术家》(Rouen-Artiste)杂志的编辑。他在十几岁时便凭借《中国回旋诗》在诗歌比赛中获奖。转引自François de Médicis and Steven Huebner.Debussy's Resonance.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18,p.275.的《中国回旋诗》(Rondel Chinois)创作的声乐作品,他在手稿中题词:“献给法斯尼耶夫人⑩法斯尼耶夫人是德彪西在为声乐老师莫罗-圣蒂(Moreau-Sainti)做钢琴伴奏时结识的一位花腔女高音,两人在相处过程中互生情愫。——唯一能够演唱这部作品,并且令人难以察觉其中那些无法唱出的中国元素的人”⑪James R.Briscoe.Debussy Earliest Songs.College Music Symposium,1984/24,p.83.。这首歌曲在德彪西生前并未出版,直到2013年尼格尔·福斯特(Nigel Foster)在伦敦歌曲节(London Song Festival)上公开了这首曲子的私人版本。⑫转引自François de Médicis and Steven Huebner.Debussy's Resonance.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18,p.272.
《中国回旋诗》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中国画面:
湖边长着杜鹃花
竹子、睡莲丛生
点缀着一叶
红木小舟
一位中国少女在舟上沉睡
面纱一直掩到脖颈
湖边长着杜鹃花
竹子、睡莲丛生
在不远处开满鲜花的阳台上
一位男子站在那里
他默默注视着
舟上的少女
湖边长着杜鹃花⑬笔者据《中国回旋诗》英译本译出,参见Angela Kang.Musical Chinoiserie.PhD thesis,University of Nottingham,2012,pp.108-109.
这首诗当然不是按照中国诗词格律所作,但毫无疑问歌曲在标题、意境中含有“中国元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宏观视角的中国为标题的作品,通常在标题中明示‘中国’字样,以之表明作品与中国的联系”⑭同注③,第21页。。我们甚至可以说,歌曲中的“中国意境”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西方式的虚构——迪拉德没有去过中国,他按照自己的想象与对“中国象征物”的使用塑造了一个虚构的中国意象。德彪西在1881年亦尚未接触过来自中国本土的音乐,但他用自己心目中的音乐建构了迪拉德想象中的中国意象——他在《中国回旋曲》手稿的标题下曾半开玩笑似的写道:“(这部作品是)中国音乐(Musique Chinoise)”。⑮Médicis,2018,p.275.
在完成《中国回旋曲》八年之后,德彪西参加了1889年巴黎世博会,这件事对德彪西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907年,德彪西创作了钢琴套曲《意象集Ⅱ》,其中第二分曲《月落荒寺》是德彪西创作的第二首明确含有“中国元素”的作品。这部作品原名为《月落古寺》⑯该曲最初被译为“月落古寺”,后被普遍译为“月落荒寺”,本文使用后者。,德彪西把它献给好友拉卢瓦,拉卢瓦也证实此曲的标题“是中国风格的”:
第二首乐曲将我们带领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那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也不必依靠书信来往,是一个我们都可以到达的梦想中的国度。与《塔》相比,《月落古寺》中的远东世界少了一分热烈,多了一分庄重,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升华,音乐变得凝练而纯粹,如一颗诞生于空旷与寂静之地的半透明精美宝石。⑰Kang,2012,p.138.
对此,有学者认为乐曲的标题应该是来自拉卢瓦,但同时认为其风格可能受到佳美兰音乐的影响:“《月落荒寺》……它的标题,据说是在作品完成以后由路易斯·拉罗(Louis Laloy)提出的(题辞)。主题看来是东方式的,显然受到欢快的‘加买隆’的影响……”⑱〔美〕弗兰克·道斯:《德彪西的钢琴音乐》,克纹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第42页。但笔者以为,无论是直接点题的《中国回旋曲》,还是《月落荒寺》这种具有东方意境的文学性标题都不是作品营造中国风格的根本所在,其中国音乐风格的体验更多是来自音乐语言自身。
二、旋律中的五声性音高材料
巴洛克、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几乎只建立在我们熟悉的大小调音阶上,这种情况在晚期浪漫主义及以后的音乐创作中得到改变。德彪西虽然并没有完全抛弃这套体系,但更多的是开发其他音阶结构,这其中就包括五声音阶。
(一)以自然音级为基础的五声音阶
五个音构成的音阶都称为“五声音阶”,包括“佩罗格音阶”“去四七小音阶”与“库模音阶”等。我们通常谈到的五声音阶,更多的是建立在自然音级上的五声音阶。它只使用大二度和小三度,且不包含半音,故而又被称为“无半音的五声音阶”。这种五声音阶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东方音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19世纪下半叶被作为具有东方色彩的音乐语汇出现在许多西方音乐作品中。

谱例1 《中国回旋曲》第19—22小节
从谱例1可以看出,在第19小节钢琴伴奏的低声部中,C、D、E、G、A五个音是自然音形成的五声性音阶。但它仍处在自然音阶的背景下,没有强调个别音,是德彪西早期音乐创作中的五声性音调。在《月落荒寺》中,德彪西对五声音阶的运用又有所不同。

谱例2 《月落荒寺》第14—15小节
从谱例2可以看到,出现在第14—15小节、第29—30小节和第54小节的五声音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入式主题旋律,是该曲的核心动机。它由B、#C、E、#F、A五个音组成,以对称并置的形式出现,与中国五声音阶中的B商调式音阶完全一致。德彪西在作品中,通常使用不止一个五声音阶。在《月落荒寺》的第27—28小节出现由#D、#F、#G、#A、#C五个音组成的音阶结构,与中国五声音阶中的#D羽调式音阶完全一致。在第37—38小节、第41—42小节和第52—53小节出现了bB、C、F、G四个音,这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不完整的五声音列。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五声音阶的运用只是在形式上与中国五声音阶相同,其旋法并不一致。
五声的自然音阶,由于缺少半音,难免显得单调,除了前文所述使用装饰音、调式转换或到其他五声音阶的转调外,德彪西对五声音阶的运用还表现出一种复合性和扩充性的特征。此处为五声音阶和中古音阶的“双音阶复合”,即将两个调式音阶作为基础,德彪西在高声部又叠加了一条B多利亚调式音阶,但只用了Ⅰ、Ⅳ、Ⅴ、Ⅵ、Ⅶ级五个音。两条音阶有三个调式音相同,所以两者的结合听起来十分和谐。跳音八分音符和三连音形成节奏上的对比,产生一种微妙、脆弱的音响效果,“像是一朵带有半透明花瓣的玉花”⑲Laloy Louis.La Musique retrouvée,1902—1927.Paris: Libraire Plon,1928,p.177.。正如有些学者总结的那样,“音乐材料分别以和声的、旋律的或音型、音调式的形式在各自的音阶基础上作横向上的对置与串联,以形成斑斓色彩的对比与复合化的音响效果,是德彪西调式布局手法的经典”⑳赵京封:《欧洲印象主义音乐研究》,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以往绝大多数关于《月落荒寺》的分析研究都聚焦于佳美兰音乐元素,许多学者认为德彪西在《月落荒寺》中使用的五声音阶是来自佳美兰音乐,其实并非如此。佳美兰音乐建立在七声音阶“佩罗格”(pelog)和五声音阶“斯连德若”(slendro)两种乐律的基础上。根据埃利斯的研究可知:佳美兰斯连德若音阶是基于狭四度产生的,在一个八度内分成各240音分的5个相等的“平均律形式的音阶”㉑饶文心:《爪哇佳美兰乐器的测音研究》,《黄钟》,1999年,第4期,第11页。。德彪西的五声音阶与“斯连德若”音阶虽然在外观上确实相似,但两者在音律结构上并不相同。爪哇佳美兰音乐学家Joko Purwano在1989年接受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索雷尔(Neil Sorell)的访谈中对所谓德彪西模拟佳美兰音乐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德彪西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有那么一点东南亚的感觉’,但绝非爪哇音乐风格”㉒转引自潘原钏、沙里晶:《佳美兰素材在西方音乐创作中的认知与应用演变——以德彪西和麦克菲为例》,《人民音乐》,2016年,第6期,第81页。。
(二)五声音阶的来源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回旋曲》和《月落荒寺》中的五声音阶既不是中国的五声音乐,也不是印度佳美兰音乐中的五声音阶。那么这两首作品中的五声音阶到底源出何处呢?关于其来源问题,冯文慈认为:其“是否渊源于阿米奥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介绍,即是否来自拉莫以阿米奥手稿为依据所进行的复述和评论,目前尚缺少根据进行判断。但是至少可以说,法国启蒙运动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很可能影响到后来的德彪西”㉓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清末》,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第261页。。冯文慈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德彪西对拉莫十分崇敬,而拉莫在《实用音乐辞典·对中国音质要素的最新研究》(1760)中认为,只要是五声音阶写作的旋律就一定具有中国风味。㉔同注③,第117页。所以,德彪西喜爱使用五声性音调可能是受到了启蒙运动后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中国音乐的误读的影响。但对此笔者还想进行一些补充。
首先,通过《中国回旋曲》中五声性音调片段和德彪西交响组曲《春天》(1887)开头的长笛五声音阶主题的对比,有西方学者指出:五声音阶并不是德彪西在世博会上的收获,他在1889年之前便通过他在巴黎音乐学院的理论教师拉维格纳克(Albert Lavignac)对其有了一定的了解。㉕转引自钟卓文:《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德彪西钢琴作品中的“东方情调”》,《中国音乐》,2013年,第1期,第171页。其次,五声音阶虽然是中国传统音乐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它同时还存在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之中,并非如拉莫等西方音乐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但凡以五声音阶写成的音乐都是中国音乐。有学者甚至认为德彪西的五声音阶可能受到了一些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的音乐的影响,如肖邦的《“黑键”练习曲》和李斯特的《bD大调练习曲》。㉖转引自Chuqiao Guo.Chinese and Other Asian Influences in Debussy's Piano Music.MaD thesis,University of Alabama,2021,p.23.再次,由于五声音阶中没有小二度、大七度和三全音这种极不协和的音响效果,特别是没有半音,削弱了功能解决的倾向,因此这一方面满足了德彪西对具有温柔朦胧色彩的声音的追求,另一方面五声音阶的使用也成为德彪西模糊调性的手段,体现了德彪西以揭示音乐的色彩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创作观念。
总之,德彪西在这首“中国音乐”中试图用五声性音调营造异域风情,虽然其并非中国所独有的音乐元素。五声性音调的运用或是德彪西对拉莫等音乐学家的理论的吸收,或是对其他西方音乐的模仿,但这种吸收与模仿不是盲目的。德彪西巧妙地将被普遍认为是带有异域风味的五声性音调与自己的创作实践需求结合起来,将其转化为可以彰显自己创作理念的工具,同时避免了落入过分强调异域风格的陷阱,这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设计。
三、和声的五声性形态与运用
在德彪西的和声语汇中,除了传统三度叠置的和弦结构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外,四度、五度叠置和弦与附加音和弦等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与运用。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上的和声场”㉗〔德〕瓦尔特·基泽勒:《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杨立青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1页。是德彪西和声处理方法的重要特征,德彪西把五声音阶和四度、五度结构的五声性音响用于《中国回旋曲》与《月落荒寺》之中,显然有把它们与“中国元素”联系起来之意。
(一)空五度的低音进行
纯五度因其空洞的音响也被称为“空五度”,很多和声论著认为空五度的平行进行应该被禁止。但因其“感人的、无边的、模糊的、遥远的、虚空的、超然的”㉘〔美〕文森特·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刘烈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音响效果,成为现代作曲中一个重要的和声因素,用来“塑造一种东方韵味或悠远消失的过去景象”㉙〔美〕库斯特卡:《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宋瑾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谱例3 《中国回旋曲》钢琴缩谱第35—40小节
从谱例3可以看出,德彪西在《中国回旋曲》中所使用的和弦依然以三度结构为主,但和声进行的功能性大大弱化了。连续的五度被放在低声部,上方的高音声部则采用反向或斜向进行。持续低音式的平行五度进行,还会给人带来一种多调性的感觉。德彪西创作《中国回旋曲》时,尚在巴黎音乐学院求学,他对五声性和声的思考与运用在《月落荒寺》中体现得更为成熟。
(二)四度三音和弦的平行进行与不解决
四度叠置和弦由四度音程叠置而成,它源于三和弦的装饰音以及中世纪的复调音乐技术。由纯四度构成的三音、四音和五音和弦具有五声音阶的特色。德彪西在《月落荒寺》中主要使用纯四度叠置的三音和弦的第一转位。

谱例4 《月落荒寺》第1—2小节的钢琴缩谱及四度三音和弦的生成
所有三个音的四度叠置和弦都可能有两种转位,采用第二转位时,像是纯四度音程的根音向下附加二度构成的三音和弦,它的音响相对浑浊,这可能也是德彪西更多采用四度三音和弦第一转位的原因所在。对于四度和声的处理,德彪西采用的是平行进行的方式,而非传统的功能性进行。并且从横向看,这些平行和声其实是旋律线条扩大了结构的同一事物,它的妙用之处就是使得旋律线条更加丰满。平行和声用来强调线条在局部的上升或下降时较为有效,如果长时间的同向进行必然显得单调乏味。所以,德彪西在之后的做法或是采用声部的反向进行,或是把守调(tonal)的平行进行换成真正(real)的平行进行。
既然德彪西抛弃了功能和声的发展手法,那么四度三音和弦的进行就不再以解决到某个三度和弦为目的。四度三音和弦在转位后所包含的纯五度,使得四度和弦展现出奇妙的和声色彩,“色彩性”亦是德彪西和声技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印象主义特征之一。万籁俱寂,草虫喓喓,如水的月色洒落古寺之上,德彪西所要表达的不正是这种缥缈悠远、朦胧清澈的声音吗?
四、“泛东方”认知中的“中国元素”
“‘泛东方’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意义的概念,指外在于18至19世纪欧洲中心传统观念和族群、社会经济上相对落后、文化上具有独特形态、地理位置相对于欧洲蛮荒遥远的广大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㉚徐波:《“泛东方想象”:建构普契尼歌剧中的“美丽新世界”》,《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第41页。当时的西方人对“广袤东方的联想——既不十分无知,也不十分准确”㉛〔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9页。,普遍体现为“泛东方”认知。因此,作曲家们并不熟知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具体位置及其音乐文化,更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异,在概念模糊的情况下常常将表征东方的不同地域性的音乐语言进行置换,以满足自身想象的构建。所以,无论是五声音阶、五声性的和声音响,还是土耳其风的增四度音程与阿拉伯花纹式的碎片化旋律,德彪西以此描绘心中虚构的中国图景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泛东方”认知的体现。
(一)土耳其风的增四度音程
“土耳其风”主要是在《中国回旋曲》的第9—10小节处以三次增四度旋律音程的运用体现出来。

谱例5 《中国回旋曲》第6—10小节
洛克在研究土耳其风格音乐时曾提到,增四度明确地展现了利底亚风格或是过去一个世纪内在大量书籍中提到的各种非西方音阶。㉜Kang,2012,p.118.对此,Angela Kang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写道:
(《中国回旋曲》)听起来更像是中东的而非中国的,尽管它的标题很清楚……通过升高G音得到的增四度——也许更能让人想起圣桑的《参孙与达利拉》或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中的和声。㉝Kang,2012,p.118.
Angela Kang之所以认为此处的增四度具有土耳其风格,是因为西方有不少通过使用增四度来表现土耳其风格的音乐作品,如贝多芬于1811年创作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中第三首《苦行僧合唱》是对伊斯兰教中根据苏菲派教义进行苦修的僧侣的描绘,其中增四度音的强调营造出土耳其的宗教氛围。㉞柯扬:《〈西方音乐中再现的东方形象:暴虐与肉欲〉书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41页。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舍赫拉查德》中,增四度音(e小调中的#A)较多出现于土耳其国王苏丹的主题里。
当然,音乐上的土耳其风格不是仅一个增四度音程可以概括的,此处德彪西主要是以土耳其风格中很具代表性的增四度音程来表现东方情调。德彪西为何在创作一首“中国音乐”时使用土耳其风的音乐语言呢?当时巴黎世博会尚未召开,他也还未结识汉学家拉卢瓦,他对东方音乐的了解或许大多是来自其他带有东方情调的西方音乐,而土耳其风格是西方音乐中异域风格的重要来源之一。
此处“土耳其”指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14至17世纪,奥斯曼帝国军事实力强大、所向披靡,并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这使得土耳其成为欧洲民众最早接触的来自东方的世界,土耳其的影响甚至逐渐从军事政治上转变、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18世纪席卷欧洲的“土耳其风”。“因而,在欧洲人眼中土耳其成为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世界’的象征,一切带有异国情调的东西都属于土耳其世界,一切表现异国情调、浪漫神奇题材的作品也自然都被披上了‘土耳其’的外衣。”㉟邢媛媛:《莫扎特音乐作品中的土耳其因素——以歌剧〈后宫诱逃〉和〈土耳其进行曲〉为例》,《人民音乐》,2013年,第3期,第81页。笔者赞同德里克·斯考特(Derek B.Scott)的见解,德彪西将具有中东、土耳其风格的增四度音作为一种表现东方情调的“生硬的手段”(a blunt tool)㊱Derek B.Scott.Orientalism and Musical Style.The Musical Quarterly,1998,82(2),pp.309-335.,并在《中国回旋曲》中加以运用㊲转引自〔美〕保罗·克里斯蒂安森:《镜中的土耳其:东方主义与海顿弦乐四重奏“五度”》,杨婧译,《黄钟》,2014年,第1期,第193;194页。,因其代表的“东方”的地理位置并不明确,甚至可以说是范围广泛——包含中国、日本、朝鲜、土耳其等东方国家。
(二)阿拉伯花纹式的碎片化旋律
除土耳其风格与五声性音调外,曲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音乐语汇。如,《中国回旋曲》开篇三小节为高音域,歌词为语气词“Ah—”的演唱,旋律悠长而华丽。

谱例6 《中国回旋曲》第1—5小节
在随后的第11—16小节,德彪西强调了纯五度、纯八度的钢琴低音,它们都持续一整小节。当音乐发展至第27—30小节时,声乐旋律呈现为“阿拉伯花纹”的形式。“阿拉伯花纹”(Arabesque)“原指建筑艺术上的一种装饰性风格,是用花卉、树叶、水果、动物或人形等组成复杂精细、线条交织的装饰建筑的雕刻图案。音乐方面借用这个词,并不是指音乐具有阿拉伯音乐的风格或模仿阿拉伯音乐曲调而写成的乐曲,而是指用具有华丽装饰的旋律音型而写成的乐曲”㊳向乾坤:《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第一首〉两种演绎版本的速度比较》,《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76页。。在谱例7中,作曲家分别以E、C、bA为核心音,并以围绕着核心音的8个音进行多样化的组合,从而形成了三组上下起伏的乐节。“德彪西喜爱阿拉伯图案的精致音型,并非将其看作是装饰音,而是将其看作是旋律线或和弦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㊴同注㉕,第173页。,这也符合印象主义音乐的和声、旋律线条较为短小、碎片化的特点。

谱例7 《中国回旋曲》第28—30小节
最后,第二段(第31—32小节)与第三段音乐(第42—45小节)都结束在绵长的颤音上。
总而言之,根据斯考特归纳出的东方主义符指(signifiers)音乐特征表,带“Ah”的装饰音的声乐段落、空五度八度的低音持续音、阿拉伯花纹以及长颤音,在西方音乐中都是东方风格的修辞。㊵转引自〔美〕保罗·克里斯蒂安森:《镜中的土耳其:东方主义与海顿弦乐四重奏“五度”》,杨婧译,《黄钟》,2014年,第1期,第193;194页。德彪西通过使用这种音乐修辞——一种“泛东方”认知下的“置换”与自我创新,实现了对迪拉德笔下、自己心中的充满魅力的中国乌托邦的想象。《中国回旋曲》显然并非纯然或真正的中国声音,它是德彪西建立在“泛东方”意义上,对具有强烈想象色彩的“中国元素”意境的早期尝试。
结语
从对《中国回旋曲》和《月落荒寺》的分析,我们可以最终对其中的“中国元素”做出基本的归纳。“中国元素”既包括中国意境的诗歌与音乐标题中的文学性因素,也包括泛东方意义上音乐语言的选择与运用——尽管其中无不带有一种“想象的声音”的特点。《中国回旋曲》是德彪西于19岁时创作的标题、意境中追求“中国元素”的声乐作品,其中可见土耳其风格、五声性音调以及阿拉伯花纹等极具特色的东方音乐语言的处理,体现了德彪西的“泛东方”认知与创新能力。《月落荒寺》是德彪西于45岁时创作的从标题到音乐语言中均带有“中国元素”的钢琴作品,其中有来自拉卢瓦与谢阁兰的影响与启发,作品中对属音的强调,对五声性的进一步开拓以及对宁静悠远而又纯粹自然的声音的追求,无不表明德彪西对中国风格的诠释更加复杂,更有见地了。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国回旋曲》中的异国元素之关键不在于真实性,而在于功能性,其本质是具象的,是一种发明,是对欧洲音乐审美和创作传统规范的合理化背离㊶Kang,2012,p.30.,体现出19世纪末西方音乐对非西方养分的需求。
归根到底,《中国回旋曲》与《月落荒寺》都是德彪西想象中的中国声音与中国意象。它们也是当时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声音,是异国主义音乐。异国主义是一种发明,也是西方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孕育未来音乐表达形式的可能性。德彪西从对异国音乐感到好奇转变为尊重、理解和肯定其音乐文化,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看待“他者”与“自我”音乐文化之心态变化的缩影,也似乎预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在后世进一步的交流与融汇。
——《幽默曲》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