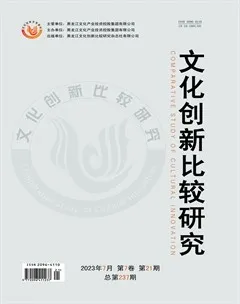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以配虑表达和敬语为例
伍志凤
(广东理工学院,广东肇庆 526100)
中日两国历史源远流长,汉语和日语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为日语翻译实践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此埋下陷阱。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独特性,反映了该民族的思维习惯和社会文化心理。在翻译行为中,译文最终以怎样的语言呈现,除受到语言差异影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如何克服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是翻译面临的一大难题[1]。
对于许多人来说,日语翻译的真正困难之处并不在于句法层面,而在于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语言活动的负迁移。如果只是对语言形式和意义进行简单置换,忽视深层的语言文化差异,轻则难以准确还原预期目的,重则会导致严重的文化冲突[2]。很多日语学习者具有较为扎实的日语语法基础,基本掌握日语语法的正确使用方法,因此翻译出来的日语译文从语法角度来看算不上误译。但很多时候译文不自然,常有令人费解之处。这或许是因为学习者受教材的影响,在日语学习过程中往往注重语法的学习和应用,没有理解隐藏语言形式之下的特殊内涵。
日语语言文化的两大显著特点——暧昧性和距离性在配虑表达和敬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翻译时应基于语言文化差异,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3]。
1 配虑表达的翻译
中国人推崇开门见山、直率明确的表达方式,而日本人通常在语言表达上会顾及对方的感受,习惯用敬语、暧昧语、省略等形式来委婉礼貌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而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交际场合的委婉礼貌表达在日语中称为 “配虑表达 (配慮表現)”。“配虑”一词的意思是“关怀、照顾”。配虑表达是日语语言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形成与日本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反映了日本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初学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很容易忽视这种差异,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导致误译。即使是表达相同的意思,两种语言在形式上有时会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进行日汉翻译时需要考虑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进行置换。
1.1 暧昧语
“暧昧”在日语中的意思是不明确、含糊不清。日本人在日常交流中,为了减轻听话人的负担或顾及听话人的颜面,会适当地使用一些暧昧表达,来模糊自己的主张。 其中,表示列举的“でも(之类的)”“なんか(之类、等等)”“など(之类、等等)”及表示概数的“くらい(大约)”等副助词作为暧昧表达形式的一种,经常用于劝诱、邀请、请求、拒绝等场合,表示说话人的委婉和礼貌。例如:
中文:我们去看电影吧!
日译1:映画を見に行きませんか。
日译2:映画でも見に行きませんか。
初学者往往会选择译文1,采用直译的方式,明确表示只有电影这一个选择。而译文2加译了一个表示列举的副助词“でも”,意思是“我们去看电影之类的吧”。举出“电影”一例,暗示对方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其他选择,采取了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来减轻对方的心理负担。虽然译文1不存在语法错误,且完整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了解中日两国在人际交往中的思维习惯差异后,会发现后者更符合日本人的表达习惯。
日本人在小酒馆点单时说 “ビールでももらおうか”,意思是“来点啤酒儿(之类的)吧”。和上例一样,该句也使用了表示举例的副助词“でも”,看似给予听话人选择的空间,实则是为了照顾听话人的感受。但在中国的餐厅点菜时,顾客往往要给予明确的指示,如果使用这种模糊的表达,将选择权交给服务员,不仅不能照顾对方感受,反而会给对方造成混乱[4]。这种模糊的表达在日语交际中大量存在,极其自然,因此汉译日时应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对这类词进行补充翻译。反之,进行日译汉时,应该进行恰当的减译,照顾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此外,中国人在拒绝他人请求时,经常会说“抱歉,我没时间”或者“不行,我做不到”等,明确表示拒绝之意。但在日本人看来,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显得语气十分冷淡、生硬,会使对方难堪[5]。在日本社会文化中,面子是极其重要的,并且自己的面子与对方的面子息息相关,直截了当地拒绝他人,是一种损坏他人面子的行为。对于重视人际关系的日本人来说,维护他人的面子和形象是必须遵守的社交规则。日本人在拒绝他人时,为了顾及对方的颜面和感受,会尽可能采取委婉的表达方式。因此在涉及拒绝表达的汉译日时,要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对汉语的某些部分进行省略处理,同时适当地增译暧昧语。例如,视情况而定可译为“せっかくですが、ちょっと都合が悪くて…… (虽然很难得,但是我不太方便……)”“残念ですが……(很遗憾,但……)”“やっぱり、ちょっと、無理かな(果然,还是稍微行不通吧)”等。翻译时选择暧昧表达,一方面,足以充分表达原文的拒绝之意;另一方面,照顾了对方的感受和颜面,避免可能因翻译而产生的交流冲突[6]。
日本人喜欢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尽量减少对方的心理负担,达到尊重对方、维护对方颜面的交际效果。这种重视委婉含蓄的暧昧表达不仅体现在口语交际中,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文学作品的浓厚深情、百转千回的心理状态多以委婉曲折、模糊含蓄的语言来呈现,追求一种含蓄的审美效果。译者进行文学作品的汉译日时也需要理解这种文化差异,培养审美意识,尽可能让目标读者在无阻碍阅读作品的同时,能够感受日语语言所传达的含蓄美。
1.2 自动词和他动词的选择
日语的动词分为自动词和他动词,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和作用不涉及其他,关注的重点在于客观结果或状态;他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和作用会涉及其他对象,突出动作主体,具有主观指向。在日汉翻译实践中,自动词、他动词的选择是一个难点。受日本人思维习惯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日语中相同含义的自他动词在句中表达的含义却大不相同。
客人来家中做客时,主人说“茶沏好了”。沏茶这个动作存在一个主体,因此很多人翻译时会选择他动词“入れる”,译为“お茶を入れました”。这句话突出了动作的主体,暗含着“我特意为你沏了茶”的意思,给对方一种强加于人的语气,无形中会给对方造成心理负担。而使用自动词“入る”,译为“お茶が入りました”,单纯描述“茶沏好了”这一客观事实,利用自动词强调客观结果,中立指向不给对方增加负担,顾及对方的感受[7]。
假设不小心弄坏了对方借给自己的电子词典,说话人需要道歉时,受汉语母语的影响,大部分人会选择自动词“壊れる”,翻译成“すみません、お借りした電子辞書が壊れてしまいました(对不起,你借给我的电子词典坏了)”。在汉语的语境中,如果弄坏他人东西并非自己本意,无需使用表示意志的他动词。但日本人在道歉时使用自动词“壊れる”,则暗含着一种责任不在我、与我无关的语气,容易令被道歉方感到不快。因此翻译成日语时,最好选择表示主观意志的他动词,承认自己的过失,译为“すみません、お借りした電子辞書を壊してしまいました”更为合适。同样地,打碎盘子道歉时也应该选择他动词“割る”而非自动词“割れる”。
这些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难以理解。因此受母语干扰,翻译时常常出现自动词和他动词的误用,忽略听话者的感受,令对方感到不安或不快。其实无论是选择他动词还是自动词,几乎算不上是语法的误用,也不会对意思的理解造成影响,但可能违背日本人的社交规则。这种误用归结于中日语言文化差异,日语中自他动词的用法差异不仅停留在语法层面,还体现出两国不同的思维习惯和社会文化心理。日语学习者在学习自他动词的使用时,不仅要格外注意助词的搭配,还应该重视这种语言文化差异,对自他动词的使用语境加以区分,避免出现误用。
2 敬语的翻译
2.1 敬语的使用语境
如前文所述,日本社会极其重视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包括地位关系、内外关系、亲疏关系、利益关系等。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语言表达形式受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资历等因素的制约,这种复杂且微妙的交际方式的典型体现就是敬语。
敬语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语言手段,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日语敬语相较于汉语更为完备和发达,从古至今在日语的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反映着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民族文化特征。日本人使用敬语这一语言形式向他人表达想法或感情时,重点不仅在于传达内容,更在于表现自己与对方的人际关系。通过使用敬语,可以体现说话人与对方的身份、年龄、资历、社会地位的差别,且使用的敬语尊敬程度越高,与对方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越远;反之,关系越亲近越少使用敬语。
日语敬语的语言结构和使用场合纷繁复杂,学校语法主要将日语敬语分为尊他语、自谦语、郑重语三大类。所谓尊他语是通过抬高对方的动作来表示尊敬的一种敬语表达方式;自谦语是通过贬低自己或自己一方人物的动作来达到尊敬对方的目的;郑重语是通过使用礼貌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教养和礼貌[8]。不同的敬语表达方式在人际关系中承担着各种作用。例如,“いい天気だ”和“いい天気です”意思完全一致,都表示“天气好”,但其表示的社交场合及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人际关系可能大有不同。前者的社交场合更为随意,而后者选择敬语,说明听话人对说话人来说是值得尊敬的对象,或者该场合需要说话人表示郑重和礼貌。将汉语翻译成日语时,要联系语境,仔细斟酌是否选择敬语。
敬语本身是一种表示距离的语言表达形式,且使用的敬语尊敬程度越高,与对方的距离越远。翻译情景对话时尤其要注意不同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根据亲疏关系、上下关系、利益关系等决定是否采用敬语,并选择合适的表达形式。关系亲密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使用了敬语,而需要表示尊敬的对话中未使用敬语或使用了错误的敬语,都可能令交际活动陷入尴尬的局面,甚至造成交流冲突。
中日两种语言的敬语系统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日语敬语的语言结构和使用场合相较于汉语更为纷繁复杂且特殊,因此敬语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是一个难以攻克的课题,也是翻译实践中的拦路虎。敬语翻译的困难不在于语言形式和内容,而在于语言活动的交际环境。译者必须理解孕育日语敬语这种复杂语言形式的社会体系和文化背景,并且要把握影响交际活动的各种复杂因素,选择确切的词语和表达形式,达到原文的交际目的。
2.2 敬称
敬称是表达尊敬礼貌的一种称谓方式,中国自古以来作为礼仪之邦,非常重视礼节,因此汉语的敬称形式多样,表达丰富。例如:人称代词敬称“您”,指示代词敬称“这位”,社会通用称谓“先生、女士”等。日本十分重视伦理和礼仪,日语的敬称也十分丰富,最为日语学习者熟悉的莫过于接在人名或身份后表示敬意的接尾词“さん”。进行汉日互译时,两种语言大多能够互相找到对应形式。但是语言文化差异同样体现在敬称的使用方式上,给敬称的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例如:跟前辈讨论问题时问 “您怎么看?”针对这句话,部分学生会按照汉语的逻辑思维译为 “あなたはどう考えますか”。 根据日汉大辞典解释,“あなた”是对对方的敬称,本身表示礼貌之意,可与汉语中的“您”相对应,因此这句译文从语法角度和意思上来看并无错误。但是这种语境下,将“您”直接置换为“あなた”是一种欠妥的处理方式,并未表达出“您”这个敬称所包含的尊敬礼貌之意,反而令人听者感到违和。这是因为“あなた”原本表示较高尊敬之意的敬语,但现在通常只对同辈或同辈以下身份地位的人使用,而且还略带疏离之感。除此之外,“あなた”还指夫妻之间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对于已知对方名字、身份的情况下,可以用名字加敬称“さん”的形式进行处理,可译为“〇〇さんはどう考えますか”,也可以直接省去敬称,用敬语句式来表示礼貌尊敬之意,译为“お考えをお聞かせください”或“お考えを伺いたいです”。
日语的敬语体系十分重视“内”和“外”的关系,“内”指自己及以自己为中心的内部关系,例如家人、朋友、同事等。这种内外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影响着日本人的人际交流活动。日语入门学习亲属称谓时,知道对外称呼自己的家人不能使用敬语,即不能加敬称“さん”;在家称呼自己的长辈要使用敬称,表示对长辈的尊敬;称呼别人的家人时为表示尊重和礼貌,要使用敬称。日语的称谓方式看似简单,但是进行日语翻译时,却存在许多问题。如翻译“您母亲”时,很多人受汉语思维束缚,照搬字面意思译为“あなたのお母さん”。若充分理解日语称谓方式的内涵,就能够意识到“お母さん”一词即可表达对对方母亲的尊重和礼貌,也足以提供正确的指示。加上“あなた”,语法上不存在错误,但属于画蛇添足的行为。同样,通篇将“我的爸爸”翻译成“私の父”也不够自然和简洁,单独的“父(ちち)”即表示对外称呼自己父亲的方式。
因此在翻译敬称人称代词时,对所属的人称代词“我、你/您、他”可以省略不译或者进行加译[9]。敬称这一入门级的语法看似简单,但是若疏忽了其内部的文化特征,不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就容易受汉语思维的影响,翻译成生硬的中式日语。
2.3 特殊的敬语句式
除敬称外,日语敬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式看起来与学校语法的讲解相异,常常让学习者在翻译时感到困惑,影响翻译的质量。例如:“させていただく”从结构形式上看是由“させる”+“いただく”构成,根据学校语法的说明,该句式表示使役许可和接受恩惠,属于敬语中的自谦语,常译为“请允我做某事”。这一句式频繁使用于各种交际场合,如果翻译时统一套用“请允我做某事”这一思维进行处理,会发现译文变得十分不自然。针对“させていただく”的使用问题,日本文化审议会于2007年2月发表的《敬语的指针》中列举了5个例子,说明“させていただく”的使用语境。
例1:请求复印对方的资料时:
コピーを取ら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请问能让我复印一下吗?(笔者译)
例2:研究发表会的开场词:
それでは、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现在开始我的报告。(笔者译)
例3:通过海报等告知本店休业:
本日、休業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从今日起本店停止营业。(笔者译)
例4:结婚典礼的祝福词:
私は、新郎と3年間同じクラスで勉強させていただいた者です。/我与新郎同班学习了三年。(笔者译)
例5:自我介绍时:
私は、〇〇高校を卒業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我毕业于某某高中。(笔者译)
通过研究以上5种使用语境的不同例句发现,只有例1满足使役许可和接受恩惠的条件,表示说话人的行为需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因此可译为“请允我做某事”。而例2~例5中,说话人的行为不需要征得对方的同意,且表面上并未得到任何恩惠,因此与使役许可和接受恩惠这两个条件无关[10]。如果对此不加以理解就直接按照学校语法进行直译的话,可能会让目标读者一头雾水。类似例2~例5使用语境的“させていただく”在日本人的交际活动中大量存在,看似不满足使役许可和接受恩惠的条件,但其实并未违背使役态和授受关系的含义。这种情况下,说话人作为动作的主体,将使役许可和接受恩惠当作既定事实,利用自谦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礼貌和尊重。如例2中的“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包含着对施以恩惠的听众的谢意和礼貌,也许听众实质上并未做出任何施恩的动作,但是听众的到场和关照对于演讲者来说就是一种恩惠,这种恩惠是一种既定事实。
除此之外,在做外贸函电相关的翻译实践时,经常需要翻译“感谢您做某事”这一句式,例如:“感谢您寄来样品”,很多人会翻译成“見本をお送り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是一种正确的敬语使用逻辑,因为寄样品这一动作是由对方发出,为表示尊敬和礼貌,所以需要使用尊他语“お送りくださる”。然而与日本客户的实际贸易往来中使用更多的是“見本をお送り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选择的是自谦语“お送りいただく”。虽然“送る”是对方的行为,但“お送りいただく”是自身的行为,可以使用自谦语。明明是对方的行为却使用自谦语,这一点对日语学习者来说稍微难以理解,甚至会觉得是误用,因此翻译成日语时不会考虑这种处理方式。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いただく”比“くださる”使用频率更高,相较于抬高他人的行为,贬低自己的行为可以减轻对方的心理负担,并且能够在人际关系中跟对方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3 结束语
翻译不仅受到语法结构的制约,还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配虑表达和敬语体现出了日语的暧昧性和距离性,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在做日语翻译时,应该理解中日语言文化的差异,力求在汉语和日语的转换间,既能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和其承载的内涵,又能贴合目标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
——“内”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