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静之美与中国诗电影的美学建构
张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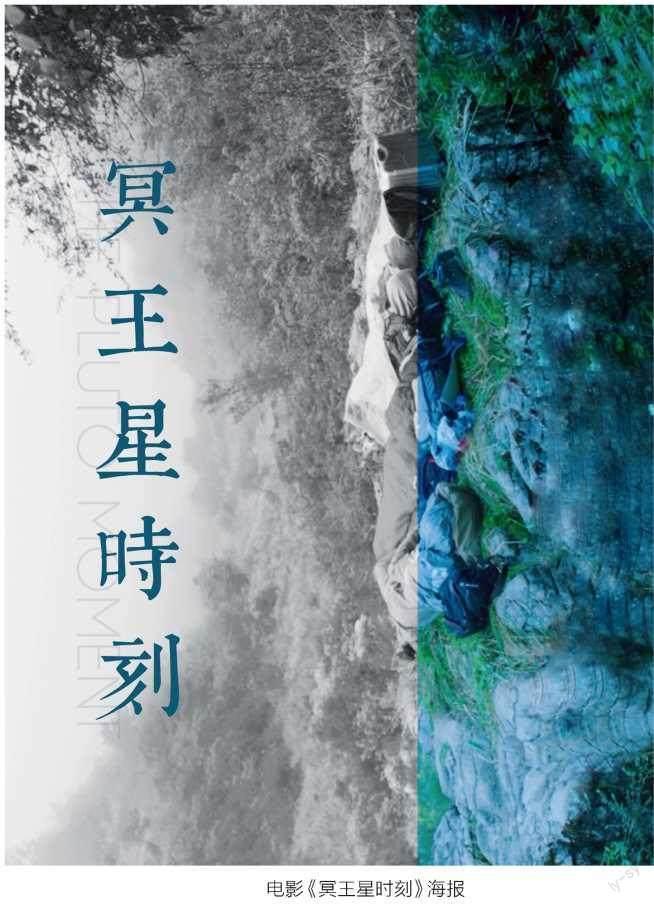

“简”与“静”构成了中国美学的两个重要倾向,“简”指简洁、简明、去雕琢、以少胜多、见微知著;“静”则指宁静、静观、冷静、以静制动、宁静致远等;“简静”蕴含着道家精神中的“虚”“无”“淡”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其审美意境也广泛地影响着中国诗词、戏曲艺术、文人山水画等传统艺术形式,营造出特殊的简静深远、荒寒孤寂的东方意境。这种审美倾向在传统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影响到中国诗电影的创作。许多创作者借鉴诗歌的氛围在影片中营造出静谧荒寒、孤寂纯美等意蕴丰富的意境。在中国诗电影创作的影响下,这一传统美学也逐渐进入当代中国电影的广阔实践中。
一、视听语言上的“简静”形式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纯简之美和静谧之境是中国古代文人自觉追求的艺术境界。在中国诗电影中,这种简静之美和荒寒之境同样体现在主题意蕴、故事题材、场景设置和空间氛围营造等方面,在视听语言的外在形式上首先完成对“简静”的追求。首先,在物理空间方面,中国诗电影通过在画面造型上融入简静寂寞的意象,以物起兴言意。与西方电影经常直抒胸臆的做法不同,中国诗电影以“物”之“言”呈现出画面简洁而意蕴深远的荒寒孤寂之境。在场景设置和空间氛围营造方面,电影利用远景、全景等偏远的构图,将观众引入深邃的空间,让人感受到荒凉、孤寂的氛围。同时,利用空旷的原野、荒芜的古寺、破败的残垣断壁等景象,进一步强化这种孤寂和荒寒之境。这种呈现方式在电影的诗主题或意蕴表达中尤为突出。在荒寒寂静的意象之中,诗电影常常以孤寂、离群索居的主人公为视角,展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无可奈何或对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例如在《小城之春》(费穆,1948)中,讲述情感生发的爱情主题却以战争之后铺满瓦砾的江南小城为背景,重病的戴礼言在沉疴中无可奈何地消耗着生命残余的能量,每天起床后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搬着几块残砖,在无望重建家园的无可奈何中顽强而无用地修修补补;他的妻子周玉纹则怀揣着寂灭的感情在小城的城墙之上徘徊,她孤单的身影和无限开阔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欲说还休的悲伤氛围渲染成为中国诗电影中的典范。
其次,中国诗电影通过借鉴文人画的留白、笔墨运用等创作手法,在构图方法上将简静之美融入电影的表现形式中。通过留白的手法,电影画面在视觉上形成简练、纯净的效果,同时给予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笔墨的运用则使得电影画面在表达情感的同时,更显深沉含蓄,给人以更多的回味和感受。电影《黄土地》(陈凯歌,1984)中几乎静止不动的机位,占据画面六分之五的苍茫黄土地,全景式构图凸显黄土高原的贫瘠。在影片开始的段落中远处传来高亢的陕北信天游民歌,幽深厚重的黄土地上蜿蜒小道似乎与天相接,一棵孤寂的枯树站在那里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体现出导演的“言外之意”,通过画面中创造的苍凉简静的社会空间,表现出一种物理和文化意义上的隔绝与残酷。例如电影《黄土地》使用一种独特的构图方式,以展示黄土高原的贫瘠和苍凉。画面的大部分都被广阔的黄土地占据,只有一小部分是天空,这种构图方式突出黄土地的厚重和沉闷,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自然景观的壮美和人类的渺小。当女主人公的身影在代代堆积的黄土上摇晃着消失时,导演陈凯歌表达了对于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思考。在画面中,蜿蜒的小道似乎与天空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场景,黄土成为世世代代积累的象征,孤寂的枯树则象征着生命的坚韧和不屈。
“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因为顺着自然法则运行的宇宙是虽动而静的,与自然精神合一的人生也是虽动而静的。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1]导演在构图上将静默深沉的自然与顽强的人生结合起来,这一呈现方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自然景观的壮美,同时也让观众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加之背景音乐中高亢而悠扬的民歌形式信天游,不仅为画面增添了一份苍凉简静的情感色彩,同时也有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
第三,中国诗电影往往通过辽远的大远景、全景式构图融入简静美学,体现出传统绘画美学理论中“简远高逸”的空间意识。这种“取象偏远”的画面造型不仅能将观众的视野拉远,让更多事物进入山水画卷般的全景图谱中;同时,这种“远”不仅指物理空间的距离之远,也指超越时空距离的精神境界之“远”,观看者与表现对象的距离也造成二者心灵空间中的疏离,可以让观众置身事外,以超脱的态度观看世间迷乱纷扰;同时,广阔的画面空间也延伸了電影角色的活动空间,允许他们在自由的行动中完成对自己的超越和延伸。在《站台》(贾樟柯,2000)中,导演以纵深的远景镜头拍摄小镇汾阳上的小小站台,画面前景是呼啸而过的火车,背景是连绵无尽的群山和天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汾阳文工团的成员们就是在这里聚首又告别、等待又分离,最终奔向各自人生的远方。“世代累积而成的文本包含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元素,它像一条穿越时代的河流,映现于这条河流中的两岸风景,是一大段历史时间的空间式铺展,对应的是历史的变化,而不是某一时刻。”[2]开放式的构图与“取象偏远”的景别给人以不断延伸的感觉,纵深远景下的小站台与火车一起成为过去的注解,有种简静孤寂的意味,渲染出象外之旨的超脱意境。
综上所述,中国诗电影在融合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将简静之美和荒寒之境融入电影的表现形式中。这种呈现方式不仅增强了电影的艺术价值,更表达出艺术创作者的脱尘之心和与天地同游的人生境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体验到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魅力。
二、虚实相生的“简静”表达
中国传统艺术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审美与表达原则,即虚实相生。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不仅在呈现艺术作品的简静之境和建构艺术空间诗意之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还可以辩证地从空无处生发出新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面布局和笔墨韵味往往通过留白手法来表达画外之意。“画面留白,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水、雾、云,是自然物象想象的空,也是充溢流动生气的空,正是这种空,使画面充盈着整体流动的气韵。空不是空无一物,而是诗意生成的关节点,画面灵动之源。”[3]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结构性留白手法,常常通过化实为虚、化虚为实,虚实转化,虚实相生等多重方法来达到审美意境也为中国诗电影的艺术表达方式提供了启示;而在电影创作中,“留白”既能让影片的节奏、画面整体更为协调,也为艺术的表达留下流动生气的想象空间。在原本写实的场景与画面中加入雨雪云雾、月光等自然意象,虚化背景,能够创造出若隐若现、充满禅意、生气流动贯通的画面。
例如《冥王星时刻》(章明,2018)中,导演在“冥王星时刻”这一半明半昧的空间里展现每个角色不可言明的心事。从入山时的混沌迷茫,到下山时的混沌初开,年轻的导演、摄影与演员之间交叉的关系架构,编织成暧昧又疏离的人际网络,每个人都在蒙昧又清醒的时空中经历着一场自我的洗礼。这些在两两互动、多人互动中,都包含有试探、犹疑的味道,也使彼此的关系程度处于“冥王星时刻”,鲜活蓬勃的欲望在山岚缭绕的氤氲中漂浮,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曾一度接近,然而最终仍沟壑重重。在人与人情感的出发点之间,他们既梳理了自身的惶惑,也在空间布局上寻到适切的落脚点,镜头在他们之间的调度显示出人物关系和叙事推进的层次。“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4]整部电影的情感与暴雨、泥泞曲折的山路进行相互作用,在影像和现实空间中肆意弥散。
相比于以画面中的留白渲染整体气氛、创造简静意境和诗意之美的做法,通过语言和动作刻画人物与人物关系的方式更具有叙事艺术的特点。在留白与笔墨、虚与实之间,诗电影的画面通过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形式可以充分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让观众产生诗性和哲理性的思考。在《长江图》(杨超,2016)中,货船船长高淳从上海沿长江逆流而上,不断与一名总是以不同打扮和身份出现在岸边且日渐年轻的女子相遇,整部影片几乎可称为一部魔幻性的影像史诗,于时空变幻中寻觅自己的逻辑,梦、诗、影像相互重合。在江水的阔远、雾蕴的迷远、山峦的幽远中,整部《长江图》正是一幅流动、寻源和多维的长江画。影片采用完全不同的镜头调度,依靠船舶的移动视角,制造出远看山水的空灵与留白。而一旦没有了现代建筑,长江看起来,就可以回到无限远的过去,回到迁人骚客出没的和悦洲、小孤山和观音阁,完成一次地理空间、心灵空间与传统文化的泅渡。
电影中构建虚实相生诗意空间的另一种表达技巧,是利用空镜头与长镜头建构影像的多义性。空镜头一般指仅仅拍摄景物、不包含角色或其他带有情感之物的镜头,因缺乏主观情感的出现在画面中而呈现出意义之“空”[5]。中国诗电影中的场景宛如传统美学中空旷寂寥的“空谷”一般,给予作品一种延宕和停顿的效果,同时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和信息。在《长沙夜生活》(张冀,2023)中,导演在讲述了多组人物的爱与恨、纠结与不舍后,以一组烟花绽放的空镜头串联所有人物,跳入湘江的情侣、失联的农民工、被观众抛弃的脱口秀演员、即将退休的大排档老板娘在同一時刻停下手中的事,也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难与痛苦,抬头仰望同一片象征理想的“星空”;而长沙这座立足在现代与传统、乡村与城市、个人与社会等交叉点上的城市,也达到了“无意图状态”,从而赋予这部由“人”构成的电影片刻间超脱世俗的洒脱与自由,具有强烈的抒情意味。
在对传统美学叙事相生的认知基础上,以电影中的长镜头观念与传统美学中的“简静”美学融合,可以进一步通过场景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富有感染力的场面,提升电影空间的表现力。在电影《路边野餐》(毕赣,2015)中,毕赣以长达40分钟的空镜头来实现“留白”的表达效果,以静态的景象来衬托出动态的人物和情节。影片中展现的西南小镇山林茂密、水汽充沛。升腾的水汽、漫长的阴天、寂寞的山林、静静流淌的河流等自然景观,都是简静美学倾向的选择,这些寂寥空灵的风景为营造影片的诗化意境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农业生产的痕迹和神秘的传说中,也舒缓了整体的空间氛围。男主人公陈升从大雾茫茫中出现,沉默寡言、相貌平凡却显得深不可测;在连续的时空中,观众的目光随他一起在小城中起起落落,沉浸而疏离地观察着他与小城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景观中,导演构建出一种陌生的离间效果,将传说与轶事杂糅、现实和幻想交融,去往不同的时间向度,并将人物轨迹平行交叠,既各自独立又有所牵连,影片整体上显得张弛有度,虚实相生,营造出丰富的想象空间。
三、简静之美与中国电影的现代反思
中国诗电影中的简静之美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在现代语境中对现代性思考和现代反思意识的艺术体现。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提到,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6];中国诗电影就是在电影中有意识地让影片的节奏放缓,并运用简静荒寒等古典美学概念完成叙事与美学建构的任务,在“流行”充溢之处寻找“空寂”,以视听语言建构出流行中的空寂。同样,宗白华将“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视为一项“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7]。
在诗意电影的实践下,更多中国故事也开始对简静之美的吸收和探索。例如故事片《暴裂无声》(忻钰坤,2017)讲述男主人公张保民寻找失踪儿子的过程,但张保民却患有失语症,因此影片中大量的段落都在语言的留白下以丰富的意象展现。例如,狩猎、弓箭与猎物、羊构成一组重要的意象:昌万年爱好射箭,密室中的动物标本也说明他爱好狩猎,象征他在商场、生活上也是一名残忍而精准的猎人,因此他用烟灰缸砸下属、喂同行吃羊肉等内容都足以说明他行事毒辣。在主人公与西北高原一体共生的沉默中,他的情绪与影片的力量层层堆积,最终在结尾以“爆裂无声”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影》(张艺谋,2021)中,导演大量借鉴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留白”技法,创造出一个全然不同于《影子武士》(黑泽明,1954)的中国美学境界。影片的山地场景笼盖着树林的氤氲之气,整部影片都覆盖着一层朦胧、蒙昧的梦幻感。通过将烟、云、水等物质具象物质虚化将水墨画流动的意蕴引入画面之中,导演一方面营造了一个虚实相生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也生发了象外之意:在影子武士境州扮演重病的都督子虞的过程中,他不仅对主公之妻暗生情愫,还产生了取代主公的意图。在不可言说的欲念中,一场真身和影子之间的生死博弈在细雨中展开。《影》中飘逸的书法、水墨晕染的衣裙都在柔和缥缈的雾气与小雨中若隐若现,画面深远,气韵生动,将人情的缠绵悱恻与诗情画意的意境之美结合在一起,同时以超旷空灵的留白展现出这场生死决斗的虚无之处。“中国美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与中国文化密切相连,所以它既是历时性概念,又是一个共时性概念。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无法摆脱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审美嗜好,所以它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中国美学的熏陶。”[8]这些影片不仅运用诗电影的表述手法,将复杂的视觉修辞和表意体系融入影片故事的讲述与人物的塑造中,还吸取诗电影的实践经验建构了影片中诗意美学的影像空间,同时也联结着当代中国电影的心灵反思。
结语
在中国诗电影的构建之中,东方审美中的传统资源成为电影艺术取之不尽的美学源泉:在画面造型语言上,偏远景别的选取和简洁的构图形式成为主导,固定镜头和长镜头则以沉默静观的方式呈现。虚实相生的留白之法、情景交融的空镜头,将叙事的真实与诗意的虚幻巧妙地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生动且具有高度意象的世界。简静之美不仅构建了电影中诗意美学的影像空间,更是包含了现代性思考和现代反思的艺术元素。它蕴含了多重意指的现代批判影像,成为电影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传统的简静美学和荒寒之境在电影视觉形象和文化精神上实现了持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4]宗白华.宗白华讲美学[M].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2020:34,35.
[2]朱刚.中国文学传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07.
[3]朱良志.论中国画的荒寒境界[ J ].文艺研究,1997(04):135-148.
[5]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1.
[6][7]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M]//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1,129.
[8]余月秋.虚实相生与中国诗电影的诗意生成[ J ].当代电影,2020(02):6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