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终罢,咏叹双重美感
张曰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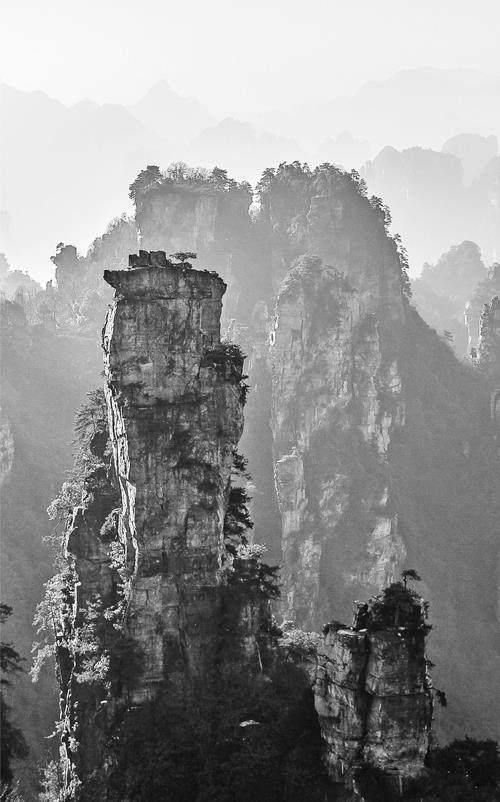
★都说诗词歌赋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它们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深厚意蕴。其实在文学历史上,有一些杂文也足以名垂千古,它们如一颗颗遗珠,闪烁着无上的智慧光芒。这就不得不提及古代文学史上的“大咖”——欧阳修。政治上,他是一位颇具宋代文人特色的普通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不为功名谋进退。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为朝廷出谋划策、推进“庆历新政”,不惜牺牲自己的官职甘受贬谪之苦,真是应了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展现了其博大的胸怀。文学上,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以韩愈为宗,极力反对浮靡、追求华丽的诗文,他的文章极负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他的诗词清丽婉约,颇受人们欢迎,尤其是杂文,充满浓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学特色,更受到了当时很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其中,《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让笔者曾经低声吟咏,其思想影响古今,其艺术手法彪炳千古。
一、文本前瞻铺好路
欧阳修既是文学家,也是具有厚重历史使命的政治家。为此,他专门撰写纪传体的史书《新五代史》。之所以说“新”,是为了区别北宋初年大臣、史学家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同学们都知道中华民族封建时代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莫过于“五代十国”。《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尤其是欧阳修居然为“伶官”作传,确实不可思议。“伶官”就是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他们专门为帝王提供茶余饭后的娱乐,但欧阳修本人对这种现象是痛心疾首的,而且他对“繁猥失实”、根本起不到劝善惩恶作用的《旧五代史》更是深恶痛绝,于是痛定思痛,干脆自己动手,私修一部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正史—《新五代史》,这本书带有欧阳修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他特别希望后世君主能够从混乱的时代中汲取历史经验,励精图治,不做乱世之君,更不要做亡国之君。另外,欧阳修本人独特的语言风格,更让这部史书与众不同,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文本感悟够深入
(一)第一重美感——深刻的思想内涵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大的存在,被称为“天可汗”的皇帝就有好几个,就这点而言,如果对中国的王朝进行排名,唐朝绝对名列前茅,但是唐朝后期实在有太多顽疾——藩镇割据、宦官专政、赋役沉重、起义不断,最终压垮了盛世大唐。虽然本文的题目看起来是为“伶官”作传,但是并未赘述伶官逸事,也未过多列举事例,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后唐庄宗李存勖身上。本文的主角李存勖是晋王李克用的儿子,他比父亲更为英勇,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六岁,当同龄人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他已经跟随父親李克用攻城略地,征战四方,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少年,后来他还在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建立了后唐,并登上帝位。登上帝位的他,谨遵父亲临终“三矢之托”,带兵灭后梁定都洛阳,此后又吞并岐国、前蜀,并拿下凤翔、汉中及两川,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南方割据势力,欧阳修也说他“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庄宗能延续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那么后唐顺延唐朝国祚,甚至超越唐朝也说不定,毕竟历史上很多开国皇帝都曾这样建立不世功勋。但是李存勖打下天下后“整个人都飘了”,开始沉湎声色,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在地方,横征暴敛,百姓过得水深火热;在用人方面,更是毫无原则,全凭喜好。最终导致君臣上下离心离德,走向灭亡。欧阳修虽然是借古论今,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一,李存勖这位开国之君较为罕见,开国皇帝一般都是要么勇猛过人,比如项羽;要么运筹帷幄、知人善用,比如刘邦。前期的李存勖两者兼具,曾被评为“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但是,建国后宠信伶官,还没有几年的时间,就被灭亡,后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第二,对当时的北宋来说,统治阶层笃信佛教,其实也类似于李存勖之宠信“伶官”。欧阳修更希望统治阶层能够践行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不满足于表面虚荣,关心时事,积极入世,无疑,这篇文章更像是讽喻时弊的文章。本文如明灯一样给北宋的很多士人当头棒喝,遗憾的是统治阶层听者、行者甚少,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观古今,知得失,我们可以体会欧阳修写此文的深刻用心。
(二)第二重美感——优美的行文表述
《五代史·伶官传序》其实是一篇典型的三段论议论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叙事,第三部分由叙事转入论理,三个部分层层深入、递进,充分显示出欧阳修说理讲究的特点。
第一部分——摆出观点。本文开篇就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开宗明义地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直接点明主旨,句子中“虽曰”“岂非”可以看出作者将兴和亡归结到“人事”上,没有冗杂多余的一个字。
第二部分——举例论证。先举李存勖的风光盛名故事,后举李存勖失败灭亡的悲惨结局。这两个段落为第三部分的主旨升华和总结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升华主题。作者由叙事直接转为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他先引用《尚书》中“满招损,谦得益”,然后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论点,而且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此之谓正反对比论证,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前后呼应,使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论述更是环环相扣,具有让人不可辩驳的说服力。
另外,本文的语言也有委婉规劝的一面。前文谈及,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时,时值北宋统治集团开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开始往享乐主义“靠拢”,作为一个有担当、有使命的政客,他完全可以奋笔疾书,上书朝廷,上书皇帝。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而是通过借史讽今的方式来委婉劝说,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