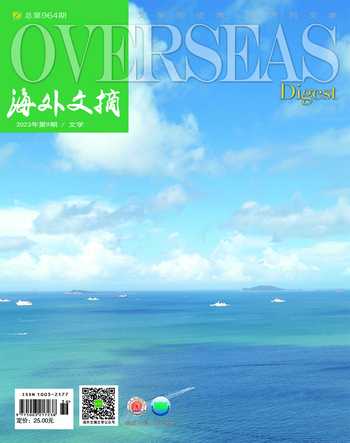父亲的头发
冯积岐

1
上世纪50 年代初,在我们村,父亲是唯一留着偏分头的年轻人。父亲从街道上走过去,他的偏分头传达的是独特,是自豪,是一份无法言说的心情,是一种美的形式,是一个时代的特征的写照。
父亲也是村子里唯一做了国家干部的年轻人。在我年幼的记忆中,父亲很英俊,高高的个子,走路时仰着头,腰板挺得很直。父亲的上身是一件灰色的中山服。父亲用配发的这件制服把自己和一身粗布的农民区分开来了。后来,父亲将浅灰色的制服换成了浅蓝色,他胸前别着的团徽闪着荣耀的光亮。那时候,我已经能够准确地记事了,对于父亲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现在捡拾起来,像做木匠的祖父在木头上打出的墨线:端直,没有扭曲或虚假之处。我拿起笔,试图将父亲的人生和印刷品相联系,可是,对我来说,父亲的人生有诸多空白之处。我没有权利去“塑造”我的父亲。填补父亲人生空白处的,是我的祖母,是父亲的档案。我要尽可能地还原从祖母口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有关父亲的词语。我是2014 年才看到父亲的档案的。那几年,弟弟担任我们村村委会的会计,合村并镇的时候,村干部把存放的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资料作为垃圾扔掉了。弟弟从一堆垃圾中拣出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的原来是父亲的档案。当代人没有见识过的“马粪纸”书写的档案,散发着浓烈的时代气息。我从父亲的档案中,读到了父亲的一段人生史。父亲在世时,从没有跟我讲述他那一段人生,只是偶尔流露几句和他的人生相关的警示性的言辭,我却并没有细细咀嚼,也没有询问过父亲。也许,父亲觉得,他那一段人生,艰辛多于成就,失意多于得意,屈辱多于荣耀,提及他的那一段人生,无异于揭伤疤。当我做了父亲之后,我才理解了父亲的心情和他当时的处境。
父亲生活的家,具有虚构般的“典型”特色:父亲是从距离我们村仅仅三里路的北郭村抱养的。父亲和祖父、祖母以及叔叔姑姑们没有血缘关系,而祖母又是祖父的第二任妻子,祖母和叔父姑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尽管,血缘一头挑着伦理,一头挑着情感;尽管,血缘和情感紧紧相依傍,但是,血缘不能替代情感;从祖母的言谈中,我能感觉到,父亲和祖父之间缺席的不只是血缘,而是情感。两个人的情感从开初就缺少河水般的清澈。情感的那棵树上结满了疤,疙疙瘩瘩的。可是,父亲在我跟前从来没有诟病过祖父一句,哪怕祖父性格上的缺陷,父亲也没有指责过。祖母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父亲14 岁那年得了伤寒,吃了好几服中药,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祖父以为父亲没救了,吩咐长工——我小时候叫他银儿叔——将父亲背到偏院里放麦糠的窑洞里去。父亲在麦糠上躺了三天三夜,银儿去窑洞背麦糠,发觉父亲没有断气,告诉了祖母。祖母吩咐银儿把他背回家。一月过后,父亲不仅活过来了,而且康复了。父亲在童年、少年时就受到了伤害,父亲心中烙印的伤痛,渗入了血液,构成了父亲性格的基因。
父亲曾经说过,他从小穿的是半截子鞋。父亲只说过这么一句,连第二句也没有。从这句话中,我窥视到父亲童年、少年时的生活状态,知道了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家,去参加革命。
1949 年农历腊月里,一个寒气逼人的日子,父亲步行一百多里路,从岐山县城到了宝鸡市,父亲拿着岐山县地下党的负责人祝培人的介绍信,走进了宝鸡军分区办的干部学校,开始了革命生涯。五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父亲回到了岐山县,参加了岐山县第五区一个乡的第一期土地改革运动。1950 年10 月15日,十八岁的父亲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十八岁的父亲满腔热情,朝气蓬勃,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
从1950 年起,父亲不再把浓密光亮的头发剃掉,而是留了偏分头。这发型,是父亲人生转折的纪念和标志,记录着他投身革命事业的心态。
回想起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还十分懵懂,不要说领导、指导一个村的土地改革,我连自己也把握不住;我的儿子在十八岁的时候,还在高三读书,准备考大学。而父亲十八岁那年,已经是土改工作队里的一名干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地负责一个村里的工作,风里来,雨里去,这家院门出,那家院门进;点亮一盏马灯,和农民们一起开会,宣传党的政策。逐户核查财产,“三榜”定案,确定家庭成分。1952 年,岐山县的三期土地改革结束以后,父亲所在的工作组给父亲做出的评价是:该同志思想进步,立场稳定,工作作风很好,能够吃苦,能广泛联系群众。父亲的同事们口中描绘的父亲的形象是:少言寡语,为人耿直,性格要强,干任何事都要极力干好。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父亲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他们那时候当干部,连群众的一支烟也不能抽的,不论什么级别的干部,必须清廉正直,秉公办事。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突然很严峻,眉宇间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后来我从父亲的档案中看到,父亲隐瞒了一个细节。1950 年,父亲在他工作的村子里,因为有一次在农民家里吃饭的时候,白吃过叫作白光浩和史培锡两个农民的几支纸烟,从父亲的名下扣除了150 斤小麦,作为补偿。岐山县刚解放,父亲他们当干部的没有工资,到年底,县政府给父亲他们小麦——究竟一个月给多少小麦,父亲没有给我说过,我至今不知道。在父亲当干部九年的时间里,他写过好几次思想汇报,也写过检讨。父亲的言语不多,但他一开口,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父亲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他们“那时候”的人格品质。父亲的干部履历表中,有一张是1952 年9 月18 日填写的,上面盖有岐山县委组织部的血红色印章,父亲被任命为岐山县第三区副区长。显然,这张履历表是组织部工作人员填写的。而这张履历表和父亲的人生毫无关系。虽然任命了,不知为什么,父亲并没有出任副区长一职,父亲的仕途二十岁的时候就夭折了。三期土地改革工作结束,父亲回到了岐山县人民政府,在农业局任干事,负责全县的会计培训工作。
父亲眼看着他的同事们一个个升为副科级或科级,而他依旧在干事的位置上,任凭他工作再卖力,也得不到提拔、重用。他毕竟太年轻,对现实缺乏洞察力,做人缺少智慧,1958 年,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父亲主动提出辞职回农村,县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人生的紧要处只有几步,那几步走错,步步错。第二年,父亲到县政府去,找到县长,说他想回县政府——当时,县长答应他,如果不适应农村生活,一年后,还可以回来的。可是,一年后,县长回答他:“现在,没有辞职干部回来的政策。父亲傻眼了,父亲即使后悔,也无法挽救了。”
2
1964 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坚硬如铁,那一年,父亲担任了七年的大队会计被撤职,他不再是生产大队里的干部。三十二岁的父亲剃去了自豪的偏分头,那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成为往昔岁月的祭奠,他的光头是步入艰难人生的标志,是悄然改变了心态的答案,是梦想彻底幻灭的词语。父亲穿上了母亲给他缝制的粗布对襟褂子。一家三代九口人,只有三间厦房。父亲为一家人的住房而发愁。那一年的秋天,断断续续地下了四十多天雨,房檐水的叮当声如同破衣烂衫,不停地在庄稼人的眼前摆动。街道霉了,房屋霉了,树木霉了,霉味儿像头顶上的阴云一样,覆盖了我的全部记忆。我和堂弟睡在被生产队拆去了屋顶的四面墙里,幸亏,土炕还在。我们上炕的时候,云团中死皮赖脸挤出的几颗星星在眨眼,不知半夜里什么时候下起了雨,等我们醒来的时候,被子已经湿透了,我们兄弟两个裹着湿透了的被子,靠住墙,坐在了厦房的房檐台阶上,坐到了天亮。到了初冬时节,父亲东拼西凑,借钱买了些木料,总算盖了一间半厦房,我和祖母才有了睡觉的地方。
1964 年的父亲,似乎老了许多,额头上显现出了明朗的皱纹。他很少说话,整天闷声不语。家里阴郁、苦闷的气氛,常常被父亲的一声叹息染得更加灰暗。父亲的神情如同搭配不当的句子,扭转了家庭里本来正常的意义。我真不知道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疲惫、沮丧,悄无声息地渗进了我的意识,使我有了一种很怯懦的感觉。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去县城。他由自负一下子跌到了自卑。他不去县城的原因是,担心会在县城街道上碰见和他一块儿工作的同事,他会因此而尴尬、窘迫,甚至很痛苦的。他躲避的不只是他的同事,他躲避的是他的命运。父亲的自卑是自尊的另一种表述。即使一把铁锨、锄头,他也不去隔壁借,而是支使母亲出面,他不向人张口。即使一座山压在身上,他也不弯腰。父亲性格上的自负、自尊和自卑的矛盾,书写在生活中的每一页。
70 年代,春夏之交,一家人常常缺粮吃,父亲支使我去亲戚、朋友家借粮,即使断了顿,父亲也不去低三下四地求人。父亲从家庭的大厦中抽去了顶梁柱的角色,使儿女们缺少安全感。支撑这个家的是母亲,母亲像一架纺车,从早到晚不停地转动,母亲的勤劳、忍耐、宽厚、仁慈,是她品质的概括,她是这个家的支柱。我记得很清楚,1976 年夏收时节,我们一家去给生产队割麦子,中午收了工,回到家又渴又饿,可是母亲没有做饭,不见了人影。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坐在房檐台上,一声不吭,冰冷的气氛充斥在夏日酷热的晌午。不一会儿,母亲满脸汗水,提着一袋子面回来了,进了灶房,开始和面、擀面。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有勇气张口询问母亲,她那天的一袋子面是从哪里讨要来的。
父亲虽然脾气暴躁,可是,他对儿女们从没有动过粗。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用粗话骂过我一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在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只要能保证六个儿女吃饱穿暖和,就是最珍贵的爱了。父亲疼爱儿女的方式是默默地去做,而不是付诸语言。
父亲不只是和我不交流,父亲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也不交流。在我的记忆里,父親在世时和我说过的话,一只竹笼子就可以提走。父亲是孤独的。不过,他偶尔说出的话,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他说:“攒钱不如攒本事。”他说:“要当干部,就不要白拿公家一分钱。”他说:“不论啥事儿出来,不要轻易表态。”这些简单朴素的语言,是父亲的经验,也是他的人生教训的结晶。
到了中年,父亲越来越怯懦了。1964 年,生产队里把家里的木面楼房拆走之后,我们和隔壁人家之间的隔墙也被生产队当作肥料拉运到地里去了。两家人的院子打通了,不论谁要去后院的厕所里方便,无遮无掩,都有些尴尬。一直到了上世纪80 年代初,我和父亲商量,把隔墙打起来。打墙的土是我用架子车拉到了后院的。打墙的那天,隔壁的女人出来阻拦,女人说,墙打在他们院子里了。我十分生气,要和那个女人说理。父亲知道,不能得罪她,也不敢得罪的。于是,他叫我和帮工的几个人停下来。父亲害怕每一个恶人,每一个强人。他为人处事,一步一步退让,只求平安无事。
3
收了又种,种了又收。日子从父亲那把镰刀上、锄头上流逝了,岁月无声地将父亲稀疏的头发染白了。留着自豪的偏分头,激情满怀地行走在岐山县城的父亲,永远地镶嵌在了时间的相框中了。满头白发的父亲,孤寂地蹲在门前那块石头上,仰望着寂寥的蓝天。他双手无力地搭在膝盖上,右手握着那杆没有烟嘴的烟锅,双目空洞,一副木然的样子。这时候,村里的一个中年女人走到了父亲跟前,说道:“哥,今天安葬你的老爹,听说,丧事过得很大,你不去拜祭吗?”
这个女人是从父亲出生的北郭村嫁到我们村里的。女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话,触到了父亲的痛处。她忽略了父亲一脸的阴郁,一脸的沮丧,还在继续说:“你去给烧张纸,叩个头。”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起身进了院门。
父亲的生身父亲去世了,本来,对儿子来说是一件悲痛的事情。可是,父亲的情感世界里没有悲痛,只有怨恨。一个郭姓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冯姓?因为什么,你把我送了人?父亲肯定这样想的。可以说,这件事,对于父亲是一种伤害,这种被伤害的怨恨从父亲懂事起,一直到他入土为安,未曾在心中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