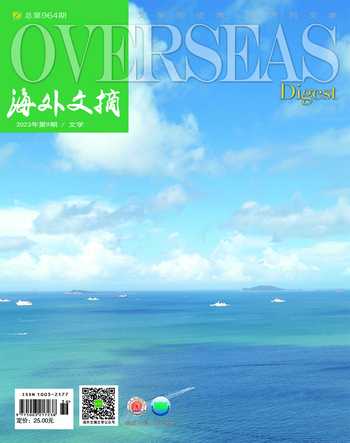过五关
胡方明

2023 年农历二月二十六,以及闰二月的同一天,我过了两个生日。
活到60 岁,居然过了61 个生日!我不在意接连过两个生日,只是庆幸自己活过60 岁,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按照我国干支纪年法,12 年为一轮回,也算是一关,每一个轮回都是一个生死劫难关,我竟然活过了五个轮回,过了五关,圆满活过了60 年一个花甲的大轮回。
十二岁那年某天早上的上学路上,一个叫张花的女学生喜笑颜开地给同学们讲述昨晚做的梦,说梦见自己出嫁,一人坐个大花轿,可美啦。就有同学问什么样的花轿,还有天真的同学抱怨张花怎么不叫同学们一起坐?张花说八抬的大花轿,可好看了,她一个人还美不过来,顾不上叫同学们坐。张花遗憾地说就是上轿时从轿里扑出的土喷了她一身一脸,她紧赶一步还是坐上了。张花她们说说笑笑向村外学校走去。
到校后不上文化课上劳动课,那个年代学习经常与劳动相结合:在学校操场后面的高崖挖焦泥。我们这里把高黏度土叫焦泥。挖的焦泥用水和成泥,再把焦泥用手团成乒乓球大小的焦泥丸(团焦泥丸劳动强度不大,和现在电子厂打螺丝一样,属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最适合学生群体干),晒核桃一般铺满操场晒干,村里打深井下管子时,要把大量的焦泥丸倾倒到水泥管外面:既要固定住水泥管,还要使地下水通过焦泥丸之间的缝隙流进布满指头粗细孔眼用棕片缠裹着的水泥管里,焦泥丸能起到固定和过滤作用。焦泥不是整片土地都有,焦泥有路线,顺着路线挖,挖着挖着在高崖上就挖成很深的洞,我们把这个洞叫焦泥洞。
这天,轮到张花他们班进洞挖焦泥,张花个子矮,自然排在第一名。张花不是扛着铁锨而是一只手拖着铁锨往里走。因为有铁锨在地上拖沓,后面的同学便和张花拉开了距离,跟在张花后面鱼贯而入的同学没留心踩在铁锨上摔倒了,后面的同学也没留心,便摔成一团,大家嘻嘻哈哈笑着往起爬。张花手上的铁锨是松松地拖着,铁锨从手上脱落掉下没有影响她走步,或许张花认为铁锨掉了,后面的同学会拾起来,替她拿进焦泥洞,或许,只是惯性使张花没有收住步子。反正张花没有停步子,头也没回,还跄了一步,快步走进焦泥洞。
不想头天晚上高崖上浇地,水钻进了禾鼠窝,一股脑全渗到焦泥洞顶上的土里。焦泥洞在张花进去后的一瞬间,突然从洞底往洞口像退坡似的发出巨大“噗噜噜”的沉闷声响,焦泥洞塌了!一瞬间塌陷产生的巨大压力,使焦泥洞里面的尘土,像我们当时看的电影里为表现主人公内心激情澎湃时、江河里突然凭空掀起的浑浊巨浪一样,一下子从焦泥洞里喷薄而出。这股浑浊巨浪般的土浪迎面冲出,冲得刚才踩住张花铁锨摔倒、这会儿已经爬起来或是正要爬起来的同学们又被冲倒在地上,一个个摔得四仰八叉灰头土脸。冲倒同学们后,这股土浪还没有散劲儿,继续往前横冲直撞,直到撞上高高的篮球架上面篮板,把篮板撞得发出“叭叭”炮仗一样的巨大声响,然后篮球板像被雷劈一般变成一缕一缕碎木条掉到地上后,这股土浪才转了方向,90°向上旋转着飘上蓝天,由粗变散,由近而远,飞走不见了。
这一切,是瞬间发生的!
老师们和学生们像魔怔一样,一下子定住了:和焦泥的停了锨,送焦泥的止了步,团焦泥丸的住了手,呆若木鸡地看着焦泥洞坍塌,看着土浪冲倒学生,看着土浪撞在篮球板上“叭叭”作响,看着土浪飘上蓝天变成尘土飞走后,才缓过神,老师们号叫着冲向坍塌的焦泥洞,同学们哭着也跟着冲向坍塌的焦泥洞,随后附近的村民们也跑来,用铁锨用手哭着喊着挖了一上午,才把张花挖了出来,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张花抬放到操场上。
一拥而上的人群不知怎么着把我挤进内圈,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几乎脸对脸地看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死人——刚才拖着铁锨神气十足地迎着朝阳往焦泥洞里走、早上从我家门前走过还在绘声绘色地讲她美好梦境的张花,这会儿被成千上万斤黄土拍成了平铺的土人——张花脸宽得几乎和双肩一般齐,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个鼻孔、一张嘴巴,全是血,血还从这七个孔洞里往外汩汩地冒着,把一张脸上的土冲出七道土红色溪流。就是多年以后看香港林正英的鬼片也没有这会儿面对眼前一米远近这具尸体的恐怖冲击力强烈。以至于直到小学毕业上完初中,我也不敢一個人在黑夜中独处,甚至包括在自己家里,即便是点着煤油灯也不敢,因为我总感到张花七窍流血的可怕样子如影随形地就在离我不远的黑暗处,吓得我浑身颤抖,边往后钻边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同学们都哭了,老师也哭了,村民们也哭了,操场上男女老少都在哭。我和同学们哭的是侥幸与害怕,老师和村民们哭的是责任和可怜张花这个花儿一样的年龄!
我第一次知道也见到死亡离我就是这样的近,就近在眼前,也有可能就是我,我只不过是侥幸者。
张花美好梦境的出嫁,竟然印证的是她如此悲惨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到现在,张花过世已快五十年,她的父母已亡故,兄弟姐妹的儿女们清明节也没人为她上香,连坟头也没有了,可怜她到世上来了一趟,像棵刚钻出土就被连根拔掉的小草一般,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
我和村人谈及张花,村人说,张花的命就是只有十几年寿命的命,可惜死的不是时候。我奇怪为什么不是时候,村里人说,若死在现在,做冥婚行的媒人能把她家门槛挤破,按现在行情,男方至少会给她家出二十万左右的冥婚钱。这娃娃白吃了家里十几年饭,没有给父母做一点点贡献。
村里人很为张花早已过世的父母愤愤不平。
十二年后,我在自己工作的剧团又见到了近在眼前的死亡。
剧团有个三十多岁的人,叫潘石。潘石名叫潘石长得也像磐石,但他不是矮壮的磐石,是人高马大孔武有力的磐石。潘石个子在一米八以上,和人打赌,胳膊展开,从脖子根到手掌间放饼子,放多少吃多少,一胳膊放了十八个饼子,潘石竟然不歇气吃完了。饭量大,力气大,潘石是剧团劳动队长,潘石干活时几乎不吭声,剧团最重的箱子是放服装的大衣箱,潘石一个人能抱起来装到车上,不管别人干不干,他不停地干。那些想躲奸耍滑者便也抹不下脸,跟着潘石干起来,大伙儿都说潘石人品好。劳动队装台是有补助金的,装卸台一次两元钱补助,一个月装台补助大概在二十元左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收入。
若要说潘石只是任劳任怨干活不惜力者那就太小看他了,潘石长得人高马大貌似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粗人,实则却是心灵手巧聪明过人的艺术家。潘石不是演员,他那么大的个子演戏谁和他配戏?也不是乐手,他的手指头那么粗壮,难按准二胡琴弦和笛子的笛眼。潘石是剧团的美术设计兼美工,他这个美工还兼木工。那时的剧团还没有现在剧团使用的LED屏幕,舞台布景全是手工绘制。潘石画舞台中间摆放的四扇屏,用木条钉好框架,把白布用秋皮钉钉好,白布不用上底色,直接在上面画梅兰竹菊。不知道别的美术家画四扇屏是怎么画的,潘石是把四扇屏靠在墙上画,不靠墙怕倒。潘石左手把一个很大的盘子托在小胳膊上,盘子里当然是各种颜色画料,右手指缝隙里夹着几支画笔,站在离四扇屏三两米的地方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挪动步子看。旁边想看他画四扇屏的演员乐手烟都吸了好几根,调侃他:“潘石,我们只看不学,不抢你饭碗。”潘石笑笑,走到四扇屏前用手在布上貌似很有章法地按几下,再后退两步看看,再上前用手按几下,然后长长出口气,按从左到右的顺序,用那几支画笔,蘸着盘子里的颜料在白布上画,也就是一两根烟的工夫,四扇屏画好了。观看者自然是一片喝彩声,潘石笑笑,连声说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大家说“胸有成竹”这个词说的就是潘石画四扇屏的过程。潘石还会在很大的白布上画《十五贯》县太爷况钟升堂的“明镜高悬”图,画《逼上梁山》高俅高太尉白虎堂的猛虎下山图,画《火焰驹》李彦荣妻母落难屈原庙里的两眼炯炯有神的屈原像;在更大的5×12 平米的白布上画或北方风光或南方竹林或农村面貌或城市街景等等之类的大布景,这样的大布景要画数十张,用作不同剧目的底幕幕布,以表现不同故事的场景,一本《杨门女将》就需要五六个背景底幕。画这样的大布景潘石得挑选风和日丽天蓝云高天气,先把剧团大院打扫干净,把让他媳妇用缝纫机扎好的大白布铺到干净的院子里,画好小样的图案摆在三角画架子上,潘石用一米五长的黄颜色木尺子和粗扁芯铅笔在大白布上画格子。画这样大布景,要用最大号板笔,一个人一天肯定画不完,剧团会通过文化局协调请剧院写戏报的美工和电影院画影壁的美工帮忙,一般一天就能画完。他还会把做四扇屏剩的边角废料三五下钉成简单的小凳子,谁坐拿走。若以为潘石只是业务能力强、是言语不多的人,那又小看了潘石,他若不动声色地讲起“黄”故事,能把众人笑倒一片。
这一年暑天还是和往年暑天一样闷热,现在已经忘记河南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只记得是灵宝县的一个有大水库的村子。
收假头一台就是这个村子。
我们坐的车子快进村时,看见了水库,大伙儿便喊了起来,装完台一身热汗,来这里游泳洗澡,美美凉快一下。装完台下午二三点钟,正是一天最热时,大伙儿成群结队出了村子。
这个水库有活水从山上流入。有活水流入的水便清澈凛冽,顺着一级一级台阶往下看,水库干净得一眼看得到底。
男男女女在水库边柳荫下坐了半圈,女孩子们把裤腿挽到膝盖,腿脚伸到水里凉快,小鱼儿竟然不怯人,在女孩子们莲藕一般的腿间穿行,惹得她们叽叽喳喳踢着水。男的大都脱了上衣和长裤子,露出那个时代时兴的两侧带白布条装饰或蓝色或黑色的运动短裤准备下水游泳。
有人问谁的水性好,大伙儿异口同声说潘石水性最好,解州人,关老爷老乡。关老爷水淹七军水性好,凭的是在盐湖里练出来的把式,潘石也在盐湖游过,当然他最好。
大伙儿夸潘石水性好,潘石不为此得意,坐在水库边沿脱着衣服,十分“气愤”地讲昨晚自己在家里的“黄”故事:两个娃娃知道明天爸爸就要走,缠着他就是不睡觉,都快天亮了才把两个娃娃哄睡着。以后几个月见不上老婆,得抓紧时间和老婆做“运动”,刚做了几下“运动”,老婆忽然不“运动”了,问他,等下次放假回来,装台费够给小麦买底肥吗?大伙儿“轰”的一下子笑了起来。潘石不笑,待大家笑声渐小,接着讲,咱正在做人类最伟大最原始最美好的神圣事情,若用电影里的手法表现,这会儿是要用宏大的交响乐陪衬,电视剧里也是用笛子领奏的《孤灯伴佳人》来烘托气氛,就是在咱舞台上,也得几杆唢呐吹着《亲家母打架》这类热闹喜庆曲子我才入洞房干這事儿,你他娘的却问我二铵做底肥好还是硝铵做底肥好?这还有什么趣味?大煞风景嘛。
男男女女们笑得都直不起腰。
潘石脱了衣服往水里走,还回头问我,怎么不到水里凉快凉快,我说不会水,他说,不怕,有我哩。
潘石踩着水里台阶往下走,才走了两步,突然嘴里似乎发出“哎哟”的吃惊声,猛地一个鹞子翻身脸朝上跌倒到水库里,并立刻沉了下去。
几个年轻的演职员便喊叫:“不好!潘石脚底打滑呛水了。”于是赶紧往潘石跟前游,“噼里哗啦”溅了满水库水花,不到五分钟,便把潘石捞上来了。
潘石死了!
懂水人说,潘石脚下打滑摔倒时,口鼻刚巧张开吸进了气,一口水呛进肺里,压得肺里的气出不去,水凉身热胳膊腿抽筋,人在水里动不了,人出不了水,水把肺憋炸了。
潘石竟然在转眼之间,就这样简单地死了?!
潘石死了,对别人没有多大影响,不过多了些茶余饭后谈资。对他们家就是塌了天:上有二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无人照顾,下面两个才上小学的儿女如何抚养,凭他妻子一个人怎么养活得起这五口之家?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人生三大悲哀,因潘石死亡,让他至亲至爱的三代亲人全都可怜地拥有了。
在我三十六岁的时候,一个名叫阎康凡的学长,因参加黑社会团伙抢劫打死人而被执行了死刑。他的恶劣事件刊登在当年的《山西青年》杂志上:阎康凡长期游荡社会,以偷抢为生,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团伙偷盗一外地人钱财,被发现后,阎康凡等人恼羞成怒,勒令司机停车,将外地人胁迫下车拳打脚踢,最恶劣的是阎康凡用钉了铁掌的皮鞋在外地人的头上狠踢猛踹,竟然把人家的脑浆踹了出来,外地人不能动弹后,他们一伙掏了钱包扬长而去。
这在我们的校友中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才毕业过三二百个学生的小型中专学校,竟然出了一个如此恶劣的杀人犯,真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阎康凡被枪毙死有余辜,这也是他应得的报应。只是他的父母成了杀人犯的父母,儿子也成了杀人犯的儿子。连他的兄弟姐妹,也被别人指指点点。从阎康凡往下,三代人都會因为家里出了个被枪毙的杀人犯而在人前抬不起头。一个人走上歧途,影响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名声。
四十八岁那年的冬天,我有了一生中最好的挣钱运气。从陕西蒲城、白水、澄县、合阳等煤厂往永济发电厂拉煤。
在此之前我是有工作的,因为认人不清,被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结婚时他家里请我做的总管和媒人,一个他自己对外号称是我狗腿子——宁力和管图,为了利益和地位,合力将我推进了泥淖,使我变成无业人员。对于他们的恩将仇报,我一直耿耿于怀。但人总是要养家糊口的,便筹钱买了辆前四后八的东风自卸车给电厂拉煤,此时大车少,赶上好时机,生意找人,一趟落千元左右,一天可以跑三四趟。司机开车,我负责给司机点烟聊天,为的是不让他瞌睡,算是个安全员角色。
这一天的心情特别不好,有两个原因:一是加油时,在加油站碰见宁力,我和他好几年没见过面,他看见了我,习惯地叫了句哥,然后油也不加轱辘冒烟地开车跑了,把反应过来的我气得,若他不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把车上这三十吨煤一股脑全卸到他小车上?二是卸了煤返回蒲城煤厂,竟然不让进门装煤,按说煤厂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可再怎么敲门说好话里面也没人理。
半夜,空车从蒲城放下来另找煤厂。司机年轻是个话痨只顾说话,我忽然发现大灯照的前面是空的,于是大喊一声停,司机出于本能踩死了刹车。多亏是空车,司机一脚把车刹死,车头已经悬在拐弯悬崖处。我和司机下车脚竟然找不着地,只能爬上司机楼顶跳进车厢从车尾下车,给救援车打电话,人家说晚上不敢上山。到天明,看见车停的形状和当年轰动一时的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里,恐怖分子卡在大桥断桥处的汽车状况一般无二。吓得司机一屁股坐在地上,当下就撂了挑子,打电话叫出租下了山。
救援吊车到中午才上来,随车人员说,前几天,他们县医院一辆救护车拉了七八个人吃席,就在这里撞断护栏掉下去,没一个囫囵个的,这会儿护栏还没有补上。把在山头冻了一夜的我气得要投诉公路段,救援人员说,救护车不到两吨都没拦住,你这前四后八那几根水泥栏杆顶个屁用,先人积了几辈子德你还要投诉?一个陌生人话糙理不糙的粗话令我醍醐灌顶,我现在不过是个底层的百姓,也快五十岁了,虽然没了工作,没了所谓的体面,但父母双全,家庭和睦,即便是没有了铁饭碗,我现在的收入,同龄人是没法相比的,人活得好好的,一根头发也没有损失,还有什么想不开?于是便释然了,没有什么想不开的。
隔日,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宁力的事知道吗?我汽修厂滴水成冰的室外,取暖不过是点着冒黑烟的废机油,虽然已经想开了,但现实的劳累还是让我心情烦躁,把手机夹在脖子里便问什么事?朋友问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看着原来舞文弄墨,这会儿被机油弄得乌黑的在给修车师傅打下手的双手,便说,你在幸福的天堂里。朋友说我还真猜得准,他就在送宁力去天堂的地方——殡仪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宁力前天突然脑出血,送到医院就迟了,他这会儿就在火葬场,脸朝西抬头看大烟囱冒着宁力的黑烟升上蓝天,也算是送宁力上天堂,进得去进不去,就看宁力的造化了。朋友听见我呀了一声,半会儿不说话,问我怎么了,我说,你还能听见?他说好好的吗?我说手机掉进机油盆里,估计马上就听不见了。
我忽然觉得天不太冷、两只手的黑油也不算太脏。假如,前天在加油站卸了煤,这会儿我还能这样幸福地用废机油取暖、双手油污、鼻尖悬着清鼻涕听修车师傅满嘴粗话修车吗?我一下子对人生全看开了,以至抱怨的念头从此消失。
今年过了年,我就有想写篇60 岁感想,没有动笔的原因是我不知道生日和意外哪个来得早,假如没有过生日人死了,却写了篇60 岁感想,不就贻笑大方?有这个顾虑也是因为前几天那个当年把我推进泥淖的管图也去世了,得的是肝癌。前一年,就开始疼痛,先是喝止痛药,后来要把止痛药剂注射到肝脏部位。去世前,让朋友捎话,想见我一面,朋友问我去不,我说,去吧,人活一世,能认识都是缘分。管图已经下不了床,用瘦骨嶙峋的手握着我的手,半晌,问我,哥,你今年平60 了吧?我说,生日还没过。管图说,哥,真羡慕你。我说,我有什么好羡慕的。管图说,羡慕你活到60 岁。我说,过了年你也60 岁。管图说,我的病我知道,熬不过今年。歇了会儿,管图又说,老辈人说,阳寿不到60 岁,都是还欠债的。
管图的话,透出点给我道歉的意思。
活到60 岁一甲子,是一个近在眼前的目标,对管图来说,竟然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难以实现。
活过60 年岁月的人,都是闯过了一个个生死关卡。活过60 岁的人,并非有高于他人的本领,是幸运,是意外,是老天眷顾,也是命中如此。活着是短暂的,死亡才是永恒。在我的熟人圈子里,已经有一部分人去了永恒世界。我的圈子从以前缓慢缩小到现在加速缩小,还有一批人以看得见的速度衰老,向着永恒世界列队而行。所谓的锻炼和医疗,不过是让迈向永恒的步子,再蹒跚缓慢点,但绝不会停步,毕竟,永恒世界是一切拥有生命者的最终归宿。
但凡活着,都要认真活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