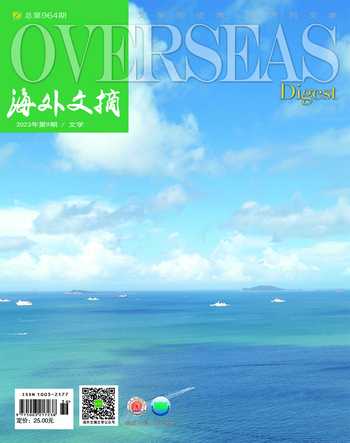少年行
於可训

少小无端惯放狂,骣骑沙牯战牛郎。
探得湖山开洞府,便教人鬼捉迷藏。
——定场诗
一、下湖路上
川儿一趴上他家那条水牯的背,小卵子就硌得生疼。
人家的牛走起路来,像戏台上的县官,四平八稳,川儿家的水牯一出村,就一路疯跑。
走得快一点儿的肉猪,被它吓得哼哼乱叫,也跟着疯跑。拖儿带女,慢悠悠地走着的猪娘,怕她的儿女被踩着了,只好带着队伍往路边避让。有那避让不及,腾挪不开的,就像下饺子一样,扑扑啦啦地都掉到路边的秧田里去了。
秧田里的头季稻正在灌浆,就要成熟。掉下去的猪儿晕头晕脑,不辨方向,往秧田中间冲了一段,见猪娘还在岸上,又挣扎着想爬回去,田里的青秧顿时倒伏一片。
就听见下湖的队伍里有人开骂,骂什么事,谁也没听清楚,无非是骂川儿没把自家的牛看好,再就是骂川儿家的水牯发疯,骂完了人就骂畜生,村里的男人女人,哪个不是张口就骂,骂人是一日三餐,家常便饭。
再说,骂的人也不是认真生气,都知道这样倒伏的秧,很快又会长回来,何况这秧田又不是自家的,骂几句就图个嘴巴快活,闭了一夜的嘴,都闭臭了,这一开一合,吸几口凉气,也是蛮舒服的。
川儿也不理会,只顾在牛背上调整自己的姿势。
水牯的背宽,川儿的腿短,除了一根牛索,又没个抓挠,调整起来十分困难。
眼见得脚下的大猪小猪纷纷乱窜,身边的骂声叫声此起彼伏,自家的水牯,却像杀红了眼的李逵,只顾挥动板斧排头砍去,挺起双角一路狂奔,哪管得了脚下磕着了谁,碰着了谁。
川儿想,像这样下去,只怕自己的卵袋子要被颠破,只好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水牯的脖颈,又用胸口牢牢贴着水牯的前脊,却把下半身抬起来,像倒立的蜻蜓,跷起双腿,随着牛背的起伏上下簸动,死活不让张开的裤裆碰着了牛背。
终于赶上了元贞家的母牛。
一靠近母牛,川儿家的水牯就迫不及待地抬起两条前腿,搭上母牛的后背。紧接着,元贞的身后,就发生了一阵剧烈的冲撞,等骑在牛背上的元贞回过头来,才发现川儿家的水牯正在跟自家的水沙(母牛)爬骚。
元贞就冲着川儿大喊,下来,下来,快下来,水沙一颠屁股,就要把你摔死。
川儿往下一看,自己已被上半身挺立着的水牯悬在半空当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
水牯的身子不停地耸动,川儿抱不紧也贴不住,只好闭上眼睛,死死地拽着那根救命的牛索不放。
谁知这一拽,竟把水牯的脑袋从水沙背上拽弯了过来,正在兴头上的水牯突然哞地叫了一声,一甩脑袋,牛索带着川儿,就像一粒泥丸一样,从半空中被抛到秧田里面,半天爬不起来。
元贞见状,也从自家的牛背上往下跳,冲过去把川儿从泥水里拉起来,一边拉一边埋怨川儿说,叫你跳,你不跳,你看险不险,要是掉到水牯的胯裆下面,公的母的,手忙脚乱,踩也要把你踩死,没听老人说嘛,宁挨千刀万刀,不惹公母爬骚。
末了还要补上一句说,你家的水牯真骚。
川儿说,你不撩,它也骚不起来。
元贞就笑,说,你说清楚啊,我没撩,是我家水沙撩。
两人就这样站在路边,你一句我一句地等着这一公一母把那事做完,才又骑上各自的牛背,相跟着朝湖堤那边走去。
被堵成了一条长龙的下湖的队伍,也开始缓缓移动,像后河的积水打开了闸门。
二、骑在牛背上打仗
翻过湖堤,是一片湖滩。
湖滩很大,像画上画的草原。
湖滩外面,是一片湖水,水面更大,像书上说的海洋。
湖水一半是从后河顺流下来的山洪,一半是从长港倒灌进来的江水。
湖滩被流过的后河切成两半,一半在东,一半在西。
东边有一段湖堤,叫东坝,西边也有一段湖堤,叫西坝。
住在东坝的人和住在西坝的人,世世代代守着这片湖水和湖滩过日子,睦邻友好,相安无事,两边的人,还有许多谁也说不清楚的亲套親、友绊友的关系,平日里来往频繁,不分彼此。
只是每次淹了大水之后,为了重新划定湖滩的边界,东坝和西坝都会有一次抢滩的争斗,那是祖辈留下来的规矩,慢慢地就成了一种习俗。
就是抢滩的时候,两姓人也顾着面子,都用长裤反包着头脸,从上面剪两个洞看人,像电影里的三K党,俗话说,人怕抵面,树怕剥皮,反正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就是姑爷娘舅,也敢放手争抢,这就叫翻脸,翻脸不认人,抢起来才尽兴。
虽然在抢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意外,却从来也没有伤着和气,抢完了,又各自守着新的边界捕捞放牧,直到下一次淹水之后。
到了川儿和元贞他们长大的时候,已不兴抢滩,说那是宗族械斗,严令禁止,但各家大人却喜欢把抢滩的故事当作饭桌上的谈资。
有那参加过抢滩的老人,或见过抢滩的父辈,更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抢滩的过程和细节,由他们添油加醋说得天花乱坠,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要夸大自己的本领和作用,让这帮小辈子一听就想起说书的猪娘嘴说的,燕人张翼德,常山赵子龙。
不论真假,除了恨自己晚生了几年,这帮听故事的小辈子,都只能张着嘴巴点头,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这些英雄脚下。
也有那不满足于听故事的,也想像大人那样过一下抢滩的瘾,东西坝都有这样的孩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东西坝骑牛下湖的孩子,过了湖堤之后,都不解牛鼻桊,也不收牛索,都把自家的牛当战马,要骑在牛背上打一仗,才把牛放开。
打赢了的,就是这天的大王,要坐金銮殿,让打输了的下跪磕头。
仗打完了以后,不论输赢,还是以湖滩中间流过的后河为界,各到各的半边湖滩放猪放牛,打草挖菜,就像大人抢滩过后一样。
堤下面正好有一片空场,堤坝上有防洪时筑的几座土牛,参差排列,错落有致,显得峰回路转,冈峦起伏,看上去,就像连环画上画的战场一样。
要打仗,总得有个领兵的头儿,东坝的孩子就公推国梁。
国梁是个哑巴,听说是小时候生病吃错了朱砂,在东坝这群孩子中,国梁最大,辈分最高,川儿和元贞他们都叫他叫叔。
国梁不光年龄大、辈分高,而且讲义气、胆子大,村里的孩子,有什么事都是他出头,有时候,大人有些事,也要找他,都说他认哑理,没有人争得过他。
其实,这只是村里人的一个说道,国梁连话都不会说,还能跟人争什么事,村里人主要是看中了他那个一根筋认死理的脾气,他答应了的事,就没见有办不到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有一次,有人差元贞的爹卖猪儿的钱不给,元贞的爹找到国梁,国梁就天天跟在那人背后讨要,那人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竟坐在那人家门口不走,直到这家人觉得实在丢不起这个脸,才给了钱打发他走人。
事后,村里人都说,这就叫哑人讲哑理,也只有用这种哑法子,才能治得了这种人,国梁于是名声大振。
国梁带的东坝的队伍,有十多条牛,下了湖堤之后,就在湖堤下边的空场子上一字儿排开,等着西坝的孩子骑牛过来,一会儿,西坝的牛队果然也排成一字朝这边走来。
看看两支牛队将要靠近,国梁举起手中的木棍一挥,就带着队伍冲了上去。
往日接上火以后,就是一场混战,不分兵将,也不讲打法,只是各自骑在牛背上,挥动手中的棍棒竹片,在对方阵中横冲直撞,挡不住的一方,就往后退,退到湖水边上了,就得认输。
东坝的孩子因为经常占着上风,从来没把西坝的牛队放在眼里,往往不到泡尿工夫,西坝的牛队就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这天的架势跟往常一样,国梁在前,川儿和元贞紧随其后,其他孩子依次呈楔形展开,跟着他们朝西坝的牛队冲去。
西坝的孩子看他们冲过来了,并不迎战,而是掉转牛头,往后便走。
东坝的孩子以为他们抵挡不住,像往常一样,在后面紧紧追赶,想把他们一口气追到湖水边上。
谁知他们没追多远,就看见前面不远处升起一股浓烟,瞬间就有一条火龙擦着地面朝这边滚来。
国梁见状,赶紧勒住牛索,指挥队伍后退,西坝的孩子却趁势掩杀过来,东坝的牛队顿时阵脚大乱,没等西坝的孩子追到水边,都纷纷跳下牛背,束手就擒。
西坝的孩子终于得了一次胜利,就要东坝的孩子下跪磕头。
东坝的孩子说,这个不算,你们用了计谋。
西坝的孩子就笑,说,哪有打仗不用计谋的,打仗不用计谋,要诸葛亮搞么事。
两边正吵得不可开交,国梁突然冲过去,把西坝的孩子一个一个拉到土牛边上,把他们扶在土牛上一一坐定,然后纳头便拜。
东坝的孩子见国梁拜了,只好跟着下跪。
西坝的孩子乐得在土牛上跳起来欢呼,一点儿也没有想到,现在他们是大王,正坐在金銮殿上。
拜过了,川儿就问西坝的一个孩子,这主意是哪个出的。
西坝这孩子就用手一指不远处站着的一个瘦瘦的男孩说,哪個,除了他,还有哪个,就他的鬼点子多。
川儿说,他这摆的是火龙阵哪,我听猪娘嘴说书说过,火龙阵就是这样摆的。
那孩子就不作声。
川儿见那孩子不说话,以为他觉得赢得不光彩。
又说,说实话,不是他,你们也赢不了,他真是你们的智多星哪。
谁知那孩子听了,嘴巴一撇,鼻子一哼说,还智多星呢,狗屁,我看是个害人精。
见川儿满脸疑惑地看着他,又把嘴巴往西坝那边一挑,说,你自己去看吧,把人家挖了半个月的霸路根,烧了个精光,人家攒在那里,今天正要一起拉回去,这下好了,又要害得人家挨打饿饭。
川儿就顺着他的嘴巴指的方向看过去,就见那边的堤坝下面,刚燃过的火龙,正冒着青烟,周边的草地,已烧成一片灰烬,灰烬场上,似乎有个人正在扒拉着什么,就拉起身边站着的元贞说,走,看看去。
两人就相跟着朝那边跑过去。
三、挖霸路根的女孩
在灰烬场上扒拉东西的,是个女孩。这女孩名叫玉霞,是元贞的表妹。
元贞的姆妈是西坝人,玉霞的爹是元贞的亲舅。
元贞小时候,跟他姆妈去他舅家走亲戚,常跟玉霞在一起玩耍。
后来,玉霞的姆妈死了,她爹又给她找了个后姆妈。玉霞的后姆妈带了个男孩过来,她只爱自己的儿子,不爱玉霞,动不动就打她骂她,有时候还不给饭吃。
玉霞的爹心疼女儿,但老婆太恶,他也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一个恶嫂子,元贞的姆妈就很少上门,元贞也就有好几年没见着玉霞了。
元贞最后一次见到玉霞的时候,玉霞还只有五岁。玉霞的姆妈就是那年得病死的。
元贞跟着他姆妈去他舅家吊丧的时候,玉霞吓得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躲在房门背后不敢出来,元贞的姆妈要走的时候,才在房门背后找到她。元贞的姆妈一把把她拉到怀里,哭得连元贞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按元贞的年龄算,玉霞也该有十来岁了,要不是她眉心的那颗美人痣,元贞差点就认不出她来了。
看到眼前这番景象,不用问,元贞和川儿就知道是么回事。
元贞和川儿都听元贞的姆妈说过,玉霞的后姆妈是从后山嫁过来的,烧惯了山柴,嫌稻草煮饭不熬火,就要玉霞到坝上去挖霸路根。
霸路根紧贴着湖堤河坝生长,细长的根须像铁丝一样,扎在湖堤河坝深处,上面的茎叶也硬如铁线,细如丝网,密密麻麻地覆盖着路面,除了经常有人畜过往的地方,所有的路面都被它霸占了。
湖区的人都知道霸路根熬火经烧,就是挖起来费力,锄头铁锹都使不上劲,得用铁扒先把泥沙扒开,让细长的根须露出一截来,再用木棍绕住,像纳鞋底一样,用力往外拉扯,有时候扯断了,还要伸出手去,绕在手腕上帮忙扯,扯多了,玉霞的手腕上就留下了道道血印子。
夏天上晒下烤,冬天趴冰卧雪,过路的人看着都心疼,知情人没人不骂那个狠心的后姆妈。
元贞心疼他表妹,就说,你为么事要让他烧,他又不是你的亲弟,你这样惯着他,迟早他也不把你当人。
元贞说的那个不是玉霞的亲弟的孩子,就是西坝的孩子指给他看的那个瘦瘦的男孩,这男孩叫春树,是玉霞的后姆妈带来的。
玉霞说,也不能怪他,总是你们赢,他好不容易想出这个赢你们法子,你们也让他们赢一回。
元贞只好摇头说,好好好好,你说的也在理,就让他们赢一回。
又放心不下说,你好不容易挖了半个月的霸路根,都让他烧了,你回去么样交代。
玉霞若无其事地说,就再挨一顿打,饿几餐饭呗,说完,又用手上的铁扒在面前的草灰中乱扒。
元贞就问她扒么事,玉霞说,我早上没吃饭就出来了,刚才看见一个烧熟了的野篙芭,我想看看还有没有,他们烧的,不光是我挖的霸路根,还有平时从湖里扯上来的篙芭秧。
元贞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身上带的吃食都拿出来,交给玉霞。
又问川儿,带了吗?
川儿说,带了,也把自己的吃食拿出来,给了玉霞。
下湖的孩子中午都要在外面吃一餐,大部分是湖里的出产,有时候也从家里带点吃食出来。
回到自己的队伍那边,东西坝的孩子都散了,牛也野放了,都在湖滩上自由自在地吃草。
元贞和川儿就把刚才见到的,都跟东坝的孩子说了,东坝的孩子都很气愤,有的就想去把那个瘦猴揍一顿,帮元贞的表妹出口气。
元贞也想趁机教训教训这个拖油瓶,省得他以后欺负玉霞。湖滩上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了算鬼打的,谁也不晓得。
国梁是后天的哑巴,人哑心不哑,元贞他们的话,他都听明白了,当下就连连摇头,表示不可,又指指划划地用手比了半天,意思是我们回去拿铁扒来,帮玉霞挖霸路根。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觉得还是国梁的这个主意实在,能够救急,瘦猴就暂时饶了他,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
湖滩离村子不远,东坝的孩子很快就从各家取来了铁扒木棍,在湖堤上摆开架势开挖。
西坝的孩子起先不知道东坝的孩子在玩么事鬼把戏,等到他们看明白了,也跑回家去,拿来铁扒木棍帮忙。
傍晚时分,东西坝的孩子把挖好的霸路根打成捆,送到玉霞身边。
春树过来帮忙把一捆一捆的霸路根都绑到自家的牛背上,又把玉霞扶上牛背,让她骑在牛背上,自己牵着牛索在下面走,就像玉霞的跟班一样。
川儿说,这还像个弟弟。
元贞说,狗屁,他这是怕挨打,做给我们看的。
川儿说,你也不要把人想得太坏了,他姆妈对玉霞不好,未见得他也对玉霞不好,我看玉霞这个瘦猴弟弟还不错。
四、元贞跟春树成了好朋友
元贞不喜欢春树,他舅喜欢。
玉霞的姆妈只生了玉霞,她爹早就想要个男孩,现在有了个现成的儿子,就把他当宝贝,出出进进,走到哪里都帶着他。
元贞的三哥结婚,玉霞的爹过来吃喜酒,也带着春树。
东西坝离得又不远,吃完了喜酒,玉霞的爹还要和春树留在元贞家过夜。
元贞家有个木楼,元贞的姆妈就要春树跟元贞在楼上睡,元贞不愿意,元贞的姆妈就拿眼睛横他,元贞只好带着春树上楼。
楼上只有一张大竹床,元贞本来打算一人睡一头,后来又怕闻春树的臭脚,就挤在一头睡了。
元贞家的房子很老,撑房子的列架都是黑的,湖区的房子都有列架,列架就像人身上的骨架,把皮肉撑起来,列架也撑着做房子的砖瓦。
湖区常发大水,大水来的时候,把列架用木桩和铁丝固定,只把屋顶盖的布瓦揭下来,把墙上砌的石砖拆下来,等大水过去之后依样还原。
年数长的列架,像年纪大的人一样,身上有很多故事,说半夜里听见列架里风吹浪打,那是常事,说听见有人呼叫,也不在少数。
到了该换列架的时候,换列架的人家从拆下的旧列架里发现的东西,就更加稀奇古怪了,列架的柱脚里,是黄鳝泥鳅乌龟王八理想的藏身之所,列架的缝隙中,也常有蛇蝎蜈蚣蝼蚁蜂虫出没,高处的梁柱,低处的榫头间,说不定就勾住了几样随水漂下来的金银首饰丝绦玉挂,后山的富人多,山洪来了,只顾逃命,这些平时的宝爱之物,也就任其随水飘散,流落寻常人家。
元贞最怕在列架里做窝的老鼠,平时一个人睡在木楼的竹床上,半夜里醒来,突然看见一双眼睛,在枕头边上一动不动地直愣愣地盯着他,把他的魂都吓掉了,有时候,这些小东西还把元贞的脑袋当了油壶灯盏,在油壶灯盏上没舔够,就到元贞的脸上舔,害得元贞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睡觉都用被子蒙着头。
这天早晨,天蒙蒙亮,屋顶上一块暗黄的亮瓦,向木楼里透着微光,元贞正想起来拉泡尿,再睡个回笼觉,眼睛还未睁开,就感到有个凉丝丝的东西,从额头上滑过,元贞以为又是那些小东西在作怪,心想,天都亮了,你也吓不倒我,就想翻身起来,哪知他刚一侧过脑袋,就看见枕头边上,一个长条的东西,嗖的一下卷成一个小饼,窝在那里一动不动,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拇指粗的花蛇,刚才从自己的额头上滑过的,就是它。
元贞大气也不敢出,一边直挺挺地躺着身子,一边在被子底下轻轻地推了春树一下,春树正好是侧面朝着元贞睡的,眼睛一睁,就看见了蛇饼。
元贞正要叫他小心,却见春树从被窝里一跃而起,伸手就抓那块蛇饼,没等元贞反应过来,蛇尾巴已到了春树手里,蛇被他倒提着,抖成了一根直直的面线。
元贞长出了一口气,也翻身起来,想下楼去拿个火钳,把蛇夹了丢出去。
春树说,莫丢,莫丢,这是一条家蛇,就让它在你家养着吧,你不是怕老鼠吗,家蛇专门捉老鼠,吃老鼠,比猫还厉害。
又把已经抖晕了的那条蛇,顺手挂到屋梁上,说,它一会儿就醒了,醒了就让它自己回窝吧。
元贞觉得奇怪,自己怕都怕不过来,春树还说要放家里养着,你就不怕它哪天咬你一口吗,虽说水蛇咬个疱,一边走一边消,蛇终归是蛇,又不是人,养在家里总有点儿吓人。
见元贞觉得奇怪,春树就说,我们后山,家家都养家蛇,有的还不只养一条,家蛇不用喂食,有几条是几条,你不赶它走就行,家蛇也不咬人,跟人很亲热,像这样卷成个饼,在你枕头边上睡觉,是常事,闻惯了你的气味,还不愿意换人,就像你老婆一样。
又嘻嘻一笑说,你身上沾了蛇气,到哪里都有蛇找你,我猜你家这条蛇是来找我的,我怕吓着你,才把它抖晕了,它醒了还要怪我太不讲客气。
经过这件事,元贞便对春树刮目相看,以后春树再到他家来,无论有事无事,都要留他过夜,也不用他姆妈叫,就拉着春树上楼睡觉,两人渐渐地就成了好朋友。
元贞对那条小花蛇又怕又爱,心里一直想着那条小花蛇,后来却一直没有见着它,有一次就问春树是么回事。
春树说,它一定是见了我的怪了。
五、春树带元贞钻山洞
湖边的孩子都没进过山,只会玩水,不敢钻山。
湖中间有一座山,不高,也不大,秋冬季节,落水的时候,看上去像一座山。春夏季节,涨水的时候,远远望去,就像菜盘子里摆的一条听话鱼,一点儿山的样子也没有。
元贞和春树成了好朋友,春树就带元贞去山上玩。
这天上午,元贞摇着自家的小船,和春树来到小山脚下。
元贞从来没有靠近小山,以为小山就像一棵树,根长在水底下,身子露出在水面上,只要靠近它,就可以攀住树上的枝杈往上爬,就像平时上树翻老鸹窝一样。
到了小山脚下,他才发现,小山是漂在水面上的,就像自己划的小船一样,只不过底下多了一个托盘,这个托盘就是山脚下的一圈沙滩,沙滩上铺了一层白色的细沙,像过年蒸粑时蒸锅外沿围着的一圈白布。
从船上下来,踏上这片沙滩,元贞就感到脚底下麻痒痒的,像踩着了稻场上的谷子,很快就听到春树在喊,山洞,山洞,走,到洞里去看看。
顺着春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元贞果然看见山脚下有个洞口,两人就一前一后朝洞口跑过去。
进了山洞,春树才发现,这个山洞和他们后山的山洞不一样,后山的洞里,石头都是黑色的,这里的石头都是白色的和黄色的,后山的山洞里石头是卡在山缝里的,这里的石头是吊在半空中的,后山的山洞里没有水,这里到处都是水淋淋的,后山的山洞空荡荡的,像一间大房子,这里的山洞挂满了石头,密密麻麻,七歪八扭,像连环画上妖怪的迷宫,这些石头长得也怪,有的像山上长的笋,有的像庙里挂的钟,有的像猪马牛羊,有的像男人女人,也有的像柱子,像镰刀,像葫芦,像麻花,外面有什么,这里就像什么,好像照着长的一样。
春树觉得新奇,元贞是第一次钻洞,更感新奇,两人相跟着在洞里转悠,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石头上光溜溜的,滑腻腻的,像抓着无鳞的黄鳝和泥鳅一样。
洞里光线很差,靠近洞口的地方,还有一些光亮,再往里走就看不到路了,一不小心就要撞到吊着的石头上,春树就对元贞说,你等等我,我去去就来,说完这话,春树就不见了人影。
不一会儿工夫,春树回来了,手里还举着两支火把,元贞问他在哪儿弄的,春树笑笑说,山里的孩子都会扎火把,山上有庙,在菩萨面前的油灯上点着就行了。
两人举着火把就朝黑魆魆的山洞里头走去。
走过了一段羊肠小道,又爬上了一个高坡,从高坡上下来,沿着一条水沟走了一阵,过了水沟,又是一些岔道,春树拉着元贞走了一条石柱不那么多的小道,走到尽头,忽然发现面前有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有村里的稻场那么大,元贞抬头一看,上面是一个圆顶,顶上不停有水珠子往下落,像家里的破茅屋正在漏雨,周围像被水冲过的烂泥墙,疤疤癞癞的,跟癞蛤蟆的背一个样。
元贞正想着从哪儿穿过这片空地,突然听见春树在喊,快来看,快来看,这里有个地窖。
元贞跑过去一看,原来这块空地的尽头有一个大坑,坑很深,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好像还有呼呼的风声和哗哗的水流声,春树用火把一照,才发现坑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东西,像家里堆杂物的柴房一样。
元贞正想从旁边的一个斜坡下去看看,春树突然指着远处的暗影说,鬼火,鬼火,快别下去,下面有鬼。
元贞一向怕鬼,听春树这样一叫,就停住了脚步,抬头一看,果然见远处的暗影中,有麻麻匝匝的光亮在忽忽闪动,元贞见过鬼火,清明前后,放牛回来晚了,从畈上的坟地经过,总有星星点点的鬼火像萤火虫一样四处飘荡,元贞赶上自家的牛,一路飞跑,真像有个恶鬼在后面追着。
春树说下面有鬼,元贞就不敢停留,赶紧招呼春树快走,两人就沿着来路往回飞奔,没跑出多远,元贞就听见身后呼呼风响,好像有一群恶鬼从坑里跳出来了,正在他们后面拼命追赶,鬼群带着阴风,凉飕飕的,吹着他们的后背,差点把他们手中的火把吹熄了,元贞好像还听见这些鬼一边跑,一边在恶狠狠地叫着,吃了你,吃了你!
好不容易跑出了山洞,元贞呼的一下扑倒在沙滩上,口里还不停地喊着,我的个姆妈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叫了半天,见身边没有动静,元贞好生奇怪,就撑起身子四面察看,这才发现春树没有出来。明明是跟我一起往外跑的,跑得比我还快,怎么就不見了呢,莫不是跑迷了路,找不到洞口,要不就是被鬼抓住了,拖回到坑里去了,元贞越想越怕,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哭了一会儿,天快黑了,元贞怕春树真的出了事,回去不好交代,就捡起火把想进洞去找,还没到洞口,又感到害怕,只好在洞口晃动火把,想给洞里的春树打个信号。
过了一会儿,春树果然从洞里出来了,不跑也不跳,不哭也不叫,就这么呆呆地往外走,手里的火把也不见了,见了元贞,也不打招呼,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径直从他身边朝停在沙滩边的小船走去。
元贞以为春树生他的气,就跟在春树后边不停地解释,春树也不理他,自己到船上坐下了,元贞只好操起双桨,把小船划到湖岸边,带着发呆的春树回到了自己的家。
六、山洞的故事
春树到家后就病倒了,起先是不想吃饭,只想睡觉,睡了一会儿,就开始发烧,烧到半夜,就说胡话,说什么,也听不清楚,元贞的姆妈有点儿着急,担心她弟和弟媳怪罪,她和这个新弟媳的关系本来就有点疙疙瘩瘩,弄不好会伤了两家人的和气。
元贞的爹说,不怕,冇得事,他这是受了惊吓。
又到畈上去扯了些安魂草,煎水让春树喝了,第二天,春树的烧就退了,只是身上没劲儿,元贞的爹就让他躺在床上不要起来,正好下雨,田里没事,他就坐在春树的床边给他讲故事。
元贞的爹讲的,就是这个山洞的故事。
说是很久很久以前,这里都是山,没有湖,也没有东坝和西坝,东坝西坝是两个山尖尖,湖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山洼,另外还有一座小山,就长在这个山洼的中间。
后来江水改道了,把山洼冲成了一片湖,慢慢地也削平了这些山尖尖,东边和西边的两座山,就剩下一些高台子,再后来在高台子上就筑了防水的堤坝,就是今天的东坝和西坝。
山洼洼中间的那座山本来也该削平了的,奇怪的是两边的山都变成了防水坝,这座山却站在湖中间纹丝不动,只是个子比以前矮了许多,就像一个人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只有肩膀和脑袋露在外面。
有人说,这是神仙有意留下的,好在过湖的时候踏个脚,有的说这座山的山神土地很厉害,湖里的龙王斗不过它们,也有的说这座山下面有很多洞,水都从这些洞里穿过去了,就没有伤着山的身子。
直到有一年发山洪,后山的村村寨寨大集小镇被冲得七零八落,一些富户人家的房梁屋架,箱笼桌柜,金银珠宝,有的都沿着后河飘到湖里,山洪过后,一些富户就打发人到湖里来打捞,打捞的人很快就发现,这些从后山冲下来的东西,多半都在山洞里搁住了,山洞是个回水湾,吸水又吸风,里面高坡低坎,坑坑洼洼,冲下来的东西,进去了就出不来,据说也有些富户真的在里面找到了一些财物,至于这些财物是不是自家的,就说不定了。
再后来,附近的村民也想发点外财,就成群结队地进洞捡落,只是后来又传出话来,说洞里有鬼,有人听见鬼叫,有人看见鬼火,有人面对面跟鬼撞了个正着,却看不清鬼的样子,像撞着了一个人影子,也有的说,这些鬼还吃人,有人带进洞去的孩子,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
再再后来,就没有人敢进洞了,有那大胆的孩子想进洞去玩,大人就吓唬他说,洞里有猫胡子,小心吃了你。
春树就问,猫胡子是个么东西。
元贞的爹接着说,猫胡子本来该叫麻胡子,我们这地方的土话麻猫不分,麻胡子就叫成了猫胡子。
春树又问,麻胡子又是个么东西。
元贞的爹到下江去卖过猪儿,听扬州人讲过麻胡子的故事,就笑着说,麻胡子是个人,不是个东西。
说是隋炀帝修运河的时候,有个管事的将军叫麻叔谋,麻叔谋长了一脸大胡子,所以人家又叫他麻胡子,这麻胡子有一次得了一种病,要小羊羔的肉做药引子,当地的小羊羔都被他吃完了也不见好,巴结他的人就想别的歪心思,有个财主为保自家在河道上的祖坟不被搬迁,就偷了一个小孩杀了当羊肉煮给麻叔谋吃,麻叔谋并不知情,却觉得这个财主献的羊肉,味道鲜美无比,此后就专门要吃这种羊肉,老百姓只好把孩子藏起来,当地找不到孩子,他手下就到别的地方去偷,结果闹得远近皆知,人心惶惶,后来大人就拿麻胡子来吓唬爱哭闹的小孩,说你要再哭闹,小心麻胡子来了,把你抓去吃了。
见春树和在旁边听着的元贞都有点紧张,元贞的爹就笑了笑说,莫怕,莫怕,这都是前朝后代的事,离我们都很远,我们这地方的人忌讳说猫,因为猫是吃鱼的,下湖打鱼的人见到猫是不吉利的,有人对下湖打鱼的人说猫,那是他在咒你,说山洞里有猫胡子,既吓了小孩,也挡了大人,所以东西坝的人平时都不敢单独进洞,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进洞去玩,也不怕猫胡子把你们抓着吃了。
元贞的爹正这么数落着,春树突然冒出一句话说,我见到猫胡子了。
元贞的爹一听,就吼了春树一嘴说,莫瞎说,这伢烧糊涂了,尽说胡话。
七、东西坝的孩子都想去山洞捉迷藏
元贞和春树进山洞的事,东西坝的孩子很快都知道了。下湖的时候,打完了仗,两边的牛都野放了,就围坐在湖滩上,要元贞和春树讲讲是么回事。
元贞起先死活都不肯講,因为他想起来还有点后怕,东西坝的孩子就说他是裤裆包的,见不得人也见不得鬼,又用激将法激他,说山洞里哪有么事鬼,自己是个胆小鬼,还要说被鬼追着跑。
元贞经不住东西坝的孩子冷嘲热讽,软磨硬泡,终于说出了那天他和春树见鬼的经过,说完了,又要春树作证,春树却淡淡地说,我没见到鬼,只晓得被鬼追着跑。
东西坝的孩子原来都想听元贞说说,鬼到底是个么样子,见他说了半天,不过是山洞么样大,洞里么样暗,石头么样多,么样怪,洞里的坑么样深,坑里的鬼火么样闪,阴风么样响,么样冷,他和春树么样被鬼追着跑,说来说去,还是不晓得鬼是个么样子,东西坝的孩子都很失望,都说他在瞎吹牛,瞎骗人。
元贞还想分辩,坐在一旁的川儿却说,这还不简单,进洞去看看不就晓得了,鬼住在山洞里,又不会跑,元贞碰得到,我们也碰得到。
说到进洞,东西坝的孩子都有些害怕,刚才还叽叽喳喳地在发议论,这时候突然都不作声了。
川儿又说,鬼怕人多,两个人,鬼敢追,人多了,鬼就不敢追了,我妈说鬼就是个影子,转不了身也弯不了腰,我们躲起来,他就抓不到我们了,我们就在洞里跟鬼捉迷藏。
说到捉迷藏,东西坝的孩子顿时又来了兴致,以前,他们也玩过捉迷藏,多半是在湖荡里,夏天,荷叶芦苇长起来了,一望无涯,铺天盖地,他们就钻进这绿叶丛中,躲的躲,藏的藏,寻的寻,找的找,有时直到天黑了,才出来拴上自己的牛骑着回家。
在湖荡里捉迷藏有个好处,就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吃的,水面是莲蓬菱角,水下是芦根藕带,无论是藏的还是找的,嘴都不会闲着,坏处就是藏的人容易被发现,动作稍大一点,就会带动荷叶芦苇,找的人抬头一望便知。
想到要到山洞里去捉迷藏,鬼不鬼的先不说他,就是元贞说的山洞里的那些怪石深坑,迷宫暗河,也让东西坝的孩子感到好奇,激动不已,当下就议定了一个日子,到时候邀上想去的孩子,摇上两条小船,先后出发,进洞后,老规矩,西坝的孩子藏,东坝的孩子找。
一直在一旁听着不出声的国梁,这时候却站起来,伸出两手比比画画,口里还嗷嗷叫着配合两手的动作,听了半天,大家都明白了,原来他要大家都带上干粮,洞里不是湖荡,什么吃的都没有,玩得时间长了要挨饿,又要大家带上棍子和绳子,见到鬼就用棍子打,捉到鬼就用绳子捆。
带点吃的进洞,大家都觉得国梁说得有理,想得周到,至于用棍子打鬼,用绳子捆鬼,东西坝的孩子都没有这个胆量,不过,国梁的话还是让他们觉得胆壮,敢不敢打鬼捆鬼是一回事,洞里七弯八绕,爬坡上坎的,带上棍子绳子,到时候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
商议停当之后,东西坝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一直坐在圈子外面的玉霞,元贞说鬼,儿伢们嚷嚷的时候,玉霞一直没有作声,但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一刻也没有闲着,一时紧张,一时惊恐,一时兴奋,一时期待,脸上的表情也在随着变化,儿伢们嚷得越起劲,玉霞脸上的表情变化得越快,就像湖面上跑过一场阵头雨,大大小小的雨点激起一片密密麻麻的水花。
玉霞虽然是个女伢,但东西坝的孩子平日里的活动却少不了她,骑牛比赛的时候,她是挥舞布帘子的司令官,轮到打仗的时候,她又成了宣布胜负的裁判员,捉迷藏的时候,两边都迷失了方向,只要穿着红大布褂子的玉霞从绿叶丛中站起身来,东西坝的孩子就找到了自己的方位,这时候的玉霞,就是万绿丛中的一朵鲜艳的荷花,乡下的孩子不知道女神这个说法,玉霞就是他们心中的女神,所以平日里,无论有事无事都护着她,帮着她,玉霞的姆妈去世后,玉霞更成了东西坝的孩子眼里的观音菩萨。
见东西坝的孩子都拿眼睛看着她,玉霞就朝他们轻轻地一点头,这些孩子就像挨了一炮铳,顿时从地上跳起来,发出一阵杂乱的欢呼。
八、山洞里的迷藏(一)
听说要到山洞里捉迷藏,西坝有个孩子就自告奋勇地要求当向导打头阵,说他爹进过山洞,知道一个容易藏人的地方,这地方进不好进,出不好出,从外边看不到进口,也找不到出口,躲在里面,别说是人,老鼠也难找得到,他晓得这地方在哪儿,愿意在前面带路。
这孩子的大名叫祖光,另有一个外号叫二糊(读瓠),叫祖光没人知道,叫二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盖因他做的浑事实在太多,比如把人家的窗户纸捅个洞,上人家的屋顶揭片瓦,在人家的牛屁眼里塞一个草把子,等等,称得上是无恶不作,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胆子大,遇到难事敢出头,所以村里的大人虽然烦死了他,在孩子堆里,关键时刻却少不了他。
当下,西坝的孩子就驾起一条小船,招呼东坝的孩子随后出发。按约定,是西坝的孩子先进洞,半个时辰以后,等西坝的孩子藏好了,东坝的孩子再进洞去找。
那几日,天气闷热,听说后山已下了几场暴雨,有几股大大小小的山洪,已顺着后河呼啸而下,却没有带来丝毫凉意,只是湖水见涨,西坝的小船到达山脚下的时候,湖水已把山下的沙滩淹了一大半。
二糊说的好藏人的地方,在山洞的一条岔道边上,临出发前,他爹告诉了他一个大致的方位,说他在那儿留了一个记号,这记号就是在一个人形的石头上,用一根绳子套住了人形石的脖子,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上面的一块石头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人正在上吊,他爹称他留的这个记号叫吊颈鬼,说你找到了吊颈鬼,就找到了要找的地方。
吊颈鬼并不难找,进洞后没走多久,绕几个弯子,就上了那条岔道,在岔道边上,果然看见一个人,头悬石脚踏地地吊在那里,听春树说山洞里的光线很暗,这次西坝的孩子就没有让他去扎火把,而是有备而来,临出发前,带了几盏马灯,马灯的光亮照在吊颈鬼身上,忽闪忽闪的,照出了许多疤疤癞癞的暗影,像一条剥了皮的癞皮狗。
西坝的孩子都有些害怕,二糊说,莫怕,莫怕,吊颈鬼是假的,又用手指着旁边的一条水沟说,你们看,水沟那边是不是有张嘴,看得见上嘴唇,看不到下嘴唇,上嘴唇露在水面上,下嘴唇藏在水下面,像含着一口水,不吞也不吐。
西坝的孩子一看,二糊说的确实是像,就有個孩子说,像又么样,嘴里又不能躲人,春树插进来说,我晓得了,从嘴里钻进去,里面一定是个大洞,躲进洞里就找不到了,二糊于是就招呼大家进洞。
洞前的水沟不宽,水流虽然很急,水却不很深,儿伢们都脱得精光,把衣服和吃食顶在头上蹚水过沟,玉霞不能脱衣服,春树也不好意思脱衣服,就一手顶着吃食,一手拉着玉霞的手,跟着过沟。
沟那边的水下,果然有一个高台,踏上高台,低头从露在水面的上嘴唇下进去,爬一个坡,就是一片空场,空场很大,上面石柱林立,撑着一个比空场更大的石顶,像草台班子搭的戏台下面立着的密密麻麻的木桩子。
进了这片空场,西坝的孩子就像孙大圣带着他的那群猴子猴孙进了水帘洞一样,眨眼工夫,就四散开来,跑得不见人影,难怪二糊的爹说这地方好藏人,别说不容易进来,就是进来了,要找到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
说是空场,其实一点儿也不空,除了中间的石柱子,周围还有许多深深浅浅的水凼子,大大小小的石屋子,曲里拐弯的石弄子,西坝的孩子各取所好,各占一处,有的找个深水凼子玩水,有的躲在石屋子里吃东西,有的在石弄子里你追我赶,你藏我捉,在大迷藏里玩起了小迷藏。
春树和玉霞喜欢安静,在刚进来的大嘴旁边看见一处高台,就捡了几个石子,爬上高台,面对面地坐着抓石子。
只有二糊特别,不玩水,不吃东西,也不跟别的孩子打闹,却像一个跑到人家屋里的小贼一样,瞪着一双贼眼睛,四处瞎逛,连一些犄角旮旯都不放过,时不时还要用手里的木棍这儿戳戳,那儿敲敲,西坝的孩子都知道他这个怪种脾气,也不去理会,依旧各玩各的,任由他像游魂一样在山洞里晃荡。
九、大水冲来的财喜
二糊在山洞里晃荡,是找一样东西,这东西是一口棺材,棺材里面有一些金银珠宝,找到了他爹就能发一笔大财。
听说村里的孩子要去山洞里捉迷藏,一天晚上,二糊的爹把二糊叫到房里,关上房门,跟他说了这笔大水冲来的财喜。
说是解放前那几年,到处都很乱,后山有一股土匪占山为王,为首的名叫杨林,号称靠山王,这靠山王出身贫苦,年轻时在土匪捅破天手下當过小喽啰,后来又当了一个小头目,再后来捅破天死了,就拉起队伍,自立山头,占山为王,趁着那几年乱,打家劫舍,拦路抢掠,积聚了不少钱财。
解放了,大军进山剿匪,攻下了杨林的山寨,却让杨林一干人逃脱了,也不见了他抢来的那些财宝,几次三番派人进山明察暗访,也没个结果。
忽然有一天,有个乡民来报,说他的一个表哥,前些时被山上的残匪劫走了,劫匪还带走了他表哥的一个独生儿子,说要他表哥去帮忙做一件事,事成了就放他父子回家,不成,就杀了他的独子。
他表哥是个老实人,被逼无奈,只得答应下来,谁知这事答应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上天还难,他表哥下山行事之前,特意到他家来告知原委,说万一他父子被害,年老的爹娘还要托他照顾。
这人问他表哥,这些土匪现在何处,他表哥却连连摆手说,莫问,莫问,他们行踪不定,我也是被他们蒙着眼睛拉上山又送下山的,我儿子还在他们手里,万一走漏了风声,他的小命就没了。
接待的干部就问,土匪绑你表哥去,到底要他帮忙做么事。
那人说,说来话长,就把他表哥说的和从乡民那里听来的故事,拢了拢,说给接待干部听了。
原来解放以后,这杨林自知好景不长,剿匪大军攻破山寨是早晚的事,自己身首异处,也在所难免,既然干上了这一行,走了这条黑道,也就把脑袋吊在裤腰带子上了,掉不掉,么时候掉都由不得自己,只是可惜了那些钱财,好不容易东家抢西家夺地聚到一起,让政府拿走了实在于心不甘,虽说自己未必有命受用,留给弟兄们,也算没白在自己手下厮混一场,后人说起来,也不枉我做了这场山大王,于是就在山里找了一个木匠,让他用上好的楠木做了一口棺材,把这些金银珠宝都放进棺材里面,外面又用烂木做旧,看上去像埋在地下有些年头。事情完了以后,又把这木匠杀了灭口。
这事本来就这样完了,谁知天不遂人愿,偏偏就不想成就杨林的梦想,棺材刚装好不久,还没来得及择地掩埋,有一日天降暴雨,下了一天之后,半夜里便惹发了山洪,突发的山洪把杨林藏身的山洞冲得个七零八落,杨林一干人等也被洪水卷走,不知去向。
洪水过后,剩下的头领想寻找杨林的尸首,无奈山林上下,沟底崖畔找了个遍,却不见踪影,有人就说,兴许顺着后河漂到下面的湖里去了,山洪过后到下面的湖里找东西,是常有的事,只是山下风声正紧,也不敢派人下山,这事就这样搁下来了。
找不到杨林的尸首,就想着那口棺材,这事本来就只有杨林信得过的几个头领知道,当下有个知情的头领便说,为今之计,只有找个水性好的人,顺着后河找下去,兴许能找到那口棺材,后河要是没有,就一定是漂到湖里去了,就是钻到湖底,把湖底的烂泥翻个个儿,也要把它找到。
大山里头,找个会爬山的容易,找个水性好的,却是难上加难,偏偏这头领的运气好,说找还就找到了,这人就是这个来报告的乡民被土匪绑去的表哥。
说来也巧,他表哥这天正在一口深潭下祭龙,祭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后山虽然常发山洪,但没有山洪的日子,却常闹旱灾,旱灾来了,就靠发山洪时积聚的潭水浇地活人,所以对管水的龙王就格外巴结,每年都要在选定的日子下潭祭龙,这祭龙的法子,就是派一个水性好的后生,带上献祭的三牲,用渔网兜着,潜入潭底,把祭品送到潭底的龙宫供龙王享用,当地人称干这事的人叫祭龙师,这人的表哥家世代都干这献祭的营生,练就了一身在水底下憋气换气的本领,在龙宫里一待就是半个时辰,直到上面的人磕头打拜完了,龙王收下了祭品才浮出水面。
这人的表哥这天刚浮出水面,就被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头领看了个正着,第二天便被绑上山了。
这事都是后来下山的土匪跟这人讲的,这股遭遇山洪的残匪被解放大军围困久了,断了粮草,又不敢下山,便零零碎碎地潜逃回家,这人村里有在这股土匪队伍里混过的人,便把这些事当故事讲给村里人听,这人听后,很为表哥的性命担忧,就跑来报告政府。
地方政府把这事转告部队以后,剿匪部队也派人顺着这人提供的线索,提审了在押的头领,又派人沿着后河河道找下去,还组织沿湖的渔民在湖中打捞,都没有结果,这人的表哥因而生死未卜,那一棺材的金银珠宝也下落不明。
剿匪部队搞了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会惊动当地的老百姓,沿湖的乡民便都去湖中寻宝,结果真像那个头领说的,把湖里的烂泥都翻了个个儿,也没有找到宝贝,有人就指着湖中间的那座小山说,没说的,就只能在山洞里了,山洞是个回水湾,后河漂下来的东西,八成都搁在山洞里,于是众人又一窝蜂地扑向山洞。
二糊的爹就这样也跟着进了山洞,众人很快便把山洞的犄角旮旯找了个遍,仍然不见棺材的踪影。
山洞中间有一条沟,水流很急,二糊的爹见众人都在干地上寻找,就想着棺材里的财宝多,分量重,兴许在这个回水湾里转着转着,就沉到了沟底,于是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就跳进沟里摸索,想吃个独食。
二糊的爹下去只走了几步,就觉得头顶上有一股阴风掠过,侧身一看,见是一片断崖,样子像一个人张开大嘴,一半在崖面上,像半边嘴唇,用脚一探,水底下还有一半,那股阴风就是从这个大嘴里吐出来的,就琢磨着,里面一定是个空洞,空洞的那头应该还有个口,不然不会兴出这股阴风,于是就踮起脚尖,把头伸进嘴里去看了一看。
这一看不打紧,二糊的爹从此便认定这口棺材是藏在这个大嘴之内,因为他在这个大嘴的另一边,果然看见了一个进口,像一座石门,对,那口棺材一定是从那儿漂进来,藏在这个大嘴里的什么地方,既然外面的洞里面找了个遍,都不见棺材的踪影,难不成它还能飞上天去,一定就在这没人知道的洞中洞里藏着。
二糊的爹本来想爬进嘴里去找一找,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在大声喊叫,走了,走了,再不走,就要碰到鬼了,二糊的爹就想到在洞里看到的许多牲口和死人的尸骨,虽然带着马灯,暗处还是看得到麻麻匝匝的鬼火,也不敢久留,就从嘴里缩回头来,跟着众人走出山洞。
大嘴里的棺材从此就成了二糊他爹的一块心病。
十、山洞里的迷藏(二)
半个时辰以后,国梁带着东坝的孩子,划着一条小船,也到了山下。
湖水一直在涨,山洞前的沙滩,只剩下一片月牙,国梁的小船停靠的地方,已经到了洞口边上。
元贞进过洞,知道洞里的情况,就在洞口对同来的孩子做了分工,又说,洞里坡坡坎坎、坑坑洼洼很多,到处都是曲里拐弯的岔道,要大家脚底下都留点儿心。
知道同来的孩子跟他一样,怕鬼,就特别嘱咐说,莫怕,莫怕,鬼怕灯火,碰到鬼不要惊慌,把你手上的马灯举起来一照,他就吓跑了。
就有孩子说,你上次不是也有火把吗,怎么鬼还是追着你跑。
元贞就笑,说,那是我胆小,其实鬼早就吓跑了,是我自己吓自己,阴风追着我跑。
国梁见他们还在说话,就拉过元贞,指指洞口,又指指湖水,口里哇哇哇哇地叫着,显得很急的样子。
元贞知道国梁是担心湖水涨得太快,不赶快把西坝的孩子找到,湖水要是封了洞,到时候藏的人和找的人都出不来了。
元贞想想也是,就一挥手让大家进洞,赶快分头去找,不管找得到,找不到,湖水进洞了,听见喊叫,东西坝的孩子都要出来,这次捉迷藏的游戏就算打个平手。
平日里在湖荡里捉迷藏,东坝的孩子也是找人的一方,时间长了,就想出了一个在湖荡里找人的法子,这法子很简单,就是把自家的泥铳带出来,架在船头上,朝四面八方放上几铳,就能见到动静。
泥铳是打排铳时惊飞野鸭大雁的,排铳不能平射,平射打不中目标,停在水上的野鸭大雁,先得想法子让它起飞,在起飞的那一瞬间放铳,才能打落一片,离野鸭大雁群近的时候,丢块泥巴石头,离远了,就要用泥铳发送泥丸,泥丸虽然不能伤人,打在身上还是有点痛的,藏在荷叶芦苇丛中的孩子怕泥丸落到自己身上,听到铳响,就免不了会有点动静,东坝的孩子眼尖,摸上去就抓个十拿九稳。
这个法子在山洞里用不上,东坝的孩子就只有硬找,找了半天,都回说没有找到,元贞便重新分配人手,从不同的路线继续寻找,这一次不但没找到西坝的孩子,还丢了一个自己人,集合的时候,发现川儿不见了,元贞和东坝的孩子都很著急。
正在着急的时候,川儿却又自己跑回来了,元贞见他浑身水淋淋的,就问他跑到哪里去了,川儿这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找到了,找到了,都在水沟那边。
听说找到了,元贞就问是么回事。
川儿说,他刚才找人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一个水沟里面,水沟的水很急,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大水冲着拐了几个弯,七拐八拐,就拐到一个石门面前,水流刷的一下,把他摔到了门边的一个石柱上面,他顺手抱住石柱,才从沟里爬了上来。
等他抱住石柱再往门里一看,原来里面是个空场,空场周围是一圈石壁,空场上白汪汪的都是水,水面翻着白花,像煮开的一锅米汤,周围的石壁上有一些人,有的抱着石柱,有的趴着石坎,有的蹲在高台上,像庙里的罗汉。
川儿觉得他们好像在喊叫,水声太大,回音太强,又听不清他们在喊些么事。
原来西坝的孩子都躲在这里,洞里比洞外的地势低,一定是湖水进洞了,他们躲在这个洞中洞里不知道,等到水头涌进来了,水涨高了,又不敢迎着水头往外冲,就只好爬到石壁上逃生,他们嘴里一定是在喊救命。
听了川儿的话,元贞的第一反应便是救人。
国梁的耳朵不聋,见元贞在分派人手,就指指画画地要大家用随身带来的绳子拴上木棍,意思是救人的时候,让对方抓住木棍,再拽住绳头把人拖过来。
又带着东坝的孩子去洞里找了一些被洪水冲进来的破烂家具房梁屋椽门板树桩,拖的拖,抬的抬,扛的扛,跟着川儿来到了他先前落水的沟边。
沟里的水流果然很急,川儿把东坝的孩子带到他上岸的那个石门旁边,大水已封住了小半截石门,再往里面一看,就见有人正从石壁上面往水里跳着。
都在湖边长大,西坝的孩子水性也好,放在平时,这样跳下来,倒无大碍,站在水闸顶上比赛往下跳,是东西坝的孩子常玩的一个游戏,眼下不同,石壁下不是一汪平静的湖水,而是翻着浊浪打着旋儿的洪涛,这一跳下去,不知深浅,没着没落的,说不定就被漩涡浪头卷到什么犄角旮旯里去,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见此情形,元贞和国梁就指挥东坝的孩子,推着抱着划着搜集来的废旧木器,从石门口顺水冲进水场,一边让石壁上跳下来的孩子,迅速向他们靠拢,抓住木棍,把他们拖上来,一边又招呼还没跳的孩子瞄准目标,尽量跳到靠近他们的地方,一时间,山洞里就像开水锅里下饺子,哗哗啦啦地砸得水花四溅。
东坝的孩子在救人的时候,元贞一直在搜寻春树和玉霞,玉霞会水,虽然是个女孩,他倒不太担心,春树却是个旱鸭子,别说跳水,就是不小心掉到水里,也必死无疑。
正在这时,国梁突然指着对面的一个高台,一边比画着,一边哇哇哇哇地要元贞快看。
顺着国梁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在一处高台上面,看到了春树和玉霞。
当下,元贞就对着高台大喊,叫他们在上面不要乱动,等他过来接他们下来。
元贞和国梁这时正把一个破衣柜当船划着,两人用手中的木棍边划边撑,还时不时要下水去推一推,拉一拉,转一转方向,好不容易到了高台边上,元贞就叫玉霞先跳到水里,再扒住衣柜拉她上来,然后把绑好绳子的木棍丢给春树,让他在上面找个石坎固定,自己再顺着绳子慢慢溜到衣柜上。
春树起先还有些害怕,想想也无别的办法,就横下一条心,闭着眼睛,顺着固定好了的绳子手脚并用地往下溜。
高台下的水很急,从石门进来的水流,像撒开的一部旋网,沿着石壁转圈儿,冲得衣柜七颠八倒,想靠近石壁,却怎么也靠不稳。
国梁怕春树双脚踏空,就伸出双手,想把春树的下半身接住,正在这时,衣柜突然忽地一下翻了个个儿,把春树和国梁都掀了下去,元贞和刚爬上衣柜的玉霞也被掀到水里,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二糊正扒着翻过来的柜沿,吓得脸色煞白。
十一、玉霞说,快救春树,他不会划水
衣柜翻过来的时候,川儿正抱着一块门板在附近救人,看见春树和国梁他们落水,赶紧游了过来,抛出手中的木棍,想把他们从石壁旁边拉到空场中间来,空场中间水流不急,站住了,就可以救他们上来。
春树落水的时候,国梁正抱着他的下半身,卡在石坎中的木棍承不住两个人的重量,叭的一声断成两半,春树和国梁也就像汤锅里下油面,哧的一声都掉下来了。
国梁落水之后,就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像被人抓住了,死命地往下拽,像要从脚底下把他拽出去。
国梁落水的地方,正在西坝的孩子从水沟进洞来的那张大嘴边上,平日里,沟里的水常从大嘴灌进洞里,洞里的水涨起来了,又通过大嘴往水沟里倒灌,拽他出去的,就是这股往水沟里倒灌的水流。
国梁见过后河的涵洞吸人,知道像这样被水吸着,脚底下不稳,就会被水吸走,这一瞬间,他想起了他爹教他的骑马桩。
国梁的爹是个教师爷,国梁跟他爹练过几天功夫,知道怎么站骑马桩,骑马桩稳当,桩子稳了,水流就难得拽动他的下半身。
就在国梁挫下身子,勾住脚趾,弓着膝盖,站成骑马桩想稳住下半身的时候,他的上半身突然被人猛拽了一下,等他抬头一看,才发现春树在那头抓着折断了的木棍,正被水流冲到大嘴正中,像一根鱼刺卡在上下嘴唇中间,被水流冲得呼呼啦啦地乱摆,他手里的木棍还连着国梁手中的绳头,那头一摆,这头也跟着摆了起来。
春树和国梁对摆的时候,川儿正在石壁旁边转着圈儿追赶玉霞,玉霞从高台上跳到水里,刚爬上衣柜,不想衣柜却突然翻了过来,当下就被卷进石壁边的漩涡里面,沿着石壁的边沿兜圈圈,川儿见状,赶紧推着门板去救玉霞,玉霞这时候也看到春树被卡在大嘴中间,就从漩涡中冒出头来,冲着川儿大喊,别管我,快去救春树,他不会划水。
玉霞正喊着的时候,春树被水流冲得站立不稳,下半身已被大嘴吞了进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国梁突然大吼一声,就着骑马桩的架势,上身往后一倒,想把春树从大嘴里拽将回来,哪知用力过猛,自己的脚下虚了势,竟被春树拽着,呼啦一下都从大嘴里被吐了出去。
川兒听见玉霞的喊声,正想转身去救春树,却见春树和国梁都被水流冲走了,就丢下门板,手脚并用地扑过去。
快到大嘴边上,他面前却呼地一下出现了一堵人墙,原来是二糊带着西坝的孩子赶了过来,扎成人墙,堵住了大嘴的出口,川儿撞到人墙上面,又被弹了回来。
这时候,被水流冲开的元贞也招呼东坝的一帮孩子,把扎好的一个木排推了过来,东坝的孩子进洞救人的时候,元贞就想把他们找到的废旧木料连在一起,扎成一个木排,一来方便救人,万一湖水一时间退不下去,还可以暂时在上面歇息一阵,就叫东坝的孩子一边救人,一边互相靠拢,等靠到一起了,又用手中的绳索木棍,捆的捆,绑的绑,扎成了晒筐大的一个木排,元贞听猪娘嘴说过赤壁大战的故事,知道曹操听了一个叫庞统的人的主意,把战船连成一片,虽然后来被周瑜和诸葛亮烧了个精光,但庞统的这个主意此刻拿来救人,还是个好主意。
等东西坝的孩子纷纷爬上木排,就在一起商量出去的办法,有的主张推着木排从石门冲出去,有的又说,水流太急,石门太窄,只怕是冲不上去,冲上去也出去不了,万一把木排撞散了,都掉到水里,又会冲得七零八落。
元贞这时候急的不是怎么出去,而是回去了怎么跟爹娘和舅舅舅娘交代,舅舅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把春树当成心肝宝贝,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到口里怕化了,这下好,被他带出来玩丢了,生死未知,下落不明,他爹不要他偿命,也要把他打个半死。
玉霞爬上木排,一直在哭,两个大活人,一眨眼就不见了,她从没见过这样怕人的事,吓也把她的眼泪吓出来了。
又想到自己的弟弟就这样没了,她的眼泪更不打一处来,自己的这个弟弟虽然不是一个姆妈生的,却比一个姆妈生的对自己还要好,平时有点什么好吃的,总要背着他姆妈偷偷地给自己留一点,他姆妈要自己干的脏活重活,他都要找个借口抢过去,她挨打挨骂的时候,他总是护着她,站在她一边帮她说话,有时候他姆妈不给饭她吃,他就把自己的饭端给她,自己宁可饿着肚子不吃,爹和他姆妈都宠着他,把他也没有办法。
玉霞一边哭,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哭越起劲,最后干脆扯开嗓子放声大哭,这一哭,东西坝的孩子都乱了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东西坝有些孩子本来就是要哭不得嘴巴扁,玉霞的哭声就像点着了的炮引子,顿时引得哇哇一片。
只有川儿稍微冷静一点,他一边安慰玉霞和身边的孩子,一边观察水流的变化,他发现石壁边的漩涡突然不见了,先前像开闸放水的石门,现在水流也平缓了许多,再跳下木排用脚一探,竟踩到了地面,就招呼东西坝的孩子从木排上下来,手拉着手,蹚着膝盖深的水经过石门,攀着门边的石柱,爬上了沟那边的高地。
外面一片漆黑,借着剩下的几盏马灯微弱的光亮,勉强还能看得清出洞的路,东西坝的孩子就在元贞和川儿的带领下,走出山洞,摇起各自的小船回村去了。
十二、会动的棺材
第二天,东西坝的大人都提着马灯举着火把到山洞里找人。
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山洪一停,湖水就退下去了,人说山底下是空的,果然不假,水退了以后,洞里的地面都露出来了,只有沟里的水,还在哗哗地流淌。
村里人在干地上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春树和国梁,都集中到水沟边上,就有人说,一定是被沟里的水带走了。
沟那头石门里的空场,已经找过了,元贞还带着村里人到国梁和春树落水的地方,细说了事情的经过。
元贞没说二糊弄翻了衣柜的事,只说是不小心掉下去的,他知道二糊不是故意的,二糊后来告诉他,他从石壁上跳下来以后,被水流冲得晕头转向,突然发现面前有个衣柜,就扒住衣柜边沿想爬上去,谁知一使劲却弄翻了衣柜。
二糊回家跟他爹说了实情,他爹就觉得儿子欠了人家两条人命,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把春树和国梁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豁出自己这条命去,也在所不惜,虽然口里不说,找人的时候,却比谁都上心,也比谁都仔细。
在找人的队伍中,只有他知道这条沟的秘密,被大嘴吐出去的春树和国梁既然不像川儿那样,转了半圈又冲到石门边上,那就只能是冲进了一条岔道,他知道这条沟往石门方向,有好几个岔道,他那次从沟里上来,就是走的其中的一个岔道,虽然当着众人的面,他不好意思说那次想吃独食的事,却是乌龟吃亮火虫,心里有数。
当下,二糊的爹就自告奋勇地跳进水沟,说要到一个岔道前面去找,东西坝的人从来没见二糊的爹对别人家的事这么上心,都十分感动,又叮嘱他小心,让他找不到赶快回来,别把自己也搞丢了。
正在众人七嘴八舌地朝二糊的爹嚷嚷的时候,二糊的爹却看见岔道的那头有一条船,正朝他这个方向逆水而来,他怀疑自己的眼睛看花了,这山洞里哪会有船呢,就算有船,船上没人撑篙划桨,也只能顺水漂流,走不了逆水,等他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船,而是一口棺材。
见到棺材,二糊的爹禁不住心中怦怦乱跳,就顺着水流朝棺材迎过去,走到近前一看,发现棺材盖是翻过来扣在棺材上的,棺材盖上躺着两个人,正是春树和国梁。
春树和国梁静静地躺在棺材盖上,身上盖着一张渔网,像睡着了一样。
二糊的爹正想招呼众人过来,没等他喊出声来,东西坝的人也看到了,便围了过来,像看天降异物一样,指着漂来的棺材不停地打啧啧,那年,湖上起龍卷风,把别个地方的水车刮到自己村里,众人都觉得没这事稀奇。
二糊的爹见众人只顾了看稀奇,却忘了棺材上躺着的人,就招呼几个年轻的后生下来抬人,二糊的爹正想找根绳子把棺材固定,却发现棺材在众人围拢来的时候,已经停下了,好像约好了的,在等着他们抬人一样。
等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春树和国梁抬上干地,二糊的爹就想看看棺材盖底下,到底有些么事宝贝,等他用力掀开棺材盖子一看,却发现里面是个空洞,连棺材底也不知哪里去了,二糊的爹正觉得丧气,面前的棺材却呼地一下顺水冲了出去,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踪影。
春树和国梁都捡回了一条命,国梁醒过来后,便对众人指指画画,意思是说,他落水后,就撞到了一块石头上,撞昏了,就么事也不晓得了,反正晓不晓得,他都说不清楚,众人便转向春树,问他是不是看到了么事。
春树便说,其实,我也跟国梁一样被石头撞昏了,后来好像有人给我喂水喝,又给我口里塞了点东西,我嚼了嚼,吞下去,也试不到味道,再后来就睡着了,么事也不晓得了。
众人便觉得奇怪,春树和国梁肯定是被什么救了,但这救人的,到底是人是鬼,却说不好,说是鬼吧,鬼是漏下巴,不吃东西,也不喝水,自己不吃喝,哪来东西喂人呢,说是人吧,那这人也好生了得,救了人,又把人放在棺材上面,逆水送了回来,送回来后,又不露面,从水底下回去了,这一来一去的,都在水下行走,少说也有半个时辰,难不成这世上真有虾兵蟹将海底龙王。
就有人想起去年寻宝的事,说那次听部队上的人说,后山有个土匪头子叫靠山王杨林,杨林当土匪攒下了一棺材财宝,却无福受用,连人带棺材都被山水冲走了,他的手下咬定棺材沿后河冲了下来,就派一个水性极好的人下来寻找,说找不到就别回去,还把他的一个独生儿子押在手上,空手回去也要把他儿子杀了。
这故事大家都听过了,讲的人无非是说,救人的人,就是土匪派下来寻宝的那个人,听说这人是个祭龙师,只有他,才有这么好的水性。
又有人说,这都解放一两年了,后山的土匪也剿干净了,听说这人的儿子也被解放军救出来了,找不到财宝,也没有土匪杀他,他也早该回去了。
二糊的爹突然说,回去个屁,他躲在山洞里,解放不解放,有没有土匪,也没人告诉他,他么样晓得能不能回去呢,他敢回去吗,要像土匪先前说的,他要是空手回去了,他跟他的宝贝儿子,都注定性命难保。
又自言自语地说,我就纳闷了,棺材里空空的,么事都冇得,那一棺材财宝都到哪里去了呢?
元贞的爹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事,就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想歪心思了,我晓得财宝到哪里去了,一定是打棺材的木匠知道土匪没安好心,打棺材的时候做了手脚,安了个机关,寻常时节,棺材盖是打不开的,除非把棺材砸了,才拿得到棺材里的东西,我听说过这种机关,后山的人都叫它鬼门关。
乡下人都晓得木匠下镇的事,但凡请到家里来做工的木匠师傅,若是菜饭没招呼好,或茶水有些怠慢,往往会在箱笼桌柜或房梁屋架上放个镇物,装个机关,轻则招灾惹病,重则房歪屋倒。
二糊的爹便说,照你这样说,难不成那人把棺材砸开了,取走了财宝。
元贞的爹说,那倒不是,钱财再贵,也贵不过他父子俩的性命,他若是拿了财宝,也会交给土匪,不敢自己独吞,一定是棺材从后河冲下来的时候,一路上磕磕碰碰,撞到石头上,砸开了机关,财宝都从棺材底下漏出去了。
二糊的爹说,要是这样,那就太可惜了。
元贞的爹读过几天私塾,就随口转了句文辞说,不义之财,得之何益。
十三、春树说,其实我见过那个人
这事过去之后,东西坝的人都为洞里的这个人操着心,就有上山捡柴的人,看见有人到庙里偷吃菩萨面前的供品,想跟上去看个究竟,一会儿又不见了人影,有一次,有人一直跟到了山洞里面,说是亲眼看见他跳进一个又大又深的水坑里,半天没有出来。
再后来,就没有这个人的音讯了,有的说是死在洞里了,有的说是他老家有人找来了,把他接回去了,东西坝的人也就渐渐地忘了这件事。
再再后来,玉霞做了川儿的媳妇,元贞和春树都成了川儿家的亲戚,元贞是玉霞的老表,春树是川儿的小舅子。
川儿和玉霞结婚那天,春树又跟着他爹到东坝来喝喜酒,晚上睡在元贞家的竹床上,又说起那次捉迷藏的事,春树说,其实救我的人我见过。
元贞问他么时候见过。
春树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进洞吧,那天我跑失了方向,火把也搞丢了,在洞里兜来兜去,就是找不到洞口在哪边,正急得没法,突然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莫怕,跟我走。
洞里黑,看不清说话人的脸,只模模糊糊地见他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披着渔网,像个打鱼的,我不敢多说话,就跟他走,快到洞口,见到亮光了,那人一眨眼就不见了,我就昏昏沉沉地出来了,总听人说,鬼吓人,不现形,人吓人,吓掉魂,我那天就是被这人吓掉魂的。
元贞说,你当时怎么不说呢?
春树说,我当时哪晓得他是人是鬼呢,直到这次他救了我和国梁以后,又喂水,又喂东西吃,还把渔网盖在我和国梁身上,我才想起来,他一定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