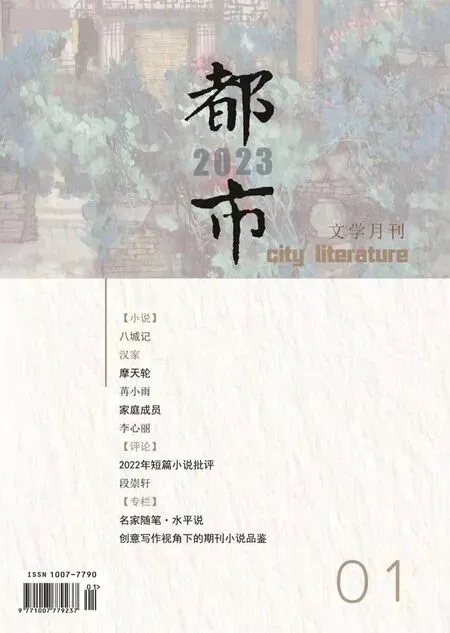物象的使用
——读子禾《野蜂飞舞》
○李苇子
李苇子,2007 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当代》《花城》《大家》《青年文学》《鸭绿江》《西湖》《山西文学》《黄河》《湖南文学》等纯文学刊物。有作品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海外文摘》《视野》《教师博览》等杂志转载。著有小说集《归址》。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子禾的短篇小说《野蜂飞舞》(《西湖》2022 年第11 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表哥因偷窥姑姑在发廊里的非正常勾当,受到剧烈刺激,后又因父亲的一次咆哮,疯掉了。他的这一失心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也让亲戚们跟着一块受罪,表哥一次次失踪,又一次次被大家找回来,众人不堪其扰,大家甚至暗暗希望表哥死掉或彻底消失。后来,表哥去后山采摘杏花跌落悬崖死掉了。姑姑则由于愧疚,每天都往庙里跑,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
关于小说题目,尽管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命名方式,可是不管如何推陈出新终究无法摆脱故事中的人、事、物三者的影响。《包法利夫人》《简·爱》《德伯家的苔丝》等,这些19 世纪的长篇小说,都是用核心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以故事的核心事件来命名的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以一个关键道具或象征物命名的如《红与黑》《项链》《麦琪的礼物》等。
倘若按照上述三种分类,毫无疑问,《野蜂飞舞》属于第三种——核心物象。实际上,这是子禾最擅长使用的一种构建方式,与其说擅长,毋宁说是主动选择,是他个人审美经验的理想状态。子禾一直在追求那种浑然天成、妙手偶得的效果,他称之为“放松的感觉”。这可能和他“前诗人”的身份有关。他更在乎一个作品的内蕴、气息、气氛、气质,一种暧昧不明。因此,他格外重视意象的使用。只要我们将他的某些短篇小说题目罗列出来,这种充满诗意的特征便能一目了然了:《悬停之雨》《灰色怪兽》《悯默之虎》《母马》。
悬停于屋檐的雨滴,将落未落,类似于达摩克利斯之剑,隐喻了一种时刻存在的危机,婚姻的动荡和不安,以及上天严厉的警示与怜悯;灰色却混沌的怪兽,不仅仅是主人公的胃病,更是他的心病,是嫉妒,是对过往的某种耿耿于怀,更是世事留给他的隐痛;默然却怀有悲悯之色的老虎,不仅仅是一个梦中物,它或许象征了我们难以探究的人之命运的深远的来源,它混杂了凶险与怜悯,是人对自我的迷惑难解,也是人爱恨交加的境遇;孤独的灰色母马在戏院里承受寒冷与落寞,最后它在众人的观看中离开人群,独自远去,某种意义上它是女主人公的精神放逐,但仅此而已,生活中的她无法离开疯掉的丈夫,需要继续承受生活的重压。
《野蜂飞舞》中有两个有趣的物象,一个是姑姑家那条养了多年的黑狗。这黑狗一直是姑父的心头肉。表哥失心疯后,姑父整天不是躲在家具店里就是去打麻将,偶然回家也从不跟姑姑交流,眼里只有那条狗。这激发了姑姑的毁灭欲。“那天后晌下雷阵雨,死狗像疯了一样,在那儿叫叫叫,叫得人心烦。”于是姑姑就砸断了拴狗的铁链,让它滚蛋了。结果这条狗再也没有回来。狗与表哥构成了一组相互对应的关系。导致狗发狂的自然界的电闪雷鸣对应了姑父的暴怒和咆哮,狗的突然发疯对应了表哥的失心疯,狗的失踪对应了表哥的历次失踪和最终死亡。小说中一共写了四次表哥的失踪,前两次失踪的时间是夜晚,家人睡醒觉后发现表哥不见了,前一次在猪圈里找到,第二次是在阁楼上,为此他还挨了姑姑一顿毒打。第三次失踪的时间是下雨的白天,村里人在村头的破窑门口找到了他,这三次都是有惊无险,是有去有回的。第四次的失踪同样是在下雨的白天,和黑狗跑掉的那天一样,表哥挣脱姑姑的阻拦跑掉了,这最后一次,竟是有去无回的。
小说中第二个有趣的物象便是标题中的野蜂。野蜂也一共出现过四次,和表哥的四次失踪相类似的地方在于,它们的物理空间(文本段落距离)挨得很近。它们出现在小说最后的四千多字里(全文约一万七千字),我们不妨将这部分称为尾段。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了子禾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硬核的故事部分出现的时间通常较晚,一般都在尾段。前面大部分段落是一种看似漫不经心、漫无目的的铺排,这是一种情绪铺垫,通过一个个细节呈现那些遭受过生活重大变故的人物越出常规的种种表现。子禾似乎一直在追求这些细节的极尽微妙,也一直在力图抵达人物关系最微妙的末梢神经。现在继续来说野蜂,这一出现过四次的物象其实并不相同,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野蜂是无实体的虚指,姑父发现表哥乱花钱买了一个“玩具摩托”,勃然大怒,姑父的咆哮声将理发店的空气逼得颤抖起来,鼓动着耳膜,嗡嗡颤响,仿佛成群的野蜂在头顶盘旋。这次的暴怒招致了表哥的失心疯。这一无实体的虚指在多年后“我”去看望姑姑,与姑姑在深夜的促膝长谈时“在那些往事的黑暗中”再次听到。第三次出现的野蜂是一个实指,“我”和姑姑去给表哥上坟,烧完纸起身时,“我”发现坟头的一棵小柏树的枝杈间,结着孩童拳头大小的一个野蜂巢。第四次出现的野蜂是在表哥第三次失踪的时候,“窑门口挂着一个野蜂窝,有狗头那样大,天亮(表哥)就躺在那儿,一群野蜂在他头上乱飞,可一下都没蛰他……”频繁出现的野蜂到底在指喻什么?子禾坦言“就是一种强烈的挥之不去的过往。人们被笼罩在过去生活遗留的情绪中。这情绪是相似的,但事情却并不相同”。就故事层面来说,野蜂象征着突然降临的厄运,或者说,更像一种奥意深刻却恶毒的咒语,它织就了一张细密的网络,让人在劫难逃。
帕慕克将小说家分为两类:图画型作家和词语型作家。作家的洞察力、思想和智慧,要么诉诸图画想象,要么诉诸词语想象。前者的代表是托尔斯泰,后者的代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者的小说中充满各种物象以及富有暗示性的道具和场景,后者的小说中尽管同样的深刻、充满着令人眩目的紧张感,我们却很难再意识中找到与之相关的物品、意象或者场景。当我们在阅读后者的作品时,我们会更加专注于词语,专注于对话的进程以及作家正在探索的种种悖论或思想,而前者的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在他们的意识里纳入不可磨灭的意象、想象、景观和物品。
显而易见,子禾也是一位“图画型作家”。据说子禾业余时间喜欢摄影和画国画,这种对于视觉艺术的偏好自然会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