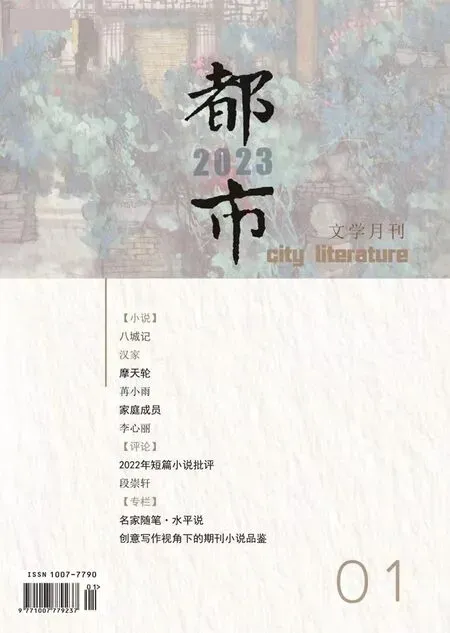月色盈怀
文 宋剑挺
高松洁的手一松,半桶泉水就倒到了盆里。这是从岩石里渗出的泉水,已是秋后,泉水并不扎手,反而变得温温的。明天丈夫就要来了,她得把身子洗洗。
她把头发散开,轻轻地摁在盆里。她感到泉水像无数只小手,在她头发上搔着。她轻吟一声,声音虽小,但陡地在房内荡开了。这是个砖房,房间太小了,拢不住这鲜活的声音,声音就哧溜跳到了窗外。外面是黄腾腾的月色,声音被月色泡了泡,又钻进了房里。高松洁没有在意,其实月色已沾到她的头上了。她把水撩到头上,月色便湿了她的头发,湿了她的脖颈,把她的脸面也沾得湿湿的。这时水拌着月色,从她的头上落下,一滴一滴的,坠到盆里,叮叮当当的显得格外脆响。
高松洁是个采油工,负责这个区域的采油工作。这里有二十一口油井,她住的房后有一口,剩下的散落在周围的山顶上。高松洁的丈夫在地方工作,没有办法,高松洁已在这里坚守了五年。厂长过意不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她丈夫调到了油田,并让她丈夫过来陪她。她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太多的兴奋,她只担心丈夫不习惯这里的生活。现在的高松洁啥苦都不怕了,酷暑天里,太阳似乎把山点燃了,她拉着沉重的工具,照样一口一口巡查油井。严冬腊月,大雪淹没膝盖,她就拿把铁锨,边清理路,边巡井。查遍二十一口油井,需一整天时间。她扛着铁锨和管钳,总是吃力地走在山道上。这里黄土多,风沙大,她感到沙粒像蛾子似的,钻到她的衣领里,钻到她的头发里。巡井回来,她必须甩甩头发,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这样一抖,头发里的沙子就会哗哗地掉下来,洗头时就省事多了。
高松洁把头发重新摁到水里,涮一涮,再猛地抽出,如此反复多次,这样才能把沙子彻底清除。她觉得洗净了,再把事先捣碎的皂茄,涂到头发上。原先有瓶洗发膏,但早已用完了,给养一月才接到一次,洗发膏用完,只有用皂茄代替了。皂茄去污力较差,但抹在头上,有种清香,是那种自然的香气,飘得满屋都是。她往头上抹了两遍,洗了两遍,撩起一绺头发闻闻,香气如一条雨丝,在她脸上轻抚一下。高松洁满意了,起码没有厚厚的油味了。
清洗抽油机时,头上沾些油污是常事,有时会弄一身一脸。清掉这些油污,又给她添了很大麻烦,起初厌烦,现在已经习惯了,她把这事当作一种工作,尽量说服自己乐意做它。为减轻劳累,她边洗边唱,不管是否走调,总唱些自己喜欢的歌。歌声从房里钻出,扑棱棱地飞到外面,飞到了山上,飞到了山泉里,泉水把歌声沾湿了,让歌声变得更加动听了。
巡井时实在走不动了,她就来到泉边,先把头洗洗,脑袋让凉水一激,会精神许多。其实闲下时,她很想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但山里没有信号,只能瞅见白糊糊的屏幕。厂长曾派人为这事整修过,但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她干脆不修了。现在啥都习惯了,她习惯了一人躲在房里,让时间风似的从脸前拂过。她觉得时间是有重量的,它从额上辗过,从颊上辗过,从手上辗过,辗过的地方就起了细细的皱纹。这些皱纹又蓦然让她忘记了时间,她不知自己何时来到了这个山里;不知地下的原油,通过自己的双手,被输出了多少;不知山上的杏花多少次开了败了,败了又开了。但她记得清楚,二十一口油井中,哪口井产量最高,哪口井产量最低,哪口井的抽油杆易毁,哪口井的电动机易毁。她脑里经常响起轰轰的声音,这是抽油机的声音。她想把它从脑里赶走,但无论怎样努力,总不见效果。
其实她是最怕安静的。夜里,黑暗水似的从外面挤来。这时所有的声音,像被冻住了。她听见自己的脑袋嗡嗡地响着,像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有种损毁的危险,于是一种莫名的恐惧便悄悄来临了。她觉得自己的身子变小了,小得像片草叶,被风呼地吹到这里,又呼地吹到那里。这时寂寞像只小鼠,从门外吱哇挤了过来。她不怕黑夜,不怕雨天雪天,最怕重重的寂寞。每到这时,她就开始唱歌了,她常用歌声把这只小鼠吆喝着赶走了。
高松洁用毛巾擦擦头发,她高高扬起头,狠狠甩了甩,发出刷刷的响声。大山深处,寂寞贼似的潜伏着,实在无处排遣时,她总是慢悠悠地洗头。洗完后,觉得舒适了,清爽了。她把头发都拢在胸前,再一点点梳理。若是月夜,她就坐在门前的土墩上,风过来了,月光过来了,它们都争着抚弄她的头发。月光把头发冲洗一遍,皂茄的香气便在月光里跳荡起来,一点点飘向山涧。这是她最惬意的时候,她听见了月光的流动声,听见了抽油机的嗡嗡声,听见了山风的嘻嘻声,它们都热热闹闹地陪着她。当然,还有两只山雀,它们住在房前的一个树洞里。清晨,山雀把她唤醒,她早已习惯和它们相处了。
高松洁认为丈夫明天中午才能来到,所以她显得不慌不忙。她又接了半盆泉水,倒在大盆里。她脱光衣服,大大方方跳了进去。水一下把她淹住了,她的四肢自然舒展着。敞开身体,周围似有晃动的蛋清,是柔软的,光滑的。尤其是到了伏天,往盆里一躺,身子宛如一块旱地,吱吱地吮吸着。不多会儿,她觉得四肢圆了,脑也圆了,它们能唧唧地冒出水来。
毕竟是秋天了,山地的凉气一日强于一日。她躺在盆里,觉得有很重的秋意。瞅瞅门外,草还旺着,树叶还旺着,只是月光显得胆怯了。月光就照在大盆子里,她挪挪身子,让光线落在脖颈上。她感到月光的温暖了,觉得它变成了一双手,在她身上轻轻地抚摸着。她闭上眼,想着月光从她身上跳下,跳到地上。地是土地,是暄地,一踩能踩个窝窝。屋里没啥家什,一个灶台,一个铁锅,几个碗碟。碗是破了边的,能勉强盛饭。里面是个土炕,炕后面是几件巡井用的管钳,它们都齐齐地挂在墙上。屋里的其他东西都是软的,唯有这些是硬的。月光飘上去,又被闪闪地折了过来。她喜欢看管钳上沾着的月光,月光在上面跳荡着,舞动着,似闪亮的调皮的眼。炕右边是两个石块,石块上面是台电视,电视没有信号,关着开着是一样的。工作之余,她就面对屏幕,悠悠地想,想那些曾经记得的画面、记得的歌曲、记得的场面。就这么想着,一天天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她认为屋里的月光都老了,老得有点龙钟了,不过月光的温度没有变化,沾在身上,仍是暖暖和和的。
其实,昨天已洗过澡,不过巡了一天井,她决定再洗一遍。她伸直手,朝胸部搓去,手指滑了一下,然后就没于水里了。月光也掉到水里了,她想捞它,伸出手,手上却布满了水珠。她想丈夫爬到这座山上,额上肯定也挂满汗珠的。她要上去给他擦汗,然后扯住他往家里走。这里是他们真正的家了。她要先让他坐在门前的土墩上,这里能瞅到屋周围的花坪。高的是面蓬草,这时的面蓬浑身变红了,红得像浓重的颜色,似要把地面染红了。面蓬后面是山丹丹花,花瓣虽然落了,但眼一晃,能瞅见它红的黄的花瓣。房周围是驴苒苒草和胖姓娃草。若是盛夏,花和坡上的草连在一起,变成一条多彩的毯子,小屋成个乖巧的孩子,安安稳稳地躺在了上面。她喜欢在土墩上坐着,一坐就是半晌。这时她啥都不想,只眯眼,瞅着花,瞅着草。
转过身子,可瞧见十来口油井,它们高高矗立着,神圣地站在山顶上。小屋旁边是一号井,电机的嗡嗡声,传到这里,变成悄然的轰轰声。声音是均匀的,像孩子的呼吸。只要有点异样,她会马上听出的。远处的油井只有凭眼光了,她能通过抽油机的摇动,猜出是否出了毛病。早上起来后,她就坐在土墩上,往前瞅,瞅山上的抽油机,如果发现问题,她会先赶到那里。夜里往床上一躺,最踏实的是听抽油机的轰轰声。她觉得,这种声音就是丈夫的鼾声,给她的感觉是踏实的,安静的。她最怕山里的风声,风声能把电机声吹散。夜里,她常常坐起,去捕捉微弱的电机响,即便听到一点,心里也是踏实的。
不过,她还是喜欢白天的,阳光在面前吱吱地响着,或者在花上、在草上跳跃着。有时风会冷不丁地窜过来,和阳光纠缠着,然后就打打闹闹地滚下山坡。更多时,她还是听山雀的鸣叫。山雀好像认识她,它们好跳到门口的土墩上,对着门唧唧地叫,然后再跳到房檐上,欢快地点头,做出觅食的动作。等她打开门,山雀已悄悄飞走了。她认为山雀不会走远的,或许就躲在树洞里。树洞像只手,总是把她悄悄拽过去。她和往常一样,慢慢爬到树上。这次她发现,窝里有两个鸟蛋。阳光正好落在洞口,她仔细瞅瞅,草下面还压着两个,窝里总共四个蛋。她高兴地想,过段时间,又有四个邻居和她见面了。风响着,阳光也响着,她仿佛听见小鸟清脆的叫声。
丈夫来了就好了,两人做伴,夜里也可以巡井了。想到这,她的脸有点发烧。这时,她从盆里站起,从墙上摘下一个小包,里头装的是荞麦花。花是干的,她抓起一把,撒到了盆里。她把花揉碎,让它一点点化到水里。水里顿时有股清香,淡淡的,像股细微的呼吸。不过,这种香气会沾到身上的,丈夫来了,会闻到这种清香的。她好长时间不用香皂了,为了除汗,就往水里加些花瓣。这样的水必须慢慢洗,洗慢了,花香才会浸到身上。多年来,她学会了慢,慢慢走路,慢慢洗衣,慢慢做饭,慢下来才能熬走日月,熬走日子。她感到时间像个瓢虫,在地上蠕动着,在炕上蠕动着,然后爬到她的枕边,呼呼大睡了。时间实在走不动了,它们在屋里、在沟里、在山上沉下,一点点把她埋掉了,然后生出漫长的寂寞。寂寞像条藤萝,把她从上到下,结结实实地缠着。不过,她不怕,她一点不怕,真呛不住了,就扛起管钳,再去巡井。来回跑上一天,往炕上一躺,就啥都不知了。
这是她惯用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不过遇到阴雨,就缠手了。山里的雨细长、连绵,慢得急人,寂寞像夏天的草,噌噌地生长着。她被困在屋里,困在炕上。时间像一扇沉重的门,把她死死地堵住了。一天过了,两天过了,雨还在下着,门是出不得了,雨点如箭镞,把房前的土掘得暄暄的。烟雨中,只能瞅见抽油机模糊的影子。不过她听得见它们的声音,嗡嗡的,没一点毛病,这样她就感到踏实了。
雨一下,似乎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她往炕上一坐,就想那抽油机。二十一台抽油机,一个个地想。从电机,到井口,到支架,到驴头。想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实在无处可想了。她瞅瞅天,天还没黑下,寂寞又像山风,呼呼地刮起了。她拍拍脑袋让思绪落下,落在房前的草丛上。为了忘记时间,她学会了遐想。她想起山上的星星草,草芽拱出地面,一弓一弓地长高了。叶子是趔着身子张开的,它们一层一层托出了草尖,草尖上冒出了一个个米粒大的花蕾,花蕾呲开后,跳出银针似的花须。秋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草。她把草的生长过程也一遍遍地想了,想得多了,觉得草们都进了屋里,偎到床前,一摇一摇的,想和她说话呢。这时,时间便跃过草们,跃过炕头,跃过门窗,哗哗地流走了。她仿佛又听到了电机响,听到了抽油机沉重的喘气声。
其实闲暇时,她牵挂的是那些山雀。隔三岔五的,她就爬到树上,往洞里瞅瞅。每次去看时,总有一个山雀在里面孵蛋。山雀见了她并不走。她故意朝里挥挥手,山雀仍死死地蹲着。
盆里的荞麦花围到了她的胸前。她拨了一下,但花瓣又怯怯地过来了。她想,这是它们怜爱自己呢,她还没这样洗过呢,等丈夫过来,她也让他这样洗。这是山里,没啥奢侈的,这也算大山给的慰藉吧。
从县城来到这里,少说也有百把里地,他肯定弄的满身是汗,然后往盆里一躺,是何等的幸福呀。不过,她得先给他弄些吃的。肉是没有的,一个月送一次给养,这里是大山深处,有肉也不敢多放。她可以给他烤玉米,烧红薯。玉米是自己种的,红薯也是自己种的。由于给养不能及时送来,她在山上开了片田地,种粮种菜。虽说辛苦,但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明天早上,她准备刨几块红薯,点着灶火,先慢慢烤着,等丈夫来了,就能烤熟了。
丈夫是第一次来这儿,多少得弄个菜的。平时一忙,她总是吃点咸菜。明天是不能让丈夫吃咸菜的,若开始把他吓住,恐怕就不好留他了。她不知应该准备什么。她从屋内想到屋外,又从屋外想到屋内。给他炒个萝卜,怕他不愿吃。给他调个白菜,怕他在家吃腻了。屋里就这两个菜,别的再没有了。她有点失望,心想要是在城里多好,城里要啥有啥。但这种念头一出,就被她狠狠打掉了。她瞅瞅外面的月光,月光水似的流淌着,地面好像都是湿的。她突然想起,树下该有地软了,这是山里的特产,明上午多拣些,给丈夫拌成凉菜。
给丈夫定好吃的,心里踏实了很多。她把身子往水里浸浸,尽量让水好好泡泡。她想把油渍味泡掉,把土腥味泡掉,让荞麦花的香气重重地缠在身上。她好久没见到丈夫了,她闭上眼,努力想着他的外貌,但记忆是模糊的。记得清晰的,倒是山上的抽油机、山上的树、山上的草,她感到对不住他。她担心,他刚到时不适应,这里除了黄天黄地,除了抽油机,其余什么都没有。她想起刚来的感觉。十年前,她来到这里,把行李往炕上一丢,头都晕了。她坐到炕上,觉得脑里空空的,里面只有呼呼的风响。她闭上眼,声音更高了,一阵接着一阵,轰轰隆隆的。她使劲把头摇摇,响声小了点,但抽油机的声音传来了。这是一号抽油机的声音,就在屋外,离她最近,它的声音是沉闷的,沉闷中有种激越。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发现每台抽油机都有自己的声音,有的是高昂的,有的是沉闷的,有的沉稳带着耐性,有的则铿锵满是爽朗。每次巡井,她不用瞅,只要往跟前一站,就知道是哪台机器。她认为,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脾性,自己的声音,它们跟人一样,得精心呵护,精心关爱。每天她都把抽油机瞧上一遍,不瞧就不踏实,不自在。她喜欢这里的阳光,尤其到了秋天,阳光是柔软的,温暖的,它们在坡上滚爬着,晃得苹果红了,柿子软了,茅草哈哈地抖着身子,照得抽油机也白亮得耀眼。这时节,满山都飘着香气,它们如轻悠的柳絮,四处游荡着。深夜难眠时,她总是深吸一口,香气就顺着鼻孔,嘶嘶地钻到体内。这时的一切都是静的,只有抽油机是动的,她梦里只有这些笨重的机器了。
当然,她不能忘怀的还有山雀。一天下午,她巡完井,像往常一样,爬上了树洞。往里一瞅,发现小山雀已破壳而出了,四个肉蛋似的山雀,盲目地伸着脖子,颤颤地晃着身体。老山雀不在里面,她赶紧找些虫子,一一地喂给它们。一连多日,她抽空就来,老山雀在了,她就把虫子搁在洞外的树杈上。老山雀不在,她就把虫直接喂了。她瞅着小山雀一天天长大,瞅着它们飞出树洞,瞅着它们在门前蹦跳,觉得一刻也离不开它们了。
一股凉风瞅准门缝,吱扭一响钻了进来。她往盆里沉沉,水漫住了脖颈。其实她身上并不脏,但她还是起劲地揉搓着。她不知自已是胖了还是瘦了,她觉得还是胖点好,胖点力气就大了,用起粗大的管钳,就更加方便了。
她往脸上捂些水,尽量让脸滋润点。整天泡在山里,脸黑了,粗糙了。丈夫来了就好了,她准备把脸好好保养一下。其实她只有半瓶护肤膏,用完也就没有了。地里有几个黄瓜,她打算将黄瓜切成片儿,一块块地贴到脸上。她要留住丈夫,帮她好好照顾这几口油井。
从内心说,她是有些担心的,她怕丈夫受不了这里的艰苦。她明白,新来这里,面对的最大杀手,就是寂寞。不过,她想好了,她要教他怎样面对寂寞。她记得自己刚来的第一个晚上,一人躺在床上,确切地说是躺在山里,躺在墨似的夜里。窗外是凛冽的风声,风好像是挂着的刀片,它们迅速划过山坡,划过树林,发出瘆人的怪叫,寂寞便潮涌似的袭来了。她听到了梭梭草的生长声,仿佛看到它瘦长的叶片,涨着身子,一弓一弓地摇晃着。她听到了山丹花的吐蕊声,听到了它血红的叶子伸展的窸窣声。她听到了山上所有草的声音,它们像在私语着,在歌唱着。它们把所有的声音,都悄悄地送给了她,她在这柔软的声音里,慢慢入睡了。
丈夫来到后,她准备让他先认山上的几种草,比如牛筋草、苦莓草;比如面条草、鸡冠草。来到这里,就得以山为家,草和树就是朋友了。当然,作为朋友的,还有山上的星星、明月,还有风。风总是斜着身子跑过来,它们先围着小屋转上几圈,然后就哧溜钻到了屋里。她把它们当成了孩子,它们在桌上跳着,在管钳上跳着,最后疯也似的跃到了炕上。它们似乎不愿走了,把落叶卷了上来,把草茎卷了上来,落叶和草茎便在屋内舞动着。
月光比先前浓了亮了。她欠欠身子,露出半个胸脯。她觉得洗净了,就从盆里站了起来。水滴从身上掉到盆里,发出嗒嗒的脆响,她感到动听极了。她觉得水滴落到了荷叶上,在叶面上悠悠地晃着,每晃动一下,都发出悦耳的颤音,她真想让这种声音永远持续下去,可是夜已很深了。她擦干身子,抓一把野菊花瓣,往身上揉搓,身子顿时冒出淡淡的香气。
月光挤满了房子,她瞅瞅身子,认为瘦的并不多,心里便安然了。她打开衣箱,拿出了衣服。这是件白色风衣,也是自己喜欢的。她穿好,想照照镜子,但房里只有一个照脸的小镜。她走近窗口,凑着月光瞅瞅,觉得不太满意,还是脱下了。她从衣箱里挑了一件红色线衣,认为应把它穿上,因为明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她穿上红色线衣,在房里走了几圈,感觉特别舒适,她似乎瞅见衣服的红光,和月色交映着,变成一阵委婉的歌声,从房里流淌出来。
夜深了许多,月光却分外明了。她想把房子收拾一下,发现并没什么可做的。房内除了几个挂在墙上的管钳,几乎啥都没有了。炕上仅铺了一床褥子,一入秋,天凉得快,明早上,她准备薅些麦秆,铺到炕上,麦秆能挡很大风寒的。她担心,丈夫睡惯了席梦思,能否适应这样的土坑。不过她已经想好了,丈夫如果嫌弃的话,她就把箱里的衣服拿出,统统给丈夫铺上。单子、被罩、枕巾都是刚洗的,上面散发着皂茄的香气,丈夫肯定喜欢这种气味的。她认为,丈夫没闻过这样的香气,这种香气才是天然的、绿色的。这时她打开箱子,情不自禁地俯下身闻闻,但又猛地抬起头,想起什么。她走到门口,把一束艾草挂到了门框上——这是用来避邪的,两人多日没见,跟新婚一样,有艾草在门口挡着,就可以放心恩爱了。
她往炕上一依,月光正好映在脸上。炕上和地上都被照得白白的。丈夫现在干啥呢,他瞅见了这圆圆的月亮吗?她抑着兴奋,一遍遍地想,明晚这个时候,丈夫就躺在这个炕上了,她要让他吃好。原先她打算给他烤玉米,烧红薯,现在改变了主意。她准备刨些土豆,给他做洋芋擦擦,然后再做一碗抿尖,里面多放些辣椒和葱蒜,让他喝得出汗,大大地出汗,把身上的寒气撵净。
这样一来,越想就越多了,她想拦住自己的思绪,但它就像一撮柳絮,忽忽悠悠地飘着。她已经想好了,天一亮,就到山口处等他。一人去确实孤单,那么除了她还有谁呢?谁也没有了,她有点失望。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六只山雀,明天一早,她就去招呼它们,说不定,它们会跟她一起去呢,她和六只山雀,将组成一支热热闹闹的欢迎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