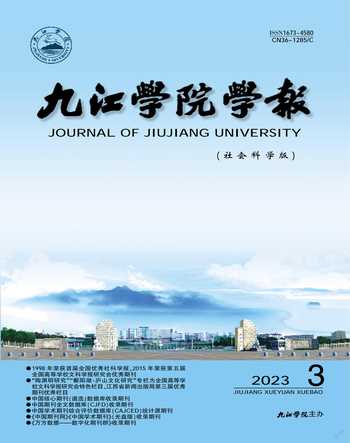麦克卢汉听觉/声音传播思想探析
周子渊 程荣荣
摘要:我们生活在虚实共生的知识和感觉时代,感官的平衡、互动和延伸在麦克卢汉的指引下与数字化生存共舞,听觉或者听觉文化成为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维度。听觉的延伸、声音的同步性和整体场等特征,不仅演绎着麦克卢汉的传播观,而且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不断被印证和实践,成为跨时空的指引和对未来的想象。
关键词:麦克卢汉;感官;听觉;声音;同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3)03-0095-(06)
DOI:10.19717/j.cnki.jjus.2023.03.017
“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1]作为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最具有探索精神的西方媒介理论思想家,被称为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圣人”“先驱”和“先知”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如是说,为我们理解其听觉/声音传播思想提供了路径指引。
一、麦克卢汉听觉/声音传播思想研究源起
麦克卢汉将人类历史上的传播方式划分为口头、印刷和电子三种,而人类社会交往则对应经历了部落化、去部落化和再部落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正是“听觉—视觉—恢复听觉”的感官动态平衡和互动的过程。部落化时代是一个听觉/声音偏向的时代,虽然包括所有的感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但却是一个耳朵的作用远大于眼睛的古老而漫长的时代,“部落人”是感官完整、没有分割的“听觉人”;去部落化时代是印刷文字“侵蚀”听觉并弱化触觉、味觉和嗅觉的时代——涉及思想而弱化感觉的文字时代。视觉登上感官等级顶端,成为西方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非部落人”是感官肢解分割的“视觉人”;再部落化时代不仅是媒介的融合时代,也是视觉、听觉等感官综合延伸的现实历程体现,听觉回归并跨越了时间—空间的掣肘,感官动态平衡和互动成为即时现象。
(一)交叉互融的学科知识背景是基础
麦克卢汉用文学语言表述其社会学、传播学思想;用文化、哲学语言论述并预言了传播的电子时代及赛博空间;用工科语言及思维探讨传播技术,等等。“他相信自己能够信马由缰地纵横驰骋,从古典文学到当代电影,从教育史到技术史,从莎士比亚到乔伊斯,从控制论到传播学,从神学争论到弥尔顿的撒旦,从丁尼生的山水诗到古迪恩的现代建筑空间理论,从古登堡到‘机械新娘,从机器文明到大脑的延伸,从‘部落鼓到‘全球村,从拼音文字到民主政治。”[2]麦克卢汉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与他从工科—文学—哲学—文学批评—社会批评—大众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学习和研究历程分不开的,作为实践跨学科研究的先驱,交叉互融的学科背景不仅使他从自发到自觉地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建构其超前思想,而且反过来其思想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他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灵活运用。
麦克盧汉的研究是从文学起步的,他敏锐地捕捉到“当代文化变迁的革命阈限”[3],并以艺术的方式阐释自己的观点。他从文学、艺术中汲取到观察视角、表达形式、环境变迁和未来趋势,并在文学、艺术学中成为洞察到媒介变迁发展的、聚焦感知而非观念的、具有“整体意识”的人。受象征主义诗人和艺术家的影响,麦克卢汉采用了“打碎并重组为模式”的象征主义手法,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艺术思维研究路径——独树一帜、天马行空、形象生动而又不够科学和严谨。也正是基于此,麦克卢汉研究媒介的想象、灵感和突破,源自于文学家和艺术学家们。在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感知分离”“听觉想象”的启发下,麦克卢汉提出了“随着主导的感官发生变化,人的总体感知也发生变化”[4]的思想,并提出“听觉空间”(或“声觉空间”)的概念——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5]。将感官、通感和感知系统聚焦到声觉空间(亦即“听觉—触觉空间”)之中,不仅表征了电力信息的声觉空间的感官偏向,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赛博空间和当下对元宇宙空间的描述。当然,这也得益于心理学家卡尔·威廉斯的“声觉空间”概念和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等对他的启发和影响。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学习经历和学科基础,没有广泛的涉猎相关知识,就不可能成就他“知识的游牧采集人”的称号,也不可能形成其混合文化的文风,更不可能先于他人提出“听觉空间”的概念。
(二)对时代发展步伐的把握是关键
交叉互融的学科背景使麦克卢汉对时代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预见性。如果说哈罗德·伊尼斯为麦克卢汉的感官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沃尔特·翁则为麦克卢汉的听觉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麦克卢汉用前者的转换理论、感知体验解释并研究了人类在快速多变的环境中运用并寻求感官平衡,这不仅是《谷登堡星汉璀璨》的理论基础,也是《理解媒介》的理论来源;后者为其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奠定了西方人在现实中从听觉为主转向视觉为主的载体就是印刷术的研究基础。
“麦克卢汉是一个处于电子时代之中的人文主义者,追寻着获取知识与现实的电子措施,从各种不同的领域和文化语言中收集素材;他对于动态情境(常常被人错误地理解为琐碎的普遍性)整体的、包容性的理解是为了揭示新的社会模式。……他的传播形态,以及他‘通过平面场的形式对情境的表现,一贯是人文主义的,同时也是卓越的和电子的:他借鉴文学和艺术传统,并煞费苦心地通过一种富于原创性的过程来表达他的发现。”[6]麦克卢汉将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转换成他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超时代性把握和预测,他的媒介隐喻远远超出了他所在时代对媒介的理解,其中就包括电子时代的听觉性意味着媒介环境已经开始了从视觉侧重到听觉侧重的重构。交叉互融的学科背景、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好奇心和创新意识等等,使他不仅把握住了时代文化、思潮发展的脉搏,而且在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思想和意义的基础上超越了时代的掣肘,从而指引着我们对数字时代的理解、对媒介环境的把握、对听觉/声音传播思想的探索。
麦克卢汉从全局的视角去观察和探索其媒介理论,用夸张的言辞传达其聚焦于感知而不是观念、观察背景而不是外形、从结果追溯原因等思想突出重围。这样,他不仅敏锐地洞察到了时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而且取得了超出时代的理论突破进展,其“媒介即讯息”“地球村”“媒介即人的延伸”以及区分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等理论及观点,就是他洞察时代而又跳出时代的羁绊而取得的。所以,他的理论及其观点时常被人诟病甚至误读,既与他文风的不严谨、晦涩难懂的暗喻等有关,又跟他与传播研究时代主流逆向而行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时代发展的把控已经超出了时代对他的理解,其场观念和声觉空间思想直接促成了其“地球村”理念的提出就是证据之一。
二、麦克卢汉听觉/声音传播思想的内涵
罗伯特·洛根总结麦克卢汉观点后指出:“视觉空间的感知偏向是线性的、序列的、一次一个的、客观的、理性的、演绎的、分割肢解的、因果关系的和专门化的;相反,声觉空间的感知偏向是非线性的、同步的、四面八方的、主观的,其特征是深度参与的、具体的、直觉的、无所不包的、神秘的、归纳的和经验性的。与大脑左半球专业性相关的模式构成视觉空间的特征,声觉空间的特征与右脑相关功能模式相联系。”[7]在麦克卢汉看来,感知偏向或者感知编制程序是我们意识的延伸,感知的过程即是转换的过程。“‘接触并不只是肌肤的感觉,而是几种感官的相互作用;‘保持接触或‘与人接触是多种感官有效交会的问题,是视觉转换成声觉,声觉又转换成动觉、味觉和嗅觉的问题。”[8]且听觉是高度审美、精微细腻、无所不包的。
(一)听觉/声音传播的本质是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传播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机器新娘》(谈工业人与广告,1951)、《谷登堡星汉璀璨》(谈印刷人,1962)、《理解媒介》(谈电子人,1964)。他对工业人的批判,对印刷人的悲叹,对电子人的赞美,既是他对大众文化先知先觉的体现,更是在电子时代对传播思想的超时代甚至跨时代的把控与预测。“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9]通常,麦克卢汉将声觉空间与口语社会/文化或部落人相联系,将视觉空间与书面社会/文化相联系。但电力时代经常性甚至即时性地逆转视觉空间和声觉空间的这种联系,重构了人的感知系统、社会结构和环境机制。所以,麦克卢汉指出“那些体验到新技术第一次冲击的人们,不管是文字还是无线电,都会有着最强烈的反应,因为视觉或听觉的技术膨胀立刻形成了新的感官平衡,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在所有感官之中唤起一个有力的新‘闭合,或新颖的互动模式”[10],是感官相互作用的延伸。“文字或印刷的‘内容是言语,……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11],已经全面升华了如何将声音“放进人类经验相关频段的问题”[12],而不仅仅是感官的某个方面。文字的偏向是视觉,言语的偏向是声音,人总是在社会、文化和技术等的进程中不断“调适”自己,感知及其延伸必然发生改变或形成新的比率。麦克卢汉指出,言语是低清晰度的冷媒介,需要听话人的高参与度,也就意味着听者需要调动更多的感官参与信息的捕捉,而这是符合声觉空间的感知偏向和特征的。
在麦克卢汉看来,视觉与声音不是绝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媒介的内化可以改变人的感官平衡和精神进程,不管是视觉导向的印刷时代还是听觉导向的电子时代,它都不仅是感官的单纯平衡互动,而且是感官的延伸,特别是在我们的感官趋于外化的电子时代。“不同媒介在不同层次承载着听觉信息。”[13]技术和媒介是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互动的中介,是人的延伸。社会与自然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同步或者最终都会被人的感官所感知。同步则是麦克卢汉认为声觉空间对电力时代的较贴切表征,也是他将声觉空间视为听觉—触觉空间的主要原因——触觉性是所有感官的互动,触觉是“整体的、通感的,涉及一切感官”[14]。
麦克卢汉断言视觉和听觉在本质上是触觉。“与其说电视是视觉媒介,毋宁说它是一种触觉—听觉媒介,它使我们的一切感官深刻地相互影响”[15]。所以,“以听觉为例,如果它被强化,触觉、味觉、视觉就立即受到影响。”[16]与其说是技术或者中枢神经系统对身体的延伸,不如说是人的感官本质的延伸——人的延伸。这种延伸不仅仅是转换,而是整个机体的改变。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麦克卢汉所说的“广播冲击的是视觉,照片冲击的是听觉”[17](强调的是视觉、听觉对象的重要性,其实质强调的是触觉——不仅是预警,更是涉及一切感官)的论断。如果说视觉的可靠性依赖于触觉的可靠性,那么听觉的可靠性则依赖于触觉的整体互动性。因为任何一种感官被削弱或者失去时,别的感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接替该感官的作用,虽然有差别但却是人体机能的本能延伸(反应)。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需要改變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还有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二)听觉/声音传播是在“场”中发生的
“场的概念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是麦克卢汉理解后谷登堡时代的重要依据,他把它看成是‘互动事件的总场。场方法论蕴含着生态方法。”[18]声觉空间是场的空间。麦克卢汉从对专门片段的注意转移到对整体场的注意,是建立在系统感知基础之上的,是他从工业人、印刷人到电子人演进的必然结果。“比如,麦克卢汉说,报纸的结构是‘听觉的。他解释说:‘成分并存、彼此没有直接的线性勾连的任何模式,都构成了一个同步关系场,就是听觉的,尽管某些侧面是可以看到的。换言之,报纸存在于听觉空间而不是视觉空间中。”[19]因为报纸更符合人们整体的模式感,是非线性的,具有形式和功能上的统一体的感觉。到了电子时代,媒介的整体场属性和人感知信息的整体场不仅再次走进了文字诞生之前的听觉空间,而且是同步甚至即时关系的整体场。
麦克卢汉说:“电磁波的发现已经重新塑造了所有人类事物的同步‘场,从而使人类大家庭存在于‘地球村的状态下。”[20]在听觉—触觉社会,人们需要运用感官的综合体去捕捉信息。由技术的延伸引起的文化转型及变化会迅速地内化于人,而感官比率的变化会将原本清晰的信息变得朦胧晦涩,原本朦胧晦涩的信息变得清晰通透。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将口语时代的听觉—触觉模式与电子时代的听觉—触觉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分和理解,就更不可能将其运用到现代沉浸式的听觉场域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同步“场”中,声觉空间里的共鸣间隙才会产生,听者所获得的信息“结果瞬间和原因融合在一起”[21]。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声觉空间就是同步“场”,是一个将时间和空间统一到整体感知体系的、生态的“并呈现出多种可能形态所镶嵌而成的全新格局”[22]的场,能让听者轻而易举、不知不觉产生共鸣。
麦克卢汉认为,听觉—触觉空间所具有的“封闭性”或“形象性”空间是在印刷术诞生之后才得以广泛应用的。麦克卢汉说:“雕塑一直是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的边界。因为雕塑并非封闭空间。它调制空间,正如声音调制空间。”[23]这个暗喻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听觉—触觉空间所具有的“场”属性,其“封闭性”或“形象性”空间是相对于视觉空间而言的,在麦克卢汉眼中,雕塑是交互性媒介,听者或者观者需要调动身体的整体感官才能够体验其空间结构。“一旦序列让位于同步,人就进入了外形和结构的世界。……人们保留着整体的模式感,保留着形式和功能是一个统一体的感觉。……在进入电力时代之后,遵循数字场的力的外形,周旋于数论和‘集合之间。”[24]精警深邃而又玄妙如谜的表述背后,其实是用艺术的描绘方式告诉我们艺术家或者艺术对环境变化的嗅觉更为敏锐,更能把握因环境变化后的人的注意场,而我们大多数人则是用“后视镜的观点看世界,我们看世界的观点总是要落后一步”[25]。因为耳朵强烈而深刻、高度审美、无所不包等的感官功能,与艺术家和艺术的很多诸如此类的特性相吻合,这不仅决定了听觉场的同步性,也是电力时代甚至元宇宙时代耳朵对声音等“瞬间”信息紧缩的、内爆的性质的匹配——对整体、同步的联系场的自适应。
三、麦克卢汉听觉/声音传播思想对现代传播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爆炸的升级,我们对信息的接收变得更加挑剔和简洁,在整个时代快速变幻的背景下,焦虑成为常态,听觉空间无所不包的特征不仅吻合了时代变迁的节奏,而且在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听觉转向中占据了先机。
(一)促进了现代听觉/声音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
人类对听觉/声音的关注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发生了。“从上古起直到19世纪,人们都是把声音理解为可听声的同义语。”[26]东西方对声音的较为系统的表述都是从音乐开始的,从中国先秦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都概不能外。声音理论和声音文化理论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兴起,而随着现代声学、医学、物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的发展,特别是在视觉转向之后的听觉转向发生后,对听觉/声音的研究日益成为显学。
加拿大著名的作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声学生态学家,麦克卢汉的学生默里·谢弗(R.Murray Schafer,1933—2021)在《声音景观》(1977)中运用格式塔理论提出的“声景”(或者“音景”)“声音帝国主义”等已经成为现代声音研究的热门词汇和研究对象,亦是现代听觉及其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声效生态学”“声效空间”“基调音”“信号音”“标志音”等概念对现代声音研究影响极大并强调声音研究中的形象、背景与“场”(承延麦克卢汉“整体场”理念)的联系,从而奠定了其在现代声学研究中的地位。在他的影响推动下,“为世界调音:第一届音响生态国际研讨会”(The Tuning of the World: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 Ecology)于1993年在西蒙·弗雷泽大学召开,随之组建的“世界听觉生态论坛”(The 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简称WFAE)每三年召开一次,极大地推动了听觉理论研究的发展,影响深远。技术派声音研究代表人物,法国人皮埃爾·沙费不但进行了听的感觉实验,而且提出了声音物体或者声音对象、声音客体的概念,强调用相互联系的整体来感知声音现象。而谢弗拿自己的研究与沙费“声音对象”做比较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主体与声音的整一性”[27]。此外,沙费还从声音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纯声学”的概念,为其学生米歇尔·希翁在《声音》(2006)中的声音符号学研究打开新视野奠定了基础。《声音》向我们展示了声音研究的庞杂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对声音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声音现象的丰富性、声音概念与听觉概念的界说和对噪音的认知等等,都让我们对声音、听觉和倾听等有了新的认知。他对声音形态学、听觉学、建构声音等的认知和研究,不仅推动了声音研究的发展,而且促使我们在更系统的理论体系、更开阔的领域去认识和研究声音、听觉和倾听。
2009 年,“对倾听的思考——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行,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已成为共识。视觉转向所带来的视觉过度膨胀及其在发展中形成的视觉霸权,不仅促进了人们探求感官平衡的动力以求释放人的全部感知潜力,而且为防范形成新的听觉霸权提供了借鉴。
(二)加速了现代听觉/声音文化的转向
麦克卢汉对传播三个时代的划分,不仅阐释了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深受其时代所主导的媒介的影响,而且使我们对听觉—视觉—恢复听觉的感官动态平衡和互动的过程有了新的认知和对比。但口语传统和书面传统各有其断裂边界,且“文字诱发了分割肢解的精神”[28],个人主义盛行。故在麦克卢汉看来,“经过千百年的感知分裂以后,当代的知觉必然是整合的、无所不包的。”[29]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变革使他确认“功能的分离,阶段、空间和任务的分割,是西方世界偏重文字和视觉的社会的特征。有了电力技术瞬间产生的有机联系,上述分割就趋于消融瓦解了”[30]。所以,偏重听觉的东方文化被麦克卢汉所推崇,电力时代广播、电影、电视等有声技术的出现使我们踏上内爆和重新整合的逆转过程——听觉及其文化的转向即将来临。
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1997)一书中表达了明确构想:走向一种听觉文化。他的构想沿袭了约阿希姆-恩斯特·贝伦特、海德格尔、麦克卢汉、罗森斯托克·休赛以及德国作家坎伯、斯罗特迪克等人将文化由视觉主导向听觉及其文化转向的呼吁。他指出:“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唯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31]虽然他对走向听觉文化还是充满了疑惑、担忧且底气不足,但还是主张我们必须去听且要防止听觉(文化)野蛮主义的产生。
由于现代听觉技术能够使声音得以大规模存储、复制、剪辑加工、超时空传输传播,且在经过处理后成为声音产品,进入市场销售。所以,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贾克·阿达利等人均在不同程度上从文化工业角度来探讨声音或听觉文化与现代工业的关系。从而“使‘声音和‘听觉不再局限于生理和物理的范围,而是广泛与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发生关联”[32]。听觉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快速发展也传导到中国。2015年,“听觉与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师范大学举办;2017年,首届“听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办。听觉文化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形成研究群体,跨越传播学的全学科、全方位的听觉文化研究正在形成。
(三)为元宇宙语境下的听觉/声音传播提供了想象空间
元宇宙传播虚实同步、部落化、沉浸式体验等特点与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生态论、地球村、整体场等传播理论和实践不谋而合,在传播技术发展到元宇宙这个阶段,进一步印证和实践了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理论。
作为数字革命和网络技术革新的新产物,元宇宙的虚实同步更强调并实践了图像、声音和视频的集成化、生态化和同步化,在事实上印证了麦克卢汉提出的从部落化到重返部落化的真实性——人的感官延伸是通过技术发展裹挟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实现的。麦克卢汉指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介。”[33]元宇宙将媒介的再媒介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完成传播从“实”到“虚实同步”的过程中,将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充分延伸。在元宇宙这个场域之中,更强调具身性传播以及人的听觉思维、图像思维与内语思维的融合互动,从而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能够有更好的在场体验。
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和形式”[34]。“任何一种新媒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就是集体经验的编码”[35]。所以,元宇宙所打造的听觉空间有无限的可能,声音运用和再生产的想象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可能我们还没有感知就已经浸透了我们的注意场。在元宇宙时代,声音的数字化传播、数字化运用、数字化变幻成为常态且变化无穷,数据身体的具身使包括听觉在内的人的所有感官都进一步延伸和再平衡,传播权力向个人回归。元宇宙本身就是要建构一个完善的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视觉和听觉率先得到重视并取得突破。而根据麦克卢汉的听觉—触觉空间理论,元宇宙率先取得突破的恰恰是触觉,其次才是视觉和听觉,其目标则是要完成人类感官的全领域延伸。在当前技术背景下,无论是听觉还是触觉或视觉,我们开发利用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挖掘各种感官的潜能及有机整合各种感官实现个人及社会的价值增值,从而真正达到以人为本才是终极目标。
四、余论
麦克卢汉说:“同步化必然坚持要求和谐。”[36]听觉转向或者听觉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要取代視觉及视觉文化,而是要使各种感官达到新的平衡。麦克卢汉整体场理论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媒介研究、媒介环境研究或媒介生态研究有更深刻的认知。而声音、技术和媒介有一定的互换性:声音既是媒介也是技术产物;技术既是媒介也是媒介催化剂,还是声音加工工具,甚至就是声音;媒介则是声音或者技术等的呈现方式。声音传播需要借助新的技术并催生新的媒介,我们不仅需要对声音或听觉本身进行深入研究,而且更有必要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研究跟我们不可分割、相互影响、无所不包的人的存在形式、生活方式和知觉协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麦克卢汉及其听觉/声音传播思想。我们对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和人的感官本身都知之甚少,而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世界的流动性在加速,世界的同步性也在加速,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新的环境中达到和谐。人也只有在和谐状态下才能够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参考文献:
[1][3][4][13][24][25][34][35][36]麦克卢汉,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413.
[2][4][19]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前言X-184.
[6][10][20][22][23]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M].杨晨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31-141.
[7][18][21][28][30]洛根.被误读的麦克卢汉——如何矫正[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8-322.
[8][9][11][14][15][16][17][29][3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4-496.
[12]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9.
[26]高文元,迟放鲁,贺秉坤.临床听觉生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96.
[27]张聪.走向听觉的格式塔[J].东岳论丛,2020(12):73.
[31]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09.
[32]曾军.转向听觉文化[J].文化研究,2018(1):15.
(责任编辑 吴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