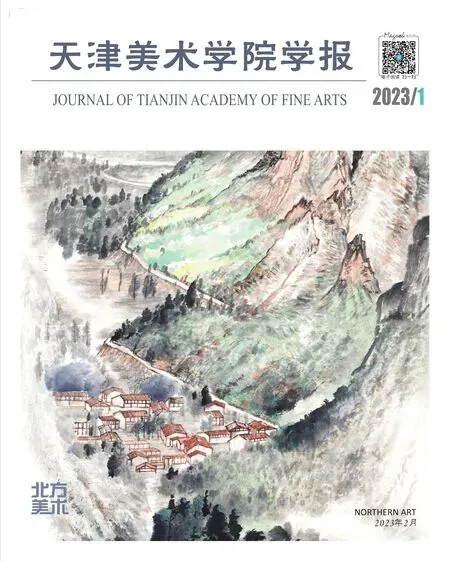从《颐园论画》批跋论俞剑华早期中国画学
祝 童
《鼎脔》,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研究金石书画之报刊,该刊由浙西名士王修主编,“巽社”同仁共襄辅办,以“究讨金石书画诸学术为宗旨”,一时流人遗老云集,声誉极盛。《鼎脔》第26期(1926年5月5日),刊俞剑华山水一幅,主编王修识云:
俞锟,字剑华,精中西绘画,为陈师曾入室弟子。山水颇似其师,创翰墨缘美术院于济南,从游者甚,众得其传,类皆知名于时。又刊行《翰墨缘》半月刊,独力主持,评鹜时贤,多中肯綮。[1]
是为俞剑华之名首次出现于《鼎脔》。关于二人之相知相识,王修在第38期(1926年7月30日)《槐堂师弟子画集序》中有言:“余识剑华于今夏,而相知则由胡佩衡先生之介,已三年矣!”[2]知民国十二年(1923),二人相知,其时俞在济南;又据《俞剑华年谱》,俞在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至十月,赴上海与名画家往还,认识黄宾虹、谢公展、张聿光诸家”[3]411。知二人相识亦于此时。从《鼎脔》来看,二人相识数月之间,即刊载俞氏画作5幅,文章4篇(不计《颐园论画》批跋,分别是《中国画写生与西洋画写生不同之点》《描稿画家之金科玉律》《恽南田与吴缶翁》《四石之盛衰》,其中《中国画写生与西洋画写生不同之点》与《描稿画家之金科玉律》皆连载二期),可见二人交谊匪浅。事实上,王修之重俞氏,不独因其为《翰墨缘》主编,互为同道,更要者,在于俞氏以“陈师曾入室弟子”身份饮誉画坛,且搜集乃师遗泽,发扬乃师学术。《槐堂师弟子画集序》称:“剑华敬其师,宁得不有是集之刊耶?且曩者已为师曾刊《中国绘画史》,辑《不朽录》,则是集之刊,固其素志矣!剑华于槐堂诸子中,不亦忠于师门哉?”[2]王修寓京时,与陈师曾过从甚密,陈还为王氏夫妇治印十余方,其深知陈门谱系。①然遍观陈氏诸弟子,唯俞氏刊《中国绘画史》,梓《不朽录》,更罗《槐堂师弟子画集》付之枣梨,矻矻不倦,弥力奔走,确是陈氏殁后知音。以是观之,俞氏之为王修所重,自无足怪耳。
《颐园论画》,清松年著。《鼎脔》第30期载俞剑华《颐园论画序》,谈及是书版本云:
(《颐园论画》)前曾刊于某报,惜未窥全豹。十有四年春于画友关松坪处假得原本,欣喜欲狂。随急印百本,分赠同好。暇日更取原书重加校定,变其前后次序,正其一二字句,并于每章之后,附志拙见。非敢好事续貂,以发挥余蕴自诩,乃由于景仰前贤不能自已耳。书既成,略志梗概如此。时民国十有四年端午节前五日也。②
是书系松年授课稿,成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现略述其版本源流如次。第一,稿本:上海图书馆藏。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影印出版。第二,光绪本:书既成,即于是年铅印刊行,世所罕见,俞氏尤未获睹,今藏国家图书馆。按,至于俞序所言“前曾刊于某报”者,难断其详,推知应为此本。第三,俞氏石印本:光绪排印后,稿本流于松年再传弟子关松坪(1895—1938)处,民国十四年(1925)春,俞氏据关藏本石印百册,今难觅其踪。第四,《画论丛刊》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于安澜据“济南俞氏藏本”铅印,收入《画论丛刊》。俞氏《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按云:“是书并未刊行,由愚为之付石印,《画论丛刊》即据石印本而章节稍加变动。”[4]241知“济南俞氏藏本”即俞氏石印本。第五,《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俞氏据“原钞本、俞剑华石印本、《画论丛刊》本”“另行排比,并酌加节名,以醒眉目”[4]241,其间偶加“研究”数则(类旁批),收入《中国历代画论大观》,其后20年屡有增订,然终流壤间60余载,2017年江苏美术出版社方整理出版。第六,《中国画论类编》本:1957年,俞剑华据《画论丛刊》本删节整理,收入《中国画论类编》,底本体例皆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两不相涉。经笔者排考校雠,各整理本皆有删节,就中以《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较优。然据《颐园论画序》,俞氏石印本因属急就,难称其意,故“暇日更取原书重加校定,变其前后次序,正其一二字句,并于每章之后,附志拙见”,是知此《鼎脔》所刊,为俞氏据原稿精校批跋之全本,不啻为诸整理本中最善者。惜乎俞氏批跋本长期在学术史上堙没无闻,俞氏本人亦未曾片言及之,个中缘由,颇值进一步探究。③
古典画论卷帙无计,俞剑华何独批跋《颐园论画》?其序云:
古人论画之书多矣,率皆辞衍意奥,悟解不易,求其不尚辞藻,平易近人,便于初学者盖少。松小梦先生年本蒙古人,宦游山左,擅六法,于画无所不能,又善书,皆自成家,不落古人窠臼,名满齐鲁,几于妇孺皆知。性方正,喜提携后进,一时画家蔚起,流风余韵,至今不衰。余生也晚,未能亲接謦欬。及束发受书,辄喜涂鸦。迨后专研斯道,而先生已归道山矣。此书本为先生画坛主盟时,随笔所录,平正通达,不囿于古,不泥于今,专家研求,初学入门,无不适合。[5]
一方面,俞氏指出古代画论“辞衍意奥,悟解不易”之劣,从而肯定《颐园论画》“平正通达,不囿于古,不泥于今,专家研求,初学入门,无不适合”之优。所谓“平正”,亦即不囿古泥今,不偏不倚;所谓“通达”,亦即“不尚辞藻,平易近人”,深入浅出,“且于实用之言”[6]337。需知,“平正通达”,为俞氏评鉴画论之最高标准;而此种学风,亦给正处于学术转型时期之俞氏莫大影响,奠定了其一生持中秉正之学术理念。另一方面,俞氏对松年画艺推许备至,指出其自成一家,“不落古人窠臼”之长。其曾于《颐园论画》“竹兰”章批跋:“小梦先生最擅兰竹,能自出机杼,不袭古人面貌,迎风含露,笔墨生动,故不惜以金针度人。”[7]“用墨”章批跋:“小梦先生善于用墨,其墨色之复杂,且不只于五,可谓超越古人矣。”[8]“用水”章批跋:“小梦先生不但笔墨擅长,而其用水之妙,允非庸史所能梦见,故此书亦于用水之法三致意焉。”[8]如是等等,对其翰墨艺术高标称首,从而肯定是书解惑之功。更要者,松年“性方正,喜提携后进”之崇高人格,最为俞氏所尊崇。据史料,松年天性刚毅,不阿权贵,名望既高,追随自众,俊彦从游,甲于齐鲁。惟娱以书画,鲜事著述,故胸中块垒,皆浇筑是书之中。《颐园论画》“人品”章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9]确是古今至论。对其中“吾辈处世,不可一事有我”“居官吏更讲政绩声名”诸世故之言,俞氏反复为之开脱:“小梦先生满腹牢骚,平生以鲠直多开罪于人,有激于中,故务反前辄平易教人,并非愿天下之画家尽为乡愿也。”[10]“先生风骨峭厉,不合时宜,屡以画贾祸,故言之痛切如此,可谓苦口婆心也矣。”[4]218“(是书)劝人和光同尘,乃出于愤激有为之言,非真劝人同流合污也。”[6]337作为松年私淑弟子,俞氏于其言行,耳闻身践,别具体悟,不遗余力维护其声名,良有以也。观夫俞氏前半生,正值民族存亡之秋,不仅多次襄办书画义卖展,还曾投笔从戎,任二十五军同中校秘书,故其为文,纵横捭阖,方正刚烈,较之松年有过之无不及;而新中国成立后更致力兴教,“提携后进”,光大学说,立派开宗,“流风余韵,至今不衰”,亦当是其生平之写照。[3]407-430.要之,松年及其《颐园论画》,于画论、于画艺、于人格,皆给俞氏指明了方向,其之所以以理论、以实践、以良师彪炳画坛,是人是书,岂可没焉。
二
《鼎脔》第31至44期,连载俞氏批跋本《颐园论画》,前后计14期。除小引、写意、制粉、辨纸绢、教画、重名、结论章7章外,俞剑华对山水、人物、花卉等34章皆作批跋,合第30期所刊序,计六千余字,从入门取法到画家意识,再至“趣”“神”之美学追求,立于松年之论,而多所发明,不啻为俞氏研读中国古典画论之精意体悟,亦诚为其早期中国画学的代表之作。
第一,辩“临摹”与“写生”
师法造化,是中国画学亘古之传统,然每一家独出,遂成定式,从学者不究根源,千临万摹,遂成宿习。松年于《颐园论画》中,曾辩证地指出临摹与写生不可偏废之观点:
凡精于此道者,固在见前人之佳本,亦须目睹真形,传诸笔墨。吾辈既应法古,尤在于以造物为师,两处贯通,融汇心手。[11]
清末画坛流于纸上烟云,鲜事写生,积重难返,早为有识之士所揭示。但直到西洋画之进入,方引起画坛之震动,反哺于中国画。此中曲折,必须有矫枉过正之声音出现,俞剑华便是典型代表。在批跋中,俞氏就对因“徒事临摹”而致泥古不化和狂怪造作两种异端,大加鞭挞。一方面,“徒事临摹”,不知通变,运之腕底,必执死法:
画家有以画一幅画用一种笔为上者,此亦未免胶柱刻舟,画中之景物不同,则笔之粗细自异,画笔(如工具,规之与圆,矩之与方)要当随时应用耳。若必执规以画方,执矩并画圆,不亦痴乎?[8]
为成法所囿,必不能生发,下笔自然流入呆板。所谓“胶柱刻舟”,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于一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12]《吕氏春秋·察今》:“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13]皆执法不变,固守拘泥,乃“痴”者也。另一方面,“徒事临摹”,眼界自窄,纵临佳品,难究其源,以致任意涂抹,趋于狂怪造作:
世风愈降,人心日浮,凡事不肯深究,不下苦工,遂至任意挥洒,名曰写生,其实与真物相去甚远,甚且绝不相似,而又袭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论以自文其丑,至近吴缶翁出,学者无其笔力,以便于东涂西抹,无以丑怪纵横相尚,而花卉一道益不可问矣。[14]
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本是文人画独立之呼号,然无知俗匠反其为用,终至狂怪造作之地。松年《颐园论画》:“每有任情涂抹,名曰写生,实不肖形,竟称之为逸品,此等画误人不浅,不可为法也。”[11]如果说,“画一幅画用一种笔”,虽是“囿于成法,不知变通者”所为,而尚存一线古法的话,那因“不肯深究”而“任意挥洒”“以丑怪纵横相尚”这另一极端,最是害人误己。《鼎脔》第36期刊其《恽南田与吴缶翁》一文,不囿缶翁盛名,径评吴派花卉“用笔粗野,赋色丑俗”“满坑满谷,红绿纵横,观者亦多厌苦之”,指出其从学者用笔赋色“任情涂抹”之乱象,诚振聋发聩之言。[15]事实上,晚清画坛,赵之谦、吴昌硕引领风骚,然不失荒野村夫之讥,其从学者天资既乏,工夫难至,自更无论矣。
既知“徒事临摹”之弊,俞剑华遂进一步深入揭橥写生之要义,以正清明。一方面,他从纵向上梳理了中国画写生之学术渊源:
中国画之写生发源最早,象形文字之取材于自然物,固为写生画之滥觞。即唐宋以来之画家,主张写生,发明写生方法者,亦代有其人。如曰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如曰天闲十万匹皆吾师也,如曰外师造化内师心源,如曰山行遇树石之堪入画者当模记于册,如曰子久写虞山,如曰河阳窃真云,其他如徐黄之花鸟,在当时即名曰写生,至于韩马戴牛吴道子之人黄叔要之雉,无不逼肖真物,其为忠实之写生画,尚有疑问耶?[16]3
把中国画之写生追溯至象形文字,应该说是一个学术突破。清季金石大兴,小学昌炽,光绪二十五年(1899),殷墟甲骨应时出土,遂为学界迅速关注,但书画界反馈无多。就书法而言,其时不过罗振玉、简经纶数人以甲骨入书而已,于书学立论既少,于画学更鲜涉及。俞氏以“象形文字”立为“写生画之滥觞”,显然并不单纯是《易传》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哲学“观物”之说,而是带有字学、画学色彩的学理思辨。《历代名画记》卷一引颜延之语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17]俞氏内理,固三者兼而有之。写生渊源诚远,其道广被,因此他继而列举范中立、董其昌诸家之论,徐熙、黄公望诸家之行,韩干、戴嵩诸家之作厘证,说明中国画写生之道素有传统,自无疑义。另一方面,俞剑华从横向上指出中西写生共通与不同之点,同时揭橥中国画写生优渥之处。《颐园论画》“鬓云”章批跋:
中国画山水之云,多画山中云,无画山上云者,天空之云只以空白了之,此乃中国画讨巧处。偶尔于山上画云,反有添足著粪之虞。然按之实际,高山大岭,云气出没,自然山腰有云;如平台低坡,或山麓岗脚,只有烟雾,并无云气,即有云气,亦必在山顶之上。西洋画所画之风景,则十九于空中画云,一方面固由于写生不得不然,一方面亦由于天空着色,如只着蓝色,易流于板滞,不能不画云以为之调合也。此中西画不同之点。[18]
同自写生而来,中国画写山中之云,西洋画写山上之云,显属“形状”上不同之点,但这里俞氏并未就此断以优劣高下。事实上,俞氏嫌批跋道之未尽,另撰《中国画写生与西洋画写生不同之点》一文,从“用具”之繁简、“画者”之动静、“构图”之难易、“画幅”之增减、“形状”之似非、“精神”之肖否、“写照方法”之行立坐卧种种方面,区别中西写生之不同,而行文多所阐扬中国画写生优渥之点。如“用具方面,十分简单,不花额外设备”“至于方法,既不用地平线,亦不用消失点”“画者之位置,可以随意变动”“构图较为容易,远山看不见亦可于必要时画出,山中隐微处看不见,亦可以想象补足”诸言,俯拾即是。[16]要之,就临摹与写生之辩而言,俞剑华既诘责规模成法,“只知有古人,不知有造化”固陋保守之徒,又批驳“述典忘祖,舍己耘人”之流,明确指出,“如以造化为师,再参以古人成法,运以己意,自然可以日有进步”[19],发挥松年“两处贯通,融汇心手”学说,申扬传统奥义,观念显得持中秉正。
第二,辨“有我”与“无我”
“临摹”与“写生”,乃入门取法之两个面向;“有我”与“无我”,则与画家意识大有关系。松年《颐园论画》所倡“有我”,为其精蕴之学说。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按曰:“书中所论以画才之独创一格,处处有我,最为正确而大胆,足破临模家之惑。与石涛《画语录》之自己面貌,同为独到之见。”[6]337故其批跋亦承而扬之。《颐园论画》“山水”章曰:“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耳。”[20]俞剑华于兹阐发云:
彼以临摹古人为不二法门者,久已证无我相,只能为古人作牛马,作留声之器,作印刷机,终身无所成就。惟能处处不忘有我者,姑能作自我之表现,独抒己见,卓然成家即不成,亦不失其为独立。自等之我与奴颜婢膝之忘我者,固有上下床之别也。[21]
所谓“有我”,即“自等之我”,抽离点画,不囿于形,把精神意志运诸毫端,借淋漓翰墨,浇胸中块垒。“有我”之倡,石涛为最,俞氏生平,亦极重之。《鼎脔》第39期载其《四石之盛衰》一文,高许之曰:“石涛、石溪俱生于明末清初,痛故国之亡,隐于浮屠,天才横溢,不可端倪,而石涛之艺为尤多。然当时吴派方盛,王画遍天下,二师怀才不遇,世无知音,虽奉常有‘江南画以石师为第一’之言,然一齐众楚,殊不足以却积俗之见。且二师之画,面貌往往不可索解,殊与升平时代之意味不合,故石涛竟以所画册页一部,乞人布施一草棚而不可得。”[22]“面貌往往不可索解”云云,实际上是肯定石涛以时代悲怆摄入性灵之“有我”之画学实践,故俞氏批跋中阐释“有我”,更引石涛《画语录·变化章》进行厘证,主张不拘于俗,表现自我,坚持独创。
相反,“无我”者,其意识处处依傍古人,毫无独立人格,故最为俞氏所不齿:
画家因怠于自创,遂抚摹古人,渐至只知有古人,不知有我,而又终不能及古人,每况愈下,致中国画日见衰落,为世人所构病。[19]
公路桥梁是我国基础交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道路运行车辆的急剧增加使得人们对基础交通建设的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确保其施工过程的高效化管理势在必行。然而从管理实践来看,我国公路桥梁的质量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路面沉陷、桥梁裂缝等工程损害现象广泛存在。究其原因,公路桥梁病害的发生和养护及加固过程的不规范具有直接关系。基于此,进行深层次的公路桥梁养护及加固技术应用具有以下必要:
“无我”之意识,“以临摹古人为不二法门”,亦步亦趋,下笔必求合于古人,“怠于自创”,乃“奴颜婢膝之忘我”。从《颐园论画》批跋来看,俞剑华常以画家“有我”意识之有无,衡量画作之优劣高下,以冷眼观照画坛:从取法之逼仄,到点画之限困,继到性情之压抑,再到教学之桎梏,终到画坛之悲鸣,作为一个捍道者,对固倡“无我”、泯灭人性之庸师及其“无识之徒”痛加诘责,可谓大声疾呼。而批跋意犹未尽,又撰《描稿画家之金科玉律》一文刊于《鼎脔》第33期,列举故步自封者十条“金科玉律”,反讽“只知有古人,不知有自己,只知临成稿,不知创新稿”之“无我”之人,并直接指出其为“中国画道之不振”之“制命伤”,若“长此以往,国画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地”,诚忧心劳心者也。要之,由“徒事临摹”引申而来之“无我”意识,固守传统,不敢逾矩,此等画家,与“牛马”“留声之器”“印刷机”“奴隶”不二,要想“拯衰救弊”,就必须有敢为天下先之“有我”之士振臂高呼,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尚“生趣”与“精神”
从“写生”入,易得其“趣”;从“有我”出,故得其“神”。“趣”和“神”,是《颐园论画》批跋所反映出俞剑华最高之美学追求。俞氏有云:
所谓稿子手者,终身不能离稿子作一画,人趣且无,况天趣耶?[18]
每作画如誊旧账,千篇一律,生趣毫无。[19]
西画之写生,对于形状方面十分注意,结果每致呆板,毫无生趣。[16]3
这里俞氏提出了三个美学话语:“人趣”“生趣”“天趣”。“人趣”者,从古人画中得来:谢赫“六法”,朱景玄“四品”,本为评画准绳,然学者往往借之文丑,不下功夫,徒取捷径,流入怪异,欲直通幽关,“人趣”自不可得。“天趣”者,从万物造化中得来:泥古不知通变之人,不事写生,只持古画,落笔有本,徒知“誊旧账”,此种“稿子手”,“天趣”自不可得。关于“稿子手”,其含义正来源于松年:“从稿本入手,半生目不睹真花,纵到工细绝伦,笔墨生动,俗所称稿子手,非得天趣者也。”[23]童书业亦曰:“明代前期人特别讲究临仿,要使临仿的作品‘夺真’,浙派的戴进和吴派的沈周,都基本上是稿子手,专讲临仿。”[24]皆同一理。“生趣”者,从画师胸中得来:既知临摹古人,亦知师法造化,唯灵府无程,随世碌碌,下笔呆板因陈,殊无韵致,其中好为人师者,更使从学之人“汨其性灵,灭其生趣”[21],最是大恶。要之,俞剑华之论“趣”,合“人趣”“天趣”“生趣”为一,而更重“生趣”,非勉力苦学,师法自然,更育以胸次,无可至焉。
“神”,向为中国画之最高美学范畴。俞剑华云:
可以看到,俞氏之谓“神”,即“精神”,而且在形神二者不能兼得之情况下,宁舍“形状”而取“精神”。他把“气”与“神”并陈,或许更能增助理解:“喜作小幅者,宜时作大幅以摭其气;喜作大幅者,须时作小幅以敛其神”[25],“点苔坏,固足以败全幅之气势;点苔好,亦足以增全幅之精神”[8]。不难看出,“摭其气”与“敛其神”,败“气势”与增“精神”,大幅不至“粕野散漫”与小幅不至“柔弱堆累”,俞氏崇尚之“精神”,有着不激不厉、平正中和之特征。他《恽南田与吴缶翁》一文,把两个时代巨擘予以比较,指出“精神”因“无我”致败之由:
恽南田以后,便有许多孝子贤孙,必恭必敬崇拜而模仿之,造成所谓恽派花卉,渐至用笔柔弱,赋色艳丽,只学恽南田之面貌而遗其精神,终至描眉画眼,俗不可耐,而恽派大衰。吴缶翁现在亦有许多高足令徒,惟妙惟肖崇拜而模仿之,造成所谓吴派花卉,渐至用笔粗野,赋色丑俗,只取吴缶翁之面貌而遗其精神,终至东涂西抹,一塌糊涂,而吴派方大盛。[15]
俞氏看到,恽南田与吴缶翁之“孝子贤孙”“高足令徒”,毫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舍“有我”而就“无我”,不究乃师造化之源,“必恭必敬”“惟妙惟肖”地模仿,由恽南田之“雍容闲雅,秀润天成”,逐步沦为“柔弱”“艳丽”,由吴缶翁之“剑拔弩张,气势雄壮”,逐步沦为“粗野”“丑俗”。“画之俗不俗,固不在乎形之似不似也。”[14]无论是“描眉画眼”之俗,还是“东涂西抹”之野,之所以毫无“精神”,徒取“形状”,都是因为追随者“无我”之意识所致。因此,他认为,欲达到“形神兼备”,需自“有我”出:
观花之时或远或近,或上或下,花头如何,花叶如何,胸中先有一种花之观念,然后再观其全体之姿态如何,观察以后,默想其花叶之配合,章法之布置如何,终至眼前似另有一花,迎风含露,绰约向人,此时始含毫吮笔,如兔起鹘落,只画胸中之花,不画实物之花,画成自然神气充足,形状类似。[16]3
平日观其行立坐卧、歌呼谈笑之顷,以取其全神,摄特微始能形神具毕,具呼之欲出。[16]3
耐烦二字,不但为学画秘诀,实为万事成功之母。[26]
一方面,就画法而言,重在提物之“神”。若画人物,不必让人物静坐,而应于动静瞬间,把握人物表征,获取人物内理,如此,可“形神具毕”,“呼之欲出”。画花卉亦然,从观察、默想至濡毫作画,下笔“只画胸中之花,不画实物之花”,如此,可“神气充足,形状类似”。另一方面,就作画状态而言,重在养我之“神”。松年《颐园论画》有云:“画到精纯在耐烦,下帷攻苦不窥园,莫贪外物,保守真机,含养性元,此画山水之真诀也。”[27]确是至理。夫形体在物,神妙在人,所谓“人之巧,即天之巧”者也。故俞氏举松年“耐烦”一词,主张作画之道,当先治心,颐情养性,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以人之“神”摄物之“神”,方能达到不激不厉、平正中和之“精神”。要之,俞剑华之谓“有我”致“神”,并不故弄玄虚,在“有我”之哲学层面做文章,反是大道至简,在画法和作画状态之具体操作层面,表述清楚明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令人有章可依,读之不觉有操笔之想,所谓“平正通达”,差可至之。
三
有学者认为民国十七年(1928)发表的《国画通论》,是“俞剑华开始对古代画论的阅读的深入”[28],然从《颐园论画》批跋来看,则颇失之。松年《颐园论画》一书,本就体系严明,而俞氏不独揭橥是书奥义,更广取前贤画论,融铸百家,化而为我,已初步显示其自成一家之学术气象。事实上,俞氏批跋作于民国二十五年(1926),其时俞32岁,正是其精力弥满、学力雄强之时。从横向上考察《颐园论画》批跋及同时期俞氏文献,从纵向上梳理俞剑华画学思想流变,略可形成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颐园论画》批跋,标志着俞剑华学术取向彻底回归传统。据笔者调查,俞氏自民国五年(1916)发表《论师范生当注意略画》一文始,至民国十四年(1925)创办《翰墨缘》止,其间所发表《青岛博山写生旅行记》《美术教育的危机》等文10余篇,虽于诸学科皆有所涉,然学术重心尚在西洋画领域,几未见专论中国画者。《翰墨缘》载其撰文如《中国历代写生画家》《辟〈画理新诠〉》诸文,其学术观念呈现明确之传统取向,然略病散漫,缺乏体系。自《颐园论画》批跋之后,先后发表于《真善美》《美展》等杂志之《现代中国画坛之状况》(1928)、《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之研究》(1929)、《提倡中国画之理由》(1930)诸文,进一步发挥批跋之核心理论,逐步成为名重士林之中国画学家。当然,其学术取向之回归,不独与其对陈师曾画学文献之整理有关,还有其时画坛盲目西化之背景在:
社会习尚,学校教科,无不以西画为主,一时西画之兴,风起云涌,而中国画益复不振。[16]3
近来浅学之士,一知半解,便据西洋画之方法批评中国画,斥中国画为不合理。[29]
故而读其批跋,不难体会其因矫枉必须过正而表现之强烈的论辩色彩。需知,俞氏之所以以激烈言辞批驳中国画坛,实际上旨在正本清源。再以写生为例,俞氏有云:“一二浮浅者流,因西画之输入,以为西画必须从写生入手,遂痛诋中国画无写生。”对此时弊,俞剑华从学术角度分析曰,“西洋画必受视点之限制,受地平线之约束,受光线之管辖,受透视之束缚”,“在画幅上,(西洋画)远处须有山始美观,如为当时画者所不能见,则恐以艺术叛徒之胆力,亦将逡巡退缩不敢贸然加入,以贻不忠实之讥”,“(西方写照家)主张肃衣冠,正瞻视,屏气息,呆若木鸡之画法”,而前引“易流于板滞”“每致呆板,毫无生趣”种种,皆是对西洋画写生针砭之言。[16]从反证角度上,亦就对醉心西风之士作了严厉批判,其苦心孤诣匡扶道统之学术取向,自可想见耳。
第二,《颐园论画》批跋,体现了俞剑华卓越之中国画史识。刘知几倡史有三长之说,而尤重在识。梁启超解云:“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他指出,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继而标以四义:由全部至局部,由局部至全部,勿为传统思想所蔽,勿为成见所蔽。[30]观夫俞氏史识,承自乃师,而多所自得。《颐园论画》“人物”章批跋云:
画道之兴,必先人物而后山水,山水既兴,人物遂衰,无论中西,如出一辙,或亦运会使然与?[14]
事实上,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屡有运用此种史观,其《清代山水之派别》云:“我国之画,汉以前多尚人物,逮至六朝,山水始肇其端,然为人物之点缀,尚不能蔚然自立。及唐王维、李思训辈出,山水之画,于焉乃昌。方之欧洲,亦同斯例。试观希腊、罗马以及中世之美术,皆以人物著称,洎夫十七世纪,英法画始有山水。然则山水画之后起,中西竟有相同,殆亦有自然趋势耶?”[31]是知,俞氏画道兴衰之观念,素有所本。民国十八年(1929),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梓行,作为“开画学通史之先河”[32]者,是书所附“历代各种绘画盛衰比例表”,就山水、花鸟、人物、台阁、龙水诸画种之兴衰,谱之甚明,而其史观,亦自陈、俞而来,可谓薪火相递者也。[33]至于画派之兴衰,俞氏《恽南田与吴缶翁》揭示曰:
有天才之画家,鉴于当时画界之堕落,另创一派,思有以拯衰救弊,其初必受一般人之卑视诋骂,渐至画法成立,遂有许多人起而仿效,而新画派以成。画派最盛之时,亦即其将衰落之时,因效者日多,真才遂少,只袭拟皮毛,无独创之能力,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救药。而具天才者,又另谋新派之建设矣,互为盛衰,互为起伏,无论古今中外,无不皆然。[15]
俞氏指出,“真才”之有无,是画派盛衰之关键因素。“真才”者,绝不因循守旧,在既有格局之下讨生活,而是具有“独创之能力”,在画派“堕落”之时,能“拯衰救弊”,易帜奋起,在画派初建之时,能忍辱负重,坚守正道。换言之,其所谓“真才”,亦即前述之“有我”之人。松年《颐园论画》曰:“此等境界,全在有才。才者何?卓识高见,直超古人之上,别创一格也,能创方谓之画才。”[20]皆同是理。要之,无论画种抑或画派之盛衰,俞氏皆以其敏锐之洞察力,博综先贤学说,能于乱象之中,窥见历史之内在脉络,确可谓优秀之中国画史家。当然,其宏阔之史识在其后所著《中国绘画史》中畅发挥运,播芳至今,此不赘焉。
第三,《颐园论画》批跋,体现了俞剑华缜密之画论分类意识。作为中国古代画论分类集大成之学者,俞氏分类方法有两种:一是丛书型:依文献类别收载原书,属画论汇编,《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是也;一是类书型:按性质采摭,随类相编排,“区分胪列,靡所不载”,属画论辑成,《中国画论类编》是也。从前述《颐园论画》版本系统而知,“俞氏批跋本”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一为单行本,一为丛书本,均经俞氏调和整理,各章皆标以“节名”,带有类书型分类之性质,故颇值比较。二本章目:
俞氏批跋本:小引、山水、人物、花卉、竹兰、画山、画水、鬓云、画石、画花、点苔、用笔、用墨、用水、设色、工笔、写意、临抚、目见、秘戏、画诀、制粉、辨纸绢、人品、渐进、择师、教画、读画、评画、论古画、辨家、真赝、神静、成名、成家、返约、重名、繁简、工细、忌讳、结论章。
《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画才、学力、自然、苦工、养气、学问、实学、明师、画品、三变、品节、敦行、避忌、合俗、人物、工笔、写意、画诀、笔墨水、皴法、天气、画水、点苔、临橅、纸绢、漂粉、鉴藏、花卉、中西、返本、结论。
松年稿本前半部分列25章,后逐以增订,终近半之篇幅未亲拟题名。俞氏二本之整理,相距12年而无承传关系,故差异甚夥。兹略举两例,以窥其分类之异同。《颐园论画》稿本“山水”章,俞氏批跋本据此仍作“山水”,而《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作“画才”。按,是章从“天地之大,万物挺生,山川起伏,草木繁兴”始,至“必须造化在手,心运无穷,独创一家,斯为上品”止,由客观之山水物象起兴,力倡主观“画才”之要。从校勘学看,俞氏批跋本忠实底本,不轻作改易,确有佳处;从开篇立论看,《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摄炼文意,别作“节名”,诚亦优者。《颐园论画》俞氏批跋本“渐进”章,《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作“自然”。按,是章稿本未拟题名,二本皆为俞氏所加。观夫松年所论,少年不必“力求苍老”,妇女仍须“秀润典雅”,贵在适宜,不可逆性。由此拟题,“渐进”“自然”皆合符节,未可轩轾。唯“自然”一词,亦有师法造化等广泛之意义,稍令人模棱难辨。事实上,就文献从属与章节性质而言,无论何种分类之法,严格来讲并无高下分别,正如俞氏《中国历代画论大观》凡例云:“惟中国书籍,不能严格分类,兹不过取其大略以便排列而已。”[4]2《中国画论类编》卷首语亦曰:“中国古籍,一时难加以科学之分类,兹仅略为区分,彼此混同之处尚多。”[6]3非经甘苦,无由道之,诚为知者良言。也正因如此,俞氏批跋本《颐园论画》,从画理、画法、画评到画鉴,对是书进行了详明整理,体现了其缜密之画论分类意识,为此后其中国画论分类体系之蔚为大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山东“骚坛树帜者”[34],松年《颐园论画》,向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古典画论之终结,具有重要之文献价值。俞剑华虽“未能亲接謦欬”,但作为私淑弟子,基本上继承了松年之画学观念,且根据时代,作出了新的阐释,具有鲜明之学术特色。同时,俞氏以卓越之中国画史识、缜密之画论分类意识,借其犀锐凌厉之文风,针砭时弊,匡扶道统,洵乃一时画坛激流,声名益重。而批跋所反映出的俞氏早期中国画学,虽未能臻于深境,然就中主要观点,皆成为其生平画学理论之核心学说,在此后的诸多文章和著作中,为其进一步挥运发覆并泽被久远,终成广大教化主,故应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注释:
①王修《陈师曾遗刻》跋云:“陈师曾先生,为愚夫妇治印,逮十余事。前岁姚茫父公诸先生,集印先生遗印,为《染仓室印存》,愚夫妇适南旋,所有印因不得与。今布于此,聊慰未得附名册末之憾耳。”参见王修《〈陈师曾遗刻〉跋》,《鼎脔》1926年第10期,第3页。
②是序《画论丛刊》本、《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本,皆据俞氏石印本作《颐园论画跋》,且“暇日更取原书重加校定,变其前后次序,正其一二字句,并于每章之后,附知拙见。非敢好事续貂,以发挥余蕴自诩,乃由于景仰前贤不能自已耳。书既成,略”一段文字,诸本皆无,当为俞氏刊于《鼎脔》时所加。参见俞剑华《颐园论画序》,《鼎脔》,1926年第30期,第3页。
③据笔者推测,一方面,俞剑华批跋刊发《鼎脔》后,应未自留底稿,故此后其对《颐园论画》的两次整理,皆鲜有此批跋本之学术痕迹。另一方面,因《鼎脔》周刊发行量小,所获不易,学界自然难以深入体察。因此,从文献来看,俞氏本人著作不下千万言,然于兹未着片言;周积寅编《俞剑华年谱》《俞剑华美术论文选》,俞述翰、谢巍、林树中编《俞剑华教授著作》,徐建融、刘毅强编《海派书画文献汇编》等,皆失收是作;而诸研究文章、论著,亦未言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