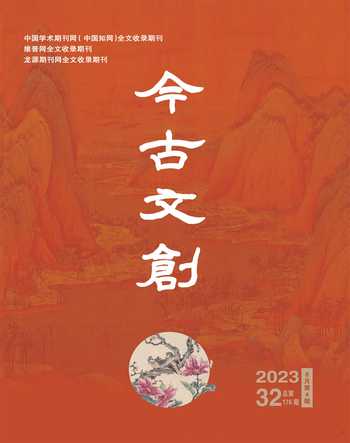从“ 他者”到反“ 他者 ”:托妮 · 莫里森小说中的树林空间书写
【摘要】空间是人类一种相对稳定的知觉图示系统,空间是托妮·莫里森小说书写的重點之一。在莫里森的11部长篇小说中,树林空间被注入原始想象的力量,阐释了美国社会中黑人种族和黑人女性主体性的丧失、主体性的重建以及走向反“他者”的努力。树林空间的书写反映出莫里森对黑人百年心态转变的深刻体察,旨在揭示黑人突破种族和两性关系中存在的主客对立的思想,寻求种族和两性和谐状态。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树林空间;“他者”;反“他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32-005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16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在21世纪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研究莫里森的方法也从21世纪前简单的作品介绍、主题分析走向了多元化的趋势。20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重要的“空间转向”,1967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空间的时代”。[1]“空间转向”为解读莫里森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角度。国内首篇从空间理论入手解读莫里森作品的学术论文是都岚岚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此论文给予国内莫里森研究者重要启示,为解读莫里森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点。但目前国内关于莫里森作品中的空间解读多局限于单一作品,缺乏总体观照和宏观视野。莫里森一生共写就11部长篇小说,纵观这11部长篇小说,从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到最后一部小说《孩子的愤怒》,每部都有树林空间的细致刻画。树林空间作为莫里森空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她审视黑人生存状态的重要场所,蕴涵了深沉的种族意识,表现出黑人从“他者”走向反“他者”的努力。本研究意图从整体上将莫里森作品中的树林空间作为重要窗口,揭示莫里森对当代黑人突破“他者编码”生存困境的思考探索。
一、“他者”空间:作为主体性丧失地的树林
莫里森通过树林空间的书写再现“他者”主体性的沦落。“他者”表示一种与主体相对的从属的、受压迫的、边缘的地位。树林空间是莫里森小说中一个典型的自然空间,莫里森在此将其与黑人族群和黑人女性的生存地位和生命状态等同,形成三位一体,再现了黑人族群与黑人女性同为“他者”的事实。
首先,莫里森在小说中将树林与黑人族群等同,将树性与黑人性交织于一体,形成“树人”他者群体。在《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的父亲为其取名时“就挑了一组他看着挺有劲和挺神气的字母”,因为他“觉得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2]《柏油娃娃》中,莫里森更是直接描写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黑人的头发总是鲜活的。即使不去梳理也像叶簇,远远望去,绝不亚于一株落叶乔木的树冠。”[3]在此莫里森建构了树与黑人的同一性,将黑人的生命用树林隐喻化。这种隐喻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莫里森的种族性,来源于其黑人民族文化基因。在非洲传统宗教中,自然崇拜是最初的形态,“树也被非洲黑人认为是神圣的,他们相信所有的树都有灵魂”[4],树常以生命的象征出现。此种隐喻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莫里森对社会环境的体察理解,在其非虚构作品《在黑暗中游戏》中,莫里森写道:“如果挂着‘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果实的树是被迫充当自由对立面的黑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棵树上提取出相当多的果汁:当个人主义的背景是刻板的、强制的依赖时,它就显得突出(并被相信)。”[5]由此观之,莫里森认为黑人是社会之“树”,而从树上结出的果实是社会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莫里森认为通过建构“非洲主义”形而上的必要性,从而鼓吹以白人为中心的主流思想是践踏黑人主体性所取得的成果,非裔黑人就像树一样为其结出丰硕果实。莫里森的这一观点为其文本中树人比喻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莫里森树人同一性的书写奠定了小说再现树人他者性事实的基调,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便构建了“邪恶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6]的暴力剥削景观,再现了黑人被白人残酷客体化的事实。《所罗门之歌》中,麦肯·戴德一世被白人枪杀于十英亩处女林的栅栏上。后来吉他也描述了这样一幅画:“一些白种母亲抱着她们的孩子,好让孩子看到一些黑种男人在一棵树上给活活烧死。”[2]176在莫里森的后期作品《家》中,一个姓克劳福德的老人坐在自己家门廊上,拒绝听从白人的指令搬离,于是他被白人用钢管和枪托打死,捆在县里最老的那棵木兰树上。在树林中被枪杀、被烧死,黑人终究难逃被宰割的命运。自1619年,非洲黑人踏上北美海岸始,黑人仅仅只是白人奴隶主“想要的财产”,并无人权。奴隶制时期、南方重建时期、种族隔离时期以及全球化时期都有无数黑人被白人处以私刑。对于黑人的生存处境,莫里森通过树林与黑人同一的物化地位,发出了尖锐的询问。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大规模扩张使得包括树林在内的自然环境逐渐丧失自身的主体性,沦为人类的“他者”。在莫里森的小说世界里,加勒比海上骑士岛原始的雨林景观遭到破坏,白人富豪在岛上建起了极具讽刺色彩的豪宅“十字树林”,“树林”在此丧失了生命力而成为冷漠文明的现代建筑的代词。农场主雅各布坚持修建的第三栋住宅,牺牲了五十棵树。莫里森在《柏油娃娃》中透过“儿子”的视角感慨道“大西洋铅灰色的波涛在文明的手掌中已经变成了什么。”[3]232莫里森作为一名非裔作家,在其小说中将黑人种族和树林空间的他者化相联系,通过树林空间书写再现了黑人成为白人客体的事实。
在莫里森通过树林空间展现的他者性事实中,黑人女性与树林的关系无疑更为密切。莫里森在其小说中建构了黑人女性与树林空间的共生关系。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佩科拉在树丛中经历月经初潮,完成从女孩到女性的转变。露丝在常青树下将奶娃哺乳到13岁,这也成为“奶娃”其名的由来。塞丝逃亡路上在林中小屋中生下丹芙。乔去往被木槿树包围的洞口寻找断断续续唱歌的母亲。在大量的描写中,树林是女性行经、怀孕、哺乳的重要场所。荣格学者埃利希·诺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中从女性被表现为物的神话中总结出了“母性”的普遍经验,树是其中母性表现的一种形式。诺伊曼在本书中写道:“女神作为供给灵魂营养的树、作为无花果树或枣椰树,是埃及艺术中主要的形象之一。但树的母亲身份不仅在于营养;还包括养育后代。”[7]从神话原型的角度看,树与生殖、营养和变形的原型女性相等同,莫里森也曾在1980年与安妮·柯宁的访谈中说道:“这个人奶娃,必须走进地球——子宫——在那个洞穴里,然后他在地球表面行走,他能感觉到它的树木—这都是非常母性的。”[8]莫里森在此建立起了树林与女性的同一性。
黑人女性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不仅遭受到白人的欺凌,还受到来自黑人男性的霸權,成为他者的他者。通过树林与女性的同一性描写莫里森进一步展现了黑人女性他者的生存状态。在《柏油娃娃》中,“儿子”对糖果商瓦莱里安说:“我对植物可是很内行的,它们像女人一样,你得不时地往上捋顺一下,让她们举止端庄,像她们应该的那样。”[3]153“儿子”的这句话体现出黑人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他们认为女性就像瓦莱里安的植物一样,是被男性摆布奴役的对象,女性是没有自主性的。在与吉丁的出逃中,“儿子”一直渴望带吉丁回到家乡埃罗,虽然他在与吉丁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但他想控制吉丁的欲望从未改变。吉丁这一女性形象,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白人糖果商瓦莱里安的资助,逐渐认同白人主流价值观念,成为瓦莱里安改造的完美产物。在吉丁与“儿子”相恋后,她又受到来自黑人男性的束缚,迫使她行使贤妻良母的职责,吉丁的一生都处于他者的地位中。通过植物空间对黑人女性地位的描写在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已经萌芽。黑人男性乔利的初次性爱是一次苦涩又惨痛的经历。在弥漫着葡萄味的松树林里,两名白人像看动物一样观看乔利和达莲娜。白人“手电筒的光”就像一把钢刀狠狠地插入乔利的心脏,杀死了乔利的男性尊严。莫里森通过这一情节书写表现出白人眼里黑人的“玩物性”,以及白人如何粗暴地将黑人完全置于客体化地位。然而在这一情节中,“达莲娜”更是不容忽视的,在整个过程中,达莲娜不仅受到来自白人的侮辱,还受到乔利的欺凌。松树林中,白人——黑人男性——黑人女性形成了一条逐层递减的“他者化”链条,而黑人女性处于这个链条的最底层,成为他者的他者。作为黑人女性作家的莫里森,在其小说中对黑人女性生存地位的这一描写无疑是感同身受且深刻的。
二、主体性空间:作为主体性重塑地的树林
莫里森通过树林空间的书写展现了“他者”主体性的重塑。树林空间一定程度上成为黑人群体和黑人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地。空间叙事学研究者龙迪勇在他的《空间叙事学》一书中写道:“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记忆的易逝性,以及以传统方法塑造人物形象的朦胧性,所以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天才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才有意无意地想到了空间或‘地方的具体性与相对固定性。而空间或‘地方,也确实与‘人之所以成为‘某人的‘自我或‘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9]在莫里森的小说中,这种主体性的建构与树林空间为黑人个体提供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有关。
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0]安全感是心理需要中的第一要素,是完善自我主体性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宠儿》的主人公丹芙拥有林中一间两米多高的“祖母绿密室”,这片黄杨树林先是一间游戏室,然后是个避难所,再过不久,其本身就成了目的地。在这里,丹芙与受伤的世界彻底隔绝。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虽然名义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南方重建的失败使得黑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在“一百二十四号”,塞丝饱受被“学校老师”蹂躏和亲手杀死女儿的痛苦记忆的折磨。鬼魂在这间房子里一刻不消停。保罗·D的造访又一次将塞丝拉入回忆泥潭。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丹芙感到不安,她被孤独苦苦地纠缠,只有“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她感到成熟、清醒,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11]。树林空间在此处将丹芙与外界隔绝,为丹芙提供庇护,给予其自我建设所需的安全感。南北战争之前,非裔美国黑人是白人奴隶主的奴隶,他们长期生活在被毒打被迫害的恐惧中,而南北战争之后黑人的社会处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黑人个体早已丧生了生存所需的安全感。莫里森的树林空间书写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一关于黑人生存状态的严重问题,黑人无法在社会语境下得到安全,只好寻求于“树林”的庇护。
在心理学上,安全感总是连通着归属感,寻找归属感是完善自我主体性的重要形式。寻根需求是人类寻求归属感最典型的形式,莫里森在小说中源于人物安全需要建立的树林空间成为人物寻根的物质载体。《家》中的老人克劳福德在白人的围追堵截中拒绝逃亡,被人用钢管和枪托打死。死后被捆在他曾祖母亲手种下的木兰树上。弗兰克和茜曾经那么痛恨家乡洛特斯,可是蹲在那棵月桂树下,洛特斯看起来既清新又古老,既能给人安全感又能满足他们对回家的渴求。莫里森在《天堂》中写到主人公寻求的这种“根性”实际上是“非洲性”。原始非洲高温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林木的生长,这使得非洲树林资源丰富,形成大片热带雨林。此外,非洲闭塞的地理环境和高温的气候条件使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远离外部世界的侵扰,在世界地理中形成一种“孤岛状态”,因此非洲具有保留原始时代的自然地理特征的条件。意象基本上是空间性的,在此处作为非洲地理意象符号的树林,带给非裔黑人的是来自远古故乡的声音,这成为其在美国社会重建主体性的重要载体。
在莫里森的文本语境中,尤其注重黑人女性主体性的重建。《秀拉》是一部描述女性自我成长的小说,主人公秀拉是莫里森笔下一个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秀拉叛逆、独立、危险与奈尔形成鲜明对比,秀拉不认同“底层”地区黑人的生存逻辑与价值观念,毅然决然决定去往大都市。在秀拉临死前,她对前来探望她的奈尔说道:“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衫那样倒下。我确实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12]在秀拉看来。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就像被伐过的“树桩”,终生都在为别人忙碌服务,没有主体性。而她自己虽然看起来危险,但有自己的处事准则,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她有属于自己的理想、情感和价值。在临死之际她通过“红衫”树进行比喻,表明自己建立起了自身的主体性。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笔下的女性人物多与自然有直接的联系,又如《所罗门之歌》中的派拉特身上就具有森林的味道。
三、反“他者”空间:作为主客对调地的树林
反“他者”是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消解,莫里森借助树林空间叙事表明自己反“他者”的文化态度。
首先,莫里森通过树林空间表现黑人反“他者”的态度。《天堂》是莫里森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天堂》中莫里森刻画了“鲁比镇”这一树林空间,小说主人公之一迪肯·摩根在二十年前曾在镇上中心街每隔十五米种一棵树,故在一定程度上鲁比镇是一个自然树林空间。在鲁比镇这一社区空间中,存在一种“黑皮肤至上”主义。鲁比镇在重建之前叫作黑文镇,黑文镇在向南流亡的过程中受到白人的歧视拒绝,所以在重建后,鲁比镇尤其排斥白人,任何白人都不能在鲁比镇居住,甚至浅肤色黑人也会受到拒斥。由此可见,在鲁比镇这一社区系统中,黑人成为社区中心权威,而白人却成为“他者”,这一树林封闭空间,成为黑人反“他者”的形式。在另一部小说《柏油娃娃》中莫里森同样做出了类似思考。《柏油娃娃》的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骑士岛一栋叫作“十字树林”的建筑中,在这座豪宅内,只有男女主人是白人,其余的奴仆均是黑人,这是一个黑人多白人少的封闭空间,白人需要黑人的伺候才能生活。在一次聚会时,女主人玛格丽特与女仆昂丁发生争执,昂丁历数玛格丽特的罪恶,主奴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男主人瓦莱里安让黑人退下时,他感到这群黑人“像灌木和树木一样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俩还留在枝形吊灯的光亮之中。”[3]244这一刻,在这座冷漠的现代建筑里,黑人的价值观成为中心。萨义德曾在《东方学》一书中提道:“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这样,本来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13]莫里森笔下的封闭树林空间,通过黑人群体寓于其中的行动从而获得反“他者”生存状态的意义。莫里森对黑人族群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的观察是具有洞见的,莫里森认为在种族熔炉的现实情况下,“唯一的公分母是黑人”[8]256,黑人是毫无疑问的“他者”。将黑人他者化并延伸至排斥非洲主义的做法莫里森认为是一种策略,用来隐藏和缓冲阶级矛盾,防止其他类型的真正的冲突。所以莫里森在小说中营造了“鲁比镇”这样一种黑人中心社区,以此来抨击整个社会对黑人“他者”的利用,但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森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小说中鲁比镇最后也面临堕落的潜在危机,“十字树林”中的主仆还是生活在一起。由此观之,莫里森并不主张“极端种族主义”,她所做的是解构一直站主流地位的二元对立思想,对基于肤色之上的黑白种族冲突进行新的反思与尝试。她在《在黑暗中游戏》中提到她的计划是努力将批判的目光从种族客体转移到种族主体,确立黑人与白人同等的种族主体地位,寻求文化的多元发展。
同样,莫里森通过樹林空间描写黑人女性反“他者”的意识。《天堂》中,多薇经常一个人去圣马太街一栋种满树木的小房子内,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远离了鲁比镇的喧哗和丈夫斯图亚特的命令。这是多薇反抗琐屑的家庭生活逃离斯图亚特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多薇反抗鲁比镇男权中心主义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树林空间与女性反“他者”的联系,莫里森在《恩惠》中做了更直接的描写。当莉娜企图告诉佛罗伦斯,她只是铁匠树上的一片叶子时,佛罗伦斯摇摇头答道:“不,我是他的树。”[14]在美国文学史上,黑人女性大多是克莱伊大婶的形象,她们是白人家庭忠心耿耿的保姆,同时还要受到黑人男性的欺凌,黑人女性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端。莫里森在小说中描绘了这一现象,但更重要的是莫里森对此做出了反叛性的思考。然而莫里森反对男性中心的意识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莫里森在访谈中说道:“只有男性与女性的平衡才能产生完整的人。”[8]107由此可见,莫里森对于女性反“他者”的书写旨在寻求的是两性的和谐发展,而不是非此即彼。
莫里森基于树林空间书写所折射出的黑人反“他者”的意识,并没有延伸成为一种极端的种族策略。虽然“莫里森本人总是自豪地把自己描绘成一棵深深植根于古老民间文化中的黑人自信和自我定义的古树上的树枝”[8]Ⅷ,但莫里森的书写仍只是旨在复原黑人种族自身的主体性,探索黑人种族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寻求种族和两性的和谐发展。
三、结语
“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9]60莫里森小说中的树林空间,连接着黑人的心灵,贯通了黑人的生存。它不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容纳黑人族群尤其是黑人女性思想情感的“场所”,体现出两者从“他者”走向反“他者”的努力。从运送奴隶的“中间通道”到奴隶制被取缔百年后的民权运动,莫里森对黑人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深刻思考,其对黑人心态转变所做的书写,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塔利.空间性[M].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4.
[2]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19.
[3]托妮·莫里森.柏油娃娃[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7.
[4]汝信,艾周昌.非洲黑人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53.
[5]Toni 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M].NewYork:Random House, 1993:64.
[6]托妮·莫里森.天堂[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8.
[7]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48.
[8]Danille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76.
[9]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60.
[10]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M].李伯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765.
[11]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34.
[12]托妮·莫里森.秀拉[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155.
[13]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1.
[14]托妮·莫里森.恩惠[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66.
作者简介:
卢禹君,女,山东青岛人,河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主要从事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