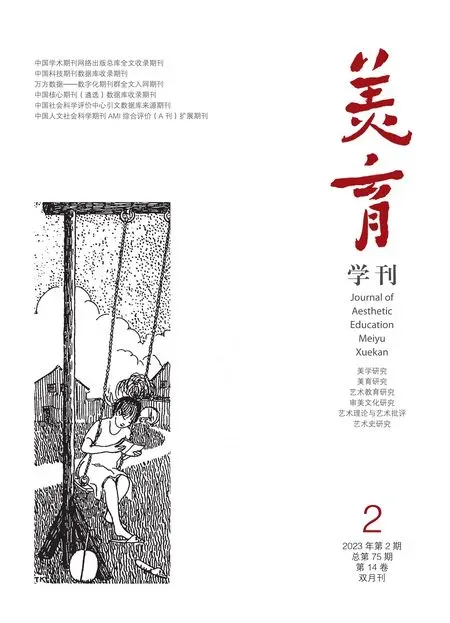“象罔”:从思维范式到美学范畴
张子尧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庄子·天地》“象罔得珠”寓言中提到,黄帝因遗失玄珠,让智慧的“知”、能明察秋毫的“离朱”、能言善辩的“喫诟”去寻找而无果,最后“象罔”得珠。道家语境中“玄珠”是“道”的象征。寓言在讲思虑、感官、言辩都无法得“道”,唯有“象罔”可得。学界已从“道”的特征、得“道”主体的精神特征等方面对“象罔”进行界定,认识到其非有非无、不皦不昧、绝思虑声色等哲学特征。“象罔”具有寓言人名以及理论术语双重身份,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触及言与意、文和质等复杂哲学命题,其内涵值得继续挖掘。它接续了《周易》“象”思维范式的传统,其缠绕多解的构词方式使其在历代思想语境中意义不断生成,并具有极大的美学阐释空间。在历代思想语境中,“象罔”意义如何演变?其由思维范式到美学范畴,逻辑演进理路为何?“象罔”之美学意蕴何在?本文拟探讨之。
一、作为思维范式的“象罔”
《南华真经疏序》云:“夫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窅冥……实象外之微言者也。”“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1]1同老子一样,庄子也思考“道”“无为”等形而上范畴,其内容绵邈精深,难以理解。基于此,他们放弃了逻辑、命题等“正底方法”,而采用“负底方法”(1)真正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而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而上学不能讲……用负底方法讲形而上学者,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讲。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0-150页。进行反向或否定言说,如“道常无名”“物物者非物”等。但有时无论正的方法还是负的方法都无法准确表达其言说内容,于是庄子便借助寓言形象。《说文解字》说:“寓,寄也。”[2]148“寄”决定了寓言的结构特征,即由表层的“象”与深层的“意”构成,寓言无法脱离“象”。而对“形象”的把握和重视肇始于原始先民的“象”思维之中。作为传统思维范式,它可从三方面理解。首先,抽象概括具体事物的类本质特征以指涉该物,即“物—象”,如《韩非子·解老》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3]148《左传·宣公三年》中:“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4]“铸鼎象物”即将外物象征化、图形化以便人们认识,因此“象”具有博物学、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人们不仅用“象”来象征外物,也常以“象”言“理”明“道”,即“道—象”,如老子用“玄牝”“橐龠”“水”等物象言说大道,《周易》以“鸣鹤在阴”“飞龙在天”等象辞预卜吉凶。其次,将图示化的“象”进一步抽象并分类、整理成符号或图式,即“象—文”,如《周易·系辞下》:“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图文八卦即代表着世间一切物象的抽象形式。《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2]316笔画亦是对物象抽象的指称和概括。而世间现象纷繁复杂,要有更为繁复的符号与其相配,更为细密的六十四卦以及由笔画构成的文字便应运而生。再次,“象”“文”的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超越世界,超越表象以领会现象背后的“意”或“天命”,即“象—意”,如《庄子》强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道德经》中老子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超验世界的神往等,均体现出思想家们对“象”的工具性、有限性的认知。因此,刘成纪认为,“象”作为一种思维的意义得到彰显,它像概念思维一样,均属于要达至对事物真知的认识[5]。
庄子借“象罔”之隐喻告诉世人要关注他所营构的“象”。“象”即有,“罔”即无。在老庄的哲学语境之中,“罔”又指向了一种抽象的本体性质的存在,它无常、无状、无形,超越经验感知,需要借“象”思维来把握,“象罔”即“以象达罔”,指向了探求真理的过程。具体而言,“象”即《庄子》寓言中纷繁复杂的形象,“罔”则是寓于其上的、希冀世人理解的大道。“象”思维方式取消了概念讲述或逻辑演绎给人带来的压迫感,而使之易于接受。于是壶子、鲲鹏、蝴蝶等各类形象都以生机活泛的姿态在场言说、对话、行动,它们都是表现“罔”的手段。
“象罔”所蕴含的思维范式指向的是“象—言—意”关系的哲学命题,可以理解为象和言在旨归上都是为了达意,亦可认为言构筑象,象以寓意。三者间的复杂内涵在其后的发展中又有新的理论延续。《淮南子·说山训》:“《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明理舍象”是对庄子“得意忘言”的继承。汉代“今古文之争”背景下,“象”思维范式又成为今文学家解经的理论依据,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提出的“辞不能及,皆在于指”[6]48和“见其指者,不任其辞”[6]49命题,不同于古文经学拘泥于文字考订训诂,董仲舒突破了“辞”对“指(旨)”的限定,重辞又超越其辞,凸显了经学的阐释价值,这种“《诗》无达诂”的理论为后学从经典出发解释世界提供了无限可能。汉代王充《论衡》中又将“意”与“象”缀合成词:“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意取名也。”可见,第一,“象”是无道诸侯的影射,射“象”即诛无道;第二,“意”对应礼法和等级观念,“象”不同,对应的身份、等级不同;第三,箭靶之图象与射箭之过程成为礼的承载,这是“意象”在政治伦理上的彰显与运用。“象”思维智慧在魏晋玄学语境下继续深化,魏王弼将其视为方法论,并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7]重新整合并创新前代思想资源,将“言”引入“意—象”之中且明晰三者关系,充分肯定言辞对“象”的捕捉与彰显,可视为文艺领域“意象”说的哲学根基。
从内在理路上讲,哲道难言,情意亦难说,故“象”不仅是言说抽象哲理的手段,亦可作为表情达意的方式。《庄子·杂篇·寓言》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1]494在徐复观看来,卮言、重言,皆广义的寓言,“这种话的本质是诗性的,所以其表现而为文章,自然也和诗一样,多采取比喻及象征的形式”[8],寓言与诗歌在形象性上具有相通之处。从文艺视角来看,“象罔”之“象”则成了内心营构之象,“罔”是朦胧复杂的内心情感状态,章学诚提到:“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9]自然之象为于人毫无关涉的自然之物,营构之象是观照人类精神世界的审美物象。而“意象”作为美学范畴从政治领域进入文艺领域,是在六朝时期。此阶段属文学自觉期,亦是审美理论大发展之阶段。刘勰对“意象”的表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10]相对于王充的政治象征性的“意象”,刘勰做了两方面的置换:首先,他将“意”的内容由政治伦理置换为个体情思,突显个性情感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进一步将“情”从汉代的“志”中解放出来;其次,他将“象”从符号图像转化为审美物象,由此,“象”由“卦象”“图像”之“象”扩展为一切摄入人心的、能够触发审美情感的物象。刘勰《神思》篇中的“意象”还是“意中之象”,尚未行诸笔端,处在“心中之竹”的阶段。后世“意象”范围扩大,溢出“心中之象”范围,完成于作品中的可感可触之“形象”亦可称“意象”,如明王廷相曰:“诗贵意象莹透,不喜事实粘着。”[11]清沈德潜评价孟郊诗“意象孤峻”[12],这意味着明清之际“意象”已成为公认的诗歌批评术语,亦可看出“象”思维对文艺创作的强大辐射能力。除“意象”外,直接与“象”思维相通的文论术语还有“兴象”“气象”,唐代殷璠论诗常标举“兴象”,强调将内心之“罔”的模糊性、丰富性与外在之“象”的生动性、鲜明性契合为一,形成一种情景交融、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亦与王昌龄的“意境”说相通。南宋严羽将“气象”列为诗之五法之一:“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3]以生命之“气”代指“罔”,特指厚重的精神境界与思想内容,与之相配的“象”也要求博大壮观,具有宏阔之美。
因此,如何观物,如何取象,如何达意,以及物与心、心与象之复杂互动关系成为文艺的重要话题。人心在情感或外物的感召之下,将“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14]56纳入心中,在心与物游、情与物动之中,情与景融合,然后“窥意象而运斤”,以语言、音律、水墨、五彩等不同的艺术媒介加以呈现,所以“意象”即作品之灵魂。胡应麟《诗薮》称:“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5]作者借“象”以抒心中之块垒。“罔”寂然不动,“象”则迁转无穷,一“罔”可寓于多“象”,所谓:“神道无方,触像而寄。”[16]如庄子借泉涸之鱼、曳尾之龟、“鼓盆而歌”等多个形象来申说生死之大道,因得“道”之难,故庄子师自然,取象万物,虫鸣鸟叫,鸢飞兽走,均可入象。另外,一“象”亦可寓多“罔”,“象”又向持有不同理念的阐释主体敞开。关于《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和“蜩与学鸠”的形象,西晋郭象从“适性逍遥”出发解释为“小大虽殊,逍遥一也”。[17]10东晋支遁从佛教波若义理出发,释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17]1。审美效果的达成就在多重复调之“象”与作者、读者内心之“罔”的互涉,“象罔”所涉及的理论内涵包含设谜与解谜、编码与解码。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象”的创造性运用使得《庄子》具有了多重阐释维度,它不仅是哲学文本,亦是能彰显无限艺术精神的美学文本。
综上,“象罔”之“以象达罔”意含,代表着庄子对“象”思维范式的总结,开启了后世对“象—言—意”命题的哲学思考,“罔”在内容上实现了从“哲理”到“政治”再到“情感”的下移,“象罔”也由哲学概念转向美学概念,并激活参与了兴象、气象、情景等美学范畴的生成。
二、“象罔”对审美空间的建构
上文“象罔”落脚在“象”,强调了“意象”建构对真理开显及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但庄子更欲阐明,“象”只能作为一个状语、一种手段存在,不能代替“道”本身。“象罔”亦作“罔象”,本指水中之精怪,《国语·鲁语下》曰:“水之怪曰龙、罔象。”韦昭注:“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肿。”[18]庄子变换字序为“象罔”并嵌入寓言体系之中,可见他对名称并不关心,重要的是“得意忘言”。构词方式的灵活迁转带来了新的意义生成及更大的阐释空间。“罔象”之“罔”,可做“不”“没有”解,庄子通过构词方式的迁转将重点移到“罔”上,表达了对“象”的警惕。
“象”思维范式不同于逻辑概念的推演,“象”的形象性、感知性诉诸人的感性经验,如《周易·说卦传》以天、圆、君、父、良马等“象”来表达乾卦刚猛精进之道,又以地、母、子、母牛等象征坤卦温柔和顺之理。首先,“象”终非“罔”。《周易·系辞下》:“象也者,像也。”“象”无法替代“罔”,“象”非本质,非大道,如钱锺书所分析的,“《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亦可”。[19]“明理舍象”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得鱼忘筌”。其次,“象”变幻不居,乱迷人眼。《庄子》更借壶子与巫咸斗法之寓言隐喻“象”之变幻多端,壶子四次变象,示以“地文”“天壤”“太冲”“未始”,巫咸执着于表象而推断壶子的生死吉凶,无法察其实质。庄子意在说明,不要为变幻不居的“象”所迷惑。最后,“象”动心愉目,易乱人心。“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从表意传道的功能来看,象与言又是类似的。语言离不开修饰,形象需要精心斧凿推敲,但过分修饰又使人沉溺藻辞而忽略本义。老子对“文胜质”充满警醒,“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亦主“得意忘言”。在庄子看来,踵事增华、饰羽而画不仅会影响人对本真的把握,而且容易使人失去质朴的本性:“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1]547-548老庄对“象”的辩证思考在同时代的哲学家那里亦有回响,如孔子主张“素以为绚”“辞达而已”;墨子云,“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20]。《韩非子·解老》提到:“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3]133
所以,“象”的繁多侈淫会扰乱人对形式背后真理内容“罔”的把握,但亦应看到,庄子的“罔”并非完全否定,还蕴含着超越的维度,即我们需要借助“象”通达“罔”,从经验来思考超验。“玄珠”存于“赤水之北”,成玄英疏曰:“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动,位在北方。譬迷心缘镜,闇无所照,故言赤水北也。”[1]224水性变幻不居,象征着不断变换的表象世界,让人眼花缭乱,意乱神迷,而探究玄珠(真理)的过程就是穿越迷障、超越表象后真理得以开显的过程。庄子“取象”之目的是冥合于本体之道,这种过程是“对物象存在意义的否定,是使自由从相对走向绝对,是使有限的‘有’走向那无限的‘无’”[21]。王弼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22]因此,体道的过程就是摆荡在“有”与“无”之间的过程。彭锋解释道:“象罔是有无的统一,而道也是有无的统一;我们甚至可以说,象罔就是道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道只能以象罔的形式存在。”[23]“罔象”在此意义上又是“罔与象”,吕惠卿注:“象则非无,罔则非有;非有则不皦,非无则不昧;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24]宗白华说:“非有非无,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象里,玄珠的皪于象罔里。”[25]艺术的韵味就体现在这种有形的符号(“象”)与无限的精神(“罔”)之间的互动,或者说美就在“有象”与“罔(无)象”之间的张力中存在。“象”是指向了意义,也可以反驳意义,可以加强,亦可反其道而为之,可明说亦可暗指,可相得益彰也可能相互对抗,这都带来了艺术上的无限可能。
六朝美学范畴“韵”的成熟亦得益于庄子“象罔”所昭示的这种“象外之象”。较早的“韵”被应用在音乐领域,东汉蔡邕《琴赋》云:“繁弦既抑,雅韵乃扬。”“韵”本义为和谐的音乐,魏晋时期该词又与人物品藻相连。钱锺书《管锥编》中说,神韵“以不画出、不说出示画不出、说不出(to evoke the inexpressible by the unexpressed),犹‘禅’之有‘机’而待‘参’然”。“韵”就是经由有形而具体的“象”所导引而出的无限而阔大的“罔”的审美空间,指引欣赏者经由表层的、有形的、可感的文艺形象进入深层的、无形的、超验的、由作者注入其中的生命精神。在文艺批评领域,萧子显认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26]钟嵘提倡:“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4]47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也提“文外曲致”,这些论断都提示艺术应追求文外旨趣,营造韵致,让读者感到滋味无极,圆转无穷。“韵”在唐宋亦演变为一种评价标准,如唐司空图论诗中“味在咸酸之外”,宋陈善《扪虱新语》评陶歌有“深远无穷之味”,宋严羽提倡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范温《潜溪诗眼》),“韵”“妙”之境就存在于“有法而无法”“有形而无形”之间,或者说自然和规则之间的平衡。明清之际,“韵”更与“神”范畴相连,王士禛以“神韵”论诗,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追求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空灵境界。而这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境更是“象罔”所昭示的有形与无形之境所衍生。
“罔”与“象”之间的游移与张力也让“意象”范畴向着“意境”演进,加之以佛教文化对心理空间的开拓,“境”论在唐代逐渐成熟。王昌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27]89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云,“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27]89-90皎然《诗式》亦有“取境”之说,“境”本义是界、域,表示某种范围,运用于审美领域,“境”是由“象”营构出来的一种审美场域,这又与“象罔”中的“罔”所昭示的无限与无形相通。对“境”的把握离不开欣赏者的建构,况周颐云:“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梁启超也提到“境者,心造也”。因此,“象”如果是极简甚至是空白,反而能更大限度地释放主体的鉴赏自由。故而老庄认为形式越繁复炫目,越远离精神之美、大道之美,朴素、冲淡、不尚巧饰的自然之美成为老、庄一致的追求,如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28]112-113,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250。推至极端,甚至可以不要形式,如庄子所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1]392。《庄子·内篇·人间世》中所说的“虚室生白”亦是对“象罔”的形象化的图解,“虚室”则是艺术形式因素,艺术借意象符号搭建了一个场域或者审美的图式,中间的无限空间则是鉴赏者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空间。
六朝时期,玄学语境下这种“大美无言”之主张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挥。在音乐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对“啸”的看重,阮籍拜访苏门真人上说皇帝、神农玄虚之道,下谈三代国君品德之美,又兼谈养神导气之术,真人默然不应。阮籍对之长啸后,真人“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29]。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中出土的砖印模画作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七贤”行为各异,而阮籍则是撮口并将右手拇指贴于口前,小指翘起作“啸”状,“啸”与饮酒、弹琴成为名士标志之一。“啸”超越人类语言之“象”、音乐之“象”,成为更接近于自然大道、精神自由的表征。这与“无弦琴”的精神旨趣有同妙。沈约《宋书·隐逸传》载:“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30]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31]陶渊明并非不解音律,但他常怀抱“无弦之琴”,并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推至极致,任何具体的声音之“象”都会束缚人对“天籁”之音的把握,所以陶渊明强调“真音”在“无音”之上,这更是对老庄“大音兮声”“天籁”“至乐”等审美范畴的实践和体认。另外,《二十四诗品·含蓄》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宋代书画美学中提倡的留白技法、诗歌追求的平淡审美风格以及明清戏剧中“虚实”范畴等均可沿波讨源至老庄之哲学。
综上,“象罔”非有非无、不皦不昧之特点成为其向美学范畴演进的又一理路,审美效果的达成就在有限、有形之“象”与作者精神无限之“罔”间的互涉,“象罔”理论所蕴涉的设谜与解谜、编码与解码,亦是文本阐释学、文艺鉴赏理论的核心。
三、“象罔”对审美心境的蕴摄
庄子不仅善于用寓言说理,而且在命名上亦匠心独运,名字与寓意相互指涉、加强,如他借“泰清”“无为”“无始”三人对话描绘“道”之恬淡清虚之特征;又以“无足”“知和”二名对举,说明知足之道。由此为线索再次回到寓言,庄子又找了“知”“离朱”“喫诟”三个人物对照,三个人物分别代表思虑(理智)、声色(感官)、言辩(语言),它们与“象罔”相反相成,共同指向了得“道”主体所具有的心态特征。郭象《庄子注》云:“明得真者,非用心也。罔象(然)即真也。”[1]224他认为“象罔”得珠源于其“无心”:“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1]124这是其“独化”思想的体现,即“独化自性”强调要排除“人心”的安排和计较,要“自然而然”,这开启了从得道主体的角度阐释“象罔”的先河。
作为理论范畴,“象罔”在历代庄学史阐释语境中最常作为悟道心境而被接受,寓言开篇提到:“皇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1]224老子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道家语境中“玄珠”是“道”的象征,“象罔得珠”成为求真悟道的隐喻,“象罔”亦成为得道者或得道之心境的代指,其中蕴含着丰富审美心境论。从主体心性论角度对“象罔”进行理解的进程亦与佛教文化对心理空间的开拓互为表里。东晋支道林在《释迦文佛像赞(并序)》中提到:“遗风六合,伫芳赤几,象罔不存,谁与悟机。镜心垂翰,庶觌冥晖。”佛教认为“我执”是悟佛的“心障”,只有做到“象罔”那般“无心”,方能戒三毒,离妄念。支道林借本土“象罔”理论概念对佛教“心性说”进行解释,显示出佛教本土化的特色,也能够看出此时期“象罔”从思维范式逐渐成为哲学范畴的演进理路。这亦是宋代“以禅释庄”阐释策略的先导。南宋林希逸在“象罔得珠”寓言下总评道:“此段言求道不在于聪明,不在于言语,即佛经所谓‘以有思惟心求大圆觉,如以荧火烧须弥山’。”[32]将超越聪明、言语的“象罔”心境视为求佛法之“大圆觉”的必经之路。明代心学语境下,“以禅解庄”延续并成为典型,方以智《药地炮庄》“集评”提到:“不为四方色相之所变易者,唯罔象为能也。”[33]在“愚评”和“闲翁曼衍”部分又提到罔明菩萨令女子出定之典,将“象罔”心境与罔明菩萨怀有廓然无别之心境相联。
“象罔”所昭示的人生境界在本土思想中亦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唐代成玄英疏云:“罔象,无心之谓。离声色,绝思虑。”“象罔”即其所推崇的“逍遥”人生之境,他在“无心”的基础上强调“离声色”“绝思虑”,透露出其境界论与修养论并重的思想特色,希冀世人由追逐外物转向自我内在之生命超越。南宋末年褚伯秀云:“心渊尘徊而障其光明,性海涛魏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烛物哉?……使象罔而后得之,益欲人屏除聪明、知识复还性海之渊澄,则玄珠不求而自见矣。”(《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象罔”亦成为其穷理尽性儒家修身功夫的图解。清代郭庆藩《庄子集释》为清代庄学集大成者,呈现出重文字校勘的时代学术特色,书中对寓言中“象罔”的解释回归词语本身,即“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曰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17]415。这亦是“象罔”所激发出的回响。
审美与悟道相通之处在于需忘记心中的功利观念,此即“象罔”从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演进的内在依据。庄子又借“知”“离朱”“喫诟”三个人物对比,彰显“象罔”所达到的超功利的审美状态。这三个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有所待”,他们各自凭借智慧、感官、言辞去极力追求“道”,暗示了求道的目的与方式。老庄强调自然无为,有心求道往往离大道愈远,甚至“求道之心”本身也会成为求道的障碍,“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有心”则会产生功利得失、恐惧担忧,这些会扰乱心境,妨碍对“道”的体认。因此,道家讲求目击道存,神超理得,这也是“象罔”概念与佛教、禅宗相结合的契机,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悟道方法亦与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
具体而言,庄子借“知”的形象来强调悬置求知之心则是审美直观的前提,这样方可物我不隔,情往似赠,神与物游。作为寓言形象的“知”可作知识经验解,《庄子·内篇·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1]63成玄英疏云:“无涯之智已用于前,有为之学救之于后,欲不危殆,其可得乎!”[1]63可知,该层面的“知”又与“智”相通,“智”又分成“大智”“小智”,所谓“大智闲闲,小智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1]27,“小智”更接近于“形而下”的具体经验知识,“大智”则指向“形而上”的大道,在庄子看来若执着于具体知识,则易“形劳神弊而危殆者也”,无法获得精神自由。而在审美领域,知识的态度则更会影响我们对外物进行审美观照,朱光潜以观照一颗古松为例提到,若以科学的、知识的态度对待外物,则只能知觉到“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外物只停留在理性认知阶段而无法进入情感世界,更无法与你形成绝然一体的整体。宋严羽所说的诗歌有“别材”“别趣”“非关书”,同样强调对审美的最终把握无法依靠知识。西人休谟也说:“一个人没有领会这种情感的敏感,他就一定不懂得诗的美,尽管他也许具有神仙般的学术知识和知解力。”[34]
“知”又指主体思虑、知晓、识别等理性认识能力。吕惠卿《庄子义》云:“使知索之而不得,则不可以知知也。”[24]鼓应注引林希逸之说:“有分别名,有思维心者也。”[35]回到庄子的话语体系中,这一层面的“知”则为“机心”,象征着人的各种心思、思虑,而庄子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又借“宋元君将画图”的寓言申说之,面对国君,众多画师惴惴不安,“有一史后至者,亹亹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蠃”[1]383,可见功利得失、恐惧担忧等思虑会扰乱心境,妨碍对“道”的体认以及审美观照和艺术创作。
“离朱”形象在《庄子》中与师旷对举出现,指代人的感官。人有耳目口鼻可识别声色香味,但感官能力在老庄的认知体系中属较低级的认识能力,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28]31庄子对“道”的阐释:“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1]222-223成玄英疏云:“至道深玄,圣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视,绝声不可以耳听。”[1]223感官只能探求到事物的表象而无法接近大道,感受到的东西往往是肤浅且不真实的表象,故老庄用寂、玄、深、远、冥、恍惚、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不皦不昧、无状无象等话语描述“道”的特征,以凸显其无法被人的感官系统识别的独特属性。要之,他们不仅认为感官无法识别大道,而且对感官功能还心存警惕。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28]27-28,为此,庄子于《应帝王》篇特意创作了“混沌之死”的隐喻,混沌浑浑噩噩,自然纯朴,无识无欲,而凿开七窍则意味着具有了人为的感官欲望之羁绊,无法悠然自得,随心所欲,故而死亡。在审美领域,人需要借感官来欣赏种种艺术形式,但艺术之超脱形式之上“玄之又玄”的妙趣确实无法用感官来直接体会。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宗炳用“澄怀味道”描述中国山水画之特质,钟嵘以“滋味”揭示中国诗歌的特征,司空图以“味外之味”传达文艺作品的审美体验,欧阳修称梅尧臣诗“如食橄榄,初觉苦涩,但真味久愈在”。在他们看来,饮食与诗、画具有同构性,艺术的超越感官之妙需用心体会方可通晓。
最后看“喫诟”,《庄子义》提到:“使喫诟索之而不得,则不可以言求也。”[24]如上文所言,庄子对语言达道功能的有限性有深刻认知。《天道篇》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24]在庄子看来,语言具有局限性,真正的“高言”“妙言”,一般人无法体味,因为它超出俗表,淡而无味,故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28]111理解能力一般的人,听闻大道只会发笑而已。所以庄子借轮扁斫轮来告诫人们,古人之书皆糟粕也,真正的大道“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但世人很少能够揣摩微言背后的大义,而是执着于语言本身,“持诵往来,以为贵重”,拘泥文字,胶柱鼓瑟,进而各家纷纷踵事增华,动心机,饰华辞,于是“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虽然语言无法完全表意,但也不能彻底抛弃语言本身,所以庄子希望人们能够领会语言背后没有传达出来的言外之旨。庄子以“坐忘”进一步对这种精神状态进行申说,“坐忘”者,“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156,即超越认知、利害、感官、言语的“朝彻”之境,物我两忘,则慧照豁然,莹彻澄明,如朝阳初起。这与同时代老子的“至虚极,守静笃”、荀子的“虚壹而静”亦相通,同样与审美心态类似,无论是进行审美观照还是艺术创作均需此种心境,它是宗炳的“澄怀味象”,亦是刘勰的“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综上,“象罔”作为悟道心境与“知(心虑)”“离朱(感官)”“喫诟(言辩)”并立,说明“道”“大美”不能通过知性、感官和言辩逻辑获得,此亦“象罔”向美学范畴演进的路径,它与审美心境相通,彰显着忘知忘利、凝神至虑的审美心境。
四、余论:“象罔”与美学元范畴的互动
“象罔”一词,集中体现了庄子的美学思想,并与后代美学核心范畴相互动。第一,“象罔”与“兴”有相通之处。“兴,起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它与“比”不同,尽管二者同样是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用一种物象引发另一种情志或物象,但是与“以玉比德”似的直喻不同,起兴之物与所引起之物之间的连接是松散的、联觉的,如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喻“后妃之德”,人需要进入那种场域,才能够理解为何这种“象”能够引起那样的情感。起“兴”机制与上文所言的“象罔”结构类似,“象”无穷无尽,但无论哪一种“象”都是达到“罔”的途径,“象”与“罔”之间亦是较为灵活自由的关系,后又衍生为“兴象”“兴趣”“兴会”等术语。第二,“象罔”与“味”相关。“象罔”追求的是有形与无形间的那种言不尽意的玄妙之旨,因此与“味”有同妙,先秦烹饪大师伊尹说:“鼎中之变,精妙之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36]这种“妙不可言”的快意,是整合了眼、鼻、舌乃至心而形成的整体性的快感。“象罔”即有与无、有形与无形的统一,恍兮惚兮,若有似无,指向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间,与艺术中追求味外之旨、余音绕梁的一唱三叹的效果异曲同工,后又有“滋味”“韵味”等次生术语。
总之,“象罔”是庄子提出的具有美学阐释价值的核心术语,它介于实与虚、有与无之间,摇曳在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之境,与艺术审美“以象达情”相通,同时彰显着主体无我无物的审美心境,集中体现了道家美学冲虚飘逸的精神,彰显着中国美学氤氲蓬勃的宇宙观念和生命意识,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