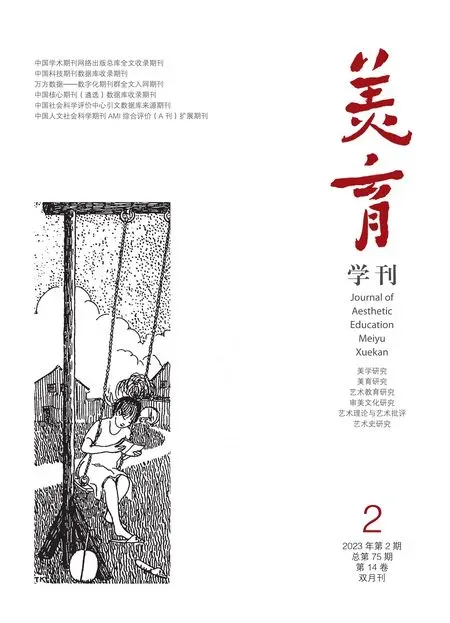“怨恨”概念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后期美学思想
陈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2488)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战争的激烈气氛中,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声称唯有坚持审美自律性,“严格界定和限制这个领域,包括文学研究对象、阐释过程和评价标准”[1],方能挽救人文危机。为此,哈罗德·布鲁姆将文化研究贬为“怨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将文化研究兴盛的时代斥为“怨恨年代”(Age of Resentment),“怨恨”(resentment)概念就此成为理解哈罗德·布鲁姆后期美学思想的枢纽。本文力图借由“怨恨”概念,探究哈罗德·布鲁姆的后期美学思想。
一、“怨恨”
就概念史而言,布鲁姆的“怨恨学派”概念借用了尼采和舍勒的阐释。尼采、布鲁姆等人对“怨恨”的用法建基于浪漫主义的天才论美学,天才论美学为“怨恨”概念的出场奠定了基础。浪漫主义将西方思想史上的艺术精英观推向极端,其本身不仅是一场有关艺术的运动,也是试图令艺术支配生活、君临一切的运动。它基于天才中心主义,强调“世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创新”,突出绝对主体的创造力,肯定“不屈的意志”和“价值的创造”[2]120,推崇“天才汪洋恣肆不可名状的想象力”[2]45。艺术被视为天才的产物,艺术创造力成为评价艺术乃至世界的最重要标准,艺术家也被赫尔德誉为最高种姓婆罗门。
作为“浪漫主义父执之一”[2]72,康德系统阐发了“天才”观念。其核心是自由的、主动的、创造性的主体。天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是“一个主体在自由运用其诸认识能力方面的禀赋的典范式的独创性”[3],与模仿的精神迥然对立。唯有天才“能够将某些东西带入艺术作品中,促使我们思考并且扩大我们的思维”[4],因此,天才的作品堪称典范,是评价他人作品的准绳和规则,并且最终占据了规则的地位。尽管康德常被称为“接受论美学家”而非“创作论美学家”[5],关注审美判断力的自我立法而非美学创造,但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康德的思想迎合了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和天才崇拜,而在费希特将天才和天才创作的立足点提升为“一个普遍的先验立足点”后,“天才”更发展为一个普遍的价值概念。[6]
在此基础上,叔本华发展乃至神化了天才观。他主张“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7],唯有卓越的天才能够实现对理念的观审任务。艺术天才作为一种绝对的主体,拥有不可阻挡的独特创造力,超越一切根据律。“一个天才具有双份的理智,一份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并服务于意志,另一份为世界准备的,即由于这份理智使他变成一面镜子,以反映出他对于世界的纯粹客观的态度。”[8]天才能够把生存的统一体作为自己的问题,创造出永恒不变的完美形式,超越平庸之人眼中沉重、混乱的世界图式,为人类提供崭新的启示。唯有天才能够创造美的艺术,但叔本华同时指出,在庸众的眼中,一切事物都带有怪异、黑暗、敌意的样子,天才故而注定是孤独的,遭受庸众的嫉妒与怨恨。
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天才论美学影响。[9]依尼采之见,生命的本质是权力意志,它代表自我肯定与行动的优越性,被视为“万物之首、万物之尺度、万物之意义”[10],天才正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作为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超人”,天才是最神圣的自我精神创造者,对立于无能的末人、庸众,这在艺术上表现为超越众人的创造力。具言之,真正的艺术天才应是日神力量与酒神力量的完美结合。前者意指有序的个体化原理,是一种赋形的力量,后者则体现了“醉”、激情与狂喜。天才首先拥有酒神般的创造力和自由,打破个体化原理的“适度法则”,超越一切旧有规则。此时,天才的自我不再是经验现实的自我,而是“根本上唯一真正存在的、永恒的、立足于万物之基础的自我”[11]19。他展现着经酒神精神改造过的“生命意志”和无限扩展的生命力。由于酒神力量具有破坏性作用,天才故而又赋予它一定的形式和原则。因此,艺术家的天才正是“法则下最高的自由,最凝重之中的神性的轻快和敏捷”[11]360。由于浪漫主义拒绝一切的停滞性,日神力量与酒神力量的结合将是一个无限前进的运动,“艺术本身就像一种自然的强力一样借这两种状态”[11]340表现在天才的身上,其评判标准为作品“是否显示出创造者极为充沛的创造力,或者是否是需求和被剥夺之后的产物”[12]。天才的卓越能力令弱者遭受持续压抑,产生怨恨心理,试图为深入骨髓的自卑不断报仇。
在此基础上,尼采从谱系学角度重新思考道德的起源与价值判断的标准,对“怨恨”问题展开更具体的究析。尼采指认西方最初的道德价值公式是善=高贵=权势=美丽=幸福=神圣,“善”既指社会等级意义上的“高尚”,也指“精神贵族”“精神特权”。“高贵的概念被尼采用来与一种特殊的肯定生命的态度相联系”[13],强者自身决定了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尼采强调强者与善的天然统一性:“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14]然而,“在超人眼光产生自律、个体性和创造力之处,末人自我无法摆脱的无力总会对此产生反感”[15],引发怨恨心理。与自发产生并肯定自我的高尚道德截然相反,怨恨本质上是奴隶道德,产生于外界的刺激,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针对强者的被动反应。怨恨者从一开始就将强者臆想为凶恶的敌人,否定其地位和价值,而将自己设立为作为背后图景和对立面的善人。具有权力、统治地位的强者是恶的,“只是因为他们被充满怨恨的毒眼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意义、改变了外形”[16]23。价值对立引致的报复心态则是怨恨心理的直接动机,但它并非一个即刻的反应,而是一个延后发生的阴谋,因为弱者习惯于隐匿复仇心态,沉默记恨,等待复仇时机的到来。其最终目标是颠倒既有的道德价值秩序。
在尼采看来,“自欺”[17]乃怨恨的本质特征之一,体现在怨恨者将正义作为颠覆道德秩序的借口。弱者坚持“让强者自由地变成弱者,让猛禽变成羔羊”这一信条,将软弱解释为自由和自我的独特性,把软弱的种种表现形式解释为功绩,而将强者视为对正义和自由的威胁。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正是此种怨恨心理的表现。基督教则是导致西方道德价值遭到颠覆的真正源头。基督教源于弱者的怨恨心理,意味着一切最高价值的没落。它反对强者,为了否定现世的生命、权力、自我肯定,创造了“上帝”“天国”和“末日审判”等虚无主义的概念,宣称唯有苦难者、弱者才是善人,精神性的最高价值乃是有罪的。基督教“把不图报仇的无能吹捧为‘善良’,把怯懦的卑贱吹捧为‘恭顺’,把屈服于所仇恨的对象的行为吹捧为‘服从’”[16]28,将弱者对强者的怨恨解释为对“非正义”“不信上帝”的仇恨和对神圣道德秩序的维护。这实乃最精巧的“怨恨之花”,怨恨本能通过否定强者的价值,摇身变为“文明的工具”,奴隶道德由此占据了主导地位,颠覆了既有的道德价值秩序,最终酿就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
舍勒对怨恨心理的研究受到尼采的影响。[18]他以质料主义价值伦理学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原则,[19]认定现代社会的价值错觉源于人们内心的混乱感受,尤其是怨恨心理。如果说怨恨被尼采视为个体性的经验和感受,那么怨恨就是舍勒眼中的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怨恨”的要义有二:第一,怨恨涉及对他人情绪性反应的感受与咀嚼,是对情绪本身的再体验;第二,怨恨是消极的,包含一种敌意的动态。怨恨源于弱者的无能所导致的内心无能感与软弱感。它作为一种针对强者的被动反应,最主要的出发点便是报复冲动。与尼采的说法相似,怨恨并非即刻发生,其两个本质特征是隐忍冲动与将对抗反应延至适宜场合。由报复感起,经过恼恨、嫉妒、阴恶,情感直达怨恨的边缘,而由于“受一种更为强烈的无能意识的抑制”[20]10,这些情绪被强行隐忍于心中,逐渐转化为怨恨。怨恨的另一个出发点则是嫉妒,弱者自身无法获得肯定价值和单独进行判断,只能不断与强者进行价值攀比,但事实上又不能相提并论,于是就越要在一种缺乏积极目标的批判中发泄怨气,从而引起指向强者本身的“存在嫉妒”,最终产生了“怨恨批判”,其特点是“它宣称自己意愿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它认真‘意愿’的;它之所以批判,并不是要消除不良现象,而是以此作幌子亮亮相而已”[20]14。从这样的心理出发,为了消除欲求与无能之间的紧张状态,意识中便出现贬低、否定正价值的意向,甚至将对象的对立面看作完满的东西。因而怨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错觉,即自欺。它不仅贬低正价值,更伪造和幻化价值本身,导致了深刻的精神危机。
舍勒同样否定了现代市民伦理,只不过现代市民伦理所导致的是基督教伦理价值的颠覆。现代市民伦理源于“价值低位者的怨恨动机所选择的价值主体化的欲求与功利目的”[21],其核心是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首先,平等主义否定了强者的价值,“爱”不再是强者对弱者的俯就,而变为了对共同体的内在价值的反感和内在对抗。其次,现代社会否定了一切崇高的价值比较标准,功利主义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这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优良品质的怨恨心理。怨恨心理同时导致价值主观化现象的产生。它企图掩盖弱者无能感受到客观价值秩序存在的事实,通过将道德价值视为人的意识中的主观现象,从而否定更高的客观价值。舍勒对社会怨恨心理的研究正是为了克服由此产生的精神危机,恢复原有的精神秩序。
二、“怨恨学派”
通过上述考察,“怨恨”的特征可被概括如下。第一,“怨恨”的主体是弱者,它本质上是一种奴隶道德的体现。无能与软弱是“怨恨”的根源,也总是弱者的必然处境。第二,“怨恨”总是与弱者无法获得肯定价值的状况有关。弱者无法直接获得肯定价值,而与强者所进行的价值比较,更使其感到自我的无能和肯定价值的遥不可及,从而产生报复心理。第三,“怨恨是在人的意识中变革那种永恒的层级秩序的源泉之一”[20]44,表现为复仇与嫉妒的冲动。怨恨者因无力直接回击强者而转向回避强者和肯定价值,通过贬低正价值,伪造和幻化价值本身。第四,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主义、功利主义、相对主义、实证主义都是怨恨的表现,它们否定了强者的地位,颠覆了既有的价值秩序,导致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巨大的精神危机。
借助对“怨恨”特征的概括,布鲁姆对“怨恨学派”的看法可被归纳为:
第一,“怨恨学派”是那些无法克服“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的弱者。他们缺乏真正的审美创造力,逃避直面前代巨擘的伟大审美成就。这与布鲁姆早年的“诗学影响”理论有关。他认为诗学历史不是子承父业、和平传承的融洽历史,而是充斥持续的冲突和斗争,每一个诗人都陷入与前辈诗人的影响关系网中。“诗学影响”便是前代诗人的诗学成就对后辈诗人的压抑。布鲁姆提出“互文性”(intratextuality)概念,强调“内在的”诗人以及“外在的”文本都共同处于影响的关系之中。[22]这种影响“既是内在的心理防备——焦虑的体验,又是外在的文本之间的历史关系”[23]6,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由此产生的“影响的焦虑”。
然而,对后辈的强者而言,“影响的焦虑”是一种创造性的偏离。由于诗人本身“注定了只能通过其他的自我的意识而了解自身最深切的欲望和追求”[24]26,因而“焦虑”激发了后辈强力诗人的创造力去追求真正的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超越前辈。只有“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者”[24]5,才能直面经典的审美价值,并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越前辈。而对弱者而言,“诗学影响”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只能始终深陷于“焦虑”的折磨中。据此,布鲁姆将“怨恨学派”称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利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3]412,本质上是审美能力方面的弱者。
第二,经典本身的审美价值给弱者带来无尽的焦虑与压抑,逼迫他们通过贬低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崇高价值来实现一种“升华的报复”。这首先表现为“怨恨学派”强烈否定“影响的焦虑”。他们否认与前辈的竞争关系,试图通过拒绝承认经典的影响,凸显自我的创造力和独特价值。诸如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认定“影响的焦虑”只适用于“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女性主义者强调自身独立于男性影响之外,并认为女性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女性作家好比被褥缝纫工一样亲密合作”,而少数族裔更坚持他们种族的“纯粹性”,强调自我不受任何文化污染之害,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且能够不断发展。[25]其次,“怨恨学派”拒斥审美自律性,将经典的审美价值降卑为意识形态或至多视为形而上学的产物,将经典建构视为社会排斥的过程。他们试图回避审美领域,宣称所谓的“审美价值”只是抽象的概念,甚至刻意抹杀审美性的独立地位。同时,他们还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文学研究必须服从政治目的,“在理论上都不只限于对艺术的讨论,或只源于对艺术的讨论”[26],用外部的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取代内在的审美价值,借此研究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如后殖民主义代表萨义德就认为,文学对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文学研究应是为了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27]
第三,怨恨是“一种为虚无的意志,一种反生命的意志,一种对最基本的生命前提的否定”[16]114,文化研究实际上将对文学的研究演变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更不是对经典的尊重和反思,而仅仅是以“政治正确性”为幌子,否定审美价值的实在性,从而颠覆经典秩序。因此,布鲁姆声称“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一副掩盖平庸的面具”[28],其背后隐藏的是怨恨心理,是“怨恨学派”试图借此减缓因个体对审美价值缺乏贡献而产生的负疚感,“怨恨学派”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在内的各种文学作品的教学日益被社会政治呐喊代替;文学经典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布鲁姆哀叹,“在文学中只属于那些附庸男人和女人,我们的修辞学中的上帝只属于那些学究们”[29],斥责这一切最终损害了文学研究和人文主义教育的未来,并加剧了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危机。
三、“经典”
布鲁姆对“怨恨学派”的批判彰显了其后期美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指向了对“经典”的讨论。布鲁姆强调自己作为“终身的审美主义者”[28],捍卫西方经典,旨在维护审美价值,与政治和民族主义无关。他既反对“怨恨学派”,也批判仅仅为了虚幻的政治与道德价值而保存经典的右翼保守主义者,主张“就对审美价值的伤害而言,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西方经典与那些宣称要摧毁或破解它的人的攻击是相同的”[23]16,都是审美价值的最大敌人。
因此,“经典”必须体现审美价值的“崇高性”和“代表性”,其评价标准是“陌生性”(strangeness)。它类似于韦勒克所说的“文学性”(literariness),都是属于审美领域内的文学特性。“陌生性”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23]2,出自无可企及的天才之手,尤其体现在莎士比亚和但丁的身上。经典作品正是以其巨大的原创力增加了美感的“陌生性”,任何一部欲战胜传统并加入经典行列的作品,必须首先拥有天才般的巨大原创性和独特性,无法被文化研究予以历史化、社会化、政治化的还原。它表现为诸如在人物的表现、语言运用中对比喻的新意进行创新从而摆脱旧有的用法,语言形象化,改变旧有的文学范式等方面。
具体而言,首先,审美与竞争是同一的,审美价值则是决定经典的标准,经典实际上是审美竞争中的强大胜利者,检验经典性的直接标准就是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服自己;唯有真正在审美创造上成就卓越的强力作家和作品,才能成为经典。他们必然属于精英阶层,堪称“精神贵族”。其次,布鲁姆反对“怨恨学派”所持的“经典秩序的构成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他认为经典的挑选规则是由精英们遵照严格的艺术标准而建立起来的,经典的秩序是由那些真正的作家根据审美价值成就而决定的,并非由文化批评家或政治家决定。经典秩序并不封闭,而是呈现开放的态势,“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23]6,但这种开放不是无条件的,唯有具备卓越美学价值的作品才能打开经典秩序,真正跻身经典行列。相反,“怨恨学派”无法真正决定经典的选择,反而会困囿于一种精英的负疚感中,因为“经典总是间接地服务于西方社会每一代富有阶级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关注与需求”[23]23,受精英决定,无法剥离精英主义色彩。
这就涉及了经典作用的问题。布鲁姆坚持审美无利害性,坚称经典并不直接服务于任何社会目标,不能拯救任何人,也改善不了社会,我们阅读也应当是无利害的,所应关注和追求的是审美价值。至于所谓的“文学批评”,则始于对阅读的真正热情。布鲁姆极端地认为,“倘若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23]21。经典的真正作用体现在经典所拥有的美学力量和普遍性特征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教会我们自省,促进我们内在自我的成长,最终使我们形成“自律”。
四、结语
纵观哈罗德·布鲁姆的后期美学思想,一些缺陷灼然可见。第一,就美学史而言,文化研究与布鲁姆美学思想代表了不同的美学传统,二者均不具备绝对优先性。如果说文化研究是对审美主义的反动,属于“怨恨”,那么布鲁姆的立场同理可被视为对之前美学传统的“怨恨”。同时,如同尼采、舍勒沉迷于对人性中负面价值的推论,布鲁姆也只聚焦文化研究对传统的解构和颠覆,忽视了其积极意义。事实上,文化研究将文本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开掘了文本更丰富的意义,使人意识到文学阐释方法与标准的多样性,扭转了早前“新批评”的理论弊端,并且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促进了社会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审美价值问题上,布鲁姆乃是激进的审美自律主义者。这集中表现在他坚持康德的审美区分思想,强调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政治价值之间的界限,坚持审美价值的纯粹性和绝对性,将文学作品的作用严格限定在无利害的审美领域内。但审美价值从来不是纯粹的,也不是绝对的,“并非唯一一种艺术价值,并非唯一一种产生内在价值体验的艺术价值”[30]。审美问题本身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状况。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并不存在纯粹的审美价值,审美趣味和文艺经典是在场域中所建构的产物,与包括教育水平、社会出身、性别、年龄、职业与收入在内的社会阶级问题密切相关,审美自主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涉及权力场域内的社会斗争。[31]因此,对文学作品“外部性”的研究不可或缺。正是这些“外部作用”与审美作用共同加深了我们对文学、世界和自我的理解。
第三,在经典建构的问题上,布鲁姆对“怨恨学派”的批判带有精英主义等级制色彩。布鲁姆的天才论美学主张文学传统依据强者与弱者之分,由“尘世不朽”[32]的天才精英所统治,尤其对立于中产阶级庸俗文化,[33]文学的评价标准被简化为审美价值的优劣,经典仅仅是美学价值层面的强者。那些不符合传统美学标准的作家以及质疑和攻讦传统美学标准的批评家被布鲁姆一概贬斥为弱者和怨恨者。然而,审美价值的具体内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布鲁姆虽然主张文学批评必须关注审美价值,但其提出的“陌生性”不足以提供可操作的具体评价标准,并且这种模糊的概念无法全面评判文学的优劣。事实上,审美价值的模糊性和多样性本身就否定了经典标准的单一性。布鲁姆审美主义的排他性假设忽视了文学价值的多样性,与之相反,文化研究通过挖掘文学的外部价值,丰富了传统的经典秩序。
此外,尽管布鲁姆承认经典的未来处于一种有限的开放状态中,但其观点背后是本质主义的独断论,即固有的经典秩序拥有超验的绝对本质,经典标准的历时性和多样性遭到否定。事实上,经典秩序首先是阐释学“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效果历史的产物,处于历时性变动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存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同时,在经典建构过程中,任何话语陈述和知识运作伴随着福柯所指出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涉及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对此问题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不正义的旧有社会规范的间接肯定,带有西方白种男人霸权的精英主义色彩,所谓的“怨恨学派”正因此要求“打开”恒定不变的经典秩序,[34]建构一个更为多元、公正、开放的经典秩序。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布鲁姆对“怨恨学派”的激愤抨击暴露了文化研究的一些缺陷,如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机械应用抽象概念和方法来强行裁剪意蕴丰富的文本,引入大量不为人理解的专业术语而退入精英化的象牙塔之中,未能妥善解决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断裂的问题,等等。同时,传统的审美价值尽管存在争议,却仍然是经典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准。这一点纵如在经典之争中与布鲁姆针锋相对的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也从未完全予以否认。杰洛瑞指出要打破目前非此即彼的经典论争僵局,就必须循沿布尔迪厄的道路前进,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经典问题理解为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分配的问题、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获取途径问题,作家的产生和经典秩序因此绝非单纯的审美问题,而是文化资本分配和再生产的产物。然而,杰洛瑞仍不得不承认在实现文化资本分配平等化和获取文学经典的条件普遍化后,剩下的依旧是“审美竞赛”[35]。这意味着在扫除种种社会不平等条件后,布鲁姆构想的“自在审美主义”图景仍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更为可贵的是,布鲁姆在理论尘嚣的年代重新揭示了审美的私人性特征。经典作家的写作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以“个人化”为核心的自我价值,而对读者而言,阅读最根本的是与孤独的内心、私人的自律目标相关。尽管布鲁姆始终怀疑孤独的个人阅读能否增进公共利益[36],但正如理查德·罗蒂所言,那些坚持审美自律性、追求审美私人性的作品同样能使我们警惕自我中心的危险,提升我们的情感敏锐力和道德想象力,“注意到我们本身的残酷根源,以及残酷如何在我们不留意的地方发生”[37],从而将他者想象成与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避免对他者残酷,促进社会团结。罗蒂据此称赞布鲁姆将成为“22世纪人们仍然将以极大的兴趣去阅读的我这一代人当中惟一的一位美国学者”[38],这或许并非溢美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