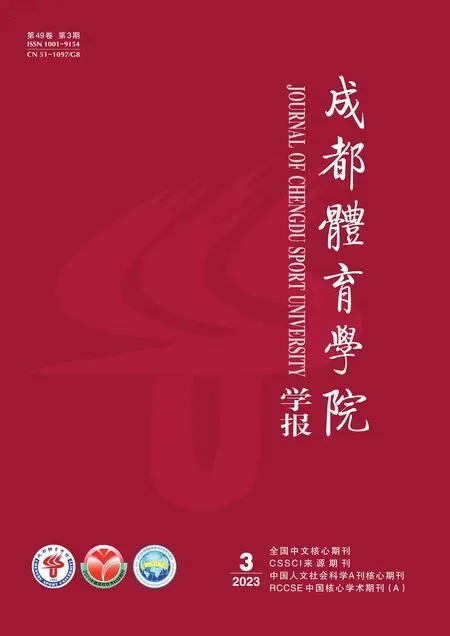再论青年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救国理念
陈廷湘,于诗琦
1917 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树人理念,受到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的高度认同和赞赏。青年毛泽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斗士,当时发表的许多著述,如《体育之研究》等都是孙中山之后新一代中国先进分子探寻新救国理念的重要成就之一。《体育之研究》及其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精深阐论一直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尤其是体育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与评说,留下了众多颇有价值的学术成就。由于毛泽东写作《体育之研究》及其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理念的阐论具有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和十分深刻的思想指向,学界对此理念的深刻意旨和思想源流的认知尚存一些歧见。鉴于此说在思想界,尤其是体育史学界广为人知,影响巨大,不应长期存在一些明显的歧见,以致后学无所适从,对此加以进一步讨论显然颇具必要性。
1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理念源流再讨论
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有如下表述:“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1]毛泽东言之甚明,此说并非源出于他,而是对近人见解表示赞同。毛泽东这一表述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问题:“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究竟源出于谁?众多学者在回答此问题时作出了颇有歧义的回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者张玲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来历及其他》(以下简称“张文”)一文中指出,“这句改变了中国人几千年传统的身体观念,影响了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话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却在不少人中十分模糊。”“一篇谈素质教育的文章中说是蔡元培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位颇有些影响的人士以无可辩驳的口气宣称,是鲁迅先生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来表述他对国民的期望。”[2]张文对这两种说法显然持否定之见,并彰明学界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名言源出的认识尚未形成人们想象的一致性。
同时,张文指出,“多数人——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民众还是把这句名言归到了青年毛泽东名下。20 世纪80 年代的一位风云人物胡平说:‘毛泽东在其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指出体育运动须强调野蛮,叫作文明其灵魂,野蛮其体魄’。中国体育博物馆的汪智、崔乐泉在2003 年毛泽东诞辰百周年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方能刚毅有为’”。张文并评论说,“这种看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随意搜索一下互联网,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其中不乏官方的或权威的网站”,诸如新华网、清华大学网站、电子刊物《中外文化交流》都有文章或评论认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名言出自青年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然而这并非历史事实”[2]。张文对后一种有较大统一性论定的否定大体上应属正确,因为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自己已说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近人”之言,他只是极表赞同。
笔者仅认为张文否定今人广泛认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出自青年毛泽东的论断大体上正确,且意欲说明张文的否定也还存在值得讨论之处。张文在否定既有主流观点后,作出了如下论断,“毛泽东很有可能是从日本人嘉纳治五郎那里读到这句话的。为了迎接大批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1904 年,日本柔道之父,远东的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嘉纳治五郎花了半年时间,到中国全面考察各地教育后回到日本,于1905 年在中国留日学生湖南同乡会上作‘支那之教育’的长篇演讲,在谈到体育时,就提到了这句名言。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1906 年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办的刊物《湘报》上。少年毛泽东在离开家乡之前,读遍了十里八乡能够借到的全部书刊,他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读到这篇演讲,然后不但用来指导自己的身心改造,而且在《体育之研究》里引用这句话来大声疾呼国民改造”。[2]论到此处,作者还特意补充说,“《体育之研究》中的这句话与《支那之教育》中完全一样”[2]。作者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提及的事实均未注明出处,笔者不得不按其说法进一步加以考实。结果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嘉纳治五郎的演讲稿并非发表在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湘报》上。笔者经多方查证,终未查到当时的湖南留日学生办过《湘报》。2014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者陈小亮发表的《清末湖南留日学生述论》指出,清末湖南留日学生只创办过《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洞庭波》这些刊物[3]。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者王天根2012 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专论《两湖留日学生刊物与政治舆论动员中的地缘倾向》一文也只提到湖南留日学生创办有《游学译编》等刊物[4]。笔者向湖南一些知名思想史学者咨询,回答亦说未见到过湖南留日学生办过《湘报》。笔者经过反复探寻,仍只查到只有戊戌变法人士办过《湘报》《湘学报》,且该两报均仅在1898 年存在过。最终,笔者查到嘉纳治五郎的演讲稿《支那教育问题》(而不是张文所说《支那之教育》)发表于梁启超当时在日本主办的《新民丛报》第23、24 号,时间并非张文所说1906 年,而是1902 年。刊于《新民丛报》第23 号的《支那教育问题》译文上半部分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日本始以代兴支那教育自任,其明年文部合力创设弘文学院于东京,专教支那游学人士。以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之。中设教育一科,又分为速成永久两门”。“嘉纳治五郎以将为支那谋兴教育,因出游于北京、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一观其国政民风,以定教育之旨。及其归,而湖南速成师范生六月期满,将归国。嘉纳治五郎乃以西历十月二十一日聚众演讲,湖南与各省师范生多来集者。而旁听者惟湖南戴君展诚、杨君度至焉”。[5]此为当时所载,可见嘉纳治五郎来华考察与在留日学生中演讲时间皆在1902 年。与张文所言并不一致。
其二,嘉纳治五郎演讲中并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言。刊于《新民丛报》第24 号的《支那教育问题》后半部分中,嘉纳治五郎在谈及体育教育时说,“人之身体能常运动则精神健拔,举事灵捷。予与贵国绅士相接,无不以车舆相过从,绝无徒步往还者。即同在一城,亦莫不然。此可以知其于事业上必有精神疏慢,气力颟頇之敝也。故教育之有体育,亦因国家之进步,个人之体有大关系。举国之任事者,能见日而不持盖,见风雨而不闭户,则外来之困难必无可以为其进步之阻力矣。故能习劳苦者一身一国皆增其气力,必不可不注意也”[5]。上段引文是嘉纳治五郎演讲时谈中国体育教育问题的译文全文。其中只是强调中国人应重视运动健体和体育教育,完全没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说法,也没有把文明精神与野蛮体魄统一起来的意思。张文所言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言与嘉纳治五郎说法完全相同看来并不是事实。嘉纳治五郎《支那教育问题》演讲是用日语所讲,翻译文字中也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说法,日语原本就更不可能存在与毛泽东之言完全一样的表达了。
当然,张文对以上论断也留有余地,表示其论断“只说是一种可能”。紧接着,张文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其言“在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中就说:‘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在陈独秀引用的福泽谕吉的‘兽性主义’教育主张中,已经明显地有‘野蛮其体魄’的意思”。并进而指出,陈独秀所引福泽谕吉兽性主义教育主张的“原话是先成兽身,后养人心,如果人人能做到‘身体象(原文如此)车夫,思想象哲学家,足能行千里,就可以明察秋毫地分析事物始末,初步成为一个文明学者’”[2]。张文这一阐论中显然存在如下逻辑关系:陈独秀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之前发表的“兽性主义”教育主张中已有“野蛮其体魄”之意,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的名言应来自陈独秀之论。而陈独秀主张又出自日本学人福泽谕吉,那么,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主张最终源头在福泽谕吉。这里存在的问题仍然较明显。
陈独秀1915 年在《新青年》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第四部分题为“兽性主义”。其中引用福泽谕吉之言“‘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用了引号,表明是直接引用福泽之言[6]。但陈独秀引文显然不是出自福泽日文原著,而是翻译文本,又未注出处,其引文出自何译本不可考。
张文又说所引福泽的原文为人人能做到“身体如车夫……”之论出自井上雄著《日本的教育思想》日文版[2]。此说显然亦不准确。这一引用也应是某中文译本对福泽思想的概括,不是日文版。且这一说法并不是福泽谈儿童教育时所言,与陈独秀引文并不存在直接关系。
由学者冯克诚任总主编,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的《日本近代启蒙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载有福泽谕吉《启蒙教育思想与〈学问论〉〈教育论〉选读》。其在介绍福泽启蒙教育思想时,简介了其有关文明教育的论述和《教育论》之体育教育论述。在体育教育部分说过,父母养育子女,“必须要象饲育牛马大猫一样注重其身体的发育”“七八岁后进入启蒙教育”[7]。此说显然也是译文,与陈独秀引用的译文意思相近,但其中并无陈独秀“兽性主义教育”的说法。
张文接着所说福泽谕吉所谓“身体象车夫……”是福泽在另一处的论述。福泽谕吉在《教育论》译文中说过“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钻研学识”。为了身体健康,福泽曾倡导设立“不乘人力车俱乐部”,要求学生作会员,绝不乘人力车,强迫学生步行锻炼,以强壮身体[7]。张文“身体象车夫……”之说显然由此而出。冯克诚总主编关于福泽之言与张文引语尽管都是译文,冯书更系统,但并无“身体象(原文如此)车夫,思想象哲学家,足能行千里,就可以明察秋毫地分析事物始末,初步成为一个文明学者”的“原话”。张文试图以上述福泽之言表明其中已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意思也并不能成立。
通过以上分析,应可以说,无论是陈独秀的引文还是张文进一步介绍的福泽本人的体育教育思想中都不存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表达,也无这一名言所蕴含的完整意义。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的表达既非出自陈独秀转述的福泽谕吉之言,也并不存在于福泽谕吉本人体育教育论的中译本中。
张文最后还论及,“陈独秀也还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宣扬‘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人,第一个在中国宣传这个思想的是蔡锷”。1902 年2 月,蔡锷在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一文中说:‘野蛮者,人所深恶之词。然灵魂贵文明,而体魄贵野蛮。以野蛮之体魄,复文明其灵魂,则文明种族必败’”。并指出,“蔡锷1899 年—1904 年留学日本,他应该是在那期间读到了福泽的书”[2]。至此,张文说明,中国人中最早言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休魄”者为蔡锷,而蔡氏此思想的来源仍然是福泽谕吉。查蔡锷原文,其说是论及严复《原强》中强调德、智、体三育中尤须重视体育时引申出的见解[8]。严复留学英国,属留学西洋名家,蔡锷从严复的思想引申出“灵魂贵文明,体魄贵野蛮”之说,其思想是否完全源自福泽谕吉确乎不便下最后结论。的确,蔡锷之说与青年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意思最为接近。但是,蔡锷仍然未完整使用过此一表述。
综上,就表达方式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名言确实是出自青年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毛泽东说:“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时显然并未直接引用“近人”原话,而是参考“近人”思想,经过自己理解而作出的表述。不仅如此,青年毛泽东此言的意指也与其他人存在颇多差别(后文将论及)。因此,今人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影响巨大的名言归于青年毛泽东名下也并非错误。
2 毛泽东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关系有独到认知
陈独秀论及“兽性主义”教育时直接提到日本福泽谕吉,可知福泽谕吉所述文明精神与野蛮体魄的相关观念对国人影响较大。要讨论青年毛泽东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关系的独特认知,显然必须将毛泽东的认知与福泽谕吉的认知加以比较。由于毛泽东并未读过福泽论述的日语原文,而是参考他人传到国内的福泽论述的中译本,因此,这里亦只用中译本加以讨论。
福泽谕吉十分重视文明教育,也颇为关注体育教育。但是,福泽论述的文明教育与强健身体并无直接关系。福泽完全接受西方学者“人们的行为最终是受‘纯粹观念’决定”“历史的运转取决于人们的德智”的思想。认为“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原因在于人们智德的提高”。并认为“文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从广义上理解,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立志修德,把人类智德提高到高尚境界”。不仅要做到个人“身体安乐,道德高尚”,而且要“实现国家的文明”。[7]福泽对文明教育论述颇丰,仅从这些译文已可看出,他讲的文明教育与体育强身教育没有直接关系。
福泽谕吉是在论体育教育时,才明确指出,人的“肉体和精神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钻研学识”。体育锻炼“是为了健壮无病,精神活泼愉快”“一个身心都健全的人,才能排除社会上各种艰难以达到独立生活的目的。”“体育是使人获得独立生活的手段。”[7]十分明显,福泽的意向中,与身体对应的精神主要指“知识”。强健身体的直接目的是利于获得“知识”,也就是说,在他的观念中,强体(有野蛮体魄之意)与文明精神的关系主要是指强体与增知的关系,且是一种单向作用关系。他认为,“使用身体与使用头脑所得的结果完全不同。前者能使人愈发强壮,后者使人愈发软弱”。即是说,锻炼身体可致体魄强壮,而获取知识(文明)则会削弱健壮,二者作用完全相反。后福泽似有只顾学习知识(增进文明)而不重锻炼才不利健康之意[7],但终究未在理论上深入阐明强健身体与增进知识(文明)的关系。
相较而言,青年毛泽东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关系的理解要更广阔深厚。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1]。这里,青年毛泽东首先从物质存在的第一性与精神存在第二性的关系上道明了人的身体与体现为知识与道德的精神之间存在着本体与载体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青年毛泽东进而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而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1]。上述论断意在说明,精神性的文明与物质性的体魄之间存在前者依存后者的关系,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必须首先“野蛮其体魄”,即必须首先奠定前者形成的物质基础,无此基础不可能产生“文明之精神”。而奠定此基础,“文明其精神随之”。青年毛泽东所以确定“文明其精神”会随“野蛮其体魄”而生的逻辑关系,在于他理解的“野蛮其体魄”中之“体魄”不仅指人与动物同样具有的“身体”,而且包括人所独有的,能产生思维的“脑筋”。相应地,“野蛮其体魄”就不仅指强健人与动物同样具有的“肌体”和体力,而且包括增强人所独有的“脑筋”和脑力。因此,通过“野蛮其体魄”增强了人的肉体和大脑思维能力,人对世间一切事物,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存在的认知和理解也就随之趋于广阔和深刻,“文明其精神”,即开阔精神境界便可随之实现。当然,这里的“精神境界”是指中性的思维和眼界,并非指带有是非判别的认知和道德精神。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中性的理解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仅就这个方面言,青年毛泽东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关系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不仅超越了福泽谕吉的认知,而且明显地突破了他“使用身体与使用头脑所得的结果”相反的见解。
毛泽东对文明精神与野蛮体魄关系的认知还远不只此,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进而论到,强健体魄不仅可以强化广义的知识获取,而且“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即“以理制心”“然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1]毛泽东这里所说感情显然相当于现代情感史学界所说的人之情绪、心情,包括喜怒、焦虑、兴奋、忧伤之类。在这些方面,身体健壮者一般易于用理智加以自我调节,体弱多病之人则多数易于形成情绪越坏,病弱越是加剧的恶性循环。青年毛泽东的见解确乎很有道理,甚至可说在今天仍有实用价值。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强健体魄“足以强意志”的论断。他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1]而“猛烈”“不畏”“敢为”“耐久”皆可“于日常体育”锻炼中形成。他还强调,“意志者也,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坚持体育锻炼可提高人的意志力在今人恐亦尽人皆知,足见百年前青年毛泽东的思考确乎具有远见卓识。
上述毛泽东有关强身健体可增强理性对情感的控制力和体魄对意志力提高的论断中之理性正情感和锻炼强意志亦应属于文明其精神的范围。这些论述展示出青年毛泽东观念中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关系远不只动物式肉体与知识的关系,而且是人的身体与整个精神世界、理性体系之间的关系。人之所以能形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上述关系,根本原因在人与动物对身体的控制力存在根本差别。毛泽东说,“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1]。这实际是说,野蛮体魄与文明精神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动物可以有“野蛮之体魄”,但无“文明之精神”加以调节,因而不能保护其强壮的身体。而人则可以用理性,即由文明之精神调节身体的运用,使身体强壮得以保护,因而不仅“野蛮其体魄”决定“文明其精神”,且“文明其精神”也有助于“野蛮其体魄”。由此,青年毛泽东进而指出,“生而强者”如“滥用其强”,则“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而“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惧其生之不永”,故而在理性支配下“勤自锻炼”“久之遂变而为强”。身体强弱并非固定不变,
在精神主宰下“滥用”其强,身体可由强变弱,在理性引导下加以爱惜且加强锻炼则可由弱至强。这些见解无论日本名人福泽谕吉还是中国其他新文化运动先进分子都未曾论及,的确是青年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思想。
3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蕴含的救国之道
青年毛泽东十分重视体育,谓体育为“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身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致远”。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致远”即是当时先进分子的救国理想。学者张玲认为,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所处时代与中国清末‘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相似,封闭的农业小国日本与封闭的农业大国中国一起被推到与西方文明相碰撞,而东方文明处于尴尬的被动境地时刻”[2]。此说显然是在呈明,福泽提出类似“文明精神”与“野蛮体魄”的体育教育主张受到处于封闭农业大国的毛泽东的重视是合乎逻辑的。青年毛泽东的体育理念与福泽的理念相同或至少相似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仔细考察当时的历史,青年毛泽东与福泽阐论各自体育教育理念的环境其实差别甚大。日本尽管也是在美舰威逼下打开国门的,但在明治维新后即开启了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进程。在转型过程中,日本不仅并未受到西方列强不断加深的侵略,且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形成了向外扩张的意图[9],此后还多次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福泽谕吉发表体育教育言论主要在1878—1894 年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近20 年之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福泽谕吉的体育教育观念的指向不可能与青年毛泽东、陈独秀等一样。福泽在论日本体育教育目的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我国开国距今仅30 余年,而欧美人则以数百年的辛勤经营才达到今天的地步,而我们今天不是已与他们并肩同步,正在进行工商业的竞争了吗?我们行动之活跃和勇敢,是不容置疑的。观瞻未来必将更有希望。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到底还有不及欧美人之处,这就是体格弱小。日本人的矮小、虚弱,不论在直观上或在统计资料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体力是生产一切财富的根本,虽然文明器械行于世,在很多方面机械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来代替人力。但是,运用这些有利条件还有赖于人力。机械的力量,蒸汽的力量,确实很大,但仍需要人力运用才行。由于体力虚弱,难于运用机械的力量,则对我国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7]。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福泽谕吉力主加强体育教育,以增强日本人的体力。不难看出,福泽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必须与国民强壮的体魄相结合才能保证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日本在与欧美的工业化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他力主发展体育教育强健国人身体,或者说“野蛮”日本人的体魄的意指完全在进一步实现强国目的。
相较而言,青年毛泽东和陈独秀等所处环境要险恶得多。在1840 年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后,中国人挽救危亡的斗争遭多次失败。洋务运动开启的经济改革,戊戌变法推行的政治改革,辛亥革命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无法挽救中国的危局。青年毛泽东参加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辛亥革命结局令国人大失所望之后新一代先进分子发动的新救国运动。形成于这个大背景下的《体育之研究》等著作中的“致远”意旨均是探寻救国之道。毛泽东在该文开篇即大声疾呼,“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也,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1]。这段情绪激越的言语,鲜明地昭示了青年毛泽东力主改造国民体质轻细无力,着力振作武风,以救贫弱之国的意向。福泽谕吉忧心国民“体力虚弱”是担心其缺乏“运用机械的力量”,无法在工业化进程中占据先机。毛泽东忧虑国人“体不坚实”则是担心其“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说得更明确点,即是担心体质虚弱的国人见到兵器就害怕,根本不可能命中目标,完全无法打倒列强,实现救亡图存目标。在此点之上,陈独秀亦有相似的见解,他在谈兽性主义教育时指出,“晰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6]。陈氏虽是说西方列强能殖民于世界广大地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强身健体教育而使国民具有野兽般强壮的体魄。但陈氏此言出于其愤愤于中国人体弱不振篇章之中,其意显然亦是力主中国人必须改变观念,重视强体,使身心“同时发展”,以造就能够改变被“殖民”境遇的能力。蔡锷则是在“甲午一役以后”,认为中国失败原因之一在于“元气凋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行伫起卧,颤战欲仆”[8]。因而倡导“灵魂贵文明,体魄贵野蛮”的军国民教育。
上述表明,福泽谕吉主张增智强体意在继续推动强国进程,而青年毛泽东等大倡心体并强,目的在挽救国家危亡。前者的忧虑相较简单,后者的忧虑则相当深重。福泽在讨论日本国民身体弱小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批评,其一,“社会上提倡体育的先生们,大都把身体的发育当做是人生的最大目的”,导致人们把体育视为“只是为了在自己主观的游戏一显身手,获得一时的快乐”,而不是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因而不能持续强身健体;其二,不少人认为,现代社会“一切文明事物可以凭借机械来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体力只能用于野蛮不文明的社会”;其三,当时的日本人“在选择配偶上,大都只限于外形的丑美,智慧”,不注重其“先代的身体健全”[7]。显然,福泽对日本人体魄弱小原因的分析涉及的都是较浅近的认识偏颇,而不涉及深层的日本文化缺陷。这与青年毛泽东等的认知相较差别确乎十分明显。第一,毛泽东认为,中国人不注重强体健身之“大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对身体的审美观存在重大错误。他说:“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瞻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而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1]这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身体观的错误在于把舒袍广袖,举止内持,目光舒缓,动作优容者视为体雅姿美;把动手露足,扭身转体,虎虎有声者视为不可入目者。毛泽东这一批评确实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尤其是在科举制形成以后,人们以赞许之情把读书人称为“文弱书生”,把美貌女子赞为“病西施”,以致有“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而为成语。《西厢记》把张生与崔莺莺的美好爱情称为“多愁多病身”与“倾城倾国貌”的完美结合。到清人曹雪芹作《红楼梦》时,实际也把病恹恹的林黛玉与贾宝玉视为“多愁多病身”与“倾城倾国貌”的一对真正美好恋人。《红楼梦》中尽管“多愁多病身”“倾城倾国貌”是由贾宝玉说笑话时道出,但内里显然是曹雪芹认为林黛玉、贾宝玉就是一对“多愁多病身”与“倾城倾国貌”的美好姻缘。上述人事虽多见于文艺作品,而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历代相传,了了不绝,也足已说明中国文化对身体美的判断至少存在一种颇有影响力的错误观念。对此,陈独秀也提出了批判,他说,中国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6]陈氏所述年轻人的病态亦是传统社会人们心目中的珍贵者形态。这种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陈旧观念,是国弱的一个表征,极其有碍于救亡图存。青年毛泽东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名言涉及文化深层的改造问题,是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较之福泽谕吉对日本国民身体弱小的思虑要深远得多。第二,毛泽东批评中国的动静观存在重大缺陷。他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人是一种动物,其体天然尚动;人又是有理性的动物,应知其体之动是有规则之动,是理性之动。人的身体天然有理性之动,也必须有理性之动,是为正常存在。但中国传统文化则长期主张“无动为大”,直到近代,仍有《因是子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视运动者之自损其体”[1]。青年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静坐,谓之“是或一道”。但观念上如果以主静而完全否定运动则是一大文化缺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本是两种优良的身体状态,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动如脱兔”就逐步成为负面形态。陈寅恪指出,“李唐一族”“固为纯粹之汉人”,其“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才得“新机重启”“创空前之世局”[10]。按陈寅恪之说,中国主流文化在唐代以前已成“颓废之躯”,李氏父子只是一时借助北方少数民族的野性精悍之风,才得创造李唐之盛,可以说正是“野性”与“文静”的暂时结合方有盛唐雄风。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主流动静观的批判确乎思虑十分深远。静坐虽是炼气一道,但如果全体皆从此道,则救国只能成为空话。毛泽东批判中国单尚文静读书,轻视勇武格斗的文化精神的目的自然也是当时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寻求救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与首先提倡健身强体体育教育者福泽谕吉的思考在深度和方向上都相去甚远。“文明其精神,野蛮去体魄”的思想尽管有一定源头,但青年毛泽东将其凝炼为中文名言,无论在表达方式和蕴含的思想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4 结语
青年毛泽东1917 年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名言在思想上受到过由陈独秀等传至中国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日本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但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影响极为广泛的名言在毛泽东写作《体育之研究》之前并无其他人以中文表述过,应是青年毛泽东接触到类似思想后经过深思熟虑而凝炼出的中文名言。在毛泽东的意识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和目的指向与其他思想者的类似见解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因此,认定这句名言出自青年毛泽东应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