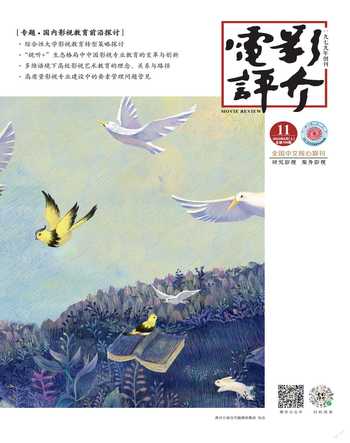电影组织的有机性:基于视知觉角度的解读
人类天生就会观看与倾听,但是否天生就会看电影,则颇受理论家质疑。观看与倾听是身体对视觉信息、音乐或动力做出的一种天然响应,同时要求发挥关注重点信息和知觉的辨识能力。一部分人认为,电影是一种根据特定“语法规范”构成的类语言系统,其本身具有组织性与深度;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我们面对艺术时,经常过于注重系统化的语言逻辑而忽视了我们原本拥有的、通过各种感觉感知事物的天分。①这是电影艺术本身具有的两种面向。电影展现了一个人对自我的理解与认知,人们在电影院中对看到的和听到的信息高度敏感,也调动了诸多视听感官彼此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观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认知和感知活动,尤其那些具有“观影门槛”的“艺术电影”,它既要求观影者具有一定知识素养,又要求观影者保持天生和自发形成的敏感性。本文将从视听感知的角度出发,对电影作用于观众的组织作用,以及电影架构本身的有机性进行评析。
一、观影过程对观众的建构性组织作用
传统电影院中的观影具有一个高度相似的明显形态。首先,观众进入电影院,坐在自己的固定座位上,行动趋于静止。在短暂的等待后,灯光暗场,银幕亮起。观众此时会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影院中唯一的发光物——电影银幕,正如柏拉图曾提到的“洞穴囚徒”一样。[1]将目光在黑暗中投向发光物不是根据后天生活所形成的经验,也不是通过教学得到的,而是人类被吸引时的自然反应。继而,观众会自然而然地将连续运动的静止画面通过视知觉联系起来,将它们当作一组运动的幻觉;其中即使有不同场景的连续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连接,观众也会在理解上将它们“误认”为是实际接续的。
如果回顾这一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观影过程,则可以从其中的三组明显特征中发现观影过场对观众的建构性作用。首先,观看电影调动是人类生物性的原始本能。尽管这一反应根本而原始,但同样需要观众发挥出精细发达的认知技能。电影如柏拉图“洞穴之喻”投射在洞穴之壁上的影子,将人类的吸引力牢牢固定在屏幕上。许多电影学者与创作者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做出了诸多努力,他们不断改进电影放映的技术,并在电影语言的范畴中制定出一套“零度语法”②,让观众始终置身于故事情景的幻觉之中。③在这些努力之外,人们将视线与注意力投射在银幕上的本能反应却不是出于人类的文化创造,而是根植于我们生物性的自然条件反射。在对银幕信息的接收中,观众的注意力在不同的视听重点之间跳跃转换,不断集中与分散。感觉、倾听,并对银幕中的事物做出恰当的反应等,调动的不仅是观众的视觉与听觉,更是一种基于视听感官产生的高级理解和认知反应——这就是被格式塔心理学者证明过的“视知觉”。格式塔心理学的关键人物阿恩海姆认为,感知,尤其是视知觉,具有思维的一切能力。“这种本领不是指人们在观看(包括同时的聆听)外物时,高级的理性作用参与到我们习惯上以为的低级的感觉之中,而是说视知觉本身已经具备了思维功能,具备了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2]换言之,视听觉本身即包含对世界的积极探索和选择,对事物本质的把握等一系列曾经被认为是“高级”的思维活动。
在电影《扬名立万》(刘循子墨,2021)中,几名电影人围绕一桩真实案件的改编剧本展开了版本各异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亲身演出”的方式参与到影片构思的过程中。他们首先以“悬疑”为切入口试图揭开案件的谜题,但很快被更具有大众吸引力的类型要素转移了视线;接着,片中的导演和编剧以打破类型和结构基本定式的方式,对电影的构成进行了批判。在此之前,电影的结构只是结构,不是故事;但《扬名立万》对各种类型电影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戏仿与委婉的批评,属于电影人的“自由发挥”,充满元叙事和互文意味,这也是该电影之所以能打动观众的亮点所在。“爱因汉姆就艺术家利用电影进行的艺术创造过程,提出电影是被人支配、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媒介。……电影媒介追求的应当是形式性的表意影像,即用电影的语言和语法进行表达。”[3]但至少潜在来讲,观看优秀的电影对于观众而言是一种快乐的源泉。在戏仿与反思的过程中,编剧、导演等某一人物边叙事边参与故事,一边与其他人探讨故事的发展和进行,但又不承担主视角;而其他参与讨论或被“邀请”到新片制作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物无不欣欣然地忘记了探讨电影拍摄的初衷。这样的故事显示出电影是怎样在被观看的过程中组织我们的。
观影过程是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也是电影对观众的“侵入”、塑造和成就。身为“观众”的主体在这个活动场景中被组织、塑造了起来。因此,观影本身是一种带有建构性和创造性的组织活动。组织活动本身是一个生物概念。“生物都是有机体——有组织的整体;而且生命留给科学的一个核心的概念谜题就是去解读单纯的物质以及本属物理学的秩序怎样被挑选出来,并以这样一种自我创造且创造世界的生命方式合成一个整体并被组织起来。”[4]组织活动不受任何主观主体的影响和操控,它体现着纯粹自然的时间结构。
二、有机架构中交错往复的视线与其功能
现代生活中的组织架构普遍存在,任何集体机构都有它的组织并依赖于组织的形式存在。组织,从根本上来讲是现代人普遍的生命状态与存在状态。只要活着、与周边的环境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就要依靠组织而存在,并被组织接纳成为其中的一体。从这一角度说,所有进行着物质与信息交换的组织都能被称为有机体。在格式塔心理学的范畴中,应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的艺术便是一种典型的有机体。“艺术是有机体的产物,因此不可能比有机体本身复杂,当然不见得比有机体本身简单。”[5]电影院中的观众与社会组织中的个体一样,被电影/社会有机体接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在自身的物质与信息交换中参与整体的互动,而整体性的有机体也在更大程度上在这些活动中被组织起来,进而成为一个由诸多部分和个体组成的统一、自洽的整体。因此,以有機性的概念理解电影艺术与电影艺术的本源,即使不是那么恰当,也是一条卓有成效的路径。
上文已经提到,电影对观众的影响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电影与观众之间在表面上是看与被看的关系,但在深层上也有视线的往返。这样复杂的感受在视知觉方面体现为对视与相互感知。在英国学者约翰·伯格对贾科梅蒂画作的论述中,当观者“站在他的位置上,遵循他凝视的轨迹”时,画中的人物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观者的凝视。“刚开始好像是画中的人物先来回打量你,他凝视,你也回应。无论你从多远的小径来回,凝视的眼光终会穿透你。在大自然里,空间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自成一体的存在状况。它是已经形成或是将要被占有的。空间在大自然里是包含在种子里的。”[6]观看电影的观众必然遭到电影的“回观”,只是大部分叙事电影会用剪辑与表演技巧掩饰这一视线的存在而已。从意识层面看,当观众与电影“相互注视”时,既可以说是观众通过电影回看自身,也可以说是观看或注视这一行为组织了电影与人,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主体,在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上组织了起来。折射的光线与视线一道形成一个围绕“观看”而形成的场域,它们将看与被看双方的行为相互联系起来,并在融洽和谐的秩序中协调它们的关系。如同相互注视的双方常常会不经意地采取同样的姿势一样,正在观看电影的观众也会不自觉地配合电影协调自身的动作。这样一来,“看”就成了一种包含观看、倾听、思考、集中精力、作出反应的复杂活动。
对视有它的功能和目的,是一种沟通感情、共同生活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机制。简单的对视只是一种原始的对话形式,更好的表达方法则是根据表达语言、观看兴趣及观看场合的不同,以不断进步的电影语言对它进行改良,并在交错往复的看与被看中展示自身。对于电影作者而言,电影的创作也是一门预判观众心理,让自身的“视线”恰到好处地与观众交错的艺术,优秀的导演会提前预知观众的反应并调动自己的创作工具,积极与观众“互动”。如芬兰电影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便将戏剧情景中应有的剧烈反应不断悬置,以角色平静的表情和行动应对本身剧烈的事件,从而营造出黑色幽默的效果:《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的开头,失忆的流浪汉M为了8个土豆与一个精明的治安员,也是将集装箱租住给他的邻居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寒暄。治安员无论如何都想得到M的土豆,最后甚至搬出他曾经救M一命的理由,要求分走一半土豆;M则默默地把小土豆对半切开,分了一半给他。失去全部身份与生存意义之后的情景本来蕴含着强大的戏剧性,但阿基影片中的主人公却总像是在开玩笑一样讨论着这些话题,而且严肃得过于认真。
布列松则以极度简洁和快速的剪辑,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应接不暇的事件,他总是能以最少的画面交代一起完整事件。影片《扒手》(罗伯特·布列松,1959)中,那些简洁流畅的动作特写镜头让人叹为观止:几个人在一起行窃,一个人摸到钱包,下一秒钱包已在同伴手中,一件外衣的遮掩又让它转移到别处。反复地拍摄这些镜头,将一个复杂的合作交代得清清楚楚。在主人公被羁押后,对准警车后排的摄影机以定机位拍摄了一位警官面无表情的神态,他旁边的小偷撬锁后冲向车外,他却丝毫没有为之动容,摄影机镜头也没有移动;很快,这个小偷便被抓了回来。镜头感觉已经由冷静转为一种喜悦,似乎能捕捉到人物动作的一瞬就是一切。布列松以这种极度简约的方式表达出小偷逃跑的不可能性。再例如,电影《驴子巴特萨》(罗伯特·布列松,1966)的开头,一声驴叫插入开头的奏鸣曲中,接着黑色的驴上出现一只白色的手,镜头顺着手反方向拍摄小孩,此时父亲的声音出现在画外音中。溶镜剪辑后,父子两人一起牵着黑色的驴走下山坡。这三个简单的镜头讲述了父亲没有拗过倔强的儿子,为他买下了驴,但两人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矛盾,驴子也注定不能在这个家庭中长久生活。当观众看到孩子的表情主宰画面,他们已经具备思维功能的视知觉,便会对这一幕加以认识和理解,意识到孩子才是最终做出决定的人。罗伯特·布列松以这样的方式,用电影语言代替复杂的话语描述,与观众进行“对话”般的交流,令人愉悦、引人入胜,令人忘我且富有挑战,如此等等。电影的意义表达深刻地借助观众与影片的互动;观众则能从不同风格中辨认出影片的作者特征。
三、视知觉组织的自然性与创造性
组织活动深植于人类的日常习惯与生物性之中。形形色色的观看以及观看之中的交流,在走路、交谈、观看等日常活动中较好地体现出来,它们是主体亲密交流、全神贯注的表现之一。观众将电影世界当作真实世界,自然并顺畅地移情于电影之中,这一活动正是“迷影”状态下,不同主体同心协力的一个典型表现。电影中的认识与现实中的认识一样,其范畴无非是“积极地探索、选择、对本质的把握。而这一切又涉及对外物之形态的简化及组织(抽象、分析、综合、补足、纠正、比较、结合、分离、在背景中突出某物)等方面”[7]。从某种角度而言,辨认出某物是某物在本质上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关键一半。从影片中看到、听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感知过程的重要一环。
在这一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事件是自然地发生在参与者神经系统里的。例如悬疑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刁亦男,2019)讲述了一场发生在南方某小城市的聚会,五名角色各异的参与者相继被卷入这场漩涡中,其中甚至包括一名罪犯与追捕他的警察。在罪与罚、冒险与爱情、人性与救赎的夹缝之间,所有观众都紧密关注着这场戏剧该如何收场。导演以精心的调度和精细的光影描摹出一场惊心动魄的宴会,经济并不发达的南方小城与城郊图景,在霓虹灯的映射下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之前贾樟柯、毕赣等导演的特别风味:山顶车灯流光、男女主人公在湖面泛舟、低矮的平房中水汽氤氲……导演展示城郊社会图景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将之升华为一种独特的审美空间,一种继承《白日焰火》(刁亦男,2014)风格的独特城市美学。在建立城市美学空间的同时,摄影机也几乎无穷地展现了足够而丰富的社会景观。电影里的人物受困于最普遍人类的困境,镜头穿过一切布景直达最本质的地方。《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南方小城”是一个无法用社会化思维来考量的空间,镜头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甚至连猫眼、猫耳,他们的恶都是天然的,是道德没有办法抵达的地方。在视知觉的组织过程中,如果要在一种有目的的状态中将其组织为工作的一部分,就需要进入“物我两忘”,忘记自己在操作这一事项的投入状态。同样,要欣赏这样一部情绪自然的“空间”电影,需要全身心投入“感受”电影的过程中。《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出现了许多道德有瑕疵的人物,但他们并不是导演设置的批判对象,而是南方小城与整个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电影空间的南方小城,则是用来欣赏和让观者身处其中的,而不是用来分析的。
换言之,知觉经验先于语言概念。因此,视知觉接受的信息也是自然发生的,其他人难以通过外在干预参与者的神经系统,改变或打断参与者的认知活动;后续建立在电影现象之上的描述性语言无法真正再现电影影像本身。这也是格式塔心理学所强调的部分所呈现的意义远远大于各个部分之和,最为本质的现象无法在分区块的范畴中体现出来。
结语
在看似“自然发生”与“自然感知”的观影活动中,人们是以一种自身缺乏了解的习惯性天然方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方法看似寻常却充满有机性,既是现代社会将个人联系为集体的基石,也是电影艺术影响观众的关键。在视觉与听觉的运动中,外物引起的刺激在大脑中互相作用,在完形心理学中完成一种可感知并记忆的有机融合。它既是原始自然的视听素材,又是一个天然的建构性文本场域,需要观众以超越既有经验的方式集中精力去观看、理解和经历。换言之,无论创作者或是观众都无法主宰影片的表达活动,不能将自身的观念通过媒介性的电影表现出来,这才是观看这部电影的方式,否则便会损伤电影本身的意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四书[M].刘小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
[2][7]李稚田.电影语言:理论与技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5,64.
[3]王微.鲁道夫·爱因汉姆的媒介论与电影形式主张[ J ].电影评介,2021(15):59.
[4][美].阿尔瓦·诺伊.奇特的工具[M].窦旭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77.
[5][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42.
[6][英]约翰·伯格.看[M].刘慧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8.
①李稚田.电影语言:理论与技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
②零度语法:即以经典好莱坞电影的视听语言为代表,利用镜头创造一时空连贯幻觉的形式與风格。
③李稚田.电影语言:理论与技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17.
【作者简介】 王新宇,男,山东聊城人,韩国清州大学电影影像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特技与特效电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