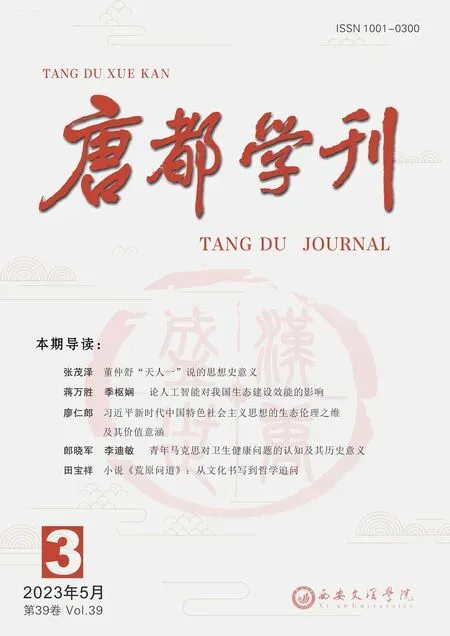“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刘书刚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100)
《史记》在传记书写上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常被推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成立的标志(1)参见赵生群《〈史记〉纪传体与传记文学》,收入《太史公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296页;张新科《〈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收入《〈史记〉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1页;安平秋等《史记通论》第五章“创立传记文学”,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傅刚《〈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史记》中涉及的人物品类繁多,客观来说,最出色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属士人群体。司马氏父子对此认知十分明确。司马谈临终时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4001“忠臣死义之士”与“明主贤君”并举,自孔子以后的四百余年间,士人们颇具壮采、令人钦慕的生命,是其着重关注的目标。“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4027渴慕名声而积极作为、秉持节义而磊落昂藏,这也主要是士人的性格特征(2)参见韩兆琦《司马迁与先秦士风之终结》,收入《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9页。。士阶层于春秋战国之际登上历史舞台,随后无论在社会政治的演变中,还是在思想文化的创造上,都展现出充沛的能量,并且,士人有着相当的生命自觉,具有反思、审视生命的意识,在思考个人命运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常见的思路和模式。因此,士阶层的发展,既是促使以人之一生为对象,详叙其始终本末、曲尽其转捩关节的传记体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为司马迁书写士人生命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范式。本文即尝试以士人“尚志”的特质为切入点,以孔子、屈原等士人中的典范人物为代表,阐述士阶层的发展与《史记》士人传记书写之间的密切关联。
一、“各言尔志”:孔子对士人生命的关注
列传描写一人一生之行迹,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体式之一,其出现需要一些条件。传记的写成,意味着人的一生经历,已经成为一个富有价值的审视和书写对象,且一生之中林林总总的诸多事件,在剪裁挑选之后,可以整合进一个首尾完具、一脉贯穿的叙述结构之中。因此,个人介于生死两端之间的作为与遭遇,足以使人们产生好奇,引起注意、观察、琢磨,进而载之于书,这是传记这种文学体式出现的前提;在繁杂事件中找到可以串联起一生大概、隐伏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之中的线索,则关系到传记书写能否完整而精彩。简言之,传记写作并不是简单地按时日巨细无遗地罗列个人经历,需要赋予人的一生以某种特定的整体性。
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出现,强化了这种为人之一生赋形的意识。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置身于秩序由崩溃到重建的历史时期,无论对社会还是对自我的未来,士人们都有诸多的期许;未成一统的天下局势、尚未闭合成型的政治机体,客观上也使他们有多样的安置生命的方式。当被问及“士何事”之时,孟子断言曰:“尚志”。赵岐注:“尚,上也。士当贵上于用志也。”[2]926以尚志为事意味着如何设计自己的生命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如何在诸多人生的关口做出恰当的选择,让短暂易逝的一生具有深沉阔大、甚至垂之不朽的意义,士人们需要仔细考量、谨慎安排。士人们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择善而固执之,而他们清醒的人生选择、执着的理想追求,以及个体命运在历史情境之间的变幻沉浮,使其一生事迹,围绕着“志”的抉择与确定、实现与顿挫,可以被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对于传记书写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
在士阶层分化而出的历史进程中,孔子及其弟子的出现有着标志性意义。孔子“士志于道”一语,成为此后士人们理所当然的自我定位。“道”之一词内涵广阔,在学道、行道、守道的总纲目之下,士人可依据自己的兴趣、境遇、遇合等因素,分殊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各立其志。孔门对于立志一事十分慎重,也乐于相互切磋琢磨,“各言尔志”,成为一种未经刻意安排、却时有发生的交流活动。《论语》中载录二例,其一如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3]204-205
更著名的一次“言志”活动载于《论语·先进》篇,发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时。这类活动往往事出即兴,弟子们的回答最能显现其心中对于人生念兹在兹的谋划与期待,由于性情、识见、才能等因素的作用,每个人的志向亦各具特色。“苟志于仁矣,无恶也”[3]141,在仁义之道的许可范围之内,孔子对弟子之志的差异十分包容,对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乏鼓励;他乐于引导、主持并参与这样的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弟子们各有不同的志向里所包含的积极、活泼的生命意识,能够给他以心灵的欣慰与愉悦。放大些说,他此时看到的,是崭露头角的士阶层无比丰富的可能性,是他们饱满的活力和可期的未来(3)有学者指出,孔门的言志活动在形式上承继了春秋时期宴飨时的“赋诗言志”,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孟令郑国诸臣赋诗观志之类。不过,正如朱自清在其名作《诗言志辨》中所指出:“献诗时代虽是作诗陈一己的志,却非关一己的事。赋诗时代更只以借诗言一国之志为主”,至战国时,屈原、荀卿等人作诗,方才“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20页。这意味着,“志”一词虽然早就为人们使用,但其内涵则随时世而变化,约在孔子之时及战国时代,方才与个人的人生选择、命运的穷达通塞关联更密,而这种内涵显与士阶层的出现有关。。
所选之志如何,可以为个人的立身行事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向往之、奔赴之,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影响一生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尽管不要求遵循某一特定的人生路径,孔子还是更欣赏自觉而笃定的人生态度。“笃信好学,守死善道。”[3]303“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354能够立志不移、黾勉从事,不仅是有所成就的关键,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德行。相反,对生命殊无自主,浑噩懵懂而随波逐流者,每为孔子所不屑。不因堕怠而丧志、不因穷约而改节并不容易,半途而废者比比皆是,克有其终者鲜得一见,需要强大的自控、坚定的意志,才能保证平生之志的达成。为此,士人需警醒于时间的平白浪费,更需对志业之难有着充分的认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3]627“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3]664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不能求学以自拔,势必陷溺于无所作为的庸碌之中。
笃行其志、渴望有所作为并传名声于后世的士人,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迫促,孔子因此十分敏感于年岁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3]352“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3]709到达一定的年龄,却无与之相应的名望、声誉,即使不算是人生的彻底失败,也已经浪费了偌许的时间。由此,孔子时时检省生命的进展,以求日益精进,以免有所偏失,对于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处世风格,逐渐形成一些总结性的话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270正是因为自信于自己的本初之志,才能学道勤勉而不倦,历经困厄而不忧,“不知老之将至”,恰恰意味着过往时日的充实。晚年之时,他历数自己一生之递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43
暮年晚景,回顾一生循序渐进,每一阶段都有适宜之造诣,终至于从容中道,无过不及,而这一切始自“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4]“志于学”实际总括孔子一生,此后若拾级而上的一再进益,都可以算是学而不厌的结果。“此章真夫子一生年谱也。自叙进学次第,绝口不及官阀履历、事业删述,可见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5]这样以立志为学为主线,孔子为自己的一生做出了一个有次第、有逻辑的叙述,为此也省略了生命的其它一些面向。虽然简略似年谱,但这样的自我总结,表明人的生命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有趣味、有意义的观察对象,而这正是传记书写的必备条件。
不仅时常反躬自省,孔子也乐于打量他人的生命。他自许能知人,这自然需要观察他人的生命历程,忖度其心灵心境,而在孔子用以观人的诸多标准中,立志如何是极为关键的一点。很多历史人物也进入到他的观照视野,特别是在人生选择上给予他启发的一些先贤。“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3]728是高尚其志、洁净其身,还是在现实处境里稍稍自我贬损,抑或隐避其身、放绝其言,在议论他们时,孔子着重辨析的正是在志向与境遇有所龃龉之时,这些人各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他自己也能从中得到借鉴,获得更通脱、更豁达的处世态度,“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3]729在孔子评价之后,伯夷、柳下惠等人,一直是儒者处理进退出处等问题时的参照,换言之,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实际影响了儒者志向的确立(4)孟子在《孟子·万章下》讨论出处去就问题时,同样引伯夷、柳下惠等人为例,并总结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立志并持之以恒固然重要,但人的命运实由诸多力量一并决定,有时即使多方探求,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在焉,由此,“天命”成为孔子思考人的命运莫测时常常需要假借的一个因素。“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3]273“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3]592“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3]593以弘道自任,以斯文之传为职责,自己立身行事合乎天道,对此孔子深信不疑。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钱穆云:“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困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6]推知天命,是行其夙志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环节,经此境界之后,方能从容应对诸般困厄。然而,尽管自信所立之志合乎道义,德行与遭遇之间的反差所折射的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幽微关系,还是成为儒者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春秋以前的贵族社会中,血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身份、地位,卿士大夫们在人生选择上享有的自由有限,而随着礼坏乐崩出现的士阶层,则需要仔细谋划自己的生活,“尚志”的观念由此产生。作为士人的先导和榜样,孔子赞赏清醒、自觉的人生态度,并格外关注立志一事,他不断省察、总结自身阅历,也自信于知人识人,这表明人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审视,甚至有审美意义的对象。并且,以“志”的选择和践行为线索,士人的一生就可以被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叙事中,而孔子自往圣前贤中寻找榜样以确立、支撑其志,自天命幽微处,扣问命运的莫测多变,则将生命置于古今、天人的交互之中。这些不仅是传记这种文学体式成长的基础,且为如何铺陈传主的命运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可以说,叙述士人生命的基本范式,在孔子这里已见雏形。
二、壹志难徙:屈原诗歌的自传性
尽管在孔子这里士人生命已经成为观察的对象,但随后的战国士人并未在传记书写上花费太多心力,士人对自我生命的文学呈现并不充分。屈原的诗作就显得弥足珍贵。他更多地面对个人的生命经验、情感郁结,并付诸繁复的修辞、深湛的比兴,诗歌这种主于抒情的表达体式,因此具有了浓郁的自传色彩;特别是《离骚》《九章》诸篇,因情而寄辞,随事而成吟,与屈原之生命相始终。探究传记文学的发展,屈原诗作应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环节(5)《史通·序传》中已注意到屈原诗歌的自传性质,并认为屈原与司马相如一道,启发了司马迁自传的写作:“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
《橘颂》常被认为作于屈原早年,其一生命运在诗中也有着谶语一般的预示。“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7]153橘外有文章之绚烂,内蕴甘美之实质,恰似君子之表里如一,如此嘉树,生于南国、不得移植,正好比屈原年少即有非常之志,并将自身命运紧紧拴系在楚国土地上。他意识到自己志向与所处环境的不合,也觉察到将遭遇难耐的坎坷,但志节既立,自无变改之义。“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7]154保持其特立独行需要对抗流俗,也必然因此付出惨痛代价,屈原似乎意识到如此执着的持志立身,很大程度上会让其命运难以顺遂。此后的诗作中,屈原不断强调其本志初心自立定就再也不得变更。他营造出一个复杂、庞大的意象体系来象征这点,如以衣着装束的盛饰华美,来隐喻自己内在的美好。“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7]128“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7]17无论以长铗俄冠、珠玉珍奇装点,还是以芳草众卉制作衣裳,都显示出屈原的不合于俗。以“奇服”自饰,即以“异志”自矫,幼年即已如此,至老毫无衰歇,早就确立并坚定不移的志向,既是他人生之路的起点,也是在遭遇忧患时会重新回归的据点;它指示的道路,必然走向与俗世的冲突,但又能抚慰碰壁而带回来的创痛,屈原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种奔赴与折返中反复。
屈原越是铺陈自己“奇服”“初服”的盛大华丽,在愚昧不明的俗人眼中,他就愈发显得满是怪癖而难以理解。无意的误读与质疑,有心的曲解与谗构,面对这些,屈原知道守护志向的难度,外在的压力或同化,内心屈抑孤独的摧折,很容易让人与世俯仰、不复当初。他反复诉说对于志向的坚守:“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7]127“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7]142“欲变节以从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凭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7]147不浸染于流俗,即使困顿倾覆也不变易其心之所善,这种表达出现得如此频繁,除了以诗句昭示内心之外,也像是一种自我训诫、自我鼓励。
志不得申的低徊沉郁、不为人知的黯淡寂寞,这些情绪在战国士人中十分普遍,但正如孟子所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2]193,既然不怀疑自己秉持的规矩原则,他们也常表现出人所不及的强韧与勇决。一些诗篇里,他就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困境,与亲友或假想的巫者、神灵讨论。如《惜诵》中,厉神告之曰:“惩于羹者而吹齑兮,何不变此志也?”[7]125遵循前路必若登天之难,鉴于此前之车覆马颠,为何不改变原本之志行?《离骚》里,女媭的建议大致相近(6)《卜居》《渔父》两篇作者尚有争议,但屈原与太卜郑詹尹、渔父讨论自处之道的基本情节架构,与此处所引段落十分类似,可以反映士人在人生选择上的心理纠结。:“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7]19但每一次他人的劝导,最终的结局都是他更加坚定地执守“幼志”“初服”。他的专心一志、深固难徙,也将自己围堵进了“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8]的境地。概言之,“志”之持守,实为屈原生命轨迹中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志向不能有所枉曲,现实又无可奈何,屈原的生命就变成一种无望的拉锯。生命的尽头是死亡,对于常人来说,死亡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局,是强加于人的,人在其面前总是处于被动;但对屈原以及一些战国士人而言,死亡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并且,这不是因不堪折辱而自寻短见,不是因心情沉郁而自求解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情形下,自杀是成就其志的手段。如果活着却哀诉无告、劝言不听,那么,以死为谏,有没有可能警醒君主、震慑世人?“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7]146以死明志警世的念头,闪现在屈原大部分的作品中,并越来越坚定。自沉不是自弃,反将升华其生命。这毕竟是种极端的方式,屈原也有些犹疑,死亡会不会带来期许的效果,能不能在君主、世人的心中,摇荡起一些涟漪。但在志向永无达成之日的境遇里,死亡却成为唯一的可能,成为屈原不得不选择的孤注一掷。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成就生命,死亡是一场关乎志向成败的豪赌。
与孔子一样,屈原在立志、行志的过程中,每每取法古人,或者试图从古人处勘悟命运之谜底。《橘颂》中,“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7]155,是他年少时自勉的典范。在萌生自决之意后,介子推、申徒狄等有着类似行为的前贤,也常出现在其脑海,而最为他所倚重的则是彭咸。“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王逸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7]13即便不能让君主幡然醒悟,这些古人流传身后的名声,也许能给屈原一丝宽慰。他还在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总结经验,确认自己坚持的那些原则正确无误,自己的本志并无偏曲,而更关乎心事的,则是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那些悲情人物。“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7]131忠正贤良之人不必善终,自己并非被噩运恰巧砸中的唯一一个,屈原以此宽慰自己,但这恰恰反映了他由来已久的迷惑:为什么命运如此经常地与德行、才能相悖谬?
“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7]144从君臣遇合这种十分具体的个体遭遇出发,屈原的追问逐渐扩大至往古来今,《天问》之作,正由乎此。自遂古之初、上下未形,直至楚国混乱衰败的当世,他有着太多的疑惑可以质询,诗篇思索的范围贯彻古今、包囊远近,稽查的对象穷极万物、遍及人伦。然而,如洪兴祖说:“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7]85历来国家兴衰成败之由,以及被裹挟在历史之中的个人命运的升降起落,才是屈原格外用心的话题,也有很大可能是创作此诗的原动力。换言之,他好奇个人命运的形成,且将之置于宇宙时空之间、古今天人之际,这与孔子颇为一致,也将影响司马迁的传记写作(7)可参考常森《屈原及楚辞学论考》第三章“屈作之历史视野”和第四章“屈原天命观及其解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诗歌以抒情言志为基本功能,情志产生于个人的经历和遭遇,更进一步说,产生于个体与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的碰触,因此,抒情诗往往具有自传性。屈原的创作与其政治上的失败密切相关,在他的诗篇中,这种失败被叙述为自己早早确定的志向,与昏昧不明的君主、嫉妒谄佞的同僚、庸常恶浊的俗世之间的冲突,甚至他的自沉,也是其坚持“幼志”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以“志”为核心语汇,屈原在诗歌中将自己的生命提炼成书写的对象,并且,因为自己的不幸,他对命运有着众多疑惑不解,又上溯古人,究极天人,追讨个中原因。尽管使用的是诗歌这种体式,但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已经浮现的书写士人生命的范式,被屈原进一步发展、充实,并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树立了榜样。
三、“荡然肆志”:《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士阶层分化而出、不断发展,感慨于生命的不可重复和时间的难得易失,以“尚志”为特征的士人十分注重志向的选择,而行志过程中有幸有不幸、当然而不然,诸多始料未及的挫折与错愕,也促使他们思考造就命运的力量究竟为何。于是,围绕着对生命的观察和考索,孔子、屈原援古证今、推天及人,逐渐形成一种总结、叙述士人生命的基本范式,直接启发了司马迁的传记书写。
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无以复加。“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1]2356他无限景仰孔子,爱慕之意溢于言表。他对屈原则满怀同情与悲悯,“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1]3034伟大的人格之外,孔子、屈原之所以为司马迁所重视,也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创造、著述咏歌为其树立典范。“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1]4001《史记》本就有取法《春秋》的意图。屈原著作中,司马迁于《天问》用力尤深,曾诠释解说,“口论道之”(8)王逸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传教,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见《楚辞补注》,第118页。,而这同样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总之,司马迁著史一事,孔子、屈原皆堪称先导。
司马迁读屈原诗歌而“悲其志”,这意味着“志”是他用以解读屈原作品、理解屈原人生的关键词。正是由于敏锐地察觉到“志”对于士人的重要,司马迁写作时对此特别关注,非仅屈原一传,在很多篇目的“太史公曰”中,他都提及了“志”这一字眼:“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3079“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1]3003屈原、刺客、鲁连,这几乎是史公传记中最出色的篇章。刺客五人,或久居下位,或藏身市井,但自信于自身的能量,一直等待着一个时机,纾国之难,为知己死,试图用非常的方式改变形势的进展,甚至将自己的生命,在一个近乎惨烈的瞬间里绚烂燃烧。“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为此,他们既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也随时准备在某个恰当的时机挥霍自己的生命。鲁仲连则是战国这个特殊时代里出现的极具个性的人物。他不乏政治才干和游说才华,几次救人急难、为人消忧,却功成身退,在他看来,政治世界虽能提供世俗的荣耀、经济的富足,但会禁锢个人之自由。他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1]2992正是因为其“志”在彼不在此,他的一生才显得那么通达,那么传奇。“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这种傲视王侯、自足其志的风骨,被司马迁描绘得栩栩如生。
后儒多有非议为刺客等人作传者,但司马迁所激赏的是,这些人虽然混迹于市井屠沽之中,却能在确立其志、认定某种特定的行为准则之后,一以贯之、至死不渝,不会有任何的退让、屈折,因此也制造了格外精彩的生命景观。很大程度上,他是以审美的态度来观察这些鲜活、热烈的生命。人之笃行其志并不容易,现实因素的掣肘,意料不及的阻滞,都有可能导致“志”的夭亡,因此,司马迁格外欣赏为成其志、隐忍以待时者。范雎、蔡泽初时贫贱不遇,屡遭折辱,“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恶能激乎?”[1]2940对他们来说,困厄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潜力,终于得以“尽意”。“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淮阴侯列传》)[1]3187正因为背负异志,韩信寄人衣食、受辱胯下才能不以为意,终成后日之大功。魏豹叛汉,虏于韩信,彭越谋反,囚于洛阳,“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1]3147二人德行不足观,人格不足道,但不甘心一身智略再无施展之日,竟能忍垢受耻。慨叹这些士人的忍辱负重,固然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有关,但主要则是因为士阶层以“尚志”为事,为求“志”之实现,不辞耻辱、甚至不择手段,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士人自觉于生命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对于死亡的意义他们也相当明确。承认死之必然则更加珍惜一次性的生命,垂名后世、功烈千古,无非就是抵制死亡抹消生命的意志。因此,忍辱以避死,不是出于畏惧,而是为了让生命更加饱满充实。季布功显于楚,堪称壮士,而甘心髡钳以求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1]3311出于几乎同样的逻辑,在必要的时刻主动赴死以成就生命的壮彩,士人们也每每心甘情愿。“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为此,司马迁总结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1]2971死亡终结生命,但若处之得当,也升华生命,司马迁赞赏这些士人们在生死之际的自我安置,与欣赏他们立志之坚、行志之笃,实为一事之两面。
在以士人为书写对象的传记中,司马迁重视传主之“志”,分外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种种倜傥非常之事。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是士阶层分化而出、不断发展的结果,太史公也以浓重的笔墨,为这一时期士人们异彩纷呈的生命传神写照。需要强调的是,描写士人的篇目在《史记》传记中所占分量虽大,但并非全部;也不是所有士人立志、立身皆有可观之处,太史公并非每篇传记都以“志”为脉络来设计结构。但在最具声色的传记之中,司马迁关注、强调传主之“志”的篇目不在少数,已经足以说明,很大程度上,是那些秉持其志、奋不顾身的士人的作为,使人的生命具有了可欣赏、可书写的价值。传记一体的发生发展,从“士尚志”这一历史现象中受益匪浅。
如果说孔子、屈原对人之命运的思考,更多源自个人遭遇的激发,那么,司马迁对命运的好奇,就更能显示出史家开阔的视野,在其行文设计、篇末论赞之中,他常常针对各类传主的经历,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命运的肯綮。扭转人生走向的,是个人的“计之生孰成败”,还是“势”之不可抵挡?(9)语出《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第3203页)《史记·楚世家》:“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第2092页)是祖先的阴德余烈提供了福佑,还是行事的酷烈残忍引发了祸报?人物不同,司马迁提供的解释也随之而异。并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9],他将个体命运置于古今、天人之间考察,这种意识较之孔子、屈原要更加明确。不妨以《项羽本纪》为例,分析司马迁对人之命运的琢磨与解释。楚汉之际,短短数年之间世局倾覆,乱局之下涌现出大批光彩夺目的人物,项羽少年得意,由籍籍无名而席卷天下,又迅速败亡而首身分离,其命运转折之剧烈,在当时无人能及。自负于勇力,项羽对自己的兴也勃焉毫无疑虑,但忽然而亡的结局让他深感不解。临终之际,他总结一生,将“霸有天下”归功于自己“所当者破,所击者服”的战斗力,败亡则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1]423。但在此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承认项羽的暴起确为“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奇观,却揣测“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1]428以生理特征上的近似之处,推断项羽为舜之苗裔,但“舜目盖重瞳子”本是无从确证的传闻,在很多时候都事必征实的司马迁却采信此说,说明在他心目中,项羽“非有尺寸”,德行亦无可称,其兴起只能根源于祖先积累之功德;或者说,是“天”兴之。至于败亡,则是其一再举措失当的结果,“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1]428,是这些具体的因素,最终导致了项羽霸业的覆灭。垂死之际试图用“天亡我”一语抹消自己的过错,只是英雄末路时的执迷不悟,而此又是长期以来将其引向败亡的重要原因。项王的命运确实是人事、天命两相辐辏的结果,但兴也在天、败也由人,司马迁的断语与项羽的自评恰恰相反,犀利而准确。
并不是所有传主的命运,史公都能有如此清晰、明确的判断和解释,他并不掩饰自己时常涌现的迷惑不解,这在《伯夷列传》中显露得最为充分。孔子、屈原等对伯夷早就十分关注,但他们主要是将其作为参照,来确立自己的一生之志,而在司马迁这里,伯夷的德行与命运之间的反差,成为他抛出一系列疑问的一个契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1]2585天道佑助善人,是否能在过往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司马迁历数所见所闻,德行的善恶与命运的顺遂或困厄,往往并不必然吻合。颜渊早夭,盗跖长寿,“操行不轨”者“终身逸乐”,“行不由径”者祸灾不绝,“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2585然而,尽管困惑于天道的幽深渺茫,司马迁还是认可这些命途不济的圣贤对“志”的崇尚。“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1]2587各从其志、至死无悔,他们原本并不计较坚持的后果如何,天道的悠邈、命运的莫测,恰恰让持志不移的士人们的生命自觉,显得愈发难能可贵。
作为史家,司马迁很清楚,这些士人热烈的生命、激切的行事,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得到恰当的称述而失落在历史的缝隙里,再也无从知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1]2588为这些淬砺志向、砥砺名节的人撰作传记,就成为他当仁不让的责任。《伯夷列传》为列传之首,在体例上也别具一格,恰恰清晰交代了司马迁传记写作的深刻用心,正是由于有为士人传播声闻的明确意识,他才在传记写作上倾注了那么多心力。
综上所述,一种文学体式的出现、成熟,往往由多种因素合力促成。《史记》传记之中,传主的身份、性情各有不同,传记的结构方式、写作手法,相应也有很大的歧异,不同类型的篇目在写作时所能汲取的前代资源,自然未可一概而论。就本文所关注的士人传记来说,司马迁津津乐道的倜傥非常之事,往往与“志”的选择和实践相关,他剖析人之命运时贯通古今、穷极天人,这种书写范式的确立,无疑是在孔子、屈原等士林先贤探索的基础上踵事增华,也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不断演变发展的结果。作为一个有着充沛活力和创造性的群体,“尚志”成为士人的一个鲜明特色,确立志向之后,为求其实现,不少士人往往异常坚韧、分外决绝,其生命因此也具有炫目的光辉,人之一生日渐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叙事。《史记》中的士人传记,正是对士阶层面貌声色做出的一次精彩的文学总结,在为士人作传的同时,司马迁也从这种写作中汲取了很多立身处世的经验和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