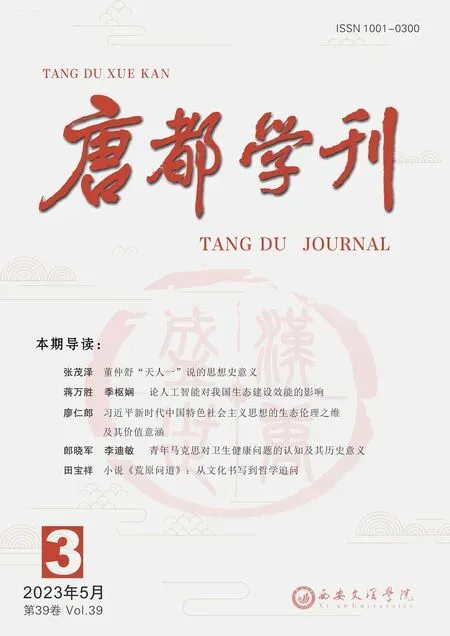青年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认知及其历史意义
郎晓军 ,李迪敏
(1.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2.香港中文大学 政府与行政学系,香港 999077)
青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也是工人阶级的“黑铁时代”[1]826。殖民地掠夺和世界市场开辟成为全球疾病的温床,工厂剥削和间歇性失业产生了庞大的易感群体,宗教麻痹和禁欲主义为神秘主义医学的复辟开路,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导致医疗服务的异化,把劳动者降为低于人的物种,社会劳动生产力和自然力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资本家为了满足其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将工人劳动卫生条件压低到最低程度。资本主义工业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流动人口“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1]765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挣扎濒死的状态,卫生健康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837—1843年,青年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认识是对资本主义系统病变的初步探察,他汲取古代哲学的辩证因子,把握事物发展的内核,批判庸俗社会观念和神学自然观的扭曲形式。在求学时期,马克思已经把平民的医疗卫生危机与贵族上层的享受嬉戏相区分,在哲学上明确了健康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社会机体的实际情况,社会机体的痼疾背后物质利益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对摩泽尔河地区农民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民众依靠自然界生存的习惯权利与资本独占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通向科学的探索之路充满了复杂性和曲折性。因此,马克思的立场逐步明晰,考察内容逐渐全面,从整体上接近问题核心,逐渐碰触到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框架,产生了新世界观的萌芽。
一、文学批评的内核:揭露社会医疗卫生危机
青年马克思是从社会上层游乐场与劳动者埋骨地的尖锐对立中叩动科学之门的。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已沉浸在欧洲经典文化的熏陶之中,熟悉古希腊语的哲学、文学、历史学著述;对西塞罗、塔西陀、贺拉斯的拉丁语作品悉心研读;学习德语世界的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作,17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文学史;阅读孟德斯鸠和拉辛等人的法语著作等。马克思不仅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知识,而且逐渐养成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进程中予以分析和定位的思维方式,还培养了对宏大主题的把握能力。1835年,马克思从家乡到波恩开始大学生活,一年后到柏林继续锻造青年时代的思想。从这一时期创作的诗词、剧本、讽刺小说等可以看出,浪漫的文化底蕴、现实的意向思路都贯穿在其创作过程中,其中部分内容以普鲁士医疗卫生问题为现实选材,通过文学批评展现了社会矛盾在该领域的郁积,映现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与贫困疾病问题的交错纠缠。
(一)艺术享受与健康状况矛盾背后的等级分化
在《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ArmidavonRitterGluck)中,马克思以夸张手法描绘穷人与艺术相隔绝,更突出了不同人群之间因财产状况、社会地位、身体素质不同而在应对气候、适应环境方面的差异。就剧场而言,它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还关联着精致而得体的行装、适应气候与环境的居所、营养而热量充分的食物等——闲暇与享受活动首先建立在衣食住行之上。剧场、舞会等文化艺术场所隐含着对生理界限与社会界限的划分,穷人经济被剥削,社会地位受压迫,健康条件遭破坏,贫民去剧场看戏获得的不是身心愉悦,而是“前胸后背一片冰凉”[2]785的身体不适,甚至追求高雅享受却因身体和精神受限而大病一场。
(二)浪漫爱情与卫生条件的冲突潜藏着普遍贫困的生活状况
“时髦的浪漫主义”[2]786(Neumodische Romantik)行为,代指部分无产者以不正当活动谋生的堕落行为,文中进行欺诈的女骗子以“我的头上没有长虱子”[2]786期望获得有钱人好感,既是贫苦人民无以谋生窘迫处境的鲜明写照,也刻画出社会底层恶劣卫生条件和健康衰退现象。穷人在苦寒和饥饿中“时髦的浪漫主义”仅仅是一种破败的体面,追求爱情的无奈。没有虱子寄生已经是平民理想的身体状况,根本无力改变过劳导致的器官衰竭、饥荒导致的营养不良、传染病肆虐导致的终身残疾等苦难现实。
(三)社会上层难逃寄生虫病的尴尬凸显了疫病的共患环境
在短章《给一个骑士英雄画像》(AufeinenRitterheroen)中,马克思描述了“总把英雄和骑士集于一身”[2]787的人,在受人尊崇、追赶时髦、大发宏论的光鲜亮丽背后,“夜里却被古老的臭虫咬出斑斑血痕”[2]787。这种被寄生虫和恶劣卫生条件造成的狼狈和尴尬,暴露了当时贵族的两面性和虚伪性,也反映出贵族同样令人堪忧的卫生状况和健康问题。社会上层虽支配大量物质财富从而获得享受和余暇,但他们不可能脱离与底层共同的生活环境条件,现实生活不存在特权者躲避灾疫的虚空,顽疾恶病只会在共患环境中无差别地传播。
(四)江湖医术盛行暴露了蒙昧主义和商品社会的无耻勾结
马克思在《致医生们》(AndieMediziner)中描绘了“市侩庸医”形象,“世界在你们看来不过是一堆骸骨”[2]789;市侩庸医的心理学是“饱吃一顿团子加面条”[2]790而免受噩梦困扰;市侩庸医的形而上学把人类与其他物种简单等同;市侩庸医的人类学把灌肠催泻作为健康文化起源;市侩庸医的伦理学只会嘱咐“旅途上要多穿几件衣裳”[2]791之类常识而对科学一窍不通。金钱和迷信充斥着市侩庸医们的诊疗过程,反科学的庸俗浅见和絮叨的常识废话是其行医法宝。因而,与其称为医,不如称其为侩。
马克思虽受浪漫主义影响而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歌作品、讽刺小说等,但他没有被裹挟进这种夹杂着中世纪幻想和现实愤懑的思潮本身,而是以自身艰苦的理论探索走向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科学审视。从医疗卫生问题的揭露和批评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停留在人与社会和睦的福音论调,或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浪漫口号上,而是意在剖析等级分化、贫富对立的病态冲突,将社会矛盾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暴发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展现出来,用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和麻木不仁为讽刺画本身注入现实动能。这种解剖刀式的观察研究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后来的理论探索道路之中,这种对不同等级、不同病态人体的剖析也逐渐向上提升为解剖社会机体的方法,转化为人体解剖通向猴体解剖的钥匙。
二、健康问题哲思:无神论倾向的凸显
如果说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体现出的是最初审视社会的浪漫主义情怀、知识结构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背景,那么当马克思经过艰苦思索,逐渐意识到不能以情感冲动和浪漫幻想去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之时,写诗本身就“仅仅是附带的事情”[3]10,如同批评普遍的病患表象一样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就需深入哲学之中。随后他专心研究,留下了七册标明为《伊壁鸠鲁哲学》(EpikuräischePhilosophie)的笔记,这是关于古代、近代哲学家著作的摘录汇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撰写了《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起始阶段的高度和水准。而健康问题在马克思的笔记和论文中是重要的研究基点之一,与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本原和元素可分性、时间作为具体自然界的主动形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逐渐构成了研究社会与自然界的广阔视野转换。马克思肯定伊壁鸠鲁的功绩——将健康具象化、实体化,指出原子作为世界本原也构成人类身体运动的基础,因此身体有朽性和健康相对性是自发偏斜辩证因素的现实表现。而基督教线性的、先验的神学世界观与疾病-健康关系中的事物运动辩证原则相悖,马克思认识到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辩证因素内含有对神创论、设计论自然观的否定。
(一)健康的物质性使其遵循原子自我运动规律
健康本身就是运动过程,“因为常有这种情况:肉体的健康状态在哲人内心里没有同对肉体的坚定和牢固的信赖结合起来”[3]74。人本身因处原子所构成物质世界而天然具有不稳定状态,所以身体遵循原子自我运动规律,健康表现为变动不居的暂时性与偶然性。神虽然是真正稳定和独立自在的纯粹平静,但神在自然规律之外,完全不受任何规定性支配。这样,上帝不在世界之内,而在世界之外,虚空中的神不关心凡人健康,也不在意个体生灭无常。
(二)健康的普遍关系性无法让渡给神
奴隶主片面个体、片段生活、短暂欢愉,只是统治阶级人群中“这一个”特殊情况,是哲人“个人本身用个人的方法”[3]74去观察和体验。平民的身体健康对于哲人代表阶级是无关紧要的,以哲人的偶然个别情况而摒弃普遍性,就相当于规定现实的人即使在自由的“虚空”也“想着各种混合物、有毒植物发出的瘴气,想着各种小动物的息气”[3]75。一方面个体作为自我特定内容不能把普遍性让渡给神;另一方面,经验个体作为原子运动具体形式必须在普遍关系中存在。所以,健康不仅属于统治者个体,还关涉众人的普遍关系,这必然与诸神的纯粹虚空相矛盾。
(三)健康与身体的同一关系排除了不朽的可能性
“健康,作为与自身同一的状态”[3]75体现为个体的本质,健康是生命运动正常过程中的表现形式,虽然正常状态表现为“自然而然被遗忘,在健康的状态中无需照顾身体”[3]75,但同一状态被破坏产生了人与神的差异性——“这种差别只有在患病时才开始”[3]75。哲人是某学说、学派体系的现实形象,哲人健康是维持这种形象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他身体健康,处在他的本质状态之中”[3]75,身体健康即处在自身本质中;“如果他病了,那么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会持久的消失状态”[3]75,以神性不朽的假象否认患病现实,视长期患病为正常状态的欺骗,只会向神祇献祭更多生命。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扉页的献词称颂“身体的健康,我无需为您祈求。精神就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2]9,反映了当时马克思把精神、自然界与身体的统一看作健康的源泉。马克思研究古代哲学时的无神论倾向,使其对伊壁鸠鲁所代表的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对研究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哲学流派深入钻研。关于健康问题的哲思否认了神对人居世界的任何干预,关注了有朽的、变动的身体状况蕴含着事物运动的辩证因素,明确了身体与健康同一作为理性的物质基础,这必然会向突出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原则发起挑战。由此也反映了马克思世界观蜕故孳新的曲折过程:无神论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尚需破解,自然观中的辩证因素与理性原则的矛盾尚待解决。总之,健康问题的哲学考察使马克思认识到神创论自然观的虚无性,逐渐意识到理性原则在解决以上两重矛盾时的片面性和乏力性,从而为马克思思想转向及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社会痼疾的脓疮:必须向社会现实开火
关于医疗卫生窘境的文学批评,使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个体的病态状况逐渐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从而为揭露健康危机背后的社会矛盾提供了现实论据;对健康问题的哲思,使马克思继承发展了古代哲学中具有辩证因素的身体-疾病观念,从而为批判神学的医学理论和设计论自然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进入《莱茵报》开始马克思又一次回到了现实,直面所谓宗教虔信的天国之神和王权专制的人间君主们的真实面目,向社会之病猛烈开火。
(一)疾病是对生命自由的限制,恶政是对社会机体正常状态的摧残
1841年,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写道:“只是在我的生命已不再是符合生理规律的生命,即患病的时候,这些规律才作为异己的东西同我相对立。”[2]176正如患病的身体不再体现为生命的本质,患者不再符合生理规律而作为异化状态与之对立。“因为不仅疾病是一种恶,而且医生本人也是一种恶。医疗会把生命变成一种恶,而人体则变成医生们的操作对象。如果生命仅仅是预防死亡的措施,那么死去不是比活着更好吗?难道自由运动不也是生命所固有的吗?疾病不是生命的自由受到限制又是什么呢?”[2]177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是一种特殊的有机体。奴役劳动的社会制度下,社会机体的病患由官方“御医们”诊断,人民的疾苦由统治阶级医治,他们把持着社会机体健康状况的话语权和操作权。“书报检查制度的出发点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状态,把正常状态即自由看作是疾病……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2]177-178统治阶级医治社会的原则是禁锢与颠倒,将社会的病态当作常态,以挖疮割痈为名切割社会机体,急于扼杀争取自由的反抗斗争。
(二)特殊利益群体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特权只会加速社会机体的朽烂
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所谓新政治生活的辩护,“等级代表们已相识多年,他们的精神像遗传病一样传给所有新来的人”[2]162,实际上形成了歇斯底里地维护特权统治的病患网络。诸侯等级辩称书报检查制度带来了德国精神的发展,新闻出版自由不符合传统信念,必然导致比利时革命那样的恶果;骑士等级以人类“不完善论”为由支持教会和国家的绝对权威,认为追求自由、废除特权的诉求来源于群众的“忌妒心”,只会引起社会混乱;城市等级则把新闻出版自由看作“为了满足个别人物沽名钓誉的欲望”[2]187,是不合理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等级制度表现的“不是国家的有机理性,而是私人利益的切身需要”[2]342,辩论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对人民权利的践踏。“如果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这种独立化是国家必然性,那么这只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正如不健康的机体,按照自然规律,必然会长出肿瘤一样。”[2]344不同的物质利益支配着不同等级的政治立场和行为,等级制度背后的特殊利益是国家内部疾病,是病态社会机体的肿瘤。马克思质问上层老爷们:“如果每一种外部的动因,每一种伤害都将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么你们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吗?”[2]349没有气节的历史法学派和官方学派只是为特权辩护的工具,新闻出版、世俗婚姻等领域的特殊利益干预只会加速其无药可救的衰弱过程。
(三)社会机体的痼疾藏于一切不合理制度之中,治疗制度弊病的真正且根本之法在于废除之
马克思结合整个普鲁士国家现实,认为书报检查制度表现出来的“这一痼疾(1)中文第二版将“痼疾”译为“根本缺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中文第一版译法以痼疾沉疴之喻突出奴役人民的制度对社会有机体侵害的严重性,结合本文立意,故选择这种翻译方式。隐藏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中”[4]30,这种对人民极端压迫、对自由极端仇视的顽症弥散在专制国家机体各部位,这一根本缺陷贯穿社会生活各方面。这是社会机体隐藏的综合病症,统治者以神学说教和政治弹压将脓疮掩盖,任其腐烂。马克思指出:“治疗(2)中文第二版将“治疗”译为“整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马克思关注到了政治生活的异化问题,恶劣制度以对立物的形式站在群众面前,结合本文立意,故选择这种翻译方式。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4]31,要让人民看清统治阶级改良的真面目,真正废除旧制度。统治阶级的特效处方是吸干榨尽劳动者,为人民灌下了蒙昧迷信的药剂。只有彻底废除维护森严等级和残酷剥削的旧制度,戳穿其痼疾缠身却装作民意所归,病入膏肓却自认为民心所向的拙劣把戏,暴露了其吸血寄生的真面目。书报检查制、离婚法等只是社会病变的冰山一角,只有彻底废除一切不合理制度,才能打碎政治欺诈和神学幻想编织出来的海市蜃楼,真正医治社会机体的疾病。
当时马克思虽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唯心主义影响,比如反对专制的依据和武器还是理性、精神这样的唯理论概念,以精神自由作为对抗压制和暴行的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制度是统一整体的理论,他肯定了国家作为有机体,而非职能堆砌和机构叠加的有机性——“把政治国家看做机体,因而把权力的划分不是看做机械的划分,而是看做有生命的和合乎理性的划分,——这标志着前进了一大步”[4]255。尽管这个有机体还被看做由理性推动,现实性的差别还被看做理念的结果,但它表明马克思已逐渐突破了黑格尔所谓“自由”服从国家利益和政府意旨的主张,把“自由”概念从专制国家的威压中提升出来,明确了自由与机体健康的同一性,区分了社会机体正常状态与病态结构的对立,自由形态与专制形态的异质性。换言之,矛头直指专制现实,把自由作为社会和国家机体的本质特征予以确认,而以疾病和健康之喻把专制压迫的病态社会结构从政治理性中抽离出去,将过去神权教条和王权专断视作与机体发展相悖的异化状态,宣扬社会机体的自由本质意味着治疗衰朽的旧躯体而赋予其新内涵。
四、工业与自然界的综合病变:转向物质利益的追查
如果说马克思在社会机体的痼疾中发现了特殊利益群体,认识到其背后森然耸立着剥削劳动者的特权制度。那么在深入追查的过程中,当探究特殊利益的发病规律时就必然触及更深层的所谓“下流的唯物主义”[2]289物质利益问题。普鲁士资本原始积累一方面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容克贵族对森林、草地和公共使用土地的掠夺;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追求将更多无偿的自然力并入经济过程中。这样,不同于英国产业革命,新旧势力的畸形结合使普鲁士的工业进程残留着小住宅制度、小土地制度(3)普鲁士的特殊性在于其货币积累和土地集中主要靠剥削农民实现。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阐明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其实质是在封建的和行会的等传统关系解体的条件下,劳动大众被迫同自己的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其主要手段是对农民的剥削、赋税、信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3、861、864页)。。随着普鲁士对境内经济、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地政、官房学和关税联盟为代表的国家管理制度兴起,从东弗里斯兰半岛到遍布泥炭酸沼的巴伐利亚,从北德平原到厄尔士山脉高地森林,实现全面控制自然界的山林湖沼是普鲁士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贫苦人民在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土地贵族夹缝中生活日益艰难,原先为逃灾荒以糊口的公有山林、草场被统治者瓜分殆尽,曾经避饥馑以营生的河湖、池沼变成了穷人的禁区(4)林地历来是贫苦农民维持生存的重要来源,日耳曼时期农奴如遇灾荒可进入领主林地采集和畜牧,捡拾枯枝是每个马尔克的惯例。马克思在文章中以林木盗窃为切入点并指出:“林木盗窃法也和狩猎、森林、牧场违禁法一样,不仅因为省议会的关系值得研究,而且其本身也值得研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所以在讨论关于物质利益的弊病时,是将森林、牧场及其自然物产置于更宽广的视野加以考察,已经认识到类似问题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形成的;既是人与社会关系的缩影,也是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展开。。
(一)奴役剥削是文明社会的人造灾荒,是对健康社会机体的野蛮肢解
代表容克利益的省议会对盗窃林木的认定,把贫苦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2]243。专制社会就其精神世界而言,不仅没有摆脱自然史的蛮荒阶段,而且使“彼此自由联系的肢体被割裂、隔绝和强行拆散”[2]248,这种野蛮肢解造成社会另一端的贫民极度衰竭、死亡。“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似有许多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2]249奴役劳动的社会,虽然在物质生产已经逐渐远离了盲目的自然必然性,但剥削劳动者的制度只是以机体一端的枯瘦滋养着另一端的肥壮,甚至猛兽之凶残不及统治者暴虐之万一,他们既是文明社会的奴役者,也是吮噬劳动人民血肉的寄生者。
(二)捏造独占自然界的法理是特权阶层的“点金石”,断绝人民生计的恶法本身就是包含弊病的药物
依贫民的观点,自然界的有机财富已预先交给了精通簿记和谋算的上层所有者,那么枯枝所代表的——失去有机联系的——自然界的贫穷就应当以其偶然性作为习惯权利交给社会的下层无产者,“代替特权者的偶然任性而出现的是自然力的偶然性,这种自然力夺取了私有财产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2]252-253。但这种偶然性又表现为暂时性,因为奴役劳动的社会机体结构,产生于对劳动者进行非经济和经济的强制而实行剥削的生产方式,统治者希望把一切肮脏的欲求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贫民的习惯权利“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2]248,只因统治阶级尚不能涉足的自然必然性而存在,一旦借助工业拓展了掠夺自然界的手段,它就会反过头来攫取一切所能触及的物质利益。统治者为窃据自然界的恶法捏造法理依据,“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不正当的非分要求点成法之纯金”[2]248,所以,马克思引用孟德斯鸠作为对林木盗窃法的评价:“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败;后一种弊病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弊病。”[2]245
(三)普遍贫困是人民视若惯常的“慢性病”,统治者的金口敕令被愚昧百姓当作医治病痛的“万应灵丹”
摩泽尔河流域的农民状况是莱茵省乃至普鲁士普遍贫困的特殊表现形式,但政府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2]375,把比较贫穷的葡萄酒酿造者的灭亡看做一种自然现象。普遍贫困是一种慢性病,行政当局的处方治标而不能治本,农民的状况与其说正在转变(Übergang)不如理解为逐渐灭亡(Untergang)。“而且这样的改善所触及的并不是具有经常性质的贫困状况本身,而只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病”[4]228,马克思认为专制政府不能治愈这种社会慢性病,臣奴也不能自愈这种顽疾——因为专制制度造成物质贫困的同时,也生产着精神愚昧的臣民,“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甚至把这句话当作具有魔力的咒语,当作能医治他们的一切病痛的万应灵丹”[2]384。在马克思看来,此时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是一件难事,因为这要基于对经济问题的科学研究,但在莱茵省林木问题和农民状况中,他已经逐渐认识到,不只是自然灾害和农民生产条件的问题,更主要是社会罪行和自然灾难的结合加剧了人民贫病的程度。普遍贫困的矛盾不是农民个人生活状况,而是普鲁士的普遍状况;掠夺不是官员个人的犯罪,而正是普鲁士的现代历史。在这里则碰触到国家与法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认识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利益关系,这种从物质利益角度提出问题的方式,为后来从政治经济学审视历史发展动因做了铺垫。
五、历史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凸显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初步明确资本主义病变的实质
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关切具有鲜明的劳动人民立场。其一,从疾病与健康关系为起点,从平民与贵族卫生条件差异的分析着手,以病患乱象揭示了德国近代市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批评了资本物役和专制压迫的混合产物——普鲁士社会对人民健康状况的冷漠,体现出关注人民疾苦的基本立场,为接续思考后来的无产阶级健康问题、与恩格斯共同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二,在分析古代哲学有关身体与健康关系中,暗含着以自由的自我意识突破传统束缚的倾向,揭示了古代哲人谈论健康问题时所代表的各种哲学流派形成和论战的源流、基础及其本质,为后来分析、理解近代德意志国家的意识形态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其三,以卫生健康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奴役劳动的社会形成、发展的动因;通过医疗卫生矛盾关注到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为后来与恩格斯共同进行阶级状况调查研究、创立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做了重要的思想铺垫。其四,由关注人民健康状况到关注社会经济状况,思考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基础的物质利益问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工农状况的进一步调查研究铺设了道路,为全面判断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勾画了轮廓。
此后不久,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工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5]115,根据资本家为满足致富欲望而使工人不断“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5]121的罪行,以国民经济学的口吻把无产者规定为“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5]124,又以同样口吻重复问题:“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5]124归结为抽象劳动就意味着直接从劳动创造者角度审视人类历史,这就需要考察长期被忽略、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的异化处境,这既包括工人身体机能的扭曲,也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考察抽象劳动就是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即“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都是人类劳动”[1]57,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脑力和体力消耗的做功过程;劳动者智力“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1]460与体力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的总体脑力、体力消耗构成了“总体劳动”[1]723的做功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肥力和人体健康 “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1]277;劳动的发展程度与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无产阶级的健康状况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解放状况。马克思对劳动者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肯定,科学论证了社会历史变化的动因,指出为争取改善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的斗争既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内容,也是建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
(二)内含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初步明确资本主义病变的动因
青年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探索,撼动了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在文学上把平民医疗卫生危机与贵族上层相区分;在哲学上把健康的物质本质与旧的宗教神学外壳相区分;在政治上把国家机体正常状态与恶法、恶政所致的社会痼疾相区分;在经济上把饥馑农民从自然界获得救偿的习惯权利与封锁霸占自然界财富的病态制度相区分。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愈益加深,不仅体现在汲取黑格尔哲学的诸多辩证因素,也体现在区分病态制度与社会有机体正常状态的探讨中。疾病对健康机体来说是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化状态,奴役劳动的制度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劳动大众的对立。
青年马克思对卫生健康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不仅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而且明确了社会机体是伴随人类劳动实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奴役劳动的社会制度是社会机体的病变,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依靠人身材料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内,“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311-312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为它所寄生的社会机体病变,也就是在劳动者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1]555。马克思主张辩证审视和根除资本痼疾——既不是肢解患病躯体,也不是将毒痈憋在体内,而是要把有机体的发病机制转化为复健机制。
(三)呼应恩格斯同时期的卫生健康观,为共同批判资本主义病变准备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几乎同时都表现出了对卫生健康问题的关切,都表现出突破旧思想限制的理论勇气和斗争热情。恩格斯在1839年翻译《咏印刷术的发明》时,通过对西班牙革命文学作品的再创作, 宣扬了革命浪漫主义理想,要实现“可怕的流行病从此绝迹,万恶的黑死病无影无踪”[6]49。将战胜疫病的勇气与革命斗争精神联系起来,向德意志各邦民众传递消除瘟疫、消弭兵燹的革命新内容(5)“地球不再是任凭战争和忌妒肆虐的贫困的星球。这两个恶魔永远消失,只要山上刮来一阵凛冽的阿奎隆,可怕的流行病从此绝迹,万恶的黑死病无影无踪。”原作者为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法国启蒙学派的追随者曼努埃尔·霍赛·金塔纳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A la invención de la imprenta》),最初发表于1803年马德里出版的《诗集》(《Poesias》)。作者以凛冽的北风之神(Aquilo)做喻,赞颂了启蒙运动对社会革命的作用。恩格斯将其翻译为德文,译文和西班牙原文同时载于《谷登堡纪念册》《Gutenbergs-Album》)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在深入工业区调查工人状况的第一篇文章《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认为健康状况是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7]44,痛心于产业工人被疾病蔓延和身体衰竭所吞噬;在《与莱奥论战》《谢林与启示》等文章中,他批判了所谓“疾病是对罪孽的惩罚”这种空洞的神学判词,认为“医学上彻底的革命纲领”[6]313只是假借现代医疗卫生条件复活中世纪的宗教自然观;恩格斯在1842年到英国后研究其历史和现状,借助政治经济学材料和社会主义文献对卫生健康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国内危机》中指出了危机背后的阶级根源:“因为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且三分之一的人口,几乎是所有英国人数的一半,都属于这个阶级。”[8]410经历产业革命全过程而造就的英国现代工人阶级是彻底的无产者,从事繁重和有害健康的劳动的工人是阶级斗争最坚决的部分,也是资本家最害怕的斗士。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见到了马克思,开启了两人的终身合作。对卫生健康问题的关切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共同的工作”[9]247,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更加洞悉了资本主义制度既沉积着神学与专制的旧病,又派生出拜物和噬人的新疾。这是推动两人思想发展的酵素,也是推动他们走向合作之路的主题。深入思考劳动者与奴役者的健康反差,科学研究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病态关系,使两人共同踏上了探索唯物辩证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革命征程,其中所体现的关切劳动人民疾苦、反抗现实压迫、注重调查研究、献身革命理想的宝贵品质深深印刻在两人的革命履历中。
综上所述,卫生健康领域的灾难根源于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与环境灾变,是资本混乱性、盲目性、破坏性的现实表现。资本逻辑包含着生产过剩导致系统紊乱从而引发人-社会-自然界灾祸的复杂机制。在资本逻辑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被奴役,它没有为穷苦大众服务,反而导致劳动人民的饥荒和痛苦,工人健康与土地肥力衰竭殆尽。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击碎了神话幻想的物质基础,“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10]35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不再为人民祓除瘟疫,而仅作为资本主义医疗卫生机构的徽标。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发展,但却以服膺于资本逻辑为代价。当我们做历史地考察时,劳动人民幻想的艺术形式本身,那些孔武有力、健康长寿、迅捷优雅的美好形象,在残酷的现实中只能是一种幻想。现实的异化状态只会使劳动人民更珍惜全面发展的理想,仇视资本主义系统病变,从而创造出推翻这种奴役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神农遍尝百草以救黎民苍生,希波克拉底在灾疫中救死扶伤的历史故事,虽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过往,但又在一个更高发展阶段上,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再现出其应然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要利用生产力的进步为自己解除疾苦、战胜灾难而奋斗,以此创造发展卫生事业、提高人民体质的有利条件。把卫生健康问题作为社会制度的系统问题来看待,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后来的思考进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为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的解放事业、为人类社会探寻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