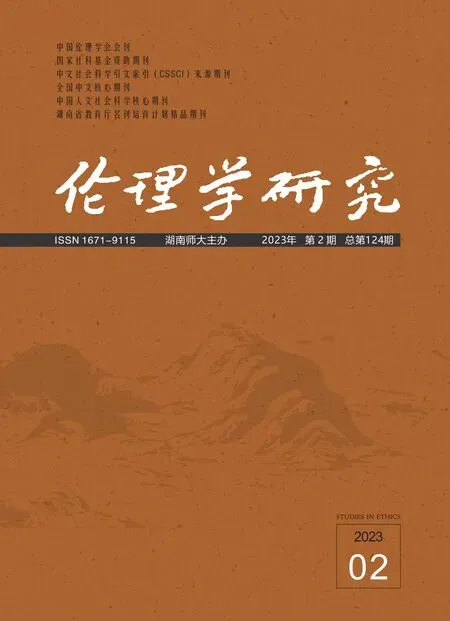论恶之伦理意蕴:从平庸之恶到诡辩之恶
孔明安,王雅俊
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善恶问题的表现形式越发复杂。只有充分认识到“恶”的复杂多变之样态,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善”。关于纳粹党卫军将领艾希曼的审判①艾希曼曾负责犹太人的“终极方案”的策划与执行,是反犹的枢纽性人物。他战后潜逃出国,后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并将其押送到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引发了许多思想家的不同思考。其中,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平庸之恶”和以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为代表的“诡辩之恶”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不同的解答。
一、平庸之恶与不思的共存
作为20 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阿伦特对恶的反思构成了她解决社会危机与道德困境的主旋律。阿伦特关于恶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根本恶”(radical evil)和“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两个阶段,其中关于“根本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康德所谓的“根本恶”不是指具体的极端的恶,而是指一切恶之可能的根据或根源。他重点从动机的角度来考察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两个相反的潜在维度:向善的秉性和趋恶的倾向。人之所以作恶,就在于人性中存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愿意反抗恶行的理性倾向,这是德性真正的敌人。换言之,主体在自由决断中颠倒了自爱原则和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恶的进一步考察,康德把人们趋恶的倾向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人的本性的脆弱、人的心灵的不纯正以及人心的恶劣。“这种恶劣或者败坏也可以叫作人心的颠倒(perversitas),因为它就一种自由任性的动机而言,把道德次序弄颠倒了,而且即使如此也总还是可以有律法上善的(合法的)行动,但思维方式却毕竟由此而从其根本上(就道德意念而言)败坏了,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作是恶的。”[1](25)由此可见,人心的恶劣颠倒了道德次序,用非道德的准则代替道德的准则,是人性中的自我欺骗和虚伪。另外,康德也提到了第四种恶,不过这类恶会让主体变成一个恶魔般的存在者,因而他直接否定了这种恶对人的适用性,认为根本没有这种不受理性动机影响的行为。
虽然在康德这类传统思想家看来“根本恶”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它根植于人性中,可以被理解或解释,但在阿伦特看来,根本恶是特殊的,它打破了以往所有的标准,是人性所不能理解的恶。阿伦特把根本恶和极权主义的统治相连,认为“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2](573)。在她看来,纳粹大屠杀的恶行之所以无法用传统的道德理论来解释,是因为它直接把犹太人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让人变成了多余人。这种多余性不仅是共同体的缺乏,而且是通过消除人的自发性和个性而让人变得多余。但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后,阿伦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她在1963 年回复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中表示:“你说的很对:我改变了想法,不再谈论‘根本恶’……我现在的确认为恶不是‘根本的’,恶只是极端的,它既无深度,又无恶魔的维度。它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它是‘蔑视思考’的,因为思考试图达到某种深度,寻找根源,当思考与恶关联在一起时,就会因为一无所获而感到沮丧。这就是它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3](470-471)阿伦特从“根本恶”到“平庸之恶”的转折,标志着她关于恶的体系的完善。
首先,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关键在于标明了作恶者的浅薄性和无思性。“恶的平庸性不是一种理论或教条,而是表示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这样的人从不思索他在做什么。”[4](19)正是这种无思与浅薄使作恶者变得不人道,失去了必不可少的道德属性。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阿伦特提到纳粹党卫军的将领艾希曼并非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体形消瘦甚至可怜兮兮的普通人。在庭审现场,艾希曼也一再强调,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具体的犹太人。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导演,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演员。而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她指出:“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儿异乎寻常地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毒,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问讯中能发现的唯一的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4](163)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思想性,或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社会分工的体系化让每个人成为庞大机器的一个零件,这个零件被置于固定的位置,接受固定的分工,习惯固定的认知,冗长的分工链条遮盖了价值的整体性,导致了人们丧失了对事情的价值评估和道德判断。这种体系化使得人们恪守自己的分工,服从上级的指令,成为一个工具人,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做这件事。就艾希曼而言,他是漫长迫害链条中的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单从具体环节来看,有的人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有的人只是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有的人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有的人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等,他们没有杀人,但是这些艾希曼们如果能够跳出自己身份的碎片,从一个更大的图景来看,他们杀了无数人。
其次,破解“平庸之恶”的关键在于思考。“思考活动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需要和意识中的差异的具体化,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运用的能力。”[4](187)“平庸之恶”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崩溃之后,个体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丧失,导致整个社会没有明辨是非的正确标准。因此,想要抵制这种恶,就需要个体保持思之能力,恢复思之样貌。一方面,思考表现为自我的无声对话。阿伦特肯定了苏格拉底把思考视为灵魂和自身对话的看法,提出要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反省,进行自我批判和追问,只有这样,才能唤醒并坚守人们内心的良知。思考是一种看不见的独特活动。“心理活动,尤其是思维——我与我自己的无声对话——能被理解为我和内在于所有意识的自我之间的最初两重性或分裂的实现。”[5](81)通过这种无声对话,就会促使人们时刻正视自己的良心,从而在思考的过程中,自我存在和自主判断得以澄清和实现。另一方面,思考与记忆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对于一个罪犯来说,逃脱罪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弃思考的能力,忘记之前不好的所作所为,但是同样地,悔恨就在于不能忘记自己所做的事且总是回忆起那件事。如果拒绝记忆,那么就意味着遗忘了经验而随时准备去干任何事情。最大的为恶者不是那些曾经犯下滔天大罪而陷于绝望之中的人,而是那些从不思考所做的错事且从不记忆的人,因为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他们继续犯错甚至成为恶魔。阿伦特指出:“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4](110)当人们失去思想和记忆这种最普遍的能力时,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而且任何才能都无法承受丧失这种完整性所带来的后果。思考是行动的内在方式,当人们思考时会离开表象世界,将思维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把不在场的事物在思维中再现。换言之,思维是一种重现的存在,是一种超越实在物体的普遍抽象。
最后,思考为判断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我们通过思考区分善恶,清除我们固有的认知习惯、僵化的规则和准则以及约定俗成的标准化的语言表达,从而为判断实现其功能打下基础。阿伦特指出:“如果思维——无声对话的合二为一——实现了在意识中和在我们的同一性之内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作为其副产品的良知,那么判断——思维解放作用的副产品——则实现了思维,使思维出现在现象世界中,因为在现象世界中,我从来不是孤单的,我因太忙而不能诉诸思维。”[5](215-216)可以看出,思考更多地体现为个人世界的精神活动,而判断则把思考从个人的世界扩展到现象世界或公共性的领域中。阿伦特关于判断的思考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康德的审美判断。阿伦特在早期深受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影响,把判断归为行动者的判断,认为判断是行动者在政治协商和行动中所运用的一种能力。而阿伦特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个转变,从行动者的再现性思考转移到了旁观者的回顾性判断。因为她认为旁观者在面对一个景象时由于不参与其中而有一个能够看到全局的位置,并且能够把他人的意见尽可能考虑在内,所以判断更加公正。因而,后期阿伦特更推崇康德的审美判断,把判断归为旁观者的特权,是回顾性地探寻人类事务意义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为分辨是非、识别美丑提供一种更加公正的态度。根据阿伦特对康德的解释,康德普遍理性的思考方式意味着接受公开的检验,即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参与人数越多,对此问题所形成的判断就越具有说服力和一般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公开运用”。由此可见,阿伦特在晚期更加强调判断能力的主体间性和公共性的维度。
“平庸之恶”在阿伦特看来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历史环境对人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恶行不具有任何深度,反而是空洞的、平庸的,因为在作恶者身上找不到恶行的动机、意图或想法,作恶者在道德和智识上也是乏善可陈的。因而,她试图为思考活动正名,重新激起人们思考的积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她晚年著作《精神生活》的重要原因。通过思维、意志、判断对精神生活的洞察来破解平庸之恶,让人们回到思考活动本身,这是阿伦特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回答,也是她的伦理追求。然而,艾希曼真的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吗?艾希曼真的是无需担当多大的罪责吗?这种看似被动的执行命令是否潜藏着经过利益计算之后的主动选择呢?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另类视角,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和解读也意味着对阿伦特“平庸之恶”这一概念需要进行不同视角的细致剖析与深入反思。
二、诡辩之恶与权力的共生
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不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就平庸之恶从另外的视角进行了别样的思考。
赫勒认为恶的观念是植根于人性中的。“恶远非是平庸的,但是平庸的人可以被恶所掌控,作出恶的行为并成为恶的人。”[6](202)在赫勒看来,恶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例如,耶路撒冷法庭之上的艾希曼与那个固执、狡猾、聪明、善于巧用计谋来策划与驱逐犹太人的艾希曼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艾希曼。那个沉湎于自己绝对权力的残酷成性的艾希曼在走上法庭之后已然消失了。坐在法庭审判席上的艾希曼变得“平庸”了。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他失去了构成恶的权力,即职位的权力。他不再是那个令人畏惧的纳粹高官,而是成为一个他原初所是的空壳。一旦权力耗尽,绝大多数恶人都会变得平庸。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他的危害往往是有限的。然而,艾希曼是反犹的枢纽性人物,拥有犹太人终极方案的执行权力,曾被称为“犹太人的沙皇”,所以他绝不仅仅是个被动的螺丝钉,而是主动成为杀人机器。在法庭的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却绝口不提他如何获得晋升而成为执行人,这显然是避重就轻的。赫勒关于“恶”的问题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恶有不同的种类,赫勒大致把恶划分为道德的恶和非道德的恶。非道德的恶主要指自然环境所引发的自然灾害,比如农作物歉收、火山爆发、干旱、蝗灾等。而道德的恶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对象,赫勒又把它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底层世界的恶(evil of the underworld)和诡辩的恶(evil of sophistication)[6](197)。“底层世界的恶”的主要特征是撕毁规范、贪图享乐。这种恶一般是由社会环境引起的,索多玛与蛾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就是底层世界的恶的化身。而“诡辩的恶”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恶,它不仅具有违反规范的破坏性,而且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诡辩之恶”的持有者希望能够在其他人身上附加“底层世界的恶”,勾起人们对于“底层世界的恶”的信念是他达到或实现另一目标的手段。没有“诡辩的恶”的支持,“底层世界的恶”所造成的危害只是暂时的和有限的。一旦“底层世界的恶”从“诡辩的恶”中获得准许和放行的信号而在外传播,就会形成瘟疫。这样一来,恶就像瘟疫一样蔓延进入无知者的身体和心灵,也感染了那些道德健康的人。
其次,诡辩之恶与权力内在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诡辩的恶在任何位置都能传播这个瘟疫,但是权力的位置是最为合适的。”[6](199)恶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赫勒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权力:政治职位的权力、知识的权力和品性意志的权力[6](201)。其一,“诡辩之恶”依赖于政治职位的权力而唤醒了“底层世界的恶”,从而摧毁了他们周围的生命。这样的人无论是处于可以灭绝整个种族和阶层的位置上,还是处于能够毁灭小范围人群的位置上,只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他所掌控的政治职位权力的大小。其二,掌握知识也意味着掌控权力。把某项工作做好需要一定的知识,而知识是分配不均的,有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知识,那么那些人就应该管理这些事情。精神病医生、律师、技术员这些特定领域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都具有特定领域评判的性质,也意味着掌握了某项权力。行动者以知识为中介,作为“知道如何”的载体,提供“最正确”的答案。而对于那些没有拥有这些知识的人来说,只需要听从专家的建议即可。其三,对于品性意志来讲,恶是一种诱惑。只有那些一直遵守善的准则而从不被恶的准则引诱的人才能拒绝诱惑。在纳粹时期道德混乱的德国,如果没有坚定地击败恶的准则的意志,甚至本质上善良的人也会被恶的准则所愚弄。另外,恶的吸引力还与人数有关。认同某一恶的准则的人越多,“底层世界的恶”所拥有的人员数量就越多,恶的权力和恶魔般的吸引力就会越大。赫勒认为,构成艾希曼恶的权力既不是知识的权力,也不是品格的权力,而是职位和数量的权力。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艾希曼是令人畏惧的“犹太人的沙皇”,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变得平庸就在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令人忌惮的纳粹军官。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旦失去权力,就失去了作恶的驱力,没有了机会,也就失去了恶的症候。一个人在恶魔的引诱下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但是当勾起他“底层世界的恶”的那种“诡辩的恶”消失了,他就不再被恶附身,也就失去了恶的“症候”。
最后,解决恶的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对恶说“不”,而且要不断确认善的准则并绝对地坚持这个“是”。在赫勒看来,不存在能够把握恶本质的单一普遍公式。恶的准则诉诸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情形,不同的恶的准则掌控着不同类型的人。与恶相对,善是能够通过一般的形式加以界定的。“如果他或她更倾向于自己承担责任,而非损害他人,那么这个人就是善良的。每一个坚守这一形式定义的人都是善良的。”[6](204)对善的肯定构成了赫勒伦理学体系的关键,这也是她预设“好人存在”的缘由。不同于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伦理学对于规则和原则的强调,赫勒更注重内在道德的重要性,她认为西方道德的出路就在于重新确立德性优于规则的地位,通过德性内在的力量重构道德权威。尽管赫勒是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也承认道德规范是一直变化的,但她依然试图把握善的一般概念并突出德性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面对文明的罪恶,赫勒认为内心的善与道德力量的坚守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因而她始终致力于构建至善伦理学的大厦。
在赫勒看来,艾希曼的恶行是诡辩之恶,这种恶依赖于权力而生。没有恶的权力的巨大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轰鸣的杀人机器。权力引诱着那些没有坚定善良意志的人一步步走向堕落,走向罪恶的深渊。面对蛊惑人心的邪恶,我们不仅要拒绝恶,同时还要绝对地坚持善,保持内心的良知和德性,让善在我们生活世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重燃构建道德世界的希望。
三、制度之恶与个人行为之责任的伦理反思
以艾希曼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线索,阿伦特和赫勒都对大屠杀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但二者所关注的焦点和理论观点大相径庭。总体来看,阿伦特和赫勒关于大屠杀批判理论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二者研究视角不同。阿伦特主要是立足于存在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性反思,而赫勒更多的是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更加重视个人责任。尽管阿伦特也承认个人责任,但她更多的是把目光聚焦于社会层面,寻找社会中普通人也会作恶的原因,这同时也是她的“平庸之恶”理论所反映的社会中人们普遍“无思”的局面。二战时期的纳粹军官甚至普通的德国人在习以为常的职务行为、工作程序和日常生活中悬置甚至消解了思考的责任,这种个体的盲目服从其实就是变相地支持了纳粹的暴政。对阿伦特来说,如何理解艾希曼这类人身上显现出来的恶,其实是理解极权主义社会道德的关键。因而,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阐释直接从纳粹政治统治逻辑的视角出发,是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反思。而赫勒的“诡辩之恶”则立足于后现代主义视角,更加强调个人责任。责任与人的行为密切关联,“凡在有行为的地方,就存在着责任;凡没有行为之处,就不存在责任”[6](61)。在赫勒看来,行动者总是要负责任的。在人们开始行动之前仍停留于沉思阶段是可逆的,但是一旦行动,就使可逆的变成了不可逆,人需要为某种行为担责。关于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划分问题,赫勒认为,“集体罪行从来都不是由特定群体的所有成员共谋的,或是在同样的程度上,由所有的行动者犯下的这样的罪行”[6](96)。可以看出,相比于集体罪行,赫勒更多的是强调个体罪行,因为即使是集体犯罪,那也是由不同的个体完成的。从历时性角度看,所有人都有责任,只是所担当的责任在程度上不同罢了。“集体犯罪的始作俑者为恶承担着‘世界—历史的责任’;他们的跟随者依据其自己的、个性的、意愿的行动而不同程度地担责,每一个人都为他自己或她自己的行为而担责。”[6](98)显然,赫勒对责任的分析是以个人责任为主要考察对象的。
其次,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是制度层面的反思,而赫勒不仅看到了制度之恶,而且注意到了人性的丑恶,看到了个体行为及其道德责任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对恶行之追溯,不能仅仅诉诸体制性的、普遍性的维度,而且也必须有个体为恶之行为担责。阿伦特将“平庸之恶”与“无思”联系起来时不仅考虑到了艾希曼这类人的思想空洞乏味,而且也考虑到了正是在特定制度下作恶者才能如此轻易地陷入盲目肤浅的旋涡。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庸性的重要论断更多的是对纳粹所犯罪行的社会结构机制的描述,而不是对犯罪者本人的道德规范性描述。阿伦特认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靠思维的眼睛把握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种解释工具”[2](585)。意识形态这种解释工具可以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有意义的世界。通常很少有人主动去作恶,但是如果居心叵测地利用意识形态,把恶翻译为善,那么作恶的人不仅会趋之若鹜,并且有可能慷慨激昂地为之辩护。当时社会中的人们普遍陷入“无思”状态主要在于纳粹意识形态的煽动。吊诡的是,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犹太人的领头人也参与了自我毁灭的行动,他们所做的一系列配合纳粹政府的行为是“受害者的不思考”。被审判的刽子手不再是艾希曼,而是德国人乃至整个人类中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艾希曼被迫成为一个形象和符号,成为所有罪孽和暴行的代言人。而赫勒是从具体的人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当时纳粹德国处于一个道德混乱的时期,但是个人的主体意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艾希曼本人来看,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犹太人的沙皇”,是因为他对于权力的追求。在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以说是一事无成,而加入纳粹党之后,艾希曼为了个人升迁而蝇营狗苟、勤于算计。他的职位的获得正是因为加入了一场恶的游戏,作恶能给他带来升迁、发财、虚荣心的满足等。这种恶深深植根于人性,正是权力的诱惑激发了人内心的阴暗面,使其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也正是人性中的自我保全的盘算使得当时德国的犹太领导人被纳粹利用,成为恶魔的帮凶。这种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了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在这场为生存而遍起的争夺中,造成的结果是更多人的死亡。因而,赫勒更多的是从个体出发,揭露出个人主动选择的“诡辩之恶”,并且通过剖析“诡辩之恶”与权力的关系看出了两个艾希曼,即法庭审判席上平庸的艾希曼和善用计谋驱逐犹太人的艾希曼。艾希曼之所以变得平庸,就是因为他褪去了权力的外衣,变成了其原初所是的空壳。
最后,阿伦特关注的是共同体之内的道德,停留于“思”的层面;而赫勒更多强调的是个人道德及其德行的示范性,即善的伦理学,驻足于“行”的层面,这也是其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典型体现。面对现代社会的困境,阿伦特最终将问题的方向指向政治伦理,她认为解决道德困境的问题要放在共同体之内来讨论,需要从“知”或者“思”的层面来唤醒人们的良知,这也是阿伦特后期之所以关注康德哲学和判断力批判的原因所在。同样,阿伦特关于复数性的概念不是数量意义上的人,而是在公共空间中存在的人。暴力会毁灭人的复数性存在,僭主虽然运用暴力获得统治,但他仍然是孤立的,他只能靠恐怖维持政治,无法进入公共空间。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在公共空间中存在的政治不是依靠暴力的征服而取胜的政治,而是体现人们之间的友爱与信任、创造辉煌的文化的政治。而赫勒更强调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强调道德行为的示范性及个人行为之责任。面对现代道德与文化的深层危机,特别是在纳粹统治下的道德黑暗的社会中,人们无法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指引一条善行之道,更要依靠自己内在的自然情感中的良善摸索前行。“正当的(好的)人是做正确的事情而不考虑社会的(司法的)约束的人。”[7](50)在赫勒看来,好人更加注重内在的良知,而且即使是在黑暗时代仍存在不允许道德之光被吞噬的好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以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这个真实人物为原型拍摄的。辛德勒在残酷制度的阴郁背景下依然展现着人性的关辉,彰显了个人道德行为的巨大魅力。他本可以对犹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不闻不问;然而他却通过自己的人脉和财产,冒险挽救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幸存的犹太人也用自己保存下的一颗金牙为他铸成一枚戒指,内刻着“救人一命,如救苍生”。良善作为内在的道德,为人们寻求一个可能的家园提供了栖息空间。在价值取向范畴的层级序列中,赫勒更是将善置于优先的位置。“‘善为先’是非常重要的,是善引导了人们的认知,而非认知引导了善。”[8](56)这种对善的优先级别的确立不仅鼓励好人恪守内在的良知,而且推崇道德示范的行为意义。赫勒对善的本质和道德力量的坚守,也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德性伦理学的回归。
不过透过阿伦特和赫勒关于大屠杀的理论思考本身,我们可以寻觅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阿伦特和赫勒作为极具深度和现实关怀的哲学家,二人都没有把大屠杀作为偶然性的特殊事件来对待,而是从社会层面或从人性本身来挖掘大屠杀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普遍逻辑,并提出破解的方案,为解决社会病症和化解邪恶做了积极的应对。其二,阿伦特和赫勒分别从社会和人性方面来探究恶之根源,这两个方面恰好构成一种互补关系,纳粹大屠杀的发生不仅与社会整体的“无思”状态相关,也与人性中恶的倾向相关。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然具有各种各样的诱因,她们二人的理论观点为人们更加全面而丰富地认识大屠杀的根源和运作机制提供了参考。其三,尽管阿伦特和赫勒都以纳粹大屠杀为反思主题,但她们的理论却没有止步于此,不仅回应了社会的困惑,澄清了某种可能性,而且丰富了我们对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生意义的理解,为后现代多元化的思考留下了可发挥的空间。
结语
尽管奥斯威辛大屠杀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或者德国的问题已经沉入历史,但这件事情的恐怖之处和不可思议正是人们应该更加予以警惕和思考的。面对这种兼具高度理性与疯狂执念的罪恶,偿罪和清算并不能穷尽大屠杀的历史意义,因而各界学者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来反思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阿伦特从社会视角出发,看到了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平庸之恶”及其普遍性的维度,因而她试图为思考正名,打破社会中人们普遍无思的状态。“平庸之恶”概念对纳粹制度之恶的揭露虽然深刻而尖锐,但它却有消除道德行为中个体责任之嫌。这也是人们为何对阿伦特将艾希曼之罪行归结为“平庸之恶”所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由于此,赫勒提出了立足于人性基础上的“诡辩之恶”,并且剖析了恶与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提倡人们坚守内心的良知,试图构建至善伦理学的体系。阿伦特立足于现代性的存在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反思,追求的是共同体内普遍性的道德伦理;赫勒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更强调个人道德的归属和个人行为之责任。此外,两者分析纳粹之恶的伦理学说不仅描绘了她们对恶的形态的阐述与反思,而且体现了她们对人的生存境遇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给予的深切关怀。
——评阿格妮丝·赫勒的《激进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