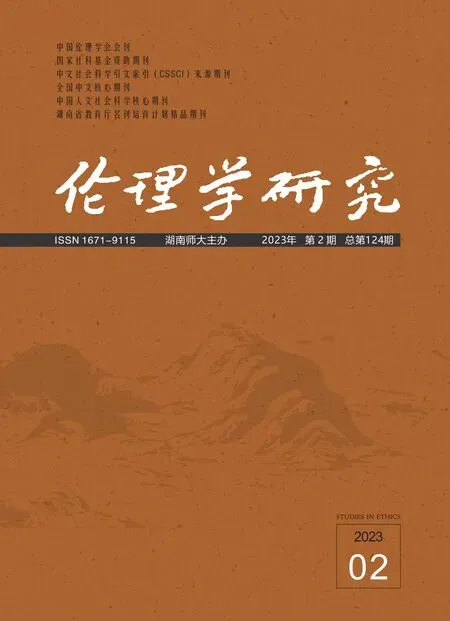哈布瓦赫论历史上社会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黄泰轲
在人类的历史上,财富的来源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人们往往鄙夷、谴责那些对财富“取之无道”的人,甚至还认为应该把他们的“不义之财”广散天下,以济贫者或以充公用。这也意味着,要想自己的财富受到他人的尊重和不受到他人的觊觎,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即是向他人“证明”或“说出”(回忆讲述是很重要的一种证明方式)所拥财富是“以道取之”和“以德据之”的,这样,占有财富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①本文所讲的合法性均是指道德合法性,即道德上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才能免遭他人质疑、非议、抢夺而得以长久。
对财富道德记忆的核心议题就是从道德的角度回忆财富的来源问题②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包括从道德的角度回忆财富的来源、使用、分配、增值、继承等诸多问题,但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主要论及的是财富的来源问题,这也是财富系列问题的“首要问题”或“核心问题”。,它能够为财富占有的合法性、神圣性、长久性提供道德证明。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阶级对财富具有怎样的道德记忆?社会主流的对财富道德记忆的框架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被更改的?深入研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的相关论述,我们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且,还能在强化道德环境建设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方面获得一些重要启示。
一、财由德聚,忠勇生财:贵族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个人或家族的财富从哪里来?在经济学史上,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站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我们坚持认为“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公理”并且对勤劳致富予以讴歌[1]。但人类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劳动光荣的观念。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贵族对生产劳动持鄙夷的态度,他们认为,从事牟利性的职业劳动是“有害的实践”,因为“这种牟利的活动低劣而卑贱,会有损于贵族的尊严。只有靠地产过活,或者至少不要变卖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才合乎体统”[2](273)。
封建贵族“靠地产过活”。地产又从何而来呢?很多人认为他们以功博得。功劳尽管是封建贵族获得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还不是最终依据。因为封建君主在“论功行赏”时,也会有“功薄赏厚”或“功厚赏薄”这样功赏不相当的情况发生。哈布瓦赫说:“贵族领主的权力基础,是其以封建分封的形式分配出去的领地的数量和规模,以及他们在以国王为顶端的等级制度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特定贵族与国王之间距离的远近。然而,可以肯定,开始的时候,是由于这些认受者的天赋和个人品性,才将财富和等级授予他们。”[2](210)这里清楚讲道:贵族拥有财富的终极依据在于德性。
哈布瓦赫认为,封建贵族之所以鄙视“财由业生”而坚信“财由德聚”,乃是他们有如下观念:职业劳动所得的财富与其拥有者之间,只存在着一种“外在联系”,这样的财富自然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只有将财富“内在联系”到所有者个人或家族的品性上,才能让人们信服并尊重其对财富“当仁不让”的所有权。哈布瓦赫进一步分析指出,贵族的上述观念其实还源自以下信念:“财富”与“命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①在英语中,fortune 既有“财富”的含义,也有“命运”的含义,这加深了贵族对“财富乃依德而命定”的印象。,一个人拥有财富,乃是他受到了命运的偏爱,即他在出生时就被上天赋予了配享财富的某些卓越品性,命运对他的垂青使得他的财富受人尊敬,而那些通过辛苦劳作而发家致富的人,他们的财富来源过于明显或无神秘可言,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神圣光辉加诸其上。
在上述观念及信念的影响下,贵族认为他们不仅继承了祖先的财产,还继承了祖先的德性。他们相信,伴随着血液的流淌,祖先的美德还在他们身上闪闪发亮。哈布瓦赫认为,只要打开对家族往事的记忆闸门,贵族的以下自我看法就会不断加深:“他们中的人能够受泽于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勇气,并使一系列的身体的和精神的特性得以永存并不断更新,这些特性通过继承而传递下来,从而提升了它的成员的个人身价……他们坚信,他们的群体在社会机体(social body)中尊贵之至、不可替代,并且是社会机体中最活跃、最仁慈的部分。”[2](213)当然,贵族也唯恐这种源自祖先的德性在自己身上消失,他们努力地用新的功绩和英勇事迹来保持它们的“连续性”。
凝望祖宗遗像,回望家族历史,贵族会想到他们的祖先如何对君主忠贞不贰,如何为君主英勇杀敌,如何得到君主的优渥赏赐。这种回忆促使他们将财富牢牢地拴在个体及家族的美德尤其是勇敢、忠诚等美德上。贵族认为,这种对财富的道德记忆能够很好地证明他们所拥有财富的合法性、神圣性、永久性。想一想,正是祖先“以德配天”才获得“命定之财”,伴随着血脉的传承,祖先把德和财一起传于后世,那么,自己从祖先那里承袭而来的东西难道不合法、不神圣、不永久吗?
由上可知,在财富来源问题上,贵族塑造并强化了“财由德聚”的认知传统:究其根本来说,财富不由辛勤的职业劳动而来,而是依德性而获神赐(君主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在贵族看来,所谓“神赐的财富尤佳”,假如一个人没有德性依恃,那么“神灵贬斥他,让他的房屋枯朽,财富在他手里瞬即消失”[3](10)。贵族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你们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你们的身体或职业,而是你们灵魂的最高幸福。我每到一处便告诉人们,财富不会带来美德(善),但是美德(善)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4](18)对贵族而言,通过君主之手,依靠忠诚、勇敢等美德而生就的财富,即是神赐之物,它无比神圣。贵族相信,财富是他们拥有的忠勇美德的外在证明。
二、贵族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如何受到社会的认可与推崇
对财富的道德记忆,贵族是非常愿意与社会“共享”的。这很好理解。站在贵族的角度看,倘若社会认同他们对财富的道德记忆或者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比如,全社会都清楚地记得他们财产背后英勇、忠诚的历史故事,毫无疑问,这肯定能给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增添无数的荣誉,从而更能够激起人们对其财富的敬重;反之,倘若社会不认同他们对财富的道德记忆或者与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记忆,即认为财富并不是来自他们祖先的功德而是来自其他“不可言说”的途径,毫无疑问,这肯定会引发人们对他们财富合法性、神圣性、永久性的持续质疑。
现在要问的是:在贵族社会里,社会认同贵族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吗?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又促使我们去思考以下问题:社会凭什么认同某一阶级或某一群体的道德记忆?在哈布瓦赫看来,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一阶级或群体对社会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哈布瓦赫认为,在每个历史时期,社会总是把那些为其带来重大利益的活动及从事这些活动的个人或群体置于记忆的“突出位置”,只有当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才能和职业对社会有更大贡献时,他才可能引起社会更多的注意,给社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哈布瓦赫说,当社会将其注意力固着在某个阶级或群体的身上并记住他们的时候,这个阶级或群体“保存在其记忆之中的那些传统价值判断便因此而形成了”[2](271)。注意这里的“形成”一词,意思是“得到社会的肯定”。也就是说,当某一阶级或群体的贡献受到社会注意和认可的时候,他们贡献背后的价值观念及判断也会受到社会的注意与认可。
有必要看看封建贵族的活动与贡献。哈布瓦赫提供了如下信息:“在封建制度时期,封臣有协助其领主的义务。在战争期间,他们要率领麾下的人马,拿起武器,驰骋疆场。他们要充当领主的智囊,协助领主管理司法事宜。封建社会展现了一种群体景象,群体的成员履行着各种各样的职能,在其中,那些维护着群体实质上的完整并使之不断繁荣壮大的人,占据着尤其突出的位置。而且,这些职能维护了秩序和某种程度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履行这些职能,群体的成员更加意识到臣服关系和效忠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等级,证明了他们的伟大,并擢升了他们的荣誉。”[2](214)这段话讲到了封建贵族“驰骋疆场,管理司法”的实践活动及其“维护秩序和统一,促进繁荣与壮大”的社会贡献。因为这些,社会才给他们以“伟大”的评价和无数的“荣誉”,将他们置于“尤其突出的位置”并予以“着重关注”。这种关注的结果就是,社会认可并记住了将姓名、盾徽、联姻(贵族传统),英勇与效忠的行为(贵族美德),向君主提供的服务(贵族职责),与王国的历史休戚相关(贵族贡献),钦赐的封号、特权、财富(贵族所得)等紧密连为一体的“贵族价值体系”[2](208-209)。显而易见,贵族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即是这一“贵族价值体系”在其头脑中留下的印记。
哈布瓦赫认为,社会不仅肯定、认同贵族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它还推崇、利用贵族对财富的道德记忆。之所以这样做,乃是社会有它自己的担忧:一个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对财富有着不同的道德记忆,多样化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使得对财富合法化的道德证明也多样化,这种情况与社会所期待的“群体之间保持观点上充分的统一性”有所背离,而后者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哈布瓦赫说:“在相同的环境里,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使财富合法化的方式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将意味着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道德,同时作为富人特权的基础,特别是给予他们的尊重的基础。”[2](261)因此,为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社会就要整合各种不同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哈布瓦赫指出,社会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原则,在记忆库里精挑细选,遮蔽乃至抹去一些可能导致个体彼此分离和群体相互疏远的记忆,并对其余的记忆进行排序,把那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巨大现实影响力的记忆凸显出来,以此引导、维护社会集体的记忆。经过这么一番筛选、排序、推送,封建社会把其认为的对它贡献最大、最受它关注的贵族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放在了“支配地位”上,现在,社会只有一种成为主流的使财富合法化并使之得到别人尊重、崇敬的道德记忆,那就是贵族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这也意味着,当社会评价其他群体所拥有财富的合法性或荣誉性时,首先所想到、所援用的就是“贵族价值体系”。为了强化其他社会群体对前述“贵族价值体系”的印象和认可,社会还经常通过举行各种仪式褒扬贵族阶级的品德并给予他们更多的荣誉、权势、财富。通过这些吸人眼球的仪式,社会想要提醒其他群体努力“寻求理解那‘隐藏’在仪式象征体系‘背后’的要义”[5](60)。在封建社会,这个要义简而言之就是:忠君之事,食君之禄。
三、资产阶级重构了社会对财富的道德记忆
因为贵族阶级的贡献力与影响力,社会才推崇贵族阶级并将其对财富的道德记忆视为社会主流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又发生了变化:贵族阶级在腐化堕落(如《红楼梦》里的贾家)。很明显,自身不断腐化的贵族阶级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贡献和影响了。当贵族阶级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减弱的时候,他们在社会集体记忆中刻画的痕迹就会变淡、占据的面积就会缩小,社会记忆空间腾出来的那些位置需要新的内容填充。
伴随着贵族阶级影响式微而逐渐走向社会舞台中心的是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的财富越聚越多的时候,他们自然也要向社会回忆并说明他们发家致富的合法性。前文讲贵族阶级塑造了一种“财由德聚”的价值认知传统,资产阶级并不能撼动这一传统并且还要遵循这一传统。不过,贵族阶级在说“财由德聚”的同时又说“德承祖来”,即他们认为自己身上仍然具有最初配享财富的祖先所留下的英勇、忠诚等美德。“德承祖来”的信念对资产阶级是一种伤害和打击。因为作为平民的后代,资产阶级并没有辉煌的过去或者值得夸耀的祖先可谈,况且他们认为,美德也难以伴随着血统而来,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在“教育和环境的熏陶下”铸就美德的。
在自身财富来源问题上,难道没有悠久家世可追溯的资产阶级会患上“道德失忆症”或“道德失语症”吗?哈布瓦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当资产阶级普遍取代贵族阶级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阶级(或者说“新贵族”)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些违反常规的现象,并设法找到一种方式,使那些没有头衔、没有靠山、没有亲属关系就闯入了贵族阶级的人合法化。因此,这时候,对社会来说,也就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重组和修改其记忆框架了”[2](225)。
哈布瓦赫认为,资产阶级有两种方式来修改社会的记忆框架:第一种是伪造传统,即新兴资产阶级也宣称自己拥有引以为傲的家族历史,但这往往是徒劳的,因为贵族阶级有贵族阶级的圈子,你伪造的家族历史很难得到全体圈子成员的一致印证;第二种做法即是以资产阶级自身的“新近的过去”取代贵族阶级“遥远的家世”,这种方法往往比较奏效,因为对人们来说,保持近期的记忆相对容易些,并且,通过近三代以来的艰苦奋斗,资产阶级不仅使自己而且还带动了追随他们的人出人头地,这就足以让社会在其记忆空间中为他们留下一个位置了。哈布瓦赫举例说,比如在法国,社会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三代拥有财产,就会被认定为“新贵族”,而不必要有完整而充分的证据。
当社会把注意的目光从贵族阶级“遥远的家世”上转移到资产阶级“新近的过去”上的时候,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确信:存在一类比尚武好战更有价值的活动和存在着一种比勇敢忠诚更为荣耀的品性,这种活动和品性就存在于城镇商人和手工艺人的圈子里。在受到大家普遍关注的时候,资产阶级也成功地把自己所从事的营利性活动推到社会生活的中心,还把在他们职业传统中培育起来的那些道德品质带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资产阶级不仅让社会记住了他们所从事的营利性活动的贡献,还让社会记住了他们如下的道德品质:禁欲、节俭、诚信、敬业等。当整个社会都认可这些道德品质的时候,一种新的财富价值体系就出现了。人们开始承认并记住以下观点:在现在的社会里,只有拥有以上道德品质,一个人才能富有,假如一个人贫穷,那是他们不具备以上道德品质的结果,而要想消灭贫穷,就得对穷人们进行以上道德品质的教化。
社会发展至此,贵族阶级不得不承认,刀光剑影已趋暗淡,忠勇可嘉已成传说,头衔再无价值,现在,决定他们身价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这些新活动,倘若要在这些新活动中施展身手,就必须增进自己与资产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之间的联系。随着形势的变化,连贵族阶级自己的“孝子贤孙”都不愿意在他们的记忆空间中为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遥远的家世”留下一席之地。贵族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至此被冲得七零八落。这样,更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就带动或者迫使社会重构了主流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哈布瓦赫说:“如今,社会必须故意将遥远的过去,连同整个价值秩序,以及建立在这种秩序之上的人和事迹的整个等级体系都统统忘掉,而更加重视晚近的过去,因为晚近的过去与现在是衔接在一起的。”[2](230)“遥远的过去”宣扬财富是对忠勇的嘉奖,而“晚近的过去”则表明,财富是社会对个人节俭生活、诚信经营的必然补偿。
四、新老资产阶级有关财富道德记忆的冲突
上一部分我们说到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的是承贵族而起并较早富裕起来的城市商人、城市手工业者、工厂主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批通过“新的门路”而迅速发家致富的人不断涌现出来,这些人即是从事股票交易、放贷收贷、金融投资等职业的人。为了区别两者,哈布瓦赫把前一类人称为“老资产阶级”“保守的资产阶级”“旧富人”,把后一类人称为“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新成员”“新富人”。
哈布瓦赫注意到了新老资产阶级的价值冲突。在老资产阶级的眼里,新资产阶级都是些“暴发户”。对这些人,他们持一种“道德谴责”的态度。因为,在老资产阶级的道德记忆中,财富是通过自己安分守己、勤勉工作、诚信交易、审慎经营而创造的,但是这些新资产阶级却不按照这样的套路或品性来赚钱,他们爱好冒险、投机取巧,所获得的财富与所付出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总是不明不白。这样,在老资产阶级眼里,这些骤然而富的新资产阶级不仅缺乏自己身上的美德,而且,他们的品性还与自己所认可的美德处处相矛盾。于是,他们就在新资产阶级身上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
这个时候,以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就要为自己“正名”了。前面讲到,社会认可某个阶级或群体的前提即是这个阶级或群体给社会带来了贡献。对新资产阶级而言,最为根本有效地去除老资产阶级“道德谴责”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对社会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为社会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帮助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满足更多的需求等。
经过自己的努力,新资产阶级确实也从社会那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哈布瓦赫强调说:“社会首先看重他们的,是他们能够一个个登台亮相,每一个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追求新奇的浅薄心理,所以,正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使得社会无限地扩展了它关注的领域。他们的多样性迫使其成员要完成的技巧越来越困难,并塑造了一种节奏逐渐加快的社会生活,社会认为这样很重要。就此而论,这些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可能理应被置于非常高的地位上,受到这个社会的敬重。由于他们只对投资和企业领域中的新兴事物才真正感兴趣,所以,只有观念、需求、品位和时尚领域内出现的新花样才能够吸引他们。因此,在财富的背后以社会优越性的形式出现而受到尊敬的东西,不再是曾经归属于老富人的道德品性,而是界定新兴富裕者灵活机动和变化无常的头脑的这些特点。”[2](258)
在哈布瓦赫看来,新资产阶级助长了社会追求新奇的心理,扩展了社会的关注领域,加快了社会的生活节奏,社会认为这些是他们的贡献,便认可他们并把他们置于非常高的地位,还在社会集体记忆中凸显了他们的如下记忆:财富并不是经由本分、节俭、审慎等美德而来,而是经由创新创造、灵活机动、适应力强等美德而来。新资产阶级已使社会逐渐接受了如下评价人的价值标准:这是一个以“最大程度地增进利益”为目标的时代,经济形势与致富之道都千变万化,如果一个人能够迅速地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能够“玩出新花样”并且带动其他人通过转变旧转念、树立新观念而赚取财富,那么,这个人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他及其创造的财富也会受到社会更多尊重。
小结
借助哈布瓦赫的相关论述,我们看到,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新老资产阶级,他们一起遗留给后人一个共同的记忆:财富与道德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能够比较有效地解释财富获得的合法性及增添财富认可的神圣性,也使财富拥有者得到其他人的尊重(至少免遭质疑)。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社会对“不义之财”或“没有资格配享其财富的人”总是嗤之以鼻的。强化对这种联系的认知,有助于人们以一种更加自信、积极的态度去创造财富。
当然,在财富与具体德目的联系上,不同社会阶级的认知是不同的,而社会不可能均衡接受这些不同的阶级道德,他必须要对这些多元甚至是矛盾的阶级道德进行筛选排序、分出主次,从而维护社会思想的“统一性”及社会发展的“凝聚力”。这即是向玉乔教授在研究道德记忆时所注意到的“集体记忆的选择性或意向性”现象[6]。“社会记忆正是在澄显与遮蔽的互动中,逐渐把那些有利于人类作为活动主体持续健康发展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澄显和确证下来,而逐渐扬弃掉那些不利于人类作为活动主体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和力量,从而成为社会历史进步和文化系统传承的内在机制。”[7](258)
社会“澄显”某一阶级道德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一阶级依其“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这样,在封建社会,社会高扬的是贵族阶级勇敢忠诚的品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中期,社会高扬的是老资产阶级勤俭谨慎的品德;在资本主义新近转型发展期,社会高扬的是新资产阶级创新灵活的品德。通过这种高扬,社会要引导其他阶级认识到,他将以其最为认可的那个阶级的价值体系来评价其他阶级的所劳所得。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并没有详细论及无产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劳动创造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观点,劳动光荣是无产阶级认可和宣扬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包括一般性的体力劳动,也包括比较复杂的创新创造劳动)才创造了社会财富,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财富积累都有剥削群众劳动成果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71)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上社会阶级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全然不提阶级压迫,明显有掩盖或美化财富剥削之嫌,这一点需要注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活力为人们更好地创造财富提供了多种可能和良好条件。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立场,讴歌勤劳致富、合法劳动、创新创业、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并使其成为社会主流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只有牢固树立上述主流的对财富的道德记忆,像一夜暴富、大赚快钱等观念及其催生的各种投机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才能在道德上受到深入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获得良好的道德环境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