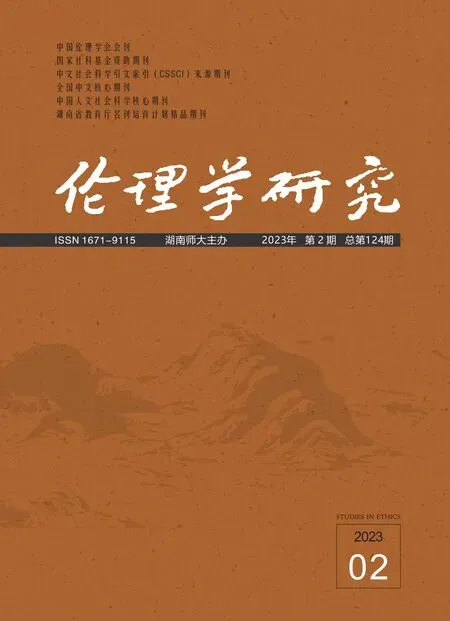评运气均等主义的三种变体理论
高景柱,王培培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平等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当今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诉求平等价值。这与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巨大影响密不可分。罗尔斯不仅复兴了政治哲学,而且将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转换为“平等”,其平等理论也在当代平等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然而,罗尔斯的平等理论也遭到了不少质疑,其中一种批判认为其差别原则没有将平等和责任结合在一起,消解了个人责任。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一些政治哲学家以罗尔斯的平等理论为坐标,通过对其的批判、修正或发展而建构了自己的平等理念,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森(Amartya Sen)和阿内逊(Richard Arneson)等自由主义者,G.A.柯亨(G.A.Cohen)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平等观的形成就是如此。在这些理论中,运气均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理论是一种重要的平等理论,它通过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从而弥补差别原则的缺陷。然而,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面临着各种批判,为了回应质疑,运气均等主义者发展了三种主要的变体理论。这三种变体理论如何回应质疑以及回应是否有说服力,将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及其面临的批判
德沃金等人构建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可以被视为传统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平等理论如何处理运气对分配的影响。在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中,选择与环境的区分极为关键,“我们的命运中的一些事情要面对承担责任的要求,因为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还有一些事情不适合责任要求,因为它并非出自人为,而是自然或运气不佳使然”[1](331)。德沃金区分了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选项运气是一个自觉的和经过计算的赌博如何产生的问题——人们的得失是不是因为他接受自己预见到并本来可以拒绝的这种孤立风险。原生运气是一个风险如何发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同于自觉的赌博”[2](73)。倘若人们因坏的原生运气而处于不利境地,人们就不应该为此负责,如被流星击中就属于原生运气。倘若人们由于坏的选项运气而处于不利地位,人们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这样,环境和选择的区分就转化成了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的区分。对于运气均等主义的基本理念,柯亨认为,“消除非自愿的不利,据此我(规定)是指受苦者对之不能负有责任的不利,因为这种不利并没有恰当地反映他所做出的、正在做出的或将要做出的选择”[3](119)。奈特(Carl Knight)则认为“根据这一原则,因先天残障、天赋差和出生于不利的社会或经济环境而产生的不利条件,通常被认为产生了补偿的权利,因为它们来自机会的不平等,而那些因选择作出更多或更少努力或追求某些目标而产生的不利条件则没有,因为它们反映了机会的不同用途”[4](173)。奈特融合了机会平等、运气、环境和选择等运气均等主义的核心概念,更加完整地表述了运气均等主义的一般立场。
首次将上述平等理论概述为“运气均等主义”的学者是安德森(Elizabeth S.Anderson)。她指出,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认为平等理论的根本目标在于补偿先天残障、较差的家庭背景等不应得的坏运气,同时,个人应当对其选择的后果负责,持运气均等主义立场的学者主要有阿内逊、柯亨、德沃金、内格尔(Thomas Nagel)等人[5](288)。罗伯斯(Ingrid Robeyns)也认为“在政治哲学中,柯亨、德沃金、阿内逊和其他人的著作产生了一系列的平等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被称为运气均等主义”[6](1132)。虽然这些学者都共享着运气均等主义的核心理念,但在“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上,运气均等主义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构成了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争论。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德沃金的资源平等、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柯亨的可及利益平等(equal access to advantage)以及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等理论。它们分别将资源、福利机遇、可及利益和可行能力作为平等的分配物。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主要关注“分配什么”和“如何分配”。就平等物而言,虽然可及利益具体指什么尚不清楚,但是相较于资源、福利机遇和可行能力,这一平等物的内涵的广泛性可以克服人们对平等物偏重于客观或主观的片面性的指责。此外,无论哪种传统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都将责任和平等联系起来,然而,这些努力是否成功,是非常值得人们怀疑的。正因如此,传统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遭到了来自平等主义和非平等主义的强烈批判。一方面,以安德森和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等人为代表的关系平等主义者对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展开了批判。他们指出了选择和环境的形而上学划分使得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无法追踪真正的责任在哪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安德森认为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对坏的原生运气、选项运气以及罕见疾病的受害者都没有真正做到平等对待①参见塞缪尔·谢弗勒:《什么是平等主义》,高景柱译,《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3 期;Elizabeth S.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Ethics,Vol.109,No.2,1999,pp.287-337.。另一方面,以优先主义、充足主义等为代表的非平等主义理论间接质疑了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不过,它们还试图避免安德森所指出的运气均等主义基于人际比较所产生的问题,并努力作出回应②参见Richard J.Arneson,“Luck Egalitarianism and Prioritarianism”,Ethics,Vol.110,No.2,2000,pp.339-349;Harry Frankfurt,“Equality as a Moral Ideal”,Ethics,Vol.98,No.1,1987,pp.21-43.。这些对传统运气均等主义的批判都凸显了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正如拉兹比(Hugh Lazenby)所言,“‘运气均等主义’这个术语被应用于一群非常不同的理论家。此外,这些理论家吸引了大量的批评和注意力,这导致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替代方案,试图解决支持这些‘运气均等主义’立场所产生的直觉上令人反感的后果”[7](282)。接下来我们将归纳和评析该理论的三种变体理论。
二、制度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及其缺陷
为了回应关系平等主义者对运气均等主义的批判,谭(Kok-Chor Tan)构建了制度运气均等主义(institutional luck egalitarianism)理论。相较于传统运气均等主义,该理论有三个明显的特征:“(a)运气均等主义是对分配正义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正义或道德的全部。运气/选择原则用于确定个人的分配权利。(b)它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基本结构;其目的是确保社会制度不会将运气转化为个人的社会优势或劣势,而不是使人的自然运气平等。(c)运气均等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分配平等提供一个正当的基础,它本身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分配原则。换言之,运气均等主义为分配正义提供了一个基础原则,而不是实质性原则。与此相关,它解释了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目的是什么,但它本身并没有说明分配什么和如何分配。”[8](108)我们将以这三个特征为依据,具体解释制度运气均等主义的基本理念。
首先,制度运气均等主义仅限于分配领域,不同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援助或救助问题。分配正义是一个关于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如何在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平等分配资源的问题,只有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选择和运气才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运气均等主义认为对基本需求的满足在道德上是不重要的。相反,运气均等主义者可以像大多数平等主义者一样,接受基本需求的满足优先于分配平等的承诺”[9](670)。其次,制度运气均等主义的主题是制度而不是自然。运气均等主义只解决自然偶然事件在社会制度的影响下造成的严重不良社会后果。例如,一个人天生是蓝眼睛还是棕色眼睛,这完全是一个运气问题。然而,如果社会制度使得棕色眼睛的人比蓝色眼睛的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或资源,那么眼睛的颜色就不仅仅是运气问题,它已经由一个运气问题变成一个正义问题,这时人们就应该改革该制度[8](103)。最后,运气均等主义致力于证明分配平等为什么重要,其证明方法是区分选择和运气,该区分只是为如何减轻运气因素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让人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提供一个基础性原则。它只是对平等观的一种承诺,这种平等观该如何实现,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运气和选择因素。这种实现分配正义的平等观会对平等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详细界定,是一种有关分配平等的实质性原则。譬如,资源平等、福利机遇平等、可及利益平等在如何实现运气均等主义的承诺方面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责任的限度和平等物等方面。它们共享着运气均等主义的基本理念,但是在如何实现该理念的实质性原则上存在分歧[8](106)。在运气均等主义内部,分配什么和如何分配的争论还没有停息。
在谭那里,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可以与安德森的民主平等观相抗衡,并且可以成功回应安德森等关系平等主义者对运气均等主义的批判。首先,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可以成功回应对疏忽大意的司机的苛刻异议。虽然制度运气均等主义主要解决的是达到最低标准的资源分配问题,但是它也承认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优先于分配平等的承诺,并不反对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当疏忽大意的司机和小心谨慎的司机同时需要救助时,制度运气均等主义也不反对选择在其中的作用,允许先救助小心谨慎者。然而,疏忽大意的司机还拥有获得救助的基本权利,只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他的这种权利不会立即得到满足。其次,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并不认为必须补偿所有不幸的自然特征,这就可以成功回应安德森提出的运气均等主义将补偿长得丑的人这一异议。对长得丑的人进行整容手术对制度运气均等主义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个正义问题,只有当长得丑的人实际上处于不利境地时,制度运气均等主义才会试图进行补偿。最后,制度运气均等主义还关注社会平等。当制度运气均等主义作为一种基础性原则出现时,它会涉及民族、种族和性别等社会问题。“它承认分配正义的动机是确保人们之间的关系最好地反映他们彼此之间的平等地位。它的运气/选择原则并不意味着对平等的社会解释的(非社会性)替代,而是对社会平等要求的另一种解释。”[9](686)此外,在谭那里,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可以直接为全球分配平等进行辩护,因为它还关注全球制度如何处理这些自然事实。
制度运气均等主义遵循传统运气均等主义对选择和运气的区分,并将其与政治社会领域的制度相结合,探讨了制度如何应对运气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然而,谭为运气均等主义所做的辩护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制度运气均等主义仍然依赖选择和运气的区分,并没有避免传统运气均等主义所遇到的形而上学挑战。谭指出,人们对选择和运气如何区分,在哲学上应该持不可知论,只将选择的概念看成是在社会的特定分配领域发挥作用,“所有运气均等主义者需要假设的是,出于实际和社会目的,社会成员可以合理地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由选择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人(因此要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另一种是没有自由选择的人(因此不需要负责)”[8](137)。既然选择只在社会领域发生作用,人们作出的选择就会受到社会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人作出的选择有可能不是在理性状态下作出的,但还需要为其选择负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个人责任的规范性评估的标准,也就是说,即使选择和运气只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判定何为选择的标准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评估社会制度时,我们应该质疑我们在运气和选择之间作出的区分这一社会共享观念。否则,在分配正义的运气均等主义原则下管理的社会制度仍然是保守的,以便符合社会习俗和惯例”[10](412)。易言之,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人们在哲学领域对选择和运气的区分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没有问题,然而,将运气和选择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社会分配领域,就会使得对其的分辨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反,倘若将选择限定在个人理性控制的范围内,让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辩护。
第二,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关注的范围过于狭窄,只关注制度如何处理运气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所有与运气相关的不平等问题。例如,一个不幸失明的人应该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其基本需求应获得满足,不管造成失明的原因是什么。然而,当一个人和正常人相比只是轻微地接近近视时,这一运气因素就得不到任何处理,因为其既不满足要求获得援助的条件,其不利影响也不是制度造成的[9](681)。不过,“这条界限实际上很难明确划定:如果人们根本上具有基本需求的主张,而且这种主张应当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考虑,那么人们由于自然因素而承受的轻微不幸为什么就不应当得到考虑?将运气/选择原则限制到原生运气通过制度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将这个原则贯彻到底,显然也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11](421)。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将其领域限制在分配正义领域,为人道主义和政治正义在平等理论的讨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种想要容纳一些其他价值的多元主义特征的努力,其实已经动摇了运气均等主义在分配平等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虽然谭极力主张自己的理论属于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但是其理想与民主互惠的关系更为接近。谭指出,“制度的公正仍然是运气均等主义者的首要目标,因为制度的设计不应该将个人的自然事实转化为针对他们的社会优势或劣势。然而,这种制度上的关注仍然是一种运气均等主义的立场,因为它从根本上关注的是制度如何应对运气问题”[8](104)。虽然制度对运气问题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它在无形之中将导致不平等的原因由自然特征和社会环境等运气因素转变成了制度行为,这种强调制度调节作用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实际上与民主互惠的社会理想相类似,它们都诉诸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统一性,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都是社会团结,正如有论者所言,“民主互惠侧重于社会合作的安排,并试图回答这种安排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被视为公平的问题。那么,至少就分配而言,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可以被视为这种公平合作条件的一个提案”[12](441)。
三、动态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及其限度
汤姆林(Patrick Tomlin)将运气均等主义分为标准(静态)运气均等主义(standard luck egalitarianism)和动态运气均等主义(dynamic luck egalitarianism),标准运气均等主义就是传统运气均等主义。标准运气均等主义对责任的认定是有问题的,它只对责任进行一次认定,如果在某时间点人们的选择带来了不平等的后果,而自身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那么以后的选择都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这样运气均等主义越是对选择敏感,就越会加剧分配的不平等,这与其平等待人的理论目标相悖。因为“标准(或静态)运气均等主义(SLE)建议,根据公正的基线,我们对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择者的责任)作出一次性判断,该判断将告知此类不平等是否公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公正。公正的不平等定义了一个新的公正的基线,下一组选择将被用来衡量”[13](396)。汤姆林将时间看成是影响责任的因素,认为运气和责任的界限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艾伦和鲍勃都拥有60 个单位的初始资源,不过,艾伦在夜晚放纵自己,消费了这些资源,而鲍勃没有将其挥霍掉。艾伦在做完该选择后,就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决心过一种与鲍勃一样谨慎的生活。他们拥有的才能和面临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这种状态持续了50 年。在这段时间中他们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因为艾伦要为自己50 年前的鲁莽行为负责。如果鲍勃将初始获得的资源拿来投资教育,并将其获得的额外收入继续拿来投资,那么他就过着比艾伦更为奢侈的生活[13](396)。该例说明的问题是,一个人在某时刻作出的选择的影响将是持续性的。换言之,“我们在t 时刻做了什么选择,通常会影响tz的选择,各种选择相互渗透。因此,当我们作出第二个选择时,第一个选择导致的不平等会因我们的不同选择而加剧。因此,即使我们在f 点作出了道德上等价的选择(如我们有多努力),我们仍然要为在I 点作出的选择负责”[13](397)。在汤姆林那里,选择对人的生活产生持续影响是不可取的,因为在50年间,他们过着同样谨慎的生活,让艾伦为50 年之前的选择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
汤姆林的上述观点受到了帕菲特(Derek Parfit)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讨论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责任不会随着个人身份的变化而转移。第一,基于对存在于关系R 中的人格同一性的考虑,帕菲特认为,个人身份是存在于关系R 中的,如果两个不同时空中的我之间存在关系R,且这种关系是排他性的,那么这两个我就具有人格同一性[14](373)。在帕菲特那里,判定不同时空的人们是否存在这种一对一的排他性关系R 的标准,就是看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是否有一种基于正确原因的“心理联系性和/或心理连续性”,而这种持续的心理联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弱,由此关系R(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之间的联系)也会随之变弱。汤姆林受此启发,总结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责任会减弱的论证过程,分别是:(1)个人身份是由关系R 支撑的;(2)个人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3)责任追踪关系R;(4)关系R 是可变的,不是二元的。他最后得出了结论:责任是可变的,它随着关系R 而减弱[13](402)。基于此,让此时的我对我在之前心理状态下作出的选择持续负责就有悖常理。第二,基于责任本身的考虑,汤姆林赞同一种“责任需要引导控制”(responsibility requires“guidance control”)的观点。例如,如果某人绑架了一个儿童,一周后突然醒悟,不再认可他之前的这个行为,并对其表示合理遗憾,那么他应该对其行为负责吗?按照关系R 理论,只要他的心理发生改变,这种责任就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但是,这很明显不符合常理,因为他可以否认做选择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否认做选择时的心理过程。“责任需要引导控制”的观点,不仅将行为者的选择与其先前行为的态度相联系,还与其当时产生行动的心理过程相联系。作出绑架行为的人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就不再将绑架行为看成是他的智力过程,似乎不妥,因为时间间隔太短,他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将关系R 对人的责任的持续影响,与责任需要引导控制的思想相结合,就可以得出动态运气均等主义的基本理念。首先,动态运气均等主义并不涉及“关于什么的平等”的争论,它在展开这一理论前就预设了人们有资源、福利和可行能力的统一标准。其次,动态运气均等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当时我负责,不代表现在我还负责。支持这一观点的方法是接受关系R(而不是个人身份)对责任的持续有影响,或者接受为了在任何特定时间对选择负责,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选择或产生选择的过程相联系”[13](405)。再次,运气和责任的区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责任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为运气问题,人们需要重新对其进行评判。最后,如果某行为者被认为不再对其之前的行为负责,那么社会就应该对其进行补偿,从而减少其行为对其之后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依汤姆林之见,动态运气均等主义可以采取下述两种措施来达到这一点:“向后看的补偿机制”和“前瞻性的阻断机制”,前者主要是通过从幸运者到不幸者的资源转移来实现,其前提是不幸者不再对其之前的选择负责,后者主要是寻求减少当前选择对未来人的影响,从而防止基于选择的运气出现[13](405)。
如果我们将标准运气均等主义看成是探讨责任如何产生的理论,那么动态运气均等主义就是探讨责任如何持续、减弱甚至消失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责任理论的深化和发展。然而,即使这一理论动态地看待责任问题这一做法似乎具有合理性,但是其在论证过程中缺乏连贯性。
第一,动态运气均等主义依赖帕菲特所建立的关系R 来解释时间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值得商榷。依据关系R 理论,如果一个人不再认同之前所做的选择,那么这一选择相对于他而言就变成了运气,因此他就不再对其承担责任。从直观上讲,该解释似乎比标准运气均等主义更具有吸引力,因为那种导致在一个时间段内两个同样谨慎生活者的生活水平不同的原因是,其中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受到了几十年前的选择的影响,这似乎不具有合理性。然而,人们可以提出两点疑问。一是,这两个同样谨慎生活者的生活水平不同,并不是因为在其付出同样努力的这个时间段内获得的报酬不同,而是因为之前所做的不同选择。二是,依赖于心理学事实来判定人们是否应该对之前的选择负责,不具有相应的稳定性。虽然人的心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之前的心理联系不再紧密,但即使人的心理变化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其也是难以捉摸的。此外,经过多少年之后人的心理联系就不再紧密,以至于可以不再为之前的选择承担责任或责任可以减弱,这是无法测量的。人际相异性决定了人的心理的差异性,而这种心理结构和认识的差异性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第二,即使从理论上而言人们对之前的选择不再承担责任是合理的,动态运气均等主义所建议的减少人们以前的选择对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的措施,也是不可行的。向后看的补偿机制也会存在标准运气均等主义中出现的对有才能者的奴役的情况,而前瞻性的阻断机制限制了个人选择的自由。然而,动态运气均等主义确实为思考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汤姆林也承认这种动态地思考责任问题的方式具有开放性,其正确与否有待进一步论证,“事实上,总的来说,道德责任理论似乎只专注于解释我们如何获得责任。思考责任是如何持续、消退或减少的,以及哪些理论对此类问题提供了更好的答案,这可能是责任理论的一个有趣的试验场”[13](404)。
四、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及其局限性
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baseline-relative luck egalitarianism)是为了回应郝蕾(Susan Hurley)所谓的运气均等主义的“无聊问题”而提出的。郝蕾认为,运气均等主义对个人责任的界定只能根据个人作出的选择,而这种责任既不能反映他人的选择,也不能反映他们之间由于选择所导致的不平等,然而,依照运气均等主义的核心观点,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运气均等主义不仅应该支持反映个人选择的不平等,还应该支持反映个人之间的选择的不平等[15](67)。为此,朗(Gerald Lang)运用郝蕾所举的欧内斯特和伯蒂的例子来进一步加以说明。欧内斯特由于自己的选择得到了X,而伯蒂得到了X+Y,他们分别对X 和X+Y 负责。换言之,欧内斯特既不为伯蒂的选择X+Y 负责,也不为他们之间的差距Y 负责。伯蒂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都不能控制其他人的选择[16](700)。郝蕾首先对她提出的无聊问题作出了回应,认为运气均等主义可以完全忽略欧内斯特和伯蒂之间的收入差距,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然而,该回应虽然突出了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认真对待平等主义。欧内斯特和伯蒂的收入差距看似是各自的选择造成的,但实际上是运气造成的。针对无聊问题的第二种回应承认欧内斯特遭遇了厄运,并建议欧内斯特与伯蒂之间的收入差距Y 应该在他们之间平分,他们都最终获得X+0.5Y,朗称此回应为让步响应(the concessive response)。然而,这一回应也是有问题的,因为造成欧内斯特和伯蒂收入不一样的原因,不一定是欧内斯特遭遇了厄运,也有可能是欧内斯特和伯蒂拥有同样的选择机会,只是自己没有作出与伯蒂一样的选择,从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存在[16](703)。这两种回应都没有很好地处理选择和运气之间的关系。
鉴于以上对无聊问题的不成功回应,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就应运而生了。第一,朗将N 作为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的基线。依此观点,收入差距Y 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欧内斯特的收入X 与伯蒂的收入X+Y 和基线N 之间的关系。N 的存在表示在分配中设置了一个界限,与这一界限相比,处于这一界限之下的收入不平等是不被允许的,处于这一界限之上的收入不平等是被允许的。此外,这一基线的存在也突出了平等的重要性,它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比较搭建了一个平台,人们之间的相对劣势是根据与基线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的,而不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比较来界定的,这就避免了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到底是选择还是运气的不确定性问题。第二,基线N 是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的理论核心,一方面,基线代表了人们有权利平等获得的资源,人们在达到基线水平后才允许进行自由选择,当选择失败后,对其进行补偿的参考标准就是平等的基线水平,这一基线水平的衡量标准就是对N 所赋的数值;另一方面,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之所以关注个人与基线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一基线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意义,它规定了一个具有普遍相关性的平等主义框架,“确保在一个公正的分配中,不同个人的分配份额对同一基线表现出同样的对选择的敏感性”[16](709)。
朗指出,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还可以成功应对史密兰斯基(Saul Smilansky)提出的对传统运气均等主义的“基线悖论”的挑战。史密兰斯基认为基线是一种有用的规范性工具,在平等主义中,标准基线就是平等。传统运气均等主义认为不平等的唯一理由是人们自由地选择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传统运气均等主义必须将基线定在顶端,这一基线是根据有效人(Effectives)的最高收入或最高潜在收入制定的,而这时无效人(Non-Effectives)也将会处于顶端,因为倘若不这样做,无效人就不会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有效人的收入也就不会通过与无效人进行比较而获得正当性。这时基线悖论就产生了,“对选择—平等主义而言,无效人必须位于最高收入(或者,甚至是最高的潜在收入)这条基线上,然而,有效人却很有可能低于基线,尽管他们毕生都在努力贡献”[17](58)。要想解决这一基线悖论,就需要重新对待无效人以及公正地对待有效人。依朗之见,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可以解决这一基线悖论,将对无效人的补偿仅仅限制在基线N,当其收入低于N 时,可以用坏运气来加以解释;有效人赚取的收入不管高于还是低于N,都可以用其自由选择来解释。
在朗那里,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还可以缓解传统运气均等主义带来的偏好和多元化的担忧问题。偏好担忧是由拉兹比提出的,主要指的是他人的选择可能会对两个没有作出任何选择的人产生影响。譬如,A 选择赠送B 礼物,相对于C 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并不是B 和C 选择的结果。依传统运气均等主义之见,A 的选择对B 和C 来说是运气因素,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他人的选择[7](271)。然而,这又违反了人们的道德直觉,因为基于友谊等的赠予活动是维持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活动。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为此提供了一种可供解决的模式,它将被传统运气均等主义看成是运气的因素,看成是选择因素。例如,礼物接收者之所以接收礼物,是因为他想表达他对友谊的追求,虽然他不能控制他人的选择,但是他可以决定自己选择什么,而自由选择是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所要维护的核心理念。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将平等看成是基线的核心价值,但是当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基线具体设定的N 值发挥相应的作用来化解多元化的担忧[16](717)。虽然平等是基线的核心价值,但是基线并不是平等本身,它可以通过具体值的设定来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
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设置了一个平等主义的默认基线标准。然而,它并没有成功地完成朗加在其身上的任务:
首先,它没有成功解决基线悖论问题。基线应该设在哪儿是不确定的,倘若基线设在顶端,基线悖论的问题还会出现。这并不是说N 的具体值是不确定的,相对基线可以为N 赋具体的值,只是具体的值在整个平等主义的分配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是不确定的。
其次,它没有成功地回应传统运气均等主义所出现的偏好担忧问题。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给出的答案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方面,将接收者的运气转化为选择的回应,偷换了实施选择的主体概念,也存在倒果为因之嫌。是选择者作出了相应的选择后接收者才获得了好运进而发展这种好运,并不是接收者作出了发展这种好运的选择后,选择者才决定要给他好处,选择者作出这一行为完全具有偶然性。另一方面,第三人没有做任何选择就处于劣势地位对他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而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与之相对照,埃尔福德(Gideon Elford)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回应,他认为假定的不一致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运气均等主义要求不平等,同时也谴责不平等。运气均等主义所谴责的不平等与其他影响选择的后果有关,因为它们创造了原生运气的不平等,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公平的。然而,因为运气均等主义只要求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自我影响的后果构成的不平等,而将其他影响选择的不平等看成是原生运气的不平等,所以该理论没有担负那种因谴责和要求完全相同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不一致[18](624)。
最后,它也没有成功回应运气均等主义引发的多元化的担忧问题。就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而言,与其他价值相结合可以看成是为其进行辩护的一种方式,但是就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而言,倘若人们将基线平等的关注范围由分配领域扩展到其他政治或社会价值领域,这不但不利于解决运气均等主义在分配领域面临的问题,反而产生新的问题。基线应该设在哪儿是不确定的,为了协调平等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而为N 赋的值,很可能会与平等价值产生冲突。譬如,N 值在50 个单位时正好可以达到平等,但是为了与团结这一价值相协调,N 值就会提升到60 个单位来使无效人获得更多补偿,这无形之中就会增加有效人的负担,使得他们的选择自由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