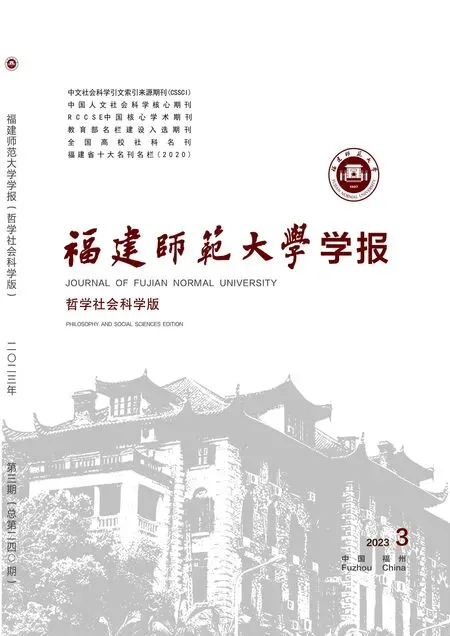南帆历史散文的智性突破
——兼论中国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
吴青科,袁勇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智性”在当代散文中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学价值趋向,其基本内涵有“知识与趣味”兼具的意味,具有一定的哲学意蕴,体现出一种“智的价值”(1)陈剑晖:《论中国现代智性散文》,《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9期,第147页。。“智性”概念作为当代散文理论得以重申,一个重要的机缘是基于当代散文创作的具体批评。孙绍振在评价南帆散文特征时谈道:“在现当代散文中,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是,叙事、抒情和幽默,但是南帆却离开了当前散文驾轻就熟的一切,超越情感和调侃,炫示他的智性的纷繁和深邃,作智性的探索。”“他的全部特点明显有异于审美,我们禁不住要以‘审智’来为它命名。”“‘审智’不同于审美之处是:它并不依赖于感情,而是诉诸于智性,从感觉世界作智性的、原生性的命名。”(2)孙绍振:《当代智性散文的局限和南帆的突破》,《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第65页。“中国美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自主性与合理性”(3)邢研、朱立元:《试论中国当代美学的“缺席”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43页。,孙绍振将“审智”概念置于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自洽性体系当中来解读,将之与“审美”“审丑”相提并论,并予以整体性把握。“审智”在概念本质上同属于一种文学批评术语,可运用于散文,但不局限于散文,可纳入建构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愿景当中。在孙绍振看来,南帆的文化智性散文由于从西方现代文论当中受到启发,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性特征,故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派散文的真正崛起,填补了中国现代派散文的空白。理解当代智性散文以及“智性”的内涵,一定程度上需要以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为根基。
“文化”和“历史”是南帆散文的两大主题,其散文的“审智”书写,可以大体归结为文化审智和历史审智,而从文化审智向历史审智的过渡是南帆散文的标志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体现为个性化的散文创作的意义,同样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理解的深化和转变。对于当代散文而言,这种深化和转变不仅意味着一种文学主题的切换,更意味着有关文学、文化、历史等范畴的深刻思考。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散文在原有智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飞跃,而这种飞跃的姿态不是一味地追求新变,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和回望。当代散文在有关历史的主题理解以及创作上体现出某种鲜明的自觉意识。“人们如此期待过往发生的一切成为现今的各种资源,以至于使用形形色色的方式给予反反复复的叙述。这表明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必然带来历史的多种理解、阐释和再写作,产生了思考历史的各种不同命题。”(4)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29、415、424页。在南帆、王尧、陈平原等人的散文作品中,“历史”不仅意味着一种叙述策略、一种主题,同样意味着一种智性的向度。“历史”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局限,由一种要素上升为一种现象,且这一现象是成规模、成体系的,孕育着散文发展的某种新趋势。
一、回望:文化向历史的智性过渡
南帆历史散文体现出的某种新变,与他向西方理论寻求突破的“另一种源流”不同,他将目光“由外向内”地投向了历史场域。就当代智性散文而言,南帆散文的这一新变同样属于一种新的“源流”,只不过这一“源流”既非中国诗学传统亦非西方诗学传统,而是有关“历史”的智性思考。南帆赋予“历史”概念一种深刻的理论意义,“‘过往发生的一切’远非仅有历史话语提供的解释和叙述,文学话语的视角或许可能建构另一种历史面目。‘历史’并非仅仅是一个抽象、模糊同时又令人敬畏的词汇”(5)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29、415、424页。,“我是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背景之下重新核定记忆的理论位置。……我的想象之中,文学、历史、记忆构成了彼此交汇的三角关系。”(6)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29、415、424页。
(一)回望历史:面对现代性的省思
如果将南帆的文化智性散文理解为寻求一种普遍化的意义阐释模式,那么,历史智性散文则体现出一种有关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这种反思方式立足于历史的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回望”,继而重新认知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之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7)南帆:《文化的活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97、204页。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南帆历史散文视为一种文化思考的创作呈现,正是通过历史叙事,南帆实现了由西方现代文明为主体的共时性文化研究向本土传统文化审视的关键性转变。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朝向“历史”的回望姿态并未成为一种退向传统的趋势,而是重新发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意义。“我们始终要意识到传统在时代文化之中的正确位置。一个时代文化的内部坐标通常隐含了纵横两轴。纵轴来自传统的继承。”(8)南帆:《文化的活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97、204页。基于历史的视角,南帆甚至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提出“中国经验”,而其核心内涵始终与传统文化认知密不可分。“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并且从晚清以来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个空间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传统的维度。不论反叛传统还是皈依传统,人们无不深深体验到传统的规约。不可否认,传统至今依然坚实地存在。”(9)南帆:《文化的活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05、277页。
以散文书写的方式重申“历史”,同时意味着一种“怀旧”与“省思”的人文主义态度。“记忆是一个可以四通八达的概念”(10)[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60页。,“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以及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11)[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60页。。南帆历史散文所传达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对历史意义的追忆、重估以及延续历史的重要性,这种基于个人和集体双重性的历史概念从认知上重设了当代智性散文的思想特征。
南帆历史散文以现代性和本土化的双重姿态出现,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偶然性以及个性化的文学行为,而应当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更为深刻的文学真相。南帆历史散文改变了有关散文“真实性”的意涵,罕见地表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质疑与探寻的态度。他无意于通过文学虚构的手段描述“历史”,而是尝试进入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人物的状态,继而关联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体验,从而实现跨越历史时空的情感共鸣。正是通过“情感关联”以及“体验共通”的方式,南帆历史散文存续了近代历史人物的“个性化”体验。从当代智性散文的表现方式来看,南帆历史散文对历史人物情感体验的再复原和再生成所产生的变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中的“他者”为中心的散文逻辑,即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体的散文表现方式。这个历史中的“他者”并非来自现实的实体存在,而来自历史的回想和重塑。“存在的意识,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意识。因为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和感受,即来自对生活之世界或处境的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史的了解’。通过这种历史意识,我们可以断定:人是在历史中活动的。”(12)龚鹏程:《近代思想史散论》,台北:东大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在内容范畴上,南帆历史散文带有明显的文学地理学特征,主要围绕八闽历史文化——东南边陲,历史上的蛮夷之地——进行叙事。这种“边缘与中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生成一种文本关系结构,反映在文学叙事层面上,象征着一种个人与族群彼此共通的齐鸣与呐喊。南帆历史散文突破了单一的有关人的思考维度,而将人与历史的关系作为一种稳固的关系结构予以思考。关于地域性的文化感受,南帆曾谈道:“我的历史兴趣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事实上是这一块土地的某种气质打动了我。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日子里,这一块土地仅仅逗留于人们视野的边缘地带,满口‘鸟语’,蛮荒之地。然而,近代史上这里出现了许多大人物,他们不同程度推动了历史的转型。当然,我没有兴趣历数他们的历史业绩,触动我的是他们的人生姿态。血气方刚,快意恩仇,慷慨激昂,愁肠百结,如此等等。这种人生与这一块土地相互养育,形成一个不同凡响的气质。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故乡。”(13)南帆:《文化的活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05、277页。在南帆历史散文体系当中,“历史”成为一种需要被重新认知、定义的概念,它不再仅仅指向一种过往的既成事实,而是内蕴于“历史”概念当中的某种尚未完成的迫切性意义,类似一种情绪暗流,成为人生之思、意义之谜、历史之殇。
(二)彰显民族性意识:“藉古以求新”的努力
不同于文化散文所体现出的睿智、冷峻,南帆历史散文由于聚焦历史关系和历史意义的思考,而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无法克服的悖论,这种悖论集中体现在人物心理体验与政治历史境遇的巨大矛盾。而南帆对这种矛盾性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和理智的思考,达到了情智交融的叙事境界。从智性的角度来看,审视这种矛盾所造就的历史“迷境”同样意味着一种审智。在历史的“迷境”当中,政治历史事件始终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人物始终努力积蓄突破“迷境”的力量,但在与历史和命运较量的过程中,人物最终选择了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这种历史与人物的关系在南帆历史散文当中生成一种持续生长的关系结构。《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宫巷沈记》《马江半小时》等提供的历史话语所忽略的主题,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历史盲肠》《村庄笔记》当中得到了延续。“不仅是这些主题的延续,同时,某些个人的独特体验与这些主题进行了深入对话……如果我的叙述仍然是历史著作记载的往事而不是这些体验的记忆,对话或许无法展开。这些体验朦胧曲折,并且交织在另一些观念之中,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提炼出来。”(14)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24页。
在散文所营造的浓郁历史氛围中,南帆试图通过一种想象和体验的方式,无限接近历史。这其中牵涉有关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的断裂与延续命题,这一命题的本质乃是南帆历史散文所具有的民族性意识,可以将之视为南帆历史散文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南帆历史散文最具深意之处。南帆历史散文所体现出的思想性和民族性视野在其“宏大背景+人物命运”的整体架构中被确立下来。南帆历史散文同样触动当代散文有关意义的思考,这种思考亦主要建立在对有关“历史”的认知深度之上。本质上,南帆对于历史的理解和思考延续了知识分子“藉古以求新”的精神传统,“可见复古与新变、传统与反传统乃是竞体为一的,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仅要有新的视野,更得调整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评述架构、放弃僵硬而不切实际的‘进步’‘保守主义’之类标签,重思传统对当代人的意义”(15)龚鹏程:《近代思想史散论》,台北:东大出版社,1999年,第50页。。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南帆的历史散文,较之他那些充满文化解构意味的文化智性散文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南帆历史散文同样是散文本土书写的嬗变和探索,而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从近代中国历史的视野转变为当代现实与历史融合的视野,从《辛亥革命的枪声》到《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再到《村庄笔记》,整体勾勒出这样一种变迁的线路,将散文叙事从纯粹的历史场域所积蓄的能量转变为有关历史和现实话题交相融合的思考当中。
二、情与智:历史智性的双重面向
有关当代智性散文的理解往往聚焦于智对情的超脱和排斥,而忽略了情与智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与由“主情”向“主智”的变革不同,当代散文在由“智”向“情”的返归途中,呈现出复杂而纠葛的内面,这种复杂性在当代历史散文中得到集中的展现。对于当代历史散文而言,抒情与智性在历史场域中如何实现统一,是一种带有历险性质的挑战。南帆历史散文以智性的方式突破了既有的抒情传统,即便在抒情意味最浓的散文当中,他所表现出的有关抒情的态度仍然是别开生面的。在他的历史散文当中,抒情既非轻松与自由,亦非理性克制与放逐,而是表现为一种难以抑制的焦虑感。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抒情是用来释放情绪感受的,而南帆历史散文中的抒情则是用来描述危险的触碰与体验以及之后的“心有余悸”。此时,抒情不再是一种个体性的放松行为,而是一种主体的生命存在体验。
(一)抒情的困境与突破:族群形象的塑造
在南帆散文中,最接近抒情特质的作品并未生成一种主题,且零星散布,比如收录于散文集《闲常之趣》中的《家居四君子》《到来一只狗》《送走三只猫》《芒果树》《别离》之类,这种兼具传统与现代诗学特征的抒情散文对南帆而言显然造成了一种类似情感失重的困境。创作实践表明,南帆无法在这种散文抒情传统中寻找到意义栖息的长久之地。《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可以视为南帆历史散文试图突破这一抒情屏障的力作。“一种渺小的焦虑、苦恼和危机感。一只小动物置身于某种毫无把握的环境之中。于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响声就会让它吓得六神无主。”(16)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如同条件反射,“抒情”成为一种潜隐于历史深处的刺痛感。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如同一场智性与抒情的博弈,南帆试图跳出既有抒情传统的影响,以智性的姿态投向历史的巨大黑幕之中。借助新的叙述模式,南帆在个人与历史之间建构起某种稳定的关系,可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历史对于个人的作用力。比如在描述父亲以及父母之间的爱情时,作为一个跨越时代的旁观者,南帆始终以一种冷峻的目光予以观照。“我必须再度提到一个事实:个人的爱情无力与历史的车轮抗衡。父亲与S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父亲与J的关系也证明了这一点。”(17)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父亲深感歉疚的是,他与母亲的爱情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磨难史。母亲必须一辈子为辛酸的浪漫付出代价。”(18)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如何摆脱抒情传统素有的平庸,成为摆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面前最直接的挑战。面对历史施加于人的种种重压,抒情最为擅长的功能面临失效的可能。在《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等历史主题散文中,南帆曾一度施展出的对人物的想象本领在现实题材中已然难以奏效。因此,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这部现实与历史交相叠加的作品中实施的抒情突破,无论从散文诗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智性的表现角度都面临巨大的困境。
散文的抒情传统表明,有关人间情感的表现看似轻松自如,但同样容易陷于乏味平庸。南帆最终在历史作用于作为个体之人的某个最强烈的着力点上寻找到了突破口。“逝者已逝。很长的时间,我一直不敢为母亲写些什么——因为我心里埋藏了一份隐隐的歉疚和恐惧。”(19)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以前写下的这些轻飘飘的隽永之言根本没有掂出疼痛的真实分量。”(20)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疼痛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巨大物质,坚硬得如同一堵厚厚的墙壁,同时,疼痛又无形无踪,没法把它一刀割去。”(21)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与抒情的柔性特征不同,南帆赋予了抒情某种“体感性”,从而将这种抽象的个体感受予以知觉化,进而将之嵌入历史的隐形躯体中。“壮士断臂,刮骨疗毒,这是历史愿意铭记的伟大疼痛。母亲的疼痛如此剧烈,同时又如此渺小。”(22)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如果将“疼痛”作为理解历史背景当中母亲形象的隐喻,那么父亲形象的代名词则是“畏缩”“沉默”。“父亲从这一次运动之中总结出一则人生哲理:沉默是金。”(23)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父亲没有逆流而上的勇气,他仅仅是本能地躲闪,收缩自己。”(24)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92、93、5、7、8、9、122、165页。父亲、母亲的两种不同形象与沉重的历史背景完全构不成相互匹敌的关系,那么,面对历史何以抒情?这是南帆提出的有关当代散文诗学的一个根本性命题。
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一书中,南帆所表达出的人物命运特征,暗示出某种历史功能的诗学隐喻,这种隐喻的内容同样表现在他对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命运的担忧。南帆历史散文从崭新的维度塑造出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即族群形象,继而以族群形象的整体性弥合个体形象的意义缺失。“南帆赋予其散文尤其是历史散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曾经真实存在过或者被虚构过的游侠实施当代‘招魂’,这一任务同样是南帆散文在人格塑造层面上的文化和审美诉求。林觉民、谭嗣同、林则徐、沈葆桢、林纾等教科书式的历史人物被南帆以游侠的人格形象重新唤醒,无疑具有多重的意义。”(25)吴青科、袁勇麟:《审美颠覆与文体突破——论南帆对当代散文的革命性意义》,《东南学术》2022年第4期,第222页。如同历史所制造的迷雾和困境,人物同样成为南帆历史散文中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如果从当代散文诗学传统来看,南帆颠覆了散文业已形成的叙述模式以及人物塑造的可信度,而赋予其历史散文一种整体性的智性思虑,即以宏观的历史性观照取代了微观的人物表演,这种有关历史智性的思虑成为南帆维持散文叙述的基本原则。
(二)历史智性的现实境遇:对当下乡村的零度叙事策略
《村庄笔记》可以视为南帆历史散文最新演进的成果。“书写中必然具有关于现世的态度与指涉”(26)徐晓军:《重返世界:论文学批评的现世性》,《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86页。,南帆通过《村庄笔记》将历史视野从近代、现代移至当下,这种视野的迁移赋予了历史智性现实层面的诗学意义,即实现了由历史想象向现实观照的转变,从而为历史智性散文开辟出现实主题表现的一种新路径。从此角度来看,《村庄笔记》在本质上仍旧属于从“历史”的视角审视即将成为历史的人类当下时代的境遇描述。“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的相当一部分乡村叙事落空了。预设的主题消散之后,粗糙而坚硬的乡村再度显露出来。无论如何,几个单薄的概念无法遮盖这个辽阔的地域。”(27)南帆:《村庄笔记》,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5、212页。这种叙事的落空与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小说对乡村的特殊关注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文学想象中的乡村叙述所遗留的现实空洞恰恰摆在南帆面前。“可以断言,当代文学提供的乡村空间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总和,一个醒目的乡村形象谱系存留于当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当代文学史内部存在着一部隐形的乡村文学史。”(28)南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第63页。这种有关乡村叙事的繁华景象几乎意味着一种意义的虚空以及诗意的嘲讽,“偌大的村庄如同一具僵硬而空洞的躯壳”(29)南帆:《村庄笔记》,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5、212页。。随着当代文学史有关乡村想象的巨大落幕,乡村被再度拖进历史的旋涡当中。南帆笔下所叙述的月洲村、五夫里、林浦村、赵家堡、石井码头、闽安村、尚干村等零星村落,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文化坐标都明显处于现实与历史的交汇地带,而《村庄笔记》与其他乡土散文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其历史与现实的“边缘性”和“变迁性”特征。南帆径直选择从脚下的土地出发去重新丈量并试图填补乡村叙述所遗留的意义空虚地带,这同样意味着南帆的历史智性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中心叙述开始兼顾到现实中正在变迁的边缘化乡村叙述。南帆的散文叙事揭露出乡村的真实且丑陋之处,乡村的丑陋是双重性的,一是杂乱无章的工业化残留,二是乡村与历史的断裂所造成的文化残缺。
《村庄笔记》延续并开拓了散文有关乡村叙述和想象的崭新空间,这一空间显然受到历史观念的内在启发。“文学显示,从本土、民族、乡村、文化传统到怪诞的美学或者宗教信念无不包含了另一些富于启示的主题。”(30)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27页。在《村庄笔记》中,南帆实现了从历史智性向现实叙事的转变,也正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南帆发现了“乡村”的真实面目。“乡村”取代“城市”作为一种地理以及诗学的双重空间,成为南帆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场域。因此,在南帆的视野当中,“乡村”成为和“历史”地位同等的诗学概念或者诗学维度,两者在《村庄笔记》中实现了真正的衔接。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南帆对于后工业时代的乡村进行了直面和叙述,当他从“丑陋”而缺乏诗意的现实乡村中脱身而出时,“这一刻我竟然产生了浮出深渊的感觉”(31)南帆:《村庄笔记》,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5、212页。,这种类似逃离梦境的真实感受在本质上类似于他一贯的历史想象体验。南帆在《村庄笔记》中所表达的“乡村”概念,已经隐约透露出他对于“乡村”的重新认知,这种认知在本质上被纳入历史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中。这种对于“乡村”的印象和理解与他曾经的知青“乡村”体验有所不同,即从个体性的生命体验转向乡村的历史体验。
正是借助历史智性的诗学思考,南帆的乡村题材散文在文体功能上实现了与小说进行比照的可能。他将小说题材擅长的乡村想象与批判转化为一种实在的乡村体验,而这种乡村体验已经不是纯粹私人化的诗意表达,而表现为对于乡村的历史思考。由此可见,地理空间对南帆智性散文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人物”“历史”成为南帆智性散文的基本诗学坐标。从福州的三坊七巷到周边乡村的地理空间变化,不仅意味着叙述空间的转移,也意味着文学表现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有关“历史”与“人物”的诗意想象普遍转化为当代乡村真实面貌的客观描述。如果说在历史的想象当中,人物尚且构成重要的散文文本因素,那么在有关乡村的描述当中,人物则彻底蜕化为一种不具备特殊意义的文本成分,这种带有符号学性质的人物认知特征,恰恰从侧面证明了南帆历史散文对传统散文有关人物和故事情节模式的颠覆。南帆历史散文的重心仍旧在于有关历史和思想的思考范畴,这从他对于散文文体的理解中可以看出。“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许多景象均可成为思想的对象。文学、思想、世界三者之间的距离远比预想的小。……我首要的意图就是,自由地表达个人与世界的对话——至于这些文字是否符合传统的散文模式,这并非多么重要的问题。有时,我更愿意把这些文字称为‘随笔’。顾名思义,‘随笔’可以自由自在,‘风行水上,自然成文’。”(32)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29-230页。《村庄笔记》时刻回响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奏响,历史与现实之间所造成的缺口没有在南帆以往的历史散文中实现合流,反而在“乡村”叙述中得以结合,这使得《村庄笔记》在南帆历史散文中显得尤为重要。
《村庄笔记》中尽管仍旧存在南帆擅长的历史想象,这种历史想象反复不停地试图将现实图景拉回到历史场域当中,但乡村实景最终有力地拒止了这种散文叙事的冲动,迫使南帆认真审视当下真实的乡村,这种由历史向现实的切换对于南帆而言无疑意味着一种挑战。南帆所采取的叙事应对策略体现出鲜明的零度叙事特征,大量客观现实甚至带有审丑意味的文本描述成为一种新的散文体验,构成了南帆历史散文对于诗学意义的重新思考。后工业化时代的零落乡村恰恰提供了促成历史想象与现实合流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合流当中,人物形象的功能同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历史想象中的人物不同,现实乡村中的人物成为嵌入乡村的构成部分,一起沦为命运与特征不可名状的后工业时代的遗留物。《村庄笔记》中出现的这种有关历史和人物内在的微妙变化,使得《村庄笔记》更具有现代小说文本叙述的特征,这种文体特征的变化本质上并没有背离历史审智的诗学轨迹。更进一步,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难以调和——描述并试图调和这种紧张的关系成为南帆历史智性书写的一个基本面向。因此,在《村庄笔记》中充斥着大量的类似于“无意义”的客观叙述,这种有关人物和现实的叙述显示出意义空虚的叙述压迫感,而缓解这种压迫感的仍旧是文本中有关历史的叙述与想象。
(三)共性与个性:历史叙事比较分析
如何洞察“历史”,当代历史散文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历史”的镜像中映现出当代散文作家的共同面相。这些作家立足于历史,选择了不同的朝向。显而易见的是,“历史”成为洞察当代散文的一种路径,尽管“历史”在各自的散文叙述当中扮演的成分、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依据“历史”的线索,可以发现当代散文的某种诗学共性,比如有关“乡村”主题的思考。
无论在南帆的《村庄笔记》还是在王尧的《时代与肖像》《民谣》中,“乡村”都由一种地理和文化概念演变为一种智性的关系概念。在南帆笔下的村庄俨然成为一种“零余者”,这种无法介入其中的多余感甚至影响到“何为乡村”的确切定义,即无法达到对乡村的清晰认知和体验。在《时代与肖像》以及《民谣》中,王尧对“乡村”进行了复杂的缠绕叙述,但他始终苦于在城市与乡村、现实与记忆的关系当中无法明确自身的位置。“从那里出来了,再说那里,其实很难。因此多年来我总是以复杂的心情对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曾经蔓延过的‘怀乡病’。人们由对现实的恐惧与回避,转而返身乡村,这当中有太多的无法对应的部分。乡村和乡村经验是复杂的。一个在当下无法安宁的人,复活他的乡村经验后是否就能悠然见南山,我是怀疑的。只有选择经验与记忆,我们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乡村经验与记忆并不单一。如果只是惦念乡村的单纯与温情,这样的怀乡对于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驾轻就熟,沿着这条道路返乡几乎太容易了。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33)王尧:《时代与肖像》,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86-187页。王尧执迷于故乡和人物的历史叙事,但这种叙事却又类似无所指涉的隐喻,从《时代与肖像》到《民谣》,这种矛盾始终困扰着王尧。直至《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王尧才摆脱了人物与历史关系造成的困扰,实现了由“乡土”到“人格”的历史叙事变革。“当我们今天回溯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和知识分子人格是融合在一起的,‘五四’催生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革新,而这个过程是由许多亲历‘五四’或受‘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完成的。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说到知识分子有没有经历八十年代一样,那一代知识分子是不是‘五四’之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后来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大学的面貌。”(34)王尧:《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86-87页。
南帆在历史概念中重新发现了近代历史、地域人文和边缘乡村的概念,王尧发现了“乡愁”掩盖下的复杂关系和真相,以及“历史”中的人格精神价值。而陈平原则表现出一种更为积极、务实的“历史”态度,他以一种极尽精微的态度和方式重温和剖析了“乡土”的内涵。他在《故乡潮州》中对“乡土”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与南帆和王尧的态度和方式不同,陈平原更倾向于将“乡土”当作一种可以建构和发现的场域,“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所谓‘四乡六里’,我的理解是看得见、走得到、摸得着、不太遥远的四面八方——包含地理、历史与人文”(35)陈平原:《故乡潮州》,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108页。。在这部书中,陈平原同样关注到了“历史”与“人物”的关系,如许地山、林语堂、丘逢甲、张竞生等。
“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人物”的发现,成为当代智性散文独特的风景。当代智性散文改变并深化了对于“人物”的理解,“人物”形象无形中构成并产生了某种“群像”效应。这些“人物”作为“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36)陈平原:《历史的侧面与折痕》,《潮州日报》,2019年1月10日第6版。,构成了“历史”的折痕。“历史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从来都是多头并进,故时常歧路亡羊。空中俯瞰,似乎一马平川;地面细察,原来沟壑纵横。诸多失败的或不太成功的选择,就好像历史的折痕,或深或浅地镌刻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折痕处,其实百转千回,你必须有耐心慢慢展开,仔细辨析,才能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些没能实现的理想、激情与想象力。”(37)陈平原:《历史的侧面与折痕》,《潮州日报》,2019年1月10日第6版。“人物”与“历史”的关系本身,在当代历史散文的具体表现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维持一种动态和张力,这种动态的关系如同“人物”与“原乡”的关系,彼此试图达到彻底的回归与内在的契合。“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不时回望故乡,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到底是真还是假,抑或真假参半、虚实相生?这种文化上的滋养与精神上的桥梁,是否有可能落实在若干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或文本?还有,那个若隐若现的‘故乡’,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所有这些,似乎都值得研究。”(38)陈平原:《故乡潮州》,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108页。然而,即便“人物”与“历史”的关系本身,在当代智性散文的具体表现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维持一种动态和张力。其中,带有某种反叛与独立个性的“人物”和“人格”显得尤为瞩目,这又将触及当代历史散文的另一重要命题——“人格”。
三、游侠与情种:南帆历史散文的人格模型
南帆在有关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论述当中,提出了“性情中人”的散文人格概念,“性情中人”连同“游侠”成为当代历史散文有关“人物”的标志性概念。“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小人物,重要的是‘性情中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从历史话语那里领取什么荣誉称号。”(39)南帆:《多维的关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18页。南帆历史散文试图重塑人格的意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相形之下,福州人似乎有些心虚。为什么他们享受不到这种美誉?肯定存在某种偏见”(40)南帆:《历史抛物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61、158、188、165页。。南帆历史散文建构起地域性散文写作的新图景,这种地域性书写图景以历史与人物的双重维度为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南帆历史散文所塑造出的系列人物群像往往兼具真实与想象、历史与现实、族群与个人的双重向度,从而生成兼具个体性和民族性的人物性格。
(一)有情与侠义:人格的双重隐喻
南帆历史散文的智性特征不是简单地借助历史的表述来实现,而是在人物的体验与历史的关系比拟和隐喻中生成,这种人物与历史的关系成为南帆历史散文最稳固的智性结构。传统散文单纯的人物或历史表述显然已经无法触及历史智性的真谛。在南帆历史散文中,作为个体性的人物身处时代与命运的双重困境,这种区别于传统散文纯粹的个人语境,使得人物陷入一种长久而普遍的“动荡不安”之中,南帆有关人物的想象叙述基本上都在营造这种“动荡不安”的气氛。他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夜黑如墨,江畔虫吟时断时续。待到同屋的两个人酣然入眠之后,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41)南帆:《历史抛物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61、158、188、165页。,这种个人的绝境并非单纯的个人原因使然,而是由于深陷历史的漩涡当中而无法抽身。“我突然明白,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对于林旭也是如此。他慨然把一条命押在了菜市口,仍然没有赢得历史。”(42)南帆:《历史抛物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61、158、188、165页。在历史的巨变当中,传统的个人情感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或是对于传统的一种个人怀旧。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正是情感与智性交融、更替所制造的体验危机当中。而南帆历史散文从人物主体性以及族群性的角度,试图寻找化解这种危机的诗学路径。南帆历史散文对于历史人物的刻画往往触及个体情感体验的前后巨大转折当中,继而触及由个体抒情传统向历史智性传统的转变。这种历史智性传统的发现显然不同于个人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觉醒,至少这种转型为中国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本土路径,且这一路径超越了个人抒情的范畴。
南帆历史散文所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中,林觉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我曾经说过,林觉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现在,我又有些怀疑。林觉民的性格之中保存了不少侠气。豪气干云,一诺千金;仰天悲歌,击鼓笑骂;一剑封喉,血溅五步——这是林觉民的形象。”(43)南帆:《历史抛物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61、158、188、165页。在众多的历史人物名单当中,林觉民的“侠义”形象近乎完美且角色特殊,南帆对于林觉民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构成了一种智性的人格隐喻,这一人格隐喻集中体现在林觉民身上“情种”和“游侠”兼具的双重人格中。《辛亥年的枪声》中,对于林觉民《与妻书》的文本解析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私人感情与民族大义交织在林觉民这一人物形象当中,最大强度地造成人物形象的内在张力。“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得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某种意义上,《与妻书》宣告“有情”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蜕变。“中国抒情传统里的主体,不论是言志或是缘情,都不能化约为绝对的个人、私密,或唯我的形式;从兴观群怨到情景交融,都预设了政教、伦理、审美,甚至形而上的复杂对话。”(44)王德威:《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8页。表面上,《与妻书》是在描述林觉民与陈意映的个人感情,实质上,是林觉民与自我“有情”形象的历史决裂,这种牺牲“有情”(个人私情)、成全“侠义”(民族大义)的理想追求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形象。
(二)血性与浪漫:人格的历史想象
以谭嗣同、林旭等人为代表的近代革命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人抒情怀旧的复杂情绪,曾以想象或漫游的方式呈现出来。“江汉夜滔滔,严城片月高。声随风咽鼓,泪杂酒沾袍。思妇劳人怨,长歌短剑豪。壮怀消不尽,马首向临洮。”(《莽苍苍斋诗·角声》)(45)(清)谭嗣同、林旭、杨锐等撰:《戊戌六君子遗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5页。同样,具有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人物群体涌现在近代中国,无论在文化的抽象场域还是在现实的政治社会境遇当中,都面临着一种自我主体性的思考与蜕变,以及“‘我’与‘群’之间的张力”(46)於璐:《鲁迅与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理想生成及悖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83页。。个人体验与现实政治体验并存,这种主体性的双重属性属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面向,即便如林纾这样带有守旧思想的知识分子,其内面的冲突以及精神彷徨的主体特征也同样明显,“综而言之,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斐洲烟水愁城录〉序》)(47)钱谷融主编:《林琴南书话》,吴俊标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76页。“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剑底鸳鸯〉序》)(48)钱谷融主编:《林琴南书话》,吴俊标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76页。。至于沈葆桢,南帆在《宫巷沈记》中如此解读:“我估计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多少像他这么热衷于辞别官场的官员。仅仅四十五岁那一年,他先后三度辞官归养;四年的两江总督曾经六上辞疏。这时的沈葆桢有些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喋喋不休地乞求放他回家。这是隐藏在功勋卓著背后一个闪烁不定的谜。……如果只有他敢于用如此执拗的形式走向朝廷表示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不是必须把这种软弱视为强硬的英雄气概?”(49)南帆:《历史抛物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03-204页。
南帆历史散文将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理解为个人抒情传统向历史智性的转变,这种理解对于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显然具有双重性的意义,一方面在文化形式上弥补了八闽之地缺乏“英雄”的历史缺憾,另一方面重新唤醒或者延续了中国自古以来具有的“侠义”气节。“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且举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50)(清)谭嗣同:《揭乡愿与大盗:仁学》,武汉:崇文书局,2019年,第92页。这种以族群性格作为人物个性来定义和塑造成为南帆智性散文的一大特征。通观他的历史题材散文创作,有关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塑造往往离不开“族群性”这一人物形象特征,正是借助人物形象的族群性,南帆历史散文才更有效地展开了有关主题的想象和叙述。某种意义上,南帆在《村庄笔记》当中为人格的想象与漫游找到了精神和文化的栖息之地,书中描述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亦象征着南帆对于“人格”的成功招魂,寄托了南帆对脚下这片乡土的热爱与憧憬。
四、历史智性:当代散文的叙事革命
对于当代散文而言,“历史”的可追忆性成为发现意义的有效手段,换言之,如若缺乏“历史”意识就意味着某种盲目性,历史感以及由此而生的迫切性是当代散文不约而同面临的共同体验。传统散文所默认的现象与叙述的一致性被质疑甚至被瓦解,而“历史”恰恰成为当代散文弥合这种差异的视角。在这种有关历史的想象和思考当中,“历史”被赋予了某种权威性意义,成为诠释人类社会、文化、情感、思想的智性方式。从诗学概念上讲,历史概念的范畴更宽更广,在历史散文的具体创作当中,它涵盖了乡土、族群、地理、政治、文化等概念,但在诗学属性上,这种涵盖关系又是一种同质性的关系,即历史等同于乡土、族群、地域等概念。正是由于“历史”概念范畴的宽广度,某种意义上,历史在本质上属于内涵庞杂的类文化概念。当代散文对于“历史”的审思恰恰显示出“历史”所蕴含的文学审美、审智的可信度和深刻性。
当代历史散文深化了有关“历史”的理解,“历史”不再只是一种“过往云烟”的情怀抒发,而是一种智性的思考和表达。“历史”由散文题材转变为一种智性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智性散文的叙述模式。当代历史散文回应了有关中国历史与现代性的命题思考,试图从“历史”的视角透视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性和合理性根源,这种有关历史文化传统的当代思考成为当代历史散文的一种自觉意识。“在我看来,关注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是众多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共有的特征。由于不同的历史情势、阶级地位与不同的知识结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观念分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民族向何处去是他们始终放在心上的重大问题。”(51)南帆:《文化的活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96页。通过历史的维度抵近有关民族性、思想性的审思对于当代历史散文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现象丰富了当代历史散文的文体表现力,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散文书写的自我革命,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诗学模式的生成,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将类似于哲学性质的“审思”带入当下的思考当中。正是这种对现有情状的不满足以及无依归感,催生出当代历史散文的诗学意义。这种以“史”为新、以“史”为鉴的智性逻辑进一步开拓了当代散文的诗学认知,突破了当代散文的文体认知范畴,开拓出新的散文诗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