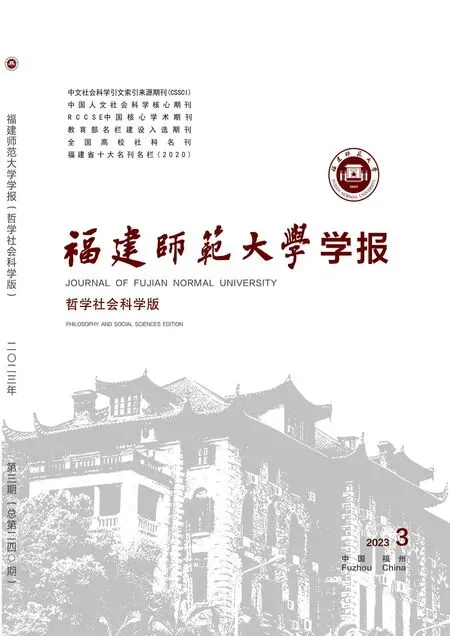加速主义思潮的历史叙事转向及其政治意蕴
雷 禹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自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终结之后,当代西方激进理论越发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言,在异常增殖的激进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千面马克思主义。(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12页。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以多种面貌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我们却无法在其中识别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实面目了。因为正是在理论多样化增长的过程中,擦除掉的是属于它们的交集与底色。作为当代激进前沿理论的加速主义思潮,更是以极大的挑衅性姿态介入了今天的社会理论,尤其是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左翼的理论及其诉求。然而,这种“介入”以极为颠覆性的历史叙事挑战了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要求,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视角。加速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与滥用,在实质上表征了当代左翼在寻求突围道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目的的强制性阐释,也深刻反映了左翼面临的复杂的现实困境。从历史叙事的视角揭示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地阐明其理论机制,才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2)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其著作《元史学:19世纪的欧洲历史想象》中对历史叙事、历史话语、叙事模式等内容作了阐释,尤为重要地指出了历史叙述与历史本身之间的复杂关联。借用怀特的表述,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一种试图去介入社会和历史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历史本身的叙述,而这恰恰可以反映其历史叙事的类型及其合法性,由此可以把握这种理论的深层次内涵。就历史叙事这一研究来看,彭刚从历史哲学领域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进行了探讨(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胡大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历史叙事的诸多模式(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转向及其政治意蕴》,《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蓝江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建构一种不同于抽象历史叙事的别样的记忆叙事(蓝江:《从记忆之场到仪式——现代装置之下文化记忆的可能性》,《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成伯清从社会学的角度拓展了社会学的叙事表征和再现空间(成伯清:《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以上研究为我们从历史叙事角度把握加速主义思潮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作为西方激进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加速主义思潮的产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在理论上的征兆。既有的研究在介绍、分析和批判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3)目前对于加速主义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从加速主义的路径方面,主要考察加速主义的加速策略(参见蓝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从加速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主要研究数字平台、数字技术与加速主义的联系(参见董金平:《加速主义与数字平台——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姜淑娟、关锋:《从数字悖论到加速转向——当代左翼加速主义批判进路及理论局限》,《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从加速主义与资本逻辑方面,主要探索资本增殖逻辑对加速的影响(参见杨慧民、张一波:《“加速”视域下的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从加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加速主义(参见雷禹、蓝江:《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当代价值》,《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马希、刘秦民:《生产“加速”:马克思与左翼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关涉》,《理论月刊》2019年第11期)。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从加速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为我们把握这一思潮的全貌提供了极富启示的借鉴。然而,作为一种理论风格独特且姿态激进的思潮,只有深入把握加速主义思潮本身的理论结构及其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准确地对其进行剖析和界定。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深层次上表现在历史叙事层面。如果不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去识别其理论的基本叙事结构,将很难切实厘清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结构及其理论内核。同时,面对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歪曲,如果不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加以回击,那么这种回击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切入,为我们理解加速主义理论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行且恰当的分析路径。
一、路径依赖:历史叙事变迁中的加速转向及其理论内涵
任何提出试图表述和再现历史的方式和视角,无疑在根本上就涉及历史叙事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如何对历史进行表述和再现,因为这一问题直接面临的是表述和再现的历史本身。可以说,全部的历史研究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影响到对历史把握的科学程度。对于当代西方的激进理论来说,历史叙事的问题亦是它们所主张的理论之依托。如果说历史叙事表征的是表述和再现历史本身的方式,那么这就决定了某一种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当代西方激进理论的纷繁复杂,在实质上反映的是表述它所面临的当代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方式不同。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表述和再现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不受到主体自身的影响,这就使得表述和再现过程本身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符合真实的客观历史本身,决定了历史叙事的科学性。马克思通过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解决了这一难题。然而,当代激进思潮因为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一难题,使得对历史本身的叙述和再现呈现出诸多缺陷。对于加速主义来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明显。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理论的历史来看,20世纪轰轰烈烈的“空间转向”一度作为新历史叙事方式试图改变和替代传统左派历史叙事的“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由此不仅促成了诸多新的激进批判理论并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进而打开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增长点和可能性空间。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来看,无论是试图“更新”或者“升级”历史唯物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有了诸多的阐释。就实质来看,“空间转向”试图逆转传统的时间(历史)偏好的叙事,从而走向空间(地理)叙事。然而这种空间转向的叙事直接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矛头,认为它要么是缺失了对具体空间问题的关注,要么是采取了以时间(历史)为主导的叙事结构。由此,新的理论在于揭示当前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存在着的空间转向,并以此逆转主流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偏好,从而占据历史叙事的主导。这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等理论家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叙事以加速逆转了空间叙事。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这种动向及其后果表现得尤为激烈。在加速理论家看来,今天的历史叙事不再是单纯依赖时间或空间,而是加速,即时空条件一体化之下的社会历史发展之维。那么为何加速会取代空间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问题呢?在加速理论家的代表之一、德国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as)看来,“在现代,没有与加速类似的、独立的空间变化的特征;时空结构的变革首先通过它们的时间的变化动力所驱动的”(4)[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页。。在罗萨看来,没有静态的、独立的空间变化,相反,空间是在时间中不断发生变革的。由此,罗萨基于社会学的维度将他的研究推进到对现代性的根本界定之上,即“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5)[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页。。在这一点上,罗萨指出加速是速度结构变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现代社会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基于自身的社会学研究,罗萨对加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分析,并一度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本体论地位。
尽管罗萨从社会学领域入手对现代社会的加速进行了考察,那么在马克思那里是否有专门论述加速以及为何又成为后来的理论家们关注的中心?对于这一问题,罗萨指出加速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次要的和未经充分发展的,因而是一个缺失,但是马克思在对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表明现代化进程表现为加速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罗萨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实质上提供了解释三种加速形式的出发基点,即“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6)[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页。。而这三种加速形式恰恰又构成了后来罗萨重点分析当代社会加速的三个方面。
早在罗萨之前就已经有理论家专门对加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了,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另译维利里奥)是绕不过去的代表。罗萨不仅将维希留的“速度学”(竞速学)奉为这个领域最为卓越的开端,而且指出对于维希留而言,“不仅现代性,而且全部的世界历史都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加速的历史,速度似乎应该是历史的主体”(7)[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页。。在维希留看来,“从来就没有‘工业革命’,有的只是‘竞速政治的革命’,从来就没有‘民主政体’,有的只是‘竞速政体’,从来就没有‘战略’,有的只是‘竞速学’”(8)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Trans.Marc Polizzotti,New York:Semiotext (e),1986,p.14.。维希留指出,速度就是这个世界的绝对命令,也是历史的火车头。现代性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加速的过程。维希留通过加速详细地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变迁机制和社会状况以及人类的处境变化。在维希留那里,时间和空间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或孤立的,而是以加速的形式存在着的。这种加速的形式,时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环境本身,也不断改变着人类自身的处境。维希留特别通过对运输交通、通信、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考察了人类的变化状况,揭示了现代技术快速变迁之下人类自身的存在境况。
可以说,维希留和罗萨等人的讨论,将加速置于现代性的核心位置,并一度有使其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体论的意味,同时也进一步为后来的加速主义的出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前提。如果说维希留和罗萨重点在于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变迁现象及其过程,那么加速主义则试图提供一种改变现状的加速策略。加速主义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开始流行起来,而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理论家尼克·兰德(Nick Land)那里就已经初见端倪。加速主义认为以技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不断加速的过程中,正如兰德对人工智能的探讨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艾利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对大数据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分析。加速主义将马克思奉为最典型的加速主义理论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加速主义化。然而,加速主义重点不在于对社会的加速性质进行详细的描述,而在于为如何走出这种加速的局面提供更为重要的指南。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兰德的右翼加速主义和以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一度使加速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持续活跃在激进理论前沿位置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流行,又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理论。
对加速历史叙事变迁的简要阐述有助于理解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激进理论的叙事转向,这为后面探讨加速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考察方向。加速成为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还是对其科学性来说都是如此。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时候,在对于加速的问题上,既不是像理论家们所称的那样,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一个缺失因而需要补充以加以完善,亦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加速化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升级,而是始终聚焦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及其条件,从而解决我们的任务。
可以说,加速转向,无论是罗萨从社会学角度对加速进行全面总结并从技术、社会和生活方面阐述加速的具体变迁,还是维希留从技术角度阐释加速状况之下人的境况的“速度政治学”,抑或是加速主义理论家对超越资本主义作出的加速主义策略,不仅在现代性批判维度方面打开了极为广阔的理论视野,而且对于当代激进理论批判的历史认识论提供了多种有启发性的思考。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基于历史叙事的更新与改变,加速转向成为新的激进理论的历史叙事基础。加速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是把握加速问题的内涵,还是将马克思主义加速化,都试图在当代加速研究上占据新的生长点。因此,要真正理解加速问题的实质,不仅要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加以阐释,而且也要把握其对应的政治规划。
就这一方面而言,暂且不论加速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只需要认真审视一下加速理论家内部历史叙事的差异就可以看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不同,尽管他们都将加速视为社会发展明显事实而作为理论出发的前提。维希留尽管提出了速度政治学,但基于对运输、通信、军事等技术的加速带来的恐惧、意外围绕着人们的生存这一事实,由此对现代性抱有极大的悲观情绪;罗萨详尽阐述了技术、社会和生活的加速带来的异化状态,以主体的关系概念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主体间性理论,又试图以此扬弃这种加速的异化状态,从而走向了基于主体关系的“共鸣”(9)Hartmut Rosa,Resonaz:Eine Soziologie der Weltziehung,Berlin:Suherkamp,2016,p.305.策略;而加速主义理论家不仅看到了前两者对社会现实加速的思考,重点更在于阐发一种以主体之维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规划和策略,由此走向后资本主义社会。
可以看到,加速主义思潮就处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加速转向的变迁之中,不同的加速理论处于竞争之中。这种竞争在实质上是历史叙事的差异,不同的历史叙事决定了对于未来的政治规划的差别,这就是历史叙事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历史叙事的变化实质上是对现实变迁的反映。加速转向的变迁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即资本为了实现增殖的目的,不断推动着交换、流通的加速,进而推动社会的加速。对于加速主义思潮而言,这一思潮本身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反映了历史叙事问题的重要性,这不仅对于识别它的内在特征的多样性和摇摆性,而且为恰当地对它的理论效应进行评估,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焦点问题:加速主义的历史叙事结构及其内在实质
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试图去再现历史,我们就能识别出其是何种历史叙事,尽管一些理论并没有明显地表明自己的元理论。对于激进理论来说,问题亦是如此。当前加速主义思潮以其惊世骇俗的理论和口号震撼人们内心之时,它的历史叙事的基本结构往往被外表华丽的辞藻所掩盖,而且其理论的科学性是值得进一步去评估的。因此,只有真正剥离出惊艳口号背后的历史叙事结构,才能真正揭示其元理论之所在,最终才能理解其让人震惊的政治规划。加速主义的历史叙事结构可以从客体向度或主体向度、实体本质或非理性主义、历史规律或意志主义三个维度进行展开。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将很好地解剖加速主义思潮令人眼花缭乱的激进理论。
(一)从客体路线到主体路线:以技术为中轴的主体之维
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的那样:“正如传统的辩证法所教导我们的,历史化操作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线路运行,而最终只能殊途同归:即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1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在詹姆逊看来,试图去表述和再现历史的历史叙事有两种路线:主体路线和客体路线。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和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cs)的主体性哲学分别代表了客体路线和主体路线。在关于主体路线和客体路线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中还有不同的导向,即主客体一致性和主客体异质性路线。如果说卢卡奇从主体路线入手,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物化的经济结构从而为阶级意识提供客观上的论证,那么这可以说是一种主客体一致性的路线。对于加速主义来说,它亦走的是主体路线,即试图以主体的强纲领叙事来为左翼的行动提供支撑。对于左翼加速主义来说,他们试图加速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就是使其加速进入到当前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即达到后资本主义阶段;对于右翼加速主义来说,他们也主张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非达到一个与当前资本主义不一样的后资本主义阶段,相反则是使资本主义本身发展到一个摆脱当前困境的更高级的阶段。
加速主义的这种主体路线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以技术为中轴和核心从而发挥了主体路线的要求。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将问题的焦点锁定在技术的维度之上,都将未来社会的希望赌在技术的命运之上。毫无疑问,加速主义极为重要地注意到技术在今天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似乎技术领域的每一项重大变革都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技术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地位异常重要,特别是譬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越来越直接主导着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将技术作为中心议题,无疑凸显了其理论的导向,这是有较大积极意义的。然而,加速主义对技术的过度关注以及看待技术的方式亦带来了重要的问题,即具有高度的技术决定论嫌疑。
无论加速与技术之间有何关联,这都表明了加速主义者希望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恰恰是这种要求隐含了其中的本质,那就是表征了从主体路线出发的叙事中的主客体异质性路线,即主体与客体在实质上是不相通的。这种不相通就体现在,基于主体路线的主张是没有客观条件做支撑和保障的。换言之,加速主义的主体叙事由于没有从社会历史的客观状况中真正找到能够提供主体叙事的依据,从而使得主体叙事的合法性和逻辑性大打折扣,进而对于其未来的行动策略和革命要求产生了论证上的困难。加速主义之父兰德在其文章《卡巴拉101》(Qabbala101)中表达了他的核心观点:“由于卡巴拉主义是一个实际的纲领,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教条,它的形式错误——误解——仅仅是计算上的不规范,而纠正这些错误实际上是它继续发展的程序要求(而不是反对)。对卡巴拉主义事业的理性否定被迫采取形而上学的立场:以所谓的原则为由排除事实上不过是指导性的‘经验 ’假设。”(11)Nick Land,Fanged Noumena:Collected Writings,1987-2007,eds.Ray Brassier and Robin Mackay,Falmouth:Urbanomic,2012,p.591.在兰德看来,卡巴拉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基于自身内部的运行机制而与外界无涉的行动纲领,它的错误可以进行自我修正。从这一要求便可以理解加速主义的实质了,那就是排斥外部客观世界的经验,而完全依赖自身的要求。这便是历史叙事中主客体异质性路线的表达。迈克尔·E.加德纳(Michael E.Gardiner)在其《加速主义批判》中对加速主义倡导的理性有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理性是不断自我扩展和自我修正的,它没有必要的目标或终点,并拒绝承认对其扩大或适用范围的任何限制”(12)Michael E.Gardiner,“Critique of Accelerationism,” Theory,Culture &Society,Vol.34,No.1,2017,p.8.。理性是自我扩展和自我修正的,而不受任何适用范围的限制,这与兰德的主张是一致的。
从实质上说,加速主义的主体路线隐含了看似客观的技术路径,从而使得其诉求具有了某些现实根据。然而,这种主体路线却把作为技术支撑的现实根据发挥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当主体的要求不是基于对客体的论证,而是从自身出发时,那么它不仅解除了客体的束缚,而且还会凌驾在它之上。因此,对于加速主义来说,重点不在于去理解客观世界本身,而在于如何使我们自己的主张更具有逻辑自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加速主义的理论依据就会是基于自身的要求或者出于经验式的实用取向了。这一点恰恰可以从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著作《创造未来》(13)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London:Verso,2015.的标题看得异常清楚。创造或者发明未来极大地体现了主体性的要求。对于马克思来说,无论单方面从主体路线或客体路线都是有失偏颇的。马克思主客体辩证法叙事的内在要求在于,以客体路线为前提的主体叙事,或者说以主体为目标的客体叙事。在马克思那里,主体路线和客体路线是统一在历史辩证法之中的,仅仅立足于一方或者割裂二者都是不科学的。
(二)从实体本质到非理性主义:作为“超信”的加速主义
如前所述,当加速主义的历史叙事不再从客体路线而是从主体路线出发的时候,那么关注的重心显然就不再是根本上决定主体行动的客观社会历史状况了,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加速主义者不仅指出了当前左翼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干预策略之困境,也认识到技术的快速进步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影响,然而却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根本性质和矛盾的诊断。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主义的历史叙事结构就是以非理性主义叙事为中心,替代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实体本质的探究,从而充分发挥了其主体路线。
加速主义的主体路线以技术为支撑,然而这种支撑在表面上以客观的技术为依据,却在本质上裹挟和潜藏了主体的意志。加速主义之非理性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方面,这种非理性主义最为明显的表达体现在他们对于“超信”(hyperstition)的建构和论述之上。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对这一概念给出了一个最为明确的定义,即“实体‘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超信过程正是一个通道,一个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潜能——已经活跃的虚拟——实现了自己”(14)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CCRU Writings:1997-2003,Urbanomic:Falmouth,2017,pp.25-26.。根据兰德的观点,重点不在于实体本身是什么,而在于它在超信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自己。简言之,超信是一个通道或转变,实体的潜能能够实现,尽管还不是现实。换言之,超信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虚构,将现实视为一种可以操作的虚构的场所,从而表达了虚构的或者人为的想法可以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实际的影响和效果。这就为加速主义在政治上的行动或策略提供了充分的论证支撑。
另一方面,加速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表现在其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即对真理的贬低。加速主义将“超信”奉为准则,那么带来的后果则是必定对客观世界真理的漠视和忽视,对理性的指责。换句话说,“超信”的规则就在于它服务于自身,而不受外在的真理或规定所约束。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体现在它是以主体的意志为依据,亦以经验的要求为导向。加速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类似于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不可通约性的世界观之间强调意志自由选择的“怎么都行”的取向。费耶阿本德指出:“人类的生活被许多意识形态所指引,真理只是其中之一,自由和精神独立是另外一些。如果真理像一些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和自由是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选择,我们可以放弃自由,但我们也可以放弃真理。”(15)[美]保罗·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和相对主义》,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正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的那样,当我们不再将真理作为我们的追求,那剩下的就是基于个人意志的选择了。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主义以“超信”为核心的非理性主义就可以理解了,它不再探寻客观世界的真理,而试图去创造。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著作《创造未来》这一标题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这一点。
这就意味着,问题不在于现实是怎么样,而在于我们所走向的未来如何以及让人们相信我们所走向的未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无论是左翼加速主义意图走向后资本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目的,都是采取加速的策略,他们二者都将未来的社会作为各自的出发点和中心。西蒙·奥沙利文(Simon O’Sullivan)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加速主义超信概念的内涵。他指出:“超信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它通过时间旅行的反馈循环使自己成为现实:它作为一种被抛回到过去的未来愿景来设计自己的历史。”(16)Simon O’Sullivan,“Acceleration,Hyperstition and Myth-Science,” Cyclops Journal,No.2,2017,p.14.
加速主义所主张的超信概念逆转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未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来主导和影响当下的现状。这就是加速主义的基本策略。它主张关键不在于真理是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创造它。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中以一种极富激情的口吻阐发了加速主义的基本框架,并指出“加速主义推进的是更为现代的未来——是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无法创造出来的另一种现代性”(17)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362.。
加速主义所面临的,一方面是当前左翼无法提供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另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加速主义必须对未来采取一种强有力的构想,才足以引导左翼跟随他们的主张和策略。然而,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加速主义以非理性主义叙事代替了对社会现实内在本质的探索。因为它一方面将社会历史锁定在以超信为形式的非理性主义之中,从而将社会历史之客观性予以悬置,另一方面又将技术这一看似客观的状况发挥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层面,由此而裹挟了主体的想象。如果说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客观运动规律,而这恰恰是历史作为实体的本质,那么加速主义则放弃了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解剖,转而强调了主体对未来的干预措施。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面临左翼的失败困境和新自由主义仍旧强大的局面,寻找一种既无可奈何又迫不得已的另辟蹊径的突围道路。
(三)从历史规律到意志主义:加速主义的动力机制
既然历史叙事是对历史的表述和再现,那么它必然涉及如何呈现历史的动力问题,因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说是历史叙事的核心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并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解决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那么其后的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么从经济决定论的客体路线过度发挥了这一动力机制,要么尝试以主体路线将之拯救出来,都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后来复杂的思想史可以表明,历史规律却被多方面所攻击。例如,出现了诸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这样直接否认历史规律性的代表。(18)[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辑、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其后历史叙事的问题为结构主义所改写,例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主张历史的客观性在于结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强调历史是多种因素的过度决定过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历史是断裂的、非连续性过程。
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人本主义的批判打开了结构主义的新视野,那么这种新视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揪出了历史发展中主体这一条意识的小虫从而保障了历史的客观性,而且将历史呈现为一种不受时间因素影响的结构,由此为进入历史的内部大大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成为人们可以任意拆解的模板,可以随意书写的纸张。那么对于加速主义来说,历史便不再具有客观性,历史规律也不复存在了。加速主义所主张的超信正是其历史叙事的写照,即它逆转了时间的顺序,历史成为加速主义者手中可随意更改历史的笔。加速主义的历史叙事主张的历史是一种可以跳跃的历史,是可以从当下跳跃到未来的历史。奥沙利文所指出的“时间旅行的反馈循环”正好代表了加速主义的操作机制。正如加速主义的批评者本雅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注意到兰德的预测是超信的——一种述行的虚构,创造了它预测的未来——他的理论化(根据兰德的说法)扰乱了线性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19)Benjamin Noys,Malign Velocities:Accelerationism and Capitalism,Alresford:Zero Books,2014,pp.46-47.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加速主义历史叙事的实质:历史变成了可以由主体意志任意改变和推动的可逆的、直线的循环运动。历史由此成为加速主义服务于自身需要的战场,同时以时间性和必然性为代表的历史之客观性将无法得到保障,终究沦为主体意志竞相争夺的工具。无论是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他们都试图去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这种加速是以可能的未来来参照当下。在这一点上,不去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而以主体的意志主导历史发展的进程,加速主义难免走向意志主义的倾向。
这种主体的意志主义特别表现在加速主义理论家对理性的过分高扬之上。雷扎·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指出:“理性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提升自己。而理性的自我实现与非人的真理不谋而合。在这里,理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僵化或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理解为一个不断演变的空间,它通过同时保留无知和减轻无知的可修改规则来重组自己。”(20)Reza Negarestani,“The Labor of the Inhuman,”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437.同时,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也提出:“普罗米修斯主义承诺克服理性和想象力之间的对立:理性是由想象力推动的,但它也可以重塑想象力的极限。”(21)Ray Brassier,“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487.加速主义所主张的理性不在于去探求客观真理,而是以自身为目的,并由想象力所推动。加德纳在批评加速主义时指出:“在这一加速的狂奔中,我们断绝了对人类过去的任何和所有形象的‘承诺’,而当我们这样做时,未来就会蜂拥而至;我们被拉向一个总是新颖的地平线,不断扩散的项目可能很难从今天的角度看出来(甚至可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22)Michael E.Gardiner,“Critique of Accelerationism,” Theory,Culture &Society,Vol.34,No.1,2017,p.8.由此可以表明,加速主义尽管看到了当前资本主义中由技术发展呈现出来的加速现象,但缺失了对资本主义历史规律的内在把握,从而以加速主义的历史叙事失却了对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考察,而走向了主体的意志主义误区。
三、政治意蕴:加速主义历史叙事的政治意蕴及其困境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揭示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结构,不仅能够使我们彻底理解这一异常激进的理论本身,也可以穿越重重迷雾理解其政治主张。这两方面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加速主义历史叙事为政治策略提供了元理论基础,提供了认识论上的论证,而政治策略则是其历史叙事的必然后果。
联系20世纪左翼的历史便能清晰地看到加速主义政治策略的调整和转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不仅使得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逻辑上走向了终结,而且在实践上亦无力组织其有效的力量来颠覆资本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在这种局面之下,新左派的崛起,意味着“第三条道路”成为可能,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通过广泛的新社会运动不断争取平等和正义。与之伴随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出台,预示着资本主义仍旧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尤其是苏东在20世纪90年代的垮台,表明在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衰弱,而似乎历史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已经终结了。
可以说,加速主义政治上的歧义性与这种局面有着极大的关联。对于右翼加速主义来说,它正是看到了福山所说的这一点,新自由主义已经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同时技术的高速发展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可能,只不过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它被束缚了。于是,右翼加速主义主张必须进一步释放技术的潜力,这样会有助于资本主义走向更高的阶段,而唯一的通道便是资本主义本身。对于左翼加速主义来说,它一方面看到左翼无法有效组织其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冷战结束后,爆发了新的社会运动,2008年之后的岁月里重新经历了运动的复兴,但这些运动同样无法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视野”(23)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p.350-351.;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左翼无法正面组织有效力量已成事实,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摧毁新自由主义,那么可行的路径就是加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让它早日达到其临界点,同时左翼准备好掌握技术、意识形态、平台等的领导权,为达到后资本主义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正如学者蓝江教授指出了加速主义策略的实质——“与资产阶级争夺技术加速的主导权,让物质性的生产力加速运动,最终在未来突破资本主义的界限”(24)蓝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2页。。当然,从本质上来说,加速主义者亦看到了在资本增殖要求的裹挟和推动下,资本、技术、社会等都以加速的姿态发展,加速主义者的策略正好在理论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社会状况。
可以说,加速主义总体来说不仅是在缺乏改变现状的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而且还是在新自由主义仍然处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应激策略。这种应激策略既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被迫选择,也是寻求迂回路径的无奈之举。然而,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暧昧使得它无法撇清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由此而导致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模糊不清而又歧义丛生的艰难困境。
第一,加速主义历史叙事无力探究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而代之以主体的意志驾驭历史本身。当加速主义不能真正面向社会历史的时候,那就只能愉快地转而背向历史。在政治层面的表达则是,当不能从当前的社会历史内部探究我们未来行动的准则和依据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行动标准则落到了主体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以加速为策略的主张便会随着主体自身的要求而作出改变了。对于右翼加速主义来说,加速的策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对于左翼加速主义来说,试图超越的路径只能是通过资本主义,即“即超越资本主义限制,超越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寻求一种新的未来社会”(25)孟献丽:《社会加速理论视域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世界哲学》2022年第2期,第38页。。当历史叙事所作的任务没有真正探究资本主义的内在运动规律从而为加速主义的策略提供真正客观的标准和依据的时候,那么其干预策略将会丧失客观真理的保障而走向实用主义的泥淖之中。
第二,加速主义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现象,然而忽视了社会历史加速的条件性。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将马克思奉为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26)这一点在罗宾·麦凯(Robin Mackay)和阿尔曼·阿瓦尼西安(Armen Avanessian)编辑的《加速:加速主义读本》(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中可以得到集中体现。在其中,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被作为“机器论片段”而放在本书的首篇位置。关于“机器论片段”与加速主义的关联,可参看雷禹、蓝江:《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当代价值》,《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第15-18页。左翼加速主义者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指出“马克思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因为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体制”(27)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353.。右翼加速主义者兰德在回应《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时引用了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提出的表述,即“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5页。参看:Nick Land,“A Quick-and-Dirty Introduction to Accelerationism,” Jacobite Mag.,May 25,2017,http:∥jacobitemag.com/2017/05/25/a-quick-and-dirty-introduction-to-accelerationism/,January 1,2022.,从而为其论证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策略的合法性作辩护。而我们想要表明的是,加速主义理论家看到了马克思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赞扬还是对其加速的描述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即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客观考察。然而,加速主义理论家不仅忽视了马克思还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误解了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论述。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充分的阐释。易言之,即使试图强调社会加速,那么这种加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状况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470-471页。加速主义忽视了社会历史加速的条件性,对于其政治实践来说有着重大的缺陷。
第三,加速主义的加速策略是在既有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霸权斗争,对于追求未来的解放是一种乌托邦幻想。首先,加速主义主张颠覆资本主义的策略不可取,于是就试图加快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缩短阵痛的时间。面对左翼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反抗策略都无法改变局面的情况,加速主义走向了相反的一面,即主张资本主义加速进入到自己的临界点。这样一种策略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与资本主义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谋。其次,加速主义试图掌握技术上的领导权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成功接管。然而,这无疑亦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因为资本主义绝不会允许左翼和平地夺取它的生产资料,这已经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史无数的事实得到证明。最后,加速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它的斗争更多只是一种为争夺话语权的霸权斗争。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加速主义在历史叙事上的严重缺陷导致了它不可能有革命的实践。因此,它的理论斗争更多只是围绕话语权的霸权之争,这不仅表现在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之间的直接对立,还体现在加速主义的话语为诸多其他的意识形态所绑架从而走向了多个极端立场。(30)在《创造未来》一书中,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指出他们现在避免使用“加速主义”一词,因为“围绕这个概念出现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解”,但仍旧坚持他们信奉的原则(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New York:Verso,2015,p.189)。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聚焦加速主义思潮的历史叙事,就是要阐明加速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因为也正是在历史叙事的维度上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穿过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惊世骇俗之语。通过历史叙事,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其根本矛盾之处,也才能识别出其内在症结。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也必须在历史叙事的层次上捍卫马克思主义。这种捍卫,不仅是为了与诸多错误的理论思潮作正面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所做的那样,而且也是始终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从而不受污染,更是为了不断加强诊断社会现实的能力。对于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前沿思潮层出不穷且形式多样的新奇话语,我们需要理智地拂去理论表面的绚丽多姿从而达及理论内核深处。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分析和解剖当代加速主义思潮,不仅要对其新颖的话语产生高度的警觉,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应对各种激进思潮的方法论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