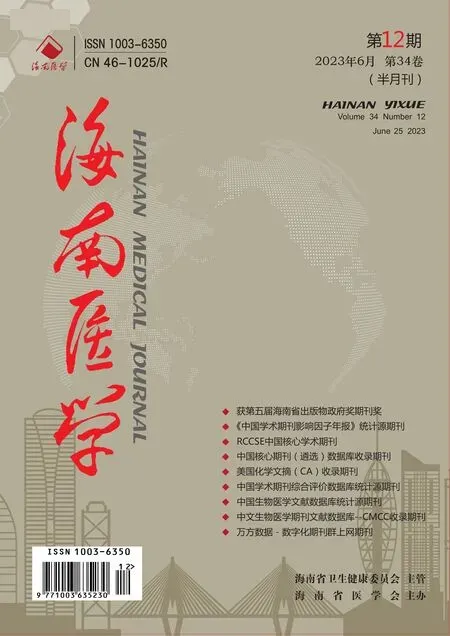血管生成抑制剂治疗脑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进展
张俊杰 综述 段虎斌 审校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山西 太原 030001
胶质瘤起源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约占所有脑肿瘤的27%和原发性恶性脑肿瘤的80%。根据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标准,胶质母细胞瘤(IDH 野生型)是所有神经系统肿瘤疾病中最致命的疾病之一[1],其特征包括巨噬细胞主导的免疫抑制、特殊肿瘤微环境、突出的侵袭与血管生成能力。近年来肿瘤切除技术、放射治疗和化疗策略方面均取得突出进展,但遗憾的是目前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患者的总体预后仍不理想,总体中位生存期约为16个月[2],如何更有效地抑制GBM 进展始终是颅脑肿瘤治疗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
诱导血管生成是肿瘤经典的标志[3]。在过去几年中,中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生物学效应、靶向血管生成的治疗方法已经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应用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贝伐单抗(Bevacizumab)是一种用于中和人类VEGF 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2017 年全面批准贝伐单抗治疗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贝伐单抗是第一个针对GBM 患者的治疗药物,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可长期维持GBM 患者的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贝伐单抗治疗GBM 的首次临床试验是2009 年的“AVF3708g/BRAIN”和“NCI 06-C-0064E”二期试验。在试验中,贝伐单抗单药或联合伊立替康治疗GBM的客观有效率为28%~40%,6个月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40%~50%,与较高的历史对照组相比改善显著,但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无改善(为38%~40%)。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患者的PFS 益处并没有转化为实际OS 益处。最新的临床实验报告发现,贝伐单抗应用于进行性GBM 时患者的总存活率未得到改善,但流行病学数据表明GBM 患者中位生存期增加[4-5]。此外,颅脑肿瘤的进展往往伴随着中枢神经系统进一步受到侵犯和破坏,必然带来神经系统功能的恶化,因此延长患者PFS 的治疗对其神经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和生活质量仍有重要意义。本文就贝伐单抗的抗肿瘤机制、治疗GBM的进展与困境等进行综述,旨在为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1 贝伐单抗能显著抑制胶质母细胞瘤血管生成
GBM具有强大的血管生成能力,这与VE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过度表达有关。VEGF是内皮细胞生长的有效刺激因子,对血管生理性和病理性生长具有重要调控作用。VEGF与受体结合后可激活血管内皮细胞,使内皮细胞基底膜和细胞外基质发生降解并被重塑,内皮细胞发生迁移和增殖进而形成特殊的内皮管状结构。最后,在新形成的内皮管及其壁细胞(周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周围形成成熟的血管基底膜,从而形成稳定的新血管。
贝伐单抗能够结合VEGF 并中和其生物学效应,可明显降低GBM 血管增殖水平,诱导血管正常化,并减少肿瘤沿新生血管侵袭与迁移。贝伐单抗还可减少GBM 患者后续治疗中对类固醇类药物的依赖。类固醇用于治疗GBM 患者的脑水肿,但具有多种潜在的副作用。在“EORTC 26101”试验中使用贝伐单抗治疗的患者完全停止使用类固醇的比例为23%,高于对照组的12%[6-7]。这可能是由于贝伐单抗促进血管内皮修复,降低血管通透性,因而减少了血管源性脑水肿的发生。
2 贝伐单抗在治疗胶质母细胞瘤中的耐药性机制
大多数GBM患者在接受贝伐单抗治疗的初期可以获得治疗益处,但后期总会出现病情的进展或复发,这与GBM 对抗血管生成治疗产生耐药性相关。因此,了解GBM 对血管生成抑制剂产生耐药的潜在机制十分必要。
2.1 胶质母细胞瘤的免疫肿瘤微环境 抗血管生成治疗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切断营养供应来饿死肿瘤[8]。然而,血管破坏后的严重缺氧和营养限制具有促肿瘤作用。低剂量的抗血管生成治疗可能会阻断肿瘤血管并出现短暂的血管正常化,并带来即时的抗肿瘤益处。而相对高剂量时则会增加肿瘤微环境中的缺氧和酸中毒,增强肿瘤细胞自噬并减少抗肿瘤药物的传递[9]。缺氧还会进一步助长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介导的功能失调的血管生成,并通过诱导生成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MMP,包括MMP-2 及MMP-9)[10]和相关促侵袭性旁分泌因子从而驱动肿瘤细胞的侵袭[11]。功能失调的血管生成还可促进GBM 细胞的干细胞样表型。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glioblastoma stem cells,GSC)能释放大量VEGF 和其他促血管生成因子[12],促进肿瘤血管化的同时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的增殖和功能,进一步加强免疫抑制微环境[13-14]。
2.2 旁路途径代偿性激活与血管共选择 研究发现VEGF-A 通路被有效抑制后GBM 可经多种方式重新激活血管生成,主要包括:(1)上调VEGF-A 或VEGF家族的替代成员(例如VEGF-C);(2)代偿性激活替代促血管生成途径如胎盘生长因子途径、趋化因子受体途径、肿瘤生长因子途径[15]、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途径[16],上述旁路途经的激活还会使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更加恶劣。血管共选择是指肿瘤细胞直接侵犯并利用预先存在的非恶性组织的血管系统,固属于非血管生成过程,目前已在多种肿瘤中观察到这一过程。通过这种方式,肿瘤可以利用已存在的血管来满足它们的新陈代谢需求,进而对抗血管生成治疗产生抗性[17-19]。此外,GBM细胞还可以通过细胞模拟血管生成、肿瘤干细胞分化产生的血管生成、将一条血管分裂成多条血管(血管套叠)等方式实现肿瘤高度血管化[20]。
2.3 贝伐单抗复杂的作用机制 传统观点认为,贝伐单抗对癌细胞并非具有直接的细胞毒性,而是靶向肿瘤微环境,依靠癌细胞、正常细胞和细胞外基质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来诱导细胞抑制。因此,贝伐单抗对GBM 肿瘤类型和微环境表现为特异性,对于GBM某些特定亚群的治疗可能无明显益处[21]。
3 克服血管生成抑制剂耐药性的探索
如何克服血管生成抑制剂的耐药性一直是GBM抗血管生成治疗的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关于GBM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方法取得很多进展。
3.1 开发新型血管生成抑制剂 研究显示,贝伐单抗作为单一疗法未能提高GBM 患者生存率,需要与化疗等联合[20]。针对GBM 对单纯血管生成抑制的补偿能力,使用不同的血管抑制疗法组合可能效果更好。因此,研发新型血管生成抑制剂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多种新型抗血管生成药物也处于临床开发的不同阶段。阿柏西普(Aflibercept,也称为VEGF-trap),是一种重组融合蛋白,可与循环中的VEGF-A 和VEGF-B 以及胎盘生长因子结合,并抑制其与VEGF受体和下游信号的结合[22]。应用于复发性恶性胶质母细胞瘤的Ⅱ期试验显示PFS6 改善率为7.7%。但该项试验由于严重的毒性反应导致了较高的退出率[23]。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是针对一个或多个酪氨酸激酶受体的小分子,可通过抑制细胞信号转导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增殖,促进细胞凋亡。此外,舒尼替尼、索拉非尼、帕唑帕尼等TKIs还以VEGFR 为靶点,可以作为肿瘤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新方法。然而此类药物如舒尼替尼、索拉非尼、帕唑帕尼等用于治疗GBM的研究却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24-26]。苏拉单抗(Suramab)是两种抗血管生成药物苏拉明(Suramin)和贝伐单抗(Bevacizumab)的组合。苏拉明和贝伐单抗在联合使用时显示出高度的协同效应,比单剂量贝伐单抗或苏拉明产生的作用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研究表明,在小鼠结直肠癌中苏拉单抗可显著降低肿瘤生长,在兔角膜血管生成模型中苏拉单抗可显著降低新生血管生成[27]。因此苏拉单抗可作为抑制GBM 生长和侵袭的潜在治疗药物,但尚未有相关的试验研究[28]。西伦吉肽(Cilengitide)是整合素αvβ3和αvβ5的拮抗剂,可增加血管稳定性。一项与新诊断GBM 的标准治疗相结合的研究显示其并不能改善GBM 患者PFS 或OS[29]。曲巴尼(Trebananib,又称AMG386)是一种与Fc 免疫球蛋白融合的肽,可抑制血管生成素(angiogenin,ANG)配体与其受体相互作用。与贝伐单抗联合治疗复发性GBM患者的Ⅱ期研究显示对预后无改善[30]。甲氟喹是用于防治疟疾的药物,有研究发现它能抑制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等多种肿瘤细胞生长并诱导其死亡。有研究表明甲氟喹能以溶酶体破坏依赖性方式抑制胶质母细胞瘤微血管内皮细胞(glioblastoma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GMEC)分化和毛细血管网络的形成,从而抑制胶质母细胞瘤的血管生成[31]。甲氟喹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已经开展并初步取得预期的成果[32]。
3.2 联合治疗
3.2.1 联合免疫疗法 最新的研究发现,VEGF在GBM 肿瘤微环境中具有额外的血管生成非依赖性作用,包括:(1)激活VEGFR-1信号传导促进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2)激活VEGF-A/neuropilin-1 通路及VEGFR-2/STAT3 信号传导促进干细胞形成;(3)与多种免疫细胞中的VEGFR作用促进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33-36]。其中关于VEGF 诱导免疫抑制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发现VEGF信号通过引起异常造血、影响树突状细胞和T细胞的成熟和功能、抑制活化T细胞的运输和存活等方式引起免疫抑制。贝伐单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组合最近已被批准用于非小细胞肺癌,并且在治疗肝细胞癌方面也显示出临床益处,是治疗GBM的一种可行的新方案。
3.2.2 联合多种血管生成抑制剂 血管生成素-2 (angiogenin-2,ANG-2)是肿瘤血管生成的另一个参与者。ANG-1 是一种稳定血管的分子。ANG-2可拮抗ANG-1 的作用从而增加血管不稳定性[37]。有关于GBM的临床研究表明,当肿瘤对抗VEGF产生耐药性时,ANG-2水平升高。小鼠GBM模型显示,与单独抑制VEGF相比,双重抑制VEGF 和ANG-2 可使血管系统正常化并减少肿瘤生长[38-39]。有报道称标准治疗(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结合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治疗可改善GBM 患者的临床预后,但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试验来验证这些观察结果[40]。Perryman 等[41]将血管紧张素Ⅱ受体2 型(angiotensin type 2 receptor,AT2R)拮抗剂EMA 401 应用于GBM 的原位异种移植模型,发现肿瘤体积减少、增殖受到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增加。
3.2.3 联合肿瘤电场疗法 肿瘤电场疗法(tumor treating fields,TTFields)是一种非侵入性抗癌疗法,利用中频交变电场靶向有丝分裂活跃的癌细胞,导致有丝分裂停滞和细胞死亡[42]。目前肿瘤电场疗法已获得FDA批准用于成人复发性GBM和成人新诊断GBM。Stupp 等[43]在EF-14 随机Ⅲ期临床试验中发现替莫唑胺(Temozolomide,TMZ)联合TTFields 治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显著长于单用TMZ 组,且两组的全身不良反应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Toms 等[44]分析的结果提示增加TTFields 治疗的依从性是改善GBM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肿瘤电场疗法联合放疗、TMZ、抗血管生成等多种组合用于GBM 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45]。
4 结语
在临床应用中发现贝伐单抗等血管生成抑制剂可能引起胃肠道穿孔、出血、高血压、延迟伤口愈合等显著的不良反应以及相关的耐药性[46],但随着肿瘤抗血管生成疗法的不断成熟以及医疗科技的不断创新,这些问题都有望得到解决,GBM抗血管生成疗法将得到持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