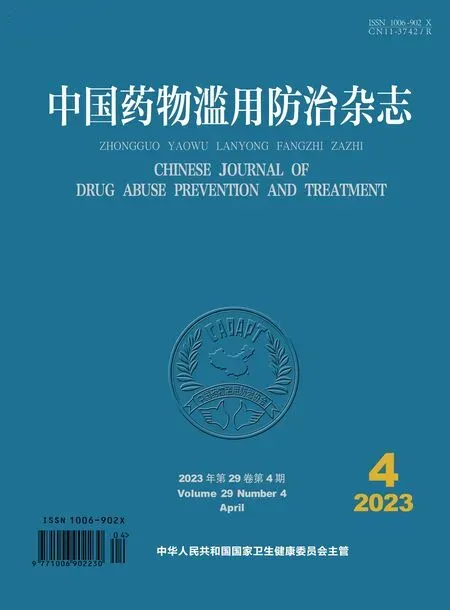朱明芳教授从肝论治口服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1 例*
覃秋艳,朱明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南 长沙 410005)
部分患者服用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等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皮肤过敏反应[1],有证据表明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解热镇痛药可导致药疹的产生[2,3]。药疹是指在患者服用常规剂量药物剂量下发生的有害皮肤反应,与个人体质和药品自身稳定性、成分等有关[4]。药疹可出现多种皮肤系统疾病,包括皮疹(麻疹型)、荨麻疹、脓疱、大疱、丘疹性或肉芽肿性病变等[5]。荨麻疹型药疹是服用药物所引起的荨麻疹样表现,主要表现为局部出现大小不等的淡红色的风团或者颜色正常的风团,部分患者可泛发,还常伴有肢端肿胀疼痛、关节疼痛、发热恶寒等伴随症状[6]。西医对于一般症状较轻者,停用致敏药物后口服抗组胺药物即可,病情较重者,若口服抗组胺药物无效,需先排除荨麻疹性血管炎性或者感染所引起的发热等可能[7]。我院2023 年1 月30 日收治的1 例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患者在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现将临床中医辨证论治措施总结如下,以期为临床治疗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患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临床资料
1.1 基本资料
患者王某,女,48 岁,初诊日期2023 年1 月30 日。患者1 月余前自行口服布洛芬胶囊解热镇痛,服药后第2 天晨起便见颜面部红肿,伴明显瘙痒,颈项部及双上肢起鲜红色红斑丘疹及少量风团,搔抓后风团数量增多,伴有头痛、小便黄,曾求诊于湘雅一附院,予“氯雷他定口服、冰黄肤乐软膏外用”治疗。患者用药5 天后病情未见明显好转,遂于当地某中医馆求诊,坚持内服中药12 剂,颜面部红肿逐渐消退,但红斑丘疹仍未消退,遂求助于吾师朱明芳教授。现症见:颜面部偶感瘙痒,颈项部、双上肢见大量针尖样红斑丘疹,夜间及遇热加重,偶感瘙痒,情绪焦虑,易燥易怒,头目胀痛,面红,口干口苦,纳可,夜间入睡困难,寐欠安,小便量少色黄,大便偏干。舌红,苔黄,脉弦数。既往史:荨麻疹。
1.2 检查与诊断
入院查体:T∶36.9℃,R∶18 次/min,P∶88次/min,BP∶120/70mmHg。临床检查:血常规:WBC 7.9×109/L、P 0.44、L 0.54、EO 0.2、RBC 4.6×1012/L、Hb11.4 g/L。PLT 225×109/L。血生化:葡萄糖7.05 mmol/L;尿酸489.1 μmol/L,胱抑素C 1.40。西医诊断:荨麻疹型药疹;中医诊断:药毒;中医辨证:肝郁化火证。
1.3 治疗与随访
中医治疗原则:清肝泻火,凉血消斑。具体方药:柴胡疏肝散合消风散加减,柴胡12 g、陈皮10 g、川芎10 g、白芍10 g、当归10 g、生地10 g、防风10 g、蝉蜕10 g、牛蒡子10 g、知母10 g、苦参10 g、荆芥10 g、甘草6 g。5 剂,水煎服,日一剂,分早晚温服,嘱患者忌辛辣肥甘。
2023 年2 月6 日二诊:患者诉颈项部及双上肢红斑丘疹完全消退,瘙痒明显缓解,但受热偶感颜面部及颈项部瘙痒,偶可伴见少许风团,情绪仍易燥易怒,面红较前减轻,口干口苦好转,纳可,夜寐较前转安,小便黄,大便正常。舌红,苔薄黄,脉弦滑。遂予消风散加减巩固治疗。具体方药:柴胡12 g、陈皮10 g、当归10 g、生地10 g、防风10 g、蝉蜕10 g、牛蒡子10 g、知母10 g、苦参10 g、荆芥10 g、甘草6 g。5 剂,水煎服,日一剂,分早晚温服。
2023 年2 月11 日三诊:患者诉颜面及颈项部、双上肢已无明显瘙痒,受热及夜间均无风团出现,情绪较前缓解,无明显面红,口干口苦好转,纳可,夜寐一般,二便调。舌淡红,苔薄黄,脉微弦滑。遂予二诊方药继续口服5 剂巩固治疗。后电话随访患者,患者病情好转,无皮疹,情绪较前稳定。
2 讨论
2.1 药疹病因病机
药疹归属于中医的“药毒”“药毒疹”范畴,中医认为该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机体禀赋不足、血热内蕴,加之药毒内侵,热入营血,外发腠理,则外发红斑、丘疹、风团及瘙痒症状。若机体湿热内蕴,则会出现热毒熏蒸肌表,并发水疱、渗液等,若药毒入里化火致使血热妄行,则红斑色深,或呈紫色,甚则可能出现结节、水疱带血等情况[8-10]。火毒炽盛,不仅会外伤皮肤,还会内伤脏腑,导致病情险重。病久则会耗灼阴液,导致气阴两伤。总的来说,药疹的主要病因病机在“热”和“风”。西医则认为这是由于机体服用药物后出现各型超敏反应,如Ⅰ型超敏反应,出现皮肤黏膜系统反应[11],比如荨麻疹、过敏性休克等;Ⅱ型超敏反应,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症;Ⅲ型超敏反应,出现下肢血管炎[12]等;Ⅳ型超敏反应出现如湿疹样/麻疹样药疹、剥脱性皮炎等。药疹常见的类型主要包括荨麻疹样型药疹、麻疹样或猩红热样型药疹、多形红斑样型药疹、固定红斑型药疹、湿疹皮炎样型药疹、痤疮样药疹、光感性药疹、剥脱性皮炎型药疹、大疱性表皮松懈型药疹等多种类型[13]。其中荨麻疹型药疹主要由青霉素、解热镇痛类药(如阿司匹林、布洛芬等)、破伤风抗毒素等引起[14]。朱明芳教授则认为,根据不同患者体质,应“标本兼治”,此阶段患者情绪易紧张,可从肝治疗,帮助患者解决皮肤问题,缓解焦虑情绪。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常因毒素蓄积于肝、情绪焦虑而出现肝郁气滞,化火生风则红斑丘疹色鲜红,风团量多且难以消退,阴液灼伤,气血失和、肌肤失养则瘙痒难耐。朱明芳教授认为从肝论治可疏肝、平肝、养肝,畅情志、养肝血,气血和则瘙痒自愈、皮疹消散,达到内外调和、疾病乃去的作用。
2.2 从肝论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荨麻疹型药疹立论依据
荨麻疹型药疹主要病机在“热”和“风”,“热”可分为“外热”和“内热”。外热是指外感热毒之邪,病毒感染后,患者机体抵抗力较差,热毒之邪可入里;内热则是指药毒热于体内,灼耗营血,加之肝郁化热蕴表,可加重内热,化热生风,故见风团、红斑、丘疹。“风”与五行相关[15],可分为“外风”和“内风”。外风为六淫之首,一年四季皆可伤人[16],可经口鼻或肌表而入,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患者多为肌里受累,由经络传入于脏腑。故可见瘙痒明显。内风系自内而生,多因脏腑功能失调致使内风而生,肝为风木之藏[17],可出现肝风内动,热极生风,阴虚生风等。《黄帝内经》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论之毒当属于六淫之毒或外毒,“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黄帝内经》载“阳胜则热”,肝郁日久易化热,肝阳上亢亦可致热,温热之邪易化火动风[18]。外在环境的病菌感染,患者机体正邪交争,故见头痛发热,患者遂常服用解热镇痛药(布洛芬等)对症治疗。但在用药中,未根据患者自身实际情况合理用药,在错误用药方式下,此阶段机体免疫力下降,且情绪焦虑,肝气失于疏泄,日久化热,常出现失眠、呼吸困难等情况,从而灼伤肝血和肝阴,致使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从而导致头晕胀痛、皮疹溢于肌表或皮疹颜色加深。因此,朱明芳教授认为,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的治疗可从肝论治。
2.3 临阵思路
2.3.1 疏肝
肝主疏泄,喜调达而恶抑郁,新阶段疫病大幅度扩散,这一阶段患者常常出现七情太过、忧思过度、情志不畅,致使肝气郁结、失于疏泄[19],不当用药下,药毒热于体内,灼耗营血,加之肝郁化热蕴表,可加重内热,化热生风,故见风团、红斑、丘疹。可见心火上炎,肝郁化热,红疹则色深。舌淡苔薄黄、脉弦/弦滑均属于肝气郁结之象,因此当以疏肝为主,主用柴胡剂合消风散。肝气得疏、气机得畅、心神得安、气血得行,热亦得解,诸证得愈。
2.3.2 平肝
肺主宣发,肝阳易化火上亢,肝阳可上蒙清窍,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属内热,易伴精神焦虑、彻夜不眠多梦、情绪急躁、双目胀痛等症,舌红、苔黄或黄腻,脉弦/弦滑有力。因此当以平肝熄风、平肝泻火为主,可加用天麻、钩藤、石决明、山栀子、黄芩等。病程日久可由肝及肾,故可加以杜仲、桑寄生等补益肝肾;睡眠不佳者,可加以酸枣仁、夜交藤、茯神等养心安神。
2.3.3 养肝
布洛芬致荨麻疹型药疹,药物内服而致机体受损,肝主疏泄,泛指肝有疏通、条达、升发、畅泄等综合生理功能。受药毒而致肝损,毒素蓄积于肝,则面颊疮疹而生。且药毒致患者情志不畅、忧思过重则致精血耗损,肝阴血受损,血为气之母,气不足则容易出现瘀血等病理产物,致使斑疹面积扩大、颜色加深,还可以伴见入睡困难、睡后易醒、睡时心烦,缠绵难愈,还可伴见头晕眼花、心悸心慌、胁肋部灼痛、两颧潮红、五心烦热、口燥咽干等症,舌红少津、苔薄、脉弦数/脉弦细数。用药应当以养肝安神为主,可加枸杞、当归等进行滋阴养肝。
3 体会
该案中患者因病毒感染后出现机体高热,便服用布洛芬解热镇痛,因药物过敏出现荨麻疹症状,西医予抗过敏+清热止痒外用治疗,中医口服中药,但患者用药后病情未完全好转。吾师通过对患者症状进行分析,考虑其因肝郁气滞并日久化热故红斑丘疹难以消退,舌红、苔黄、脉弦数亦属于一派热象。故治以清肝泻火、凉血消斑。方中柴胡、陈皮能疏肝解郁理气,患者头目胀痛,川芎可活血行气开郁,白芍可平肝止痛养血,荆芥、防风、蝉蜕、牛蒡子四药合用疏风散邪,使风邪从肌肤外透,共为君药;瘙痒明显,以苦参清热燥湿止痒;知母滋阴;治风先治血,治血则风自灭,故以当归、生地补血活血,凉血息风止痒;甘草调和药性。诸药配伍,共奏疏风清热,疏肝解郁养血之功。二诊时患者红斑丘疹消退,但仍偶有少量风团,肝郁症状明显减轻,故以消风散加减继续巩固,患者头目胀痛消失,故去川芎、白芍,余方同前,续以疏风清热、疏肝解郁。三诊时患者症状已基本好转,后继续随访病情基本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