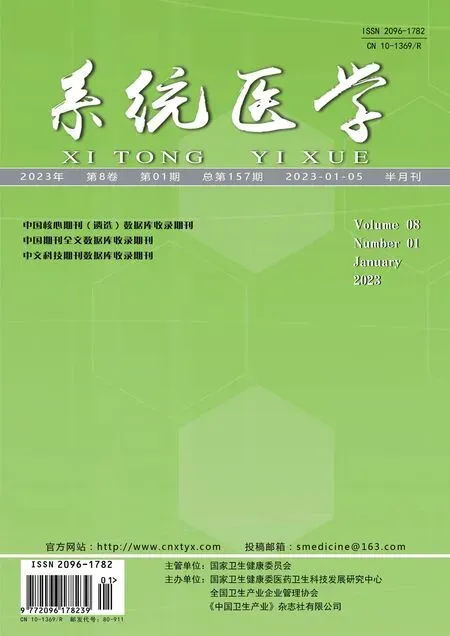宫颈癌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吕加金 ,冯秀秀 ,李玉凡,张清嵛,靳双玲
1.长治医学院,山西长治 046000;2.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浙江嘉兴 314000;3.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妇科,山西长治 046000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全球每年宫颈癌新增人数高达50万,死亡人数约30万[1]。宫颈癌的治疗方法通常以手术治疗为主,辅以放射治疗和化疗,大多数早期患者能达到长期生存的目的。但对于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治疗方式的选择十分有限,且治疗效果不佳[2]。
免疫治疗是通过增加免疫细胞数量、改善免疫微环境和打破免疫逃避等方式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在肺癌、黑色素瘤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为分析免疫治疗在宫颈癌的治疗中的优异表现,本文就宫颈癌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新发现的免疫检查点
免疫检查点是表达在免疫细胞表面并调节免疫激活程度的蛋白质分子,其异常的表达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常见的宫颈癌免疫检查点有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L1)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 CTLA-4),针对这些常见免疫检查点的药物已部分应用于宫颈癌的临床治疗并取得一定疗效。此外,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3, TIM-3)、淋巴细胞活化因子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 LAG-3)等新发现的免疫检查点正处于研究阶段,针对这些免疫检查点的单克隆抗体作为单药或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对于宫颈癌的治疗效果尚未可知。
TIM-3是一种负调节因子,作用是抑制免疫反应。Cao Y等[3]通过分析85例宫颈组织标本(包括43例宫颈癌、22例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和20例慢性宫颈炎)发现TIM-3在宫颈癌细胞中高度表达,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患者的预后,认为TIM-3在宫颈癌细胞中的表达可能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且可能促进癌症的转移。Zhang L等[4]最新研究发现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UV39H1通过下调TIM-3的表达以打破宫颈癌的免疫逃避,但目前尚未有针对TIM-3检查点的药物问世。
LAG-3是一种与MHCII相互作用的分子,主要存在于活化的T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表面。LAG-3的过度表达能导致免疫衰竭和恶性肿瘤的发生,但其中机制尚未完全清楚。LAG525是一种抗LAG-3的单克隆抗体,Schöffski P等[5]进行的晚期恶性肿瘤中单用LAG525和LAG525与斯巴达利珠单抗联合用药疗效对比的Ⅰ/Ⅱ期临床试验(NCT02460224)初步数据已经发布:联合治疗组121例受试者中有11例出现部分缓解,1例完全缓解;单药组数据尚未公开,最终的分析正在进行中。此外,Zhang Q等[6]进行的LAG-3的另一种单克隆抗体IMP321联合紫杉醇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的Ⅰ/Ⅱ期临床研究显示了50%的治疗有效率。但目前尚无宫颈癌相关的临床试验公布。
2 常见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2.1 PD-1/PD-L1通路抑制剂
细胞表面程序性死亡配体I(PD-L1)与表面程序性死亡受体I(PD-1)结合,使肿瘤细胞免受CD8+T淋巴细胞的攻击,达到免疫逃避的目的。一项荟萃分析认为PD-L1是宫颈癌预后不良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7]。Meng Y等[8]研究发现PD-1在宫颈癌肿瘤间质中表达率为46.9%~60.8%。PD-L1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率为34.4%~96%,但在正常宫颈组织中很少表达[9],提示PD-1/PD-L1抑制剂可能对宫颈癌治疗有效。
2.1.1 帕博利珠单抗 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是一种靶向PD-1/PD-L1通路的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 KEYNOTE-028(NCT02054806)[10]验证了帕博利珠单抗在宫颈癌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的Ⅱ期临床试验 KEYNOTE-158(NCT02628067)[11]纳入的98例宫颈癌患者,平均年龄为46岁(24~75岁),包括 83例(84.69%)PD-L1阳性患者和 15例(15.3%)PD-L1阴性患者;93例(94.9%)患者为Ⅳ期患者,77例(78.6%)因肿瘤复发或转移接受过一种或多种化疗。受试者每3周通过静脉单次给予帕博利珠单抗300 mg,持续两年。期间受试者出现药物毒性作用或受试者拒绝治疗时终止给药。结果显示:中位PFS为2.1个月,中位OS为9.4个月。PD-L1阳性组中位PFS为2.1个月,但中位OS达到11个月,揭示了帕博利珠单抗在PD-1阳性宫颈癌中的潜在治疗价值。2019年,NCCN宫颈癌诊治指南推荐帕博利珠单抗为PD-L1阳性的晚期宫颈癌的二线治疗[12]。2022年更新的NCCN宫颈癌诊治指南[13]中推荐PD-1阳性的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首选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
2.1.2 纳武单抗 纳武单抗(nivolumab)是另一种PD-1抗体,2014年被FDA批准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随后被推荐成为多种恶性肿瘤的一二线治疗。Grau JF等[14]进行的Ⅱ期临床试验NRG-GY002(NCT022257528)首次研究纳入单抗在宫颈癌中的治疗价值。研究纳入的25例晚期宫颈癌患者中,仅有1例显示治疗有效,但该例的中位生存期达到14.6个月。因此纳武单抗被推荐成为PD-1阳性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新二线治疗[14]。但目前尚无临床试验直接比较帕博利珠单抗与纳武单抗对宫颈癌的单药疗效,期待关于两药在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治疗中疗效对比的Ⅲ期临床试验。
2.1.3 新型PD-1/PD-L1单克隆抗体 目前正在研究的新型PD-1/PD-L1单克隆抗体主要有阿替唑利珠单抗(atezolizumab),阿维鲁单抗(avelumab)和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Ⅲ期临床试验BEATcc正在研究顺铂-紫杉醇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方案中加入阿替唑利珠单抗能否提高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总生存期[15]。另有一项Ⅱ期试验正在评估标准化放疗中是否加入阿替唑利珠单抗对宫颈癌的疗效比较[16]。阿维鲁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在宫颈癌中应用的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结果令人期待[17]。
尽管PD-1/Pd-L1通路抑制剂显示出对宫颈癌的潜在治疗性,但其中大量的研究都存在着样本数量不足和随访时间较短等缺陷,导致缺乏OS、PFS、不良反应、耐药性及治疗机制等准确的数据。因此,PD-1/PD-L1通路抑制剂的研究道路依旧漫长。
2.2 CTLA-4检查点抑制剂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检查点,通过共刺激受体CD-28间接减少信号传导,下调抗肿瘤的免疫应答。Lheu⁃reux S等[18]通过一项荟萃分析发现,CTLA-4高度表达的宫颈癌患者的OS明显小于CTLA-4低表达组,提示了CTLA-4可能是宫颈癌免疫治疗的又一潜在位点。
伊匹单抗(ipilimumab)是一种抗CTLA-4单克隆抗体,美国FDA已将其批准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一项关于伊匹单抗治疗晚期复发性宫颈癌的Ⅱ期临床试验纳入42例患者,每3周静点伊匹单抗10 mg/kg,持续12周,结果显示:可评估的34例患者的PFS和OS分别为2.5个月和8.5个月,有效率为3%[19]。尽管该试验结果显示伊匹单抗表现出的单药活性不尽人意,但试验中观察到机体免疫功能发生了明显改变。因此有学者提出伊匹单抗能否作为一种新型辅助用药以提高免疫治疗的疗效,但尚无相关研究证实。
替木西单抗(tremelimumab)是另一种CTLA-4单克隆抗体。Chung KY等[20]进行了一项Ⅱ期临床试验以评估替木西单抗在难治性大肠癌中的疗效,结果表明替木西单抗在这些受试者群体中并没有表现出单一药物活性。目前正在研究替西木单抗在宫颈癌的治疗中能否表现出令人满意的单药活性。
3 探索中的免疫新疗法
3.1 细菌免疫疗法
李斯特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杆菌,能够激发机体产生细胞免疫。Axaliimogene filolisbac(又称adxs11-001)是对减毒李斯特菌进行生物改造的新型免疫治疗药物,其结构中包括一段溶血素O(tLLO)片段,能与HPV e7蛋白融合,激活MHC Ⅰ类分子抗原递呈途径,促进T淋巴细胞的增殖,降低肿瘤的免疫耐受[21]。
Galicia-Carmona T等[22]在2018年完成了一项Ⅰ期试验,纳入了15例常规治疗无效的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接受ADXS11-001治疗(分成3个剂量水平,1×109CUF/mL,3.3×109CUF/mL,10×109CFU/mL),结果显示1×109CUF/mL是安全剂量。在此基础上,关于ADXS11-001的一项Ⅱ期试验[23]在印度进行,该试验共纳入110例初始治疗无效的晚期宫颈癌患者,随机分成单用ADXS11-001和ADXS11-001联合顺铂治疗两组,在接受治疗的109例患者中,整体OS为8.3个月(95%CI:5.9~10.5);单用ADXS11-001组OS为8.8个月(95%CI:7.4~13.3),12个月OS为35%(38/109)。此外,Huh W等[24]对50例晚期宫颈癌患者进行了ADXS11-001单药的两阶段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12个月OS为38%。目前尚无相关3、4期临床试验的报道。因此,关于细菌免疫疗法能否成为宫颈癌的新型免疫治疗方法尚需更多试验验证。
3.2 转基因T细胞转移疗法
转基因T细胞转移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er, CAR)是一种将特异性的肿瘤细胞抗原受体人为的转移到T淋巴细胞表面,并在体外扩增,之后重新输入到患者体内,从而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目的的新型免疫治疗方法。黄晓岚等[25]进行了一项Ⅰ期临床试验(NCT02280811),检测HPV16+肛门癌肿瘤细胞对靶向HPV16 E6蛋白的转基因T细胞的反应性,结果显示:这类转基因T淋巴细胞对HPV16+的癌细胞系具有特异性识别和杀伤能力。此结果为CAR治疗HPV相关性宫颈癌奠定了基础。目前国家癌症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正在进行HPV相关性宫颈癌CAR的Ⅰ/Ⅱ期试验(NCT01583686)[26],尚未公布研究结果。CAR能否针对非HPV相关性宫颈癌,针对不同类型HPV感染的晚期宫颈癌的疗效如何尚无试验数据证明。
3.3 溶瘤病毒疗法
溶瘤病毒疗法是借助溶瘤病毒的细胞毒作用和免疫刺激作用达到治疗恶性肿瘤目的的新型免疫疗法,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溶瘤病毒是一类选择性感染并且杀死肿瘤细胞但对正常细胞基本无害的天然或人工重组病毒。溶瘤病毒识别并进入癌细胞内通过直接的溶细胞作用或激活全身的抗肿瘤(抗病毒)免疫应答,并将免疫细胞募集到肿瘤周围的免疫微环境中,达到治疗恶性肿瘤的目的[27]。目前,研究人员已经进行了多种病毒的临床试验,如疱疹病毒、腺病毒、麻疹病毒等。2020年一项有关溶瘤疗法治疗复发性黑色素瘤的Ⅲ期临床试验中,转基因疱疹病毒T-VEC被证实对黑色素瘤有效且安全性好,获得了FDA的上市批准[28]。此外,Keshavarz M等[29]研究了新城疫病毒(newcastle diease virus, NDV)对小鼠宫颈癌模型的溶瘤能力大小,结果显示NDV通过在肿瘤细胞中优先复制、产生活性氧和激活癌细胞早期凋亡途径,诱导细胞产生抗肿瘤活性。这为溶瘤疗法在宫颈癌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Kagabu M等[30]正在研究疱疹病毒的溶瘤疗法在晚期宫颈癌中的应用,但其临床效果尚需大量相关数据支撑。
4 结语与展望
免疫治疗给宫颈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仍缺少大样本试验数据证明,如何处理宫颈癌免疫治疗经济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