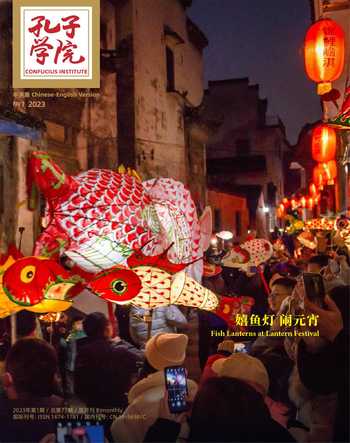新安画派



上海博物馆历代绘画展厅里有一排橱窗,常年陈列清代新安画派的作品。要了解中国绘画的发展史,新安画派是不能跳过的一个部分。
画家群体——新安画派形成的人文支柱
画派的形成需要一批“志同道合”的画家,这是第一要素。新安畫派有相对明确的艺术追求,推崇元代倪瓒、黄公望的山水画。其中,渐江应能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倪瓒”,他追求倪瓒清新淡雅的风格,画面毫无半点俗气。众所周知,倪瓒是有洁癖的,我们在渐江的画上也能看到这种一尘不染的风格。渐江(1610—1664)一生服膺倪瓒的笔墨,以实际行动“复刻”倪瓒的画风。作为“清初四僧”中最年长的一位,他的作品富有禅意,留出大量空白,却又没有空洞的感觉。渐江用笔的方折比起倪瓒有过之而无不及,笔下的那股拗劲也是每个观众能够感受到的。观众与其说喜爱他的画,不如说是喜欢那股拗劲。同样作为山水画家,贺天健(1891—1977)对渐江的认识入木三分,他说“弘仁和尚(渐江)的画,是新安画派中的佼佼者。他笔如钢条,墨台海色,每每纵横交织地表现石的姿态和体积。但觉静穆、严在、朴实、恬洁,规行矩步,一点也不放失。”
新安画派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是查士标(1615—1697)。他受董其昌的影响很深,又能上溯元人,和董其昌一样得到前辈真传,其画作气韵格调与众不同,是艺术上所谓的“雅”。与渐江比起来,他的笔墨略多,但又能够在倪瓒、黄公望之间游刃有余;画面的墨色浓郁,正好与渐江的疏淡形成对比。但是其画作浓郁中又显清洁,和渐江的疏淡又不单调一样,都显示出艺术家驾驭笔墨的高超能力。
如果前文说的是“人杰”,那么这里说的就是“地灵”。无法想象画家,尤其是山水画家的创作能够完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无关。中国古代绘画很早就形成了“外置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路径,在不同时代,每个画派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新安画派就是古徽州地区沿着新安江聚集的画家群,除了新安江,还有黄山。提到新安画派不能不提黄山,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魅力可想而知。黄山对于一般人尚且如此,对于山水画家,再怎么说也不夸张。程嘉燧(1565—1644)的画有一些是写生册页,在不大的页面上写生,图像未必与黄山景色高度吻合,但笔墨中流露出的却是与黄山精神高度契合的气韵。古人说,“惟软笔而变化生焉。”中国书画使用的是软笔,这样才有变幻莫测的笔墨效果。“健”表示毛笔弹性好,用来形容程嘉燧的画作则十分贴切。他的笔墨既结实又不呆滞,画出了蓬松的感觉,这就是文人追求的轻松与闲适。
商业氛围——新安画派形成的“催化剂”
经过明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画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艺术品”形象,其“商品”属性越来越强。极端的例子就是扬州画派与海上画派的形成,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艺术的发展。晚明形成的新安画派,其商业影响不及上面这两个画派,但亦不容忽略。新安画派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群体——“徽商”。徽商在当时富甲一方,以诚信精明、吃苦耐劳著称。他们在全国各地经商,同时还有扶助同乡的传统,形成了庞大的财富集团。在拥有了巨大财富和较高的经济地位后,他们顺理成章地关注起文化品位与精神消费。其中,不少名商大贾特别重视文教事业,中国传统的绘画就这样成为他们关注的“艺术品”。画家群体离不开商业环境,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徽商在本地与外地从事经营活动的同时,不忘收藏书画,并以有无书画收藏定雅俗。这为新安画派画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徽商还会与画家们一起交流自己收藏的宋元名画,后者也不断锐意进取,使自己的作品取得徽商的青睐。
余论——新安画派的影响
近代中国画坛,举起新安画派大旗的画家中,最有声望的非黄宾虹莫属。黄宾虹(1865—1955)和齐白石(1864—1957)并称“南黄北齐”。两人都主张近代中国美术要与西方拉开距离,要全力继承中国画传统,不必受西方影响。这成为近代中国画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黄宾虹的中国画理论与实践有着明显的“新安”烙印。黄宾虹的画在“笔墨”上最能体现“民族性”。在充分提炼、总结、概括新安画派画家在内的前辈笔墨精髓后,黄宾虹提出了“五笔七墨”的重要画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离不开黄山,离不开新安画派的滋养。《黄山汤口图》是黄宾虹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在2017年夏,这件作品以3.45亿元的高价成交;另一方面这幅画作也体现了他的黄山情结:他一生九上黄山,92岁的时候还以黄山为题材创作巨制。这件作品的画面墨色层层叠叠,浓处不腻,淡处不薄,这除了体现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满是新安画派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