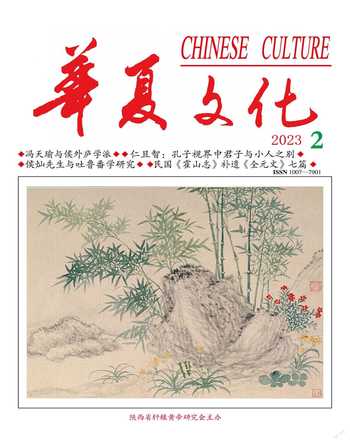孟子天命观探析
陈鼎
天命一直以来是儒家注重的部分,也是先秦诸子集中讨论的话题,孟子的天命思想是继承孔子及其之前的天命思想。孔子受到西周时期天命观的影响,他认为“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拥有绝对权威的力量,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主张“畏天”,但个体在面对“天命”时,也并不是无所作为,正如孔子所讲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说明孔子也十分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知天”的目的,但孔子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又说“天道远,人道迩”认为天之事难以捉摸,因此将目光转移至人身上,以上种种观点都对孟子思想有所启发。
一、天命思想的内涵
(一)天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秘力量
在孟子看来,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神秘莫测的力量——天命,这种力量不为人所熟知,但却真实的存在于世间,让人难以琢磨,这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对于人的行为活动甚至人类社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里的“天”和“命”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包括神秘的主宰力量,于是孟子将其合称为“天命”。面对这种力量,孟子本人也对之无可奈何,在《孟子·梁惠王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20年,第49页)记载这样一件事情: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平公去见孟子,孟子也愿意与平公相见,双方都按照仪礼的规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臧仓却认为后丧踰前丧有违礼制,甚至孟子弟子充虞也认为:“木若以为美”(《公孙丑下》)。此次会面看似正常,孟子也希望面见鲁候,一展平生所学,但结果确是君未来见孟子。孟子这样解释说:不是由人可以决定的,“不遇鲁侯,天也”。这里的所说的“天”即是“天命”,孟子认为不遇鲁侯的原因就是天命。朱熹注曰:“乃天命所为,非人力之可及”(朱熹:《孟子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1页),行动或停止都取决于天命,并非人力所能影响。
孟子一生都在推行仁政思想,周游列国,将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于诸侯,但一生四处奔波,都劳而无获,志向也终究没能实现,就算有滕世子虚心请教以行仁政,使得士人闻之皆“自楚之滕”,奈何滕国弱小,处于强国之间,面对强国侵扰,孟子亦无力回天,只能寄希望于天:“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下》)。以上种种都是孟子为其志向所做的努力,经过一番折腾,孟子也清楚地认识到成功与否,不在于己,而在于天命,以至于说到:“顺天者昌”(《离娄上》),在无情天命的支配下,人只能被动地服从。
(二)性即天命
按照孟子所说,天命在天地之间表现出一种不为人意志所影响的力量,当这种力量下落在人身之时,便体现出人之性。孟子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告子上》),仁义等道德是人先天而生的,而孟子所讲的“天爵”正是这些先天固有的道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告子上》)所谓的“仁义礼智”,在孟子看来不是由外部而获得的,是个体本身生而具有的先天属性,而这种先天属性是由“天命”所赋予的。正是由于人之性有了天命的赋予,才使得人与禽兽才得以区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尽管人性生来具有仁义礼智等先天禀赋,但在孟子看来,人还要进一步将之发展、完善: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可以看出:仁义礼智之四端是人生来具有的, 在孟子眼中这就是天所赋予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有四体也”,人人都禀赋了天所赋予的东西, 但孟子将其称为“端”,表明这只是一个源头、萌芽,还需要进一步的扩而充之,如果不能将之发展,孟子就认为其“自贼”,即自暴自弃。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弱小者遇到危险,人人都会起同情之心,正如朱子曰:“孺子入井时,其心怵惕,乃真心也”(《孟子集注》,第44页),人都不由自主地显露善心,人之善心的显露,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在执行天的“命令”,显现出人善的本性。正是因为此,所以先王由此推行不忍人之政,人的善的本性也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提供了理论根基。
(三)天命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
天命在孟子那里不仅表现为人之善性,同时还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发展趋势。首先,与孔子不同,在孟子时代,天下统一的观念似乎已经出现,诸侯之间的争斗已由孔子当时的争霸战争逐渐向统一战争过渡,《孟子》文本也多次出现“平天下”“王天下”等言语,在《梁惠王上》,梁惠王卒然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说:天下归于一统,即天下统一便会安定。梁惠王能有此问,在某种方面也已感到动荡生活的不安,而孟子也以此回应他,天下一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其次,孟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战国时代,各诸侯为一己之私利,大动干戈相互征伐,以梁惠王为例,初见孟子便先言:何以利吾国?整个社会被利益所充斥,大欺小、强欺凌弱,面对如此社会现状孟子非常不满。为了缓和战争带来的伤害,孟子提出了“天命”,“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孰与之?曰:天与之”(《万章上》)。孟子认为得天下,是由天命所给予的,并不是天子所传的,人只有顺应天命,得到天命的认可才能得天下。同时孟子将“天命”與人民相联系,孟子将老百姓的拥护与否作为统治者是否得天命的依据,与其说得到天命,倒不如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得民心呢?孟子说:“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万章上》),使百姓得到安定,百姓接受他,才能把天下授予他。在此基础之上,孟子认为只有实施仁政的人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而老百姓的认可与拥护是孟子天命观所表现的最为直观的内容。
于是,孟子的天命思想表现出三个特征:首先,天命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却对天地间的事物以及人的成败得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天命是人善的先天表现,仁义礼智等先天道德根植于个体本身,人善的信念以及行为也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天命的促使;最后,天命在孟子这里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经过春秋时代的磨合,天下统一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孟子将天命与百姓相结合,告诫统治者,必须行仁政方可得到百姓的拥戴。
二、人力对天命的抗争
孟子思想中的天命对社会与个体有着种种约束,根据上述研究,社会与个体从属于天命,尽管天命对个体的制约是人难以抗拒的,但孟子天命观的最大魅力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天命面前有所作为(任素月:《浅析孟子天命观》载《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从儒家整个价值体系来看,不管天或天命在社会中有着多大的作用,但是其关注的重点一直在人身上,换言之,强调天命或天的主宰,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人这一主体,当然在孟子这里也是这样,面对天命的支配,主体也有自我能动性。
(一)道德领域
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是人先天固有的,也是天命在人身上的表现,如前文所言,仁义礼智,犹如四端,端即源头、萌芽,也就是说,天命只赋予了人善的本性的源头,而不成熟的善性,则不如“荑稗”,由此便是天命的局限,更能体现出人的能动性。早在孔子便有“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宣告了,人在道德领域是具有比天命更为突出的主体地位,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心上》)
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尽心上》)
根据孟子所说,个体有两种追求,同时也有两种追求的路径,其中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是个体所固有的,需要个体求之于自我本身,因此只要个体有所追求便可得到仁义礼智等道德,得与不得的最终决定权在于个体本身,因为这些根植在个体自身的道德追求便会得到,而舍弃也就会丧失。
“求”则体现了个体的自觉能动性,在道德领域,主体道德虽然是天所赋予的,但是仍然受制于个体本身。孟子认为个体能否在道德领域达到理想的境界,这并不是天命所能决定的,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体本身,“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离娄上》),自暴以及自弃都表现了主体在道德方面的堕落,而这种“不能居仁由义”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个体自身的选择,孟子在暴与弃之前加上“自”,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由此观之,在道德领域中,人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在这里,人或多或少被理解为一种自由的主体,这种自由不仅表现在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且展开于强恕而行的行为过程中”。(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二)非道德领域
与道德领域的“求在我”相对应的是“求在外者”,这里的“外者”指的就是除去道德因素的所有方面,包括富贵、显达、生老病死、政治需求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外者”的范围(非道德领域)。和道德领域的“求在我者”不同的是,“求在外者”并没有相对的自由选择或者说相对于道德领域,非道德领域并没有相对多的个体自由。在“非道德领域”主体便无法像在道德领域一般,可以决定行为活动的结果,个体对于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天命,能做的就是“俟命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中排斥个体的能动性以及作用,“俟命”也并非毫无手段或者说并非没有个体意志的参与,只是表现出一种温和地顺从。
个体在面对不为意志所转移的天命时,只能温和地顺从,因此孟子讲“事天”,因为“天命”是通过“人事”来展现的(侯璐,李葆华:《浅析孟子的天命观》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从个体方面来说,就是要“知天命”: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孟子认为“知天命”的途径就是“尽心知性”,首先要“尽心”,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四心是天所赋予的,个体需要对其扩而充之,充分的扩充四心才是尽人心之善性。再者就是“知性”,先要区分“性与命”,孟子对“性与命”作了区分: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孟子认为“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至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这五种人之欲望,孟子是承认它们的存在,至于欲望的得到与否,属于天命,所以孟子不把这五种欲望视为人的本性,即“君子不谓性”。“君子不把欲强调为‘性, 欲得到满足也好, 未得到满足也罢, 都不去做过分的追求,这就是孟子的倾向”(见《浅析孟子的天命观》),与之相反,仁义礼智等道德因素,是根植人自身的,能否实现属于命,但是更人的天性的必然,取决于自己,与命运无关,所以君子“不谓命”。
只有正确理解了“性”与“命”的关系,分清了“性与命”的界限,才能在属于性的领域上作人为的、自主的努力,更为广泛地扩充人的善的本性,这就是知性。将天所赋予的四心推广,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加贴合天命, 以此来“俟身”以等待天命。
对于“命”而言,孟子也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孟子将“命”分为“正命”和“非正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天下所发生的无一不是命运,“正命”就是顺理而行,在大义面前舍生取义就是受“正命”;相反,立乎危墙之下、桎梏而死就是“非正命”。天命虽是捉摸不定的,是不为人所控制的,但是在如何面对“正命”或者“非正命”,个体是可以选择的,“这是主体在意识到天命的普遍力量之后,便自觉的加以顺从”(《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第68页)。
既然命有“正与非”之分,那么作为个体就要有所区分地对待“命”,即对“正命”,人要顺理而求之,哪怕求道而死也在所不惜;对“非正命”,个体应对之避尤不急。人要在人力范围内争取到好的结果,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做到“知命”。
在孟子的思想中,天下事“莫非命也”,在道德领域,人之所求在我(个体本身),虽说道德是天所赋予,人在道德领域中却可以自主地选择和决定结果。自暴、自弃皆取决于个体本身,该领域也是个体的“自由世界”,在其中人的主体地位更为凸显,但是过多的夸大道德因素,就会流向一种“道德无敌”的弊端,孟子常说“仁者无敌”(《梁惠王上》),事实上,“仁者”究竟无敌与否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在“非道德领域”,是天命统治的区域,人在这一领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在“非道德领域”所求不在我,而是在外者,其受制于“天命”,但是人在此并不是意味着没有丝毫的作用,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天命”,个体往往自觉地顺从“天命”,即俟身立命,通过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使得自己的言行举行更加符合“天命”的要求。
三、结语
综上,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及以前的天命思想,在强调天命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同时又注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天命观,为神秘的‘天命注入了人性的道德因素,为道德宗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力博:浅析孟子的天命观,今古文创,2020年第5期)。在天命所控制的范圍,个体只能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使其更为贴合天命的要求,尽管天命不可违背,但孟子还是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人身上,所谓的“知天命”,重点是为了凸显“尽人事”。在孟子的天命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主体自由向个人的道德实践与心性涵养的靠拢,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儒家的内圣走向”(《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第68页)。
(作者: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 7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