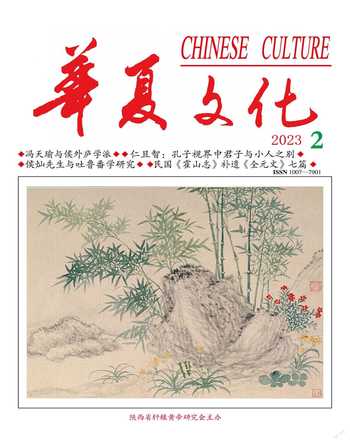诗可以兴——《管锥编?兴为触物以起》再议
赵凯

“兴”是《诗经》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定义的表现手法,对于“兴”义,历代学者多有探究。在《论语》中,孔子提出“诗,可以兴”的命题。之后,《毛诗序》明确“兴”为“六义”之一:“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胡渐逵等整理:《毛诗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范文澜:《文心雕龙译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01页)认为其他五义通俗明显,易于辨识,而唯独兴义难解。朱自清在梳理历代“兴”义的源流时指出:“兴”之义“最为缠夹,可也最受人尊重”(参见 陶水平:《“兴”与“隐喻”的中西互释》载《中国文学批评》 2022 年第1期)。钱钟书在读《诗经》时,也认为“兴之义最难定”(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2页),并且在《管锥编》中,专辟一章《兴为触物以起》,探讨 “兴”义。本文通过深入考察钱氏文本,阐述钱氏观点论证的不合理性,进而通过分析《诗经》中三首典型“兴”诗——《关雎》、《桃夭》、《汉广》,揭示“兴”作为《诗经》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所具有的三重功能:在形式上引起下文;在内容上与下文“物”与“意”层面的呼应与类似关系。
一、钱钟书:兴乃触物以起,功同跳板
在《管锥编·兴为触物以起》中,钱钟书引用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并解读了“兴”的涵义:
“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兴之托谕,婉而成章。”是“兴”即 “比”,均主“拟议”、“譬”、“喻”;“隐”乎“显”乎,如五十步之于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靳也。六义有“兴”,而毛郑辈指目之“兴也”则当别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盖毛郑所标为“兴”之篇什泰半与所为“比”者无以异尔。(《管锥编》,第62-63页)
可见,钱钟书批判了刘勰对于“兴”义的解释,指出刘勰为了“依傍毛、郑”,对“兴”义进行了歪曲。钱钟书认为,刘勰的“比显而兴隐。……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是把“比”与“兴”混为一谈,“比显而兴隐”说明“比”“兴”本质相同,“隐”乎“显”乎,只是“五十步之于百步”,程度稍异,二者“均主‘拟议、‘譬、‘喻”,本质上都释为比喻,不同之处,只是比喻的程度稍微不同,并没有分别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使得“兴”成为“比”的附庸,无法与“赋”、“比”二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足而立。钱钟书进一步解释道,刘勰之所以这样做,是在为毛公和郑玄补苴罅漏,因为毛、郑所标注的《诗经》中“兴”之篇目大多数与“比”之篇目并无区别,而刘勰继承了毛、郑的经学思想,必然要为二者曲为辩解,强生解释,把“兴”向“比”靠拢,而毛、郑从经学角度对“兴”的解释与《诗经》本意的“兴”并非一回事,因此刘勰的解释不足取。
在批判刘勰观点的基础上,钱钟书进而提出自己对于“兴”的理解——触物以起,功同跳板,仅起过渡作用,而无实际意义。钱钟书赞赏北宋李仲蒙对于“兴”的解释“颇具胜义”——“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指出“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管锥编》,第63页),兴所用之“物”并非着意索求,而是无意看到,随口咏出,与后文虽然附着,但是在前之“物”与后文之“情”并无衔接与联系,只是为了引出后文。钱钟书进一步引用项安世、朱熹、徐渭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与李仲蒙一致,皆可以阐释“‘触物起情为‘兴之旨欤”,他们的观点“皆深有得于歌诗之理”。除此之外,钱氏自己引用曹植的《名都篇》、甄后《塘上行》、汉《饶歌》、现代儿歌和西方示威口号为佐证,再次说明六义之兴 “功同跳板”(《管锥编》,第64页),只起到引起下文的过渡作用。
二、钱氏之误
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刘勰《比兴篇》与钱氏观点,可见钱钟书对于刘勰观点的误读以及自身观点论证的不合理性。因此,钱钟书对于《诗经》之“兴”的阐述,尚须进一步商榷。
一是他对于刘勰的理解并不真切,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刘勰《比兴》篇原文: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興”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文心雕龙译注》,第601页)
仔细分析本段,可见刘勰本意并非钱钟书所理解的——“比”、“兴”本质相同,都是比喻,只是程度不一——而是认为“比”“兴”本质不同。刘勰认为“‘比显而‘兴隐”是指从效果而言,“比”明显易识别而“兴”隐微难辨认,所以毛公对于“六义”唯独标出“兴”义。就本质而言,“比”“兴”含义不同,“比”是“附”,“切类以指事”,“比是比附,以切合所写事理的类似事物为比喻来说明”,“兴”是“起”,“依微以拟议”,“兴是兴起,因微小之物触发情思,托以取义”,一个比附,一个兴起,二者截然不同。至于“兴则环譬以托讽”意为“用委婉比喻以寄托讽意”(王运锋 周熙:《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1页),意指“兴”包蕴比喻,或者说把比喻作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但并不等同于比喻。因此,刘勰并未如同钱钟书所理解的把“比”“兴”混为一谈,而是严格区分了二者界限:“比”用来比喻,说明类似事物,直出胸臆,容易辨别;“兴”用来兴起,依据微小事物,托以讽议,较难体悟。
二是钱钟书对于自己的观点——“兴”乃触物以起,功同跳板——的论证并不充分,难以立足。他所引用的诗篇,并不具备相关性与可靠性,不能支持其观点。项安世、朱熹、徐渭以及钱氏所引例证,以汉代乐府诗居多,钱氏的例证还涉及现代儿歌俗语以及西方政治口号,这种以后世文本解释《诗经》“兴”义的做法,并不可取。文学表现手法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后在文学作品,并不能用来证明前代的文学手法。对于汉魏时诗表现手法的流变,朱光潜在《诗论》中,已有阐述:
在汉魏时,诗用似相关而又不尽相关的意象引起本文正意,似已成为一种传统的技巧。有时这种意象成为一种附赘悬瘤,非本文正意所绝对必需,例如: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起首两句引子,都与正文毫不相干,它们的起源,与其说是“套”现成的民歌的起头,如胡适所说的,不如说是沿用《国风》以来的传统的技巧。《国风》的意象引子原有比兴之用,到后来数典忘祖,就不问它是否有比兴之用,只戴上那么一个礼帽应付场面,不合头也不管了。(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
朱光潜的这段话直接表明不宜用汉魏时诗来解释《诗经》之“兴”,明确指出汉代时,用以“引起本文正意”的“意象成为一种附赘悬瘤,非本文正意所绝对必需”,已没有“比兴之用,只戴上那么一个礼帽应付场面,不合头也不管了”,而《国风》的“意象引子原有比兴之用”,原是“合头的”。可看出汉魏诗歌的“意象引子”已与《诗经》的作用不同,用作材料来解释《诗经》中的“兴”义并不合理。
虽然项安世选用了《王风》、《扬之水》与《郑风》、《扬之水》来释《诗经》之“兴”,但是,这两首诗并不具有代表性。分析诗经的“兴”义,不宜用《诗经》之外的文本,也不宜用《诗经》中非典型的、有争议的“兴”诗作为材料,而应选用《诗经》中典型“兴”篇。因此,本文选用了《诗经》中无异议的三篇“兴”诗——《关雎》《桃夭》《汉广》作为文本,力图揭示“兴”义内涵。
三、兴的三重功能:引起与类比
本文选取三首代表性“兴”诗——《关雎》《桃夭》《汉广》。《关雎》是一首贵族青年的恋歌,表达了一个贵族青年追求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而产生的愁苦之情,并描写了青年在想象中与女子恋爱、结婚的场景。《桃夭》是一首贺新娘的诗,诗人看见农村春天柔嫩的桃枝和鲜饱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貌美。《汉广》描写了江汉间一位男子爱慕一位女子,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参见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年,第12-18页)。在对这三首诗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分析“兴”句与正文之间的关系,归纳总结“兴”义之功能,揭示“兴”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兴”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在形式上起到引子的作用,用小引子引出大主题。“兴”乃起也,是引起之意,开篇的兴句所引之物起到“引导、兴起的作用”(曹凤:《兴与隐喻——中西诗学比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引起下文“终须直率说出”的“话”。所引之物一般是“草木、鸟兽、虫鱼”等微小之物,而下文“所咏之事”则意义重大,因此,是以小引大。《关雎》开篇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雎鸠鸟开篇,但是后面引出的男女恋爱结婚之事,却是“人伦之始,王化之基”的人生大事;《桃夭》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用常见的桃花和桃树兴起“之子于归”的婚姻之事;而《汉广》也是同理,用“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来兴起“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因此刘勰言:“起情者,依微以拟议”,以微小事物兴起情思和主题,但“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后面类比的事物却比较大。
若是仅是引子的作用,那与钱钟书的观点——“兴乃触物以起,功同跳板”并无不同。“兴”的引起作用,只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在“物”的层面,所引之物与所咏之物,还有相似之特点或者品质,起到类比作用。“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起者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便指出所引之物与所咏之物的“引类”特点,亦即朱光潜所说“所引事物与所咏事物在情趣上有暗合默契处,可以由所引事物引起所咏事物的情趣”。比如在《关雎》中,所引之物是雎鸠鸟,所咏之物是窈窕淑女,雎鸠鸟情意专一,用来类比后文女子的淑善坚贞;《桃夭》中,以夭夭桃树类比新娘,桃树正茁壮少盛,用以类比新娘的壮硕美好;《汉广》中,以“南方之木美兴汉上之女贞”。可见,起兴之物并非无心“触物以起”,随意选取,而是诗人匠心独运的结果,与后文所咏之物在特点上有契合之处。
不仅在“物”的层面,所引之物与所咏之物相似,而且在“意”的层面,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也有相似之道理。所引之物并非静态,往往跟随某个动作或某种状态,构成一件“事”,传递出某种“意”——道理或者情感,与后文所咏之事的“意”相通。孔颖达说“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毛诗正义》,第12页),隐含之“理”即“意”也。刘勰讲“兴则环譬以托讽”,“讽”即传达出的“意”(刘勰是封建正统的卫道士,遵从诗歌具有“美刺”功能的观点,因此认为传达出的“意”是“讽意”)。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描绘了情意专一的雌雄雎鸠鸟在水中小洲关关和鸣、情深意切的场景。而后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刻画了夫妻双方在一起琴瑟和鸣的美好画面,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皆表现了坚贞幸福的爱情。在《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描写了盛壮的桃树不仅花朵鲜艳、枝繁叶茂,而且果实累累。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表达的意思为壮硕的女子必定会多生子嗣以“宜其家人”。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具有相同的繁衍生息的主题。而《汉广》篇,“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表明乔木虽高大壮直,但由于“上竦者,其上曲,其下少枝叶”(《诗经注析》,第18页),故而不可在下纳凉休息。后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表明汉女虽壮硕坚贞,但却求而不得。二者也传达了相似主题——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难遂心愿。可见,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在表达的“意”上是相似的,并非钱氏认为的毫无关系。(以上所探讨的是“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有相似之‘意”的情况,《诗经》的少量诗篇,如《唐风·杕杜》、《秦風·晨风》,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具有相反之“意”,起到反衬的效果,是谓“反兴”。如《唐风·杕杜》篇云:“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意为“诗人见到孤生独特的甘棠尚且有茂密的树叶保护它,不禁感慨自己的孤独无亲,还不如杕杜”。但即使是“反兴”,所引之事与所咏之事亦具有相关性与相通性。)
四、结语
对于《诗经》,孔子多有论述,曾云“不学诗,无以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页),表明当时《诗经》对于沟通表达的重要性,但是这并非仅指在外交辞令、日常讲话中引用《诗经》辞句。因为孔子还讲:“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9]135可见仅仅寻章摘句远远不够,学《诗》后,还要达到能够熟练处理政务以及在外交场合游刃有余的地步,这便需要进一步揣摩、学习、使用《诗》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等。而孔子在劝诫弟子学习《诗经》时,给出的第一个理由便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功能的点评,把“兴”作为第一要义,可见诗经中“兴”的重要性,这也从侧面证明“兴”并非“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而是“同索物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管锥编》,第63页),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发挥作用。
但是“比显而兴隐”,相较于“比”,“兴”隐微含蓄,委婉曲折,不易体会,因此需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所引之物的含义,才能解其寓意。如果不了解雎鸠代表着忠贞的爱情,便难以理解雎鸠鸟与“窈窕淑女”之间的关系,也难以领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之间的相通意境。所以刘勰一直强调“兴”“婉而成章”的特点,也正是由于“兴”的这个特点,常常用来讽刺或者劝谏,因此,刘勰更加青睐“兴”,认为有教化意义,对于当时“比”的繁盛而“兴”的衰微痛心疾首,认为是“习小而弃大”(《文心雕龙译注》,第602页)。但是,“兴”在后世并未消亡,反而被后世文学家如孟子、曹植、杜甫等不断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学核心的表现手法甚至中国人重要的思维方式。
(作者:北京市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注释:
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