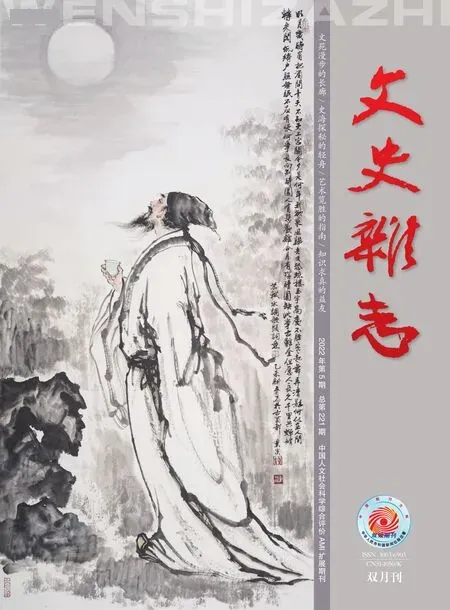雎鸠未必是天鹅
李凤能
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姚小鸥《〈关雎〉兴象及其文化内涵》一文,就《诗·周南·关雎》中“‘雎鸠’为何鸟”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证之后,他认定“雎鸠必为天鹅”。
话虽说得信心满满,但却经不起推敲。姚教授解说《关雎》兴象,依据是《毛传》。他说:
最早提出“雎鸠”为《关雎》兴象的现存文献是《毛传》。《毛传》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汉代学风质朴,故《毛传》注释甚为简略,什么是“王雎”?“挚而有别”所指谓何?给后人留下了解说的空间。
接下来姚文便围绕“什么是‘王雎’”和“‘挚而有别’所指谓何”这两个问题展开。本文不对姚教授全文进行讨论,仅就“‘雎鸠’为何鸟”的问题发表拙见。
《毛传》据说是鲁人毛亨(大毛公)所作。他指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兴也”虽然正确,但对《关雎》内涵的阐述却靠不住。西汉之初,鲁国人申公、齐国人辕固、燕国人韩婴传授《诗经》,认为《关雎》一篇是刺诗,具体地说,是讽刺周康王“失德晏起”。而《毛传》却把《关雎》说成是赞扬“后妃之德”的颂诗。刺诗也好,颂诗也罢,尽管主张有别,但他们都把《关雎》扯到帝王后妃身上,从而偏离了该诗的主旨。
《关雎》是三百篇之首,也是十五国风之首。什么是“风”?朱熹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他对国风的定义,无疑是正确的。春秋之际,本有仲春之月未婚男女欢会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所以,《关雎》一篇,应与帝王后妃无涉。
《关雎》以“雎鸠”在河洲上啼鸣起兴,接着叙述某个采荇菜的男子对他心仪女子的思念和追求,既有求之不得的惆怅,也有得遂所愿的欢愉。
弄明白了《关雎》一诗的内容,再回到“‘雎鸠’为何鸟”的问题上。《毛传》说是“王雎”,因为说得“甚为简略”,于是给姚教授“留下了解说的空间”:
《说文》鸟部:“鷢,白鷢。王雎也。从鸟厥声。”需要说明的是,《尔雅》郭璞注说,白鷢“尾上白”。这一说法是不可靠的。古人名鸟兽毛色、羽色时,言其为某色,意即通体为此色。若杂以他色,则有专文名之。《说文》马部字析之甚详。段玉裁在解释“鹭,白鹭也”一语时,指出许慎著《说文》之体例“多因《毛传》”,即“以人所知说其所不知”(《说文解字注》)。由上述可知,通名为“王雎”的“雎鸠”,又名为“鷢”或“白鷢”,是一种褊喙的大型水禽。其毛羽白色,所以不会是褐色的大雁。综合考量,非天鹅莫属。
经姚教授这一解说,“王雎”一转身就变成了“天鹅”。既然他引用了许慎的《说文解字》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我也用这两本书的内容来回答他。
《说文解字》于“鷢,白鷢,王雎也。从鸟,厥声,居月切”后紧接着就是“雎,王雎也。从鸟,且声,七余切”。
显然,许慎认为“鷢”与“雎”并非为同一种鸟。至于为什么许慎《说文》在释“鷢”为“白鷢”后有“王雎也”三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作了说明:
按《释鸟》云:“雎鸠,王雎”与“鸉,白鷢”划分二鸟。许乃一之,恐系转写讹误,非许书本然也。当为正之曰:“鷢者,白鷢也;雎者,雎鸠,王雎也。”乃合。《毛诗正义》曰:“陆玑疏云:‘雎鸠,大小如鸱。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谓之鹫。’而杨雄、许慎皆曰白鷢。”
段氏还说,把雎鸠当成“鹫”的错误是出在陆玑身上,并不是出在杨(扬)雄、许慎身上。他进一步指出:“‘杨雄、许慎’已下,孔冲远语也。所谓杨雄者,今不见于《方言》,未知其所本。”
既然许慎《说文解字》“鷢,白鷢”后的“王雎也”三字可能是“转写讹误”,而在扬雄的《方言》里又找不到“王雎”是“白鷢”的说法,那么孔颖达的话便值得怀疑。段氏一句“未知其所本”,差不多就是否定。姚教授既然说了“段玉裁在解释‘鹭,白鹭也”一语时,指出许慎著《说文》之体例“多因《毛传》”这句话,那么他对段氏《说文解字注》并不陌生,怎么就仅取自己所需,而对段氏如此重要的纠正《说文解字》中衍文与评说《毛诗正义》阐释不当的那番话视而不见呢?
或是姚教授真没读过段氏原著,他引用《说文解字注》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或是他虽读了段氏原著,却并不赞成其见解,所以他才在找寻他心中理想的雎鸠时对段氏之言故意回避。他根据《毛传》谓雎鸠为“王雎”,凭“王通训‘大’”断定它是一种大鸟;根据许慎《说文解字》“鷢,白鷢。王雎也”断定它是一种白色的大鸟;根据朱熹《诗集传》“雎鸠,水鸟,一名王雎”断定这是一种大型水鸟。他还根据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鷕鷕”,断定雎鸠“是一种褊喙的大型水禽”,经联系“鷢,白鷢。王雎也”而指出“其毛羽白色,所以不会是褐色的大雁”。最终是:“综合考量,(雎鸠)非天鹅莫属。”这样的推论也太主观牵强了吧!
雎鸠真的“非天鹅莫属”吗?我看未必。下面说说未必的几点理由:
首先,天鹅在先秦时代的称谓是“鸿鹄”或“鹄”,而不是“王雎”。《孟子·告子上》“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庄子·天运》“夫鹄不日浴而白”便是证明。甚至“鸿”也是天鹅,《辞源》释“鸿”㈡:“鹄,即天鹅。《诗·豳风·九罭》:‘鸿飞遵渚。’三国吴陆玑疏:‘鸿鹄,羽毛光泽纯白,似鹤而大,长颈……今人直谓鸿也。’”天鹅不属鸠类,这是普通常识,因而古人从来没有把雎鸠与天鹅混为一谈。据此,雎鸠能是天鹅吗?
其次,天鹅喜欢群体活动,而《关雎》里的雎鸠则是雌雄一对儿关关和鸣,互诉衷肠。天鹅求偶的方式主要是靠肢体语言,雌雄趋于一致地做出相同的动作。伴侣间体贴地互相梳理羽毛以示恩爱。天鹅的生活习惯及求偶方式与雎鸠也不符呀!
又次,天鹅的鸣声与“关关”不类。天鹅分许多种,鸣叫声也不尽相同。拿白天鹅来说吧,飞行时鸣声拖得稍长,有如“嘎哩——嘎哩——”,秀恩爱时先发短促小声再提高嗓门,有如“谷谷谷皋,谷谷谷皋”,而且雌雄不同,季节不同,表达需要不同,鸣声也有差异。郑樵“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鷕鷕”,不过是就其大略而言;具体到某种禽鸟身上,则当别论。譬如“喙褊”的鸭子,母鸭鸣声清脆响亮,公鸭鸣声则低沉嘶哑。有了“公鸭嗓子”,你说鸭子在求偶时能“关关”和鸣?这也有点可笑吧!
最后,回到《关雎》一诗的内容上。该诗的主人公是一个采荇菜的男子,雎鸠鸣叫的地点则是“在河之洲”,而姚教授的解说在引用《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之后,断言“人们能够在‘两涘渚崖间’听闻河中沙洲上雎鸠之和鸣,目睹其雌雄相随的优游之态,则必为形体硕大,鸣声响亮的雁鹅类禽鸟”。把一个男子变成了“人们”,且剥夺了该男子到河洲上活动的权利而把听闻雎鸠和鸣的地点搬到了庄子寓言里的“两涘渚崖间”,这种解说显然偏离原诗意境。再说,“百川灌河”有那么大的阵势,自然少不了与之相应的水声,人们在“两涘渚崖间”怎么听得见“河中沙洲上雎鸠之和鸣”?“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人们又怎么看得清天鹅“雌雄相随的优游之态”?姚教授的解说也不符生活逻辑啊!
综上所述,“雎鸠必为天鹅”的判断不能成立。
下面,就“‘雎鸠’为何鸟”的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雎鸠,除《诗经》外,《左传·昭公十七年》也有记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
五鸠,既是官名,也是对鸠类的划分。它说明鸠有多种,雎鸠只是其中之一。
雎鸠既然是鸠之一种,那么我们最好是在鸠类中去寻找它名称变换的蛛丝马迹。扬雄《方言》提到过大小不同的鸠:

扬雄《方言》也说到了鸤鸠。说是各地叫法不同,有“鶝抟”“戴鵀”“戴南”“鶭鸅”“戴鳻”“戴胜”“鵀”“服鶝”“举鶝”“艰”等称谓。
看来汉代五鸠的叫法都有改变,虽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鹘鸠”“鸤鸠”的名目,但祝鸠、雎鸠、爽鸠之称已不复存在了。

据此,斑鸠很有可能就是后来人们苦苦寻找的雎鸠。
斑鸠虽是锐喙(尖嘴),但它“咕咕”的叫声却与“关关”相近。尤侗《摊破浣溪沙·春闺》上阕:“愁倚东风唱踏莎。画屏十二自腾那。殃及斑鸠天外去,唤哥哥。”“关关”“哥哥”“咕咕”,一声之转罢了。
斑鸠是常见之鸟,它们不大惧怕人类,可与人较近距离接触。而且总是两只搭伴,成对成双地过着自己悠闲的小日子,春天里特别喜欢一唱一和地咕咕啼叫。河洲上出现它们的身影,也很正常。我虽不敢像姚教授那样斩钉截铁地说“必”、说“非……莫属”,但至少说《关雎》里的雎鸠是斑鸠要比说是天鹅有理有据。
[1]姚小鸥:《〈关雎〉兴象及其文化内涵》,载《光明日报》2021年8月16日第13版。本文引述姚教授言论,均出自该文。
[2]朱熹:《诗集传·序》,中华书局2017年版。[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同。
[4]《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左传》,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引同。
[7]王引之注解《康熙字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8]尤侗:《百末词》卷二,清康熙四年刻,民国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