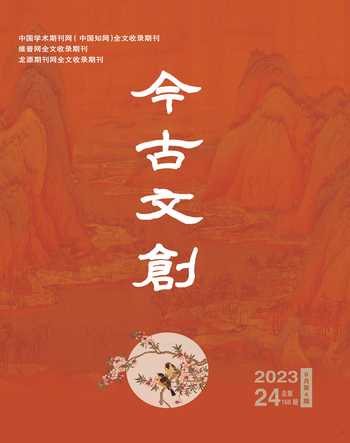凝视理论视角下电影《霸王别姬》分析
【摘要】电影《霸王别姬》是有关两位京剧伶人的故事,影片展示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遭遇,触动人心。电影在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剧中人物角色多处的“凝视”与“被凝视”寓意深刻。本文将在凝视理论的视角下,聚焦于程蝶衣、段小楼、菊仙三位人物,对电影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凝视理论;《霸王别姬》;拉康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4-009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4.030
《霸王别姬》是陈凯歌于1992年执导的一部影片,它在叙述两位京剧伶人的故事时,也对程蝶衣、段小楼、菊仙等主要人物进行了刻画。在电影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凝视”与“被凝视”现象,而这些更是与主体的心理、行为和性格展现紧密相连。因此,本文将采用凝视理论对《霸王别姬》进行分析解读,以求用此理论进一步理解剧中人物并品悟到电影背后的深刻寓意。
一、凝视理论简要介绍
凝视理论也被称为“视觉中心主义”,它侧重于对“凝视”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凝视”展现欲望机制。因此,凝视并非实际的看,而是看的机制下隐藏的关系。凝视理论是当代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萨特、福柯、拉康、劳拉·穆尔维皆对“凝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启发后人。
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曾经从存在主义的视角表明了观者与被观者关系中主体的确立。萨特指出在“注视”行为之下,主客体存在相互建构的情况,在“凝视”行为中,主体与客体相互影响。当我注视他人时,我是关系中注视的主体,我存在且自由,然而当他人注视我时,我在被注视的一方,我的存在可能是“异化”的,个体的自我建构在他人观看和社会观看之下,往往变得异常艰难。[1]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也十分关注观看行为对主体的构成意义。在他的众多理论中,镜像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镜像理论中,拉康认为,当处于6—18个月的婴儿透过照镜子的行为,在镜子中认出来“他者”的存在,并将这种“镜中之象”认成自己,从而确立了主体意识,完成了自我认知,但此时镜中的自我只是虚幻的镜像。[2]后来,拉康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镜像理论,提出了“三界”理论。“三界”指的是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而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自我认知处于想象界的层面,此时只是虚幻的镜像。而随着个体进入符号化的世界之中,主体被纳入符号化的社会秩序即象征界(也称为“大他者”)之中。在象征界中,社会的秩序符号使得主体的自我认知动摇,主体被阉割。如果说,处在想象界的镜像阶段的自我认知是我希望在别人眼中呈现的理想自我,那么进入到象征界,想象界的理想自我被来自大他者的自我理想取代。在象征界中,我们必然接受他者的凝视,从而形塑自我,此时的主体是“为他”的,并非必然是我们自身想成为的样子。从想象界到象征界是想象界被符号化的过程。在象征界,主体被符号阉割,所谓的符号阉割,在齐泽克看来是通过令主体感到失去了某样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拥有的东西,实现对情欲的禁止。[3]在象征界失败的地方进行回溯性建构,便能找到实在界的踪迹。拉康有关实在界的思想主要来自齐泽克的解读。实在界就其本质而言,它既不同于想象界有“镜像”,也不同于象征界,它代表空无。实在界是存在的一个创伤性内核[4],这种创伤性内核会由于主体在符号界的种种限制而被压抑,这些被压抑的客体是不为象征界所代表的社会秩序所接受的“残渣”,他们是主体被压抑时所产生创伤性欲望的成因。他们被压抑但并不会消失,他们被称为客体a,存在于实在界中,是欲望客体—成因。客体a作为欲望客体—成因,会不断吸引主体去满足被压抑、不被社会秩序所接纳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客体a往往驱动主体构建幻象,在幻象中实现欲望的满足。需要注意的是,实在界虽然很难察觉,但有时仍能在符号界中找到它的影子,“创伤性回归”即是实在界显现的一种方式,它是指被社会—符号秩序从现实表层抹除的否定性存在,以幽灵般的方式回返并宣示他们的权利,他们闯入现实,他们的爆发将打破日常生活的平衡和秩序。[5]
福柯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萨特和拉康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凝视”和知识、权力的关系。虽然其未对凝视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研究,但是他在对学校、医院、监狱等机构展开分析时,已深入到“看”的问题即背后的权力问题。他对全景敞式监狱的思考体现了“看”背后的权力属性。
与其他几位理论家不同,劳拉·穆尔维站在了女性主义的立场上,用凝视理论分析女性,她着重于对电影的分析,在她看来,当今好莱坞电影普遍存在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这与男性的窥视癖联系密切。主流电影往往站在男性视角,将男性放在注视者的位置上,对女性予以凝视。
以上是对本文涉及的凝视相关理论的简要介绍,基于以上理论,以及对以往研究《霸王别姬》文章的分析,本文将对剧中人物角色及镜头进行具体分析。
二、被凝视中的认知错位
影片中的主角程蝶衣原名小豆子,母亲是一名妓女,在年龄尚幼之时,小豆子便被母亲送进戏班学戏。年岁尚小的小豆子初入戏班,便被戏班孩子捉弄调侃,接受“窑子里的”这一来自他人的凝视,而敏感且自尊心强的小豆子则以烧毁“窑子里的东西”——母亲的衣服来试图与其出生地划清界限,重塑自我认知。但这一斩断出生地联系的行为也使年幼的小豆子在现实和心理上都彻底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安全感缺失。此时戏班里师兄小石头(艺名段小楼)却对他犹如兄长一般照顾有加,成为其在戏班可依靠的对象。
小豆子作为一个9岁的男孩,对自身性别有着清晰的认知,但其所处的戏曲行业对于伶人在戏中扮演角色的性别认定并非根据现实中伶人生理上的性别而定,戏曲行业有自身的一套评价规则与秩序,主体身处其中需要通过认可社会的秩序符号而获得自身的统一性。戏曲行业独特的规则与秩序设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认定为象征界,即“大他者”一般的存在。小豆子踏入戲曲行业,便须服从戏曲行业的规则秩序,因外形上清秀、瘦小等原因,在戏曲行内人看来,小豆子更适合唱旦角,他须接受在戏曲中女性的性别认知。但他坚固的性别认知使其抗拒来自行业的凝视,忍受惩罚痛苦坚持唱“我本是男儿郎,不是女娇娥”,拒绝异化。此时他承受双重折磨,不仅承受练戏时肉体鞭打之苦,心理上自我性别认知也同时受到来自行业的“凝视”。
双重受创使小豆子萌生逃跑的想法。便与小赖子溜到街上,看剧院的伶人唱戏。剧院里,当红的伶人正以楚霸王的扮相唱着《霸王别姬》。戏曲中楚霸王的重情重义使小豆子受到震撼。电影镜头在小豆子和楚霸王脸上来回切换,在来回切换的镜头间,小豆子与楚霸王完成了第一次对视。电影中,该段表演虞姬并未出场唱戏,且小豆子有着坚定的男性性别认知,此时镜头给了楚霸王脸部以正面特写,仿佛以小豆子的视角与楚霸王正面凝视,小豆子凝视着楚霸王,深为楚霸王的情义与精神品格所感动,此时他的欲求是做楚霸王而非虞姬。愿做楚霸王,重情重义,两人互相扶持,从一而终,楚霸王身上的品格气概,使小豆子自小缺失的依赖感、安全感得以弥补。成为楚霸王的念头也促使他最终决定返回戏班,继续演戏,只有返回戏班学戏才能离楚霸王更近一步。
然而返回戏班意味着仍需受制于戏班行业规则秩序构成的象征界,离楚霸王更近一步却只能扮演旦角,永远成不了戏中楚霸王,自我性别认知在戏曲行业代表的象征界中不断被分割,最终妥协,唱出“我本是女娇娥,不是男儿郎”一句。由此,主体最终被阉割,在他者的凝视下被迫调整了对自身的“观看”和“刻画”。然而主体受到符号界种种符号限制压抑,楚霸王这一给主体留下深刻印象的形象却并未消失,潜藏进实在界中,促使产生创伤性欲望,为满足“是男儿郎”、成为楚霸王从一而终的欲望,主体在“引诱”之下建构起自身的幻象。
齐泽克认为艺术和现实都只是一种符号再现,或者说是主体建构的幻象,从此种角度看,戏曲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身便是幻象的“最佳栖息地”[6]。在往后程蝶衣唱的众多戏曲中,程蝶衣虽然无法扮演霸王,却扮演了《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此曲也成为其构建自身幻象的场所,虞姬的身份无法使其成为楚霸王,却至少使其从一而终的欲求得到满足。“师哥,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程蝶衣渴望与段小楼唱一辈子戏,做一辈子虞姬与霸王,从一而终。程蝶衣始终陷于幻象之中,戏与现实不分,生活如在戏中,唱戏如在生活。
在现实中,实在界与现实存在悖论性的两面,一方面需要将“成为楚霸王”这一欲望客体从现实中移出,这样现实秩序才不会被打乱,现实才会被框定。但另一方面,实在界支撑着日常生活的平衡,现实感需要服从超我的律令,“一小片实在界”可能是偶然的,但却被主体视为一种支撑。[6]现实戏曲行当中,“虞姬”并非程蝶衣的唯一角色,程蝶衣也并非虞姬的唯一扮演人。但程蝶衣将自身与虞姬相连,“我就是虞姬”“我与霸王从一而终”,这一幻象的构建,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程蝶衣从一而终的欲望,也因此使得程蝶衣在现实戏曲表演中将虞姬扮演得活灵活现,支撑着现实的平衡。
但正如前文所言,实在界在与符号界的复杂关系中,并不仅仅通过“一小片实在界”显现自身存在。另一种方式更为激进,正如第一部分理论介绍中所言,实在界可作为创伤性的回归,闯入现实,破坏日常生活的平衡。借用齐泽克《皇帝的新衣》的例子,穿着新装上街游行的皇帝,被所有人认为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但其实是裸体,唯独一个小孩说出皇帝裸体这个事实,在所有人承认皇帝新装构成的场域形成拉康的“象征界”,所有人受制于皇帝权威的恐吓,不敢说出真相时,天真无邪的孩子却使自己作为实在界留存在象征界的楔子,点破真相,使所有人来到实在界。[5]在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在人戏不分的状态中度过几十年,其间历经北洋政府、抗战等多个时期,饱尝人情冷暖,屡遭背叛伤害。几十年的唱戏生涯,同为伶人的程蝶衣和段小楼呈现完全不同的状态。相比于程蝶衣的人戏不分,段小楼始终将现实与戏划分出清晰界限,“唱戏得疯魔,不假,可要是活着也疯魔,在这人世上,在这凡人堆里,咱们可怎么活”“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段小楼很清醒,他仅把唱戏当作谋生手段,对戏曲艺术探讨不感兴趣,唱完戏即抽身回到现实世界享乐。而程蝶衣热爱戏曲,在戏曲中满足自身对“从一而终”的执念。段小楼的清醒,从某种意义上使得他成为实在界嵌入圍绕程蝶衣而成的象征界中的一点。当在十一年后,再次与程蝶衣重逢之时,此时在几十年唱戏中形成的所有人都默认的程蝶衣“女儿身”扮相的象征界中,段小楼一句“本是男儿郎,不是女娇娥”点破真相,使程蝶衣如梦初醒,来到实在界。前文中有言,现实中我们需要将小客体移出才能框定现实,实在界一旦溢入现实,即符号界的主体一旦“知情太多”,现实的平衡将被打破,主体则无法保持常态[6]。段小楼一句话彻底点醒了程蝶衣,“我本是男儿郎,不是女娇娥”,幻象被打破,我本是男儿郎,不是女儿身的虞姬。主体直面幻象的空无本质,他不是虞姬,而多年的背叛伤害也使他直面段小楼扮演的楚霸王,段小楼终究也不是《霸王虞姬》中的楚霸王。此时作为符号界主体的程蝶衣“知情太多”,无法保持之前的“常态”,而他以男儿身,成为楚霸王,择一人而终的欲望在现实符号界中又难以实现,处处被限制。自我终究土崩瓦解,主体走向“疯癫”。
纵观程蝶衣几十年的唱戏之路,皆由他者凝视下的认知错位酿造,他者凝视下的性别错认,不被象征界秩序接纳的欲望的压抑与幻象的建构,成就了风华绝代的“虞姬”,也为拔剑自刎的结局做了铺垫。
三、他者凝视与自我建构中的女性
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都处于较低的位置,女性的主体性被瓦解,被男性、社会所压迫,毫无疑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始终处于被凝视的状态。[7]电影《霸王别姬》中女性角色并不多,而菊仙作为其中较为突出的女性角色,本身极具分析价值。以下将围绕菊仙,来分析电影中对女性的凝视,以及女性在这种凝视下的自我建构。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行走于充斥着男权观念的社会中,必然会受到社会秩序父权化的影响,而社会对于女性的凝视也会显而易见地影响到女性的认知。
菊仙这个角色作为电影中少有的女性,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其特殊性来自其“妓女”的职业,在那时也俗称“下九流”的存在,这本身会受到他人的歧视。这意味着菊仙不仅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女性群体中,她也是被鄙视的存在。作为一个边缘人物,其既作为女性,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下,也作为妓女被整个社会居高临下地凝视。影片中她的现身场所一开始便是妓院,在妓院中遭调戏后被段小楼承诺娶回家。于是菊仙掏出自己近乎全部家当找到老鸨为自己赎身,老鸨对她的行为极为轻蔑,“你当出了这门儿,把脸一抹,你还真成了良人啦,你当这世上狼啊虎啊就都不认得你啦?”“我告诉你,那窑姐永远是窑姐”,老鸨的这些话一句成谶。菊仙虽然为自己赎了身,从良跟着段小楼。但是社会对其凝视的目光并未改变。剧院的马老板还用妓院称谓称其为“菊仙姑娘”,程蝶衣直言其为“妓女”。即使在成为段小楼的妻子,嫁做人妇之后,段小楼的师父仍面露轻蔑“哟,您是花满楼那姑娘不是”,在社会的凝视之下,曾经的“妓女”身份标签必将跟随她一生。
她努力做一位好妻子,为丈夫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分担责任。影片在刻画菊仙时,巧妙地运用了两个相互呼应的镜头。一个是菊仙正式嫁给段小楼当晚,她坐在梳妆镜前,一身红嫁衣,带着出嫁的耳饰和珍珠项链,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带着终有归属的踏实感“不唱戏了,往后啊,我太太平平地跟你过日子”,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在与镜中自己对视之中建构起了“妻子”的身份认知。但在段小楼眼中,菊仙虽为其妻子,但自始至终于他而言只是一个附属品般的存在,菊仙在段小楼与程蝶衣的师父惩罚他们时插嘴,立马受到段小楼的呵斥和掌嘴“老爷们的事,没你说话的份”“我他妈打死你”,在段小楼的眼中,菊仙从来并非平等的存在,可以随意动手辱骂,在这一段掌嘴中,段小楼挽回了面子,在对菊仙的轻视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中树立了男性权威。与第一个镜头相呼应的第二个镜头,发生在程蝶衣被抓,菊仙流产后,菊仙决定帮段小楼说服袁四爷出手救程蝶衣之前,此时菊仙与段小楼进行了谈话,孩子没了,她只剩下段小楼可依靠,在得到段小楼救出程蝶衣后便与其划清界限的承诺后,她决定帮段小楼一把。在临行前,她再次透过梳妆镜凝视镜中的自己,此时她身穿一身白色旗袍,佩戴着出嫁那天的珍珠项链和耳饰,凝视镜中自己,流露一丝愁苦和担忧,她不断抚摸着出嫁那天所戴的首饰,对“段小楼之妻”的认知隐隐产生动摇之后又再一次坚定。最终外出前往袁四爷家,通过自己的聪明头脑和高明的谈判策略帮助段小楼说服了袁四爷。
菊仙这个角色是复杂的,她曾为妓女的身份被社会所不耻。但她随后从良,嫁作人妇协助丈夫操持家庭,与此同时,又善于察言观色,有聪明的头脑和谋略,能屈能伸,有能力也识时务,这些都远非段小楼所能比肩。然而她所有的能力和才华皆被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凝视掩盖。在社会的凝视中,她是妓女出身。在段小楼的凝视中,她是可以随意辱骂轻视的存在。她一次次在镜中凝视自我,坚定对于“妻子”这一身份的建构,因而终究没有跨出丈夫的“半径”,并成了丈夫眼中附庸般的存在,最终被摧毁于社会和男性的凝视之下,心灰意冷,结束悲剧的一生。
菊仙的悲剧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凝视与剥削,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其依赖、仰仗丈夫心理背后当时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一种凝视的转化。
参考文献:
[1]蔡圣勤,何马楠.电影《乱世佳人》凝视理论三个层次分析[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03):94.
[2]孙峰.“凝视”理论与女性主义电影研究[J].电影文学,2018,(24):23.
[3](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8—19.
[4]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40-441.
[5]刘明明.拉康的凝视理论与个体的主体性建构——以娄烨电影《推拿》为例[J].衡水学院学报,2015,17(06):125.
[6]张婉婉.齐泽克凝视理论研究[D].辽宁大学,2022.
[7]席嘉敏.凝视与反凝视:《沉默的羔羊》中的女性意识[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1,41(07):238-239.
作者简介:
李元嘉,女,湖北荆门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2021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