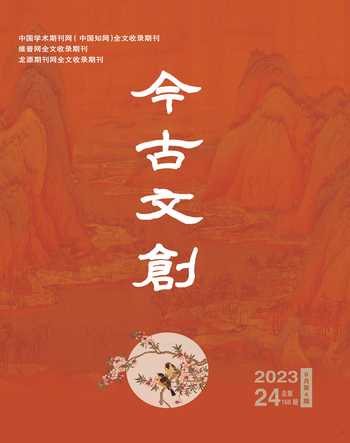语言文化学视阈下俄汉语中“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概念对比分析
徐心航
【摘要】“概念/概念世界图景”是语言文化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已成为语言文化学界的研究热点,是各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界普遍采用概念分析法对某一概念进行系统且详细的研究与分析。分析一个民族的概念世界图景,是掌握各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民族对于一件事物的认知和态度,从而进一步研究其文化背景。“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是俄汉语中共有的概念,通过俄汉语中“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概念的对比研究和分析,能够发现俄汉民族语言世界图景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减少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语言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
【关键词】语言文化学;俄汉对比;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概念世界图景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4-013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4.041
对于词语概念的研究往往会涉及词语的内部形式,内部形式是由組成词语的词素所构成的字面意义,词汇的语义发展导致内部形式可能会逐渐模糊暗淡,被人遗忘,或者与词的词汇意义产生矛盾,所有的内部形式都存在于派生词语义中,这似乎是语言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是研究对象在过去的认识痕迹,其意义能够被创作者所理解(Н.Б.Мечковская,2001:15)。
一、“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日常生活概念和科学概念
在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初阶段,对于事物的称名往往取决于事物最本质的外在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理解能力的提高,事物的指物意义和概念意义会产生分离。在认识一件事物时,我们将其分为日常生活概念和科学概念加以分析,前者不带有抽象分析的过程,往往能够体现出人类对于一件事物最直观的感受和认知,同时能够体现出人类对其最朴素的理解与认识,而科学概念则是有关实际事物类别的抽象信息。
(一)俄语близнецы的概念分析
要想研究一个概念及其文化语义,就要先了解其原本概念和内部形式,再加以延伸和使用。
1.词源分析
俄语单词близнецы是由一个古老的斯拉夫形容词близный组成的,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接近”。确实,从表面特征来看,没有比孪生子更亲密的了,他们一起在母亲的子宫里待了近十个月。
2.俄语близнецы的日常生活概念
близнецы在莫斯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的释义为:“Дет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рожденные одной матерью.”(С.И. Ожегов,1975:50)即同时由一位母亲生出的孩子。在该词的释义上,用比较通俗直观的方式描绘出其最基本的特性。
3.俄语близнецы的科学概念
普罗霍洛夫(А.М.Прохоров)主编的《苏联百科词典》(?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以下简称《百科词典》)对близнецы的解释即从其科学概念出发,做出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在《百科词典》中该词有三个不同领域的基本意义:
①人类或哺乳动物几乎同时产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后代,存在同卵孪生子(一个受精卵)和异卵孪生子(两个或两个以上卵子同时受精);
②两颗相互靠近的明亮恒星——波拉克斯和卡斯托,双子座,以苏联的纬度在秋天、冬天和早春都能看得很清楚;
③孪生素数,指相差2的素数对,例如11和13。(А.М. Прохоров,1986:63)
(二)汉语“孪生子”的概念分析
1.词源分析
“孪生子”一词在汉语中最早出现在《扬子·方言》:“东楚闲,凡人嘼乳而双生,谓之釐孖,秦晋闲谓之僆子,自关以东谓之孪。”(周祖谟,1994:7)早在西汉时期,人们便对于“孪生子”有了比较初步的认识,“人和哺乳动物所生的成双的后代”是当时人们对于“孪生子”的解释,在不同的地区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呼,在山海关以东的地区对其称呼为“孪”。
2.汉语“孪生子”的日常生活概念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孪生”一词为形容词属性,释义为“(两人)同一胎出生,通称双生。”(江蓝生、谭景春、程荣,2012:850)在日常生活概念方面的理解中,中国人对于“孪生子”的认识变化并不大,认为其所指为同一胎出生的两人。
3.汉语“孪生子”的科学概念
“孪生子”的科学概念为:“一胎双生的婴儿,也称双生儿。约占总分娩数的1.2%。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各占1/3和2/3。前者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成的两个个体,后者分别由两个受精卵发育而成。”不难看出,这一解释已经脱离了所有汉语使用者都能够理解的释义方式,而是运用更加科学抽象的方式解释了“孪生子”一词。
二、俄汉语中对“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认知和理解
语言被认为是文化“天然的”基础,文化产生了语言的方方面面,是认识精神世界变化的工具和巩固民族世界观的方法。自70年代以来,术语“民族性”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这一词被视为一种群体现象,是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组织方式:“种族不是选择的,而是继承的。”(С.В.Чешко,2001:13)。因此,对于一个单独的词语“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不同的民族对其认知和体现在文化上的表征也有所不同,在将两者进行对比时,我们不仅仅能看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继承性,还能够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两者之间意识、民俗、传统之间的不同,从而深入研究中俄的精神面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一)俄语中对于близнецы的认知和理解
1.古代俄罗斯人对于близнецы的认知和理解
古时俄罗斯各民族对于близнецы这一自然现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本民族所熟知的神话。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文本仍未完全流行的古代,神话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和思想继承的手段,瑞士心理学家荣格(К.Г.Юнг)曾提出原型(архетип)这一重要概念,他在遗传学理论框架中指出,原型与神话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神话是原型的储所。原型是一种固定形象,这种形象普遍地出现在个人意识中并在文化中有着广泛传播(С.Сендерович,2001:24)。对于原型,荣格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本能与无意识》(《Инстинкт 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中有较为清晰的阐释:所有人都拥有下意识构成一些普遍象征——原型的能力,这种原型存在于梦境、神话、童话和传说中。荣格认为,原型是作为“集体潜意识”表现出来的,即这种潜意识的部分不是个人经验的结果,而是人们自祖先那里继承的(Маслова.В.А,2001:6)。
在很多文化中,孪生子被认为是文化主角、神话人物、奠基人、创始者、不同社会群体的祖先。在俄罗斯东南部的阿穆尔地区的传统文化中,孪生子的诞生被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现象,因为女性与超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建立在动物先祖的精神之上的,在传统的阿穆尔文化中,孪生子的生前和死后都受到尊敬,他们的灵魂被送到他们超自然父亲的世界(上文中所提到的动物先祖)。在孪生子死后,对他们的崇拜扩展到仪式塑像(通常是由木头制成),例如,萨哈林区边缘博物馆保存着威尔特孪生子标志性雕塑的单独样本:阿达乌孪生子的人形护身符。在传统文化中大多数阿穆尔民族认为孪生子的诞生对整个群体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被认为是女性善良的精神与熊或老虎形象的结合(И. И.Галечко,2019:69)。
如上文所述,古时有关孪生子的神话故事并不十分完整,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人们的典礼仪式、习俗中得知,当时的俄罗斯人对于未知的超自然现象怀有一种敬畏和尊重,同时能够看出古时的俄罗斯人对于美好精神的歌颂和追求以及其想象力的丰富。这些当时人们对于孪生子这一现象的看法也随着很多习俗和仪式流传了下来,很多被运用于文学创作当中,也成了研究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對象。
2.科学发展时期对于близнецы的认知和理解
在认知水平逐渐提升的19世纪、20世纪,人们逐渐了解和认识了孪生子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不再将其奉为鬼神之说,但是其代表善恶对立的分裂意象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正因为了解了близнецы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人们不再将其视为一种超自然现象,而是会利用以往的意象将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过去的典礼和神话也成了保留民族文化和对于这一现象看法的痕迹。
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著作《萨哈林旅行记》中有如下描写:“据说,萨哈林的气候特别适合于妇女受孕,老太婆在这里都能生育。甚至在俄国被认为是没有生育能力,不敢指望生孩子的女人,也能受孕。好像女人们都急于要使萨哈林人丁兴旺起来。还听说,孪生子是常见的事。”(契诃夫, 2022:623)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孪生子形成的原因,虽然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把孪生子这一自然现象的出现与气候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根据神话和典礼将其与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
(二)汉语中于“孪生子”的认知和理解
1.古代中国人对于“孪生子”的认知和理解
与上文中所提到的古罗斯人对于孪生子这一现象的态度相似,古代中国人同样是将孪生子视为一种值得敬畏的超自然现象。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往往将孪生子的诞生视为一种不祥与禁忌。这同样也与自古流传的神话以及能够体现这些神话的典礼和仪式有关。由于地理和文化环境不同,中国人相对于俄罗斯人往往更加含蓄和谨慎,因此对于未知和不确定的事物往往抱有恐惧和不理解的态度。
彼时的人类在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很可能已经认为自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然,因此试图与自然和普通的动物进行区分和辨别。正是由于认识水平尚且底下,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也是哺乳动物的一员,认为通常只有动物才会产下多个后代,因此对于这种现象存在一定的抵触心理,自然就会在大家的排斥中发展成一种禁忌。
此外,古代孪生子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中也是不详的存在,《易经》中记载:“一为阳,二为阴”,古人认为一胎双生阴气很重,降生后便会相冲。这其实也与中国人认为阴阳相对有关,而这一认知也为后世人们将孪生子作为两种秉性的对立放入文学作品中做出了铺垫。
以上的多种原因使得中国古代对于孪生子的态度是排斥甚至禁忌的,这些态度与民族文化、神话传说、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2.近现代中国对于“孪生子”的认知和理解
在科学发展和认知水平有所进步的近现代中国,孪生子的形成规律同样也被人们所了解。而中国人历来就有着希望多子多福的愿望,早在《诗经》中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的描写,来表达对于子嗣繁盛的愿望的描写,所以一旦人们摒除了对于孪生子的未知恐惧,孪生子的降生便成了值得一个家族喜悦的事情。
除了大众对于孪生子的认识的改变,很多作家也如俄罗斯当时的情景一样,将孪生子这一有趣的现象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
(三)俄汉语中对“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认知和理解的对比
从上文的分析和描述中可以看出,在一定时期内,中俄对于“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在认识水平低下的古代,中国古代对于孪生子是持有禁忌的态度的,而大多数古代俄罗斯人则认为,孪生子是祥兆,人们对孪生子往往比较尊重和敬畏,这种敬畏甚至延续到孪生子死后的风俗和他们的母亲身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性格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一件事物,即使持有相似的认知(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都认为孪生子是一种超自然的現象),也会由于文化环境的不同对其抱有不同的态度。
三、俄汉语中“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概念的文化语义分析
文化语义包含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概念上的差异,也包含因语言文化影响对某一事物产生的独特含义及情感评价。而分析“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分别在俄汉语中的文化语义及其在文化中的应用情况,而文化语义的体现往往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不仅能够为人所理解,也有一定的隐喻功能以表达作者想要在作品中传递的思想。
文化对语言来说并不是同构的(完全相符),而是同态同形的(结构上相似),因此在现代两国人民都已经了解了“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形成原理并不再为此感到恐惧时,仍然有过去的意象被保留下来,在文本中展现其文化语义。
“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在中俄两国的文学作品中并不是一个非常受人瞩目的文学意象,但是部分作品中也会出现这一意象,很多以“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为主人公或者重要人物的小说都以一种比较独特又简单易懂的方式传递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下面我们通过中俄文学作品来分析中俄“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这一对象的文化语义。
(一)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孪生子”意象
相对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来说,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孪生子”意象通常是较为明确的,作家通常是以分别独立的孪生子个体作为描写对象,但是如上文所述,这些人物虽然有着相同的基因外貌,但是性格气质却截然不同。
在《西游记》中,就出现了相当于“孪生子”的描写。在第五十七回《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眷文》中,便出现了主角之一孙悟空的“孪生兄弟”六耳猕猴。原文中对于六耳猕猴的描写是:“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者,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六耳猕猴与孙悟空外貌完全相同甚至也如孙悟空一般神通广大,但两人性格完全相异。孙悟空虽原是妖猴但对师父谦和知恩,但六耳猕猴却顽劣粗鲁,在两人言语冲突之间甚至要“打杀”唐三藏。作者以此突出孙悟空对待师父的真心,并由此师徒二人建立了更加深厚的信任。但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第五十八回的章节标题为“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迹灭”,似乎是在暗示六耳猕猴是孙悟空分裂出的心魔,这与俄罗斯作家对于“孪生子”意象的应用不谋而合。
除了中国古代名著以外,受到广大中国人欢迎的经典武侠小说中也不乏将“孪生子”作为主角加以描写。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和古龙都描写过孪生子主角,金庸的《侠客行》和古龙的《绝代双骄》都是以自小分离的孪生子为主角,这些主角拥有相同的容貌,但是由于生长环境不同,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在将孪生子作为主角或者描写孪生子时,通常会将其确定为两个明确的相互分离的主体。而且通常来讲,作为孪生子的主角都有着相互对立的性格,这种性格并非简单的善恶之分,而是更加具有个性化的区分。中国作家在应用“孪生子”这一意象时,更注重的是强调平衡,同时利用外貌相同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来引起误会,进而制造戏剧冲突,不仅能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还能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二)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孪生子”意象
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孪生子”的意象出现得更早,这很大程度上与早期俄罗斯人对于孪生子现象的崇拜态度有关。早在11世纪的《往年纪事》中就出现了孪生子的原始模型,而其作者涅斯托尔(Нестор)于11世纪70年代至12世纪初期又写就了《鲍里斯与格列布传记》,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鲍里斯和格列布是双胞胎兄弟,但是其代表的宗教神圣性和两人不论是在艺术作品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相似,都很突出地表明了早期俄罗斯人对于孪生子的崇拜心理。
而在19世纪面临社会变化的俄国,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分身现象”变得突出了起来,我们不妨将其视作близнецы的一种变化形态。当时的俄国面临着社会改革和人们寻求自我的压力,很多人会与自己的内心产生非常严重的矛盾冲突,而很多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表述,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心理描写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双重人格》中的主人公戈利亚德金是一个九品文官,拥有双重人格的矛盾体,他不擅长投机取巧,也不屑于做这种事,而内心深处又非常羡慕八面玲珑,能通过阿谀逢迎而获得高升的人。
虽然俄罗斯文学中的“близнецы”与中国文学中的形象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孪生子形象虽然在性格气质等方面有一定的对立,但是文章整体讲求的往往是平衡,这符合中国传统思维中阴阳平衡,文学作品的最后是通过平衡和调节两者各自的特性而走向一种和谐的局面;而俄罗斯文学中的孪生子(或“分身现象”),除了有高度统一的情况之外,往往更加注重双方特异之处的矛盾冲突,当然这与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作家往往是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表现出当时人们的内心的压抑,以寻求改变之法,传递先进思想,推动社会进步。
四、俄汉语中“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隐喻
在定型这一概念中,有一个概念分支“准定型”又称“类定型”(квазистереотип),专指那些“与异文化大致吻合”但“又有原则性细微差别”的定型。(赵爱国,2006:137)俄罗斯和中国对于孪生子现象的认知也有一个大致统一的方向,但是如上文所说,两者之间由于民族气质、社会环境的不同,也存在着差异,可以加以对比研究。对此我们可以先从“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字形加以入手。
(一)俄语中“близнецы”的构成及其隐喻
根据《俄语词素词典》(《Словарь морфем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的词素构成, близнецы一词由词素“близ(ближ)”和“нец”构成,前者突出的是临近,而后者通常表示一种人,因此在俄语中,“близнец”更加突出的语义为相近、亲近的语义。
(二)汉语中“孪生子”的词语构成
当我们将“孪”字进行拆解時便会发现,“孪”由“亦”和偏旁部首“子”组成,“亦”字在中文里的释义有“又”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将“孪生子”理解为“又一”“再一”出生的孩子。在汉语中,对于“孪生子”强调的多为双重这一语义。而双重的两件事物通常为一致或者对立的,所以除了在准定型下使用“孪生子”描述非常相似或者相近的事物,也会通常使用这一意象描绘拥有对立特点但性质相同的事物,预示二者对立统一、此消彼长,共同成就一个整体,这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调和、八卦两级等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结论
语言学处于人类中心范式的指导之下,人们摒弃了过去由于未知而对孪生子现象产生的恐惧或崇拜心理,不再将其视为一种现象或者预兆,而是将孪生子看作普通人类,并不给予他们或高或低的待遇。不仅如此,受到了人类中心范式的影响,人们对事物进行认知或命名是以人的特点为中心进行,但是因为汉语中“孪生子”的特指性较高,指代的就是“同一胎出生的两人”,相比较之下близнецы被用于更多的指代,因为其特点是相近。在人们对自身以及自然科学的进一步了解之下,“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成了非常易于本民族理解的隐喻工具,甚至也能够为异文化民族所理解。
通过对比分析,中俄民族对于“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的理解认知及其在文化中的应用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通过对“близнецы/孪生子”这一意象的研究,我们不仅仅了解了中俄对于其词义理解的异同,也通过这些内容了解了两国的社会特点和民族气质,这能够帮助人们将两国的文化求同存异,更好地进行交流和发展。
参考文献:
[1]Викторович.Ж.С.,ОНекоторых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х Дуальных Образах В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J].УДК821.16101,2018.
[2]Галечко. И. И.,Культ Близнецов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Амур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J].?Вестник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Шолом-Алейхема?,2019(35).
[3]Маслова. В. А.,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M].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Академия》,2001.
[4]孟慧丽.双生意象与“复制”母题[D].首都师范大学,2006.
[5]张松.孪生子禁忌和崇拜的民族学解释[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20,(3):122-130.
[6]赵爱国.“定型”理论及其研究——文化与认知空间双重语境之阐释[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0):7-11.
[7]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8]郑体武,王宇乔.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分身现象[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82-88.
[9]郑小芳.俄罗斯文学中的分身现象[J].文学教育(上),2020,(10):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