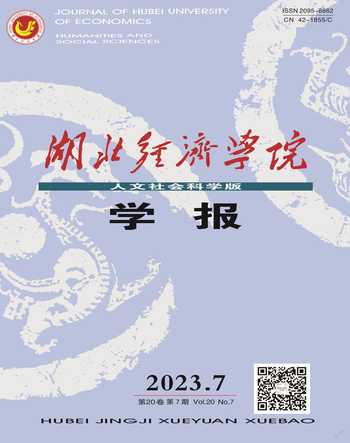社会工作破除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有效机制研究
杨竹茹
摘 要:基于增能理论,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方法,探究了社会工作参与改善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的有效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在介入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过程中存在反被扶贫对象依赖的“悖论”。需要从与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心理帮扶和构建熟人社会网络等三个方面出发,以确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问题。
关键词:社会工作;福利依赖;增能理论;有效机制
一、引言
福利依赖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建立之初,身体强健的流民被认为是“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却仍会得到社会救济,人们认为这些身体康健的流民不劳而获,依赖社会救济。英国社会救助制度之初的福利制度饱受各方诟病不已。20世纪70年代末乔治·吉尔德在其著作《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首次提出福利依赖[1]。在社会进程中,福利依赖被公众认为是接受公共救助项目的受助者会产生依赖心理,使得受助者意志消沉,甚至会产生异常的价值观和消极的生活态度[2]。中国自1999年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来,扶贫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建立[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与2014年5月《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更是代表我国扶贫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从“广覆盖”向“全覆盖”转变[4]。以湖南省为例,截至目前,社会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4.6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41.9万人;已有28711个社区服务站和1393个社区专项服务机构和设施成立运营[5]。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社区化精准扶贫救助建设实践中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重要主体。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思想、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平等互助的理念、以福利为核心的社会服务观,与精准扶贫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其所秉持的系统理论、增能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为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王守颂,2016)[6]。社工介入可让精准扶贫从“增能型”向“合作型转变”,进而提高贫困户的发展能力(李文祥,郑树柏,2013)[7]。从总体上看,湖南省社会工作介入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在助推全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有重要的经验借鉴作用,也是对社会工作发展成果的检视。然而,现剩余贫困人口规模仍旧巨大,致贫原因复杂且对福利政策的心理依赖更加顽固,导致贫困户好吃懒做依赖政策救助的现象依然存在,贫困户对福利救助产生依赖初显端倪。这种怪异的社会现象,不禁让人质疑社会工作对于改善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的有效性。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湖南省长沙县S社区为例,了解社会工作在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中的真实状况,以深入探究专业社会工作参与改善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的可能空间与专业突围。
二、理论视角:从增能视角开展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发展框架
要从理论视角下进行恰适性的观点分析,首先有必要对增能理论应当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进行阐明,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以增能理论为蓝本并符合当前社会工作参与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实践的新型分析框架。
增能(Empowerment)又被译作增权、赋权,巴巴拉·索罗门(Solomon)在1976年其著作《黑人的增能:被压迫社区里的社会工作》中首次提出增权赋能这一说法[8]。增能是指赋予或充实社会个体的权力,增强个体应对环境影响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应该将专业力量发挥于缺乏权能的个体及群体成员身上,帮助他们增加权能,使他们学会应对外在环境的影响,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9]。增能理论逐步变成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中主要的基础理论和社会实践模型,其主要强调对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社工要帮助服务对象提高自身所拥有的社会权能,激发服务对象的自我效能,关注自助与互助。因而,对需改善福利依赖的农村贫困户的增权赋能主要是指对农村贫困户的潜力进行挖掘和激活,寄希望服务对象通过自身力量谋求发展以完成对福利的“戒断”。根据范斌学者对增能层面的划分[10],社会工作者主要是从个人、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个层面建构增能视角下开展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发展框架:
第一,个体层面是社会工作从增能视角开展实践工作的首选,社工的增能实践主要将聚焦在服务对象的个体能动性和自信心的提升。通过激发服务对象的内在潜力让服务对象能提高对环境的适应力,进一步提高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自我能力。在以往对服务对象个体能动性的提升上,主要是针对有关“获取自我财富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帮助农村贫困户尽量脱离政策的扶持,获得提高自我生活水平的自我主导权。同时,试图通过“回顾旁人发家致富”与“你也可以”等鼓励的方式,帮助农村贫困户从身边人的故事中汲取正面且积极的力量,以此帮助农村贫困户确立自信,增强个人权能。
第二,社会工作者试图通过人际层面的增能促使服务对象与身边的人达成合理、良性的互动模式以此提升服务对象的个人权能与自我形象。在农村贫困户家中,其核心交往对象除了来探望的扶贫干部、社工之外,甚少与他人接触,会有一定的落寞与孤独感。针对农村贫困户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問题,社会工作者往往发挥组织者和中介者的角色,通过联络、动员各方资源,为农村贫困户搭建社区支持网络。例如,组织同村贫困户召开交流会,促进彼此的生活了解,鼓励农村贫困户参与同村小组活动,积极尝试与他人接触,拓展同村中的人际关系网来认识新的朋友,通过教服务对象一些人际交往技巧,改善服务对象人际交往不善,人际互动困难的问题。
第三,社会参与层面的增能往往指社会工作者通过“个体主动”与“外力推动”的双向互动模式为农村贫困户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以此激励并强化农村贫困户的权力意识。同时,通过调动服务对象的积极性,促使服务对象借助村里的活动或平台产生自我价值认同并获得优越感与成就感。此外,还能帮助农村贫困户学习一定的知识与生活技巧来实现个人内在的增能以摆脱与社会脱节的不良行为并逐渐良好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增能,社会工作者试图摆脱农村贫困户因自身能力与资源弱而深陷弱者泥潭、不能积极自我增能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往社会工作者主要从个人、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个层面提出和发展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发展框架,但由于部分农村贫困户受教育程度低,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思想。同时受落后文化的影响,相信命运的安排,对扶贫持冷漠态度,从而对社会工作者的助人工作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这种关系体现为农村贫困户事事以社工的意见为中心无法自己做主,试图通过社工“事无巨细”的帮助以达成脱贫的目的,无法真正地形成自助。因此,在借助“增能理论”思想时,要抓住这一理论的核心并把握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背后的内在本质以此来分析改善这一社会现象。在考虑如何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时,要先分析清楚是否对“依赖”进行脱困、能否对服务个体产生自我增能、服务机制等问题。以往研究很少关注对社会工作服务产生依赖从而导致社会工作介入失败的问题,本研究基于增能理论,对实践活动中社会工作介入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行动案例的失败与困境进行分析。
三、直面现实:当前社会工作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困境
(一)案例背景
湖南省长沙县S社区始建于1968年,是长沙县H镇上唯一一个条件极差且存在诸多隐患的社区。其中处于社会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93户235人,占比不足0.6%,但相对贫困人口较多,约占11%。该社区存在着需要社会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管理压力大、风险高等问题,为社会工作能否有效改善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提供现实情景。本文的调查对象为该社区内处于社会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均为汉族普通群众,男女比例为1∶1,家庭户均人口4.5人,家庭年收入在22000元以下,社会救济的原因多为缺乏劳动力或疾病。为满足调研需要,本文主要以S社区社工参与改善5位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服务项目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5位贫困户与相关社工机构工作人员(督导、社工等)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多次参与组织社工服务活动等质性研究方法来获得实证资料,着重分析在两种不同依赖原因下社会工作参与改善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的不同服务逻辑与现存问题,了解其经验与发展态势。
(二)贫困户福利依赖产生的原因
该案例对象来自S社区处于社会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为93户,Q女士就是其中一户。Q女士今年40岁,汉族,初中辍学,家有7口人——身体健康欠佳一直需要吃药的妈妈、弱视的婆婆、残疾的公公、夫妻俩和两个14岁的孩子,其中劳动力仅夫妻俩。Q女士家庭困难,2016年建档立卡为贫困户,目前仍是需要社会救助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在社区领导和社工的帮助下,Q女士仍过得并不舒心且对生活满腹怨言:
一是经济压力与生活压力。镇政府给Q女士家在郊区分了两亩地,为此丈夫在郊区种了两亩玉米。近几年秋季玉米收成每次大约只有2000元,遇上干旱期一季农活下来甚至根本没钱赚。丈夫更是因为种地从来不做家务,家里老人小孩需要照顧,所以照顾家里的负担大多都在Q女士一个人身上。种玉米给家里带来的收益并不能得到相对的经济压力缓解反而生活压力都集中在Q女士身上,心生怨恨。二是受到不公平对待。Q女士觉得社区干部针对她家,受到了差别对待。Q女士听说每年贫困生有3000元补助但自己两个小孩读书从来都只有几百元的补助,她认为社区领导是欺负她家没关系,不给她家小孩办理高额补助,心生不爽。三是扶持力度不够。Q女士认为自己家挣钱又少,又没有提高补贴,除了社区干部和社工时不时地沟通外,隔壁老头家比她家多送了米和油,前一栋某户家多发的沙发和洗衣机她家也没得到,政府不关心她家,因而心有不甘。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Q女士对政府福利存在明显的依赖性,而产生这样的抱怨或那样的依赖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家庭经济困难,养成了依靠别人的习惯;二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对问题的理解不够透彻,逻辑思考存在偏颇;三是缺乏靠自己变好的内在动力,且内心一直存在与他人攀比的不良心理。
(三)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该社区社工机构经过两年多的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项目运营实践,社工针对农村贫困户服务过程中问题逐渐暴露。从实践中可以发现,社工团队难以真正帮助农村贫困户摆脱福利依赖,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工作与原有扶贫方式之间存在极大的落差,社工机构在帮扶方式上缺乏决定权、服务活动上缺乏自主性等。
1. 帮扶方式上缺乏决定权
社工机构原则上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是平等合作关系,应当相互协助一同推进农村贫困户帮扶工作,但由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输血式”扶贫方式的灌输,导致部分农村贫困户习惯了“拿来”式受助方式,如“等”、“靠”、“要”、“懒人群体”等。另一方面,社工很难与农村贫困户建立良好关系且服务活动往往难以开展持续下去,导致社工开展服务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在面对服务对象时处于被动地位。
为了能够继续针对Q女士一家开展服务,社工机构只能“屈身”在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的帮扶活动下再开展折中的活动,反映了社工团队由于帮扶方式上缺乏话语权和决定权,在针对农村贫困户的帮扶过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2. 服务活动中自主性不足
社工机构在这种与农村贫困户看似拥有主动权实则被动的关系格局中开展活动进一步导致社工在服务活动上缺乏自主性。部分农村贫困户属于代际传递式贫困人口,其思想与价值观认为自己无法真正脱贫,“认命式”深陷贫困的泥潭无法走出,这部分农村贫困户使得服务活动的话语权并未真正掌握在社工手里,社工开展服务活动都得和服务对象“讨价还价”,进一步促使社工所开展的服务活动无法实现对服务对象的能力提升。S社区辖区内的社工机构尝试过邀请Q女士来参加活动却被拒绝。
社工开展活动得看服务对象的“脸色”,甚至有时被迫在活动中为服务对象准备礼品才能邀请到服务对象参与社工准备的活动。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社工在服务活动上缺乏自主性、项目资金紧张、服务对象对社工认知程度低等问题,导致社工只能被迫选择妥协以服务对象的物质需求为吸引点安排服务活动,这使得其自身的专业性大打折扣。
3. 良好关系网络难以建立
S社区的社工机构虽然入驻但一直没有打入社区关系网络内部。一方面,社工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并不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没有群众基础未能良好地融入社区中建立起自己的熟人网络;另一方面,S社区居民对外来人员相对不愿接触,特别是谈及家庭等隐私的问题不愿与外人沟通,社工既未能开展全面地邻里间探访,也由于不在一个社区居住缺少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与S社区的居民之间的信任度较低。
服务对象与社工的疏离使得社工始终难以有效提供增能服务,而与服务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恰恰是社工完成服务至关重要的一步。因而目前社工虽然进入社区参与到改善农村贫困户的福利依赖的工作中,却没有完成服务工作的底层基础,这导致社工的工作难以开展并提供有效服务。
因此,当前在解决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问题上出现了多重困境,呈现出了明显的“强专业、弱实践”状态,社工机构在服务活动中难以展开拳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在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问题上依旧需要寻求新出路。
四、有效机制:社会工作破除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的三重维度
社工在服务工作中角色是可以随着实践项目与实践对象的不同而转变的,不仅可以是服务提供者、治疗者,也可以是资源筹措者、能力培训者、关系协调者和倡导者,从而体现社工在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问题中发挥出“增权赋能”的真正作用。
(一)并肩前进:与居委会街道办合作办事
社工机构在入驻社区时需要与本社区的居委会和街道办中相应负责人进行沟通,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与积极和谐的共事方式,使得两拨人的帮扶方式能融合并形成体系。正是积极的互动关系能够在帮扶过程中不仅注重物质方面更能重视心理精神层面。社工机构与居委会、街道办一同针对该社区的帮扶对象逐一进行调研并分析福利依赖存在的原因与帮扶对象的重点需求,根据帮扶对象的实际情况,共同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帮扶对象量身打造服务计划,两方帮扶步调一致才是有效解决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问题的基础。如此,从前期计划设计到具体实施都足够重视避免福利依赖问题的持续,从而实现扼住农村贫困户“不想脱贫、无法脱贫”的思想。
(二)以退为进:注重打开服务对象心结与服务递进
大多数农村贫困户还是希望变好的,奈何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又可能存在代际传递式贫困,其内心觉得通过自己使家庭条件逐渐向好的难度过大。在开展活动时,有必要先以身边的人与事的变好经历对其进行心理调适并逐步打开服务对象的心结,激发其内生动力,让服务对象的心理从“要我变好”逐渐向“我要变好”转变。同时针对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在服务过程中的活动安排需要更有灵活性,积极为服务对象争取利益。如前文案例中所提及的Q女士对种玉米意见颇多,有大部分原因是她觉得付出与回报不对等。针对这种情况,在活动安排时可以给予Q女士经济效益更高的种植种类方案,并整合资源帮助Q女士找到产业项目帮扶,根据引进的帮扶产业项目的订单,标准化种植,统一收购,帮助Q女士一家提前对收益有预估并明确收益有保障,让其更有动力变好变强。故在改善农村贫困户福利依赖问题上社工需要一户一法,更有耐心地对待服务对象,避免“速效”和“霸王硬上弓”的现象。
(三)加强熟人网络建设
社工机构在首次入驻某社区时不要急着开展服务活动,而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关系以非正式的方式与居民建立私人友情,逐步了解更多居民信息和社区概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区居民对社工的信任。社工在进行服务活动时不仅要了解服务对象,更要在社区建立起自己的熟人网络和社区服务空间,通过居民的认可和建议,积极完善服务机制以更好地安排服务活动。同时,社工能更好地與农村贫困户积极对话也不能缺少熟人网络的支持,服务对象看到邻居可以从社工那里获益,其实也能让服务对象更进一步地相信社工并愿意接受社工的服务安排。
参考文献:
[1] 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刘璐婵,林闽钢.“养懒汉”是否存在?——城市低保制度中“福利依赖”问题研究[J].东岳论丛,2015,36(10):37-42.
[3] 刘宝臣,韩克庆.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分裂与整合:对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16(6):9.
[4] 蒋蕊,张文.关于“十二五”时期上海社会发展的初步思考[J].科学发展,2010(12):3.
[5] 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2022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EB/OL].[2022-12-6].http://mzt.hunan.gov.cn/mzt/xxgk/tjsj/202211/t20221128_
29139135.html.
[6] 王守颂.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性研究[J].前沿,2016(12):6.
[7] 李文祥,郑树柏.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扶贫模式创新——基于中国村寨扶贫实践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4):6.
[8] BARBARA BRYANT SOLOMON.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19.
[9]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作.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指导教材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2021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1:356.
[10] 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学术研究,2004(12):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