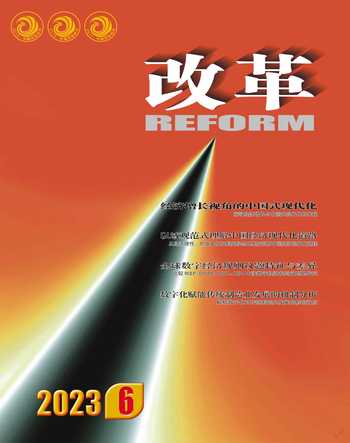经济增长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



摘 要: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及分析框架未将经济增长作为重要内容,与现代化研究关联较大的发展经济学也没有把经济增长放到应有位置。对历史资料的梳理表明,1979年我国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是出于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步水平较低、经济增长追赶过程较长等方面的考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战略谋划,都将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变得更加具体、更可测度。不过,到2035年,如果把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需付出更大努力,应对一些重要挑战。充分挖掘潜力、释放民间活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合理经济增长,应与发展质量的提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须遵循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增长;发展质量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06-0001-14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精辟论述。在此之前,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还对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了描述,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着中国发展道路,引起了世界关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现代化研究在世界学术史上曾经是“显学”,在我国学术界也一度属于热门领域,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大都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而较少来自经济学领域。这无疑是一个学术遗憾,因为没有足够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支撑的社会,很难被认为实现了现代化。从文献来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似乎涉足了现代化理论领域,但也是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来开展对现代化的分析。这显然不够,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从业人员占比几乎可以与所谓的“后工业化国家”比肩,但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仍然不高。即使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流动性较强、城市化程度较高,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在名义上几近免费,甚至有选举制度或文官体系,民众也接受了比较现代的生活价值观,但若把它们视为实现了现代化,则少有人赞同。
本文认为,需要补上现代化理论中的经济增长短板。如果没有足够深入的经济增长研究,就很难对现代化的实质和表征有清楚的认识;如果缺乏足够强劲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现代化不可能成为现实。而足够强劲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就基于经济增长判断;下一步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韧性和合理速度的经济增长不可或缺。
一、传统现代化理论的缺失环节:经济增长
马蒂内利对世界范围内关于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与概括后指出,尽管这一词汇在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就得到了较多使用,但对现代化的系统性研究,并成为一门理论,是“二战”之后的事情;现代化进程大致体现于如下方面:基于科技的工业化,社会分工和流动性的深化,人口的城市化及基础教育的普及,大众消费的兴起,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平等主义价值观的蔓延,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等等[1]。这种对现代化的认识,在学术界具有普遍性,并被许多学者用于衡量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也基本使用这样的分析框架,譬如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的教授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宗明义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在科技革命影响下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工业化和服务业化导致了社会结构变迁;其分析框架就是政治结构变化和政治发展、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社会分工深化及流动性提高、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性[2]。这些学者尽管对新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一些刻画,但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方面,而非经济增长本身的价值。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长期从事的现代化研究,基本上也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现代化,经济领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现代化,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化特征与进程[3]。
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研究远比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更有影响。亨廷顿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性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审视现代化的视角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所揭示的内容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和社会觉醒的大变动中,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政治参与相对不足问题,以及引发的政治失序问题及其对后续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4]。亨廷顿的现代化研究虽然触及了经济发展,但主要还是把视线放在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开放方面。福山对政治秩序的持续研究具有更新近的影响力,他从民主与法治、问责制之间关系的视角对现代化进程展开了研究[5],尽管也涉及经济发展对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但他的研究以及大量的类似研究终究缺乏足够的经济增长考量。
即使那些从发展经济学切入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也较少讨论经济增长问题。罗斯托是現代化理论研究领域少有的经济学家,其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虽然明确指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基于科技创新的长期经济增长,不过他着重强调长期增长在部门结构变化方面的显著特征,即主导部门及其引致的扩散效应对于经济起飞的意义;同时又认为,一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不应以人均实际收入来衡量,并明确批评了世界银行等机构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方法;他还特别指出,把当时同样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中国、印度与马里、海地放在一起是错误的[6]。罗斯托的洞见具有重大意义,但遗憾的是,他还是忽视了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时也忽视了前沿创新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罗斯托进一步质疑了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他问道: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正当目标吗?全球资源有限难道不正是在使人类逼近增长的极限吗?[7]
对于这种情况,发展经济学内部在后来的研究中也进行了一些反思。譬如,拉布什卡简略地,但也郑重地表明,他发现了在欠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与公民权利、自由之间的积极关系,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很可能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因而经济增长十分重要[8]。速水佑次郎也意识到,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待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停滞是现代化的噩梦[9];尽管他也强调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道路,但认为经济增长恰恰是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跋涉的共同途径;他甚至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缪尔达尔的发展思想[10]提出明确批评:缪尔达尔对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可能性有着深深的怀疑主义,亚洲一些国家后来却有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显然,速水佑次郎把这些亚洲国家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与它们的现代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罗德里克更是明确指出,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发展的内容虽然远多于经济增长,但无论如何增长是第一位的事情。事实雄辩证明,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的最大推动力[11]。
二、现代化研究须有经济增长视角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总收入(GNI),特别是人均GDP或人均GNI衡量的经济增长,尽管被许多人认为失之偏颇,并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也的确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纠偏性指标,但GDP、GNI仍然是最受认可,也最能代表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而且,绝大部分国家都已建立比较完整的机构和方法、手段来统计和计算这些经济增长指标。恰如罗德里克所言,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代表着人们生活得到改善,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加普及,即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11]。
实际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已经将增长指标直接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联系起来。世界银行专家吉尔和卡拉斯撰写的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就从人均GNI角度,分析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复兴、城市化推进、教育发展、公共部门改革、治理改善等层面的工作,并提出了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重大命题[12]。这是一幅典型的现代化推进的图景,展示了持续经济增长对于现代化的意义。这样的研究,走出了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着眼于欠发达国家如何启动经济增长、低收入国家如何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式。而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公平竞争、机会均等、减少贫困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以及良好的政策和治理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并揭示了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13]。这些文献既在告诉人们如何跨越经济增长领域的中等收入陷阱,又在提醒人们如何避免现代化陷阱。
其实早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各国的经济增长业绩进行了比较分析,只是他们并未有意识地将这些分析深刻嵌入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谱系。但这些分析以较为完整的数据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造就了国民富裕,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富裕不仅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联系在一起,而且与那些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如更好的医疗、教育、工作机会、社会流动性、基础设施与城市化、公共服务等)联系在一起。库兹涅茨就对西欧和北美国家一些重要时段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就是高增长率,将高增长率维持较长时间才能成为发达国家[14];与现代经济增长相联系的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主要归功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因而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提高(如教育的推进、知识的增加)都非常重要,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与现代社会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从地位到契约的转变,以及法治的確立[14]。后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继续并深化了库兹涅茨的工作,如赫尔普曼深刻揭示了资本形成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生产率增长如何刺激资本积累,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和法治等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作用,明确指出了对合约和产权的法治化保护正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15]。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仔细审视了印度等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什么不如人意:大量的失业人口、糟糕的卫生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腐败和官僚主义,都与低迷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因此,促进增长的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改革[16]。
有意思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还研究了经济增长对于改善民众道德和社会文化的意义。弗里德曼就指出,经济增长可以提振人民的自信心、包容性和关爱情怀,以及对于民主的支持度,并营造一种乐观向上、鼓励创造的社会气氛[17]。当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有着更宽广的视角,如麦克法兰的分析表明,过去几百年,基于分工、交易和产业革命的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意义远不止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而是促进了个性解放和个人自主,促进了公民契约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形成,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将英格兰带入迈向现代社会的良性循环之中[18]。
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可以更加全面。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两个方面;党的二十大同时描绘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第一项就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高质量发展,还首次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把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结合起来考虑,就非常切合实际,因为发展质量的提升,包括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与量的增长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含有经济增长方面的内容。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谋划
几乎没有人会把经济落后的国家视为现代化国家。这种常识也体现在中国近代以来那些志士仁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中,那时一些人使用近代化一词,其实就是英文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早期中文译法,而且近代化、现代化常常与基于现代科技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之前,就确立了比较明确的现代化意识。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讲了经济工作,提到了“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20]。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在审阅工业发展有关文件和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1]。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2]。在1975年初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2]。很显然,毛泽东、周恩来所论述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基于现代科技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郑重提出,“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2]可以看出,邓小平开始把现代化与改革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把我国现代化正式地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而且与首次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3]。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与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座谈中指出,“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是很高。”“1977年,美國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23]。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即使达到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23]显然,邓小平所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相对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二十世纪末达不到那个水平,只能达到“小康”,这实际上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周恩来提出的二十世纪末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并走在世界前列这个目标的回调;第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值上,要以国际标准来衡量,即以美元来衡量,争取达到一千美元。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认为,至此,经济增长已经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这是一个可统计、可核算、可进行国际比较的指标,也可认为是核心内容之一。
自此之后,经济增长指标一直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谋划中居于重要位置。邓小平后来谋划,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直接与经济增长指标联系在一起。1984年10月6日,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的外方代表时,邓小平提到,我们的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4]。1987年3月8日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邓小平说:“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4]1987年4月16日,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我国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了”。他还特别指出,“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24]。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目标: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从200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进行了展望,指出届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论述意味着,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表,由此前的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提前到2035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提到,展望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很具体、很明确的经济增长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把这个指标正式列为2035年的“总体目标”;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设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中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见,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邓小平1979年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谋划,以及此后四十余年关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谋划,是一脉相承的。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国家在谋划和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时,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在谋划到2035年及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时,都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视角,都把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人均产值或收入的增长速度,作为极为重要的指标。正是这种具体、明确、可核算的经济增长指标,引导和督促国家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工作向着现代化方向不断推进。
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现代化的基本实现
邓小平在谋划中国式的现代化时,显然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特别是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比较目标,并进行追赶。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就是争取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靠近的追赶过程,也是大致复制先行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迁的过程。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意味着许多国家对少数发达国家、先行国家进行学习和追随,而且通过国际经贸活动来实现。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榜样—学习模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文化、政治的全方位学习,不意味着不能走各自独立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模式下,一国的经济增长结果,常常以发达国家的货币来衡量,或者以国际元来衡量,现在主要以美元来衡量。
也正如邓小平分析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很低的起点上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现今的统计方法来计算当时的GDP,而且那时我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比值也不清楚。但根据学者推算,中国人均GDP1952年约为50~100美元,1978年约为130~250美元[25]。在这26年里,我国人均GDP也有了明显增长;如果取1952年最低值和1978年最高值,则增长了4倍;如果都取中间值,则增长了1.5倍以上。不过在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1979年初,中国人均GDP还比较低,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至少是中国的20倍以上。所以邓小平认为,到二十世纪末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 000美元的目标,也需要经过艰巨努力,“不容易”。不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增长活力得到释放,经济增速超过了预期。实行改革开放26年后,到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 500美元。即使取上述推算的1978年人均GDP的最高值250美元,26年也增长了5倍;如果取1978年的中间值,则增长了近7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的26年,以美元衡量的人均GDP增速,是改革开放之前26年的数倍。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大约维持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以本币衡量的GDP增速,在改革开放后30年里达到9.9%,这在所有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也是罕见的。此后,我国经济增速开始震荡下行,但人均GDP还是于2019年站上了1万美元的台阶,而2021年则达到了1.25万美元,离世界银行划定的当年高收入国家门槛线近在咫尺;2022年以美元计算的我国人均GDP尚未被世界银行发布,而宁吉喆的测算大约为1.27万美元,但由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线因全球通胀而上调,因而我国仍未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不过,经历约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趋势性议题,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开始得到讨论。刘世锦等人就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时指出,追赶者实现一段时间高速增长后会面临增速明显回落问题,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视为成功追赶者,其增速下台阶的时段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1 000国际元左右,而其他国家增速下台阶的时段则在4 000~7 000国际元左右;中国虽在2008年人均GDP已经接近8 000国际元,但其经济增速大约会在2015年前后“下台阶”[26]。此后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增速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确开始下滑。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即2001—2005年和2006—2010年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为8.8%和11.2%;而“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分别为7.8%和5.7%。当然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经济增速只有2.3%,但此前几年也只有百分之六点多;2022年经济增速也只有3.0%。
虽然进入经济增速趋势性下滑的挑战期,但我国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信心没有改变。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如果经济增长潜力得不到继续释放,经济增速过于疲弱,那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二十大谋划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实现就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更难以实现。
基于这些考虑,一些学者就2035年中国人均GDP能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了分析。陆挺根据国际比较研究提出,2019年人均GDP达到24 492美元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门槛,而当年我国人均GDP为10 262美元;我国在2020年至2035年期间需要保持年均5.4%~6.4%的人均GDP增速,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27]。刘伟经过估算后提出,2019年,人均GDP達到3万美元左右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28]。贾珅则提出,2019年人均GDP 2万~3万美元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未来15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速只要达到4.7%,就可于2035年达到2.1万美元,如果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1∶6,人均GDP 可达2.4 万美元,升至1∶5则可达到2.9 万美元(均为2020年不变价)[29]。吕光明和陈欣悦主要借鉴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进行分析,认为2019年人均GDP达到17 739.6美元,或者16 723.5美元,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他们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回归拟合外推,认为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线为25 722.7美元,或者25 343.8美元;他们的分析还表明,汇率升值对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至关重要,如果未来十几年人民币对美元能够像1987—2019年那样年均升值1.25%,那么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25 424.8美元,可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30]。
这些研究和阐述很有意义,不过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所设定的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相差较大,有的是一万六七千美元,有的达到3万美元;或者留有过大的空间,譬如2万~3万美元之间都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二是都忽略了通胀因素,或者没有把汇率变动因素和通胀因素结合起来完整地考虑,譬如,要么没有同时考虑通胀和汇率因素对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的影响,要么没有同时考虑通胀和汇率因素对2035年本国以当年美元计算的人均GDP的影响。
本文从经济增长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可以主要参考陆挺[27]、刘伟[28]和贾珅[29]的标准。因为吕光明和陈欣悦把中等发达国家标准设定得比较低[30],似乎不太符合常识,譬如将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标准设为当年人均GDP为一万六七千美元,而此年人均GDP在1.7万美元左右至2万美元的经济体是乌拉圭、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希腊等国家,捷克和葡萄牙则达到2.3万美元,斯洛文尼亚达到2.6万美元,西班牙和韩国超过3万美元,意大利超过3.4万美元,再往上就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综合他们的分析,本文认为至少应该以希腊和斯洛伐克2019年的水平来设定当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所以可设定为2.0万美元;而如果以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为目标,则应设定为2.5万美元;以西班牙和韩国为目标,则应设定为3万美元。综合起来考虑,可把门槛线设得稍低又不至于太低,故将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设为两个档次:2.0万美元和2.5万美元。
解决第二个问题则稍微复杂一些。首先应该考虑,2020—2035年许多国家的通胀因素会将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提高到什么水平。坦率而言,要预测和分析未来十几年许多国家的通胀水平是不可能的事情。为此,可以采用比较简单而又大致靠谱的方法,这就是根据此前十几年有关门槛线的抬升幅度来外推。吕光明和陈欣悦的回归外推很有参考价值,他们认为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将比2019年提高45%~52%[30]。另有测算显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在1991—2005年这十五年里大约上调了40%,2001—2015年这十五年里大约上调了35%[31]。大致可以认为,在35%至52%之间进行选择,不会太离谱。考虑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全球低通胀时期,各种门槛线上调幅度偏低,譬如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线早在2012年就超过了12 000美元,而十年之后的2021年仍然为12 695美元,但由于2021年全球通胀明显加剧,2022年上调到13 205美元。考虑这些原因,本文将2019—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分两个档次上调,即上调45%或50%。如此,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就存在表1(下页)列出的四种情形。
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分析,我国未来十几年应该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才可以如期在2035年成为人均GDP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即届时至少达到2.9万美元,或者达到3.75万美元。下面的分析将假设在2035年之前我国人口数量不变。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特别准确,但不会过于偏离真实情况。
下面,本文将采用与绝大多数研究不一样的方法,即以GDP名义增速而非实际增速为基础来预测各年现价GDP。尽管这种方法的预测值不能与其他学者的预测值进行无缝对比,但好处非常明显,就是把通胀因素直接纳入各年GDP数值中。当然,这需要假定,未来十几年我国不会出现极为异常的多年严重通胀或通缩现象,而为了研究方便并基于我国以往控制通胀和通缩的经验表现,这种假定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可以将各年名义GDP按当年汇率折合成美元。
已知的情况是,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 551美元,当年平均汇率为6.45。而2022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可以选用宁吉喆测算的12 700美元。现在假定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比2022年贬值3%,而2024—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致保持在2023年的水平不变;并预测“十四五”时期剩下的3年,即2023—2025年我国GDP名义增速为8.0%,从而各年人均GDP将达到13 335美元、14 402美元、15 554美元。
更困难的事情在于预测我国2026—2035年的GDP名义增速。目前已有一些机构对这十年的GDP实际增速进行了分析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预测,“十五五”时期各年实际增速在5.09%和4.73%之间,年均为4.92%;“十六五”时期在4.66%和4.33%之间,年均增速为4.48%[32]。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十五五”时期各年实际增速在5.17%至4.65%之间,年均增速为4.88%;“十六五”时期各年实际增速在4.57%至4.21%之间,年均为4.37%[33]。2022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预期当年增速为5.5%,并解释说这个预期目标同近两年平均增速及“十四五”规划目标相衔接;不过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实际增速只有3.0%。202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将当年预期增速设为5%左右。
本文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综合研判,首先选择比较乐观的情景,将“十五五”时期实际年均增速仍然设定在5.0%左右这样一个较高水平,“十六五”时期设定为4%。如果简单地将“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各年的GDP缩减指数都设为3%,那么“十五五”时期各年名义增速为8.0%,“十六五”时期为7.0%。此外,已经假定“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且人口规模不变。这些设定和假定作为情景一,据此可以得到各年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见表2)。
不过,将“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设定为5.0%和4.0%,可能过于乐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与前几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判断相比,党的二十大对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学术界,也有一些研究对未来的经济增速预测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刘伟和陈彦斌就预测,基准增长情形下,“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我国经济平均增速分别只有3.99%、2.21%;而在基准增长+基准政策效果情形下,则为5.43%、4.28%[34];所谓的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市场化程度、国企改革的深度,等等,这些都非易事。因此,至少应该将“十六五”时期的增速设定得更低一些,才可能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考虑将较为正常的情景作为基准情景,即情景二,就是在情景一的基础上,将“十五五”时期年均实际增速设定为4.5%,“十六五”时期年均实际增速设定为3.5%,“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各年的GDP缩减指数都设为2.5%,从而“十五五”时期各年名义增速设定为7.0%,“十六五”时期各年名义增速为6.0%。同时,假定2024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然不变,从而得到各年折算成美元的人均GDP数据(见表3,下页)。
考虑到情景一和情景二假定汇率不变可能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因而还应就汇率变化作出一些合理假定。由于2022年和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主要是美国激进加息所致,预计2024年美国加息结束并可能开始降息,因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假定,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5%,2025年继续升值5%,此后一直到2035年保持汇率稳定。如果2024年和2025年我国名义人均GDP增速均为8.0%,那么这两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将每年增长13.0%,因而2024年、2025年我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15 069美元、17 027美元。在情景一和情景二基础上考虑这些假定,作为情景三和情景四,那么各年人均GDP见表4和表5。
结合表1 和表2—5,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如果将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设为2.0万美元,2035年该门槛线可能会在2.9万美元或3.0万美元上下,而届时我国人均GDP要达到3.0万美元,年均名义增速必须要在“十五五”时期达到8.0%、“十六五”时期达到7.0%,对应的年均实际增速可能分别为5.0%和4.0%,且人民币币值能够基本稳定。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情景,意味着我们届时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不能出现这种情景,则不易登上人均GDP3.0万美元的台阶,但也有可能超出2.9万美元。如果将2019年的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线设为2.5万美元,到2035年,我国不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通过努力则有可能达到和超过这个门槛线。
应该指出,对未来十几年进行准确预测非常困难。一是实际和名义GDP增速很可能出现较大起落;二是汇率问题,这更加难以捉摸,因为汇率涨跌不仅取决于国内基本面,而且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情况和相关政策变动。总而言之,对于2035年能否成为人均GDP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以及能否成为经济增长视角下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保持信心,但不应盲目乐观。
五、结语
到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和换算成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通胀、汇率等复杂因素,都会涉及生产率提升问题。即使表2—5的预测值,也隐含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假定,但这方面的假定并不一定会无障碍地自动变为现实。许多研究已揭示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Brandt等人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仍有一些严重的市场扭曲需要消除[35-36]。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同国家的国民收入差距,大都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因而他们把萎靡的全要素生产率视为通向富有的屏障,并强调了竞争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37]。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下一步,如何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些重要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盖庆恩等人的研究显示,垄断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大敌,促进公平竞争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8]。伍晓鹰所作的反向分析表明,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在提高储蓄率、投资率以及促进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没有良好表现[39]。刘伟和陈彦斌认为,如果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譬如推动利率市场化和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破除行政垄断和释放创新动力,就能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十五五”和“十六五”期间的经济增速比基准增长情形下提高1.44~2.07个百分点[3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指出,改革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警示了2007 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断下滑的情况[32]。针对国有部门的研究表明,即使进行比较温和但持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有利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速的提升[40]。因此,未来十几年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推进国有部门的深入改革、约束政府的不当干预,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部署,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未来十几年,中国还需妥当处理与市场化改革密切相关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全球关系安排问题。当今时代的市场化,无法与全球化和开放性割裂。但对处于经济和技术追赶位置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就会引发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即所谓的依附性问题,以及自主性、安全性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就出现了依附发展理论,到七十年代形成了很大的政策影响。这一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中心—外围关系,认为中心控制了科技、资本以及高附加值产业,外围不得不依附于中心。这一理论主张政府应实行广泛干预政策,甚至对西方国家实行抵制性政策[41-42]。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内含一种无法抹掉的隐痛:西方发达国家在我们的前面。同时,发达国家价值观的全球流行,可能会使其他一些国家感觉到某种不安全感和颠覆性。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后,類似政策思维可能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激烈而又复杂,因为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型关切,如一些人谈论的互联网主权、数据主权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国家主导乃至控制全球经贸规则属于蓄意“打压”。未来会不会出现具有鼓动性的新依附理论,或者某些变种和翻版,并且以这些理论来发出对发达国家实行新型抵制的号召,不得而知。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会日益考虑自主性和安全性问题。这些都会给经济增长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化事业带来新变量。
此外,日益严峻复杂的债务和金融隐患,也会对未来十几年的经济增长构成重大挑战。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提出了“伴险增长”(growth at risk)问题,即在债务不断堆积、杠杆率节节上升、资产价格相应膨胀的境况下,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就要冒较大的金融风险。2020年以来,不仅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各种债务有了大幅度跃升,而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连通性也显著增强,从而把世界经济猛力推进了“伴险增长”通道。随着低通胀、低利率的结束,各种风险组合将进一步复杂化,使经济增长变得更加脆弱。正如Adrian等人所揭示的那样,金融条件恶化,会将经济置于脆弱性增长轨道[43]。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类似问题,如果发展政策不能很好地平衡各种因素,经济增长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继续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平衡性经济政策在未来需要受到重视。
当然,从经济增长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发展质量的丝毫忽视。恰恰相反,进一步释放民间活力和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生产率的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不仅不冲突、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表明对保持合理增速与提升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更完整的认识。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就难以促进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民生福祉的增进就缺乏支撑。保持合理经济增速,也意味着不应盲目追求超出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严重失衡和扭曲的经济增长。有了合理经济增长作支撑,就应该合理增加研发、教育、社保、生态投入,以及民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致力于提高发展质量,而且投入成果又会反过来促进可持续增长。中国式现代化,应该遵循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对经济增速和通胀、汇率的预测非常困难,至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方法和模型能够应对现实中各种变化莫测的因素,而未来十几年的新风险、新挑战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定不会是平坦大道。“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我国GDP实际年均增速如果高于或低于5.0%和4.5%左右,以及2035年人均GDP高于或低于3万美元,一点儿也不奇怪。历史上许多著名机构的模型预测常常出错,但历史事实同样显示,市场化改革、民间活力释放往往使经济增速超出模型预测值。2035年成为经济增长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期许,而不是由哪个国际或国内机构来评定。即使以折合成美元的人均GDP来衡量2035年的现代化程度,也有待事实来回答,并且衡量人们实际生活水平还需考虑购买力平价指标。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更长道路要走,无疑也需要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此外,除人均 GDP外,还有许多要件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而言也十分重要,包括科技、教育、人口素质、国家治理、社会文明程度,等等。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尽管维持足够速度的经济增长至为重要,但并不是全部。
参考文献
[1]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何傳启﹒国家现代化的原理与方法: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2001—202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4]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罗斯托﹒发展:马歇尔长期政治经济学[M]//杰拉尔德·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8]拉布什卡﹒税收、经济增长和自由[M]//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阿兰·A.瓦尔特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9]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GROSSHOLTZ J, MYRDAL G.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J].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1969, 62(4): 1278.
[11]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M]﹒张军扩,侯永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2]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M]﹒黄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3]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14]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常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5]E.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M]﹒王世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6]贾格迪什·巴格瓦蒂,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M]﹒王志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7]本杰明·M.弗里德曼﹒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M]﹒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8]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M]﹒管可秾,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M]//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M]//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23]邓小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张文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6]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7]陆挺﹒2035年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需要多快的GDP增速[J]﹒企业观察家,2021(5):20-21﹒
[28]刘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增长目标与新发展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5-13﹒
[29]贾珅﹒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战略[J]﹒发展研究,2022(4):44-48﹒
[30]吕光明,陈欣悦﹒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J]﹒统计研究,2022(4):3-20﹒
[31]張文魁﹒聚力于非资源性实体部门,迈进高收入安全区[M]//刘世锦﹒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3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20(8):4-23﹒
[33]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4):5-22﹒
[34]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4):54-68﹒
[35]BRANDT L, ZHU X D.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Z]. Discussion Papers No.4764, 2010.
[36]BRANDT L, TOMBE T, ZHU X 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cross time, space and sectors in China[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 16(1): 39-58.
[37]斯蒂芬·L.帕伦特,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M]﹒苏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8]盖庆恩,朱喜,程名望,等﹒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5(5):61-75﹒
[39]伍晓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对国家或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M]//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0]张文魁,袁东明﹒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41]FURTADO.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42]CARDOSO F H, FALETTO E.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43]ADRIAN T, BOYARCHENKO N, GIANNONE D. Vulnerable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4).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spective of Economic Growth
ZHANG Wen-kui
Abstract: The class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analysis framework do not regard economic growth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dernization research, does not place economic growth where it should be. The sorting out of historical data indicates that the concep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posed by China in 1979 is mainly due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e low starting level of China'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the long process of catching up with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lmost every time China has made a strategic plan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ause, it has taken the economic growth index as one of the core goals, thus mak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ore specific and measurable. However, by 2035, if the goal of China'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aching the level of a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y is taken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achiev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greater efforts will need to be made and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 need to be addressed. A reasonable economic growth that fully exploits potential, unleashes folk vitality, and constantly improv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ould complement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development qualit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ust follow this virtuous cycle of development model.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quality
作者简介: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