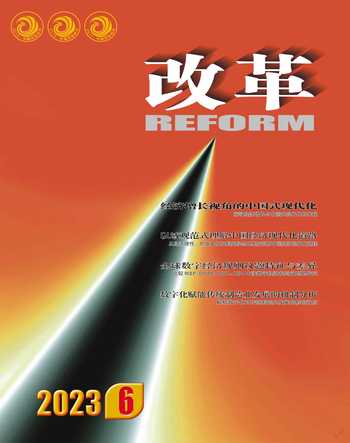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机制与效应分析
黄宗远 王凤阳 阳太林



摘 要:作为技术经济范式的重要新形式,数字化在关键要素、技术体系、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方面呈现新的特征。基于数据要素及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综合创新的视角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对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赋能作用,其中数据要素是数字化赋能机制的基础,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则呈现滞后期牵绊效应和适应期正向效应的两阶段效应,产业竞争程度的提升也可以促进数字化赋能效应的发挥。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字化进程中的历史机遇,传统制造业应更加注重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加快推进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并进一步消解社会技术创新滞后期的牵绊效应,促进其正向赋能效应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传统制造业;赋能机制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06-0040-14
目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演进,数字化形成的新动力驱动着现代经济更加强劲、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和运行方式的全面变革[1]。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更是分别高达45.5万亿元、39.8%[2],这充分说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彰显其强大力量的重要途径,对制造业的数字化赋能则是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制造业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性大,能够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设备和技术等基础保障,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既关系到我国能否通过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进行“弯道赶超”,又关系到能否实现新形势下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赋能的内在机理、决定因素和复杂效应,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
近年来学术界就数字化赋能问题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集中在数字技术进步的作用方面,主要分析了数字技术对降本增效[3-4]、技术创新[5-6]、企业管理[7]、就业[8]、经济增长[9]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二是对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技术融合问题的分析[10],认为数字化技术催生了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11-12],促进了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13-14]。三是对数字技术在产业价值创造、价值获取方式的变革[15-16],以及企业间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共生关系等方面的研究[17]。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从技术要素的应用视角展开,对其他非技术因素的作用过程还缺乏深入探讨,数字化赋能机理的“黑箱”尚未完全打开。
实际上,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一场嵌入技术、管理、制度、文化、政治等多维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与创新[18-19],数字经济正作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常识”为社会所接受[20-21]。因此,数字化赋能的机制本质上就是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机制。作为技术经济范式的一种新的重要表现形态,数字化赋能机理的内在意蕴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的行为模式和各个主体间的社会关系[22]。由旧范式衰退到新范式成长的变迁过程还会引发从新关键生产要素发挥作用、认知方式提升、技术创新到制度共同体创新变革的复杂演化过程[23]。因此,数字化赋能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数据化技术融入生产要素开始,会逐渐遍历新关键生产要素形成到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数字化等各种物质要素、技术要素数字化综合作用的过程。
在这一逻辑架构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构建基于生产要素赋能、技术系统赋能的数字化促进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赋能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从中探索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赋能的逻辑和机理,并深入分析其决定因素和赋能效应。
一、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途径及机理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性创新,都会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的这一作用,往往都是通过技术经济范式体系的变革与创新来实现的。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最早是由佩蕾丝和弗里曼等人在库恩的“科学范式”和多西的“技术范式”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用以描述被广泛传播的技术革命通过经济系统影响企业行为和产业发展的过程[24-25]。作为技术革命扩散的载体,技术经济范式是社会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运行遵循的“基本法则”,决定了运用新关键生产要素和新技术的最大获益方法或最佳实践模式。奠基于新技术基础上的技术经济范式发展一方面会催生一批有强大影响且相互依赖的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另一方面新范式下新关键生产要素的应用、新技术的传播、新规则的渗透也会对已成熟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从而为其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动力。
从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过程来看,新关键生产要素的形成和大量应用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范式的创新除了自然技术的创新、社会制度框架的重新设计与更迭之外,还包括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信念和行为观念的修正,从而构成一个推动产业发展的巨大的、复杂的、演化的技术系统。因此,数字化赋能机制本质上就是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对于产业体系结构变化的作用过程,是通过生产要素体系的重塑和大技术系统的创新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技术创新、社会技术创新和思维技术创新构成的大技术系统创新对于传统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的研发设计、流程再造、生产制造过程、组织变革、营销体系和生产经营管理等诸多重要生产经营活动环节的绩效提升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基于这一思想,考虑到传统的范式—制度框架对现阶段的一些重要技术经济问题缺乏足够有力的解释工具和方法,本文将其扩展成生产要素赋能和技术赋能两种机制相结合的新框架。
作为现代技术经济范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发展的赋能也是通过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系统的持续创新机制来实现的。虽然从表象来看,这一赋能过程也可以简称为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但其实质则是传统制造业使用根植于数字化通用技术的新数据生产要素,通过包括自然技术创新、社会技术创新、思维技术创新三大维度的整个技术系统的深入创新来实现的,是对传统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全环节、全要素的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事实上已经在我国的现实经济进程中深入而广泛地展开,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体量、增长速度和对数字经济的贡献度远大于数字产业化等数据有力地佐证了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进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展现的重要力量[2]。
数字化的发展包括导入期和展开期两个阶段。在导入期的初期阶段,数字技术实现突破,新技术簇群不斷涌现、交叉融合、加速迭代,数字化要素逐渐取代成本较高的要素并被密集使用,而制度体系、管理模式等社会技术的转变则往往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快速扩散的需求与非技术因素滞后供给的不匹配,导致数字化在其发展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个无序和低效率的阶段。进入展开期后,随着数字化要素的广泛应用,成本结构的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发生改变,数字化带来的外部效应重组甚至重构了整个经济体系。适应数字技术逻辑和要求的社会技术与思维技术转换逐渐完成,数字化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赋能潜力开始充分显现,在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将发挥巨大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需要回答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以及这一作用是如何发生和实现的。这显然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困难的问题。事实上,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过程进行了诸多分析,但正如当年索洛余值困扰研究者的局面一样,迄今为止关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具体作用机理仍有许多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地方。破解这种困难局面,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而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范式。这也是本文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分析框架的内在原因。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主要通过两大方面得以实现和完成。
(一)数字化推动关键生产要素的形成与发展,极大地释放出新要素的潜能,促进传统制造业降本增效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形成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就像佩蕾丝所指出的那样,关键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一组特定的投入,具有生产成本的下降性、供应能力的无限性和运用前景的广泛性三大特征。技术革命总是能够通过关键生产要素潜能的释放来推动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促进社会财富积累。面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浪潮,数据规模、数据采集存储加工能力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26]。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具有高流动、易复制、强互补性、强外部性、自我增值性的新型生产要素[27],在传统制造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不仅可以将自身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而且能依托虚拟空间作用于物理空间的产业活动,对传统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数据贯穿于产业研发、生产、流通、服务的全流程,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产业主体可以即时地对各环节数据进行自动化采集、传输、加工、处理与分析,将原本无法被采集、识别、分离的信息高效地转化为具备应用和开发潜力的数据要素,从中挖掘出有效信息并作用于其他传统要素,使传统要素质变为全新的数字化要素,这一过程在增强要素间协同性的同时,还可以降低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浪费,从而促进传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8]。
(二)数字化促进三大技术系统的协同创新,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予新的强大动力
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的赋能是在数字化要素基础上通过大技术系统中三大技术的协同创新来完成的。事实上,任何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技术赋能作用的发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实经济活动中总是同时存在着多种复杂的范式结构,数字化的作用就在于它能重塑已有范式中的技术体系,引发思维技术、社会技术和自然技术的数字化创新,并能够对传统制造业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等各种活动中的诸多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从而提升其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构成大技术系统的三大技术交织缠绕在一起,彼此之间还可能存在干扰和冲突,因而会导致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的赋能效果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只有对这些同时运行着的复杂技术体系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并在数字化范式的引导下实现协同创新,才能推动传统制造业发展朝着有利的方向演化。换言之,提升各种复杂技术系统的数字化协同创新效率,提高各种技术创新活动的适配性,正是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进程、发挥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正向赋能效应的关键。
1.通过数字化的融入实现自然技术的创新效率倍增,促进传统制造业发展的高级化、合理化、高效率化
事实上,自然技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技术。在数字化向传统制造业渗透的过程中,数字技术首先会融入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体系,通过其创新来引发生产体系乃至生产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嵌入可以颠覆传统制造技术的创新逻辑、模式和过程[29],如数字孪生、数字仿真等数字化设计工具能够精准模拟物理实体的各种参数,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在动态、不确定的环境下支持多场景研发活动,提高研发的精确性;同时,这种虚拟化运作方式还可以降低创新主体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技术创新活动的范围经济[15]。另一方面,数字产业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重构了新的生产技术条件,实现了生产流程的自动化、专业工艺的智能化以及劳动力的机器化,有力地提升了传统制造业解决复杂工艺问题的能力。如在智能制造模式下,传统制造业可利用软件系统和硬件设备结合智能工厂实现生产全流程的一体化和智能化,替代传统的劳动模式;各种精密数控设备、传感器等的应用,可助力传统制造业实现工艺、设备参数的实时采集,提高产品的精度和加工装配效率;人机智能交互、增材制造等技术和装备的应用可辅助传统制造业最大化地削减不必要、低效率的工作环节,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增强产业生产系统各环节的协同,从而促进产业经济效益提升。
2.数字化的融入能够提升社会技术创新的科学化、精准化和快捷化,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业态创新和效率提升
社会技术本质上是人类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方式和手段的总和。一项新通用技术的扩散往往需要多种社会技术(如新制度体系、新组织形式、新法律、新监管框架等)的发展和协调[25],而实践中管理政策、制度、规则等社会技术的变迁和创新往往都是较为滞后的。当数字化渗透程度较低时,激励社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这种滞后性会对传统制造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当数字化发展进入展开期后,各种管理政策、制度、规则、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将会更加精准和快捷[30],并催生全新的企业组织形态和产业组织结构[31-32],企业也由过去相对封闭的组织结构形式变成通过各种信息和合作关系相联结的网络结构与生态结构形式,形成越来越扁平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使得管理技术越来越数字化和智能化。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创造出了大量新业态,互联网+、智能+、智慧+、云+等业态的出现丰富了传统制造业的经营形式,产业可以实现跨主体、跨领域、跨集群、跨区域的开放、合作、共享;平台化、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将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链、技术链和创新链中的要素和资源联结起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在整个生产经营网络中形成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协作模式;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传统制造业基于生产、经营、消费数据,精准识别各环节发展情况,从决策端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错误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管理手段可以帮助产业管理部门更有效地挖掘组织内外各种资源的潜力,并更好地实现对个体劳动者的监督和考核;数字化工具的运用推动了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制度创新,使服务于传统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制度设计更加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更加健全,治理更加精准,服务更加高效化,政策制度的红利发挥机制更加科学。可见,社会技术创新也必然会促进传统制造业经营效率提升。
3.数字化的融入使得思维技术创新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各类经济主体的信息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
经济决策是一个信息搜集、分析、加工和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各种方法、规则和程序的变革都是思维技术的创新。数字化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技术革命,而且是一种認知革命。在资源有限性和时空局限性的条件下,人类需要不断通过思维技术创新来构建更高效的认知管理系统,从而以最低的大脑能耗实现最合理的认知功能[33]。传统制造业发展中各类主体出现的决策偏差主要源于决策主体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不足。数字化的融入使得大数据技术以及视听觉、生物特征识别、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涌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决策者收集、分析、加工非结构化数据、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能力;人机交互可以帮助决策者明确产业发展目标,将高度抽象、机械式的静态思维分析过程转化为智能化的动态过程,并通过建立模型提供各种备选方案来辅助其决策;决策者可以将数字化决策工具与传统决策方法相结合,构建实时在线的决策树、影响矩阵和龙卷风图,结合人的主动决策和机器的自动决策的特点,优化供应链管理、洞察新的客户价值、发掘新的业务机会、改善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和优化流程,从而实现更加高效、实时、优质的决策;决策过程中可以通过即时通信、工作场所协同软件等工具随时随地举行线上会议,参与讨论、分享文件,使沟通变得更加便捷,还可以与系统协同交互,共同决策,从而大大提高决策效率。显然,数字化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还能有效地增强传统制造业中各类决策主体的理性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有效消除与化解各种认知偏差和机会主义风险,保障传统制造业更好地发展。
二、变量、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在计量检验中使用到的变量包括:
1.被解释变量
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效益(lnY)。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的赋能作用结果最终表现为对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因而下文分析中用传统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在数字化作用下的趋势性提升来表征赋能成效,并用剔除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来表征传统制造业。
2.解释变量
为了反映上述机理,我们在实证分析中使用以下解释变量:
(1)数字化水平(DIGI)。关于数字化水平的测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考虑到单一指标只能体现数字化发展的部分进程与特征,难以反映技术经济范式发展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而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4],本文从信息化指数、互联网发展指数、数字交易指数三方面构建衡量数字化水平的指标体系(见表1,下页),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计算得到各地区数字化水平,公式为:
DIGIit=∑ WjXit(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j表示三级指标,Xit表示标准化数据,Wj表示第j个三级指标权重。
从测算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份数字化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省份间数字化水平系数标准差由2013年的5.82%增加到2020年的11.66%,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间标准差由2013年的3.85%增加到2020年的9.24%,说明我国省域、区域间数字化水平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发展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2)数据要素(DATA)。目前,数据要素还没有独立的核算方法和体系,但在实践活动中,企业主要通过现场设备数据采集系统、企业信息系统等管理软件获取、记录相关数据,企业使用互联网、软件等信息技术服务的情况直接决定了其数据要素的拥有量和处理能力。因此,本文用各地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量作为数据要素的代理指标。
(3)大技术系统创新(SYST)。为考察基于三大技术协同创新的大技术系统创新赋能效应,本文以三大技术创新的乘积表征大技术系统创新。囿于这些指标目前还鲜有成熟的现成统计数据和指标,因而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尝试根据这些变量的内涵、特征和数据可得性来选用和构造相应的指标。考虑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任何单一指标都具有片面性,本文通过熵值法分别确定三大技术创新指标,即用由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研究与开发费用/主营业务收入)、技术获取与改造投入强度(技术获取与改造费用/主营业务收入)、产品创新投入强度(新产品开发经费/主营业务收入)、产品创新成效(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构成的综合指标表征自然技术创新(TECH);用由营销效率(主营业务收入/营销费用)、管理效率(主营业务收入/管理费用)、人力资本制度创新(R&D人数/总就业人数)、科技制度创新(有科研机构企业数/总企业数)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来衡量社会技术变革(SOCI)。另外,目前对于思维技术尚无可直接使用的量化指标,从思维活动过程来看,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其知识存量,是思维创新活动的基础;科研项目活动代表了思维创新活动的活跃度;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人均计算机拥有量决定了思维创新活动的效率;发明专利表征了思维创新的技术成果;政府重要专项规划代表了思维创新的制度与政策成果。基于此,本文以各省份大专以上就业人数占比、科技活动课题数、百人期末使用计算机数、发明专利申请数、政府专项规划数构成的综合指标作为思维技术创新(THIN)的代理指标。
3.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以下控制变量:市场化程度(MARK),用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表示;开放水平(OPEN),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表示;资本化深度(CAPI),用固定资本总额与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全面性、可得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2013—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及各省(区、市)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年鉴、工业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劳动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北大法宝数据库,由于西藏缺失数据较多,因而将其剔除。
(三)模型设定
结合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以检验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总效应:
lnYit=α0+α1DIGIit+α2Zit+Vi+Ut+εit(2)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Yit表示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DIGIit代表数字化水平,Z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Vi代表省份效应,Ut代表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可通过融入生产要素体系直接对产业效益产生影响,因而本文构建如式(3)所示的生产要素赋能模型,其中DATAit表示数据要素。
lnYit=β0+β1DIGIit+β2Zit+β3DATAit+Vi+Ut+εit(3)
数字化还通过由自然技术创新、社会技术创新、思维技术创新构成的大技术系统创新机制为传统制造业赋能。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式(4)、(5)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其中Mit代表大技术系统创新或三大技术各自的创新。
Mit=δ0+δ1DIGIit+δ2Zit+Vi+Ut+εit(4)
lnYit=γ0+γ1DIGIit+γ2Zit+γ3Mit+Vi+Ut+εit(5)
三、傳统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析法,检验结果显示可能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表2(下页)列(1)、(2)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并控制时间效应和省份效应,以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计量方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列(3)、(4)以数字化水平滞后一阶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①。
表2中列(1)、列(3)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2)、列(4)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仍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化水平与传统制造业产出效益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列(2)显示,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以使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提升0.893%,表明数字化可以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因此,基准回归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同时,OLS和2SLS两种计量方法得到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没有实质性区别,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传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LP)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指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下页)所示。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本质性变化,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出于严谨性考虑,本文还通过替换工具变量、采用滞后期回归的方式(选择滞后一期、两期数字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进一步检验。在替换工具变量法中,借鉴已有研究[35],以各省份1984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IV)。事实上,作为早期的信息运输、信息交流方式,邮局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情况,因而数字化的兴起和发展也更容易出现在这些地区,历史上邮局数量较多的地区也极有可能是如今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同时,1984年各地区的邮局数量并不会对现今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因而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及外生性的原则。另外,由于1984年邮局数量为横截面数据,为避免不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难以应用,本文选用上一年数字化水平与1984年邮局数量的交互项作为当期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下页)所示,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可视为有效的工具变量。滞后期回归结果如表5(下页)所示。在替换工具变量、采用滞后期回归方式进一步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依然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三)作用机制检验
为弄清楚数字化到底是如何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的,这里进一步检验了数据要素和大技术系统创新机制的赋能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同时,本文还检验了自然技术创新、社会技术创新与思维技术创新各自的赋能效应,结果如表7(下页)所示。
由表6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数据要素赋能机制成立。列(1)中数据要素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悖,无法说明数据要素可以促进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提升,为此,本文在列(2)中引入数据要素二次项,结果显示数据要素与产业经济效益之间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说明当数据要素达到一定程度时,其促进传统制造业发展的能力才能发挥出来。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我国数据资产化、资本化建设起步晚,目前数据孤岛、数据质量低下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影响了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第二,列(3)中数字化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对大技术系统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同时,列(4)中大技术系统创新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大技术系统创新的赋能机制成立,即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大技术系统创新,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
由表7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列(1)、列(2)结果表明,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自然技术创新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在列(1)中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自然技术创新强度提升1.820%,同时,自然技术创新强度每提升1%,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将提升0.273%,这表明自然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在数字化和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之间起到了传导正向赋能效应的作用。第二,考虑到社会技术创新的滞后性,本文在社会技术创新机制检验部分同时引入数字化水平的二次项,结果如列(3)—(5)所示。由列(3)、列(4)数字化水平的系数与列(5)社会技术创新系数均显著可知,数字化可以通过社会技术创新机制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其中,列(4)中数字化水平系数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表明数字化水平与社会技术创新呈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有效激励社会技术变革,这也正说明了管理与制度变革的滞后性,所以当数字化水平较低时,低效的管理模式与制度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字化的赋能效应。第三,列(6)、列(7)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可以促进思维技术创新强度提升1.048%,同时思维技术创新强度每提升1%,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将提升0.409%,表明数字化可以通过思维技术创新机制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以上结果均与理论预期相符。
(四)检验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这里将产业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对前文的回归结果作进一步检验,以探讨产业技术经济特性对数字化赋能效应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本文用各地区企业平均规模(生产总值/企业数)衡量产业集中度(CONC)。
由表8可知,产业集中度的调节效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列(2)中数字化水平与产业集中度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产业集中度过高导致的资源过度集中,反而会给数字化赋能效益的发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就现阶段而言,降低产业集中度,引导、鼓励产业间良性竞争可以促进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发展作用的发挥。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数字化技术革命正在快速推进,对数字化的主动适应不仅是我国传统制造业在新形势下生存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运用大技术系统理论的分析思路与方法,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赋能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作用过程与实现途径,这在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与创新,对于我国传统制造业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也有望提供一些有益启示。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化可以为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各省份数字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省域、区域间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在逐渐扩大。从数字化的赋能机制来看,生产要素的内在赋能机制会推动数据要素的不断积累,并带来显著的经济绩效。需要注意的是,数据要素资产化、资本化建设的滞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促进大技术系统创新效率提升的同时,推动了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其中,自然技术创新可以有效传导数字化浪潮对传统制造业经济效益的正向赋能作用。
第二,社会技术变革的滞后在数字化为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的过程中起到了牵绊的作用。在数字化发展初期,必须有效解决社会技术变革激励动力不足,在位范式的社会文化惯性、组织行为逻辑、权力以及利益导致的内在惰性较大,适配数字技术应用的组织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传统制造业数字化下的新业态、新模式应用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中等问题,加快推进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制度规范和社会文化等社会技术范畴的诸多创新,借以促进数字化中社会技术子系统正向赋能效应的发挥。
第三,在数字化由导入期向展开期的不断深入扩散过程中,思维观念的转变作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前置变量起着关键作用。只有遵循新技术发展规律,善于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勇于打破惯性思维的桎梏,创新发展理念,才能使数字化中潜藏的巨大力量转变为现实的巨大推动力。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快数字化的发展,促进数字化赋能效应的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的实质是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机制不断导入和展开的过程。因此,既要针对各种具体的产业活动推出各种相应的规制,做到一业一策、精准施策,又要高屋建瓴,做好全局的谋划和顶层设计,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创新和变革。
第二,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保障数字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将带来数据生产要素的集聚,给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冲击和影响。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创新浪潮,这种冲击和影响既有正面的推动与促进,又潜藏着诸多威胁和风险。因此,在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过程中,应鼓励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并加快建立数据治理与监管体系,推动数字化进程。
第三,树立大技术系统创新理念,加强数字化技术体系的系统化创新,把握数字化进程中的历史性机遇。具体而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加大数字化创新投入,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研究,促进数字化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加强数字化制度体系构建,促进数字化政策创新,从制度和政策体系上保障和促进数字化过程中的有序衔接和发展;注重现代决策技术与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学习新思想,吸收新知识,掌握新的思维决策技术和方法,提高各级各类经济主体的决策水平和能力,更好地顺应数字化浪潮,把握数字化进程中的历史性机遇。
参考文献
[1]张路娜,胡贝贝,王胜光.数字经济演进机理及特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406-414.
[2]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R/OL].(2022-07-08)[2022-07-09].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3]张磊,张鹏.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动力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16(12):7-14.
[4]RELICH M. The impact of ICT on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EU[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2017(4): 706-722.
[5]温湖炜,王圣云.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22(4):66-74.
[6]周文辉,王鹏程,杨苗.数字化赋能促进大规模定制技术创新[J].科学学研究,2018(8):1516-1523.
[7]刘淑春,闫津臣,张思雪,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J].管理世界,2021(5):170-190.
[8]戚聿东,刘翠花,丁述磊.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J].经济学动态,2020(11):17-35.
[9]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9(2):66-73.
[10]张龙鹏,张双志.技术赋能: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创新效应[J].财经科学,2020(6):74-88.
[11]邢小强,周平录,张竹,等.数字技术、BOP商业模式创新与包容性市场构建[J].管理世界,2019(12):116-136.
[12]LATULLA V M, URBINATI A, CAVALLO A, et al. Organizational re-design f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hile exploit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 single case study of an energy compan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1(2): 204002.
[13]余东华,李云汉.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创新——以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为例[J].改革,2021(7):24-43.
[14]李晓华.“新经济”与产业的颠覆性变革[J].财经问题研究,2018(3):3-13.
[15]戚聿东,肖旭,蔡呈伟.产业组织的数字化重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30-147.
[16]吕铁,李载驰.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视角[J].学术月刊,2021(4):56-65.
[17]陈剑,黄朔,刘运辉.从赋能到使能——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运营管理[J].管理世界,2020(2):117-128.
[18]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8.
[19]MANSELL R. Adjusting to the digital: societal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J]. Research Policy, 2021(9): 104296.
[20]杨青峰,李晓华.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结构、制约因素及发展策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26-136.
[21]王姝楠,陳江生.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J].上海经济研究,2019(12):80-94.
[22]黄宗远.技术经济工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J].学术论坛,2015(8):56-62.
[23]黄凯南.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梳理: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J].南方经济,2014(10):100-106.
[24]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沈宏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5]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6]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12):1-13.
[27]朱恒源,王毅.智能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主导逻辑[J].经济纵横,2021(6):66-72.
[28]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64-83.
[29]AGOSTINI L, GALATI F, GASTALDI L.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0(1): 1-12.
[30]HININGS B, GEGENHUBER T, GREENWOOD R. Digit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2018(1): 52-61.
[31]STEIBER A, ALANGE S, GHOSH S,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firms: an innovation diffusion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2021, 24(3): 799-819.
[32]刘洋,董久钰,魏江.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管理世界,2020(7):198-217.
[33]孙烨.技术创新涌现性的特征表达及其认知演化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39-44.
[34]刘军,杨渊鋆,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6):81-96.
[35]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①2SLS法中K-P LM Statistic的P值为0.000;K-P Wald F Statistic P值为836.650,大于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表明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可视为有效的工具变量。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UANG Zong-yuan WANG Feng-yang YANG Tai-li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new form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digital presents many new features in key production factors, technological system,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value concep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ata factor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of natural technology,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inking technology, and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enabling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w framework, then analyzes the effect by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can strongly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data factors are the basis of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digital innovation of natural technology and thinking technology all have strong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while the digital innovation of social technology includes lag effect and positive effect, enhanc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In order to better grasp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data factors value, accelerate the digital innovation of natural technology,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inking technology, and further eliminate the lag effect of so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us promote the positiv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empowerment mechanism
作者簡介:黄宗远,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凤阳,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阳太林,广西师范大学高级实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