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灯塔去》的情节观解读
曹晓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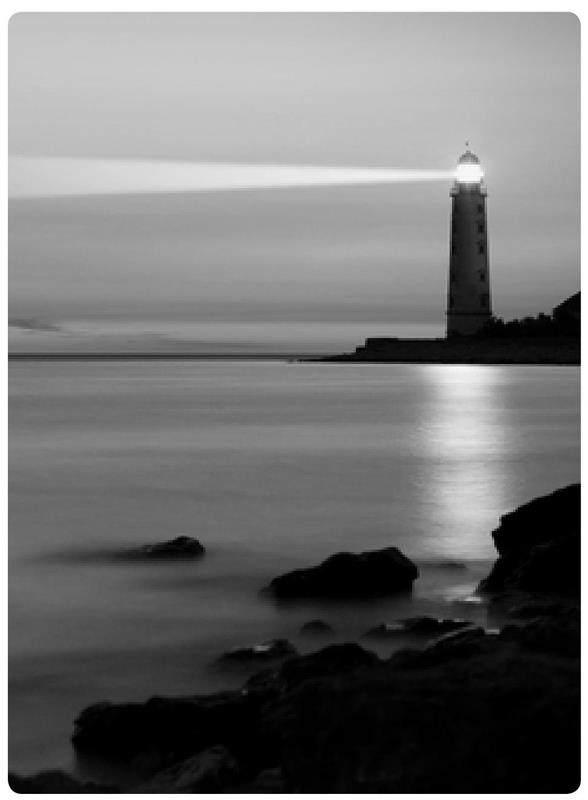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围绕其意识流叙事技巧的研究卷帙浩繁,主要包括对间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视角转换的分析,鲜少有对情节观的探讨。“意识流小说”是指小说家重视对人物思维、心理和感觉的复杂多变进行刻画,不采用传统的逻辑论证和叙述顺序的方法。如何界定“传统”呢?申丹在《西方叙事学》中指出:“小说情节探讨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著作《诗学》。《诗学》虽然以悲剧和史诗作为分析对象,但是,其中涉及悲剧情节的论述为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情节观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基础。”由此可见,对于传统情节观而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情节的探讨构成了“叙事情节研究的开山鼻祖”。因此,本文将以亚氏情节观为基础分析《到灯塔去》的情节观,旨在挖掘其对传统情节的突破。
首先,是对亚氏情节观中必然率的背离。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得出人意料,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或较好地)取得上述效果。”(《诗学》)由此可见,必然率强调的是情节的因果关系,因为“只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脉络设计符合因果关系,才能与人类的认知规律步履一致”(魏艳辉《〈项狄传〉情节模式与隐匿的道德伦理制》)。然而,《到灯塔去》的情节不是根据因果关系安排的,而是根据联想关系。下面是对拉姆齐先生一段思考的描述:
真是杰出的头脑。如果思想如同钢琴的键盘,分成众多的琴键,或者就像二十六个字母完全按照顺序排列的字母表……此时,在插着天竺葵的石瓮旁驻足片刻,他看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道坐在窗边……瓮中的天竺葵令人惊奇地明显可见,他能出其不意地看到它的叶子中间展现的两类人物之间古老、显著的差别……他纹丝不动地站在开满了天竺葵的石瓮旁边。他问自己:在十亿人中有多少人能到达Z?……再次看到蔓生红色天竺葵的石瓮,那些天竺葵经常装点他的思想历程,开出花朵,并将其详细记载在它们的叶子中间。
拉姆齐先生的思考由一盆色彩鲜艳的天竺葵蔓生开来,偶尔回归到这盆天竺葵,再继续展开。这里有趣的是,他的思维变化过程是由同一个景物天竺葵联结起来的,整段描述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到灯塔去》中充斥着类似的联想关系,习惯传统情节的读者或许会认为这种情节过于跳跃,但实际上这种描述才更符合现实中人类的思维习惯。
其次,是对亚氏情节观中统一率的背离。“统一率”是指“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它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诗学》)。塞缪尔·约翰逊在《漫游者》中把统一率称为“诗性结构的原则”,认为只有达到统一率的小说情节才具备“坚实感与美感”。伍尔夫表明自己有意破坏《到灯塔去》的统一率,她对统一率的思考也体现在小说中的莉丽对绘画统一率的思考:“她可以这样做,把树枝的线条横过来;或者用一个物体(也许是詹姆斯)来填补前景的空缺。但危险的是,如果这样做,整体的统一性可能被打破。”统一率要求小说中所有事件服务于一个中心事件,但在《到灯塔去》中显然没有中心事件,所有人物都有各自的关注点。拉姆齐先生关注事业,莉丽关注成长,拉姆齐夫人则关注家庭,这一点在她对婚姻的坚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必须,明塔必须,她们都必须结婚,因为无论全世界抛给她多少桂冠(可拉姆齐夫人对她的画不屑一顾),或者她获得多少成就(或许拉姆齐夫人已经分得了她的那一份)……有一点毫无争议:一个不结婚的女人(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片刻),一个不结婚的女人错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房子里似乎睡满了孩子,拉姆齐夫人倾听着;灯光昏暗,呼吸均匀。”“她在这,她在思考,怎样让明塔嫁给保罗·雷利……她说明塔必须结婚,必须生孩子。”除了婚姻以外,拉姆齐夫人的关注点也几乎都是家庭事务,如照顾孩子、照料房子、筹备聚会等。也就是说,《到灯塔去》以每个人物的所思所想为中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事件。
最后,是对亚氏情节观中以行为为中心原则的背离。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劇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由此可见,传统的情节观基本围绕人物行为展开。在《到灯塔去》中,行为并不是重点,关于这点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有评价:“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其他人所写的‘感性小说,刻意摒弃了旧小说效果所依据的大部分价值观。在《到灯塔去》中,几乎没有试图根据一个或多个人物的道德或智力特征让我们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支持或反对情绪。相反,‘感性的价值被置于事物的核心;那些像拉姆齐夫人一样具有高度发达的感性的人物是值得同情的;‘恶棍是那些像拉姆齐先生一样不感性的人。我们阅读的动力几乎是出于发现更多的感性事例,而不是为了发现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情……是对整体感觉的揭示,而不是对事件意义的揭示作为主题。”可见,《到灯塔去》更加重视人物的感觉描述。首先,人的感性是小说的主要主题。例如,莉丽艺术事业完成的关键即是她对感性的发觉。当莉丽创作拉姆齐夫人的肖像时,她产生了如下思考:“你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察,她陷入深思。要全方位观察那样一个女人,五十双眼睛都不够,她想。其中定有一双完全看不到她的美。你最需要的是某种完美如空气的秘密感官,它飘过锁眼,在她坐着编织、聊天或静静地独坐于窗前时笼罩着她。”起初,莉丽十分不屑于感性的表达,这体现在她对婚姻的抗拒中。然而,艺术创作需要某种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感性的缺乏让莉丽的创作历经挫折。在对拉姆齐夫人的追忆中,莉丽终于感受到感性的力量,她猛然意识到对拉姆齐夫人的美的呈现需要“某种完美如空气的秘密感官”,继而终于完成了创作。此外,具体而言,这本小说对感性的重视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拉姆齐夫妇的对比之中可以发现情节对感性的偏向。相对于拉姆齐夫人温厚、感性的形象,拉姆齐先生却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拉姆齐先生初登场时,伍尔夫以“瘦如刀,窄如刃”来描绘他的形象特征。以下是对拉姆齐先生与妻儿相处的三段描述:
始终放松地将儿子抱在怀中坐着的拉姆齐夫人振作精神,转过半边身子,似乎努力要让自己更挺拔……同时她看起来神采奕奕、生机勃勃,就好像她的所有精力都化为力量,燃烧,发光(尽管她安静地坐着,再次拿起她的袜子),那个了无生机的男人则冲进这场甘美丰饶的盛宴、这座生命力的瀑泉水雾,就像一柄空空荡荡的黄铜壶嘴。
身体僵直地站在她的双膝之间,詹姆斯感觉到她所有的力量都突然燃烧起来,正让那柄黄铜壶嘴吮吸解渴,那把男性的渴血弯刀无情地砍来。
詹姆斯僵直地站在她的双膝之间,感觉到她化身为一棵枝繁叶茂、开出玫瑰色花朵的果树,拔地而起,那柄黄铜壶嘴,他父亲的那把渴血弯刀,那个自大的男人,冲进中间,挥刀砍伐。
其中,拉姆齐夫人是“神采奕奕、生机勃勃”的,她好似一棵枝繁叶茂、开出玫瑰花朵的果树,她的感性能量能让周边的人感到温暖、振奋;而拉姆齐先生则是“了无生机”的,他好似“刀”“黄铜”等尖銳而锋利的金属,总是满不在乎地伤害他人的感情。当他的儿子詹姆斯为去往灯塔的旅途雀跃不已时,拉姆齐夫人考虑到儿子的心情,不愿打破他的期待,安慰他旅行是可能实现的;拉姆齐先生却毫不留情地告诉儿子因为天气原因旅行不可能实现,而且对妻子的态度十分不满。因为这件事,詹姆斯一直记恨着父亲。不仅是他,家中所有的孩子都不喜欢这样一位过于自我的父亲。
第二,从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括号中也能发觉情节对感性的重视。对括号的应用是《到灯塔去》一个明显的实验性叙事特征,如下面这段对晚宴之中拉姆齐夫人思维的描述:
但她确实没有嫉妒,只是时不时地,当她看到她的杯子时有点怨恨,她已经变老了。也许,也是她自己的错误。(温室的账单和所有其他的东西)她感谢他们对他的调笑(“你今天抽了多少烟,拉姆齐先生?”等),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年轻人;一个对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没有负担,没有被他劳动的伟大和世界的悲哀以及他的名声或失败所拖累,而是又像她第一次认识他时那样,憔悴但英勇;她还记得他扶她下船的场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就像现在这样(她看着他,他看起来惊人得年轻,正和明塔说笑着)。
在晚宴中,拉姆齐夫人看到丈夫与一位美丽年轻的姑娘谈笑,继而产生了一系列想法。在这段描述中,只有拉姆齐夫人对这个场景的想法才是重要的,其他任何描述皆被抛到次要地位,包括突然冒出的关于温室维修的想法、其他的对话描述以及场景描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括号也是为了把人物的想法和感觉推到第一位。
第三,对人的感觉的具体化描述在《到灯塔去》中随处可见。张中载指出:“文字符号在读者心中引发的联想和意象像绘画中的色、光、影、形一样,同样可以营造空间意识和空间美学效果。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就是善于营造小说空间美的小说家。她在小说创作中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用文字表现空间景物的光色,并使描写色彩、形状的页面文字在读者心中产生联觉和空间感。《到灯塔去》是一部小说,也是一幅生动的风景画。因此,不仅要读,还要去‘看,看文字符号而不是颜料所建构的空间美。”(《小说的空间美—“看”〈到灯塔去〉》)可见,文字对光、色、影、形等客观事物的描绘可以刺激感官、引起联想,展示立体图景。笔者认为,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加立体化地感知抽象的感性描述,伍尔夫主要运用了“色”与“形”两个方面的情节叙述技巧。前者指对色彩的强调,后者指对人物感官的形象化。例如,以下这段对明塔进入晚宴场景的描绘:
此外,她直接走进房间,就知道奇迹发生了;她带着她的金色烟雾。有时她有这种烟雾,有时又没有。她从来不确定它突然消失或者出现的原因,也不知道她是否拥有它,直到她走进房间,然后她从某个男性看她的眼神中立即知道。是的,今晚她拥有这个烟雾,肯定有。
这里,明塔的女性魅力被具体描述成“金色的烟雾”,以“金色”来形容其耀眼,“烟雾”形容其朦胧的状态。
总而言之,虽然读者无法在《到灯塔去》中发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却能为其中精妙细致、生动形象的感性描述赞叹不已、拍案叫绝。
综上所述,从亚氏情节观来看《到灯塔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部意识流小说的创新之处。此外,亚氏情节观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情节构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