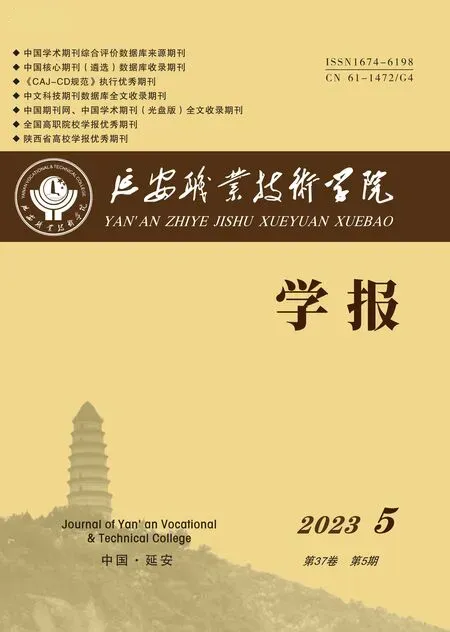论歌剧《白毛女》对革命集体记忆的建构
何秀勤,王宗峰,王 伟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歌剧《白毛女》改编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该民间传说本身并无政治色彩,但经过文艺工作者们多次改编,最终经由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贺敬之、丁毅两人之手,明确地将主题设定为新旧社会的对立,这样一来,就赋予其鲜明的政治色彩。《白毛女》的诞生,让许多与“喜儿”一样有着共同遭遇的贫苦农民认识到面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唯有奋起反抗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白毛女》不仅坚定了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决心,还给当时受压迫的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剧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小人物着手,突出了时代的阶级矛盾,其中以政治力量建构的革命集体记忆,是剧作魅力之表现,更是其核心要义之所在。歌剧《白毛女》烙印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革命印记,永远闪耀着革命光辉。
一、革命集体记忆主题建构明确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20 世纪40 年代我国革命文艺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总结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还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方向。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的结尾处对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1]877文艺的能量巨大能够引领整个社会思潮,这也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既要联系底层生活,又要努力做到政治与文艺的统一。《白毛女》正是沿着这一路径,从中找寻到了珍贵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源泉。在主题上,歌剧《白毛女》始终以革命为己任。贺敬之在谈到《白毛女》的创作主题时说:“没有把它作成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没有把它作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的积极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2]211这样的处理迎合了那个时代人民的革命诉求,也发挥着唤醒和加深现代人的革命集体记忆的作用。
歌剧《白毛女》创作于抗日战争末期,取材于河北省某县杨格村发生的故事。地主恶霸黄世仁将佃户杨白劳逼死后,又打起了其女儿喜儿的主意,设计将喜儿抢到身边,逼得喜儿走投无路只能逃进深山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青丝变白发的她被人撞见误以为是“白毛仙姑”,后经八路军解救,得以重获新生。黄世仁与杨白劳及其喜儿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全剧主干,在情节的设定上,杨白劳和喜儿所经受的苦难全都是由地主黄世仁施加的,这是革命发生学的必要条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3]625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爆发的农民起义就多达数百起,歌剧《白毛女》就是描述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典型范例。
歌剧《白毛女》不单单着眼于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剧作家还将其上升为阶级的对立,展现出革命斗争的宏大主题。在情节的设置上,喜儿和大春的爱情退居第二,革命第一是优先考虑人们的政治需求,爱情第二是兼顾人们的情感需求,“反映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争夺紧迫之时,力图保持老百姓的审美趣味而不悖乎政治需求所采取的折中方案。”[4]117-119虽然爱情这条线索退居第二,但正是在革命的羽翼下,喜儿和大春最终走到一起,其爱情也得以升华,从而带有革命化的色彩。爱情在服务革命不喧宾夺主的同时,既保证了革命的严肃性又展现出自身独有的魅力。歌剧《白毛女》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当时的革命景象,建构起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集体记忆,同样也建构起人们对于革命的强烈信心。
二、革命者形象建构鲜明
歌剧《白毛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强化了革命集体记忆。地主有权有势还坏事做尽,而地位低下的农民虽受尽折磨却不畏强暴勇于抗争。这样的脸谱化人物形象,虽些许失真,却更能加深人们的印象。如《林海雪原》中长着络腮胡子的许大马棒与健美儒雅的少剑波,读者仅凭其外在就能迅速划分两人的善恶阵营。“脸谱化的虚构与想象,总是能瞬间唤起读者的道德伦理评判,从而满足他们对恶贬斥,对善张扬,对阶级敌人鞭挞的内在诉求。”[5]17-19这样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刻画,迎合了人们心中坏人的形象,同时也符合那个时代政治宣传的需要,同时歌剧中对好人赞扬,对坏人憎恶的鲜明态度,也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善恶制裁的诉求。
主人公喜儿,作为一名女性农民革命者,她的革命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一系列的悲剧施加在她身上,才激起她的斗志。起初她天真淳朴、心地善良与革命理想大于天的革命者相差甚远。但随着爹爹离世,自身受到欺凌的一系列打击后,革命的火种就在她的心中悄悄点燃。地主阶级对喜儿的迫害越深,喜儿反抗的意识就越强烈,革命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她在逃入深山时唱道:“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6]63但是喜儿凭借着一己之力的抗争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革命胜利的关键是八路军的及时出现并枪毙了黄世仁。在八路军的解救之下,喜儿伴随着“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的歌曲声,正式加入革命阵营,至此,作为革命者的喜儿跃然于纸上。
而喜儿的爹爹杨白劳就没有这么幸运,正如名字的寓意一样,白白地为地主阶级劳动。他虽勤劳却也软弱,虽然看到黄世仁的可憎嘴脸,可一想到县长、财主以及衙役们的庞大势力,就退缩了。面对剥削与压迫,他选择了屈服——在女儿的卖身契上按下手印,最终走投无路的他含恨喝下卤水自杀。杨白劳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不反抗,不走革命的道路,终会遭到地主阶级的残害。同样,从他的抗争结局来看,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被完全地暴露出来,长期遭受压迫的他们,其认知层面也有着狭隘性。剧作家将旧中国农民的处境通过杨白劳这个人物形象合乎情理地展现出来,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暗示着农民阶级是难以独立地扛起革命的大旗。
黄世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旧中国农村统治的阶级支柱。首先在于他身份的独特性,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不劳而获还掌握着多数的土地,而那些辛勤劳作的佃户,不仅没有积蓄,反而欠债累累。他通过地租和高利贷的双重剥削使得杨白劳不堪重负,喝下卤水身亡。其次,他心狠手辣,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丝毫不关心穷苦百姓,甚至还想方设法从这些穷苦百姓身上获取更多利益。他还将剥削的魔爪伸向杨白劳的下一代,让杨白劳用自己的女儿抵债,仅用一石五斗粮和二十几元钱就将喜儿买入家中。视人命如草芥的黄世仁在将喜儿买入黄家后,对她进行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最后,他不仅与反动政府相勾结,还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上层势力相勾结,贪婪地侵吞广大佃户的土地。像他这样的剥削阶级注定是得不到人民的拥护的,也注定要被革命力量所消灭。因此,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进入杨格庄时,“黄世仁”们以绝对的劣势败下阵来。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剧作家正是通过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宣扬“农民阶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的观点。至此,人物形象的描写服务于革命集体记忆建构正式形成。
三、集体力量建构革命集体记忆
20世纪40年代,邵子南先生就着手收集“白毛仙姑”传说的相关资料,周扬先生为了献礼七大,决定在鲁艺组建创作班子,力掘《白毛女》背后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1945年4月,由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杨家岭的中央党校大礼堂进行公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多名中央首长前来观看演出,当饰演喜儿的女演员王昆唱出“太阳底下把冤申”时,连同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多名同志纷纷为之动容,眼里不禁流出泪水。歌剧《白毛女》首演后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就向剧组传达了意见:第一,《白毛女》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7]152这三点意见,无疑给了《白毛女》至上的荣誉,也肯定了歌剧所展现的革命主题,确立其政治生命。
获得中国共产党顶层领导的高度认可后,该剧便从延安演到张家口、哈尔滨、北京,乃至全中国。为了更好地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表明坚定的革命立场,同时还要符合观众的审美趣味,《白毛女》的情节不断被修改:人心所向,击毙了黄世仁;喜儿躲进深山老林也誓要活着,突出其反抗意识;大春、大锁被迫出走后加入八路军,将革命领导权递交到共产党的手中,赋予革命正义性等。主题明确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又以歌剧的形式展出,是这部歌剧成功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该歌剧的成功也归功于它选择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唱出了农民阶级对于新政党、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总体来看,《白毛女》的整个创作,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故事原型来说,它依据“白毛仙姑”的民间传奇故事,是经过无数百姓口耳相传,一代传承一代的“大”集体创作。在将民间传奇故事改编成剧本时,它又经过众多文艺工作者的批评补充,更有中央加以指导,这些指点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剧作者的再创作。最重要的一点,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学者、艺术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在观看《白毛女》演出后,通过信件、报纸等途径对该歌剧提出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据统计约合十五万字,足可见《白毛女》的受众之多,影响之深。也正是集体力量的汇聚,在不断地修改、演出和完善的过程中,《白毛女》最终呈现在舞台上带给观众完美的观剧体验,同时也将革命的火种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四、建构革命集体记忆的影响力
歌剧《白毛女》能够成功地塑造革命集体记忆其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该剧作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正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在那时,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艺术载体,《白毛女》的出现符合主流意识,其艺术功能升华为政治功能,对广大群众和干部起到了动员作用,大家同仇敌忾,空前团结,纷纷与地主阶级抗争。“《白毛女》在舆论上赋予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对黄世仁的仇恨转化为对扶持黄世仁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团的仇恨。”[8]91-100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两大支柱,《白毛女》将农民阶级对黄世仁的反抗转化为对地主阶级以及国民党的反抗。通过歌剧中人物形象的矛盾冲突侧面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冲突,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仅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也是成功的。《白毛女》巧妙地将无形的文艺作品转化为对抗地主阶级的强大力量,为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贡献力量,并为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革命力量。
文艺作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其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持久的。首先,作为一部进行阶级教育的歌剧,它提高了农民参与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为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创造了思想上的前提。由此,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篇章被不断续写。其次,它作为宣扬革命集体记忆的“活教材”,对于民族歌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指引作用。《白毛女》之后,解放战争中涌现出《刘胡兰》(新中国成立前本)等优秀新歌剧,新中国成立后,有《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民族新歌剧与《白毛女》所倡导的革命道路一脉相承,强有力地推动着革命的历史进程,历史价值巨大。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白毛女》剧组随军而行,演到哪里,哪里就掀起革命浪潮,前线战士们观看《白毛女》之后,革命前线处处洋溢着“打倒黄世仁,为喜儿报仇”的口号。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在观看《白毛女》之后,深受感动,纷纷脱离国民党反动派,主动投身于正义的阵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白毛女》依旧发挥其引领作用。
歌剧《白毛女》还在国际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部优秀的作品,《白毛女》不仅能够打动众多国内观众,还能够跨越国界和语言的障碍,演绎出一场别开生面的“芭蕾外交”。日本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观看了改编的《白毛女》舞台剧剧本,深被喜儿的悲惨遭遇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所感染。于是,她决心要将白毛女的故事搬上芭蕾舞的舞台。1955 年,她作为日本访华代表团的使者,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在聊天中周总理得知松山树子想要排演《白毛女》的芭蕾舞剧,周总理对她寄予的厚望,嘱托她:“一定要带着《白毛女》来中国”。1958 年,松山树子成功地兑现诺言将芭蕾舞剧《白毛女》带来中国,此后还多次来华演出,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2020年2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向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中国人民发来视频并致以深切问候,他们高声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用中文呐喊:“我爱中国!我们爱中国!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人类加油!”
结语
文艺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它们共同致力于建构民族和国家形象的伟大事业。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的引领下,《白毛女》成功地将革命集体记忆建构、保存和弘扬,可谓功不可没。歌剧《白毛女》既改编自民间传说,落实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内核,又听取多方人士的建议不断完善,可谓是集体力量的大融合。同时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牢牢把握政治脉搏,以革命集体主义的建构为使命,弘扬《讲话》精神,成功地将文艺融入生活。作为中华儿女精神宝库的革命集体记忆,承载革命集体记忆的歌剧《白毛女》也定会在时代变迁中历久弥新,魅力永存。
—— 以民族歌剧《白毛女》选段《杨白劳》为例